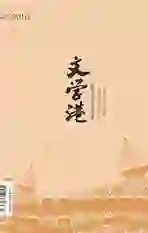父亲
2016-07-06
父亲三岁丧母,真不知道怎么成长起来的。祖父办实业,那是为官家办,所以一旦无官做,家境就连供儿子读书也困难了。父亲十一岁开始学徒,冬天空心穿一件旧棉袄,西北风直接往身上灌。父亲十八岁时,祖父也病逝了,想想父亲从小也真的够苦的。
父亲二十一岁时,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件幸事——娶了美丽聪慧的妻子。
夫妻和睦,辗转北京,山东,闯关东,虽历经战乱、失业,但父母带着六个儿女,总算熬到了1949年,过上了安定日子。
但没过几年,一场变故,父亲的苦难又开始了——一九五四年,我母亲受尽病痛折磨后去世了。
多年后,我自己也长大成人,才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场家庭变故对父亲是意味着要面对人生多么深重的苦难。
那时,父亲其实只有四十四岁。壮年丧妻,情感上的煎熬自不必说。多少次,我夜里醒来,发现父亲靠墙坐着,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的夜空,多少年后,父亲仍然会对我们说:“你妈没了,我失去了一个宝。”生活上面临的长期困难,更是常人难以想象。为给母亲治病和发送,欠下了近千元的债务,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近乎天文数字,如何偿还?六个儿女,最小的才七八岁,要吃要穿要上学,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的压力一齐像山一样压到了父亲身上。那些年,父亲体重一下减了三十多斤,不到五十,已是满脸皱纹,头发几乎全白。
债大部分是向工会借的。按规定,每月必须按比例还一部分。还有一些是向私人借的,周围人也都不富裕,总不能长期欠着,总得还一些,这样,每月开支那天,本应高兴,却总是发愁。因为把工资拿回家时,那钱已经差不多少了多一半。先凑合买棒子面咸菜让家人能吃上饭吧。如果连这也不够,那就只好月底再想辙了。每月还一笔旧债,月底再借一笔新债,生活的拮据,欠债的那种难以诉说的心里痛苦,沉重的包袱压在父亲身上,如沉重的石头压在父亲心头,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十年。
这十年,父亲的第一个举措是把原来租的四间房退掉了一半,全家人挤进两间小西屋里。里屋姑姑带着我和姐姐们挤在前沿炕上,靠墙有两个旧柜子,一个放全家的衣物,一个放锅碗瓢盆等杂物。外屋两张床是父亲和哥哥们睡,还有一点儿地方放了两口缸,一口装水,一口装粮食,旮旯里摞着两把一坐就直摇晃的木头椅子。这两间小屋除了走道儿就没什么地方了。这让我从小就懂得什么叫“一间屋子半间炕。”有一个方形炕桌,全家人吃饭,孩子们写作业,就是它了。里外屋共用一个十五瓦的灯泡,挂在门框上。有时为了看得清楚些,我常常把那把破椅子端到灯泡下,坐在小板凳上,好在椅子面还算平,那就是我的书桌,从小学二年级直用到快上完高中。
姑姑能把窝头蒸得很暄腾,把白菜汤熬得很有滋味,可往往还没等白菜汤熬好,刚揭锅的窝头就一人举一个吃光了,爸爸看着也就是说一句:“这群孩子,推一车石头子儿来都能给吃喽!”有一次可是真紧张了。月底最后一天该做晚饭了,既没粮票也没钱,再找别人借?能借的人几乎借遍了,爸爸实在左右为难了。全家刮净缸底,把几个粮食口袋翻过来抖落个干净,又找出来几片白菜帮子,洗罢洗罢剁碎了,好歹熬成了大半锅糊糊粥,撒了点儿盐,大家喝了,算是没有断顿。几十年后,我还没忘了那碗菜粥的味。要说那粥有棒子面,有碎米粒,带点儿咸味,其实不算太难喝,但当时的个中艰难辛酸,至今想起眼圈发红。
穿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小学四年级,全校开家长会,特意借了礼堂。我代表全校学生向家长们致辞,那内容恰恰是一首散文诗《娘呵,我的亲娘!》,听得台下的老太太们直掉眼泪。有的人小声说:“这孩子朗诵这么好,怎么穿得这么破呢?”知情人说:“这孩子没妈。”同院的几个孩子都在一个学校上学,这话自然传到了父亲耳朵里。父亲好几天没说话,也好些天没吃早点,后来,一件粉色的短袖布连衣裙摆在了我面前,恰逢六一,我穿着它和同学们在外边参加各种活动,乐得走路都连跑带跳,可现在想,那十年,父亲没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为了给我买这件衣服,父亲不知怎么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呢!
孩子多,有一个好处,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轮到老六我这里,哥哥的蓝制服已经洗得发白且打着补丁。一次,年节要去串亲戚,我高兴地跟着父亲出了院门,父亲回头一看,我的裤子膝盖上两大块补丁,父亲说:“回去换一条。”我跑回家翻腾半天,找了一条我觉得还算好的穿了出来,说:“您看这条行吧?”然后就快步走在了父亲的前边。想赶紧去串门儿。父亲看到了我裤子后屁股上的一大块补丁,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十五六岁的姑娘了……”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衣服怎么难看,但听到那一声叹息,我知道了父亲心里有多难过。
最难的是每逢学校开学前。四个孩子同时要交学杂费、书本费。愁得父亲直搓手。姐姐抹眼泪,不懂事的我也冲父亲嚷过:“这点儿钱哪儿够呀?”再急再气,父亲说的最重的一句话也就是:“你们这群孩子呵,简直要逼死我……”转过脸却又对天长叹一声:“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我只有这六个儿女呵!”然后默默地走了出去。我想,那或是向同事求助,或是站在工会主席面前,踌躇半天,说:“您,能不能再借给我点儿?”总之,父亲最终还是让我们按时交上了学费。现在想想,那时我的好多同学初中毕业就工作了,进工厂,当售货员售票员……,但在我家,就是家境再窘困,父亲宁可自己吃万般苦,也从来没有对哪个孩子说过:“不要上学了,去工作挣钱帮着养家吧!”只要考得上,几个孩子上了高中上大学,现在想想,这真不知该怎么感谢父亲的仁慈和远见。
生活再艰难,烦心事再多,父亲只是说:“一步一步往前过吧。”父亲也从不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孩子再不懂事,父亲也只是自叹自语:“忍无可忍之忍,耐无可耐之耐……”
苦难中,父亲也会寻求乐趣,宽慰自己那颗滴泪滴血的心:要是有一块白水煮豆腐,如果能再抹上那么一点点儿麻酱,父亲就知足得不得了;孩子考上好高中,高兴,孩子考上了大学,更是高兴。钱?再说!我外出劳动带回了一顶狗皮帽子,爸爸便戴上,到处说:“老闺女给的。”别人问:“什么皮?”爸爸哈哈一笑答道:“蹲门貂。”有空儿时,父亲会带我到护城河边,看杨柳轻拂,河水缓缓流过。父亲有时会从土里挖出一块瓷片,在夕阳的金光里,仔细端详,然后跟我说一套宋元明清,官窑民窑之类的。父亲能拉一手好京胡。每次厂子组织联欢演京戏,父亲是少不了的琴师。夏天的夜晚,我常靠坐在父亲身旁,听父亲拉上几曲:《夜深沉》《二泉映月》,那悠扬沉深哀婉的琴声,就是父亲的心声。就是在最苦的日子里父亲也会拉上一曲《步步高》,曲调层层高吭激昂,那是父亲对自己的鼓励。
1964年,我家终于有了转机。一个周末的晚上,平时住校的我回到了家里,眼前一亮:多年斑驳脱落的顶棚和墙壁都已糊得雪白,屋里添了一张方木桌,原来两间屋共用的一盏十五瓦灯泡变成了两盏灯还加上了简单但好看的灯罩。我惊喜地看看周围,看看父亲,父亲看着我许久,说了一句话:“咱们家欠的债,全都还清了。”说完,父亲走到院子里,长长地舒了口气,久久地望着朗月繁星的天空,十年的艰辛,眼前的喜悦,百感交集,难以言表。
债务还清,上大学的儿女都毕了业,父亲本可以轻松一下了。两年后,祸及全国全民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十一岁学徒,干了一辈子陶瓷彩绘。技术上在全厂从来是一把手。虽然只上过四年私塾,但写得一笔好隶书,画得一手好花卉。为了提高质量,增加日用瓷品种,父亲还搞过几次技术革新,如用胶皮戳印花,如釉下贴花,为了丝网印刻铜板,父亲还中毒病了一场。而父亲亲笔手绘的作品,也摆在了陶瓷展览会上。因为这些成绩,父亲两次被评为轻工业系统先进工作者。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罗织成罪名:“业务尖子”,“车间主任就是工长,工长就是工头”……已放出风要把父亲揪出来批斗,父亲的车间主任职务被撤了,罚去推煤,给车间生炉子。年近六旬的父亲,要从很远的地方把煤装满车,再推到车间,再把煤装进一人高的大炉子。父亲几次晕倒在挖沟、推煤的路上……
文化大革命是轮着整人。后来,那些最初打算整父亲的造反派头头也挨整了。这其中的人有的曾是父亲的徒弟,父亲原本视他如子侄,视她如亲女,准备把技术全教给他(她),那些人被揪到台上时,下边不少人都为父亲抱不平,说:“您还不上去批这没良心的!”父亲却一言不发,脸色发白,眼含泪花离开了会场。父亲是“心痛、心疼”,唉,父亲,这位宽厚的老人啊!
死别。父亲其实早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左心室肥大、胃肠病。只是那时条件不好,也没什么太有效措施。大约七四年,父亲鼻部大出血,其实这已经是一个警号了,接下来连续几年,消化道大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七八年惊蛰那天,在单位接到电话说父亲病重,我放下电话直奔医院,大夫正给父亲做腰穿检查,只见鲜红的血液一下升到U型管顶端,我顿时泪如泉涌。因为一年前做这个检查时,U型管中液体是透明的,只是在显微镜下看到有红细胞,现在的情况颅内出血肯定是很严重了。父亲深度昏迷。接着是腹胀如鼓、呕血、高烧和肺炎等一系列并发症都出现了。父亲熬了四天。第四天傍晚,父亲开始抽搐般地用尽全身力气大口吸气,喘气,那是在死神面前的挣扎,是对生命的最后的护卫和眷恋,是求生的渴望和本能。看得人真正心如刀绞。父亲吐出最后一口气时是很痛苦的,但不久,面部表情便趋于平静,且极安详,善相。我想是父亲的灵魂被接到了天堂——享年六十八岁。
思念与歉疚: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父亲自然对我疼爱有加。对父亲的记忆,始于我四岁左右。我得了急性肠胃炎,输完液从儿童医院出来,父亲抱着我在马路边踱步,嘴里哼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我无力地躺在父亲怀里,觉得那么厚实,那么温暖,后来我才懂了,那是人生最安全的港湾。我长大结婚了,临产,是父亲大冷天大半夜截了一辆平板车送我到医院。月子里闹乳腺炎,是父亲用小竹车推着我一趟趟去医院换药。父亲生病了,还想着呵护我的孩子……这其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我结婚前,竟没什么积蓄。父亲带着我上王府井,买了真丝软缎被面褥面,一件织锦缎棉袄,一条毛华达尼裤子,后来我才知道:为这笔钱,父亲卖了自己的一件皮衣和一块怀表(那是条件稍好些时父亲为自己添置的唯一的物品)。嫂子在洗衣时偶然发现了衣袋里的票据,才知道了这件事。我哭着问父亲:“您怎么不说呀?怎么能让您为我卖东西呢!”父亲只是淡淡地说:“那大衣我嫌它沉,那怀表,不上班了,也不怎么用得着。”唉,我的老爹呀!
如果说,对母亲和姑姑是思念,对父亲,思念之余,我更多的是歉疚。比如父亲出于好意爱护我的孩子,我却因自己心烦顶撞父亲。父亲偶尔也叹自己老了、有病,我虽心疼,但竟不知怎么安慰父亲。工作后,就因为父亲从来不向我们要钱,我也就从来没给过家里钱,倒是父亲有时补贴我。一次我回家看父亲,父亲执意一定要送我到北线阁口,我当时第一次心里有点儿感悟,掏出了身上几乎所有的钱(大概拢共也没几块钱)给了父亲,说:“路口有个小吃店,您去吃点什么吧。”想想就做过那么一点孝事。
孝事不多,最愧疚的事却有:上初中时一次上学的路上,我和班里几个穿着漂亮的女同学走在一起,迎面遇到了父亲。父亲穿的是一件衣面破旧且有油渍的老羊皮袄。我没有叫父亲,父亲看了我一眼,只那一瞥,让我痛心愧疚了一辈子。事后父亲也一直没说过我什么。但我却明白自己内心深处的虚荣,那又当爹又当妈千辛万苦把我拉扯大的父亲,我的亲爹,我为什么不能高喊一声“爸爸”,为什么不能在阔同学面前荣耀地介绍:“这就是我的爸爸!”这心态,我事后一直没跟父亲说过,但我内心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样伤了老父的心。有时我真希望有灵魂,那时我将寻遍各处,在他老人家的灵魂前忏悔。
父亲去世已经三十来年了。我对父亲的思念,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淡薄,反而时间越久,思念越深沉。子女对父母所做的,永远也不及父母对子女的十分之一。现在年纪越大,越懂得了父母恩,想让父亲吃上好的,看上电视,听听京剧,可是,子欲孝,亲不待了,痛哉!
父亲去世前,曾留给我几支他老用过的画笔。那是一个周日,我回家看父亲,父亲当时身体也还好,给我这几支笔时,也没多说什么,似乎很随意。没心没肺的我当时也没多想。不料这几支笔却成了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物。小时和父亲一起走路,总抱着父亲的胳膊,觉得像靠着一棵大树。坐在院中树下听父亲那悠扬的琴声,那样的时日是永远过去了。我想念父亲时,便拿出这几支画笔,便似乎感到了父亲的手的温暖。父亲几乎没留下什么财产,但父亲的坚忍、仁慈、宽厚、乐观,这无价的精神财富,却让我受用终身。像父亲这样做人处事,是我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思念无边,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