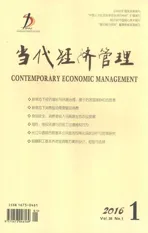理性、维权环境与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
2016-03-22潘光辉赵小仕
潘光辉,赵小仕
(广东金融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广东广州510521)
理性、维权环境与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
潘光辉,赵小仕
(广东金融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广东广州510521)
摘要眼演不少研究将农民工的过激维权行为归因于其素质低下而出现的非理性行为。经济学分析表明,农民工维权行为是在当前维权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基于个人行为决策的角度,在高维权成本的环境下,稳健维权的预期回报率低,而过激维权尽管具有高风险的特征,但由于容易引起政府及媒体的介入,结果提高了维权的成功率和回报率。基于社会稳定的角度,过激维权却容易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干预措施以减少过激维权行为。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成立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基金,政府部门承担维权的最终责任,提高侵权者的侵权代价,降低稳健维权的成本,增加农民工组织维权的途径。
关键词眼演农民工;过激维权;经济学;理性;期望效用
网络出版网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105.1414.020.html网络出版时间:2016-1-5 14:14:24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过激维权
过激维权是指特定的行为主体,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是走正规的渠道和程序,而是通过采取某种过激行为威胁侵权方,或者以过激行为向有关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从而使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维权行为方式。现实中常见的过激维权方式有绑架、杀人、堵门、堵路、跳楼、跳塔、爬塔吊等。
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研究农民工维权现象的文献数量在2012年达到高峰(如图1),但是专门研究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的文献数量非常稀少,近年来每年仅有少数几篇。

图1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维权研究的文献分析(篇)
在不同的研究中,过激维权有不同的称谓。王亮把农民工维权分为三种方式[1]:第一种是合法的途径,即农民工到政府相关部门,以上访、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和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方式展开维权行为。第二种是非法的途径,即农民工采用闹事、打架、武力威胁、绑架甚至杀害侵权人的方式来进行抗争,以达到维权的目的。第三种是“中间途径”,即通过采取牺牲尊严苦苦相求、跳楼、跳桥等自我伤害方式来维权。过激维权属于上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董玥玥把维权方式分为制度维权与非制度化利益抗争两种[2],这里的非制度化利益抗争与本文所指的过激维权是一致的。李煜玘的调查表明,多数农民工会选择正当的体制内维权方式,而当体制内维权困难重重时,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倾向于参与集体罢工、上访等体制外途径维权[3]。还有的学者把维权方式分为制度化正式渠道和非制度化的非正式渠道两种方式[4]。本文所指的过激维权与非制度化利益抗争、体制外维权、非制度化的非正式渠道等称谓不作严格的区分,与过激维权相反的方式是稳健维权。
中国历史上不乏“过激维权”的故事,古代有蒙冤者拦轿喊冤,当今有受害者过激上访,典型事件古有《水浒传》里的武松杀嫂,今有2004年宝马彩票案中刘亮以死相争等,这些事件维权者有的是以自己的武力剥夺了他人性命,有的以剥夺自己性命相威胁,都是过激维权的不同版本[5]。
(二)关于过激维权者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
围绕农民工过激维权的背后行为逻辑是否符合理性,学者们展开了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过激维权是一个非理性行为,特别是从素质论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更是如此。对于过激维权现象,不少研究认为原因在于农民工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进一步地,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维权“具有集体性、非理性、主动性、利益性和制度性等特征,且近几年呈扩大性、破坏性和严重性的趋势”[2]。上述观点更多的倾向于认为农民工的行为具有非理性特征。但是,现实的世界中的过激维权行为并不罕见,这是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挑战呢?
一些学者则认为,农民工过激行为具有理性的特征。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具有传统小农与现代市场理性的双重特征,其维权逻辑包括损失最小化原则、总体性算计原则与功利性原则[6]。不能谴责农民工不走正规渠道维权,而选择地缘组织、黑帮组织维权,扭曲的市场所扭曲的不是人们的理性而是人们的行为,问题是制度的“不理性”而非农民工行为的“不理性”[6]。过激维权行为频频发生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法院没能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不能通过制度上的“第三方实施”来保证契约的履行[7]。在保证契约强制实施的第三方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工对求助于司法体系讨回公道失去了信心,被迫更多地使用了私人性质的手段[8]。上述角度说明了农民工在处理工资纠纷中的过激行为并非首选,而是在理性维权无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一些学者则认为农民工的维权行为界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具有徘徊在自力救济与他力救济之间、理性与冲动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推动之间等多元化特征[1]。由于农民工与农民具有相似特征,对农民抗争行为的解释也侧面说明了农民维权行为的逻辑。斯科特从“生存伦理”解释了东亚农民的抗争行为,黄振辉和王金红则认为“生存伦理”解释力不够,提出了“底线正义”被践踏是农民工抗争行为尖锐化的根本原因[9]。上述研究说明了过激维权行为触发的原因,或者说,过激维权行为是在维权环境作用下产生的。
虽然农民工行为观念与现代市民有差异,但这并足以推论出他们的维权行为是非理性的必然结论。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假设,引入期望效用函数对过激维权行为进行解释,分析农民工选择不同维权行为的决策逻辑。
二、农民工维权行为决策模型
(一)农民工的维权策略
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企业侵犯时,他有三种策略选择:一是忍气吞声,二是稳健维权,三是过激维权。
假设合法交易,农民工获得正常收益为Y。当侵权发生时,以Q代表侵权的数量,如果农民工忍气吞声,农民工的收益为Y-Q;如果农民工采取稳健维权行为,农民工稳健维权成本为C,稳健维权收益为Y- k1Q;如果农民工采取过激维权行为,农民工过激维权成本为mC,过激维权收益为Y-k2Q。
其中k和m说明如下:
系数k表示农民工采取维权行为失败的概率,取值是:0≤k≤1。即,当k=1时表示农民工仍遭受到与采取维权行为前一样的侵权,即维权完全不成功,当k=0时表示受到侵害的程度为0,维权成功,其全部应得收益归还。根据前述条件,在政府界入的情况下,k2<k1。
系数m表示过激维权与稳健维权相比的激烈程度,m≥1,m的取值越大,表示维权行为激烈程度的加大,成本越高。
(二)政府的干预策略
政府面对农民工维权行为有两种选择:消极干预和积极干预。下面说明政府不同行为的收益与支付。
由于侵权Q造成社会不稳定增加,政府收益为aQ,其中a<0,a的取值与农民工的维权激烈程度m存在相关关系,如果定义相关系数为r1,可以用a=r1m来表示,可知r1的取值为负。
当政府采取消极干预时,其支付为X,采取积极干预时,支付为nX,其中n≥1,n的取值与农民工的维权激烈程度m存在相关关系,如果定义相关系数为r2,可以用n=r2m来表示,可知r2的取值为正数。由于政府采取干预行为的成本与农民工维权激烈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对于政府而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农民工忍气吞声(见表1)。

表1 农民工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分析
对于发生侵权后农民工维权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可以用博弈树表示为(见图2):

图2 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博弈树
三、维权环境对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的影响
(一)高维权成本下的两种维权行为预期收益比较
将忍气吞声与稳健维权两种行为的收益进行比较可得:

式(1)的大小取决于中k,Q,C三个因素,分析如下:
第一,由于0≤k1≤1,在Q和C不变的情况下,随着k1的增加,稳健维权的净收益也随之下降。在现实中,由于农民工与侵权当事人及其主管部门直接谈判的交易成本高,维权成功概率低。这表现在:一是侵权的雇主推托甚至拒绝谈判。二是主管部门没有履行应尽职责。大部分维权者在选择过激维权之前,通过都有与侵权企业多次交涉未果的行为以及找劳动部门投诉未果的经历,有的还曾拨打110报警,但各种稳健维权的努力均未有结果,维权失败率较高。
第二,在Q和k1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维权成本C的增加,采取稳健维权的净收益也随之下降。
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稳健维权成本高的情况表现在:一是举证困难。由于用人单位掌握着劳动者工作表现、业绩提成、出勤情况等大量的证据,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往往在相关案件中难以获得此类关键证据,又很难证明用人单位确实掌握这些证据,也难以要求他们提供。另一方面,部分劳动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有证据时未注重及时保留。这些直接证据的缺失导致劳动者维权难以为继。二是诉讼成本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也是需要成本的。按照时下的业内标准,根据律师的知名程度及案件的复杂程度,标的在1万元左右的案子,律师费一般在1 000~3 000元之间;标的在10万元左右的案子,律师费一般在4 000~ 10 000元不等。如果加上案件受理费、申请财产保全费、申请支付令等其他费用,诉讼人所需费用更高。据《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的结论,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 000亿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 000亿的成本。[10]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8个省(市)的调查表明,每个维权案件综合成本都超过1万元[11]。
第三,在k1和C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受到侵犯的权益的增加,维权的净收益也随之上升。这与一般市场上消费者权益受损时的表现一样,如果商品价值小,人们一般也较少采取维权行为。
第四,式(1)结果有可能为正,有可能为负,其大小取决于(1-k1)Q与维权成本C的比较。农民工维权执行难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维权的农民工即便通过诉讼赢得了官司,最终能否真正得到权益补偿也不好说。“赢了官司,赔了费用”已不鲜见,加之相对高昂的费用,诉讼并非农民工维权的最佳途径。稳健维权不但成本高昂,面临的风险还体现在付出巨大成本后权利仍然得不到维护,结果难以执行,甚至是收益不能弥补付出的成本。这些现象说明了维权的收益并不总为正。
(二)政府干预对农民工选择维权方式的影响
农民选择两种行为的净收益比较如下:

上式的大小取决于中k,Q,m,C四个因素,分析如下:
第一,由于k1,k2的取值区间均为[0,1],m≥1,上式结果可为正数,也可能为负数,说明在稳健行为与过激行为的选择上,过激行为并不是一个优势策略。在实际维权案例中,更多的情况是:当侵权事件发生后,由于责任难以认定,又没有统一的补偿标准,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快速仲裁机制,农民工面对实力强大的企业,自然处于弱势,通过与企业协商甚至是法律诉讼来维权以及争取经济补偿的愿望屡屡破灭后,往往没有信心再去争取,容易转而寻求“过激维权”手段。
第二,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k1-k2的值越大,过激维权的净收益越高。进一步地,随着维权激烈程度m的增加,维权的成本在增加,但同时随着激烈程度的加大,政府干预的可能性也越大,k1-k2的值越大。其结果是,被侵权的权益收回的数值也随之增加。过激维权常常迫使企业最后迫于舆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而对其进行赔付,从而扭转了谈判维权过程中的劣势,维权成功的概率在增加①。
第三,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受到侵犯的权益的增加,采取过激维权的净收益也随之上升。这一点前面已论述,不再赘述。
第四,由于m≥1,在Q和k1,k2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维权成本C的增加,采取稳健维权的净收益也随之下降。与稳健维权的成本相比,过激维权随着维权激烈程度也在上升。有些农民工选择的过激方式维权往往具有高风险和高成本的特征。过激维权例如选择跳楼、跳塔等方式,事主可能本意并不想轻生,但因处境往往较为险峻,在长时间僵持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失足坠落,造成意想不到的伤亡。另外,过激事件很容易激化纠纷双方的矛盾,甚至维权行为可能扰乱了社会秩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维权者会受到公安机关的罚款、拘留等处罚,这也是维权者要承担的成本。
农民工维权博弈分析表明,对于侵权行为,政府干预维权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且随着维权行为的强烈程度加大,干预成本也随之上升,因而,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看,政府最希望看到的是忍气吞声,但这不是农民工的最优策略。理性分析表明,当农民工面临多种不确定性的维权结果时,他可以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判断自己的维权方式选择是否合理可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过激维权并不一定是最优策略。因而,政府部门的作用应着眼于如何改变相应的影响因素,以减少过激维权行为发生数量。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从源头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减少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发生只有雇主是受益者,其成本由政府和劳动者承担。当然,雇主侵权可能会短期表现在企业利润中,对政府形成税收贡献。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劳动者选择“用脚投票”的空间在增加,并且通过各种丰富的媒介传播某一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声誉,最终企业将形成招工难的困境。从中长期来看,企业和政府都是受害者。因此,更有必要通过法律保障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改变现有的制度设计,加大在侵权的机会成本,维权者为维权行为付出的代价越大,侵权者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这样,巨大的侵权代价会迫使侵权者放弃“过分”的侵害行为,随着侵权行为的减少“过激维权”行为也就会随之减少。在德国,欠薪事件待事实查清后,恶意损害工人权益的企业不但会受到严惩,还将被列入黑名单,其相关负责人也会被禁止从事同类行业的经营。
(二)政府部门要建立事前的防范和事后的保障机制
维权需要成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前述分析也表明,农民工不管采取何种维权方式,维权成功的概率并不总是等于1。事实上,一旦受到侵权而遭遇雇主逃避等事件,农民工无法得到补偿,可能会导致生存风险,因而政府应承担维权的最终责任。以欠薪为例,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形成对企业欠薪等侵权行为的前置监控[12]。在德国,企业员工,包括建筑工人,不管何种原因讨不到应得的薪水,都可凭相关证据,直接到政府劳动部门等额免费领取。通过建立合法权益保障基金,可以用于支付权益补偿、行政仲裁、司法诉讼、临时救济等用途,防止由于遭遇侵权而导致生活困难甚至生命危机等极端风险而导致农民工直接走上过激维权的道路。这说明,事前的防范和事后的保障机制不但能保障受侵权者的基本生活,而且还能有效减少过激维权行为。
(三)降低农民工稳健维权的成本
现有的稳健维权的方式非常明确: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而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于大部分农民工而言,合理维权成本太高,维权时不通过正常程序维权有时也是无奈之举,因而需要改革现有的相关维权制度设计,降低收费,简化程序,降低维权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这才是根本之策。
在政府和媒体共同努力下,农民工维权意识显著提升,但如果农民工缺乏合理维权相关知识和途径的了解,会误认为稳健维权成本特别高昂,形成错误决策,导致维权过程中出现过激、过当等行为。当遭遇侵权行为时,农民工法律认知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依法维权[13]。维权宣传中,政府不仅要重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内容的宣传,也要重视宣传稳健维权途径与成本方面的知识。通过舆论加强针对性较高的维权方式与途径的宣传,减少关于维权的信息不对称,引导农民工走合法合理的维权之路。
(四)增加农民工组织维权的途径
在现行体制环境下,缺乏组织的农民工个人维权成本高,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缺乏博弈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在与雇主等强势集团的博弈中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例如,较高比例的农民工在讨要欠薪的维权过程中受过包括恐吓和羞辱等不公正待遇[14]。为此,要努力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具体包括:一是输入地工会组织应积极吸纳农民工,二是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12]。通过组织维权,能够适度分担成本,增加谈判力,降低个人维权的风险。
(五)对过激维权进行合理限制
理论分析隐含的是,随着维权强烈程度的加大,政府干预的可能性也越大,农民工收回被侵占权益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对过激维权形成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因而,制约过激维权应有一种合理的制度设计。过激维权的农民工在谈判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有必要对法律关系中的弱势方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法律援助,以增加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稳健维权的激励。当然,发挥激励作用的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约束制度。政府部门可对“过激维权”进行适当限制,例如对过激行为实施者造成恶劣影响时,也要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包括加大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以减少维权者自身的过激冲动[5]。当然,这是建立在降低稳健维权成本的基础上的。
[注释]
①除了收回受侵犯的权益外,甚至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补偿。
[参考文献]
[1]王亮.当前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方式、特征与原因分析[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5):33-37.
[2]董玥玥.非制度化利益抗争:农民工维权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6):76-79.
[3]李煜玘.农民工维权途径选择调查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0(10):61-62.
[4]周斌.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路径分析[J].学术交流,2009(1):136-139.
[5]戴福.“过激维权”的背后:从武松和刘亮说起[J].民主与科学,2005(4):45-46.
[6]苗瑞凤.传统与现代——论农民工维权的综合性特征[J].调研世界,2009(4):12-14,21.
[7]莫林浩.过激维权为啥屡屡发生[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 (11):60.
[8]杨瑞龙,卢周来.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对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契约论解释[J].经济研究,2004(5):4-12,75.
[9]黄振辉,王金红.捍卫底线正义:农民工维权抗争行动的道义政治学解释[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2-27,158.
[10]张燕,石毅.《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出炉讨薪成本知多少:至少三倍于收益[J].中国就业,2005(7):39-40.
[11]安广实,杨山鹰.当前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及对策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7(6):27-31.
[12]孙友然,杨文健.构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49-51,55.
[13]郑卫东.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J].社会,2014(1):120-147.
[14]王美艳.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研究——利用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6(6):23-30,80.
(责任编辑:张丹郁)
Rationality,Rights-defen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Radical Rights-defending Behaviors of the Migrant Workers
Pan Guanghui,Zhao Xiaosh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Many studies claim that the radical rights-defending behavior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migrant workers comparative lower diathesis. How鄄ever,through economics analysis,these behavior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rational op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urrent rights -defending environment. From personal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perspective,in an environment of high rights-defending cost,the expected return rate of robust rights-defending activities would be comparative low. While radical rights-defending behaviors possess the feature of higher-risk,it is easy to lead to interven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As a result,the rate of success and return is high. On the other hand,from the social stability perspective,it is with high possibilities that radical rights -defending behaviors result in negative social influences Therefore,some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radical rights -defending behaviors. The government could take some measures,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migrant workers' legal rights protection fund,taking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ies of migrant workers' rights defending,increasing the cost of infringements,decreasing the cost of robust rights-defending behaviors and providing more the routes of migrant workers' rights defending.
Key words:migrant workers;radical rights-defending;economics;rational;expected utility
作者简介:潘光辉(1973-),男,福建人,博士,广东金融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赵小仕(1975-),男,湖北人,博士,广东金融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劳动关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劳工过激维权行为的多元规避机制研究》(13YJC790215)。
收稿日期:2015-10-19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1.008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1-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