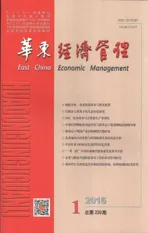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研究
2016-03-18郭旭红李玄煜
郭旭红,李玄煜
(1.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2.新疆喀什国际博览中心,新疆喀什844000)
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研究
郭旭红1,李玄煜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2.新疆喀什国际博览中心,新疆喀什844000)
摘要: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新常态下的攻坚阶段,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力度,尽快渡过“三期叠加”期,为GDP中高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文章立足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变革的视觉,研究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遇到的突出矛盾,深入剖析造成当前产业结构问题的原因,探讨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因素,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对策建议。关键词: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6.01.008
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12年经济增速下降至7.8%,自1980年以来首次跌破8%,预示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将由过去保持10%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下降为7%~8%的中高速增长,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过去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结构将由重化工业和低端产业为主向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转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价值链,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是“十三五”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保障“中高速”增长的客观要求。
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变革的趋势与特征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全球竞争进入新一轮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变革的历史时期。各国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动态变化,从而带来国际分工的动态调整,并重塑全球的产业发展和竞争格局。
(一)制造业再次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焦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认识到危机前过度“去工业化”存在严重缺陷,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如美国提出“制造业本土化”战略,拉动经济增长,抢占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抢占新工业革命的领导权;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以期未来能继续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英国将信息经济确立为产业发展总纲;法国提出要建设“新工业法国”,将工业作为发展的核心;日本政府出台《日本再兴》战略;欧盟实施“未来工厂伙伴行动”等。各国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回归或者是重复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而主要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强化制造业竞争力,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其核心是将信息技术、低碳技术、柔性制造技术等高端前沿技术应用于制造领域,占据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二)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为全球产业调整提供重要驱动力
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孕育,技术创新渐趋活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各国纷纷加大科技投入,支持科技创新。例如,美国为了垄断全球软件产业,推出“美国创新战略”、创新网络计划等,推动高校、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产学研结合,促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1]。德国政府出台“2020高科技战略”,推动在气候与能源、健康与营养、流动、安全性和通信等五大领域进行创新。新技术的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如麦肯锡研究表明,2020-2030年,全球节能投资将达到近2万亿美元。未来10~15年,全球纳米相关产品市场将超1.3万亿美元。费雷斯特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云计算市场到2020年将达到2 410亿美元[2]。
(三)智能制造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方向
在全球资源、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制造业逐步向“智能制造模式”变迁。智能制造是先进制造技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集中和深度融合,各国和企业积极发展智能制造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的产业发展重点都是智能制造。如德国“工业4.0”项目的核心内容就是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生产方法。美国政府为打造国家创新网络,建立区域性的制造创新中心,并相继成立了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数字化制造与设计创新研究所等。日本发布的第四期科技发展基本规划(2011-2015年)要求加强智能网络、高速数据传输、云计算等智能制造支撑技术的研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应对全球智能制造模式变迁的重要战略举措。
(四)制造业服务化成为重要趋势
制造业服务化延伸了制造业的价值链,促进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实现制造业的高端转型。目前,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服务业对制造业价值增值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统计资料显示,在发达的制造业市场上,产品生产价值占总价值的比重仅为30%左右,产品服务价值占比高达70%左右[3]。从经济绩效的角度来看,服务创新的价值有时甚至高过技术创新。许多国家纷纷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全球制造业正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制造和服务之间呈现明显融合和相互增强的态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
二、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突出矛盾
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矛盾表面上存在三次产业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实质上是关键核心技术缺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程度较差,由此带来产能过剩、产业结构的能源效益偏低等一系列问题。
(一)高耗能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的能源效益低
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高速增长,使得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总体较高,能耗效率较低。2011年、2012年、2013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有所降低,分别为0.76、0.51、0.48,但还是高于国际平均0.45的合理水平[4]。2012年,中国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仅仅5.14国际元,远远低于美国7.42、日本9.87、印度7.79、世界7.46国际元(图1)。据WDI Database数据计算可知,2013年,中国GDP占全球的13.36%,人均GNI接近美国的1/4(PPP法),但消耗了全球22.4%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6倍。中国产能利用效率极低可见一斑。2012年,中国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为361 732万吨标准煤,其中工业能耗252 463万吨,占70%;从工业内部结构看,六大类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占工业能耗的70%左右。这显示出高耗能的基础型重化工业比重偏高与能源效益偏低的矛盾,并与循环经济减量化原则相悖[4]。这与2003年以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业迅速扩张和基础型重化工业比重过高密切相关。

图1 2003-2012年中、美、日、印和世界GDP单位能源消耗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单位: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程度较差
中国产业结构矛盾与其说是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协调、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比重偏低,还不如说是以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为标志的名义高度化较快,而以附加价值、技术含量为主要特征的实际高度化水平较低。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表现为多居于价值链的低端,市场调研、研发、设计、咨询、营销、供应链管理、物流和品牌等关键环节薄弱,在产业结构上则体现为加工制造业的过快扩张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按照WDI Database提供的数据,2013年,服务业占比升至46.1%,尽管高于工业占比43.89%,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0.49%、中等收入国家54.55%,也远远低于美国78.05%和日本72.58%的水平,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人均GDP在830.16美元时服务业占GDP比重52.87%,以及同为中等收入的巴西在人均收入为5 888.29美元时服务业的占比67.11%。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服务业比重过低主要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如国际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等比重偏低所致。服务业价值链增值环节与制造业价值链增值环节尚未形成融合型产业价值链[5],各自的利润空间和增长潜力尚未形成动态优势互补效应,产业融合的结构升级效应较弱。这不仅阻碍高端制造业的生产率,也会影响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外包发展。
(三)部分新兴产业出现成长性产能过剩
目前,传统产业产能尚在加快去产能过程中,部分新兴产业的成长性产能过剩十分显著。从具体行业看,多晶硅、光伏电池、风电设备和煤化工行业是产能过剩现象比较严重的新兴行业,其中部分行业过剩程度较高,多晶硅行业、光伏行业和风电设备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是35%、57%和67%[3]。从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成长性过剩是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在市场需求拓展过程中,过剩情况会逐渐得到缓解。在低技术水平上重复发展是目前我国新兴产业的成长性过剩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是由部分重点行业中的核心技术缺失造成的,这一现象在光伏和多晶硅行业尤为突出。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能的严重过剩对“调结构”造成极大的障碍,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从微观层面来看,会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产业整体效率和效益下滑,甚至引起企业破产;从宏观层面来看,会加重生态环境压力,使“资源、环境红利”更趋减弱,容易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严重的产能过剩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严重的挑战。
(四)技术来源对外依赖程度高,关键技术缺乏
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竞争能力和产业结构水平是成功国家的基本经验。尽管中国企业设备更新很快,新产品也不断涌现,但总体来说,中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不足,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引进。由于有色金属资源核心提炼技术缺乏,2014年镍原料对外依存度高达82%,2013-2025年我国镍需求量将超过1 300万吨,但目前我国保有镍储量仅193万吨,不足消费量的15%,资源瓶颈短期难以解决[3]。中国企业大约只有3/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仅有40%的企业拥有自己的商标,1%的企业申请专利。多数企业处于无“创造”和无“知识”的状态。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高端医疗设备基本依赖进口,80%的石化装备和70%的数控机床、胶印设备依赖进口[6]。高端零部件、高端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导致重大装备和主机产品设备陷入“空壳化”困境,这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逆向创新模式密切相关。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制约我国技术创新的三大短板:一是缺乏具有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突破前沿技术的大型骨干企业;二是缺乏技术多样性、多元化技术路线的战略性创业企业;三是缺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共性技术供给机构。
三、形成当前产业结构问题的原因
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问题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产生的,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较大关系,而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则是其深层次原因。
(一)源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国充分抓住了国际生产环节转移的机遇,确立了全球最大的代工平台的贸易模式,加快了工业化进程,迈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然而,中国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反而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智能化发展要求日趋紧迫,而且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也成为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我国力推的“市场换技术”实践并没有成功换来高端技术,“世界加工厂”的“要素租金”并没有给我国带来丰厚利润。国际产业的碎片化植入与本土产业融合性不足,外生比较优势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贡献较低;同时,GVC分工网络固有的高利润性、封闭性,不利于实现制造企业向制造服务企业的高端转型。
(二)源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归结为“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即产业发展中过度依赖投资扩张、全球分工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和加工贸易、竞争战略过度依赖成本价格,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缺失。这种模式在过去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缺陷和矛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贸易条件恶化,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甚至是难以为继。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经济增长,但也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结构存在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结构失衡、三次产业失调、贸易条件恶化、收入增长缓慢以及能源、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等矛盾的重要原因。着眼于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摆脱上述“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
(三)源于新世纪以来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投资带动的原材料型的重化工化特征凸显。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作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34.1%上升到90年代的35.4%和新世纪的52.1%。相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979-1984年的69.4%下降到90年代的62.2%和2001-2013年的45.1%[4]。2011年,重工业在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61.6%,比1990年高出11个百分点。从工业内部结构看,1998年、1999年、2000年轻工业占比分别为42.93%、41.97%、39.8%,低于50%。从2001年起,中国工业统计口径方式改变,在同一口径内,六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中,2013年与2003年相比,除了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外,其余高耗能产业资产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工业总资产的增长率(表1)。中国希望在短时间内实现赶超目标,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能源、原材料、化工及机械装备等重化工业的发展[7]。但是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阶段决定了后发国家赶超的难度[8]。

表1 高耗能行业资产值亿元
四、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利因素
从国际上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制造业服务化正在引领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全球制造业分工正处于重塑演化阶段。从国内来看,国民经济步入高速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信息化和工业化正处于深度融合发展阶段,“互联网+”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找到了新的突破点。
(一)经济增长“新常态”提出新要求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较往年有所放缓,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较高增速,而在此过程中,更加强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而质量效率的实现就需要产业结构以“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为目标的深度调整,更好地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推动经济在中高速稳定增长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显著调整。换言之,新常态下,要求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更上新台阶,通过质量效率的提升支撑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引擎
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化的数控技术、新型轻合金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互联网+异军突起,物流快递、电子商务等新业态快速成长,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特点的科技革命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大产业变革初现端倪,这也为“十三五”时期加快产业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强国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空间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非常广阔,这将在中高速背景下为“转方式”、“调结构”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我国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就服务业内部结构来说,2014年,生产性服务业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增长最快的五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同比增长38.6%、36.2%、34.7%、25.7%、23.6%(表2)。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促进结构调整和中高速稳定发展,既可以扩大内需、创造就业岗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实现服务业与工业等在更高层次上有机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表2 2014年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速
(四)大国人口“二次红利”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虽然近年来,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廉价简单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但是我国可以抓住高素质劳动力人数众多、成本低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机遇,发展金融、咨询、创意等高端服务业。并立足中国工业大国国情,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延伸中国的产业价值链。1980-2010年,中国人力资源占全球的比重稳步上升,从17.6%增加至24.1%,是美国的2.58倍;到2020年高达26.8%,是美国的3.31倍[9]。科技人力资源是人口资源的中坚力量。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从2000年的92.2万人年增长到2014年的393.7万人年,后者是前者的4.27倍,由世界第四位跃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研究人员是美国的1.76倍[10]。
(五)“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机遇
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过去的对外开放是以利用外资和对外出口为主要模式,近年来,随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表明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对外投资高速增长的历史拐点,由单纯靠“产品出口”发展到“资本输出”增长更快的新阶段,极大拓展了资源配置的范围和手段。近期,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这是着眼于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与各国互利共赢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近6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人口达44亿,占全世界的43%;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29%;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世界的23.9%[3]。全面深化对外开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将为我国带来新的全球化红利,不仅为国内化解产能过剩和促进产业升级留出了发展空间,而且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创新要素和资源,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五、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对策建议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要基于全球价值链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关键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主题由强调增长导向的数量比例向强调发展导向的产业融合转变,重点由规模比例调整向提质增效转变[11]。
(一)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产业结构升级
在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条件下,产业结构演化升级通常是指高生产率产业价值链或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替代低附加值价值链或环节的过程,它是对传统的产业间结构转换的发展和演进。也就是说,它超越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单向演化路径。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就必然导致与全球经济体不同价值链环节的产业主体间“攀升与反攀升”的较量、同一价值链环节不同主体间“效率与生存”的竞争、不同价值链链条市场生存的竞争。在GVC分工时代,基于全球产品价值链分工的拓展,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可以拓展为三个路径[12]:一是总体上遵循传统的由劳动密集型——资本性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变的产业间的高级化路径;二是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价值链前端的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三是从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价值链后端的服务与管理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图2)。换言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不仅在于产业间的结构高度化演进,而且关键在于产业价值链的结构高度化演进以及产业价值链结构转换能力提升[13]。

图2 GVC分工模式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
(二)培育和发展本土的高级要素
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的GVC分工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发挥高级要素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以获取更大的市场控制力,谋求全球新兴产业的市场垄断。跨国公司正是利用关键技术垄断和终端渠道控制实现对我国的“结构封锁”[14]。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市场需求也就成为GVC分工的关键点。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培育中高速增长的市场空间,通过国内市场容量所包含的对于创新活动的引致功能,内生培育出本土高级要素,即内生需求所引致的基于创新的良性循环机制[15]。这样,我国就能够有效利用中高速增长创造的市场需求空间,培育和发展出本土的高级要素条件,这就具备了相对于发达国家高级要素竞争优势的同等竞争力,从而摆脱发达国家对GVC的“结构封锁”和“俘获型”GVC①,从而完成产业结构从低技术状态向高技术状态的转化。
(三)工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和关键
中国的工业应立足于大国经济、社会、国防的特异性,积极借鉴德国、日本的柔性制造、个性制造技术,充分发挥大国人口“二次红利”和资源禀赋优势,通过智能制造、互联网+与大规模生产的有效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智能制造能力,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信息化的高度融合,争取在未来全球智能制造中显示出中国智能制造的优势和核心能力。第一,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提升工业化的“广度”。首先,发挥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高档数控机床、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高端装备制造业,选择重点行业进行智能制造试点,加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数字化、绿色化与智能化建设。其次,通过高端制造业引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要围绕“做强工业”展开,重点推进研发设计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八个领域的高技术服务业,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更高层次上有机融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第二,制造业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工业化的“新度”[16]。重点依托大国国内网络市场优势,建立全球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货物配载中心,使物流与制造业联动发展,在保留产业集群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现制造业从标准化、长渠道向个性化和短渠道转变,打造信息化的制造业产业。
(四)围绕智能制造的发展要求,为关键装备和技术的研发创造条件
目前,全球制造业智能化的加速发展将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倒逼机制,推动我国制造业加快向智能化迈进。智能制造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是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新引擎。然而,从产业准备条件和基础看,智能制造在我国尚处在起步阶段,制造业的很多领域尚未实现全面的自动化,更缺乏支撑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关键装备和技术。因此,我国智能制造仍需夯实基础,重点是围绕智能制造的发展要求,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并为之创造条件。一是支持发展加工精度更高的加工装备;二是加快发展适合智能制造发展的新材料;三是加大高端传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执行器等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设备、技术研发力度,不仅要以税收、金融等政策支持从事相应领域企业的研发创新,同时国家也应相应制定专门的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地引导传感器、伺服电机等新产业的发展。
(五)加大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力度,倒逼企业加快技术更新
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近年来已被证明是倒逼企业加快生产技术和设备更新的有效措施。目前,传统产业正在去产能过剩的过程中,部分新兴产业已出现长性产能过剩,因此新常态下仍然要继续用化解产能的政策措施,迫使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更新技术设备。政府要选好着力点,关键是建立严格环境和技术等准入标准,健全常态化的化解产能过剩工作机制。首先,建立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制度。在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行业新(改、扩)建项目中,实施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将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推进高端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创新资源,促进国内过剩产能化解,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
注释:
①“俘获型”发展模式,即“A小+B小+C中+D大”模型。在该模式中,发展中国家既没有本土和国外高端市场的支持,在本土的低端市场容量也相当有限,完全依赖于国外的低端市场。在这种市场结构和规模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由市场需求引致的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和产业升级活动的空间受到极大的抑制,由此也决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GVC分工多为“俘获型”。
参考文献:
[1]Cusumano Michael. The Business of Software[M]. Cambridge:Free Pree,2004:15-16.
[2]王忠宏.把握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N].中国经济日报,2013-9-13(11).
[3]王鹏. 2014-2015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蓝皮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5]武力,李杨.新世纪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的思考与回顾[J].中共党史研究,2015(7):36-45.
[6]王传涛.“专利大国”为何成了“创新小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12-21(5).
[7]速水祐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6-59.
[8]Linsu Ki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The Dynamics of Ko⁃rea's Technological Learning[M]. Cambridge: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26-29.
[9]胡鞍钢,鄢一龙,魏星. 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1]黄群慧,贺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2025》[J].中国工业经济,2015 (6):5-17.
[12]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研究课题组.跨国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13]崔焕金.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结构演化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4]张杰,刘志彪.需求因素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J].财贸研究,2007(6):1-10.
[15]Zweimuller J,Brunner J K. Innovation and growth with rich and poor consumers[J]. Metroeconomcia,2005,56:233-262.
[16]黄群慧.新常态下工业增长动力机制的重塑[J].新重庆,2015(3):11-13.
[责任编辑:余志虎]
A Stud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under a New Normal in China
GUO Xu-hong1,LI Xuan-yu2
(1.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2.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of Kashi,Kashi 844000,China)
Abstract: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in a crucial stage under a new normal. China must increase the efforts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get through the period of“superimposition of three phases”as quickly as pos⁃sible,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edium and high speed growth of GDP. The paper,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studies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under a new nor⁃mal in China,mak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curr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blems,discusses the favorable factor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and puts forth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peed up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Keywords:a new normal;industrial structure;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作者简介:郭旭红(1983-),女,河南洛阳人,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宏观经济;李玄煜(1986-),男,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方向:政府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BJL015)
收稿日期:2015-11-03
中图分类号:F26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6)01-00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