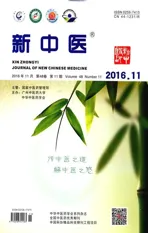陈伟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经验介绍
2016-02-22许宝才陈伟陈刚
许宝才,陈伟,陈刚
衢州市中医医院消化科,浙江 衢州 324002
陈伟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经验介绍
许宝才,陈伟,陈刚
衢州市中医医院消化科,浙江 衢州 324002
慢性萎缩性胃炎;经验介绍;陈伟
慢性萎缩性胃炎(CAG)是胃癌癌前病变的状态之一,治疗尚无明确有效的方法途径,故CAG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研究的一个热点。李东垣有“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善治病者,唯在调脾胃”之说,可见脾胃功能正常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转尤为重要,也间接说明脾胃的调治尤为不易。陈伟主任是衢州市名中医,从医二十余年,擅长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治疗CAG,疗效显著,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管窥其用药特色一二,特浅析如下。
1 标本兼顾,虚实同理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在饮食物及水谷精微的消化、吸收、传输等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CAG病程较长,常因饮食不节、情志不遂、劳逸过度或外感六淫邪毒等因素损伤脾胃而致病,病情多错综复杂,在辨证时首先要辨标本虚实。CAG的病机特点是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既有因实致虚,实中有虚,也存在由虚致实,虚中有实[1]。故临床表现既有虚象又有实邪,虚证主要是气虚或气阴两虚;实证主要是气滞、血瘀、痰浊、湿阻、热毒等。临证中以上各病理因素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兼为病,各有侧重。治疗时须标本兼顾,虚实同理,既要重点突出,又要兼顾全面,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虚不忘实,治实不忘虚。清·汪昂在《医方集解》中指出:“盖脾为中枢,使中枢运转,则清升浊降,上下宣通,而阴阳得位也。”CAG的治疗当顾护脾胃之气为先,脾胃之气得固,才能逐渐恢复其纳运、升降的功能,故治当首先补虚固本。陈老师常选用党参、太子参、白术、茯苓、山药、白扁豆、莲子、炙甘草等补脾益气而无伤阴之品。但一味补虚固本,而忽略实邪趁脾胃虚弱之际对机体的慢慢侵蚀损害,则脾胃更虚,故以攻补兼施为宜。脾贵在健运,脾胃虚弱患者长期用静的补药,则为呆补、壅补,只有通过健运脾胃逐渐恢复脾胃功能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补脾,故应注意动补、行补,陈老师为避免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常配以醒脾助运之品,如陈皮、木香、砂仁、谷芽、麦芽、神曲、山楂等,既能改善食欲,更能促进药物的吸收,使补脾而不碍运。此外,在治本的同时亦不能忽视治标,补虚之时不忘祛实邪,同时需注意攻邪而不伤正,防止过用苦寒、辛燥之品,脾胃运化功能恢复,则生化之机旺盛,气血才能生化无穷。兼夹气滞者,用香附、苏梗、八月札、香橼皮、佛手调畅气机,理气而不伤阴;兼夹痰浊者,加用陈皮、半夏、浙贝母、瓜蒌以化痰;寒湿偏重者予藿香、佩兰、苍术散寒化湿;湿热偏重者酌加黄连、黄芩、大黄清热祛湿;对久病湿浊不化者,常选石菖蒲、砂仁、白豆蔻醒脾化湿,蒲辅周曾言:“砂、蔻、木香用数钱,这类药物辛温香燥,少用化湿悦脾,舒气开胃,用之太过则耗胃液而伤气”[2],故临证之时用量宜轻。湿为阴邪,“风能胜湿”,既能行气发散,宣散湿浊,又可防湿邪凝聚,以解湿邪困脾,常选用防风、白芷、葛根、紫苏等祛风散湿。兼夹血瘀者,须防破血太过,喜用活血兼能养血之当归、丹参、赤芍、鸡血藤及活血生肌之品如莪术、三七、血竭等。兼夹热毒者,加用蒲公英、白花蛇舌草以清热解毒。
2 阴阳平调,寒温相适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中医认为脏为阴,腑为阳,就脾胃而言,脾为脏,属阴,胃为腑,属阳,脾与胃通过经脉与络属构成表里关系,成为一对阴阳。阴与阳,相反相成,叶天士云:“胃易燥,全赖脾阴以和之,脾易湿,必赖胃阳以运之,故一阴一阳,互相表里,合冲和之德而为后天生化之源也。”周慎斋言:“胃气为中土之阳,脾气为中土之阴,脾不得胃气之阳则多下陷,胃不得脾气之阴则无运转。”胃阳上济脾阳,脾阴下济胃阴,则脾气升而不陷,胃气降而不逆,从而阴阳互助,共同维系脾胃升降运化功能。CAG的发病患者多为中老年人,常久病不愈,反复发作,病久必虚,由胃及脾,脾胃同病,纳化无权,必致机体失养,气血亏虚,阴阳俱损[3]。在治疗过程中,因“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扶脾阳与养胃阴常同时进行,只是用药主次不同。李东垣的方剂,常将泻阴火药物寓于升阳益胃药物之中,最有代表的是升阳汤,方中以柴胡为君,以升下陷之阳气,辅以人参、黄芪、苍术、炙甘草补脾益胃,佐以石膏、黄连、黄芩泻阴火,又加升麻、羌活以助柴胡升阳之力。陈老师常说,健脾益胃之法,要特别注重升发脾阳与潜降胃阴相辅相成,阳气升发,元气充沛,有利于阴火潜降,而阴火的潜降也有利于阳气的升发。陈老师常在补脾益气之时,除了加用升麻、柴胡、葛根、荷叶以升发清阳之外,常适当加用黄连、蒲公英等苦寒药以降阴火,以防助阳太过而伤阴化燥。在养阴益胃之时,常少佐干姜、桂枝等顾护脾胃阳气的药物,以防滋阴太过而致寒凉伤胃。临床中陈老师常用百合与乌药以平调脾胃之阴阳,百合甘寒柔润,滋胃阴而润燥;乌药辛开温通,温脾阳而散寒,两药相伍,一动一静,寒温相适,阴阳共使,刚柔并济。
脾为阴脏,故脾病多寒,赖阳以煦之;胃为阳腑,故胃病多热,须阴以和之。然脾与胃同居中焦,病理上必然相互影响,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形体劳役则脾病……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故脾胃常同病。脾脏的病理特点是“阳气不足,阴气有余”,邪在太阴,易从阴化寒,脾土受抑,清阳不升,运化不及,水湿下趋,虚寒内生。“积阴之下,必有伏阳”,在脾阳虚生脏寒基础上,必有相火内郁化热之变。胃腑的病理特点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邪在阳明,易从阳化热,若湿、痰、瘀等病理产物滞于胃腑日久易化热,热邪煎熬津液,进一步伤及胃阴,从而虚热内生。同时胃阴损伤日久,又易感受寒邪,伤及脾阳,出现脾胃虚寒之象。故临床上单纯的寒证、热证并不多见,往往多表现为寒热错杂之证,因此用药不能截然分开,若用药过于寒凉,则抑遏脾阳,中气受损;用药过于温燥,又易灼伤胃阴,胃失濡润[4]。清代张志聪说:“寒热补泻兼用,在邪正虚实中求之。”这提示了寒热补泻之所以兼用,是以病证为主体的。CAG每多寒热错杂,故用药宜考虑到脾胃的不同生理特性,权衡寒热主次,以求寒温相适。用药配伍中陈老师常根据病情于寒剂中加一两味热药,热剂中加一两味寒药以求脾胃寒温相适,如在用黄芪、白术、茯苓、甘草等温药之时,酌加黄连、蒲公英等寒凉药,或在用黄连、黄芩、蒲公英等苦寒药时,酌加砂仁、白豆蔻、陈皮、半夏等温燥药。另外,陈老师临床中遇到寒热错杂之证每每常用半夏泻心汤或左金丸,根据患者的寒热情况辨证加减,调节寒药与热药的分量比例,如使用半夏泻心汤时,寒重热轻加重干姜用量,热重寒轻则加重黄连、黄芩用量。而在用左金丸之时,亦需根据患者的寒热阴阳情况调整大热之吴茱萸和苦寒之黄连的用量,如热证明显,可多用黄连,少佐吴茱萸;若寒象甚者,则多用吴茱萸,少用黄连;若寒热等同,则二者各半为宜。
3 升降相宜,润燥相济
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脾主运化和升清的功能正常,则水谷精微才能吸收与输布,气血生化有源;胃主受纳,降浊正常,六腑才能传化水谷,完成其生理功能。两者升降相因,出入有序,才能维持人体各种生理功能活动。“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胃的“升降相因”是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基础,正所谓“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脾之升清有赖于胃之降浊,胃之降浊有赖于脾之升清。若脾胃气机紊乱,脾不升则清气下陷,胃不降则浊气上逆,则变生诸证。二者只有升降相互为用,“脾升胃降”协调平衡,才能“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维持机体内部的相对平衡。因此在临证过程中,虽CAG证型多样,但在各型的治疗中均要顾及脾胃气机的升降,陈老师常用枳壳配桔梗二药以畅达脾胃气机使升降有序。另外,肝主升而肺主降,肝气升发,助脾升清,肺气肃降,助胃和降,二者相互协调,则脾升胃降,中焦斡旋,清升浊降。若肺气失肃,则胃不降浊;若肝气郁结,木郁乘土,则脾不升清。陈老师常将既可疏肝解郁又可升举脾之清气的柴胡与既可降肺气化痰又可降胃之浊气的旋覆花组成药对,以调肝肺气机,复中焦斡旋之职。
脾喜燥而恶湿,胃喜润而恶燥;脾病易从湿化,胃病易从燥化。燥可祛湿,润可濡燥,燥湿相济,阴阳相合,方能完成饮食物的传化过程。《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若脾胃之间燥湿不相既济,就会发生脾胃之疾。由于CAG发病多为脾胃同病,用药不能截然分开,若用药过于寒凉,则抑遏脾阳,中气受损;用药过于温燥,又易灼伤胃阴,导致胃失濡润,通降失司。因此,治疗时应兼顾用药,在使用燥湿之剂时,为防止伤阴耗液之弊,常佐以滋阴润燥之品,在使用滋阴之剂时,为防止滋腻太过而有助湿之虞,常佐以芳香辛燥之品,从而润燥相宜,刚柔相济[5]。陈老师指出,健脾温燥不宜过用附子、干姜等温热之属,养胃润燥不宜过用黄芩、黄连等苦寒之品,应中病即止,以防日久损伤脾胃。燥湿之品,皆芳香燥烈,易耗伤阴津,用药常选淡渗利湿之茯苓、猪苓、泽泻、冬瓜皮,芳香化湿之藿香、佩兰、石菖蒲、白芷、苏叶、白豆蔻、砂仁等,为防其弊,常佐以石斛、麦冬、玉竹甘润之品,使燥湿而不伤其阴津。益阴之品,常滋腻助湿碍脾,在用南北沙参、麦冬、百合、石斛、玉竹、五味子、生地黄、玄参等养阴柔润之类时,为防其弊,常佐以白术、扁豆、薏苡仁、茯苓之类健脾化湿。理气之品,大多辛香温燥,过用伤及肝胃之阴,常选用佛手花、绿梅花、玫瑰花、代代花、苏梗、生麦芽等理气而不伤阴之品,且每在方中加用白芍、乌梅、五味子等酸甘化阴之品以防温燥伤阴。陈老师常用麦冬和半夏二味药对,润燥之麦冬可制半夏辛燥之性,辛温之半夏可防麦冬之滋腻碍胃。
4 病证结合,轻重得当
中医是根据证候进行辨病,只有在证的基础上认识疾病的本质,才能病证结合,进而辨证论治。随着西医学的引进,中医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发展,取长补短,积极借助现代科学仪器及设备去认识其微观的特性,视作中医四诊的延伸,运用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去总结它所反映的宏观方面的证候特点,然后病证相结合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陈老师在治疗CAG时,在传统中医辨证论治基础上,借鉴现代医学的胃镜、病理结果及中药药理,病证结合,从而更好的针对性用药,不仅消除患者临床宏观症状,又可改善患者微观病理情况,逆转病变进一步发展,截断病势。如幽门螺旋杆菌(HP)阳性者,可选用白花蛇舌草、黄连、黄芩、蒲公英、连翘、丹参等具有根除HP作用的中药;若胃酸过多,可选用煅瓦楞、乌贼骨、浙贝母等抑制胃酸分泌;若胃酸过少,可选用山楂、乌梅、木瓜、白芍、五味子等具有刺激胃酸分泌;若兼见胆汁反流者,通过腹部彩超排除肝胆胰腺的问题后,一般考虑肝胃不和,胃肠动力差所致,常选用旋覆花、柴胡、郁金、香附、陈皮等疏肝和胃、调节胃肠动力;胃镜下若见胃黏膜灰白,色调不均,多认为脾胃虚寒,可加黄芪、桂枝、干姜等益气温阳;若见胃黏膜分泌黏液量少,多属阴虚津亏,可加玉竹、石斛、麦冬等养阴生津;若见胃黏膜充血水肿明显,多属湿热中阻或湿阻水停所致,加用黄连、黄芩清热燥湿或猪苓、泽泻燥湿利水;若见胃黏膜糜烂出血,多为血溢肉腐之证,酌加白及粉、三七粉、木蝴蝶以敛疮生肌护膜;若病理见肠上皮化生者,多考虑脾胃虚弱基础上痰瘀互结所致,可加九香虫、丹参、莪术、陈皮、半夏、瓜蒌等健脾胃化痰活血;若病理见低级别上皮瘤变者,多考虑热毒所致,酌加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藤梨根、石见穿等清热解毒药物。
临证之时仅仅选择了正确的方药还不够,药物剂量尤为重要。古人云:“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药量太轻,如杯水车薪,达不到预期治疗效果,但剂量太大,则药过病所,不仅造成脾胃损伤,还浪费药材增加患者经济负担,故药物剂量的轻重得当尤为重要。对于CAG,由于药力可直达病所,故用药比其他疾病更易取效,但也更易致损。孟河学派治疗脾胃病时遵从温病大家吴鞠通“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之论,强调临证处方药味少而精,不能过大。但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也绝不是药物剂量不能偏大,若片面强调精简,而不能针对主要矛盾,也不足取。在辨证的基础上适当应用大剂量的药物,中病即止也非常安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言“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指出经方是根据疾病的轻重确定药量的轻重,不是一味的蛮攻。陈老师临证之时,不拘泥于古人之论,若患者气虚明显,非大加温补不足以治其本,炙黄芪常可用至30 g,同时为避免虚不受补,适当加入陈皮、枳壳、白豆蔻等理气醒脾和胃之品,可防其中满之弊。CAG寒热错杂之证多见,最忌甘温壅补,陈老师常用清补平补之品补虚扶正,太子参少则用6~10 g,多则用到25~30 g;仙鹤草少则用10~15 g,多则用到30 g~60 g;白扁豆少则用10~15 g,多则用到30 g。陈老师指出,用药剂量的轻重多少与医者的学术渊源、个人经验、剂型、配伍、药物生长年限、药品毒性大小以及病情不同的因素有关,故临证中贵在思路清晰,需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恰到好处,而不必硬性规定,谨守病机,轻重得当,临床效果最为重要。
[1]周芸,王一庆.详辨虚实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3,27(4):1-2.
[2]中国中医研究院.蒲辅周医疗经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26.
[3]赵美娥.周乐年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经验[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6):77-78.
[4]刘晓谷,蔡淦.蔡淦辨治慢性萎缩性胃炎经验[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9,43(7):5-7.
[5]许宝才,李春婷,陈伟.单兆伟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经验[J].中医杂志,2011,52(12):1002-1003.
(责任编辑:冯天保,郑锋玲)
R573.3+2
A
0256-7415(2016)11-0158-03
10.13457/j.cnki.jncm.2016.11.069
2016-05-25
浙江省中医药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6ZB137);衢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4169)
许宝才(1982-),男,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道疾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