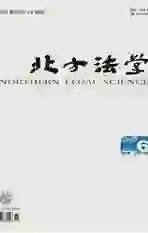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宪法解释
2015-12-02李勤通
李勤通
摘要:八二宪法的集体土地制度包括所有权层面和使用权层面。无论是五四宪法还是八二宪法,从农民土地所有权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变化无非是国家管理农村经济手段的变化。但八二宪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确立既带有国家管理手段变化的色彩,也带有基本权利的色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现与自留地的保留一样,也是农民用生存权进行抗争的结果。因为其生存权属性,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对抗国家性,当然这种对抗国家性是伴随着现代法治观念的传播逐渐增强的。同时,由于其内在缺陷,生存权无法完全有效对抗国家权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需要从生存权本质转向自由权本质。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 集体土地所有制 宪法解释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6-0140-12
时至今日,土地仍旧在扮演财富之源的角色,尤其是当拆迁这一问题不断出现的时候。围绕土地展开的矛盾深刻而又尖锐,核心问题则在于土地产权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带来的讨论仍旧不绝于耳。在八二宪法确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趋势在实践中逐渐形成。①在无法轻易变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市场化乃至金融化成为众多学者所提倡的推动农村经济、保障农民权利的重要举措。②土地承包经营权重要性的逐渐提高需诉诸于《物权法》将之物权化。民法学界为此用力甚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这种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宪法上是如何定位的?如果说民法研究解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障碍及对抗私人的功能的话,是否也解决了其所应具有的对抗国家性?财产权的对抗国家性本质上需要来自于宪法。③但宪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质上是什么?八二宪法所确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能够发挥对抗国家、保障农民权利的功能?对此,民法上的思考并未涉及根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保障的限度取决于其宪法地位。本文尝试用历史解释与文本解释的方法对五四宪法以及八二宪法中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解释,从而试图揭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宪法本质。
一、 五四宪法中规定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及其原意解释④
五四宪法中规定了个人所有制,也规定了农民土地所有权。所有制与所有权并无本质差异,农民土地所有权是土地私有制从政治层面向法律层面转化的结果,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八二宪法的土地制度与五四宪法的土地制度一脉相承。作为根本土地制度,五四宪法规定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八二宪法则规定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但五四宪法所确定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土地私有制,农民也没有获得对抗国家层面的土地所有权。从本质上来说,五四宪法的土地私有制正是八二宪法中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身。或者说,八二宪法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正是五四宪法中土地私有制在党的经济发展策略中的必然命运。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公有制在五四宪法中的矛盾与融合正好能够反映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宪法中的基本定位。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⑥ 顾龙生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⑧ 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
⑨ 韩大元编:《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3页。
⑩ 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B11 前引B10,第105页。
B12 参见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宪法,之前的共同纲领被认为起到了临时宪法的功能。从共同纲领开始,土地制度就是核心的经济政策。共同纲领第27条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第6条)在否定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提出:“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五四宪法第8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按照这三条规定,农村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而农民被认为取得了土地所有权。但这种所有权是否为现代意义的所有权还需进一步探讨。
解读这一点,需要回到党对农民土地私有制的认识上。从思想背景来看,党的建国方针及社会发展方针是建立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设计中的。“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⑤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的《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农业方面要从个体逐渐转变成集体方向发展的经济。⑥而且,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⑦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就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与国家计划经济的冲突为前提进行的,私有制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的阻碍。⑧因此,走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党在农村的发展战略,农民土地私有制的设立不过是为了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而妥协的。从立宪背景上来看,五四宪法的制定是为了确定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巩固革命成果,保障社会主义理想在实践中的展开。⑨从社会主义与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冲突来看,五四宪法反而内含着反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要素。从立宪内容上来看,五四宪法的序言中已经明确了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方向,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五四宪法第7条有同样内容的规定。从经济政策上来看,农民对土地的占有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是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存在的。1946年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进而带动工业化对发展农村土地私有制的需求,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B11当农村生产力被认为不再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时,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直接提出了实现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B12甚至此后,为了保障市场供应和工业化进程,农产品买卖成为国家控制的一部分,统购统销迅速席卷多种重要农作物,农业被纳入计划经济的范畴。B13“不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家,大家一律平等:大家都成为无地农民,成为集体这个虚拟主体,其实是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农民”。B14最终形成了相沿至今的城乡两元分立机制。B15从历史发展来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农村合作化迅速展开,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短短几年间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竟然实现了。当这种冒进的农村合作化受到农民抵制的时候,党采取了两条道路大辩论和全社会整风的形式在整个社会层面宣传农村合作化的好处,并且斗争了一部分反对者,早期的自愿、互助原则被否定。B16农民的所谓土地私有制很快就通过合作化等方式转变为集体土地所有制。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五四宪法中所谓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实践。这种权利无法对抗国家权力,而且需要根据国家政策的转变而摇摆,甚至宪法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就包含内在冲突。这种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是一种国家主导下的使用权。
B13 前引B10,第272页。
B14 周永坤:《解禁中的人权》,元照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81页。
B15 白永秀:《城乡两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路径》,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
B16 参见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而且自愿原则是五四宪法第8条的明确规定。但是同条又规定了消灭富农的内容,属于强制平均分配土地。
B17 比如需要区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活资料所有权。毛泽东在1958年针对以调拨方式支配农产品的建议时提出“我们国家你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54页。)由此来看,毛泽东似乎认识到了所有权对抗国家的属性。但问题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观念是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被认为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参见[苏]卡列娃、费其金主编:《苏维埃国家和法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沈其昌校,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382页。)区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毛泽东那里也是非常清楚的。(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385页。)在生活资料具有对抗国家权能的同时,生产资料由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根本意义而在五四宪法中就已经被规定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五四宪法也将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8条)和生活资料所有权(第11条)区分规定。这说明所有权概念在五四宪法中并非一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被认为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可以是国家处分的对象,而非对抗国家的法律工具,至于何时处分、如何处分则取决于国家政策。
B18 对抗国家作为宪法最为重要的功能体现在五四宪法第13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但宪法序言又明确提出五四宪法反映的是“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而按照总路线的规范,农村土地所有制必然转化为公有制,这种必然性使得土地所有权从根本上不具有对抗国家的能力。可以说五四宪法内对待宪法财产权的矛盾态度并未排除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支配。
B19 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普遍性。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485页。
B20 参见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B21 参见陶艳梅:《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述论》,载《中国农史》2011年第1期;参见郑有贵:《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等。
B22 如蔬菜、粮食、棉花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9页。
一般来说,严谨的宪法解释无法将所有权解释为使用权,但五四宪法背景下的某种解释是确乎当然的。五四宪法规定的所有权虽然用词一致,但内涵并不一样。B17这种土地所有权根本上只具有对抗他人的权能,而宪法中的土地所有权如果是真正的所有权,它必然具有对抗国家性。B18显然,五四宪法所确定的农民土地所有权并不具有这一特征。第一,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受到国家限制。B19农民土地所有权之目的首先在于使党能够获得农民的支持,B20但耕者有其田的斗争策略本质上服从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规划。故论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的根本落脚点在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建设铺平道路。B21这导致土地用途在某种意义上必须符合国家需求。B22五四宪法第14条明确指出:“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求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土地使用权受到国家的计划限制。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确立并没有排除国家对土地的最终所有权。一方面,如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以没收土地为手段,以带有权力机关性质的农民协会为具体分配主体,其实质就是国家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因此,五四宪法所确立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土地再分配之规范化,与传统的均田思想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土地私有制乃是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个步骤,农民所有权从制定之始就注定了走向公有制的必然命运。毛泽东在1953年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B23五四宪法是接续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的,尤其宪法序言和总纲集中体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原则和精神。B24甚至有学者认为,“1954年宪法是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宪法化”。B25五四宪法第7条明确了私有制的命运,“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五四宪法的农民土地所有权之命运已经被宪法所规定,根本不具有宪法财产权的对抗国家性。正如田家英对资本家所有制的宪法命运之预言一样:“我们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资本家所有制虽然将来要消灭,但在宪法仍是一种所有制,这是事实,是需要写上的。”B26宪法上的私人所有制被认为是一种事实确认而不是规范保障。第三,五四宪法的土地制度体现出了管理性特征。五四宪法制定时期是我国新的身份社会建立的奠基时期,资源分配、社会管理主要基于身份。B27其规定的土地制度是身份管理制度的附属。依靠贫下中农、限制富农、消灭资本家作为既定政策是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的基本策略,其反映的身份利益中也体现为所有权保护的差异。故五四宪法第8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又规定“国家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贫下中农与富农的土地所有权之保护在宪法层面直接显示出了差异。党和政府对人的身份管理延伸到所有权制度上,为不同身份的人及其所有权确定了不同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私有制为党所认可的重要理由在于这是解放生产力的方式,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并非目的,国家目的之实现才是根本。一旦国家目的与农村土地私有制产生现实冲突,B28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B23 参见前引B22,第119页。
B24 参见韩大元:《1954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
B25 殷啸虎:《过渡时期理论与1954年宪法》,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
B26 前引B24,第98页。
B27 参见王爱云:《试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身份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2期。
B28 五四宪法的制定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确认已经取得的经验与成果,二是把人们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法定化。(参见前引B24,第69页。)而私有制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背离的,“‘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参见前引B22,第120页。)这说明,五四宪法内含的国家目的与当时农村土地所有制间的矛盾,如果将土地所有权认为是真正的所有权就意味着宪法提供了土地所有权对抗国家的要素,但实际上宪法所确保的国家目的却与之相违背。
B29 前引B24,第91页。
B30 [苏]坚金、布拉图斯主编:《苏维埃民法》(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民法教研室译,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B31 参见[苏]库德利雅夫采夫主编:《苏联法律辞典》(第一分册),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1页。
B32 前引B25。
B33 在五四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意见中,地方单位和军事单位提出将“第8条第1款中的‘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可改为‘国家在过渡时期依法允许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参见前引B24,第171页。)尽管这一意见并未被采用,但也反映了时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B34 毛泽东认为五四宪法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原则性指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灵活性则强调“一时办不到的事情,必须允许逐步去办”。(参见前引B22,第127—128页。)社会主义原则注定了私人所有制的必然命运,而灵活性则指出了当时所确定的私有制的政策性及其规范效力的有限。
还需要注意的是,五四宪法受到苏联宪法的很大影响,B29苏联宪法也规定了所有权制度,但苏联法律中的所有权受制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差异。尽管两者都处于所有权概念涵摄范围,但苏联法律极力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所有权与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差异。B30个人所有权的占有、使用、处分等权能受到了严格限制,B31而且其本质是国家与亟需满足基本生活之民众的妥协(考虑一下苏联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即可知),无论个人所有权的权能还是本质都无法与现代所有权相类比。受此影响的五四宪法之土地所有权也无法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
宪法规定的“这种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既保护、又改造的政策,正是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矛盾运动的一种反映”。B32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策性并没有转变成五四宪法的规范性,反而使得五四宪法的规定带有了政策色彩。B33或者如毛泽东所言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B34因此,五四宪法中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规定缺乏所有权的权利内涵,也不具有根本规范性,本质上是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现实步骤。因此,无论宪法表述是土地所有权还是土地私有制,其本质是一种国家管理农村经济的手段。B35但从一开始,这种手段就被认为是低效的而需要被社会主义化。而当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在八二宪法中被确立后,其国家管理的属性仍旧没有消失,只是国家管理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二、 八二宪法的土地所有制之变化及其解释
到了七五宪法、B36七八宪法,B37土地私有制已经基本从宪法中消失,土地公有制奠定绝对地位,并且得到了八二宪法的承认。王人博在分析七五宪法的时候提出“1954年宪法文本凸显的是宪法的国家性而不是党性,七五宪法强调的是党性而不是国家性。就此而论, 1982年的现行宪法在党性上与七五宪法而不是五四宪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B38党的意志在中国社会前途上具有根本指导性,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宪法命运是与党对中国社会判断的整体状况勾连在一起的。单从土地制度来说,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党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全国一盘棋,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
但仅从宪法规范层面来说,八二宪法相比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在土地制度上有一个退步,那就是八二宪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了“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土地所有制,而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5条)的方式表达出来。与八二宪法的全称规定相比,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是用“主要”一词来表述的。问题是,在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病后,为何还会如此表述?B39前文已经指出五四宪法对土地私有权的规定与其说是一种所有权不如说是一种使用权,八二宪法不过是将之从事实转变为文本。
B35 参见汪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三重功能性》,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2期。
B36 七五宪法第7条规定:“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B37 七八宪法第7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现在一般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向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B38 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3期。
B39 彭真在1982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个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它的存在并不妨碍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它的顺利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以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
B40 参见刘连泰:《政治宪法学的疏漏与吊诡》,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八辑),法津出版社2012年版。
相比五四宪法,八二宪法主要通过调整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来管理农村经济。其第8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七五宪法与七八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方式,但它们的三级所有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将财产的公有形式与使用方式挂钩的。而八二宪法对土地的使用方式做出了开放性规定,除第8条外,第17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这个更加开放的条款,B40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关系开始分离。
这种放开土地使用权的做法根本上来自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反思。无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是生产关系在党的话语中都是与解放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目标追求在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说明,“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B41生产关系被认为是推动生产力的关键工具,因此显得最为重要。但仅在集体经济上做文章导致的却是农村的普遍贫困。B42“文革”之后,左倾开始受到清算,这种反思成为党走向改革开放的观念基础。B43比如胡耀邦在1978年就指出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化的路线存在问题,开始反思集体经济,B44因此生产关系被认为需要重新调整。但土地公有制并没有受到影响,这里面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B45首先,尽管“文革”对经济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但对“文革”错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并不被认为是犯了很大错误。B46其次,农村中存在的问题被认为是管理层面的问题,恢复经济发展反而需要国家政策的指导,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这要求国家必须掌握主动权。B47再次,土地公有制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对集体所有土地的保护,这一点在1978年《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表现的很明显。B48最后, “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仍旧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绩,“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生产关系需要发生变化,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发生变化。
生产关系的变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层面都要尊重经济规律,生产关系要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消极层面来说,领导层认识到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但主要认为属于管理问题。B49从积极层面来说,土地使用权的放开从文革时期就开始发挥作用。不仅放权被认为是“文革”期间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B50而且地方的土地使用权也逐渐放开,增强生产队的自主权、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等纷纷出现。B51土地使用权的多元化、农业生产经营的多元化都对原有的土地制度产生了冲击,并且实践证明效果显著。从实用角度来说,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对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无需否定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于是,八二宪法进行了折中,集体土地所有制象征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放开则使得对土地的管理更加多元化。随着党的政策改变,农村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B41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1958年12月10日),载《法学研究》1958年第6期,第4页。
B42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35页。
B43 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B44 童青林编:《回首197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B45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可能还有路径依赖上的问题。参见马耀鹏:《制度与路径依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载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81页。
B46 前引B42,第610页。
B47 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页。
B48 “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前引B44 第372页。
B49 参见前引B44,第365页。
B50 前引B42,第612页。
B51 前引B44,第296页。
B52 钱福臣:《八二宪法的属性》,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
应该说,五四宪法是通过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来调节农村经济发展,而在八二宪法中则通过直接调整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来调整宪法,这就使得五四宪法与八二宪法的土地制度不具有对抗国家性,也就很难证成其基本权利的属性,同时也使得“宪法的制定及其修改是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改革政策的重大变化引起和决定的,宪法的制度和修改历程是对执政党改革政策演进历程之记录与确认”B52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但土地制度既具有国家主导调整的成分,也具有被动调整的成分。八二宪法中土地使用权的放开既是国家有意为之,也是国家不得不为之。土地使用权的放开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现,既是国家管理农民经济的手段变化之表现,也带有基本权利的属性。
三、 八二宪法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原意解释
自八二宪法以来,集体土地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不断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所赖以为存的基础是生存权。正是基于生存的抗争才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现在宪法文本中,也正是生存权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断得到固化。
(一) 八二宪法以来集体土地制度的变迁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固化
B53 关于广东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宪法案例,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实验》,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不过张千帆关于八二宪法的中心原则是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观点值得商榷,不可否认这些基本观点是理解八二宪法现在状态的关键词,但这是在八二宪法的解释流变中发展起来的,而非自始就有。
B54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16期。
B55 参见前引③刘连泰书,第119页。
B56 参见张英洪:《农民权利论》,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B57 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0页。
B58 董景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模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B59 杨一介:《中国农地权基本问题》,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八二宪法后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并没有被废除,但却有两个显著变化:第一,土地使用权制度发展迅速,土地使用权转让成为可能。1988年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将土地不得出租从宪法中剔除出去大概是对广东集体土地使用权出租情况的回应。B53这是宪法对政府改革开放实践的认可。而从生产关系上,从1993年修正案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9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体现了宪法在土地使用权方面的变化。这种土地使用权的宪法变迁遵循着传统发展思路,在实用原则指导下从良性违宪走向宪法文本,财富最大化超越意识形态。由于土地使用权的重要性,而土地承包责任制又集中体现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特征,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农民最为重要的土地权利。第二,土地征用制度转变为土地征收制度。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1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求,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求,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从征用到征收与征用并行并不仅是修辞上的变化。按照王兆国的解释,“征收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规定……从内容上看,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的情形,实质上是征收”,B54征收意味着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有学者认为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集体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作为私权已经发育成为一项内涵饱满的权利。B55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得重要,所以宪法对它的地位作了重新调整。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运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集体土地的观念也不得不进行修正。从1984年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确定土地承包以15年为期,到1993年的30年不变,再到2003年《土地承包法》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权和收益权的归属,最后到2007年《物权法》将土地承包权用益物权化,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认为正在逐渐形成有效率的私有产权。B56有学者甚至认为物权法的规定使得“就农业承包经营户和承包地之间必须应对配置而已,土地承包经营权发挥着与无期物权相当的作用”。B57
与此同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概念却逐渐失去主体意义。原本农村实现的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但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政社分离,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被虚化,“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农户”B58而不是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土地所有权虽然被规定在宪法上,但却出现主体虚化,其宪法地位在理念上被土地承包经营权超越。这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虽然政社分离,但村社区居委会还存在,“土地集体所有权所具有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使得所有权在人为操作中,可能将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强化为乡镇干部的土地所有权”。B59乡镇干部能够对集体土地的出让、转化等发生很大作用。第二,农民能够超越集体对土地进行控制,无论是在土地处分还是收益分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对后者来说,宪法提供了一定保护,但这究竟是权利保护甚或基本权利保护,还是如同从前一样仅仅是国家管理手段的变化?
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逐渐物权法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本质属性为何?宪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又属于什么性质的保障?这两个问题的解答都需要对宪法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之根本属性进行解释。
(二) 从生存权延伸出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于自留地的考察
农村土地制度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制度,并创立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一方面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健康运转后,这一变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背后是农民基本生存之必须,因此是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必然选择。土地承包经营权背后所勾连的是农民的生存权,在这种意义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了基本权利的属性。
之所以如此认为,主要来自对农民生存和土地关系的认识。 无论是当下还是古代,土地都与农民有着根本联系。孟子云:“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B60他之所以主张井田制就是希望通过分配土地能够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之基。土地代表着农民的生存条件,农民满足了基本生存国家也就稳定了。这也是为什么历代都会对分田、抑制兼并感兴趣。即使宋代之后国家层面的分田已经很少见到了,但又迅速发展出永佃权制度并获得国家认可。B61到了近代革命,均田地的口号仍旧能够吸引大量的民众。B62土地透过生存这一命题与农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49年以后,这一命题也并无改变。即使农村改革失败甚多,但其目的也包括发展农村经济,而这也是满足农民生存的必要条件。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目的,只不过是国家的发展首先必须保障农民的生存。因此,农民的生存权与国家发展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博弈。这一点从自留地存留中充分体现出来。
B60 《孟子·梁惠王上》。
B61 参见柴荣:《中国古代物权法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B62 参见陈扬勇:《建设新中国的蓝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205页。
B63 黄长久:《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自留地经营的演变及其特点》,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B64 前引B47,第39页。
B65 参见黄荣华:《革命与乡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B66 前引B65,第120页。
B67 前引B65,第155页。
B68 前引B62,第220页。
B69 参见朱金鹏:《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自留地是在农村土地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产物,“自留地经营存在的历史条件就是单靠集体经济不能满足社员家庭对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多种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补充办法”。B631949年以后,在农村土地制度集体化的过程中,考虑到农民在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中的“两个积极性”,B64党和政府在推行合作社经济的同时对自留地采取了保留态度,允许自留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自留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自留地经历多次存废之争,最终保留了下来。在合作社运动中,合作社要完成国家经济任务和社员服务任务,使得农民的负担有加重趋势。B65另外,合作制及其带来的平均分配使得农民无法在集体经济中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自留地经济发展起来了,B66这使得农民能够通过私有经济的方式获得自己的生活所需。然而自留地的私有性,使得它不断受到质疑,但“由于集体土地化生产造成的低效益,分配不能兑现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社员的口粮减少,牲畜饲料也发生困难,自留地和开荒成为缓解社员生活困境的现实选择”。B67第二,自留地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在中国的发展策略中,“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刘少奇语),B68因此农业承担了推动工业发展的职责,农业的收益分配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控制。结果农民自身的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于危及到生存。因此,自留地就成为缓冲国家需要与农民需求之间的隔离带,对农民的基本生存具有重要功能。第三,自留地经历了从私有到公有的过程。1955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还能够看到自留地的私有性质,但1958年《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自留地就被转变成了公有属性。B69第四,自留地经历了从党的政策到宪法地位的过程。自留地是政策的产物,但后来却被逐渐法律化。无论是1955年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还是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我们都能够看到自留地的存在及被承认。
为什么在集体经济如火如荼的年代,自留地这种带有私有色彩的土地制度不断反复出现并最终在宪法中确认?主要原因就是它与农民的生存联系在了一起。没有了自留地,农民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抵抗灾荒的能力,甚至在普通时期也会生活困窘。生存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是第一位的,即使是国家在推动公有化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让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诞生也具有相同原因。“在当时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农民冒死搞的‘包产到户,绝不是为了什么神圣的私有产权,只不过是为了眼前的活命”。B70因此,无论是自留地的存在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在,都与生存权联系在一起。国家对之的承认也是建立在生存权基础之上,即使是国家也不得随意剥夺人的生命,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抗国家的根本点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生存权之间的关系使它不再与五四宪法以来作为调整经济手段的土地制度相一致,此时产生了真正的观念断裂。对抗国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核,而不再仅仅是管理对象。
(三) 八二宪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重新解读
一旦认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与生存权间的关系,重新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就成为可能。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生存的重要意义,所以它从来源上就是生存权的组成部分,应该属于基本权利,其在宪法中具有不可更易的地位。一般来说,生存权意味着“国际人权公约上的相当生活水准权”,B71这是一种狭义的生存权概念。但对中国农民来说,土地与生命、生活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他们需要土地去维持自己的生命,而且需要土地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应该用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广义生存权来理解农民的这种生存权。明确这一点,再来分析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理性。八二宪法同时规定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两者实际上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矛盾。土地所有权意味着对土地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却被虚化,这一点在八二宪法当时就已经有所显现;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断强化使得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意义削弱,谁来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然而与其说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弱化是一种侵蚀,不如说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宪法地位确确实实在下降。原来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但却起了反效果。与之相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宪法地位却因为其依存于生存权而逐渐提高。这就有理由推断目前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宪法地位更像是政治宣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确认。而在我国的人权发展史上,生存权被认为是首要人权。“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B72土地被认为是农民生存保障的基础,B73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了基本权利的地位。
B70 前引B56,第161页。
B71 上官丕亮:《究竟什么是生存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B72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B73 参见孟勤国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B74 金春明:《大变动年代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B75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必须掌握政权是邓小平权力思想的核心之一。参见平文艺:《邓小平权力观初探》,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4期。
B76 参见李步云:《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B77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因为基本权利的根本意义在于国家对抗性。即使宪法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本权利,它还需要面对国家权力的态度问题,因此在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基本权利的取得是渐进式的。很多人认为“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权力过于集中,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保障。B74但是,个人集权只不过是权力集中的一种表现而已,同样还有集体集权,这一问题却被忽视了。权力集中仍旧被认为是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B75因此,彭真在八二宪法的草案说明报告中阐述宪法修改的重要目的就是“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未设宪法监督机关。B76在这种意义上,陈端洪认为中国宪法内含五个优先顺序的根本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是有一定道理的。B77但这种对权力的认识不过是阶段性的,是一种静态的八二宪法观。这种静态宪法观在八二宪法中体现为对权力善的判断。因此,基本权利保障与国家权力运作被认为是一致的。
然而人们对权力的理解在发生变化,这也带动了宪法解释的变化。党对权力看法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治观念的产生及入宪;二是具体的权力制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权力是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的核心概念,对权力的恐惧与警惕是西方社会的共同心理,如何限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矢志不渝的目标。这种努力可以分为形而下与形而上两大类。在形而上的诸多努力中,当然首推规范主义的努力:将权力置于规范的权威之下”。B78对权力的不同态度,推动着人们对权力结构模式从人治向法治的认识转变,只有认识到人性的不足以及可能受到的权力诱惑,才能够使得法治成为主流话语与追求。由于我国传统观念持有人性善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影响更产生了阶级与善恶之间的直接联系。人治甚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话语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法治观念所需要的人性恶理念并没有被认识到。但“文革”对中国人形成的冲击如此之大,又受到西方法治观念的影响,人们逐渐开始全面认识权力。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B79这种认识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民主与法制成为意识形态中的重要话语,并且被认为是推动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法制进程的基点。B80但这种法制理解并非是建立在对权力恶的理解上的。法制仍旧被认为是管理社会的工具,这一点从行政法管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阶段依法行政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大量的立法建设督促由‘依政策行政或‘依命令行政转向‘依法律行政,行政法律的手段性和工具性较浓,内容上主要是规范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而不是制约和限制行政权力行使”。B81这种法律家长主义背后对权力持有的是信任态度,是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与其说是依法行政,不如说是以法行政。到90年代之后,《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相继出台,国家权力形象才开始发生重大变迁,行政法不再被认为是管理法而呈现出监督法的转向。B82 权力之恶被逐渐认识。在宪法层面则逐渐实现了从法制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尽管从1981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念就已经出现,但其真正达致战略高度则要到1996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B83在经过十多年关于法制与法治的争论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开始提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命题,并于1999年写入宪法。这种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意味着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因为从形式法治的角度来讲,“法律可以……设定奴隶制而不违背法治”,B84但实质法治却内含对自由、人权的更高追求。有学者指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明确了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而客体却指向了国家机器,依法治国的根本在于依法治权、治吏。B85这是学理解释,但法制与法治之辩却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反思,并于1996年—1997年进行了集中大讨论,嗣后成为主流话语。B86应该承认,正是对权力制约的观念才真正产生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而这种理念背后正渗透着权力恶的人性认知。也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对抗性得以增强。
B78 周永坤:《权力机构模式与宪政》,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
B7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B80 参见王人博主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B81 蒋传光等:《新中国法治简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
B82 参见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B83 参见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B84 参见[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B85 参见郭道晖:《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与我国法治与法学的现代化》,载《法学》2008年第1期。
B86 前引B83,第254页。
B87 张翔:《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载《法学家》2005年第2期。
当土地承包经营权被法律不断强化的时候,试图证明它的基本权利的权能是比较难的。“从立宪主义的精神来看,公民基本权利首先的作用在于对抗公权力,防止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受到公权力的侵犯,从而维护个人免受国家恣意干涉的空间”。B87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用来对抗国家侵害的,反过来说,只有当土地承包经营权表现出对抗国家的现实之时,我们才能够实证地认为它被基本权利化了。尽管八二宪法规范土地征用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但1982年《国家建设用地征用土地条例》第4条直接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凡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被征地社队的干部和群众应当服从国家需要,不得妨碍和阻挠”,公共利益与国家需要实际上直接等同了起来。这种对国家需要的善良看法直接导致了1982—1997年间征地泛滥的情况。B88伴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发展和入宪,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从文本回到了“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的宪法话语,依据的正是新的宪法精神。国家征用集体土地的用途被限定,国家需要不再被认为与公共利益划等号了。由此能够看到具体法律制度也在迎合着宪法精神的转变。
四、生存权所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限度及其应有之趋势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种从生存权引出来的认识与一般的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财产权之间相互勾连的看法并不相同。有学者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B89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并列在一起,财产权并非生存权的延伸。“生存权并不必然导致私有财产权,因为在原始共有状态下,人们仍可以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品。可以说,生存权是私有财产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B90作为独立的权利,财产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功能。格劳修斯认为,“衡量一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乃是看这场战争是否是为了保护个人乃至社会、国家的财产权”;洛克则认为,“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是个人的天赋权利, 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政府的作为不是别的,就是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权,最大限度地防范政府与国家利用暴力侵犯个人和社会的财产”;伏尔泰又认为,“私人财产权极端重要,是抵制专制王权的堡垒”,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联邦宪法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把私人财产权置于首要的地位,认为它们是现代人得以存在的法权基础,是个人自由的保障”。B91因此,在西方法律传统中,财产权与个人自由存在着密切关系,财产权是个人自由赖以实现的前提。B92
B88 参见高汉:《集体产权下的中国农地征收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B89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B90 蒋永甫:《西方宪政视野中的财产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B91 高全喜:《财富、财产权与宪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5期。
B92 前引③刘连泰书,第35页。
B93 前引③林来梵文。
B94 章彦英:《土地征收救济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B95 前引B73,第48页。
B96 当然权利制约权力的命题本身就存在问题,只有权力才能真正制约权力。参见胡玉鸿:《“以权利制约权力”辨》,载《法学》2000年第9期。
在自由主义观念下,西方社会对自由的追求构成了国家限制个人财产权的限度。限制财产意味着限制人的自由。而人的自由则是有弹性的概念,又极为广泛。与自由权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权并非是不受限制的。这与生存权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权有其相似之处。由于财产绝对私有观念的破除,各国宪法对财产权的态度出现了嬗变,即“去除了近代财产权的神圣性、绝对性,确认了财产权的内在界限以及公共福利与社会政策对财产权的制约作用”。B93尽管如此,对自由的追求仍使西方社会对财产权采取了很大的保护。财产权受制约的限度需要与自由受制约的限度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生存权却是一个缺少弹性的概念。即使超越“生命必须”将生存转变为“体面生活”,法律对生存权的保障仍旧能够在此之外对公民的财产进行有偿剥夺,因此,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但却很难有足够的弹性支持政府以含混不清的公共利益之名对其进行有偿剥夺。B94因此,同样是基于公共利益制约公民的财产,自由理念下的财产权对公共利益进行了很大限制,生存理念下的财产权则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有限性。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来看:一方面,这种有限性表现在它仅仅为了维持农民的生存而存在,即使逐渐承认土地流转的合法性,但“在土地私有的国家,土地流转主要以土地所有权流转的方式流转,而所有权的流转是永久性的。但我国的土地所有权不能流转,不管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流转给谁,土地始终是特定的农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有期限的,期限届满,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B95因此其作为一种财富的地位并不确定。另一方面,它对权力制约性有限,比如即使是地方政府侵害了公民在土地上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其并没有真正侵害到大多数人的生存,所以该基本权利也并没有真正起到制约政府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功能。B96
同时,当宪法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念仍旧停留在生存权层面之时,它将承担着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与制约的双重功能,而且这种制约功能可能会非常强大。当农民不再依靠土地吃饭的时候,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还能够保持下去令人怀疑。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理念应该由生存权支撑转向自由权支撑。“自由作为法律价值具有终极性,它是人的尊严的直接体现,不自由的人谈不上尊严;它是正义有效的前提”。B97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自由的现代国家,而自由的实现也不能想象没有财产的支撑。 “如果公民不拥有私有财产权,那么,公民拥有的只是特权而不是权力。在政府面前,他们就像恳请者和乞丐,而不是权利所有人”。B98而农民要想获得更大的自由,就需要财产,他们所能拥有的最大财富也就是土地。
结 语
当民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不断扩张时,这种扩张性是否能够对抗国家权力的侵害,最终需要依靠宪法层面的理念支持。自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土地制度乃是国家调整农村经济发展的手段,无论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土地所有权,本质上都是党和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通过宪法的历史解释,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宪法地位的确定却并非如此,它本质上来自于农民的生存权。无论是自留地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当涉及到农民的生存之时,政府总会采取一定的慎重态度。正是在农民与国家的生存博弈中,农民的权利得以发展壮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才最终确立。但生存权是一个有限的基本权利。生存似乎对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再是问题,因此,法律对之并没有采取绝对的保护态度。因此,民法学者所认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属性虽然有《物权法》的依靠,却没有宪法的支撑。然而,法律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人之自由,农民亦有自由之追求。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只有表现出其自由的面相才能真正具有对抗政府侵害的能力,也才能够真正从宪法效力转变为实效。
B97 周永坤:《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B98 [美]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Abstract:In accordance with the 82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in 1982, the collective land system includes the ownership and the right to use. The change from the land ownership of farmers to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in both the 54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in 1954 and 82 Constitution have indicated change of means for national management of rural economy. However,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conferred by the 82 constitution mean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approaches but also bears the feature of basic rights.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is just like the maintenance of individual plots which is the fighting result by the farmers using the right of survival. Because of the attribute of the right of survival,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tends to go against the national power which is enhanced by concept dissemin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eanwhile, because of its inherent defects, the right of survival cannot be effectively against the national power, so that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should change from the nature of survival rights to the essence of right to freedom.
Key words: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land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system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