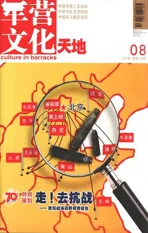冉庄:陷敌于灭顶之灾
2015-11-18
文/特约记者 李 雷
冉庄:陷敌于灭顶之灾
文/特约记者 李 雷

冀中民兵在地道中转移
一个寻访故地的老鬼子
浅尾公平曾是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日军士兵,1939年前后,他曾在保定张登镇据点驻守,任军曹。有一次,他所在的小队60余名士兵在一村庄休息时,受到中国军队袭击,经1小时战斗后,只剩下24人。
1987年7月,浅尾公平来中国访问。在冉庄,自称当年只是一个伙夫的浅尾参观了地道遗址,地道的种种巧妙出口,让他惊奇不已。他的嘴唇不停地嚅动着,但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浅尾回国后,给时任冉庄地道战纪念馆馆长的王树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公开了自己当年的军曹身份,并回忆说当年那损失惨重的一仗可能就发生在冉庄。冉庄人民在抗日期间先后对敌作战157次,共打死打伤日伪军267人。许多时候,只知道鬼子来了就打,打的是准,是敌人什么部队的,并不清楚。张登是当年日军在当地最大的据点,那里的鬼子和冉庄有过多次的交火,地道战让鬼子尝尽了苦头是有史料记载的。
浅尾在信中说:“对冉庄民兵队长的尊姓特意告知表示谢意,他是中国之强者……”
这是一个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人对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拿起武器自卫的中国农民的称赞吗?
“二战”之后,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战史上,这样记载当年在冀中平原的情况:
“(冀中)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进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
同许多年轻人一样,笔者也是通过电影《地道战》才知道地道战这段历史的,那里的台词,那里的人物,那里的场景,那里的故事,已经成为最耐岁月磨损的童年记忆,电影是在冉庄拍的,地道战里的人物也大都以冉庄当年的民兵为原型。冉庄就是“高家庄”,“马家河子”就是马庄,张登就是“黑风口”。
十字街口,钟声已经凝固
车出清苑县城不久,遇到一座现代化的立交桥,桥头有一座雕塑:两柱冲天,上端是一个代表着科技的圆形标志,下面则是一口大钟。这钟就代表着冉庄。电影《地道战》中多次表现过这口钟,它挂在村口的古槐上,钟声响起,既可以是村民开会的信号,也可以是鬼子进村的警报,鬼子“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结果还是被百倍警惕的老支书“高老忠”发现了,在鬼子的枪口前,他凛然敲响大钟,英勇就义。
艺术跟历史开了个玩笑,其实“高老忠”并没有死,是当年导演让他死的,导演做他的工作,说:“咱们这里边得死个人,那样才能唤起人们对鬼子的仇恨。”于是老村长就为艺术献身了。据介绍,高老忠的原型叫王玉龙,1938年任冉庄村的村长,曾经因为挖地道、杀鬼子得到过县里奖励的一支手枪;解放后,他还当过乡长,因为没有文化,1957年主动“弃官为民”到北京干临时工,后来在酒仙桥电子管厂食堂工作。老人在80多岁的时候,还支持抵制日货。有一年冬天,他要腌“腊八蒜”,可是转遍了附近大大小小的副食店,发现卖的醋都是中日合资的,结果那一年他买的蒜都没有腌,白买了。
钟还在,树还在。但现实之中,那棵树不是在村口,而是在十字街上。街宽约10米,街道两侧的房屋全由青砖建造。古槐共是两株,都已枯死,被铁栅栏保护着。树的表面呈青灰色,有数个大大小小的洞。导游小姐解释说,大洞是当年的射击孔,小洞是敌人射击时留下的枪眼。树心已空,直通地道,当年民兵利用树身作掩体射击,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电影里曾有过这个镜头。两株古槐都是唐朝的古物,20世纪80年代还有绿叶,现在却一点也没有了。它们是看到子孙胜利并过上幸福生活以后才寿终正寝的。
古槐的旁边是沿街的店铺房,现在已空,地面铺着花砖。靠墙一侧,笔者看到了地道的“地面出口”,几块钉在木板上的砖头,下面有钢质的轴承,很滑,用脚轻轻一推就开了。当年民兵高传宝对假扮的武工队说:“地道,这里就有,请吧!”那时没有钢质轴承,用的是枣木小滑轮,导游说,也非常好用。
街道两边都是青砖平顶房,就是电影里民兵们可以自由行走转移的空中通道。据介绍,冀中民居多为平房,主要是用房顶晾晒粮食,夏天太热时,人们也可以到房顶上乘凉,并非特意为战斗准备,更不是从抗日战争起才有的。“高房工事”则是建在房顶一角的小角楼,居高临下,用以观察和火力封锁,是为战斗而建。
“村边石碾有神枪,井中抛出手榴弹,马槽猪圈皆暗堡,锅台灶膛藏身好,墙壁有刀敌头疼,烟囱无网擒敌巧……”冉庄后人编撰的顺口溜,生动地记录了地道战的形式,描述了当年的战斗情形。其所述,笔者没能一一见识,但在街道上,笔者也看到了“石头工事”、“烧饼炉工事”、“夹壁墙”等,就是这些工事、射击口,当年让鬼子有去无回,陷于灭顶之灾。

在华北平原地区抗日的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道使家家相连,村村相通,形成地下交通网。这是冀中人民在挖沟掘道改造地形,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地道里,我们屈膝而行
那时,地道在整个冀中平原,正如歌里所描述的那样,“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不独是冉庄才有。导游王静宇小姐就不是冉庄人,她的老家是距冉庄10公里的抄纸屯。据王小姐说,她小的时候,一到下雨走路就常常不敢使劲往下跺脚,因为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塌陷——到处都是地道。整个冀中平原究竟有多少地道,至今没有完全的统计数字。1961年,冀中发大水,好多地方的地道塌陷,这个数字就更没有人理会了。
冉庄地道共长16公里,以十字街古槐为中心,分为四大干道,干道又分成24条支道,四通八达,犹如迷宫。现在向游人开放的只是十字街附近的700米左右。
在地道里,橘红的灯光接连不断。王小姐指着在洞壁上凿出的“灯台”说,当年群众钻地道时就依次点亮油灯,前面的人点,后面的人负责熄灭。
地道壁每隔一段还开凿有高约三尺、宽约二尺、纵深一尺左右的单人掩体。这些掩体,平时可以用于让路,战时可以用于埋伏。设身处地想,在宽仅一米多的地道里,这些很不起眼的掩体,应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奇用。
在通往十字街指挥部时,我们又钻了一段长30米左右的矮地道。这段地道高仅1.2米左右,宽度也更狭窄一些。人在里面穿行,必须把腰弯下,把膝屈起。这种地道,才是当年大部分地道的原貌;我们方才直立通过的地道,是后来为游人参观方便而改造的。当年的民兵们在地道里都是屈膝弓腰而行,30米长的矮地道却将我们折磨得腰酸背痛、呼吸憋闷。王小姐说,还有好多地道都是因为逼仄而不能对游人开放,有的地段须爬行才能通过。在这里,笔者深切地体会到面对生存危机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
王小姐告诉笔者,当年的民兵和群众把地道战称之为“耗子战”,这个称呼虽不甚雅,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却要形象、传神得多。
抗日战争时期在冉庄第一个挖地道的人叫张森林,他是冉庄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曾任冉庄抗日政权秘书、武委会主任以及清苑县大队政委。自1938年开始,鬼子不断骚扰冉庄,到1942年前后,仅冉庄周围9公里方圆内就有炮楼、据点15座,公路4条,呈现出“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起狼烟”的悲惨景象。群众为了少受损失,常在敌人到来之前,带人携物躲到村外的青纱帐里。秋后,青纱帐一倒,人们就在野外和村里挖隐蔽洞用来隐身藏物。张森林首先在自己家里挖了隐蔽洞,既可以自己躲藏,也可以供区、县委干部使用。这样,从单口洞到双口洞、多口洞,到复杂的地道,冉庄人民终于挖出了一个近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为了再现日军残酷统治的情景,冉庄村老支书王全喜在距冉庄最近的姜庄炮楼遗址附近,仿照当年黑风口据点修建了一座特别的日军罪行陈列馆。笔者登上四层的“炮楼”,冉庄景象尽收眼底,一览无余。400米范围内,连一只鸡的走动都能看到。但就是在这种看似无险可依的情况下,冉庄的地道绝处寻生,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不可攻克的要塞、“翻眼”、“囚笼”及地下兵工厂。
据记载,1942年定县的北瞳村地道口被鬼子发现,遂将事先备好的大批毒瓦斯灌入地道,致使当地800多名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弱和部分民兵惨死于毒气之中。在冉庄地道里则有一种“翻眼”,就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在地道的地面以下再开挖一条更深的地道,然后再挖上来,如同在直行的地道里堵了一堵厚墙,人从墙的下面通过。“墙”两侧的洞口可以随时用东西堵上,土层能有效地防止毒气入侵。
地道里还有很多机关,这些机关都是为了对付进入地道之敌的。最常见的是“陷阱”,隔不多远就有一个,下面埋着竹扦利刃。除了“陷阱”还有“囚笼”。“囚笼”是一种地面上的陷阱:地道在前进中被分成两股,中间有夹墙,夹墙内设栅栏,若敌人进了地道,埋伏起来的民兵就会把栅栏从夹墙的一边推到另一边,把敌人困在里面,“关起门来打狗,堵上笼子抓鸡”。夹墙上有孔,民兵无须绕道栅栏口就可以用红缨枪把敌人刺死,或者用枪将其击毙。有了这些设施,冉庄地道就不单单是消极的躲避工事,而是积极的战斗工事。
1945年夏初,日军一个中队伙同两个伪军团,三路进攻冉庄。当时村里的民兵只有30余人,但他们依托地道和地面战斗工事,在大敌面前毫无惧色,从早晨打到下午5点多,整个战斗延续了13个小时,在区小队和各村民兵的支援下,以轻伤一人的代价,大量杀敌,击毙敌伪军团长一名。这一仗后,日伪军留下一句口头禅:“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黑风口是张登的老地名,电影中亦如此称,现称张登)。
这次战斗结束后,县武委会召开大会,总结历次地道战的经验和取得的战绩,颁发冉庄“地道战第一村”奖旗一面。同时奖励大枪3支,地雷1000枚,子弹300发。
打仗就需要武器,没有这些奖励的武器时,冉庄人民靠的是自己的兵工厂,它也在地道中。
地下兵工厂的面积共有约140平方米,分为4个车间,即:锻轧车间、铸造车问、炭窖车间及组装车间。此外,还有一个成品室。火药是枪炮的根本,配方却极为简单:一硝二磺三木炭。难题在于有火就有烟,怎样把烟排出去而不让敌人发现呢?当时的民兵,把兵工厂的一面墙和兵工厂负责人梁连恒家的围墙对齐,地下的“墙”和地面的墙同时掏空,墙上方挖出无数的小孔,这样,烟就从那些小孔里慢慢“渗”出去,让人难以察觉。在兵工厂,笔者感觉到空气比一般地道要清新一些,气压也正常,这都是那些气孔的作用。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
在成品室,笔者看到了当年保留下来的一些武器:有用便壶做的地雷,有用瓶子做的地雷,有用老鼠夹子做的地雷,还有用石块做的地雷,五花八门。史料记载,战争年代,这个兵工厂共造地雷1200个,翻火子弹5000余发,土炮弹200余发,扫帚炮2门,榆木炮1门,撅枪百支。为了防止兵工厂出事故,组装车间还有一眼深井,一旦有险情,还可以把危险品扔进井里。
离开兵工厂的时候,有一个岔道被一扇门堵住了。王小姐使劲嗅了嗅,笔者也跟着嗅了嗅,是地瓜甜甜的清香。王小姐说,上面的那户农民,截了一段地道做了地瓜窖。
其实,在战争年代,地道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发挥它的“民用功能”,甚至还演绎了一段“地道姻缘”。1938年,18岁的冉庄姑娘王新娥当了冉庄的妇救会主任。1942年,她被调到清苑县公安局,但仍在冉庄开展工作。当时的副局长李志也在冉庄开展工作,两人常常一起在王新娥家的地道里藏身,后来经张森林撮合结了婚。当时,张森林还作了一首诗:“地道长,情亦长,张某为君作红娘;待到东瀛败归日,再补喜酒和喜糖。”
人去留得英魂在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的地面建筑就建在烈士李连瑞的家中。李连瑞出身地主家庭,但积极抗日,日本鬼子进入冀中以后,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于1939年入党,任冉庄“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牺牲前,他曾动员父亲李老旗捐献抗日公粮,他们家一次就捐献3000斤小麦。1942年,李连瑞因叛徒告密,只身一人被100多鬼子和500多伪军包围,壮烈牺牲。
院落因为有新建的展厅而并不显大,院落内还保留着过去的几间老房。新修的展厅很宽敞,灯光明亮,展出的图片、模型等都很逼真。在所展实物中,有三件引起笔者的特别注意:一件是李连瑞烈士的血衣。衣是青灰色的土布上衣,血迹已成黑色。一件是张森林烈士的遗诗手稿复制品。发黄的毛边纸,书写着黑色的仇恨和光闪闪的豪情:“鳞伤遍体做徒囚,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一件是地下兵工厂自己制造的榆树大炮。表面看上去就是一段长约7尺直径1尺的榆树原木,细看就发现直直的那端截面正中有钢管。说是大炮,其实只是一个放大了的霰弹枪。
此外,还有缴获日军的94式山炮,以及当年农民用的织布机、群众为八路军“熨”军服用的大方石等物。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初建于1959年8月,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上级斥拨巨资重建,与各家各户签订保护旧居合同,保证200多处遗址、560余间房屋基本维持当年原貌。除地道外,老街道、关帝庙、武委会旧址等都保存得很好。
当年的武委会现存办公房两间,一张正桌朝门而设,两边两把椅子,一张小桌摆在另一侧山墙下,一个立柜摆在房屋一角。年久的木器虽然没有灰尘,但都星油黑色,显示着时间默默地努力。正桌上摆有一个断掉半截壶嘴的瓷茶壶,一个青花大瓷碗。吕正操将军当年曾经使用过这只青瓷大碗。
吕正操将军是冀中军区第一任司令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地群众在士绅带领下组织了“不抗日,不降日,防土匪,保村庄”的联庄会,为了团结群众共同抗日,1937年10月,吕正操领导人民自卫军第二团到清苑、蠡县、博野一带开展工作,决定收编这些“杂牌部队”。联庄会要求谈判,地点就是冉庄。1939年7月,冉庄遭敌人包围,损失惨重,吕正操又匆匆赶到,为群众打气,帮助大家重建家园。在吕正操演讲的过程中,全场欢声雷动,一个小伙子见吕司令员说得口干舌燥,就用这只青瓷大碗给他端了一碗水,吕正操一饮而尽。
这只碗在群众手里,只是一只普通的瓷碗,吕正操使用以后大家就尊称为“将军碗”;就像“耗子战”是当地群众的称呼,而“地道战”是组织上的定义一样。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民族的朴素,后者是一个政党的英明。称呼的背后,是一条从群众自发到党组织领导,从消极躲藏到积极反抗的必然之途。★
责任编辑:邢玉婧

祖国山河,不容侵犯(沙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