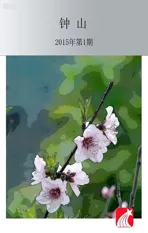为什么是“80后”?
2015-11-14甫跃辉
甫跃辉
“文学:我们的主张”主题讨论会上,范小青老师问,来参加笔会的,是否都在《钟山》杂志发表过作品?贾梦玮老师说,百分之九十九吧。范老师问,那百分之一是谁?我说是我。其实我想说,我是代表那些没在《钟山》发表过作品的广大写作者来参会的。是一家家杂志、一位位编辑,伴随我一直写作到今天。我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我写作从来只是遵从内心,不是为发表写,也不是为读者写——因为读者实在太少,我也不知道这读者在哪儿。但真的如此吗?若完全不发表,完全没读者,我还能一直写下去吗?写作是孤独的事业,但人都是脆弱的,绝对的孤独,是太难承受了。
所以,我们需要让写作变得热闹一些,比如,一堆写东西的人不时要聚一块儿聊聊,算是抱团取暖吧。我常听到人们——尤其年轻人谈论文学。说实在的,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了。因为差不多都是那么些话,都说的西方文学、哲学、历史。并不是说这些不好,但就只能说这些吗?它们让文学成为比较谁聪明和渊博的游戏。
我们这代人接触的书和信息很多,聪明和渊博,在某些时候,反倒不是最重要的。
我读同辈人的作品虽不算很多,但也不少,多数重要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今年,好多本重要刊物集中刊发“80后”的作品,我都找来看了。“出道”十多年了,“80后”仍旧被这些刊物当做“新人”对待,真是个奇迹。“80后”写作者一直被当做早熟的一代,多少人头顶“少年天才”的光环啊?!其实是特别晚熟的一代。或者说,我们被媒体和大众的“早熟”论骗了,反倒晚熟得厉害。以致“80后”写了这么多年,仍被当做“新人”,得到各种刊物的“优待”,作品即便不是很好,仍然可以因为“新人”的标签被发表。
为什么“80后”会这样?有两个原因或许比较重要:一是这代人有不少独生子女 (说“8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也是个带有迷惑性的提法。我曾经看到一个数据,“80后”中的独生子女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容易自认为“独一无二”;二是这代人完全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较好,能够比较早地开始写作,但很快就被商业利用了,进而让一些“80后”沉浸在“天才”的迷梦之中。“天才”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特别牛的作品么?
同样作为“80后”,让我说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80后”作品,一时还真说不出来——或许是我没读到?我把这几本刊物翻出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一篇一篇读下去。可如今,要问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我仍旧很难说出来。
我接着读了几篇关于“80后”的文章:李敬泽老师的《一种毁坏的文化逻辑》,王干老师的《80后作家的分化与渐熟》(《光明日报》2014年9月22日),徐妍老师的《文学生产机制视角下解读青年写作现象的新格局》(《上海文学》2014年第11期),以及同辈人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今天》2013 年秋季号),黄平、金理的对谈 《什么是80后文学?》(《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岳雯的《80后创作新观察:80后作家,文艺的一代》(《光明日报》2014年11月3日)。这几篇文章,在分析“80后”这一十多年来的重要文学现象时,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和我此前对几家刊物上“80后”作品的阅读印象也比较接近。
首先,假现实。几年前,不少人提倡“底层文学”。很多人赞同,也有很多人反对。我也不喜欢这提法。首先是怎么界定“底层”,其次是对所谓“底层”的书写,变得非常模式化,写来写去,村支书都是欺男霸女的,打工者都是极其悲惨的。“80后文学”多的不是“底层”叙事,而是 “校园叙事”、“青春叙事”、“文艺青年叙事”。随着“80后”纷纷告别校园,“校园叙事”算是偃旗息鼓了,后面两种叙事,尤其最后一种叙事却越来越大行其道。这些叙事和“底层”叙事其实有同样的毛病,读多了,也一样地觉出模式化。什么逃避城市到乡下隐居啊,什么妓女都是善良无辜的啊,哦,还有一路开着车到哪儿哪儿去朝圣啊……读多了这样的小说,再离开屋子到这世界上走走,会觉得这世界无比陌生。
岳雯说:“如果说50后试图介入社会政治,60后则回到了人性的领域;如果说70后的写作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楼阁之上,那么到了80后,他们将日常生活又推进了一下,也就是说,他们更在意的是被个人体验过了的现实,是精神现实。于是,现实呈现出更为精巧、幽微,也更为狭窄的图景。”“我将80后的创作特质归结为两个字:文艺。”在我看来,这是对“80后”的极大批评,绝非赞美。
其次,伪先锋。如果说活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们是向西方学习,我们现在不少所谓“先锋”小说,要么是继续向那些已经被学习过无数次的西方小说家学习,要么是向八十年代那些先锋作家学习。也就是说,要么继续做西方小说家的学生,要么做西方小说家的学生的学生。那些早就“先锋”过的东西,拿到现在来炒冷饭,还能算作“先锋”么?怕只能是“后锋”了吧?
近百年来,我们在文学上一直向西方学习,包括很多大作家。如今,年轻一代写作者仍旧如此。甚至于,我们不再向西方的大师级作家,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克纳等学习,而是向那些三四流作家学习。很少有年轻写作者谈论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和《海上花列传》等作品。我们的作品里,也很少看到这些作品的影子。这些作品真就过时了?这些从我们的土地上自然生发出来的作品,是否仍然存有再度先锋的可能呢?我们能否真正创造出适合于今日文学的最恰当形式?
在我看来,“先锋”文学就是为文学提供新的、最恰切的形式和内容的文学。但“80后”文学里,并没出现这样的作品。黄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文学发展构成发展的 ‘80后’作家还未出现”,实在是一针见血。
最后,真撒娇。这是让我最为失望的一点。有些“80后”写作者,缺乏直面自我的勇气,或者说,有勇气,但演技实在太好。这几年,“体制”成了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词汇。很多写作者在网络上批评“体制”,比如莫言获奖,就有人批评他是“体制内”作家。但那些批评的人呢?不少就是所谓“体制内”的人。事实上,没人能够脱离“体制”。“80后”写作者也有不少人做出反抗的姿态,在网络上表演,在作品中表演,仿佛这世界都在迫害他。然而呢?现实中“体制”带来的好处他们全没落下,他们不过是在跟他们“反抗”的对象“撒娇”。杨庆祥说:“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在对物质的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的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抵抗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抵抗社会的失败)?”这无疑是痛苦的,但只有看得见我们自身的黑暗,才有可能去寻找光明啊。
若我们连那个趋利避害的自我都不敢面对,谈何反抗?
若我们连真诚都做不到,谈何写作?
这三个印象,其实不光针对我看到的某些同代人的作品,也针对我自己。
回首自己近十年的写作,我越来越感觉到,实在没有哪一篇是值得一提的。到现在为止,我写出的所有作品都注定速朽。它们不是我期待的文学。通过它们,看不到这个巨变时代的疼痛和温暖,也看不到身处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我”。
是的,我想写出一个虽然卑微,但又巨大的“我”。
有人认为“80后”写作者特别自我,没能写出“广阔的世界”,就连小说的叙述者往往都是“我”。我不赞同这观点。文学本来就是自我的,作家的世界,都是作家看到的世界。没有“我”,哪里还有世界?这并非远离世界,相反,是更贴近世界。我们应该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有更深的认知。我可以去写农民工,写妓女,写战士,问题是,我为什么写他们?他们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只有把这关系弄清楚了,才有资格去书写他者。这也正是为什么我那么一再提起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这些人认为要写“广阔的世界”,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世界太精彩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都在发生。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家虚构?问题是,写作的好坏,并不是以情节是否奇特为衡量标准的啊。再者,虚构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奇怪”。虚构是小说家的根本,是小说家对世界的态度。为什么在小说里让一个人死,让另一个人活?对小说家来说,这是天大的问题。这里有对整个世界的全部绝望和希望。
今年我三十岁了,不再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了,应该好好看看自己,看看世界了。
“80后”是这大变革时代催生的怪胎,也是这大变革时代的最佳观察者。当我们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自己,看清楚我们的虚假、虚弱、虚伪、虚荣,以及这之后的挣扎、无奈、妥协和奋起,当我们能够直面这一切,并把这一切行诸文字,或许我们才能写出“时代中的80后”和“80后中的时代”。我相信,那样的作品将是最接近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