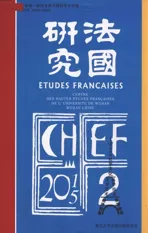中西方文化对程抱一“死亡观”的影响
2015-04-17刘天南
刘天南
中西方文化对程抱一“死亡观”的影响
刘天南
虽然在文艺创作中,作家与哲学家的界限有所区分,程抱一先生的文学语言却处处力显其人生哲学。旅法半个多世纪的他是法语文学界成功的文化摆渡人之一。熟谙中西方文化精髓,程抱一通过其文学作品成功地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在经历了大部头的文学艺术评论、小说、诗歌创作之后,晚年程抱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对“死亡”的思考上,而这一初衷是为了通过“死亡”来探寻生命的意义。观其作品与语言,西方“俄耳甫斯之道”与东方的佛教禅学,道家的生死观与基督教的生死观对其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超越死亡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成了他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程抱一 死亡观
[Résumé]Bien que les frontières entre les écrivains et les philosophes soient évidentes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le langage littéraire de François Cheng fait pourtant preuve de sa pensée philosophique. Grâce à ses expériences de vie en France pendant plus d’un demi-siècle, il est devenu aujourd’hui l’un des passeurs de culture les plus connus du domain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 En tant que grand connaisseur des meilleures parts de la culture occidentale et orientale, il a pu réussir une création littéraire qui fait lien entre les deux cultures. Aujourd’hui, écrivain du troisième âge et fécond en nombreux ouvrages essayistes, romanesques et poétiques, François Cheng consacre davantage son temps à la méditation sur la mort, dont l’intention est de quêter le sens de la vie à travers ses réflexions. L’ensemble de ses œuvres littéraires révèlent donc de multiples influences profondes qu’elles ont subies : la voie orphique, le chan, le bouddhisme, le concept de la mort du taoïsme et du christianisme. Ainsi, « poursuivre le sens de l’existence tout en dépassant la mort » constitue sa quête de vie inlassable.
引言
死亡,本该是大多数活着的人需要避讳的话题,程抱一[1]程抱一先生原名程纪贤,1929年生于大学教师家庭,1949年通过其父亲在联合国教科文工作的关系,获得一份奖学金,随后赴法国留学。1969年在巴黎高等社会实践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中国古代诗词,同时从事中国美学和中国古典绘画研究。他一生笔耕不辍,早期主要从事西方传统诗词翻译,40岁开始用法文创作,此后依次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古诗词、绘画、美学等方面的著作。晚年的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歌和杂文随笔创作上,这些作品也更多侧重对哲学性问题探讨,尤其是对死亡的思考上。先生却毫无忌讳地在其作品乃至平常的交谈中频频谈及。他本以为自己最多能活到二十岁,然而今天却“不经意”活到了一个意外地高龄,他的阅历和人生体验,他的沉思与领悟以及他中西贯通的学识足以让他轻松畅谈“死亡”。
继2008年出版了《对美的五次沉思》之后,程抱一先生又于2013年完成了《对死亡的五次沉思——或者说对生命的思考》[2]以下中文简称《对死亡的五次沉思》。这部作品是七年前作者与一群朋友通过五个难忘的夜晚交谈的结果。七年之后,年达84 岁高龄的他深刻感到用文字系统地表达当晚谈论结果的迫切性,因为作者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他单纯地把自己关在工作室对某一主题进行专门性研究是不够的,而生命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交流。因此同《对美的五次沉思》的诞生一样,《对死亡的五次沉思》也是作者与其朋友在国家瑜伽联盟会大厦热情交流的结果。见原著F. Cheng,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mort, autrement dit sur la vie, Albin Michel, 2013, P.8, Avant-propos de l’éditeur. 及音频材料 France Culture,Ça rime à quoi, François Cheng, Première méditation, par Sophie Naulau. 2013。这部作品很好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完美结合,也体现了作者思想的升华。事实上,“死亡”这一主题在程抱一先生各类文学作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这一部新作则以更加系统和睿智的方式对“死亡”或者说对“生命”进行了论述。他笔下的“死亡”,有着西方俄耳甫斯式的感性,也有着东方哲学的沉稳,同时还始终敏锐地畅游在西方基督教和中国道家思想中。
一、“俄耳甫斯之道”与里尔克[3]赖内.玛丽娅.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著名德语诗人、作家。1875年生于布拉格,1926年卒于瑞士。大学攻读哲学、艺术和文学史。1897年始怀着孤独的心境周游欧洲各国,期间给法国雕塑大师罗丹当过秘书,诗歌创作受波德莱尔等的影响。1919年侨居瑞士。其诗歌深受法国人欢迎。其代表诗篇为《杜伊诺哀歌》(1922),《俄耳甫斯十四行诗》(1922),散文《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1903-1908),《论罗丹》(1903)等。对程抱一的启发
(1)程抱一对“俄耳甫斯之道”的新发现
诗的心声始终贯穿于程抱一先生的作品和思想当中。西方诗歌艺术的传统也深深浸染着作者的创作思维: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到浪漫主义时代的英国雪莱、德国的歌德,以及法国的拉马丁、波德莱尔、兰波,一直到现当代诗人,都对程抱一先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而“俄耳甫斯”诗歌程抱一先生在早年的学习中注意到的一种西方古典诗歌艺术抒情诗体。俄耳甫斯首先源于古希腊的神话故事[4]俄耳甫斯是古希腊著名诗人和歌手,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有一天他情投意合的未婚妻与众仙女在田野间玩耍时不幸被毒蛇咬死,俄耳甫斯伤心欲绝,一心要把未婚妻带回人间。他凭借其非凡的音乐才能闯入地狱,冥王怜惜其才能,答应了俄耳甫斯的请求,但要求其在返回人间途中,不准回头看其未婚妻,否则她将永远不能返回人间。俄耳甫斯答应了冥王的要求。不幸的是,在返回途中,由于未婚妻伤口疼痛难忍而抱怨未婚夫的无情,俄耳甫斯忘了冥王的叮嘱,回头拥抱未婚妻,结果未婚妻瞬间被地狱魔爪抓走,从此俄耳甫斯独自返回人间,郁郁寡欢,终日酗酒。后来由于不敬酒神而被杀死并碎尸人间。其头颅被漂流到列斯波斯岛,随后这里变成了抒情诗的故乡。,他把该故事与佛教故事“目连救母[5]目连母亲生前无恶不作,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尽地狱百般折磨。目连不忍母亲遭受地狱之灾,终日祈福并诚心行善替母赎罪,最终感动阎王,答应目连将其母亲带回人间。”联系在一起。两者虽然主题不一样,但故事情节有很多的相似性。“俄耳甫斯”神话后来发展成为西方的传统抒情诗歌最重要的风格之一。程抱一因为崇尚俄耳甫斯之精神,喜欢俄耳甫斯式文风,因此把这一风格命名为“俄耳甫斯之道[6]程抱一将“俄耳甫斯之道”译为“La voie orphique””。这种说法也是程抱一先生的首创。称其“道”,显然也是居于对这种诗体的欣赏与向往。
程抱一还发现,俄耳甫斯神话人物与中国的爱国诗人屈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几乎被作者化为等号:他们分别是东西方抒情诗人的鼻祖,两者都有着壮烈的英雄事迹,而前者的思想发展脉络也与佛教的禅学高度一致。程抱一通过早年对西方传统诗歌艺术专研,对这种抒情诗体风格非常熟悉,并发现俄耳甫斯诗歌中借物言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表现手法高度一致。此后在他自己的抒情诗歌创作中,似乎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西方艺术传统,哪些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传统。如在程抱一早期的诗集《树木和岩石》中,就采用了这种中西合璧式的创作方法:
岩石说:
你寻找火焰,它就在这儿
你寻找源泉,它也在这儿
你寻找地方,它也在这儿
叶丛,阳光
在黏土中的金子与影子之间
空气中永恒的宁静
将瞬间的存在凝固[7]笔者的翻译,原文见F. Cheng, À l’orient de tout, Paris : Gallimard, 2005, p.30.
(2)里尔克对程抱一的影响
而在纷繁的西方诗歌艺术传统和众多的伟大诗人当中,奥地利诗人里尔克[8]程抱一早年就为里尔克写了一些散文,如《和亚丁谈里尔克》(台湾纯文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在其《法国七人诗选》中也翻译了里尔克的诗篇。是对他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位。在作者看来,与里尔克的“结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里尔克本人就是一位俄耳甫斯风格诗人,程抱一先生从自己身上也找到与里尔克的作家情感、思想和敏感性上的契合点。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程抱一先生承认自己深受里尔克这位伟大诗人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创作主题上。里尔克的作品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死亡”的思考。程抱一也认为死亡是人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死亡,生命将会变成乏味的重复或者是一种无意义的延长。正因为有死亡的存在,人们才会永不停息地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改变和升华自己。”
虽然有一段时间作者曾尝试远离里尔克的影响,但是谈到对“死亡”的理解上,作者又不得不回到里尔克这边。“所有的诗人都应该面对死亡的这个主题,但是对里尔克而言,‘死亡’则已经构成了他生命的主题。”因为里尔克曾吟唱道:“主啊,请赐给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死亡”。而这一诗句也多次被程抱一先生引用。在其《对死亡的五次沉思》中,里尔克的大段诗章被直接引用,以引证程抱一自己对死亡的理解:因为人生的短暂性促使人有活着的紧迫感,并且因为死亡的意识促使个人希望在有生之年作出一些事迹。为此,“死亡”成为程抱一先生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这种对“死亡”的思考也应源于里尔克对他的启发:
“主啊,请赐给每个人他自己的死亡
这个死亡来自于生命,
在生命有它的爱,意义和绝望”
因为我们只是树叶和树皮,
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死亡
则是让一切改变的果实。
[……][9]笔者的翻译,是程抱一引用的里尔克诗篇,原文见F. Cheng, Cinq méditations sur la mort, autrement dit sur la vie, Albin Michel, 2013, p.25. 后文凡出自本作品的引文,将并简写为“F.Cheng, 2013,页码” 并随文标明。
从这一首诗中,程抱一先生注意到里尔克对于生死循环的认识与道家的生死观一致:如果说死亡是果实,那么果实落地,借助土壤,或重新生根发芽,重获新生。因此土壤成为生和死的共同源泉。这种循环也是一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轮回。这一领悟也是程抱一先生的重大发现。因为他发现里尔克的生死观与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关于道德循环的论述相对应[10]早年程抱一刚到法国不久,就去法兰西讲学院听汉学家Paul Demiéville的汉学课,由于他较早接触了里尔克的作品,因此在当时的课堂上他敢于主动向这位著名的汉学大师阐述了道家学说与里尔克的思想高度巧合一致性。可以说这也是程抱一内心对里尔克的一种“感激之情”。而事实上,里尔克从来未曾接触过道家思想,但程抱一发现了中西方在哲学思考上的高度一致性。而这一发现也曾经成为程抱一先生人生的转折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程抱一译文为: “ Telle est la mère de l’univers./ Dépourvue de nom, je l’appelle Voie,/ Faute d’autres mots, je la dis grande. / Grandeur signifie étendue, /Etendue signifie éloignement, / Atteindre au loin et effectuer le retour. ”。”以及《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12]程抱一译文为:“ Retour, le mouvement de la Voie, / Faiblesse, la loi de son usage, / Toutes choses naissent de ce qui est, / Ce qui est de ce qui n’est pas.”。”(F.Cheng,p.27-28)
受里尔克的启发,他学会了正面这一主题,并且在自己的诗歌中抒发了对死亡的超越:
“死亡不是我们的出路
因为比我们更伟大的是我们的欲望
连接着初始的欲望
生命的欲望
[……]
死亡不是我们的出路,
它只是确定一个极限,
告知我们尽头,
告知生命的要求,
给予,升华,盛开,超越。” (F.Cheng,)
(3)借助俄耳甫斯传统,抒发对“死亡”的见解
不可否认,里尔克同时也是程抱一先生创作俄耳甫斯风格诗歌的启蒙老师。俄耳甫斯故事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诗人里尔克写的《俄耳甫斯十四行诗》[13]《俄耳甫斯十四行诗》是由里尔克在1922年写的55首短小十四行诗的组诗,次年首次发表。里尔克也因此事被公认为最负盛名的德语抒情诗人之一。他的55首短诗仅在三个星期内就完成了,而灵感主要产生于他女儿的玩伴Wera Ouckama Knoop (1900-1919)的突然离世。同年,里尔克也完成了最富哲学和神秘色彩的诗集《杜伊诺哀歌》。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里尔克最重要的代表作。程抱一也注意到了在这部十四行短时中里尔克提到的类似道家的气韵。。程抱一钟情于这种诗体,不仅因为它的抒情性,还因为它能给作者带来丰富而即发的灵感。里尔克先生提出的“双重王国[14]双重王国法文为“Double royaume”。”——即生与死的双重维度,被程抱一完全接受并引用。程抱一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的诗歌都是俄耳甫斯式的。这种风格已经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参照。因此自己的事做也充分体现了俄耳甫斯式情怀。
“已经历过的,会再次回到梦中,
出现在梦中的,获得重生。
我们没有太多的长夜,
悄悄地去焚烧掉落的残枝,
去储存焚烧后的持久余香[15]笔者的翻译,来自原文: “ce qui a été vécu, sera rêvé, et ce qui a été rêvé, revécu. Nous n’aurons pas trop de longue nuit, pour brûler les branches tombées à notre insu, pour engranger l’odeur durable des fumées.” F. Cheng, Vraie lumière née de vraie nuit, Éditions du Cerf, 2009. 以下凡出自本作品的引文将随文简写标明:“F. Cheng, 2009, 页码”。”
上述诗歌通过“梦境、长夜、残枝、余香”表达了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残枝”是否就意味着风烛残年?余香是否又意味着精神和灵魂的永垂?事实上,文章一经发表,作者便几乎同时失去了解释的权利,而读者,也可以根据他们阅读时的不同心境和知识面作出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论何种理解,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往事追忆和对生命永恒的追随。
程抱一认为,俄耳甫斯式诗歌的价值,还在于它通过抒情的方式引起共鸣的特质,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共鸣使人类能够超越对死亡的限制,从而跨过死亡重新回到被隐藏的生命的原点,这就是所谓的“道”。从下列两位诗人的诗歌比较中便可以发现,程抱一对“道”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能看到里尔克的影子:
程抱一诗歌:
[……]
听我们说说吧
为了让你我之间融合在一起声音,
出现于短暂夏日的颂歌,
建立起一个王国。”
[……]
(我们听从)
那些回来就不再离开的,
回来就消失在暮色中的,
每一颗消失在夜晚的星星,
每一滴风干在夜晚的泪水,
一生中的每一个夜晚,
一个非凡夜晚的每一分钟,
因为在这一夜,
所有的一切在重逢,
被遗忘的私生活,
被废止的死亡。”(本人译文,原文见F.Cheng,)
再试着比较一下里尔克的《俄耳甫斯十四行诗》:
“只有那个提起里拉琴并置身于阴影处的人
才能演奏出无尽的赞歌。
只有那些和死去的人一起吃过罂粟的人,才知道戒毒,
而这只不过是一首最轻的插曲。
池塘中的倒影在我们眼中常常变得混浊,但只有它认识影子的原型,
终于在双重王国中,声音变得温柔而永恒。”
(本人译文,原文见F.Cheng, 2013 : p.31)
两首诗中的“双重王国”都是指“生”和“死”的两种境界,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中心主题一致。通过俄耳甫斯风格的诗歌以及里尔克的启发,作者最后提出死亡体现了我们作为个体最内在的、最隐蔽、最秘密,并且最为私人的一面。但这也是与生命紧密连在一起的必要部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直视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不如直视生命,从生命来反观死亡。因此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那么我们的一切行为和方向都将朝着生命的激情奔放。由此程抱一建议:从生命角度去凝视死亡,从死亡角度去预见生命。
二、基督教死亡观、禅宗“虚无观”与道家死亡观对程抱一的影响
(1)基督教死亡观、俄耳甫斯与禅宗的“虚无”观的契合
“如果没有基督,我终将是一个儒学者”。程抱一如实回答记者关于“基督教在作者心目中的意义”。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种信念主要来源于基督教将世间的罪恶与痛苦全部转化为大爱。而也正是基督教帮助作者解开了对爱与死亡的关系的理解[16]程抱一对基督教的爱的表达:“没有爱,任何一种欢乐都不能达到其真正完美的境界;而有了爱,肉体、精神和灵魂才能真正地融合在一起。”“也因为有了爱,死亡变得不仅仅只是生命终结的一种迹象,而更应该是至爱的一种体现。因为有了爱,死亡的性质和境界也随之发生改变,死亡变成了一条真正通向质变和重生的阳光大道。” (F.Cheng, 2013 : p.70,p.123),因为他十分认同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人死后,只有在被上帝“评判”合格之后才有资格获得“重生”,并且因为有“大爱”的存在,人死后其肉体和灵魂都会被爱所拯救。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从柏拉图时代便已经获得认同,并且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也得到大力的弘扬,至少盛行至十八世纪。直至今天,受无神论的影响,“灵魂不死”的观念才逐渐被系统地批判。但是基督教和俄耳甫斯均更加强调“死亡”这一必不可少的过程。程抱一先生对待死亡的思考也体现了这种精神:
“死亡的美,就在于它的存在。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被爱着的灵魂的存在,它在面对我们泪眼始终微笑。被哭泣的人消失了,却始终没有离开。我们再也不望见他/她那张曾经温和的脸,但我们仍然能感觉到受他/她的保护。逝去的人是那些再也看不见的人,但他们却不属于不存在的人。”(本人译文,原文详见F.Cheng,)
在作者看来,基督教与俄耳甫斯之道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两者都是西方传统文化之根基,尤其是传统诗歌文化最为重要的源泉。俄耳甫斯通过其化身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授予神品,借助大自然来抒发人的情感。而在早期的西方宗教作品中,绘画与诗歌也同样是通过大自然的意境、情景来体现人的情感。二者几乎被作者认定是同一体的关系。
此外,基督教和俄耳甫斯同时还跟东方文化有着许多的共性。如俄耳甫斯与禅宗的关系则体现在他们“虚无”或“不可见”的共同特点上。禅宗主张通过“非存在”与“非隐现”来达到真正的“存在”与真正的“预知”,这一点与西方的俄耳甫斯精神相通。作为中国古典诗词方面的研究专家,程抱一尤其推崇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因为它们正好体现了俄耳甫斯式的通过“不存在”来感知“存在”,通过“不见”来看“见”,通过“不言”来理解“言”,正如他所引用的《辛夷坞》以及《鹿柴》两篇五言绝句:
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本人译文,原文详见F.Cheng,)
第一篇《辛夷坞》中描写的场景清无一人,但是山间美景和芳华尽收眼帘,而被景色包围的诗人已然忘了自己的存在,正是这种“忘我”使诗篇的内涵获得非凡的意境。作者认为在面对“死亡”上,也应该只有通过这种“忘我”的方式才能真正进入升华的境界,使死亡转化为重生。第二篇《鹿柴》则是通过听觉来描写诗人那种“空灵”的感觉,颔联出句中的“返景”为夕阳返照,而在生命意义上,则被作者看作是一种生命的回光返照。由此作者建议诗人应当像俄耳甫斯那样只需回头看看日落的夕阳,因为它照亮着内心最深处的东西:“青苔”,指引我们回归到原始的存在。
(2)道家死亡观
然而在程抱一的信仰中,基督教并不是唯一。深受道家思想熏陶的他,在其创作中,始终不离道家学说的根源。首先,受《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启发,程抱一在其多部作品中均极力推崇:“生生不息[17]程抱一将“生生不息”译为:La vie engendre la vie, et il n’y aura pas de fin.”的观念。在其小说《此情可待》中,他引用了道家思想关于死亡的解释:“道家深信灵魂不会消失,因为在每个人死后,他的灵魂都将进入所谓的‘道’。由于‘道’是一直存在的,所以灵魂也不会消失。为了达到这样的‘道’所以每个人都应经历死亡[18]本人译文。原文为:“ Que les taoïstes croient que l’âme ne périt pas, c’est parce que, selon eux, après la mort de chacun, son âme réintègre la Voie. Comme la Voie dure toujours, l’âme non plus ne périt pas. Ça se comprend. N’empêche que chacun doit mourir. ” François Cheng, L’éternité n’est pas de trop, Albin Michel,2002, livre de poche, p.134.。”
因此,在道家看来,只有肉体会死亡,灵魂是永远不会死亡的。灵魂中明亮的部分将升天,暗淡的部分将入地。道家的“道”便成了超越死亡的一种方式,而所有被爱的生命都可以各自形成一种“道”,这种道既颂扬了真正的生命,又超越了死亡。作者对佛教关于死亡的解读也有一些了解:佛教更加强调“化身”和“来世”,在不否认肉体的死亡的同时,将这种复活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肉体身上,以实现来世的生活。道教与佛教的共同点在于两者均祈求在肉体死后,灵魂有一个最终的归宿,而不至于迷失或流离。道家学说中强调的“化”也正与程抱一先生多处提到的“升华”一致。只有像道家那样,将人的生老病死的系列变化看作是整个大宇宙变化的一部分,是宇宙自然规律的组成部分,才能更为正确地看待死亡,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心理。
(3)中西方文化的内在升华:程抱一对“道”与“灵魂”的解释
跨越于两种文化之间,熟谙两种文化的根基,程抱一巧妙地将基督教和道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主张,即对“道”和“灵魂”的独特解释。
“道”在汉语中,既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作为名词是“道路”,作为动词是“说”。而在法语中,程抱一有幸找到了两个同音异义词:“voie”和“voix”,饶有趣味的是,前者正好可译为“道路”的“道”,后者可以译为“说话”的“道”(语言,声音,歌唱)。这更进一步帮助程抱一推演出:通过“语言”接近“道”的重要性。即通过语言达到思想和行为的升华。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则更多地是通过其诗歌创作,以精炼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所思所想,引起读者的深度共鸣。作者理解的“道”是所有生命体的被导向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充满变化的道路。而人的变化也是大宇宙变化的一部分。
同样,“灵魂”在古往今来的中华文化中并不陌生,但是在今天的西方文化中却显得“过时”。因为今天的西方人们谈得更多的是精神,民主和人道主义等。程抱一先生却不遗余力地在不同场合,不同作品中畅谈和颂扬“灵魂”。
“肉体、精神和灵魂”仍然被程抱一认为是人的三个组成部分。肉体和精神不容易被忽视,然而“灵魂”作为每个个体最高的境界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其实唯有“灵魂”才是最能体现个体“唯一性”的因素,而“精神”体现的是一种普遍和集体式的因素。因此作者利用法语文字游戏,总结出:“精神活动,灵魂激动;精神推论,灵魂回荡。”“精神应朝着共鸣的方向去推理,灵魂则因推理而共鸣[19]本人译文,原文为:“L’esprit raisonne selon la résonnance, et l’âme résonne selon la raisonnance.”(F.Cheng, 2013 : p.73);“L’esprit se meut, l’âme s’émeut ; l’esprit raisonne, l’âme résonne. ” (F.Cheng, 2013 : p.72)。”因为灵魂是人存在的最秘密,最亲密,并且是最不容易意识到的一部分。灵魂是人的最高境界,而共鸣则可以使灵魂通向宇宙。
程抱一认为:不论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三重境界:“肉体——精神——圣爱”还是道家学说中的三元论“人——地——天”至“道”或者说“阴气——阳气——中气”都应当承认生命包含多重境界,并且人类的命运最终不能仅仅局限在肉体的生命上。“灵魂”是生命的低音符,这种低音符与灵魂一样,伴随着人的出生至死亡,一直在回荡。如果说精神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发生改变,灵魂则如同低音符那样不易改变并始终回荡着乐曲。中国传统文化喜欢与大自然,大宇宙对话,以至于体现在文学和绘画艺术中,也是一种从灵魂到灵魂,从吟唱到吟唱,从低音符到低音符的节奏,逐步将人引入共鸣的境界。程抱一的诗歌也体现了这种对生命低音符的吟唱:
“歌唱,就是这样唱!歌唱,不就是为了有歌声回荡?
还有什么在回荡?是生命么?
歌唱,真的歌唱,以接近生命的呼唤,这才是真正的存在!
兴许在偶然的机遇,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宇宙间的一颗激动的心,一只机灵的眼?
呼吸着生命的气息,忘却生命的极限、呼唤着颂歌,朝着更高,更明亮的地方,载着未满足的欲望直到永恒的边界。” (本人译文,原文详见F.Cheng,p.167)
三、透过死亡看生命,争做“生命诗人”
(1)争做“生命诗人”
深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的他,不论在作品还是节目访谈中均能让人深刻感知其极度谦虚的态度。然而在给自己身份界定的问题上,程抱一先生从来都欣然接受“诗人”这一头衔,不但如此,还常常自我封为“生命诗人”,并宣称自己要“诗人式死亡”[20]“生命诗人”:un poète de l’être;“诗人式死亡”:mourir en poète。。
“生命诗人”是指作为一名诗人,他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自己情感和感觉的抒发,而应该更加重视通过诗歌创作来质问在这个大宇宙中生命的神秘性。而探索生命秘密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经验去设法接近真实。对“经验”与“真实”的探索对作者而言是密不可分的。他在诗歌创作中对死亡的沉思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更好看透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作者对死亡的五次沉思的初衷。
“诗人式死亡”并不是说以浪漫或诗意化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始终带着一种“声音”走到生命的尽头。这里的“声音”来自于生命的平凡,敢于直面死亡,并力争使这种“声音”产生共鸣,超越死亡,最后与生命中被隐藏的源泉[21]这里的“生命中被隐藏的源泉”应指“重生”,“升华”或者是死后的另一种“生命秩序”。汇合(F. Cheng, 200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抱一认为所有的真正的诗歌都应该是俄耳甫斯式的,即所有的诗人都应该正面“死亡”这一主题,将“死亡”融入至其创作视野,并且通过诗的语言超越死亡。
(2)通向“生命诗人”的方式
那么,如何超越死亡,如何成为真正的“生命诗人”,如何真正能以“诗人式”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程抱一先生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积极阳光向上的。纵观其作品和思想,我们看出:渴望的意念、激情、交流和对话成为其超脱死亡的重要方式。
首先是对生命的渴望,对实现人生意义的渴望。“死亡不是我们的出路,因为比我们更强大的是我们的意念,这种意念与生命的初始紧密相连,这就是对生命的渴望[22]本人译文,原文为: “La mort n’est point notre issue,/ Car plus grand que nous /Est notre désir, lequel rejoint / Celui du commencement, /Désir de vie.”。”程抱一认为人类的存在并不是一场盲目的旅行,没有目标和企图,它也不会关上变化或超越的大门;相反,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布满了各种符号和朝向,因此人的存在是充满了渴望的意念和生命的冲动的,人朝着某个方向前进,他/她的存在也因此变得有意义。“如果说生命是短暂的昙花一现,那么经历过昙花一现生命的这个事实便成为了永恒。”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生命和实现人生意义渴望的意念,才会不畏生活中的艰难险阻,不管是经历痛苦还是欢乐,这些经验都会让我们更加接近最为真实的生活的本质。正如夏多布里昂说的:“道德是通过‘死亡’来体现生命的意义的”。
其次是要对生命充满激情。而激情源于对死亡的意识。激情可以使我们走出生命的平凡。因为知道生命终归要走向死亡,因此就有了关心社会的激情,冒险的激情,成为英雄的激情和爱情的激情……死亡对于作者而言,已经成为其生命中最大的源动力。在其职业生涯中,他深刻理解激情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关系。如果说激情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动力,那么死亡也与文学艺术不可分离。因为所有的艺术家都需要满足对“美”的要求,但他们同时也需要应对来自死亡的挑战。艺术家之所以孜孜不倦,竭尽全力挖掘自己的艺术才能就是因为人类无法逃避躯体死亡的命运。因此所有被称为艺术的东西:诗歌、音乐、绘画、雕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有形的艺术作品试图将孤独开化,将痛苦分解,将哭喊旋律化,以美妙的旋律超越生死离别之痛楚。
再次是通过交流和对话实现生命的意义,并始终不离人道主义思想。程抱一先生认为,交流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只有通过交流才能获得思想的升华。“死亡是必然的,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预知死亡的具体日期和时间,这使得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确定。然而现在能确定我们都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共享诚挚交流的幸福。”他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最终也是来自于相遇、交流和分享。而纵观其所有文学作品,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中西方文化精华的对话。也正是通过交流,程抱一在《对死亡的五次沉思》中充分表达了其人道主义思想: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一些基本禁忌,其中一条便是禁止乱伦,但是‘你不能杀人’却成为最为核心的禁忌。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三十年之后,我听到了“禁止‘禁止’”的声音,这让我感到害怕。不合理或者镇压式的禁止固然是要反对的,但是如果完全撇除任何界线,那么文明与野蛮的将没有了区别。事实恰恰是因为有了法律人才有了相对的自由,而不能随其胡作非为。” (本人译文,原文详见F.Cheng,)
“没有敬畏心理的世界将是一个混沌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要承认最为基本的神圣之物——生命。由此可以认定每个人的死亡也是神圣的。而丑陋的死亡,则会成为一个不可轮回的果实。因此所有的罪行在侵犯受害者肉体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自己死亡的权利。大规模的罪行则是反人道主义的。” (本人译文,原文详见F.Cheng,)
结语
简而言之,生命是一种馈赠。程抱一认为,死亡不应该成为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结,相反,它的不可避免性正好使我们更好地看清生命的意义:生命并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生命的一部分。生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而应该看作是一个奇特和神圣的赠予,他们使我们鼓足勇气使自己变得更加唯一。正如马尔罗所言:“生命不值任何东西,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值生命”,“死亡将生命转化为命运”。
生命是一颗果实。透过死亡看生命,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死亡不应被看做是一种荒诞的终结,而是我们命运的一颗果实。这种果实不但意味着大圆满,也蕴含着重生的可能性。因为在汉语中,“果实”是指包含着精华和种子的包裹物,这与圆满结局与重获新生是一致的。纵观程抱一先生的死亡观,他的文章始终围绕的是死亡的“意识”,而并不是死亡“本身”。这里不是对死亡的颂歌,而是通过对死亡的透视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圆满。
(责任编辑:许可)
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