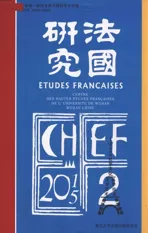亚洲职场上的文化碰撞(二)讨论:Bernard Ganne 与吴泓缈
2015-04-17翻译朱钰珏
翻译:朱钰珏
亚洲职场上的文化碰撞(二)讨论:Bernard Ganne 与吴泓缈
翻译:朱钰珏
译者单位:武汉大学外语学院
障碍与误解
2.2. 群体关系
视频开始:
甄女士:在中国文化里,中国员工不会主动去提什么问题,说什么“不,我认为还是换一种方式为好”。在对老板保持尊重的前提下更好的完成一项工作。在人事管理上,这一点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很小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一套中国式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们从不鼓励你提问题,而是要求你守纪律。我就从未想到过要与别人不一样,这就是管理中国员工时遇到的最大问题。
视频结束
讨论,不同文化视角的交锋
BG : 在某种方式上,她的说法对前面是一种补充。不过她将其归诸于文化,按她的说法,是你们在成长与学习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于遵守纪律而不是发明创造;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样,发明被视为犯规。
吴泓缈 : “发明被视为犯规”,这说法我不敢苟同。
BG :嘿嘿,这是我的说法。
吴泓缈:请原谅我直来直去。
BG :没关系,没关系。
吴泓缈:上边的现象涉及到好几个方面。其实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边学习一边长大成人。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学习过程或曰长大过程呢?社会和家庭向他的头脑中灌输各种观念和编码,他逐渐学会掌握和应用这些概念和编码。当然,这个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重复。一个小孩如何学习说话?就是不断重复,通过重复就可以良好地掌握一门语言,一些社会和文化规范也会在学习过程中根深蒂固地记在脑中。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分岔点:倘若一个小孩突然表现得格外与众不同,他是受到惩罚还是受到鼓励?有些东西,在不同文化中的确是有所不同的。通常来说法国人倾向于鼓励孩子的这一面,只要这差异未伤及到他人利益;在中国,我不认为会这样。在中国,差异可以被视为——从好的、积极的一面来说——是一种顽皮,但当人岁数越来越大时,就不允许顽皮了,因为顽皮是儿童的专利。
BG :它可能对群体构成威胁?
吴泓缈:当然。有时候差异可能被阐释为一种反叛,反抗,一种破坏性力量,于是社会会予以惩罚。由于常常受到类似惩罚,我们无意识中便会生成一种自动管制器;久而久之,我们再也不善于发表不同意见,不善于表现得与众不同了。你知道,如果所有个体都相互雷同,没有差异,那么世界就会变得,不知这样说是不是过分,就会变得一片死寂。
BG : 是的,这是一种重集体轻个体的构建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极端依附于集体,集体的规范居于优先地位。
吴泓缈:在第一阶段,也就是牙牙学语阶段,肯定会有这种反复灌输各种规矩、各种文化编码的倾向。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必要的。但在这必要性中,我们应容许一些差异的存在,因为当这个阶段完成时,一个小动物就彻底成为了一个人。到那时,我想要成其为我就必须与他人不同,我之所以为我就在于我的标新立异和创新。因此在学习的开始阶段,有了对差异的宽容,或者我用一个比宽容更厉害的词,即鼓励,对差异的鼓励,对下一阶段的创造力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一种文化是这样的,那么其民族必将充满创造力;反之,如果一种文化遏制并窒息差异和创造力,那么它很难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BG : 是的,我发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种模式,两种相互对立的模式。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内敛,但问题也许是有些缺乏创造力;另一个注重培养独立的人格,或者说它通过个体的多样性来建构社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吴泓缈:因此我想到了物理学中“熵”的概念。
BG : 怎么讲?
吴泓缈 : 我认为熵这个概念很好的描述了上述状况。一个好的世界当然应该有良好的秩序,如果没有秩序,到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杂乱无章,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恐怖的事。
BG : 难以生存。
吴泓缈:是的,难以生存。但这世界上的个体如果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世界离毁灭就不远了,处在毁灭的边缘了。一端是完全无序,另一端是完全雷同,彻底消除差异,这两种极端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熵的极大化,是一回事,是死亡。当然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分寸,一个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最佳点。有哪种文化有可能自动地找到自己的最佳点吗?
BG : 是的,就是说个性不极度膨胀贻害集体性,反之亦然,集体性也不极度膨胀贻害个性。
吴泓缈:说得太对了。
障碍与误解
2.3. 工作关系
BG : 我们继续观看我们拍摄到的日常难题。这是一位法国年轻工程师在企业实习的经历。该企业在中国,她的这段经历很短,仅有两个月。
视频开始(工厂会议场景):
法国工程师: Ok,现在放下样品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谈谈主设备的交货期限。你们也清楚,有好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最最要紧的就是排风机,周一的会议上你们说X011和X021型排风机这周到货。可今天已经周四,请问你们作何解释?
中国企业家:关于设备的交付问题,我们不想做任何解释,但明天设备一定到达场地。
法国工程师:这样的保证我听得太多了,实在是太多了。我希望明天它们真的能到!
琼斯小姐,法国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实习工程师:平日里与中国人打交道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但与他们一起工作却相当困难。也就是说……你不能让他们没面子。要小心翼翼,最好不要当面说一个中国人的工作没做好,这对我们而言真的很难……我们不能当面说他有错,即使在讨论中我们不赞成他也不行。所以每次讨论我们都小心翼翼,用词委婉,生怕说了什么有伤他的自尊。你不能让他面子上过不去,因为丢面子对他来说是场大灾难,然后他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在工作上再也不配合:所以和他们一起工作真的很难。我们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来讨论,来慢慢地说服他,最后让他觉得是自己在拿主意…… 随便举个例子吧,所有的技术解决方法我们都可以直接提供给中国人,但他们总是要自己去找一个解决方案。很多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于是我们又拼命地去把时间赶回来,而当你的工程项目工期比较紧迫时,你就很难时时处处保持冷静了。最难的就是保持冷静。
视频结束
讨论,不同文化视角的交锋
BG :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看法,相当直言不讳。我以为,她的谈话内容表达了在与中国人共事时首先遇到的确实存在的沟通难的问题。她试着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解释这件事,所以将其部分地归咎于所谓的“中国人爱面子”。我以为她还明白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件好事。因为方法不可能死记硬背,不是说你一告诉人家人家就能学会,有时候过分生硬地要人家按自己说的方法做,会伤人自尊,结果最后什么事也做不成。
吴泓缈: 关于“面子”,中国法语界已有一些反思。广外的郑立华先生曾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他还有一本书,关键词之一也是“面子”。我曾经很想比较一下中国的“面子”和西方的“荣誉”这两个概念,但实际上尚未做过深入的研究,所以只能是顺便提一下。面子和荣誉显然不是一回事,简单地说,面子只涉及到外表,是外在而非内在,所以与本质存在是相对立的。这方面确有一些可深挖的东西。对此我只能点到为止。
BG : 你说的这些,我觉得太重要了。的确如此,法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如 Ph. D'Iribarne就认为法国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荣誉的逻辑”,并说如果不参照荣誉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理解许多行为。通过观察和研究,他发现在企业中,人们特别倾向于坚持某种态度,如果你攻击这种态度,那就是人身攻击,就是否定我的本质,我当然无法忍受。我想荣誉和面子肯定有某种共性,不过面子在中国应该是属于个人的,也就是说在面子的背后藏着的是个人之于集体的形象。面子既是个人的又不是个人的,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模型来理解它,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个人主义的纯个体的东西,因为面子是个体在集体视线下由集体给予的表象。所以我说面子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吴泓缈:说得太对了,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被看重,被认为有分量,那么他就应该按某种方式行动,得到某种尊重,我们对他也必须采取相应的态度。不这样,就会让他没面子。
BG : 在某种程度上,他就会失去在集体中的位置,失去他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
吴泓缈:不完全是身份(identité),我也说不清。
BG : 那是什么?
吴泓缈:因为对我来说荣誉可以算得上是身份。
BG : 是的,没错,一种在集体中的身份。
吴泓缈:但面子并不完全是身份,它仅与他人的态度和评价有关。
BG : 别人眼中的我。
吴泓缈:就是这样。
BG : 如果别人不再这样看我,我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存在了,如果别人对我的看法是负面的……
吴泓缈:对,就是这样。它不完全是身份。应该承认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一个社会的构成,一个被社会所定义的元素。如果社会不承认你,你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集体或者说社会在对个体的定义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就说这么多吧,以免说傻话。
BG : 不会的。我觉得你开始说的话十分重要,就是说面子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我想说在中国社会中它确实有特别表现,但这种现象到处都能见到;比如说荣誉现象,在非洲国家和穆斯林社会中也能找到。我甚至认为它的存在是普遍的。因社会结构不同,其构造有所不同。
吴泓缈:关于这一点我想再强调一下:面子与荣誉,当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我个人认为,确切地讲,面子属于表象层面,荣誉属于本质层面,两者有一些根本的区别。
BG : 表象与本质?
吴泓缈:是的,这是我的看法。
BG : 嗯,我想可能你是有理的,因为荣誉的背后是某种社会的价值观,我捍卫这种价值观,不管它是封建的还是贵族阶层的。也就是说荣誉的背后有着……它与原则发生关系。至于面子,则是我当下的具体处境,我有面子或者没面子。
障碍与误解
2.4. 与时间的关系
BG : 我们继续,还是对刚才那位女士采访的视频,涉及到人与时间的关系。
视频开始:
甄女士:时间对我们来说是结果的时间,而对你们而言,时间是每个反应,每个运动,时间必须进行计算。因此你们总是显得很着急,总在赶时间,而我们则比较从容,因为……
记者: 人们确实有这样的印象。
甄女士: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对自己说:“不急,还有十年,或还有一年。”可你们会把一年拆成每一天,然后每天都必须干点什么,都必须完成什么…… 我们会说:“一年,一年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而不会将其分解成每一天,不会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做什么。我认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急你们急!事实上,当我们说“还有时间”时,我们其实在心里激励自己,打算好好利用剩下的时间完成任务。因此实际上呢,我们是在心里急,虽说外表上显得没你们那么急,而你们却会说我们在那儿无谓地晃荡。
视频结束
讨论,不同文化视角的交锋
BG : 我认为这段视频很棒,它点明了不同的时间观,对时间概念的不同理解,不同掌控,以及对效率的追求方式,涉及到时间的行为差异等等。我能感觉到甄女士很想说清楚这差异到底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到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ien),他在《效率论》中非常漂亮地描述了两种讲效率的方式以及标准的西方行动方案。西方的行为方针是:“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找到达成目标的办法,暂时搁置其他一切无关的东西,这就是我行动主要指导原则。”所谓无效率,就是不遵循这一原则。西方人迫不及待地期待这个行为体系四处开花,所以甄女士才会说:西方人指责我们不按此方式行事所以效率低下。但这决不是说我们不讲效率,我们也讲效率,但我们的效率不同。我们的效率,确切地讲,是利用每一刻推进工作进度。于是两种效率观产生冲突。我们不想说哪一种效率观是主流,惟主流能成事,主流必取代非主流等等。我认为其实存在着两种立场,一种是行动主义(actionnaliste)的立场,它强加于人并自认为是惟一的真实,要成为效率的标准。另一种是情境主义(situationniste)的立场,实际上,人总是处于具体情境中,处于众多无法把握的因素中,要利用种种因素为目标服务。我们也关注目标,但实现目标并非只有一条路,不应扼杀所有其他可能性,应该利用一切因素,只要它有助于实现目标…… 这大概就是甄女士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意思,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
吴泓缈:就是,就是。而且你提到了弗朗索瓦·朱利安,很有道理。举个小例子,大大简化的小例子:一个法国人要完成一个任务,为了鼓励他推动他完成任务,人们会说:“去做点什么,再做点什么!”但如果是个中国人呢?人们会说:“耐心点,再耐心点!”我这两个简化版的例子可能过于夸张,用弗朗索瓦·朱利安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可能会更清楚一些:面对一个目标,一个西方人首先需要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参照体系,然后根据理想世界制定一个理想规划,规划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这是弗朗索瓦·朱利安描写的模型,不是我想出来的。两个重要部分,一部分由原则构成,另一部分便是程序。也许弗朗索瓦·朱利安会批评我过分简化了他的模型…… 那么很对不起。原则这一部分,是不可更改、必须遵守的,所谓原则问题不容妥协,是这样说的吧?
BG : 是的,一定要坚持原则。
吴泓缈 : 也就是说原则是不能修改的,不能动的!当然也有修改某些原则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把原则分为两类:一类不可违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动摇,另一类主要用来指导应用,所谓的应用原则。这后一部分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调整的。但第一部分,作为基本原则,碰都不能碰。然后呢,在实施过程中,人们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或修正另一个部分:程序。调整顺序,比如——用一个语言学术语——前后倒置,通过一步步调整、完善程序,让结果越来越接近理想世界。最后的评判:谁最接近理想世界,谁就是最好的。
BG :当然也是最有效率的。
吴泓缈:没错,最有效率的。
BG : 也就是达成了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吴泓缈:是的。但对于另一种文化,比如说中国文化,在面对一个任务或一项工程时,我们似乎不需要这样一个理想世界来作为参考背景。不存在理想世界,确切说,是不存在超验世界。那我们会如何行事?我们先是确定一个目标,然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考察实际情况;我们也会分,也是二分,比如说把实际情况分为有利的和不利的,弄清现实中哪些是对实现目标有利的条件,哪些是不利的条件。再然后呢?当然是促使有利条件发展壮大,渐渐形成积极趋势,然后我们尽量利用之……
BG : 最大限度地利用之。
吴泓缈:对,最大限度地利用之,利益最大化,你说得对。我利用这一积极趋势,顺势而为,顺势利导,自然而然地,不甚费力地达成我的目标。那么对于那部分不利的、消极的条件我该如何处置?我尽量避开它,不让它成为我前进的阻力。或者,将它们转化为积极因素。化不利为有利,这,在我们文化中被视为最高智慧,就是善于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比如说某个人明明是我的敌人,但我却有可能诱使其做出一些对我有利的行为,对实现目标有利的行为;就这样,他变成促进我实现目标的成分。到这一步,我们发现因为没有理想世界,所以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规划,更遑论原则。请注意,没原则,这一点隐含着极大的危险,但对此我此刻不作深入讨论。那么最后我们如何评判成果呢?一切皆取决于结果,取决于目标达成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对我们而言当然与你们的大不一样。法语里好像也有这样一句谚语吧,充满智慧的谚语,怎么说来着?有耐心者……
BG : 有耐心者事竟成。
吴泓缈 : 只要有耐心,事无不成啊。这句谚语表达的是同样的精神,一种法式智慧,却更像中国智慧,因为它是中国人行事的主要策略。
BG : 是的,在刚才说的这段话里,我觉得最重要的,嗯,应该是《论效率》所揭示的对积极采取行动的肯定,或曰盲目崇拜:为实现目标就应该动起来,进行组织,采取行动,不能只是等待,等待让人远离目标。但听了刚才那段话,我才明白其实“无为”就是“有为”,等待就是行动;等待是整体的必要构成,等待有利因素出现,等待消极因素转化…… 实际上人总是处在一个具体环境中,一个行动的环境,永远会受到种种突然而至的因素的影响,它不可能是孤立的,而人也不可能掌控所有这些难以预计突然而至的东西的。
吴泓缈:是的,你说得太有道理了。记得我曾跟你说,我把西方这种强调行动的做法称为“行动英雄主义”,而你的说法是英雄行动。
BG : 是,英雄行动,行动被偶像化,受到盲目崇拜。
吴泓缈:比如像西齐夫那样,不停地推石上山,一次又一次,永无休止,他正是在这种反复推石上山的英雄行动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浮士德的一生也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地投入新的行动。而我们中国人却有着另一种哲学:有时候有利条件开始涌现,有时候不利开始转化为有利,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采取一个行动,它就有可能阻碍甚至打断这种好的趋势,于是这行动反而有违初衷,反而不如不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最好还是停一停,等一等,仔细观察介入的时机,找到了那最恰当的时机,你只需轻轻一推,事情便会飞快地进展,这当然是另一种效率。
BG : 这当然不符合行动哲学的观点。
吴泓缈:没错。
障碍与误解
2.5. 行为方式
BG :我们接着往下看。我觉得这一节也还是属于同一个主题,接下来有两个人接受采访,他们两个在同一家中国工厂工作。
视频开始:
圣热朗女士: ……时至今日,公司上下每个月都会有人问我们这笔进口业务做到哪一步了,我们已经做好并提交了所有文件,而且已经过去一年半,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是不是还需要做点什么?是的,那就是等待,等待一个契机。契机到来你正好在场,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总会出现这么一个契机,你要抓住它,契机它转瞬即逝,几小时,一周或两周,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还缺什么文件或材料,那就非常被动,非常糟糕,因为那缺的可能是一份须由美国法律顾问提供的文件;当你找他要这份文件时,那家伙会说:“怎么可能?我们讨论这笔进口贸易已经一年半了,结果今天你才想起要这份文件,而且让我必须在两日内做好?!”可我们现在就把它做好有用吗?没用的,因为我甚至不知道那文件是什么内容,因为突然间你有可能被接受被通过,可那原因,在今天我们不可能想得到。机会来了,你却没备好所需文件,或者找不到人来做这份文件,或者找谁也来不及了,那你就惨了!你没机会了,这就是中国的实情。
李蒙迪: 是的,我想中国不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人们反复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国家,而是一个喜欢说“为什么不?!”的国家。一切皆有可能!
视频结束
讨论,不同文化视角的交锋
BG : 一切皆有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不!”,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她讲的东西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行为哲学。也就是说其精神核心便是耐心等待机会出现,而不是事先把一切都计划好。等待一个恰当时机介入,采取行动,而且恰当时机不容错过。这种策略,所有这一切,她很难向西方同事们解释清楚。后者一定要计划好一切,致力于预见一切,并坚持认为你若需要文件就必须明确地告诉他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文件,以及要文件的准确时间,你不能到了最后一刻才告诉他们要某份文件。对于他们所说的不能拖到最后一刻,她的回答是:“我所处的环境非常复杂,到底什么才是合格的文件,我也不知道,真的无法知道。唯有当人们来问你要的时候你才能清楚地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时候到了你才知道该如何反应,否则就会错失良机。”此处的确存在着两种逻辑:一种随机顺势,必须把握好时机;另一种强调计划,事先规划好一切行动。
吴泓缈:我不敢肯定我的看法是对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去国外建厂,肯定会有有利的方面和不利的方面,有阻力,比如说有人认为你不行,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但突然间机会来了,反对派因某种无法预计的原因暂时噤声,或者支持你的那一派暂时有了决定的权力,于是对你文件的审批一路绿灯。机会来了,理想的机会,这时候你若已备好所有材料,适时递去,你当然就收获了成功。但你们西方人会说:我准备好了一切,我无一遗漏,所有文件一样不缺,凭什么我不能过?这与机会是好是坏没有关系:只要我的文件和材料没有任何问题。还记得我刚才说过的吗?中国人与文本的关系与你们的不大一样,有时候就算你的文件完美无缺,不让你通过你还是通不过;有时候就算缺了一两样,没关系,还是可以给你通过。不过也必须指出,现在我们对待文本的态度在向你们靠拢,逐渐靠拢。
BG : 当前吗?
吴泓缈 : 是的。目前越来越靠近你们对文本的态度。当然,我刚才所说的中国方式,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绝对的。
BG : 当然不是!它们是不同搭配的平衡状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是一些性质不同的动力结构。来到国外,无论是哪个国家,我们都必须弄明白这种在搭配上或剂量或中轴的不同,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另外,毫无疑问,所有文化都在进化,在渐变,于是又会出现一些新的搭配平衡,这毋庸置疑。
吴泓缈 : 我想,就你拍摄的这几段视频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没有亲身体验过文化差异,从未遇见过类似的文化冲突,并身临其境时,这时来看你的视频,我们可能不会有多大感触。但一旦去国外建厂或做生意,且遇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那时候再来看你的视频,感觉就一定完全不一样了。
BG : 是啊,与实际相联系,就容易理解。
吴泓缈:有亲身经历,才会出现理解的契机;此前,则不能同日而语。
BG : 谢谢。
吴泓缈 : 事实就是如此,就是如此。
(责任编辑:罗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