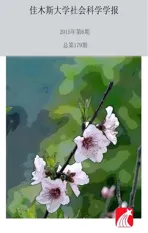东丹国南迁缘由初探
2015-04-15耿涛
耿 涛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东丹国的南迁学界一直争议较大,该问题又以耶律羽之墓志的出土作为节点,依凭该墓志,学界改变了以往认为是耶律德光授意迁都的观点,一面倒向耶律倍出于本意授意迁都,但经过考证不难发现,耶律羽之墓志很多记载仍需进一步商榷,耶律倍并非东丹南迁的授意者,耶律德光才是东丹南迁幕后的操控者。①在笔者看来,耶律德光操控东丹南迁的缘由不外乎两点。其一,耶律德光希望平复渤海旧裔谋图复国而不断爆发的叛乱,同时借此机会消除耶律倍借机起事的可能;其二,耶律德光欲逐鹿中原,留下一个东丹国势必成为他南下征伐的隐患,故此想借南迁消减东丹国的实力,以便将其纳入大契丹国的一部分。
一、幕后操控东丹南迁,巩固皇位
东丹国在建立后就叛乱不断,“渤海既平,改东丹国,倾之,已降州县复叛,盗贼蜂起”[1]1224,“另外还有大量的遗民逃亡高丽和女真”[2]238,耶律德光自己亦曾亲身参与平叛,据《辽史》记载:“未几,诸部多叛,大元帅讨平之”[3]1210。渤海遗裔据旧地叛乱自然成了耶律德光的亟待处理的问题,可武力并非长远之计,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将这些渤海遗裔迁走,使其失去作乱的力量。
另外,在如此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争夺皇位失败,心存愤懑的耶律倍趁着东丹国局势不稳势必会有所作为,耶律德光自然也考虑到这种情况,早早下手,迁都徙民,使其失去作乱的基础。这样一来,不仅打击了渤海遗裔的势力,也剥夺了耶律倍叛乱的可能。对此问题,杨雨舒在文中指出“(耶律德光:笔者注)改变了他父亲耶律阿保机建东丹于渤海故地的政策,将其南迁。”并且也认为“耶律倍归国会对其(耶律德光:笔者注)产生威胁”[3]190-196。李桂芝也曾在书中提到:“这次南迁,除便于控制外,或许也有缩小东丹国规模,限制东丹王势力的意图”[5]33。除此之外,从《渤海国志长编》的记载中也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在迁都事项确定之后,“王寻归国”,耶律德光怕的就是耶律倍归国后借机叛乱,所以才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放耶律倍回到东丹。对此问题,《太宗本纪》和《耶律羽之传》所载稍有曲笔之意,但《义宗倍传》的记载则一阵见血的指出了迁都的症结所在。“太宗既立,见疑”,“疑”的就是耶律倍是否会依靠渤海旧裔的力量发动政变,更有可能是《耶律羽之传》中提及的“恐为后患”。韩国学者李龙范针对此问题也提出:“太宗为防止人皇王之起义于未然,故意出演的演剧作品”[5]17。
可既然耶律德光是授意迁都的人,那么又为什么非要让人皇王下诏进行迁都而不是自己直接下诏呢?其实很简单,无论耶律倍是否拥有实权,他都是东丹国名义上的领袖,从他口中说出迁都一事更加具有信服力,耶律倍的下诏仅仅是一个过场,只是为迁都加上砝码而已。除此之外,这还与耶律德光精心设计的布局有着密切的关联。联系上文提到的耶律德光最怕的就是耶律倍会联合渤海旧裔拥兵作乱,杨雨舒曾在文中指出:“更何况耶律倍在东丹又拥有最高权力,一旦他利用这一点控制了驻渤海故地的契丹军队,并借用怀有强烈复国愿望的渤海遗裔势力来发动讨伐耶律德光的战争,那么其危险性将大大超过渤海遗裔本身的反抗,甚至将会危及耶律德光的统治地位”[3]190-196。故如何消除耶律倍与渤海旧裔联合的机会成为了其着重考虑的一点,他先是让耶律倍下诏授意迁都,将迁都一事归结于耶律倍的授意,然后在大规模强制性移民之时,不顾民怨,采取了破坏性极大的徙民方案。据《辽史》记载,很多“因诏困乏不能迁者”最终都“许上国富民给赡而隶属之”[1]30,除此外,“上京龙泉府渤海王宫的所有建筑,包括寺院庙宇皆葬身于大火”②。这样一来,那些受到迫害的渤海旧裔很自然的将仇恨的矛头指向了耶律倍,使耶律倍不仅在软禁于皇都的过程中失去了掌政大权,亦失去了民众基础,断掉了耶律倍联合作乱的可能,亦打击了渤海旧裔,在此基础上,耶律德光的皇权得以巩固。
二、归整东丹,以期南侵中原
耶律德光意欲南迁东丹的另一大原因就是想变东丹国为地方政权,也就是将统治大权完全的收归己有,剥夺东丹国的独立地位,以便于自己南下中原的宏图大略。李雪梅在其文中就提到了东丹国这一变化过程:“东丹国也确实逐渐地从二级政权转变成一个地方政权”[6]116-119,范树梁和程妮娜在文中也认同了这一变化:“实际上,东丹国迁到辽东后,在契丹朝廷的严密控制下,政权机构削减,独立自主性日渐削减”[7],除此外,田野于其文中也提及了这一变化:“辽太宗南迁东丹于东平,升东平为南京后,尽管东丹国的建置还在,但其性质已非同昔比。从东丹国的角度上说,南京是其国都,但从辽朝的角度上说,南京却又同时是辽朝的设在地方的派出机构,具有地方行政设置性质。由天福城到辽南京,这实际上是淡化了东丹国的相对独立资格,是变属国为地方二级政权的开始”[8]。
耶律阿保机建东丹国初始,是打算将其建立成一个国中之国的,金毓黻先生曾指出:“契丹改置东丹国的意思,与契丹使石敬塘为晋帝统治中原,金使刘豫为齐帝统治中原的道理一样”[9]430,在此笔者并不认同王德忠的观点,他认为“东丹国是辽的基层政权,东丹国在形式上是契丹的基层政权,但实际上却具备了“国”的体制和规模”[10]37-43。此观点恰好说反了,东丹国应在形式上是“国”,实质上在南迁之后则变成了契丹的基层政权。在耶律阿保机在世时,“国中国”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建制,但在耶律德光继位后,对于早就有入主中原之志的德光而言,“契丹在南下时就会有后顾之忧(指东丹国:笔者注)”[3]190-196再加上猜忌兄长耶律倍还会与其争夺皇位,东丹国成为耶律德光势必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耶律德光采取了两个步骤,即先一点点压缩耶律倍在东丹国的权力,进而一步步将东丹国变为一个地方政权,而南迁就是变“国”为地方政权的重要一步。
第一步,压缩耶律倍的权力,据《辽史》记载,“天显元年二月,改渤海国为东丹”[1]22,耶律倍自此主东丹国事,可在同年七月“上(指阿保机)崩,年五十五”[1]23,耶律倍在东丹国并未把持多久国政就忙于奔丧“乙巳,人皇王倍继至”[1]23,“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1]1210,在此之后便一直留在了皇都,完全脱离了东丹国的权力中心。“由此看来,耶律倍被任命为东丹国人皇王,至离开东丹奔丧止,主持东丹国务不足六个月,而从与其父辞别始,单独主持东丹国务,则只有四个多月”[11]181,而此时真正掌握东丹国实权的是耶律羽之,失去实质统治权的耶律倍在接下来南迁一事中自然处于了“无为”的状态,有关耶律倍此时实权一事,《契丹国志》亦有记载:“突欲自以失职,帅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12]150-151,金渭显也曾指出:“如此之事,不是东丹王的处决,而是太宗直接处决。东丹王没有统治权”[13]14。故在这样的情况下,南迁一事自然也水到渠成。
再看第二步,据《辽史·太宗本纪》的记载,“升东平郡为南京”,耶律德光竟将东丹国的新都城纳入自己契丹国的五京之一,已然在行政区划上将东丹国视为一体,同化东丹政权之意不言而喻。换句话来讲,东丹国南迁之后的都城已不仅仅是东丹国都城这么简单,而是作为契丹政权中的一部分存在。这样一来,东丹国的独立性和耶律倍的东丹王身份更是名存实亡。退一步说,就算东丹国尚保存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其所谓的国都已经是契丹政权下的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亦已落实了东丹国臣属的地位。除都城外,东丹原有的州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毓黻先生曾在文中指出:“东丹国多既徙,而渤海诸州亦随之俱迁。上京、中京之民多迁于辽阳,东京之民迁于开州,即今凤城,南京之民迁于海州,即今海城。其所领诸州之名,或仍其旧,如开州所统之盐、穆、贺三州是也;或易其名,如海州所统之耀、嫔二州为椒、晴二州之易名是也”[14]286,杨雨舒则依据《辽史》统计出“……等十三州条下均记有‘本渤海某府某州(或渤海置州),故县某,皆废’,其所废故县共计六十六个”,并提出“而废除如此众多的渤海故县,显然是在大规模地改变渤海旧的地方行政机构”[3]190-196。由此可以看出,耶律德光并非是单纯地进行迁都,而是想通过迁都将东丹国原本相对独立的情况打破,植入契丹国统治的势力,将东丹国纳入大契丹国的版图,以此杜绝南下时的隐患。这点在其后史实中体现的非常明显,耶律倍南逃后唐,太宗并没有另立一位新的东丹王,而是在名义上扶植耶律倍的妻子,实质上则为心腹重臣耶律羽之所掌柄大权。而世宗即位后,辽与中原王朝的实力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对中原的战事相对较少,所以对东丹国又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政策,封安端为王将东丹国稳定下来。接下来,圣宗即位后,契丹国力兴盛,大举侵入南方,在南下中原再次成为契丹统治者的政策时,东丹国的存在自然又成了契丹的肉中刺,可此时东丹的实力已被多次削减,故圣宗时直接废去了东丹国,完全的将东丹融入了大辽中。
综上所述,在史料的佐证下,对志文内容稍加推测,不难得出耶律倍其实在南迁过程并未处于一个主导地位,反而由于耶律德光的压制而处于一个十分被动的地位,不仅违背本意授意迁都,更在归国无所事事,最终浮海适唐。而耶律羽之也只是耶律德光旨意的执行者,真正操控着南迁一事的人应系耶律德光。
[注 释]
①耶律倍并非东丹国南迁的真正授意者,耶律倍的授意南迁其实是耶律德光幕后操控完成的,有关该问题的讨论详请参见拙作《耶律羽之墓志所载”人皇王诏书“考疑》拟刊于《兰台世界》2015年12月。
②详参朱国枕、魏国忠《渤海史稿》之《东丹的始末》。
[1](元)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M].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3]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1993(5).
[4]李桂芝.辽金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5][韩]李龙范.中世东亚细亚史研究[M].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6.
[6]李雪梅.论东丹国的建国原因及其性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7]范树梁,程妮娜.辽代东丹国设置浅析[C]//冯永谦,孙文政.辽金史论集:第十一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8]田野.论东丹王浮海去国事件的性质[J].沧桑,2009(6).
[9]金毓黻.东北通史[M].台北:洪氏出版社,1976.
[10]王德忠.辽朝对东丹国的统治政策及其评价[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科版),1987(2).
[11]张博泉.东北历史名人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2](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韩]金渭显.东丹国变迁考[J].宋史研究论丛,2003(00).
[14]金毓黻.东北通史[M].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