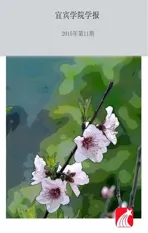左翼转向前后王鲁彦乡土小说的创作变化
2015-02-14林双
林 双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左翼转向前后王鲁彦乡土小说的创作变化
林双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摘要:王鲁彦1923-1935年的乡土小说创作在左翼之前和之后有明显的转向:左翼转向之前,小说着重揭露农民的封建思想,批判乡民的国民劣根性,表现了商业资本冲击下扭曲的人伦关系;左翼转向之后,则主要表现出农民革命意识的萌芽和喷薄而出。革命话语的流行、现实形势的需要以及“为人生”的思想是王鲁彦左翼转向的主要原因。王鲁彦乡土小说对中国农民革命和乡土叙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这样的变化表现出他作为知识分子具有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王鲁彦;乡土小说;左翼转向
目前,学界关于王鲁彦的乡土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写作风格、乡民人物以及风土人情等方面,对于其左翼转向前后乡土小说的变化研究很少,而这一变化对于搭建中国现代乡土叙事——农村叙事——的链条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力图探讨王鲁彦左翼转向前后乡土小说创作内容的变化及其相关问题,能更深刻地把握历史洪流中的王鲁彦对于故乡人事的思索与书写的变化,为中国乡土叙事的发展流变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一王鲁彦左翼转向之前的乡土小说创作
王鲁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之下走上新文学创作之路的,他从1923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但是他早期的如《秋夜》一样的文学作品有一点浅白的浪漫主义,带着一些主观抒情色彩。不久以后,王鲁彦的创作开始慢慢转向现实主义,而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在描绘一幅幅浙江滨海农村的画卷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在这一部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作者更加坚实地关注家乡民众,不仅关注他们贫困的状态、艰难的生活,更关注他们麻木的精神状态、愚昧自私的灵魂。
(一)展现了农民的封建思想和国民劣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启迪了不少中国人。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农民的思想中。这一思想在王鲁彦的小说《菊英的出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发人深省。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菊英因为白喉病已经去世整整十年了。十年来菊英娘没有一天不想念女儿,她幻想女儿已经成年,想给她找个丈夫疼她爱她好好过日子。于是母亲通过媒人找了一个去世的小伙子,风风光光地把女儿“嫁”了过去,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冥婚。小说中的民众显然是相信鬼神存在的,认为人过世后仍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此外,菊英娘的愚昧还表现在她不相信西医,在菊英的病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仍不忘记带着香烛和香灰去求仙药。她拒绝科学,诉诸于虚幻的神灵,其实这才是导致小菊英死去的真正原因。菊英娘是众多农村愚昧民众的代表,换言之,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背负这样的枷锁浑浑噩噩生活着。作者在小说中发出令人心碎的呐喊和深刻的批判。
王鲁彦的乡土文学有很多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品,其以鲁迅式冷峻的笔调直指人物灵魂深处,剥落出旧式民众的麻木、愚昧和冷漠等性格弱点。如在小说《柚子》中,作者写到,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战乱结束刚三天,他和两个朋友在湖南长沙的酒楼上,想着去岳麓山玩,突然听到有人喊“看杀人去呵!看杀人去呵!”[1]23很多人趋之若鹜地奔向现场去看如何杀人。他们议论着、庆幸着,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这“令人兴奋”的场景。最后,“我”和T君在卖柚子摊位前的对话对于以上场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尤其是那句“湖南的柚子呀!湖南的人头呀!”[1]29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阀混战时期民众的生命之轻。军阀杀人如麻,民众人人自危。王鲁彦借此揭露了军阀混战和专制带给人们的戕害,而这样的戕害不只在身体上,更是在精神上。
人们麻木冷漠地观看着杀人的场景,并且把它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来观赏以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王鲁彦无疑受到鲁迅批判国民“看客”的思想影响——看客一样的麻木冷漠的人们在看杀人,他们又在作者冷峻的眼光下“被看”。小说所刻画的虽然只是一时一地的一群人,但是这些人却是整个中华民族麻木“看客”的典型代表,所以,王鲁彦对此的批判也就有了超越时空的力度。
(二)表现了商业资本冲击下扭曲的人伦关系
茅盾在《王鲁彦论》中说:“王鲁彦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在我看来,是一些乡村的小资产阶级,例如《黄金》里的主人公和《许是不至于罢》里的王阿虞财主。我总觉得他们和鲁迅作品里的人物有些差别: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2]王鲁彦的家乡宁波是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最早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冲击。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文明在影响宁波经济的同时,更大程度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精神。所以,宁波的农民和传统中国农民不同,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了他们,金钱支配着他们的情感,人际关系呈现出冷漠自私的特点。
在王鲁彦的小说《黄金》中,如史伯伯家本是有产者,也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但是因为在外工作的儿子年前没能寄钱回来,导致如史伯伯家的生活日渐窘困,更加可怕的是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压力——乡亲们无尽的嘲讽,人们不复淳朴善良,而是把金钱当作衡量人际关系远近的标准,表现出冷漠、自私的一面。《许是不至于罢》中的王阿虞财主非常富有,王家桥的人们表面上与他友好,对他很尊敬,但是暗地里却总是借机占他便宜。王财主回复记者的那一句“许是不至于罢”道出了因为金钱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自私与冷漠。
然而,在左翼转向之前的作品中,王鲁彦批判了商业资本冲击下扭曲的人伦关系,但更在批判之余表达出对故乡温情的怀念。这种情感在《小小的心》《童年的悲哀》中表现得很明显。《小小的心》在批判人们的冷酷之外,更通过孩子表现出一种人性美,进一步表达了对家乡深切的怀念。在《童年的悲哀》中,通过“我”对阿城哥的怀念,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
二王鲁彦左翼转向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
谢秀琼说:“那些侨居都市的乡土书写者,离乡却又无法抗拒思乡的诱惑,他们依据怎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去想象乡土世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的文学表达。”[3]王鲁彦在左翼转向之后的乡土叙述中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在想象乡土世界的过程中融入了革命话语。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中。小说《乡下》体现了革命叙述的萌芽,而《愤怒的乡村》则体现出革命叙述的火焰喷薄而出。
(一)《乡下》——革命叙述的萌芽
在小说《乡下》中,王鲁彦描述了江南某农村三个忠厚善良的农民,因受反动政权的欺压而相继家破人亡。面对乡政府的残酷的压迫和盘剥,阿毛、三品和阿利三个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阿利是一个小商人,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他的生意渐渐破败。而特殊的时代与自身的人生境遇造就他矛盾的性格:他既感叹命运的不济,又对往昔充满眷念。所以,他既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平,又怕反抗的行为引来灾祸。他表现出反抗的意识,但是反抗的行动还不够坚决。三品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相信宿命论,不仅自己向反动政权妥协,而且劝说阿毛缴税。即便后来无端入狱,也归结为运气不好,直至在变本加厉的欺凌之下抑郁而终。在对待压迫的态度上,阿毛不同于他们,他一贫如洗,对反动统治者繁重的苛捐杂税极为痛恨,因此想和掠夺者、压迫者拼个你死我活。但是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薄的,他反抗失败,被关入监狱,最终也被折磨致疯。
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剥削和压迫的平民百姓,虽然都是以悲剧而结束,但我们从中看到了他们的愤怒和反抗。三个人中,阿毛与众不同,他的反抗即使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微弱不起眼,即使只表现在精神之上,但我们却看见了革命意识与行为的萌芽。
(二)《愤怒的乡村》——革命叙述的火焰
如果说《乡下》人们反抗的火苗刚刚被点燃的话,那么在《愤怒的乡村》中,人们的革命火焰逐渐喷薄出来。小说通过轧米事件、挖井事件、三次抗捐事件以及最后华生被反动军队抓走逐步表现出来。
阿城去轧米的时候正好赶上刮东南风,轧米船里的黑烟和细糠不时被卷到岸上,最后吹到坐北朝南阿如老板的丰泰米店。阿如老板有钱有势、仗势凌人,乡亲们都怕他。见此情况,阿如老板开始骂人,华生非常生气,据理力争,随即遭到阿如的追打,结果阿如反被华生砸了货柜。虽然乡亲们都站在华生这一边,但是依然以葛生哥放爆竹赔罪妥协告终。华生忍不住要报复,但是听从了阿波哥的话,等待时机。之后的冲突发生在遭遇大旱天,河水干涸,乡亲没水喝,于是大家都去挖井。华生挖了一口很深、很清澈的井,他让乡亲们喝井里的水,却不让阿如老板喝。华生的一句“告诉他去吃混水吧!休想吃老子掘出来的神水!”[4]128再之后是三次抗捐事件,第一次是在迎神之后,乡公所的温觉元和益生校长挨家挨户以募捐掏河的名义收钱,华生非常气愤;第二次是温觉元和阿品以“随缘乐助”的名义让乡亲们募捐,还欺负调戏秋琴,华生和阿波制服了他们,并逼他们写下服状,以示反抗;第三次是人们恐慌出逃归来之后,乡长派温觉元到华生家让他们捐五元钱开欢迎会,办一桌酒席,并让华生背旗欢迎官兵,华生奋力反抗,但是收效甚微。最后在荒年歉收的情况下,地主却逼租更紧,阿如老板在逼租的过程中打死了阿曼叔。这一切已经让华生、阿波哥等人忍无可忍,他们在愤怒的呼号中带着乡亲们走向反抗。
虽然这次的反抗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已经为广大受苦受难的穷苦农民指出一条出路——要反抗。他们反抗的火焰已经慢慢地燃烧起来,深知统治阶级只会忠于自己的利益,不管遇上天灾还是荒年,他们都会最大限度地剥削和压迫群众,群众只有反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王鲁彦左翼转向的原因
(一)革命话语的流行
胡景敏说:“自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后,左翼文学开始兴起,并逐渐占据了文坛的舆论制高点。在文学观上,‘五四’理念为革命话语所取代;在文学创作中,乡土经验开始为左翼文学所征用。”[5]王鲁彦是以乡土题材著名的作家,虽然没有加入左联,但是他与左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胡景敏还提到:“革命许诺的是直接而又速效地改造乡村的动人幻景,于是在王鲁彦们的作品中出现了暴烈的反抗的乡村叙述,含混的政治理念对他们的乡土经验造成了压迫,乡土写实派的转向实际上成了之后革命文学乡村叙述的前驱。”[5]
如果说王鲁彦在左翼转向之前的乡土小说创作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想象和怀乡想象的话,那么左翼转向之后则表达出作者的革命想象,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思潮盛行,从而使得乡土文学的作家作品自觉地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服务,换言之,由于写实与意识形态相结合,使得革命话语流行起来,指导了乡土文学的革命叙述,使得叙述主体“将自身视作各种理论话语尤其是现存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甚或常识所构筑、所操纵之物”[6]163。
(二)现实形势的需要
从1931年开始,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始实行土地革命,农民获得土地。但仍有很多人生活在反动统治之下,受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样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农民的悲剧加剧,他们自救的愤怒彰显出一种昂扬而悲壮的革命精神。在《乡下》中由于受到反动统治的压迫,三个主人公走投无路,以悲剧结束。但是,阿毛身上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革命意识的萌芽,这样的精神意志力量使得他最后的悲剧更为悲壮,更有警醒群众的作用。在《愤怒的乡村》中农民们不仅遭受到瘟疫、大旱等天灾,还要受到官绅勾结残酷毫无休止的压榨。人们忍无可忍,发出愤怒的吼声,起身反抗与革命。在此,王鲁彦利用了阶级分析的思想,设立了两个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通过对苦难农民租税的盘剥来体现主要的冲突。这样的叙述模式虽然简单,还有些概念化,却反映了当时农村苦难日益深重的农民的境况。茅盾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向的对于运命的挣扎。”[7]241由此看来,茅盾也认为此时的文学应该从现实出发来反映革命的倾向。
(三)“为人生”思想的指导
王鲁彦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文学研究会宣言》有这样一句话:“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8]3王鲁彦左翼转向前后的创作都是在“为人生”思想指导下创作的。在左翼转向前,鲁彦的作品主要表现了反封建、批判国民劣根性等内容,这样的内容是以自己生活多年的故乡经验为基础的,持着“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优秀传统,切切实实地反映生活、揭露现实,不去粉饰太平,也不作无边无际的幻想。王鲁彦因为寓居他乡,所以他的这些创作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乡土想象相结合的,表达了自己的思乡情怀。而左翼转向之后,王鲁彦创作具有革命意识的作品也是为人生的表现。鲁彦的夫人说:
一九三三年鲁彦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浙江镇海县乡下,他在家乡住了一个时期,认识了农村中各色各样的人物:有男女农民们,进步的农民青年,小学教师,也有地主兼商人的老板,乡长和乡长的狗腿子一流人。他感到封建统治的恶势力压迫的深重,他热烈地同情农民的反抗精神,对当时现实产生了强烈的恨和爱,因此他开始想要写一部以农民反抗统治阶级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他计划用三部有连续性的长篇来完成它:第一部题为“野火”,是取“野火烧不尽”来象征农民群众反杭的开始;第二部题为“春草”,是以“春风吹又生”来象征斗争的发展和人民力量的壮大;第三部题为“疾风”,是用“疾风知劲草”来象征在斗争的风暴中坚贞不屈的人民英雄。[9]275
由此可见,鲁彦的乡土文学创作不管是左翼转向前,还是左翼转向后,贯穿其中的一直是“为人生”的思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创作才会根据时代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四左翼转向前后王鲁彦乡土小说创作变化的意义
(一)现实意义
王鲁彦左翼转向的乡土小说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这些作品以文学叙事的方式为三十年代的农民勾勒了一条武装革命的现实生存之路,成为共产党反阶级斗争的精神文本。三十年代农村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广大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品中刻画反抗的农民形象和表现的反抗精神、革命方式与革命勇气,为现实中像华生、阿毛一样穷苦的受到压榨的底层农民树立了榜样,促使他们认清统治阶级本来面目,鼓舞他们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让他们看到通过革命的方式可以获取新生活的希望。革命叙述中华生的愤怒,又何尝不是王鲁彦的愤怒和广大农民的愤怒呢?
在三十年代,党所领导的农村斗争或者在这一斗争影响下农民自发的反对剥削的斗争,正如暴风骤雨般迅猛异常地席卷广大农村,规模空前,王鲁彦热烈地歌颂农民的反抗精神,对当时的现实产生了强烈的爱与恨,加上受左翼文艺思潮的推动,他的作品内容开始走出旧农家的屋顶下、小院里,开始关注时代风云,运用革命现实主义手法,写下了《乡下》和《愤怒的乡村》两部力作,尤其后者是标志着他走上革命现实主义峰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是他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跃进”[9]276。党领导的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促进了乡土文学中革命叙述,而这样的革命叙述又启迪了更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促使他们觉醒起来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二)文学意义
王鲁彦左翼转向的乡土小说也有着很强的文学意义。他转向之前主要是一种启蒙的、批判的和怀乡的文学表达,而左翼转向之后主要是革命的、阶级的和政治的文学表达。由此来看文学本体总是与叙述主体、历史语境、美学观念有着密切关联。而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胡景敏提到:“在政治理念征用乡土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与理念之间的互动和制衡,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乡村叙述表现为‘乡土叙述——乡村叙述——农村叙述’的发展线索。”[5]可以说新文学主流从左翼时期开始与政治表达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也由此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表达出一种强烈的革命倾向。而通过左翼时期的革命表达,很自然地转换到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抗日救亡囯族叙述。同理,“五四”以来“淡淡的乡愁”的乡土文学在国破家亡的历史语境下表现出阶级性的“农村叙述”,期间,王鲁彦等乡土作家在左翼转向后的“乡村叙述”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过渡作用。
结语
王鲁彦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作家,成绩卓著。他寓居他乡,乡土写作对于他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左翼转向之前,他不仅描绘了故乡深重的苦难、惨烈的现实、麻木愚昧的民众,也刻画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由此表达自己的怀乡情怀和启蒙思想。而左翼转向之后革命表达,更好地鼓舞了人民大众,即使王鲁彦的乡土小说出现了这样的转向,但作品中贯穿一致的是他“为人生”的思想,在历史洪流中念念思索着家国的命运和前途,表现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1]王鲁彦.柚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茅盾.王鲁彦论[J].小说月报,1928,19(1).
[3]谢秀琼.乡土空间的“永恒”与“变迁”:论王鲁彦的离乡与精神返乡[J].学术交流,2014(4):170-174.
[4]王鲁彦.愤怒的乡村[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9.
[5]胡景敏.被征用的乡土经验: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村叙述[J].燕赵学术,2007(1).
[6]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茅盾.关于乡土文学[M]//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8]茅盾.导言[M]//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1962.
[9]覃英.《愤怒的乡村》后记[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9.
〔责任编辑:王露〕
An Analysis on Change of Wang Luyan’s Agrestic Novels Before and
After the Left-wing Turn
LIN Shuang
(CollegeofLiberalArt,HebeiNorm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24,Hebei,China)
Abstract:Before and after the left-wing turn, there is an obvious steering in Wang Luyan’s agrestic novels from 1923 to 1935. Before the left-wing turn, his agrestic novels emphatically expose the feudal ideas of farmers, criticize villagers’ national bad habits, and express the distortion of ethic relation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mmercial capital. After the left-wing turn, his writings mainly manifest the peasants’ buds of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The popularity of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the needs of realistic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guidance of the thought for the life are the main factors of his left-wing turn. Wang Luyan’s agrestic novels have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and literary value to Chinese peasant revolution and native narration. This change shows Wang Luyan’s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deep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n intellectual.
Key words:Wang Luyan; agrestic novels; the left-wing turn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11-0095-06
作者简介:林双(1988-),女,河北廊坊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