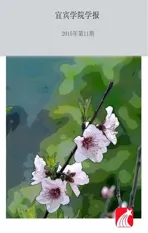思想居所的革命——论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哲学的突破
2015-02-14李华
李 华
(苏州市农村干部学院科研处,江苏苏州215011)
思想居所的革命
——论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哲学的突破
李华
(苏州市农村干部学院科研处,江苏苏州215011)
摘要:海德格尔分析了主体性哲学由于“我思”的自身封闭而无法突破意识内在性的基本困境,作为自近代以来一直占居主导地位的存在领悟方式,主体性哲学的这一基本建制在当代呈现为可能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生产主义和技术主义。基于对人类自我毁灭可能性的悲悯和寻求可能出路的急迫,海德格尔强调了发动思想居所之革命的本质重要性。从存在真理之发生平面出发,晚期的海德格尔在其所展示的深度历史之思中,孕育着一条应对全球性虚无主义蔓延的可能道路。
关键词:主体性哲学;基本建制;时代困局;出路;思想居所;革命
笛卡尔以降近现代西方哲学,始终是以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为主流。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要求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处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历史性存在。马克思在批判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同时,又在新的基点上重建了历史性的实践主体性哲学。[1]海德格尔对此进行了大力的批评,在批评笛卡尔及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阐述了自己对主体性哲学的颠覆和突破。
海德格尔在阐述他的技术哲学的时候,突出地展现了他的哲学的非主体性。他指出,面对“诸强制”的“匿名统治”,即技术的统治,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究竟是拯救还是毁灭?在一篇采访中,海德格尔对此问题最初的回答非常绝望:“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2]1306,“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2]1304,“我们还找不到适应技术的本质的道路”“我全不知道任何直接改变现今世界状况的道路,即使说这种改变就是人可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2]1310,“无人能够知道即将到来的变革。技术的发展在此期间将越来越快且势不可挡,人的位置越来越狭窄。以任何一种形态出现的技术设备装置每时每刻都在给人施加压力,种种强力束缚、困扰着人们——这些力量早就超过人的意志和决断能力,因为它们并非由人做成的。”[2]1237言下之意,人对目前这种状况是完全的无能为力,不仅普通人不能,思想家们同样也不能有所作为,“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这个世界之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它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能是通过人做到的,但也不能是没有人就做到的……我认为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我称为‘座架’的这个东西中……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座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就是要帮助达到此种见地:再多的事思想也不要求了。哲学到此结束。”[2]1306-1307难道这就是海德格尔对于此问题的全部答案?显然不是!我们还有希望,那就是通过思和诗。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保持一种专注于存在的思想,突破意识的内在性,从与意识不同的此-在出发,完成思想居所的革命,从而为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来临作出准备。
一保持一种专注于存在的思想
我们特别注意到海德格尔对“天命”“命运”的不同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之中。座架归属于解蔽之命运”,这是海德格尔晚期技术追问的基础性结论,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句子的意思全然不同于那种四处传播的说法,即所谓:技术是我们时代的命运;在后一种说法中,‘命运’意味着某个无可更改的事件的不可回避。”[2]943此处,海德格尔明确指出,我们说座架归属于解蔽之命运,“天命”“命运”并不是历史决定论的某种必然的不可更改的东西,而是“当我们思考技术之本质时……我们因此已经逗留于命运之开放领域中,此命运绝没有把我们囚禁于一种昏睡的强制性中,逼使我们盲目地推动技术,或者——那始终是同一回事情——无助地反抗技术,把技术当作恶魔来加以诅咒。相反地,当我们特别地向技术之本质开启自身时,我们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为一种开放的要求占有了。”[2]943-944海德格尔的这种补注,实际上为他的技术的追问、存在之思留下了向另一种可能性开放的空间,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的开启。
也就是说,面对技术的全面统治,海德格尔还是给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唯一可能是:依靠思和诗为上帝的出现作准备。”[3]355在场的上帝,我们已经明确,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不在场的上帝、隐退的诸神似乎留下了存在之光澄明的可能,而我们能够依靠的,就是“思和诗”,以领会这种敞开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指出,“我不把人在行星技术世界中的处境看成是不可解脱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是恰恰认为思想的任务,能够在它的限度之内帮助人们与技术的本质建立一种充分的关系。”[2]1311-1312唯一的希望,在于一种对今天这种危险状况的“沉思”,这也是当今之时代留给思想者的主要任务。
他指出,面对技术,“我们要让技术对象……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我想用一个古老的词语来命名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说‘是’也说‘不’的态度:对于物的泰然任之。”[2]1239泰然任之,是哲学家给出的建议的第一部分。同时,“存在”这个在技术世界中“显示自己同时隐匿自己的东西,乃是我们称之为神秘的基本特征。我称那种我们据以对在技术世界中隐蔽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为: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2]1240对神秘的虚怀敞开,是哲学家给出的建议的第二部分。另外,“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给与我们达到一种新的根基持存性的前景……重要的是拯救人的这种本质。因此,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深思。不过,对于物的泰然任之于神秘的虚怀敞开从来不会自动地落入我们的手中。它们不是什么偶然的东西。两者唯从一种不懈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2]1240-1241
是拯救还是毁灭?直面时代困局,沉思新的可能性。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回答。这个工作“取决于,有那么几个人在公众之外孜孜不倦于鲜活地保持一种专注于存在的思想”[3], 这是一个寻找家的行动!寻找人们可以安身立命、“诗意的栖居”的家的思之行动。这就要突破主体性哲学,突破主体性哲学的基本建制——“意识的内在性”。
二克服主体性哲学,突破意识的内在性
海德格尔阐明了主体性哲学基本建制的根本缺陷——无法突破意识的内在性。近代以来,笛卡尔以“自我意识的立场”确立了人的理性的绝对法庭地位,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个体的主体性(Subjektivitaet)。但是,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的主体性乃是借助于意识的内在性被规定出来的,提出了意识的内在性(Immanenz)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以“意识的内在性”制定了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在此基本建制之下,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广延处于一种二元对阵中,“自我意识”如何突破自身到达“存在”,成为决定性的难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乃至胡塞尔,都被框定在这一“基本建制”中而无法超拔。海德格尔把坚持提出解决此类问题的现象称为“真正的哲学‘丑闻’”。伽达默尔说:“海德格尔嘲弄了这种对实体化‘意识’的批判,他把这个问题转变成一种理解被‘意识’预设的存在的本体论批判。他以下面的断言为他对意识所作的本体论批判找到了口号,即此在是‘在世的在’。自那时以后,许多人都开始认为追问主体如何达到对所谓‘外部世界’的知识是荒谬的、陈腐透顶的。海德格尔把坚持提出这类问题的现象称为真正的哲学‘丑闻’。”[4]在三天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对突破意识的内在性、突破主体性哲学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海德格尔首先阐述了“识-在”的问题。何谓“识-在”?在海德格尔这里,“识”乃是指意识,而“在”应该是指存在。因此,大致说来,“识-在”的意思,应该指称一种作为意识的存在。也就是说,意识,本身是有存在特性的,并且是以它的存在特性为根据的。意识本身,是不自足的。海德格尔是从“识-在”与“此-在”的对比中来阐明“识-在”的存在特性的。海德格尔分析道:“识-在(Bewusst-sein)与此-在(Da-sein)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为了切中问题,必须在两个词之中来澄清动词‘存在’的意义……conscience仍然包含着一种存在特性……意识之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Subjektivitaet)被规定的。”[5]意识之存在取决于“我”,意识本身的存在特性,是通过“我思”得到规定的,亦即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个主体性的“我思”并没有就其存在得到询问,亦即我成为主体性的我思,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被就其存在论性质得到追问。在没有得到追问的条件下,人就成为主体并且成了一个不正自明的前提、理论预设。
但是,人,并不直接的就是主体。人称为能思的主体,来源于“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这样一种谬误已久的形而上学规定。这种规定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并在近代科学中,在笛卡尔那里被当作不正自明的理论预设接受下来。总而言之,笛卡尔是从一个很有问题的理论预设出发的,但是他并没有也不会就这个理论预设发问,进行存在论的追问。而且,自笛卡尔以来,这个很成问题的主体性的存在追问就成了禁地,主体性变成了一种障碍,“它阻挠〔人们〕把对存在的追问引向正途”。也就是说,在意识的基本建制之中,人成了主体,并且免于被追问。而海德格尔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个主体性进行存在论的追问,追问其合法性。
意识的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被规定的,因此,在意识中,人成了主体。物,成了客体,成了表象。因为,明确了意识的主体性规定,物被我对设为对象而发生了当前化,被禁锢于意识的内在性之中。因为,意识的基本建制是使自身当前化,而这种当前化的方式,则是问题之所在。“所有的意识都是‘自身使当前化’……这种自身使当前化发生在意识之内在性(Immanenz)之中。”[5]即在主体性之中,所以,意识的存在特性,就是在意识中的存在总是使自身当前化,就是在主体性中的存在总是使自身当前化。这种存在使自身的当前化被意识即主体性的我思,带到了当前使之在场并保持一种当前性,这就是意识的存在特性。也就是说,物,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本应如其所是地存在于存在之空明中,但是,由于意识的基本建制,物被主体性的意识人为地带到了当前,保持为固定的在场,保持为主体性我思对它的表象,失去了与存在的关联,失去了作为对象本己的存有特性(Bestand-haftigkeit)。物被作为表象保持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或者说,在意识与作为对象的物也就是客体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要说与作为物如其所是的存在之间的巨大差别了。
故而,在意识的内在性之中,人成了主体,而物成了表象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这就是近代哲学所面对的“二元论”困难。笛卡尔的“神助说”、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说”、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等,直接地说,都是为了解决这种“二元论”的困难,但更为本质地说,是为了解决意识的内在性这种困难。然而,他们都是不成功的。
为了突破意识的内在性,胡塞尔在意向性中保留了意向客体的位置。胡塞尔认为,所有的意识,都是关于……的意识。这就是意识的本己结构——意向性。何谓意向性?就是在意识中总有意向客体的位置,这是意识的最内在特征,它总是要留一个位置,否则,它就不是意识。而在笛卡尔那里,问题恰恰在于,在意识中,只有表象,关于意向客体的表象,却没有意向客体的本己位置。所以,海德格尔指出,胡塞尔将意向性和意识联系起来,在意识的内在性中保留了意向客体的位置,并使意向客体(即对象)取回了它本己的存有特性,从而挽救了对象,这是胡塞尔的巨大贡献。
但是,“胡塞尔挽救了对象……然而其方式却是,把对象嵌入意识的内在性之中。”[5]意识的内在性的基本建制并没有被突破。主体和客体,内在性与超越性,这两个领域并没有被贯穿。原因在于,“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兹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就此而言,我思是一个封闭的区域。‘从’该封闭的区域‘出来’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5]从我思出发,必然无法到达对象,因而必然导致怀疑论、二元论的困境,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这一西方形而上学之天命。这就是主体性哲学基本建制的困境。
三“识-在”与“此-在”
海德格尔指出,“因此,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5]胡塞尔把对象嵌入意识的内在性之中,虽然保存了对象本己的存有特性,却依然无法到达对象领域,对象领域自身存在仍然是遥不可及的彼岸。因此,从意识的本己结构出发,仍然是从意识出发,从我思出发,必然不可能真正地克服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必然重新落入形而上学的传统之中,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必须从某种与我思不同的东西出发。
“重要的是做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这种经验的进行需要一个与意识领域不同的领域。这另一个领域也就是被称为此-在(Da-sein)的领域。”[5]我看见这个墨水瓶,不是认识、知道这个墨水瓶的质料、范畴,而是领会到这个墨水瓶自身,领会到这个墨水瓶的存在,作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即是领会物自身,而不是知道、认识物自身。领会物自身,作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是与知道、认识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后者,就是“识-在”,就是意识,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态度。前者则需要从一个与意识领域完全不同的领域——“此-在”(Da-sein)出发。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中的在,与“识-在”中的在,完全不同。在“识-在”中的存在,指的是意识的内在性,在意识之内。而在“此-在”中的存在,与之完全相反,其中的“在”表达了在……之外……存在。在什么之外存在呢?在此之外。“此-在中的‘在’表达了在……之外……存在……此-在的意思就是:此出-离地在(dasDaek-statischsein)。”[5]“此-在”,是这样一个敞开的区域,是一个一切可以称为物的都能自身前来照面的领域,是一个让物能够进来的区域,而不是封闭的我出不去物也进不来的我思。在“此-在”这个区域中,物不是被主体当前化的,不是“此-在”努力的结果,而是由自身而来的在场者,物自身前来与我们照面,面对面的相处,是物物相生的结果,与存在有关。因此,“此-在”,变成了一个中间地带,使得所有的可称为物的都能够进来并腾出空间让所有的“物”进来,是一种敞开,一种让渡。“此-在”,作为这样一个敞开的区域,必须守护一种在外,在此之外,让那由自身而来的物明明白白地在外面,共同属于这个敞开的区域。因此,“此-在”的含义是,此出-离地在。在敞开的区域中,“此-在”一向是已经在外的,一定是与那可以称为物的面对面的相处、打交道的。
于是,意识的内在性就被贯穿了,由意识的内在性而导致的存在论的根本困难被破除了。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本质地就是出-离式的。“此-在”之出-离,不仅在于与这个在场着的东西相关,而且与曾在者、当前者和未来者有关。也就是说,“此-在”本质地出-离性是有时间指向的出离,是历史性的,这个在场着的东西,并不是被主体对设的对象,并不是永恒地在场的东西,而只是与我们面对面的相处、相对而逗留于其位的。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这一表达中的“存在”的意思就是生-存之出-离性(dieEk-statikderEk-sistenz)。“此-在”之出-离,就是“此-在”之本质,就是此在之存在,就是此在之生存。意识的意向性,在更源初的意义上,是建立在“此-在”之出离性这个根据上。没有此在之出离性,没有此在之生存,便没有意识。“一言以蔽之,必须认识到,意识是在此-在中得到根据的。”[5]也就是说,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追问意向性的存在论根据,这一根据就在于此在之出离之中。意识是以此在为存在论根据的,是在“此-在”中得到根据的。意识,是此在在世的一种方式。“识-在”不是一个自足的领域,它植根于“此-在”之“出-离”中。所以,海德格尔说,在《存在与时间》中是没有意识的。这即是说“识-在”自身并不是自足的,没有不以此在为根据的意识。这与马克思的说法不谋而合,马克思说,“精神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只有精神的根基即现实个人的对象性活动所生成的物质生活关系的历史。
于是,“识-在”与“此-在”中的“存在”的根本不同的涵义就得到了澄清。“识-在”中的“存在”是被主体性的我思保持在意识的内在性中的存在,这种意识内在性中的存在,是以此在为根据的。而“此-在”中的“存在”,则可称之为物的东西的如其所是的存在,物在此在之出离中,就是在世之中,在存在之空明之中。此在在世,就是世界在此在中。在此在在世中,再也没有“识-在”的独立的位置。
四思想居所之革命
思想不再从我思出发,而是从与我思不同的东西“此-在”出发。思想的出发点的改变,带来了一种存在论革命的发生。海德格尔指出,“从今往后,人出-离地与那是某物自身的东西面对面地相处,而不再通过相对立的表象……对于希腊思想来说没有对象,有的只是:由自身而来的在场者(dasvonsichherAn-wesende)。”[5]海德格尔描述的这种思想出发点的改变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此在出发,人与物,面对面地相处,共同逗留盘桓在存在之中,在此在中,不再通过意识的中介。反倒是意识以此在的出离为根据。
人,不再是主体,不再是貌似统治一切的主人。物,不再是主体建构的表象,不再是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也不再是无法贯穿的对象领域。海德格尔说,对于希腊思想来说没有对象,有的只是由自身而来的在场者,有的只是物物相生,有的只是由自身便已在。在古希腊,没有主体,更谈不上客体,作为客体的对象,完全是近代的事情,是“我思”设定自我为主体时,客体才出现的。而且,对象与在场者不同,因为对象决不可能首先由自身而在场。对象与由自身而来的物不同,是由我思而来,不可能由自身而在场。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之居所(Ortshaft)的革命。
实际上,海德格尔认为,称之为革命,仍然有主体性哲学的色彩,不如称之为“移居”或者说“迁回”“回家”,“也许,将之简单地理解为那原初意义上的‘移居’(Ortsverlegung),便比理解为‘革命’要好一些……思便将哲学曾经置于意识之中的东西从一处迁移到了另一处”[5]由于是哲学把思的源初的居所从世界中、从此在中迁移到了意识中,由于哲学在此在的位置上人为地设立了一个自身封闭的处所(即意识),那么,思想居所的“移居”或者说“返回”就指的是,思将这些离开家园已久的东西“迁回”去源初的处所。“回家”,就是把意识中的东西迁回到此在中,即是回家。
于是,意识与“此-在”的关联便已经被完整地阐述了,也已经可以明确,“意识植根于此-在之中”的含义了。实际上,这种转变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发生,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强调,这种新的世界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现实个人的对象性的活动生成历史,必须从这些现实个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出发来切近历史的真相。
因此,海德格尔指出,要想真正的思,就必须推动思想出发点的移居,进入此在的领域。“离开意识领域,而抵达此-在之领域,是为了正确地看到;作为此-在来理解(也就是,从出-离出发来理解)的人仅仅存在着,就人从自己出发而到达那个与他自身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便是存在之空明)而言。”[5]思想居所之移居的重要意义在于存在之空明对于人的根本性。人,仅仅是与存在相关的生存着,仅仅与存在之空明相关,人不曾创造这个空明。存在之空明、这个空旷敞开者,它不是人。相反,这个空明把自己指派给人,人恰恰属于这个空明。所以,思想居所的变迁,恰恰在于要求从这个空明出发,从这个空旷敞开者出发。这是晚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指涉。
《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似乎根源于它追问存在的意义的方式。《存在与时间》是从此在之出离来切入对存在问题的探讨的。虽然作者的目标一直是存在问题,但是,由于以此在之生存作为切入点,竟然导致许多学者将此在之出离看成是《存在与时间》的目标,竟然导致了对一种存在哲学的人道主义的误解,似乎《存在与时间》仍然停留于主体性哲学的阴影之中。因此,晚期的海德格尔抛弃了《存在与时间》的切入问题的方式,不再从此在之出离出发,而是直接从存在的历史出发,从存在本身出发,以避免落入他所批判的主体性哲学的危险。历史,不仅是此在之出离的历史,更加是存在史。
因此在此,海德格尔再次重申:“我不想再简单地谈论出-离,而要谈论守护在空明之中。”[5]从存在史的角度来看,此在之出离性,其实就是守护在空明之中。从存在之空明来看,此在之出离是处于三重出-离之中,是在存在的历史中的出离。而且,此在之出离,并不是主体、主人,而仅是存在的守护者,要通过整个此在守护存在且持之不堕。
事实上,笛卡尔之后,哲学一直企图走出“意识的内在性”这一“封闭的区域”,不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如此,海德格尔、科耶夫乃至德里达和列维纳斯,都是如此。[6]海德格尔成功与否,我们暂且存而不论,但他要求实现思想居所的革命、思想出发点的转移,对西方哲学的进展而言,还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所谓的存在论革命,就发生于此。只有在这个革命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地克服主体性哲学及其灾难性后果。海德格尔于是指出,“在其新的居所中,思想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意识的优先性及其后果——人的优先性。”[5]只有人的优先性的放弃,代之以存在的优先性、人的存在的优先性,才有可能呈现人与存在的新的可能关联维度,才有可能克服技术的全面统治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海德格尔指出:“当人们把在哲学上将人规定为意识(这种做法)与从此-在出发去思想人的尝试对立起来,此时明显发生的是什么的话,那就很清楚,与放弃意识优先性(这种放弃有利于一个新的境地,也就是此-在的境地)相呼应的是,对于人来说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对这个崭新境地有所准备:这也就是,接近这个境地、投身这个境地,在那里重新得到自己的规定性,以便与那不是人者息息相关。”[5]因此,离开意识领域,而抵达“此-在”之领域,与放弃意识优先性相应的是,人类历史性的此在为投身于存在之空明作出准备,重建人对存在之关联纬度。
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再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历史再一次证明,人类的这种遗忘存在的技术的存在方式带来了人类自身毁灭的危险。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是安全的,或者说,现在人们被迫再一次正面人类无家可归的境况。各国政府在核事故的巨大危险面前仍然对核电站的安全性或者说对人类技术的进步充满信心,这只能再次证明主体性哲学的虚无主义仍然继续在全球蔓延。
21世纪,仍将是一个寻求出路的世纪。这种寻求,也许是乐观的,但也许更多的是绝望。人类将走向何方?在强大的进步强制的必然规制之下,是否还存在自由的可能?晚期的海德格尔从存在真理之发生平面出发,也就是从存在的平面出发,确实展示了这种存在历史之思的深度,也指明了一条应对虚无主义在全球蔓延的可能的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开启。也许海德格尔的指引不是那么明确,也许他的指引同样沦为一种无力,象黑格尔、尼采等思想家的吁求一样。但是,人类历史性此在的本质就在于筹划,而思想家们的指引恰恰就是伟大的筹划本身。因此,让我们在这种筹划中继续前行,也许或者必定可以有新的可能性的开启,会在存在历史中呈现新的世界。因为,对出路的寻求就是我们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郗戈.历史性视域与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命运:以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人的本质”理论为中心[J].人文杂志,2011(5).
[2]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5]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丁耘编译.哲学译丛.2001(3).
[6]张守奎.“意识的内在性”之批判及其限度[J].学术研究,2014(10)
〔责任编辑:李青〕

Revolution of the Field of Thought:
Heidegger’s Breakthrough of Subjectivistic Philosophy
LI Hua
(DepartmentofScienceResearch,SuzhouCountryCadreInstitute,Suzhou215011,Jiangsu,China)
Abstract:Heidegger pointed out the plight of subjectivistic philosophy,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self-closing of “cogito” and disability of breaking the internality of consciousness. As the dominant ontological theory, the basics structure of subjectivistic philosophy may appear as the producerism and technicism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self-destruction of human beings in the modern era. In order to dispel the danger of human beings’ self-destruction and find a solution to it, Heidegger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launching a revolution of the field of thought. There lay a possible road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nihilism in Heidegger’s later profound historical thought.
Key words:Subjectivistic philosophy; basic structure; the plight of era; outlet; the field of thought; r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11-0057-08
作者简介:李华(1976-),女,江苏徐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