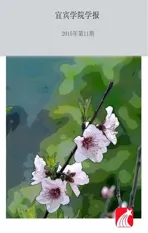“自觉”到“自我”:生命真实存在的历程——基于唐君毅道德哲学的思考
2015-02-14秦碧霞
秦碧霞
(1.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2.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100875 )
“自觉”到“自我”:生命真实存在的历程
——基于唐君毅道德哲学的思考
秦碧霞1,2
(1.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2.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100875 )
摘要:在儒家哲学的语境中,生命的真实和整全,非一节时空片段之现实存在所能表达和呈现,某一具体时间、具体情境中的生命的现实存在,并不就意味着它实现了其真实的存在。对于生命真实存在“历程”的察觉和体验,需要生命主体对经验流变的把握,以及伴随经验流变过程而同时实现的自我主体间转换(超越)。一切纯粹的心理活动和自我主体的确认,皆本于能自觉而后可能,故人之生命真实存在的历程由心之“自觉”而呈现。“道不远人”,生命主体随处直下自觉人性之自然,将我之“我性”与我之“人性”合而为一,即为真实自我的实现,亦生命的真实存在。
关键词:自觉;自我;生命存在;历程;唐君毅
人的生命以何种方式存在,才算是真实的生命存在?这是哲学思考的一个不朽话题。对此,唐君毅先生的回答是:“无不存在之可能之生命,即所谓永恒悠久而普遍无所不在之无限生命”,且“其为人人之所可能”,若“吾人之生命能真实通于无限之生命,即能成为此无限之生命”。[1]20
在儒家哲学的语境中,生命的真实和整全,非一节时空片段之现实存在所能表达和呈现,某一具体时间、情境中的生命的现实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实现了其真实的存在。生命的具有,使得生物的目的并不只在求单纯的存在,而在求生命活动之扩展;生物由此而从物质中提升,进而将“可能”纳入其生命的维持和呈现过程。“可能”甚至比“现实”更为真实。从生成意义上看,“可能”蕴涵着一种改变和创生的“能”,意味着对未实现之“现实”的创造和生发,以及对已实现之“现实”的改造和超越,是生命体(物)与外界(境)相互交感能力的实在。故而,在此意义上,一棵小草的存在比一座大山更为真实。
所谓“历程”,即“凡过程均以不住为性,均以携带过去跨越现在而连接将来为性,亦即均以实现其可能为性”[2]445。由时空流转而成就之生命“历程”,与之赖以生成的“时间”和“空间”一样,虽不依赖于他物而永恒自在,却不可直感,不能从实体的意义上加以理解,须借助一定的载体方能体现。时间流淌于生命体的瞬息忽然、生心动念和行为之间,我们虽无力捕捉,却可通过连接过去和将来的当下经验实存去把握;空间遍在于一切物体中,我们虽不能单独感觉,但可自物体中去丈量。此即,由反省而知有时空。同样,对于生命真实存在的“历程”的察觉和体验亦是如此,它需要生命主体对经验流变的把握(这主要是通过记忆、判断、想象、意志、同情等心理活动来实现),以及伴随经验流变过程而同时实现的自我主体的转换(超越)。一切纯粹的心理活动(通常所谓只有人才能有的心理活动[3]92)和自我主体的确认,皆本于能自觉而后可能,故人之生命真实存在的历程,由心之“自觉”而呈现,它是“自我对体认的实在过程的参与”[4]31。“道不远人”,生命主体直下就人之自然生命与人初生而有之赤子之心处[1]682加以自觉,将我之“我性”与我之“人性”合而为一,即为真实自我的实现,亦生命的真实存在。
一经验流变基础上现实自我的延伸
人由之觉察和体验生命真实存在历程的“自觉”,其终极主体是人的至善本心、能觉之心,它由客观的本体世界(天)所赋予。天是儒家精神性的源头,是一切形式的生命的起源,也是人生活意义的源泉。人之能觉、至善的本心,非西方的mind①,而是heart-mind②,它同时指称人们的思维、判断和感情活动。[5]32“心”之作用在于(与“境”“物”相互)感应、感通,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赋予人以决定能力(“念”),使得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得以呈现。在儒家思想中,“心”是人之为人的道德活动的根本动因,这一点由《中庸》“成己”“成物”之说,以及《大学》中描述自我从认识世界、获得关于外物的知识,直至使美德显明于天下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明晰地体现出来。自此“物我一体”的互感出发,生命个体就能够直接由人心之体验以言天性、天德,以人心通于天心。
至善本心的先天具有,从根源上解决了自我实现的朝向(价值取向)问题,从而使体察生命主体经验流变的自觉得以实现。如查尔斯·泰勒所言:“与我们对认同的需要相关的自我概念,意指突出人类主体性的这个关键的方面,在没有趋向善的某种方向感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获得这个概念,正是依靠它我们每个人才本质上(即至少特别是规定我们自己)拥有立场。”[6]46“我们只是在进入某种问题空间的范围内,如我们寻找和发现向善的方向感的范围内,我们才是自我。”[6]47
“自觉”和“自我”是两个相依而生的范畴,讨论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回避另一个,在强调心性内修的儒学中更是如此。杜维明先生将儒家的自我视为“一个精神发展的动态过程”[7]116,是一种回归先验本质的活动,这主要体现在儒家独特的自我对他人参与的需要和与他人不可避免的共生[7]116。事实上,在生命主体经验流变基础上而展开的现实自我的延伸,亦是对这一“精神发展的动态过程”的另一诠释。
自我起源于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积极的生命活动中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体现着天道的完美个体的实现。因此,自我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不变实体和静止状态,而是生命个体连续生成的过程,从个人现在(的状态)延伸至过去和未来。只有当个人显明了人性中所包含的天道(理)时,他才具有自我的特征,成为真实的生命存在。故在自我确认方面,“我是谁”的问题本质上与“我从哪里来”及“我将成为谁”紧密相关。傅振中从时间、空间、身份和角色四个向度对个体自我所作的解释,对我们理解现实自我的延伸有一定的启发:在时间向度上,个体自我不是一个确定的实体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成长或修为的过程;在空间向度上,个体自我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领域,而是一个经由广延的交往关系而共同塑造出来的意义领域;在身份(status)向度上,个体自我并不呈现为一般的人、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政治国家中的人等人格上的转化与断裂链条,而是一个通过生命实践而逐渐呈现自我完整目的的人;在角色(role)向度上,个体自我并不呈现为一种单向的绝对排他性,而更多地通过双向互惠、互为的方式,在一种融历史传统与当下人际于一体的人文环境之中,通过彼此制约与相互给予而共同成就。[8]
现实自我在生成上所体现出的延伸性,源自心之自觉能力所产生的个体生命经验的流变。与天心相通的人心,“其所思者,恒能上穷碧落,下达黄泉,前通千古,后达万世,无得而限定之”[9]814,人心之特质便在于能自觉。人的自觉能力是构成一切纯粹心理活动之基础,一切纯粹的心理活动都由人有自觉能力而后有。如记忆、判断、想象、意志、同情等,都是待人之能自觉而后有。以记忆为例,记忆是以过去我之经验内容为对象,故是一种现在我回溯过去我,亦即是现在我自觉过去我的活动。如果没有自觉,则记忆不可能。
“现在我”自觉“过去我”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现在我与过去我之对待不同,其间有时间之间隔;二是现在我与过去我之间虽有时间间隔,但我们同时却知道过去的“我”即现在的“我”,过去我之经验内容即是现在我之经验内容——不同时的我之经验内容,是一致的、相贯通的、统一的。此即表明,自觉是(过去、现在)经验之统一者、贯通者,它能超越经验之限制而活动。以记忆而论,在记忆中我们于现在重现过去之印象,而又知此印象之内容是我过去之经验内容。这一方面表示我之自觉力,能将过去、现在的经验贯通统一;另一方面即表示我之自觉力能超越我现在之生活经验,以回向过去;同时使过去我之经验内容,超越出其过去所隶属之经验系统,不复限制于过去我之经验系统范围,而成我现在之经验内容,隶属于一现在我之经验系统。因此,自觉力之本质功用,正是使我们超越经验之限制[3]94。
可见,由自觉对经验限制之时空超越所生发的经验流变,使现实自我的生命存在能够在时间的流动中以过程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以当下为纽带在不可穷尽的来龙去脉之间将过去和将来连结而无限延伸,从而成为一统一贯通的自我。正如墨子刻所言:“自我意识‘同时兼知’新的对象物和储存于在先前体验的记忆之中的事物。这就是说,它在持续着一种比较的过程和包含着理的‘范畴化’过程……意识自我‘不利用它所储存的过去的感觉去损害它将要获得的感觉’。这就是说,体验的观照和范畴化过程是完全客观的,它允许过去的感觉和新近获得的感觉保持一种非程序性的联系。”[4]31
二现实自我主体的转换
墨子刻指出:“道德生命不仅仅是‘感’,它也是‘成’。”[4]36意指由“如实知”起“真实行”,是生命个体自我实现的必经过程,其间有一个从经验体认到身体力行、自我确认的转折。此处之“成”,既是“成己”也是“成物”“成人”,所成之己、物、人的终极归指是同一的:“成仁”。这既为天性普遍于万物之中的儒家基本理念所决定,亦由至善本心为自我实现所确定的善的方向感所至。成人(仁)之道的实践不须远求,唯待人于日常生活中人性之自然表现处而加以自觉,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始终是处于具体情境和“关系”中的,这就使得作为个体普遍道德理想的“仁”必须落实于具体的现实,考虑自我与他在的关系协调。
如果我们用“己”指称“自我”,则可以用“物”“人”(他人)来指称与自我相对应的“他在”,由此描述自我与他在的关系。《中庸》之“成己成物”,孔子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0]即是分别对自我实现过程中,己与物、人关系的论述。唐君毅先生亦从自我的“关系”视角,就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人道之实践时当如何用心,提出数点:“自觉我是人”“自觉我是人之一”“自觉我是一定伦理关系中之人”“职分与所在群体之自觉”“我之唯一性之自觉”等。[9]813-824不难看出,如是五点相互之间有着层层递升的逻辑关系,是生命主体逐渐显发真心真性、呈露真我的历程。其中,第一点“自觉我是人”重在就“自觉人之异于禽兽者之‘几希’”[9]813而言,当然,亦可从儒家更为广阔的物我关系视角来解读;第二、三、四点则是就己与人的关系来谈。从将自我与非人的万物区别开来而定位于人之类,进而从伦理关系、职分与群体关系中获得自我之自觉,最后于任一时之当下情境中实现我之“我性”与“人性”的合一,这从表面看是自我关系范围的逐渐缩小,事实上是现实自我在主体上的转换。
教学督导委员会根据调查问卷和访谈记录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各项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可以按达成、基本达成和未达成得出定性评价结论。
此处论及自我的划分问题。在心理学及社会学中有对自我的二元论划分,或从主客体上作“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之分,“主格的我”(I)与“宾格的我”(me)之分,或从个体内部作“心灵的自我”与“身体的自我”之分,等等。事实上,体现为“关系自我”的儒家自我,在构成上是非二元对立的。借用“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划分的名称,自我所对之任一他在,事实上在自我身份的确认中都是一“外在自我”,自我总要根据具体的他再来进行自我确认。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其它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在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确认的。亦即,真实自我的确立是以自我与他在的统一为基础的,在这种统一中,他对自我的反映不仅仅被视为映现人真实自我的想象性“镜子”,也不被视为是隐藏个人真正同一性的“面具”,而是作为人的同一性的重要部分,成为自我的内容,这一内容与人自己的观念一样真切而实在。
在此意义上说,自我是不可作结构上的二元分离的——在现实自我向真实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其被区分的相互之间总是维持着动态的相互转化和生成的关系。我们可从自我在生成上的延伸性视角,将其区分为“现实自我”和“真实自我”,现实自我主体无限趋近于“仁”的真实自我是在现实自我主体(现实自我参照相对的他在而对自我所作的身份确认)的不断转换过程中逐渐显现的。以上文唐君毅先生对人道之实践的五层划分为例,现实自我的主体则经由己物关系中的“大我”(物)转换至己人关系中的作为类的人,进而转换为类中之个体的人,再转换为一定伦理关系中的人,直至特定职分与群体中的人……在这一主体的转换过程中,现实自我因主体的不同而自觉体认和践行相应的不断细化的德性要求,充量地实现我之“我性”与我之“人性”的合一,以逐渐趋近真实自我。这也是自我确认过程中主体转换的意义所在。
(一)己与物的关系方面
天性的赋有使得人心能够在与境之感通过程中获得对外物的体认,这种相互体认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甚至存在于意识与动物以及诸如石头之类纯粹物质客体之间。由此,我们也就更好理解作为“‘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11]9的“礼”的形成,成人(仁)过程中的主体关系的处理必然关联着“礼”的考虑。“礼”在本源上具有“祭祀的”意义,后引申为“合乎时宜”,当其与“仁”相联系,并以“仁”为核心、互为表里的关系时,方获得人实现“自我转化”的“行动”的意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维明将“礼”视为“人性化的过程”[11]14,认为其基本含义就在于:“如何采取适当的步骤以便使自己或者遵从超越的他在给予的命令,或者从这超越的他在身上引发出祈求得到的回答”[11]22。
人的自我必须在己与物的关系中才能建立起来。己、物关系中的物,涵盖所有与己相对的他者,当然也将己与人(他人)关系中的人纳入其中。故,己与人的关系从属于己与物的关系。在己与物的关系中,天赋仁心为自我实现提供的善的指向,使自我的确立直接基于对人类以至整个宇宙的终极关怀,达到“视天下万物无一物非我”的地步。如此而来,“成己(小我)”与“成物(大我)”的过程是合一的,如在亲子关系中,父母不过是与“自我”相联系的“物”,而个人对父母赐予其生命的感激意识基本上被指归于宇宙自身,只不过派生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而已。故《孝经》中说,在孝顺中,没有比“配天”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二)己与人的关系方面
此处己的关系对象“人”,包括了与己相对的他人、群(团)体、国家等。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0]172即言人必须生活在人伦之中,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不能说没有,但那只是变态而非常态,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生活关联中才能实现自我的确认。
儒家的自我并不是脱离生活细节而存在的孤立个体,而是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如孟子指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是社会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由此亦可说,人的个体生命是由他所属的群体支持和塑造的,尽管其生命自觉总是从对独特自我的意识开始,但这种对自我的意识也是从他人的反应中获得。如孔子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10]28,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则是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0]2这三个方面进行,这种内省反思型的思维方式类似于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所谓“类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的态度,即“整个共同体的态度”[12]156,“个体从同一社会群体中其他个体成员的立场或从他所属的作为整体的社会群体的一般立场,如此间接地而不是直接地体验他自己。”[12]144若将自我的确认简单地看作是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那么“我是谁”的问题和“你是谁”的问题实际上是同一探究的两个方面,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可视为在此意义上形成的行仁之方。所以,郝大维和安乐哲亦指出,孔子所区分的“己”与“人”的对立面是相互涵衍、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反映某种内在的本体差别的二元。在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中,“己”总是在“成人”,“人”亦总是在“成己”。因此,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内在的,也是自我的组成部分。[5]30杜维明也认为,儒家的自我是一种“发展的自我”,“是一种对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的毕生承诺”;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系统”“在自我修养中不断深化和拓展他人存在的意识”,从而“保持健康的人格同一性”。[7]117
三人格独特性的确认
虽然儒学承认生命个体对普遍“天性”的先天秉承,且强调个体在后天生命活动中对共有天德的自觉追求,以期实现真实自我,这既是人心向天心的超拔,亦是人对其本性的自我复归。但个体的人对同一德性的践履和复归,并不意味着人格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抹煞。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所强调:中国人的人格独特性是内在的,存在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永不止息的变化过程中[5]30;一个维护恰当意义上的个性的社会模式,能够保持怀特海所说的“个体的绝对性”(individual absoluteness)与“个体的相对性”(individual relativity)之间的平衡,这种模式将个人同社会组合的关系解释成丰富和加强个人自我实现的潜能[5]31。因此,现实自我经由个体的自觉体验和修为历程,转化而成的真实自我,涵盖了我之“人性”与“我性”,且于当下即可呈现。
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克己”一般被理解为自我约束、竭力克制自己的物欲。事实上,这也意味着人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华莱(Waley)指出,“克”也表示“有能力的”③。故“克己”与“修身”是同一的。由此,“复礼”也就具有了主动意义:使人按“礼”来行动,是积极的干预而不是消极的顺应;其中,“礼”从词源上讲,象征着祭祀的活动,后引申为“合乎时宜”的行为,当其与“仁”相联系,并以“仁”为核心、互为表里的关系时,便获得成为人实现自我转化的行动的意蕴,通过对行为的规定而赋予一个人(或人类)以意义。居于儒学价值体系最高层次的“仁”,作为形而上学的实体,是自我修养和本体论的基础,指称通过个体修为而达到的最高的人生境界。“为仁由己”,强调了“己”之天赋“仁心”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含义,故有“我欲仁,斯仁至”之说,它揭示出“成仁(人)”的自我实现活动是生命主体的内在决断,“克己复礼”的能动之源存在于自我的“仁心”之中。
因此,从历时性角度看,行礼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是在沿袭形式化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表现自我的意义。这一过程不是个体去向外追寻,而是向内对自身的“性”“理”“良知”“良能”等进行把握的自我认知的过程,是对自身的精神状态的理解和内在情感的体验,它不仅仅是对现实自我的反映和理解,而且更是对现实自我的超越和创新。儒家的希贤希圣以至最终圣人境界的实现,均不是生命机体从外界投射、获取,而是真实自我本性的展现。礼的实行永远是独特的,因为作为禀赋天性之实体的人,是富有活力、不断变动的,故而人的进步、教养和完美的潜在可能性,亦不可限定。
真实自我的实现,即“成仁(人)”之道自何处始?我们的答案实亦无他,即“直下顺此自然之生命,与人之赤子之心性之善”[1]682而充量地加以表现。此即言,生命真实存在的历程,并不待远求,不待对人性有穷尽之研究与分析,而唯待人就此日常生活中、人性之自然表现处加以自觉,以知其所以为人,此之谓“道不远人”,亦即道在迩而不须求诸远,事在易而不须求诸难。
墨子刻认为,基于唐君毅的这种生命个体自觉体认感的自我实现的观念——现实自我与他在之感通的产生,内在地渗透、贯穿于生命个体本性自觉中,从而掩盖了主客体之间的任何隙距——最终必然导致诸多现实因素的撇除,如冲突、对抗的困境意识,当时人所体验的精神上的不确定的苦恼,被肆意滥用的帝制权力、官僚的腐败、绅士和商人的压迫以及经济的衰败等等。[4]38的确,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问题。儒学的道德理想来源于人的生活实际,它一旦知识化、规范化、制度化以至本体化而成为人的精神家园,便又不可避免地形成对现实生活的遮蔽,理想的精神家园随之就可能异化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的桎楛。人的真实生活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建构于其上的伦理精神家园亦须与时俱进,这就需要我们时时透过精神家园回望现实自我与他在共有的生活世界本身,这是自我的存在根基、超越之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唐君毅先生以“丧失意义的危机”为基底,揭示近代中国伦理文化在外来文化思潮冲击下的状况:一是存在的惶惑,二是道德价值的失落,三是终极信念的失落。反观时下,人们因丧失意义的危机而产生的“精神迷失”非但无减轻之势,且有加剧之态。当代中国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飞速发展,人的身份感、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在多元价值文化的冲击下发生着急剧变化,存在的惶惑和自我认同危机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如何在自我与他在的互动中,探求合理的自我确认,实现生命的真实存在是人们普遍面临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唐君毅先生基于生命个体自觉体认感而构建的自我实现的探索路径,或许在当下这一人化于物、只知求生于自然而不知生于内心的时代,所起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我们同样难以否定,其对现实因素及困境意识的撇除或许亦能在这一生命力薄弱、缺乏道德勇气的时代,激发人们追求生命真实存在的魄力。
注释:
①mind指柏拉图意义上的心灵、精神,或者理性的心。
②heart指生理学、生物学上的心,也指主要表现为情感的精神、心理状态;mind表示心灵、心智、理智、智力和知识。
③转引自郝大维,安乐哲著,施忠连译:《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98页。
参考文献:
[1]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M]//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C]. 全集校订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8.
[3]唐君毅.心物与人生[M]. 全集校订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9.
[4]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颜世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5]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M].施忠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6]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7]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曹幼华,单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8]傅振中.传统儒学对现代民主理论的“兼容”与改进:以个体自我的理解为基点[J].学术探讨,2012(6):15.
[9]唐君毅.哲学概论: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M].胡军,于民雄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12]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从社会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出发[M].胡荣,王小章译.周晓虹校阅.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5.
〔责任编辑:李青〕
From “Self-consciousness” to “Self”: The Course of the True Existence of Life:
Thinking Based on Tang Jun-yi’s Moral Philosophy
QIN Bixia1,2
(1.College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XinjiangNormalUniversity,Urumqi830054,Xinjiang,China;
2.CollegeofPhilosophyandSociolog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 real existence in a section of time and space cannot express and present the true life and the whole of life, and the real existence of life in specific time and concrete situation does not mean that it has achieved its nature existence. The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 of the “course” of the true existence of life need the subject of life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ce, along with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experience to achieve transformation (transcendence) between self-subjects. The possibility of all pure mental activities and confirmation of self-subjects is rooted in that the subject of life can be self-conscious, so the course of the real existence of human life is presented by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heart. “The way to be human is always in your heart”. The subject of life gets straight down and is conscious of the true ex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and it merges my “self-nature” and my “human nature” into one, that is the realization of true self, as well as the true existence of life.
Key words:Self-consciousness; self; the existence of life; course; Tang Jun-yi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11-0009-07
作者简介:秦碧霞(1980-),女,四川广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