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在武乡监漳村
2015-01-26崔晋峰
崔晋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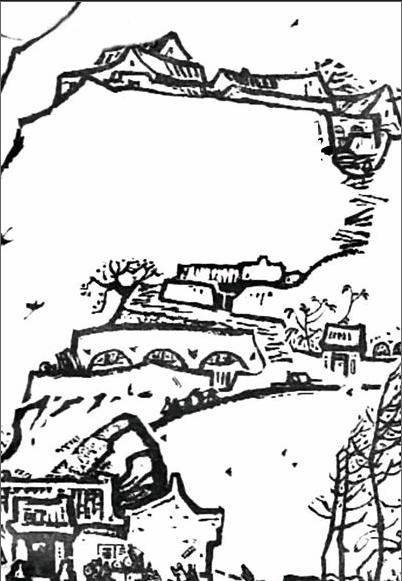
1951年春,中共长治地委在全国首开先河,分别在7个县9个村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山西武乡县监漳村试办了东、西两个合作社。
这一年的3月,当代著名作家赵树理随同地、县工作组来到监漳村。他参与了该村合作社试办的全过程,以后又亲历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和发展。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亲身参加了村上的扩建灌渠、修筑道路、平整土地、春种秋收以及田间管理等各项工作。
老赵每天与老百姓一起开会学习,一起下田劳动,一个锅边吃饭,一盘炕上谈心。村上的人们都知道虽然人家是北京来的大干部、大名人,但看到他衣着一般,与老百姓说话随和,又没一点架子,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庄户人,所以人们都愿意和他接近,见了他不拘束,见面打招呼随随便便,不论大人小孩,都称他为老赵。
当时这里的每一块土地,每一项工程,每一件工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奉献了他的智慧。他和这里的老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他以监漳村为主要背景,以扩社、修渠为主线,以村上各有特色的人物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三里湾》。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
老赵进村以后,全身心投入合作社的试办工作。他和地、县工作组的同志们一起,日夜操劳,不辞辛苦,制定试办的总体方案,进行入社土地的评产,制定合作社章程以及各项经营管理办法和远景规划。
为了提高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他把试办的宣传鼓动工作紧紧抓在手上,依靠村党支部的领导,充分发挥青年团、民兵和妇联会的作用,通过改造原有的业余剧团,组建了俱乐部。俱乐部分编辑组、板报组、演出组、读报组等。编辑组负责编写演唱材料和大众黑板报文稿;板报组负责全村六块大众黑板,每星期换写一次;读报组由9名读报员组成,负责选定报刊文章。每逢午饭时,分头到村上的各个饭场给群众宣读讲解。
村上规定农历每月十五为“爱国日”,这一天,村干部要向群众做前段工作小结并表彰好人好事,然后是文娱节目,由演唱组登台或在广场进行演出,既有戏剧、鼓书、相声,还有学校儿童们的小花戏、霸王鞭。当时山西省文工团的全班人马常驻本村,一是体验农村生活,二是辅导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他们往往与俱乐部同台演出,为“爱国日”助兴。
监漳村的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到处是一派社会主义的崭新气象。农民艺人程志全说:“沿村看黑板,饭场听读报,看戏听说唱,每月十五号。”当时黑板上写的、读报员讲的、台上唱的,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天下大事(当时正值中苏友好,抗美援朝);二是社会主义美好远景;三是办社动态;四是本村的好人好事。凡是村上出现的好人好事,都要上大众黑板表扬。所以在全村出现了人人争办好事的积极氛围。办社初期,集体缺乏实力,购买牲口和新式农具有困难,社员程四元就把土改以后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20万元存款(旧币,当时折合小米1800斤)取出来入了社。老赵抓住这一典型,在群众会上讲,在大众黑板上写,编辑组还及时编成文娱节目登台演出。程四元的行为产生了积极的效应,社员们有的投粮食,有的投现金,还有的投木料,不仅充实了集体经济,而且增强了入社农民爱社如家的集体主义观念。
当时编辑组编写出的材料,老赵都亲自过目进行审查和修改,由于他多才多艺,不仅能编会写,而且精通锣鼓管弦等民间乐器。这里不妨插个小曲,据说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有一次他到黎城县的一个农村下乡,当地遭遇灾荒,由于天灾敌祸,老百姓苦不堪言,情绪低落。干部下乡工作不仅很难召开一个群众会,甚至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找不到。老赵进村以后看到一个磨盘上有几个人摆弄锣鼓乐器,他便走过去随手抓起一件家伙,有板有眼地敲打起来,一边敲打,一边按鼓点演唱起抗日歌段来。周围的人们都乐了,惊叹他如此高超的乐艺,个个拍手叫绝,不一会儿就把全村的老小都招来了。
老赵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讲起了边区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自救的重要指示,把人们来看稀罕看热闹变成了群众动员大会。他的讲话鼓起了大家的勇气和信心,纷纷表态要抓紧生产,战胜灾害,做好抗日支前工作。会后,人们都争抢着要老赵到自己家里吃饭。老赵有如此特殊的艺术才能,除了审查和修改文艺演唱材料,还亲自参加演唱组的戏剧节目排练,从文武场口到每个演员的唱腔、道白和手脚身势、面部表情,他都要一一认真加以指导。由于他的辛勤工作,为监漳村培养了一批文艺编写人才、戏曲演员和民乐队员。
后来,在山西省文联主办的《山西文艺》杂志上曾开辟过“监漳社员快板集”专栏,并出版了《歌唱高级合作社》单行本,全都是本村农民的板话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监漳村俱乐部成为武乡农村文化的一面旗帜。
形象生动的临场讲话
老赵爱说爱笑,会讲故事,但老百姓最爱听他在会场上的讲话。他的话幽默动听,格外吸引听众,加上他会说武乡土话,老百姓听了更加感到亲切、实在。如武乡土话说“昨天”是“夜来”,“下午”是“晚期”、“玉米”是“玉茭”,“窝头”是“干粮”,“黄花菜”是“金针”等等,这些土话都进了老赵的口头语。他进村以后,多次在群众会上讲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当时在场的听众多数是不识字没文化的老百姓,他从这一实际出发,在讲话中很少用理论术语,也没有多少哲学名词,而是用老百姓的口头语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好。如武乡土话讲“富”是“有”,我们一般人讲到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但老赵是这么讲的:到了社会主义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
监漳人们最早听到的“到了社会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出门坐汽车,家家住高楼”的佳话,就是老赵在群众会上讲的。当时在太行山区,不用说在乡下农村,就是在武乡县城也见不到一辆汽车,电灯电话就更不用说了。监漳村距省城太原不足200公里,当时去一趟最少得三天半时间,七天才能折个来回,去一趟长治最快也得两天多。有个小孩问他70多岁的爷爷这辈子到过太原没有?爷爷回答说:“我—个老庄户,哪有本事去那个天边?”由于交通不便,山河阻隔,人们把长治、太原都看做是“远在天边”了。
老赵当时讲,到了社会主义,咱们监漳也会通汽车路,如果你有急事要上太原或长治,当天就能折个来回,把“远在天边”一下子变为“近在眼前”。他的讲话中没有用“发展生产力”这个句子,他讲,到时耕地种田有拖拉机、播种机,还有收割机,吃水用水有自来水管,吃米吃面有机器加工,再也不用牛拉石磨人推碾了。
当时老百姓最辛苦的活儿,一个是推碾滚磨,—个是肩上挑担。妇女们整天围着碾磨转,也供不上全家人吃,有的小户人家往往是吃一顿碾一顿。男人们一年四季肩上离不开扁担,早起挑水,春天送粪,秋夏两季往回担庄稼,冬天到煤窑上担炭,反正两个肩膀通年不得闲,一条扁担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为了让老百姓好懂,老赵讲话时没有用“解放生产力”这个词语,而是讲让妇女们从碾台磨坊跳出来,男人们的肩膀也要解放,让扁担失业。他的讲话是那么动听,令人向往,令人振奋。在场的听众个个聚精会神,都仰着头,两眼紧紧盯在老赵的身上,只嫌他讲得时间短,连讲两三个钟头,人们感觉只有几袋烟的功夫。人们说,听老赵讲话比看一场好戏还来劲。
自从老赵进村以后,开群众大会不用专门通知,人们都及早赶来会场坐下,比看戏还抓得紧。老赵每次讲完后人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往往会议已经结束,人们还不肯散场。
有天晚上,群众大会结束,时间已经很晚,但人们就是不肯散,还想请老赵搭个小插曲讲个小故事,哪怕逗个笑话也可以。老赵不想扫大家的兴,他指着东社的生产组长程志全说:“听说你夜来黑夜做了好梦,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呀?”这位生产组长既是种田能手,又是民间艺人,虽没上过学,却满肚诗文,每每出口成章,开口就是一大套。老赵一进村就和他交了朋友,两人见面无话不说,因为他张嘴就是顺口溜,胜过当年陕西临潼的王老九,所以老赵称他为“赛老九”。老赵几次在会上的讲话,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深感社会主义的美好。于是他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顺门念道:
一听老赵发号令,
志全立马就响应,
黑来做了一个梦,
不由浑身都来劲。
春风吹来监漳滩,
合作经济打头阵,
学习苏联老大哥,
乐坏全村老百姓。
到时耕牛不下田,
青壮劳力不担粪,
牲口不推磨,
碾台无人问,
扁担失了业,
自来水管进水瓮,
机器耕、机器种,
肥料都用汽车送。
深耕细作产量高,
家家户户粮满囤。
白面大米家常饭,
金针木耳猪肉炖。
穿新衣,住楼房,
黑夜电灯亮堂堂。
梦想何时能兑现,
明天再请老赵讲。
“大家说好不好呀?”
“好!”
下边应道。人们在欢笑声中散了会。
老赵眼里朋友多
老赵进村之前,县领导认为他是个全国名人,级别又高,不同于一般干部,所以计划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吃住固定在一户卫生条件较好的人家,省得今天东家明天西家。
谁知老赵进村后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坚持要住农家吃百家。由于他吃派饭住农家,进村后不久,就结识了许多朋友,有村社干部,有种田农民,有羊工,有匠人,还有学校老师、乡村医生,在他的眼里,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用他的话讲,他的朋友就是老百姓。时过60多年,老赵给人的印象,还深深留在监漳人们的心里。
一位80多岁的老农谈起当年老赵住村上工作的情况时,深有感触,津津乐道:“老赵那么大的职衔又满肚文才,站在咱老百姓堆里,谁能认出人家是个当干部的?平素吃饭时,常好端着碗来到饭场上,和俺们这些扛镢头的,耍放羊鞭的挤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三和面抿圪蚪,一边有说有笑,用咱监漳人们的土话拉家常,成天和俺们这些庄户人滚在一块儿。”
村上有个外号叫“常有理”的王大娘,为人处事爱占便宜不吃亏,惹得众人不待见。但老赵对她也不下看,见了面照样用关爱的口气问长问短。老赵讲:“有点毛病不能算赖人,毛病可以改,应该多看人家的长处。”后来,王大娘也报名入了社,在扩建灌渠时又扛石头又和泥,总结评比时还得了奖。
1953年6月,监漳农业社长任焕孩到首都北京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时,老赵专门去招待所看望她,两人一谈就是两个多钟头。老赵除了听取焕孩关于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详细汇报外,就是打听村上那些老朋友,从老支书任余庆,村长崔晋财,社干部任磨成,一直问到“赛老九”程志全,“活鲁班”崔全林,“翻的高”成来水,“猛张飞”暴海云等人的近况。当焕孩给他讲“猛张飞”暴海云最近结婚成了家时,老赵高兴地鼓起掌来。他说:“海云是个好后生,心直口快,就是脾气大,一阵风,但工作起来一盆火,有作为。”村上的人们说,海云肯发火,三句话不对头就能和你吵起来,说他急了是云遮雾罩,圪雷炮仗,过后是烟消云散,一片晴天,所以得了个外号“猛张飞”,老赵进村不久就和他交上了朋友。他是个放羊的出身,也没上过学不识字,一直担心自己打一辈子光棍。老赵劝他不用着急,慢慢来,还教他认字学文化,在群众会上几次表扬他公字当头肯干工作,又在民校扫盲学习班当了模范,于是在姑娘们的心目中对他产生了好感。后来老赵也把他以“一阵风”的外号写进了《三里湾》一书。
监漳人走进了《三里湾》
1951年,农村行政建制还没有乡这一级,区以下是村。村政办公的地方叫村公所,监漳村的村公所设在一户原财主的房院里。这所房院分前后两个院,前院是村公所、民校和民兵队伍,后院住着一户贫农。其中一户是位烈属,老伴早年下世,儿子是民兵,在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老人善良厚道、手脚勤快,很受众人的爱戴,因为她住在后院,人们习惯了都叫她“后院奶奶”。平素,她常到前院来给村公所不是扫院抹桌椅,就是送开水,冬天帮助看火送炉灰。上边来了女干部,晚上就和她睡一个炕上,老赵在村上时有空就进后院和老人拉家常,有时还帮她担水、推碾子、和煤泥。事后老赵把老人写进了《三里湾》一书,在书里展现了“后院奶奶”可亲可敬的生动形象。
村上的权威老农崔全林,当年已经六十开外,是个多面手,不仅会种地,而且精通各路工匠手艺,修房盖屋,做木器家具,开石头做碾磨、生烘炉、打造铁器农具,样样都是好把式。由于他心灵手巧,做工精细,所以人称“活鲁班”。老赵进村以后,对“活鲁班”老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两人成了好朋友,见面无话不谈。老赵叫他“活鲁班”,他称老赵“文昌爷”,老赵一有空就和老人谈心,征求他对办社的意见,欣赏他的工艺制作。社里扩建灌渠时,渡槽石桥上有处漏水,好长时间无法解决,老赵就把老人请到石桥工地,他上下左右仔细查看,终于找着了漏水的根源,一个下午就把问题解决了。老赵称赞他说:“你真确有办法啊,真不愧为‘活鲁班。”老人笑着悦:“咱一个老庄户,只会干些粗笨营生,哪敢比你文昌爷?”《三里湾》一书中外号“万宝全”的老人王保全,其原型就是“活鲁班”崔全林。
老党员成来水,是抗日战争时的老八路,又是村上的主要干部,土改分配果实时他是头一份,好房好地还有大牲口,粮食和钱。人们说他不仅翻了身,而且翻得高,即使这样,人们也对他没意见,都认为他在旧社会吃尽了贫穷的苦,从抗战到土改样样工作挑大头、卖力气。问题是他翻身以后,只顾个人小家庭,忘了当年的穷兄弟和老同志,工作不愿干,开会常不到。对试办合作社不仅不热心,而且有抵触情绪,原因是他的土地好,牲口壮,入了社怕吃亏。试办开始时,支部分工让他担任宣传组长,负责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及试办合作社的重大意义,并动员农民入社。因为他本人就不愿意入,支部却让他负责宣传动员工作,这不是给他出难题,将他的军吗?不过他当过多年干部,在政策上要比一般老百姓懂一些,他抓住了一条,这次入社是讲自愿,不准强迫命令。他在支部会上讲,入社要自愿,你们还能强迫我入吗?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支部的领导成员,竟说出这样的话,立刻受到同志们的严厉批评和指责,有人提出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老赵说:“撤职开除并不难,关键是思想问题要解决。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我们应当争取他的觉悟。”后来,经过同志们的批评教育,他还是觉悟了。事后他对人们讲,是老赵打开了我这把生锈的锁,把我拉回正道上来的。《三里湾》中的村长范登高,外号“翻得高”,其原型就是监漳村的成来水。
1955年5月,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出版问世,轰动了中国文坛。
当监漳人们见到刚出版的这部书时,一看书名,便想起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南滩到北滩,三里一道湾”的顺口溜。人们兴奋地双手捧着书本,扑面袭来的是油墨的清香。他们迫不及待地将书打开,一页一页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恨不得一下子从头看到尾。当发现书中的许多人和事以及书中的不少地名如“青龙垴”、“三十亩”、“刀把上”、“上下滩”、“黄沙沟”等都是取材监漳村,甚至把外号“常有理”的王大娘也写进书里时,人们读着、读着,感到格外亲切、实在。大家高兴地说,咱们临漳人都走进三里湾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