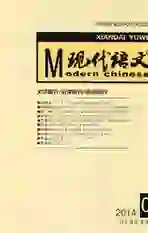语义方阵中《白鹿原》的白嘉轩形象研究
2014-04-09吴谦红朱媛
吴谦红+朱媛



摘 要:《白鹿原》中人物的自我矛盾、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框架,展现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焦虑感,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多面性。《白鹿原》中人物自我意识的矛盾以及价值观与外在环境的不融,导致人物无法寻求准确的定位而被束缚在矛盾对立中,最终走向悲剧。
关键词:《白鹿原》 语义方阵 人物形象
拥有宏大结构与深厚历史背景的《白鹿原》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别具匠心。《白鹿原》人物身份特征和命运发展都存在一种独立平等的不相融合的声音,构成了二元对立的语义方阵。《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于人物身份、命运两个方面都存在二元对立关系。首先,身份决定人物之间的关系。文本中有着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人物各自身份决定了人物之间有鲜明的对立关系。这其中有隐藏着的矛盾,有支持的辅助者,也有反对的迫害者。从身份立场看,文中的人物关系应划分为三层:对立关系、矛盾关系、补充关系。与之对应的身份人物形象构思也存在主角、对手、反对者、辅助者四个元素,从而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其次,文中人物命运发展的叙述模式在“有、非有、无、非无”之间反复循环。文中人物命运发展轨迹遵循着“有无”二元对立模式。下面就以白嘉轩为例,分析《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的二元对立模式。
“语义方阵”是根据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与《白鹿原》中的二元对立关系相契合。格雷马斯认为“故事的发展轨迹与语义方阵的运动方向是相对应的。故事的展开也是从某一特定因素向其相反或矛盾方向转化”[1]。所以我们结合语义方阵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有无”二元对立方阵分析人物形象,用图一来分析人物的身份,用图二解析人物的命运轨迹,如下所示:
一、族长身份
白嘉轩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矛盾结合体,他既是族长,也是父亲,亦或是代表男权至上的丈夫。首先我们来分析族长白嘉轩的语义方阵:
白嘉轩在方阵中居于主角的位置,是一个有着多重文化内涵的圆形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白嘉轩在成长中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每个阶段都展现出不同的形象特征。他的身上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辉,同时也具有人性的弱点。白嘉轩具有农民朴实勤劳的特质,坚守着“耕读传家”的圣训,精通耕作种植。同时他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汉子,策划发动交农事件,拒不接受任何官职,与军阀直面对阵。作为封建家族的大家长,白嘉轩兼具领导能力和责任感,在村民眼中树立了仁义族长的完美形象。与鹿三的朋友情谊、对子女的严格管教、修祠立碑、兴办学堂、设法搭救鹿子霖和黑娃等事件,体现了白嘉轩作为族长的仁慈宽厚以及作为父亲的严苛自律。但作者并没有把白嘉轩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物,他也具有人性的弱点和内心的阴暗面。在小说中,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贯穿始终,白嘉轩自认为一生中做过最见不得人的就是“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仁义族长的形象因此大打折扣。再者,白嘉轩为了聚敛财富种植罂粟,罔顾民族大义和鸦片泛滥的严重后果,体现其功利自私的一面。最能体现其矛盾性的一点是他一方面维护封建道德的秩序,另一方面却允许借嗣求种的龌蹉行径。作者想要刻画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并不需要掩饰其不足的一面。
白嘉轩的对手是鹿子霖。同为家族继承人的鹿子霖顺理成章地成为白嘉轩比较的对象,所以他处处和白嘉轩作对。鹿子霖谋求乡约的职务是为了挑战族长地位的权威,买白家的地、拆白家的房全是为着灭族长的威风。权力、利益的争夺还是其次,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格魅力、人文内涵的差距。鹿子霖身上更多地体现出其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对于权力地位来者不拒、“官瘾比烟瘾还大”等特点。对待田小娥,鹿子霖威逼利诱强占了她的身体,还可耻地利用田小娥盲目的复仇心态对白孝文下手,以达到报复白嘉轩的目的。鹿子霖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轻浮随意的,他接受的是儒家圣贤文化的教育,却在实践中藐视族规,剥削乡民。他亵渎了传统文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虽然作者用大部分笔墨来塑造一个功利虚伪、自私贪婪的形象,但他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就比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鹿子霖就有白嘉轩做不到的开明,支持孩子上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再者,在修建祠堂、开办学校等事情中,体现了他很好的组织和领导才能,把事情处理得干净利索。所以鹿子霖也是一个矛盾结合体,他和白嘉轩的身份决定他们的对立状态,不管从行事作风上还是从思想价值观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他们基本上处于对立的两方。
田福贤是主角白嘉轩的反对者。田福贤和鹿子霖本质上都有贪婪、虚伪、恶毒的一面,因金钱和权势两者联系在一起。在官场上他们互帮互助,田福贤对鹿子霖说不上真心相待,但至少两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这就促使他们成为工作上的伙伴和朋友。从加码征地和银钱、借戏楼耍农协的人、凶残地对待贺老大等事件中反映出田福贤极其虚伪贪婪的一面。所以他和族长白嘉轩背道而驰,反而和鹿子霖不谋而合。田福贤和白嘉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处于矛盾关系中。田福贤是虚伪的革命者,而白嘉轩是作为封建宗族的一族之长。阻碍革命的因素就是旧时代的封建制度和思想,虽然田福贤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代表着个人利益,但就其担任的职务来说,其矛头直指白嘉轩维护的宗族利益。但是文中并没有把他们的矛盾升级为对立关系,一方面,描写田福贤和白嘉轩对立关系的篇幅并不算大,另一方面,双方都不把对方当成自己最主要的对手。田福贤的悲剧性源于错误的价值观和处事原则,使其难逃被批斗的命运,失去他苦心经营的一切。
反人鹿子霖和非反人鹿三是矛盾关系。由于传统农民阶级的盲目性,鹿三欣赏支持的是维持封建正统的主角白嘉轩。所以在白、鹿两大阵营的选择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白嘉轩的这一方,他们一直维持着十分和谐的主仆关系。鹿三以白嘉轩或是说儒家文化的崇拜者自居,从始至终都维护着白家的利益。他认为农民就应该具备诚实守信、质朴纯厚、吃苦耐劳的品格,应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娴熟的耕作技能获取所得。所有的这些性格品质对他和鹿子霖矛盾关系的构成起着最主要的作用,也促成了他和白嘉轩的补充关系。白嘉轩视鹿三为同宗兄弟,是白家“非正式的、但却不可或缺的”成员。对鹿三而言,他既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也没有争取独立人格的欲望,他并没有想要摆脱现状的想法,同时还满足于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劳动关系。“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2]不论从行动上还是思想观念上,他都以白嘉轩作为自己参考的标准,以传统的仁义礼教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和判断是非。作为和白嘉轩一样的儒家文化的践行者,鹿三具有盲目性的特点,所以他的一生注定是悲剧的一生。endprint
二、家庭身份
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族长白嘉轩的人物关系网,但是他的身份并不局限于此,他还有丈夫、父亲的身份。如果说族长身份的白嘉轩主要是仁义光辉的话,那么白嘉轩残酷绝决、固执死板的缺点,更多的是在他家庭身份行为中做出了隐晦表达。如下图:
作为白灵的父亲,白嘉轩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一开始他并不是作为白灵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而是疼爱女儿的父亲。当白灵的角色开始由女儿转变为革命者时,白嘉轩也从迅速地从父亲的角色中抽离出来转而成为反革命者,双方的关系开始走向对立。白灵是文中的一个理想形象,是女性叛逆者的代表人物。她拒绝缠足,拒绝传统教育,努力靠向革命的方向,是一个果敢坚毅的革命斗士。她有两次被囚禁的经历,第一次是悔婚之后被父亲锁在家里,白灵逃走时在墙角写下了“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打倒”,彻底与父亲撕破脸皮,也卸下了家族的负担而走向独立。第二次,因为党内的政治斗争而被陷害,她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比我渺小一百倍”。白灵坚定的革命态度正是与父亲决裂的关键点,白嘉轩生活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不可能包容一个叛逆者来挑战他的权威。当家长的威严受到威胁时,他毅然决然地割舍了亲情,所以他向全家人宣布“权当她死了”。在小说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嘉轩和白灵的矛盾在一步一步激化,最后到达无法调和的地步。父亲的传统思想和处事原则显然已经不被年轻人所接受,老派和新式的对立也必然会产生。从白嘉轩同意白灵到城里上学开始,他最疼爱的女儿注定要被整个社会环境所改变,进而导致关系疏离,最终父女关系破裂。
鹿兆海是白嘉轩的矛盾方,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白灵的绝对支持者。虽然鹿兆海和白灵就党派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但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着民族大业而奋斗,并且鹿兆海从没有伤害过属于敌党的白灵,反而甘愿冒着危险保护她。撇开国共两党问题,鹿兆海绝对是白灵最忠实的拥护者。文中鹿兆海为国家、为民族大义英勇牺牲。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他是勇敢、执着、单纯的,这一点和白灵十分契合。在鹿兆海看来,党派问题并不影响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上学时期一起抬尸体的情意并不假,所以他们之间界定为补充关系。白嘉轩和鹿兆海矛盾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白、鹿两家本身存在矛盾,白嘉轩坚信在鹿子霖的教育方式下鹿兆海只能是个残次品;另一方面是因为鹿兆海接受的新潮革命思想以及他对白灵的绝对支持挑战了白嘉轩作为封建族长的权威,所以鹿兆海并不受白嘉轩青睐。当初抬尸体的时候,白嘉轩就说过“甭跟鹿家二货拉拉扯扯来来往往”。
吴仙草对于白嘉轩有着特殊的地位,她是继白嘉轩六个妻子死去之后唯一一个成功为白嘉轩繁衍后代的女人。一直以来她都是作为白嘉轩背后的支持者,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努力作到社会规定的一切应该由女人承担的家务。吴仙草并不以此为痛苦,反而妻子的身份要求她顺从丈夫的一切决定,所以她和白嘉轩是补充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吴仙草作为母亲是疼爱白灵的,但是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都决定着她和白灵的阵营归属。传统女性观念和新时代女性观念的矛盾也是无法避免的。白灵拒绝缠足,独自离家只为上新式学堂;在婚姻问题中,她不顾父亲的脸面,毅然决然地用讥讽的口吻捎信给对方,拒绝了这门婚姻,这些都是仙草无法认同的事。虽然母亲的身份还在,但是她的生命里更重要的角色是白嘉轩的妻子,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观念禁锢了仙草的行动自由,即使是在临死的时候想见女儿一面也是痴心妄想。所以吴仙草作为传统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一员,在绝对男权文化的压迫下最终只得走向悲剧的命运。
对两个矩阵进行对比,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白嘉轩的性格特点和身份特征进行解读。“一个性格元素整体的各种性格元素间往往有不同性、甚至是对立。”[3]首先,在第一个矩阵中,他作为深受尊崇的族长而存在,道德因素对他的形象建立起着重要作用。白嘉轩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追求的只是安居乐业的最低要求。而且他能用正确的是非观去处理问题,对待村民也是尽心竭力,有着高尚的人格。“仁义”是作者给白嘉轩贴上的标签,但是白嘉轩并不是完美的,就拿鹿三来说,白嘉轩只是站在地主阶级的高度去俯视贫穷的农民阶级。对于黑娃和田小娥,他采取的手段是直接剥夺自由恋爱的合法性,给他俩打上离经叛道的罪名。不仅如此,白嘉轩为着自家的利益偷偷换地,种植罂粟发家致富,他的性格中隐含着功利性的一面。最终堂堂的族长也避免不了被拉上台批斗的命运,只得宣告放弃乡约的行使权,标志着他所维系的宗法制度在现实的打击下彻底崩塌。所以在第一个方阵中,族长白嘉轩既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又是一个失败的封建卫道士。其次,在第二个方阵中,家庭身份的白嘉轩更多地表现出狠心残忍、固执呆板的一面,因为他不仅继承了优良传统,也承袭了宗法文化“吃人”的一面。身为虔诚的封建卫道士,私下里却任由母亲逼迫儿媳妇去借种生子,体现出他自私自利的一面。而且作为父亲白嘉轩,他能够对败坏白家名声的儿子痛下狠手,对待离经叛道的爱女白灵也是毫不留情面。不仅如此,历史与现实的冲突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白嘉轩迷恋封建统治,认同皇权至上的原则。当晚清政府被推翻后,他说“没有皇帝了,以后的日子咋样过哩”。社会的发展进步彻底打碎了他的模式,女儿白灵拒婚出走,沉重地打击了白嘉轩。尽管如此,家庭身份的白嘉轩仍然是一个对家庭负责、高度重视亲情的人。吴仙草染上瘟疫,他一直默默地守在身边。就算是子女的忤逆损害了他的名誉,他依旧坚信血浓于水的亲情,到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们。所以家庭身份的白嘉轩既是一个热爱家庭、守护亲情的家长,也是一个狠心残忍的父亲。
三、命运轨迹
白嘉轩身份的矛盾对立在上面两个方阵中得以体现,除此之外白嘉轩命运发展轨迹也能让我们看到二元对立的存在,从“无”到“有”再到“无”,可得出下图:
从上图可知,白嘉轩的命运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转化。小说一开始写到了白嘉轩一直忙于娶妻、埋妻,这使得原本还算富足的家庭变得拮据。与此同时,白嘉轩命硬克妻的生理秘闻在原上肆意疯传,聘礼也是水涨船高、难以负担。再加上父亲白秉德的突然死亡,屋院里顿然空寂得令人窒息。此时白嘉轩的“无”是父亡妻死、家道不济,连同精神上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个契机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上演了偷换“福地”的戏码,看到“无”的背后隐藏的“非无”。不久就娶妻生子,接着种植罂粟积聚财富,彻底扫除了白家母子心头的阴影和晦气。接替父亲族长的位置,“仁义”族长的名声家喻户晓。至此,白嘉轩收获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财富,是一个“有”的状态。但是紧接着白嘉轩儿女的成长,问题随之产生。白嘉轩坚持严格按照传统教育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却导致了父女决裂,儿子白孝文也走上堕落糜烂的生活。这不仅使白家四分五裂,而且也动摇了白嘉轩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从“有”转向“非有”。endprint
之后饥荒到来,饿死了白家的长媳;瘟疫带走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就连鹿三也因为田小娥“鬼魂上身”而变得萎靡。后来还因气血蒙目挖掉了左眼,整个身体成佝偻的姿态,白嘉轩已不见往日的风采,失去了健康的体魄和精神的依托,处于一种“无”的状态。但是此时的“无”已非原先“无”的状态,至少内心已经开始自我反省,转向“非无”。“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紧绷,全都现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许多白发和那副眼镜更增添了哲人的气度。”[4]结尾处,白嘉轩在家门前得知白灵已死的消息时,“以不可动摇的固执和自豪大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5]。很明显他已经放下了对白灵的怨恨,不再执着于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思想。而且在鹿子霖被批斗之后,会想起自己换地的做法,觉得对不起鹿子霖。作者在此的意图是为揭示出白嘉轩人格的一种升华,相信感情可以化解矛盾。所以白嘉轩并非是“全无”,反而可以说是一种“有”觉悟的状态,拥有的是更珍贵的人生领悟。但在“有”中掺杂的一丝遗憾就是白嘉轩到死都还是一个人,不免有些悲凉凄清。
在这样一个命运轮盘中,我们看到了白嘉轩一生坎坷的经历。白嘉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族之长;既是宗法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又是封建文化的执行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多重命运的人物形象。多重身份意味着多重的责任,这也禁锢了白嘉轩人性的自由发展。他所秉持的仁义礼的标准,不仅圈住了族人,也是自我解放的巨大障碍。他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背景格格不入,这是白嘉轩从“有”到“无”命运转换的最关键因素,也是造成了他悲剧结局最主要的原因。历史把沉重的文化内容沉淀在他身上,把沉重的历史传播责任加诸在他身上,导致他负荷过重、失去自由。当白嘉轩的自我意识与外在环境发生了冲突时,他产生了自我意识矛盾,于是出现了两面性,是一个勇敢而又怯弱、仁义而又残酷、崇高而又虚伪的矛盾悲剧结合体。
《白鹿原》利用了一系列价值观、行为方式的有无二元对照论述了传统宗法家族制在近代社会中的大变迁,并呈现了作者对这一变迁不知其将何去何从而产生的历史焦虑感。运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分析《白鹿原》,不难感受到这一理论的魅力。但是语义方阵理论还是存在缺陷的。比如在确立X项的标准问题上还不够清晰,人物关系复杂有时不能简单概括。所以我们在运用语义方阵理论的时候,要注意避免生搬硬套。
注释:
[1]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页。
[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3]刘再复:《文学反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0页。
[5]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吴谦红,朱媛 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文学院 312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