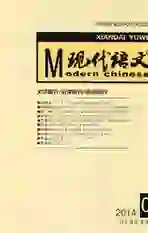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中的家族人物关系微探
2014-04-09王卉娟
摘 要:生长于贵族遗少家庭的张爱玲,在其小说中有比较明显的旧式封建大家族日渐式微的模式。由于自身的经历,在她的笔下,封建旧家庭变得苍白而悲凉,衰落而沉沦。处身于这样即将没落的封建大家庭中,“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得刻薄而残忍,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揭示了婆婆对媳妇无尽的折磨,父母对子女无情的摧残,兄弟姐妹间的相互啃噬,夫妻间的漠然与相互利用。在本文中笔者以张爱玲的部分中篇小说为例,透过那些封建旧家庭中的家族人物,揭示出生活在封建家族中人与人的本质关系。
关键词:张爱玲 家族人物 关系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一文中写道:“我姊姊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宣泄,她赤裸裸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这样残酷地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做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1]
生长于贵族遗少家庭的张爱玲,其小说中有比较明显的旧式封建大家族日渐式微的模式。张爱玲深切感受到封建旧家庭所带来的精神与情感伤害:没有得到正常的母爱,遭到后母的感情冷落;在父亲家中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被迫逃离至母亲家后,又逐渐产生失望的情绪。于是,在她的笔下,“家”无疑就变得苍白而悲凉,衰落而沉沦。正如《传奇》中姚先生的家、川娥的房间等等,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单个来看,并没有什么超出特定地点、场所的意义,然而他们与《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茉莉香片》中的传庆家,《留情》中的杨太太府第等等,由于一个内在的相似性而在读者的心目中相互重叠、发生关联、构成一个独特世界时,每一个具体环境就在作者统一的命题下获得超越自身的新的意义(一个场景如果重复出现,它就可能变成一种象征)……他们内在的相似性都是没落的旧式家庭,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同样灰暗的色调,同样腐烂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又使人们可以将他们当作同一个来看待。
张爱玲难以忘怀封建旧家庭给她造成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又摆脱不掉无家可归的阴影。她极少感觉到家的安全感,稳固感和温暖感。家庭对她意味着痛苦的回忆,不堪回首,亲情的面纱一旦被撕裂,“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得刻薄而残忍:婆婆对媳妇的折磨,父母对子女的无情,兄弟姐妹间的相互啃噬,夫妻间的漠然与利用。笔者以张爱玲的部分中篇小说为例,透过其笔下的那些行将就木、苟延残喘的封建旧家庭对家族人物关系进行浅要的分析。
一、婆媳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传统的封建大家庭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与风光,光鲜的外表背后正面临着解体与崩溃的危机。然而传统的生活方式、旧的道德伦理仍被封建家长奉为金科玉律,穿长袍子、留长辫子、呼奴唤婢、早晚请安,他们依然悠然自得地挥霍着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大家族最后的余晖。与巴金笔下的封建专制家长不同,我们看不到“高老太爷”,更多的是姜老太太(《金锁记》)、白老太太(《倾城之恋》)、杨老太太(《留情》),阴盛阳衰注定了即将没落的封建家庭的最高统治者是这些“贾母”似的老太太。年轻时作为媳妇,在公婆面前,在丈夫面前,她们的地位无疑是最低下的了,是封建礼教最直接的受害者。她们默默忍受着,熬去了青春,熬死了婆婆,熬死了丈夫,终于“苦媳妇熬成了婆”,置身于封建家长的宝座,她们摇身一变成了家族伦理的维护者。作为封建家族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她们曾经饱受折磨的身心、压抑许久的情感爆发了。她们要维护做婆婆的“尊严”,要享受做婆婆的“威风”,还有那居高临下、俯视全家的无限“乐趣”。然而,儿子终究是自己的骨肉,所以“老太太对儿子们向来是非常客气的”。于是这些脾气乖张、喜怒无常的老怪物们便变本加厉、想方设法地加倍折磨年轻的媳妇,她们年轻时失去的一切要从媳妇身上找回来。悲剧一代又一代地重演。
且看《金锁记》中的丫鬟、媳妇们一大早就来到老太太卧室隔壁的起坐间里等着给老太太请安:
玳珍探出头来道:“云妹妹,老太太起来了。”众人连忙扯扯衣襟,摸摸鬓角,打帘子进隔壁房里去,请了安,伺候老太太吃早饭。婆子们端着托盘从起坐间里穿了过去,里面的丫头接过碗碟,婆子们依旧退到外间来守候着。里面静悄悄的,难得有人说句把话,只听见银筷子头上的细角链条魁魁颤动。(张爱玲《金锁记》)
单是早上请安,媳妇们便是大气也不敢出一个,这高高在上的姜老太太是何等的“威风”!姜家是个大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也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比起《小艾》中的席老太太对媳妇们的苛刻严厉、不近人情,那姜老太太对媳妇们倒算是客气的了。媳妇们早上要给席老太太请安,在午觉醒来也必须一一前往问候:
照规矩她们全得去,但是如果大家一同去,老太太势必要疑心,说怎么这许多人在一起,刚好一桌麻将。所以只好轮流地去。他们老太太其实是最爱打牌的,现在因为年纪大了,有腰疼的毛病,在牌桌上坐不了一会就得叫别人代打,所以不大打了,就也不许她们打。老太太每天一大早起来,睡得又晚,媳妇们也得陪着她起早睡晚,但是她每天下午要睡午觉,却不许媳妇们睡,只要看见她们头发稍微有点毛,就要骂出很不好听的话来。不过她从来不当面骂人的,总是隔着间屋子骂,或者叫一个女佣传话,使那媳妇更觉得羞辱些。(张爱玲《小艾》)
作为小说家,张爱玲确是一出手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了。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那么,这“最美的收获”中的女主角姜公馆的二奶奶曹七巧又是怎样的卑微与恶毒呢?作媳妇自然是卑微、低下的,但作了婆婆便是无尽的恶毒与残忍了。
北方一家麻油店铺的女儿,曹七巧高攀了簪缨望族,可她嫁的丈夫却偏偏是一个患骨痨的残废人,是一堆“没有生命的肉体”,使她难免受叔伯妯娌之间的鄙夷,孤立无援。然而老太太明知七巧嫁给自己残废的儿子,心里有说不出的苦痛,靠抽鸦片麻醉自己,却有意装作不知道,常常给她派差使,零零碎碎让她受罪。旧式公馆生活沉滞枯槁,日日如此,曹七巧以气血充盈的十年青春,终于在这个公馆望族中赢得了新的生存地位。一个附庸于“废人”丈夫的女人变成了一家之长,于是又新一轮的悲剧上演了。不同的是七巧的角色由媳妇变成了婆婆。如果说姜老太太、席老太太对媳妇们是无声的戕害,那么曹七巧带给媳妇芝寿的就是无休止的羞辱:
三朝过后,……七巧啐道:“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真的!你信不信?”这话传到芝寿耳朵里,急得芝寿只待寻死。然而这还是没满月的时候,七巧还顾些脸面,后来索性这一类的话当着芝寿的面也说了起来,芝寿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若是本着脸装不听见,七巧便一拍桌子嗟叹起来道:“在儿子媳妇手里吃口饭,可真不容易!动不动就给人脸子看!”(张爱玲《金锁记》)
尖酸的话语犹如刀子般阉割着芝寿的灵魂,曹七巧在姜家葬送的幸福需要人来殉葬,逝去的青春需要人来补偿,第一个被索取的便是她的儿媳——芝寿。七巧尝到了“乐趣”,更加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张扬起来,她是婆婆嘛!她在烟榻上逼迫儿子长白供出床笫秘闻,然后迫不及待地大肆传播开来:
七巧一夜没合眼,却是精神百倍,邀了几家女眷来打牌,亲家母也在内。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地打岔,然而说不上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地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涨,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张爱玲《金锁记》)
面对七巧的羞辱,“亲家母”已无颜再见女儿,无地自容了,年轻的芝寿被摧残地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她的灵魂被婆婆无情地扼杀了,犹如行尸走肉:
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首的颜色。她想死,她想死。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明天她婆婆说:“白哥儿给我多烧了两口烟,害得我们少奶奶一宿没睡觉,半夜三更点着灯等他回来——少不了他吗!”芝寿的眼泪顺着枕头不停地流,她不用手帕去擦眼睛,擦肿了,她婆婆又该说了:“白哥儿一晚上没回房去睡,少奶奶就把眼睛哭得桃儿似的!”(张爱玲《金锁记》)
七巧像剃刀片一样的声音,尖酸刻薄的话语,阴魂不散地缠绕着年轻的媳妇,终于芝寿一病不起,抑郁而终。
在婆婆的手里,原本应该幸福的“家庭”成了媳妇们生命的枷锁,固然有出头的一天,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完整的“人”了。媳妇们犹如任人宰割的羔羊,闻“婆婆”而色变,“婆婆”就是折磨的代名词。而所谓的“婆媳关系”也多是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关系,吃人者和被吃者的关系,并由媳妇变为婆婆而长久地轮回下去。
二、母子(女)、父女(子)
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繁华世家,她曾享受过短暂的天伦之乐,母亲抛弃她到法国留学,使母爱在她的感情世界成为空白。父亲因听信继母的一面之词对她的毒打与监禁,使她彻底丧失了对旧家的眷念。出走之后从未再踏进旧家的大门。感情上的伤害使父母之爱的神话在她心中从此破灭。
历来文人所歌颂的神圣的父子之爱、母子之情在张爱玲笔下也显示出可怕的一面。“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作儿子而不作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3]即使是母亲身上所体现的自我牺牲的美德,在她看来也并不能以此自豪,因为“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与之相应的是,张爱玲作品中的母亲没有我们通常想象中的那种自我牺牲式的仁慈,更多的是毫无情义的自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破坏了儿子的婚姻,把媳妇折磨致死。被其耽误到三十岁的女儿,与留德归国的童世舫谈起恋爱后,她便大骂女儿“多半是生米煮成熟饭”,“火烧眉毛,等不及要过门”。尽管女儿因恋爱而戒绝了鸦片,她还要在长安宴请童世舫的席间演出了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张爱玲《金锁记》)
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使一个留学生心目中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烟片鬼,女儿一生中唯一一次爱情被她亲手扼杀了,幸福被葬送了。
又如《十八春》中的顾太太为了一摞钞票,明知女儿身陷魔窟却置之不理,成为蹂躏女儿精神与肉体的恶势力的帮凶。《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亲眼目睹自己的女儿流苏受儿子、媳妇的欺负和人格上的侮辱,也不愿站出来为她说句公道话,一味避重就轻,让女儿大失所望。
母亲神话的消解与父亲神话的颠覆互为一体。封建旧家庭中的父亲在走向衰老的过程中,其作为道德、人格典范的美誉早已过去,为了自己生存利益的满足,他们身上一点点的血缘亲情也消失殆尽,有的只是自己私欲的满足。《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把女儿作为生存的资本,花光了她的积蓄后,又千方百计的利用夏宗豫对女儿的好感乞求工作,而在丢了饭碗后为了获得80万元的钱款,情愿让女儿给人做姨太太。《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把对妻子的憎恨转嫁到无辜的儿子身上,结果把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孩子虐待成为精神上的残废。《花凋》中的郑先生面对病危的女儿,听说要买药立即“睁眼诧异道:‘现在西药是什么价钱?……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我花钱可得花的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郑太太呢?“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他们的无动于衷,导致自己女儿的年轻生命被疾病夺去。而他们却在女儿的墓碑上把她形容成一朵花,美丽的天使,“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终于把笼罩在父母身上神圣的面纱撕破了,露出的是他们的自私与虚伪。
面对如此疯狂的摧残和残害,我们再来看看儿女们是怎样诚惶诚恐地生活着。《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儿长安在恋爱时想到母亲时的心态是这样的,“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一段多么绝望害怕的心理,反映出了长安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而长安如她自己的预言一样,最后的结局是“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
弗洛伊德著名的俄狄普斯情结包括一点,即“幼儿性欲在受到父亲的强大的力量的宰制,又亲自施以体罚获以阉割威胁时,会导致幼儿产生一种‘阉割焦虑,不得不屈从‘现实原则,压抑欲望,认同其父”。从长安的心态来看,我们可以体味到她对母亲深深的恐惧,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戕害,灵魂也变得支离破碎、惊慌不安,应该说她已经具有强烈的“阉割焦虑”了,与弗罗伊德所说的不同的是:她是被母亲彻底地“阉割”了。
父母狰狞的面目成为扼杀子女青春和幸福的刽子手,父慈母爱只存在于金钱构铸的“金锁”里,只是这把金锁锁住了血肉之情,锁住了天伦之乐。血肉之情是比不上金钱闪耀的。
三、兄弟姐妹
“兄友弟恭”“姐妹情深”一向是封建家庭引以为豪的家庭理想,“兄弟怡怡”“姐妹陶陶”的手足关系在衣食无忧、地位显赫的封建旧家庭中多能保持,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与旧家庭的日益衰败,传统的家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生存危机面前,充满诗意的兄弟亲情、姐妹情义开始暴露出其不近人情的残酷一面。往日掩藏在温情脉脉背后的人情冷漠、人性虚伪、手足相残的丑恶浮现出来。且不说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单是鲁迅在家道中落之后,他首先感受的就是亲人之间的残酷,其他各房对孤儿寡母的欺负。他到亲戚家避难,昔日备受优待的礼遇转而被冷眼所取代,且被称为“乞食者”,我们就不能不对人情的冷漠嗟叹许久。至于手足相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表现地更为突出了。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丈夫离婚后带着自己的私产回到娘家。虽然她年仅20多岁,且颇有姿色,但从未考虑过再嫁的问题,她慷慨地把自己的钱借给哥哥白三爷、白四爷去做股票、金子生意,然而她的钱被赔光之后,白家生存日渐艰难之时,他们却劝她以寡妇的名义去为死去的前夫奔丧:“你这会子堂堂正正地回去替他戴孝主丧,谁敢笑你?你虽然没生下一男半女,他的侄子多着呢?随你挑一个,过继过来。家私虽然不剩什么了,他家是大族,谅是拨你看守祠堂,也饿不死你母子。”与之相承相应的是四奶奶的冷嘲热讽:“我早就跟我们的老四说——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有沾上晦气!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三爷也把股票的惨败归罪于妹妹的加股,一向讲究礼仪廉耻的白公馆却上演着“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战争,此时流苏才认识到人情的虚伪和哥哥的不良用心。
《金锁记》中的姜家在老太太死后兄弟们开始相互争夺家产,七巧虽据理力争,财产分割一度出现僵局,但最后还是按原定计划分了家,“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兄友弟恭的理想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如果说白三爷、白四爷以及姜家兄弟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人世间悲凉的话,那么《十八春》中曼璐的自私就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了。顾家的大女儿曼璐为了撑持整个家族作了舞女和私娼,在青春渐渐逝去的时候,曼璐嫁给了吃交易所饭的祝鸿才。但她曾两次打胎,已失去了生育的能力。看到祝鸿才对妹妹曼桢垂涎三尺,曼璐为了自己婚姻的稳固,她设下了圈套,称病把曼桢引到祝府,让祝鸿才奸污,“借妹妹的肚子生个孩子”,以吊住丈夫的心。可怜曼桢被禁闭在祝府十个月,终于借在医院产婴之机,逃离魔窟。这便是一母所生、情同手足的亲姐妹!为了一己之私,就把妹妹推向万劫不复的火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在这些每况愈下的封建旧家庭中,亲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张爱玲苍凉的笔触中,无论兄、弟、姐、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谁是可以利用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自己争夺家产的对手!自私与虚伪已经渗入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四、夫妻
张爱玲的名字是母亲黄逸梵在女儿小学入学时起的,据说是“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于是取名为“爱玲”。关于张爱玲名字的英文译法,通常译为“Eileen zhang”,有人考证说:“爱玲”这个字译自哪个英文词,她本人也没有说,也没有人考证过。有这样一种说法:“爱玲”这个词的音译,与汉语最靠近的英文字就是ailing,如果成立,那么“爱玲”的英文意思就是:烦恼,苦恼。从当时她母亲的心情处境来看,下意识地取了这个名字是很有可能的。
张爱玲的一生始终与烦恼为伴,这似乎又是一个不幸的征兆。旧式婚姻造成了父母感情裂变,带来了家庭的不幸与痛苦,这给幼年的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她与胡兰成之间的乱世之恋带给她的则是挥之不去的烦恼。张爱玲笔下的夫妻之情多多少少受到其自身的影响,而变得冷漠,如同交易一般。
中国的封建家庭自古以来所奉行的门第婚姻观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对家族的意义远大于对夫妻自身的价值,即使在没落衰败之际也是如此,造成了无数的悲剧,葬送了无尽的青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年轻时原本是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让一个健康活泼的妙龄少女去陪伴身患绝症的残废人度过漫漫人生,何谈爱情?何谈幸福?姜老太太自知儿子的生理缺陷,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儿不可能与其结亲,她接受出身低贱的七巧实属别无选择,七巧只是姜家传宗接代的工具!
在传统社会,自出嫁之日起,女人就无可选择地沦为丈夫的私有产品,她们所面临的只有被遗弃。在《小艾》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五太太一听见声音就想着,不要是他回来了,顿时张惶起来,景藩(五老爷)是从从容容走的,态度很自然,五太太却是十分局促不安,一双手也没有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先是伸着一只脚,雪白的丝袜,玉绣花鞋,这双鞋似乎太小,那鞋口扣得紧紧的脚面肉唧唧地隆起一大块,越发觉得自己胖大得无处容身,因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站在那里进了半天,方才搭讪着走了出来。(张爱玲《小艾》)
一个失宠的太太张惶失措的心态就这样被绝妙地刻画出来。这就是曾经同床共枕的夫妻见面的情形,比之陌路又多了一份尴尬。夫妻间的冷漠比起婆婆对媳妇的折磨,父母对子女的摧残,手足间的无情更让人为之痛心。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似乎对爱情没有什么兴趣,她们感兴趣的是金钱,即使走出家庭,其目的也是为了寻找一个舒适的生存场所。《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年轻时不惜与家庭闹翻,自愿嫁个粤东富商梁秀腾做姨太太,她希望丈夫早点死去,以便自己过上既有钱又自由的生活。她嫁给他,为的是钱,谈不上任何情感的诱因。
婚姻被套上了金钱的枷锁,夫妻间变成了最明白不过的物质交易:他娶,为的是传宗接代;她嫁,为的是富裕生活。肮脏的交易使得同床异梦的夫妻关系,在金钱的照射下,变得苍白没有血色。所谓的“婚姻”是用来交易的契约,而“夫妻”关系是用来联系交易的纽带,至于爱情,是可笑的。
旧的家庭给张爱玲的精神创伤是沉重的,而这种痛苦的生命体验又是她一生宝贵的财富,她创作上的成功无不来源于她旧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的积累。正是因为在家庭、情感上的失落,才造就了张爱玲笔下的这些颇具讽刺意味的人物,以及这复杂而引人深思的人物关系。
注释:
[1]张子静:《<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3]张爱玲著:《流言·谈跳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参考文献:
[1]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2]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余斌.名家张爱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4]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5]张爱玲.流言[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6]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经程[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7][韩]赵炳奂.张爱玲小说创作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王卉娟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22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