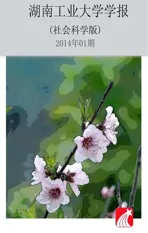奥康纳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困境*
2014-03-31吴端明
吴端明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州510000)
奥康纳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困境*
吴端明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州510000)
弗兰纳里·奥康纳被公认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她的作品阴郁,诡异,对人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她的创作中大都有浓重的南方意识和天主教意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她的小说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困境。以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为例,小说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不仅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描写上,还反映在个体的体验上;同时,作品还体现了人与人的相处中的折磨与纠缠,“他人就是地狱”;尽管社会本身是有着多元色彩的,人却只能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体验存在的困境,人只能有相对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反英雄义无反顾地追逐着自己的自由,尽管这样的追逐很荒谬;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于宗教的态度或神父角色的描写,小说拷问了现实宗教的意义。
奥康纳;存在主义;困境
弗兰纳里·奥康纳被公认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她的作品阴郁,诡异,对人性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她的创作中大都有浓重的南方意识和天主教意识,她提到:“在我看来,使我避免成为区域作家的唯一原因是我的天主教信仰,而使我避免成为天主教作家的唯一原因则是我的南方人身份。”[1]由此总结了影响她创作的两个关键因素。围绕奥康纳的作品有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南方农村社会文化的观察,也包括对其中的宗教意识的批判。同时,一些研究针对小说中的哥特传统,包括其中的畸人形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奥康纳小说体现了一种存在主义困境。以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为例,小说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不仅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环境的描写上,还反映在个体的体验上;人与人的相处本身就是折磨与纠缠,“他人就是地狱”反映了人存在所面对的困境;尽管社会本身是有着多元色彩的,但是人只能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体验存在的困境,人只能有相对的自由,但是,也有一些反英雄义无反顾地追逐着自己的自由,尽管这样的追逐很荒谬;就生活方式而言,所有的行为守则都是不重要的,人物表现出对周围一切的无比淡漠;通过小说中人物对于宗教的态度或神父角色的描写,小说拷问了现实宗教的意义。
一 厌恶感的传递
奥康纳的小说洋溢着“厌恶”的氛围,这种厌恶不单表现在自然环境中,还表现在城市图景中,乃至人物的外貌描写中。同样的厌恶情绪也体现在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早期的作品中。两者都强调一种颓废的情绪,反映的是人的孤独与绝望。
在“河”这部短篇小说中,去往受洗的河流的路上,有这样的景物描写:“周日炙热的太阳在身后不远处跟着他们,掠过浮沫般的灰色云头,好像是想追上他们。走在最外侧的贝富尔一边拉着康宁太太的手,一边低头去看混凝土路上冲刷出的橙色和紫色沟槽。”在对于乡村的描写中作者着重写到了猪圈,刺鼻的垃圾味,兽类的响动,和猪的湿乎乎,泛着酸味的脸。而在“火中之圈”中,文章开头便写道:“最末一排树木有时仿佛一堵坚实的灰蓝色墙壁,颜色略深于天空,但这个下午却几近黑色,后面的天空是一片触目的灰白”。这些景物描写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单调的天空似乎在奋力推着那堵树墙,想要破墙而出。横贯边上那块田地上的树木像一块块灰白色和黄绿色的补丁。”
这样的自然景物描写是灰色调的,让人觉得压抑的。整个自然就像一个巨大的牢笼,将人罩在其中,让人有强烈的逃离的欲望,同时,又是阴郁的,窥视的,伺机而动的。
城市图景的截取也表现了这种厌恶的倾向,“好运降临”一文中,在鲁比的眼中,“楼梯是这栋公寓大楼中间一道又黑又窄的缝隙,上面铺着的黒褐色地毯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在她眼里,它象尖塔的楼梯一样笔直向上。“人造黑人”一文中,黑德先生带着外孙尼尔森进城,他唯一有能力带他见识的就是下水道,“黑德先生向男孩讲解了下水道系统。什么整座城市地下都埋着下水道啦,什么排出的污水都在里面啦,什么老鼠在里面窜来窜去啦,什么人会掉进去,被黑洞洞的管道吸下去,始终探不着底啦。”在这样的视角中,城市是无精打采的,藏污纳垢和破落的。用奥康纳自己在小说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个“烂透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只渴望着能“爆发吧,把这个世界的污垢洗去吧”。[2]67
奥康纳长于对“畸人”的描写,她曾说:“为什么我的人物都是怪诞、畸形的,根本在于我的写作天资的本性使然。就某种程度而言,一个作家可以选择他的主题,却无法选择他能够把什么写活、写得精彩,而我能写活的恰恰是如《好人难寻》中的格格不入的人和《善良的乡下人》中的销售员之类的畸形人。”[3]这些畸人的描写同样传递了一种厌恶感,研究哥特传统的王晓姝曾经这样总结,“奥康纳小说中典型的畸人形象并非简单的、一维的创造,而是表现出了复杂的极端心理状态的人。盲者、跛者、聋哑者等身体残缺者,心理变态者、智力迟钝者、行为怪癖者等精神残缺者皆可归入此列。”[4]167奥康纳对于这些畸人的刻画,往往一两句话已经让人印象深刻,如“救人就是救己”中的史福特利特先生,“他转身面向落日,慢慢挥舞着那只完整的胳膊和另一只残缺的胳膊,比划出一大片天空,他的身形摆成了一个扭曲的十字。”又如“河”中的康宁太太,“她脑袋向后仰去,他看见她慢慢闭上眼睛,张开嘴巴,露出稀稀拉拉几颗长牙,有的发黄,有的比她的肤色还要黑。她打鼾的时候象是一具会奏乐的骷髅。”
总的来说,小说中展现的生存环境与人物图谱都传递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惨淡的,令人生厌的,杂乱无章的,毫无意义的,恍惚如鬼魅的,荒谬的,丑恶的,这样的环境与人物体现了人作为个体的孤独感和无奈感。
二 他人就是地狱
在奥康纳的小说中,人物的关系大都不能跳脱几种相处模式:隔膜的,不能真正交流的,尤见母女之间或母子之间不能沟通,迫使其中一方逃离;充满威胁感或张力的,看到危机正在逼近的,毁灭性的关系。这些相处模式令人的存在变得空前孤独与绝望,甚至是透着愤怒的绝望。
在短篇小说“善良的乡下人中”,霍普韦尔太太最爱说的三句话是“世无完人”,“生活就是如此”,还有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别人也有别人的想法”。霍普韦尔太太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奥康纳短篇小说中的南方妇女的角色,大都如是,不爱思考,陈腔滥调,也正因如此,与她们进行的沟通都是空洞和无望的。
在奥康纳小说中,母女关系或母子关系大多不睦,其中在“救人就是救自己”中的女儿就是个智力迟钝的人,老太太盲目地爱护着她,一心要为她寻个好丈夫,却把她推到不速之客的怀抱中,使这个痴儿流落在异乡。而在“善良的乡下人”中,陈词滥调的霍普韦尔太太与她的女博士女儿之间并不能真正的交流,她为女儿改名为“乔伊”(JOY),希望她得到快乐,但是乔伊却执意改名为“胡尔加”(Hulga)这个“所有语言里最难听的名字”。
小说“救人就是救自己”结尾出现的小男孩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角色,他带上他的纸板箱,似乎表示他要永远离开某个地方了,史福特利特先生对母亲的颂扬反倒激怒了他,小男孩吼道:“我老妈是个邋遢货,你妈是个臭婊子”,就往车下一跳,并摔进了沟里。小男孩的愤怒暗示了母亲的自我放纵和对抚育幼子责任的漠视。儿童角色在奥康纳笔下往往是个孤苦无依的角色,尽管双亲犹在,但是因为感情上的过早孤立令这些小孩早熟起来,早早地盲目走上自我价值探寻之路,但这种探寻又往往是碰壁和无果的,令人扼腕叹息,这是个荒谬的世界。
奥康纳笔下的外来者往往是隐隐带着威胁感的,“救人就是救自己”中,不速之客木匠史福特利特先生帮寡妇修理房舍,最终却让她的家业彻底破产,而“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女博士则被伪装真诚的骗子夺去假肢,弃于谷仓顶楼上。金莉总结道:“外界暴力入侵时,往往采取改变人物生活环境的方式...精神世界的黑暗成为了现代罪人生存状态的显著特征……奥康纳总是让他们陷于一种处境,发觉不能用习惯的陈腔滥调去译解,以环境的陌生化震荡并撕裂他们的精神地理,在外界暴力之助下体味被生活表面所隐盖的深层现实主义。”[5]170
“他人就是地狱”原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对现代社会中人恶劣生存环境和恶化的人际关系的总结,但同时也是他号召人们冲破自我的牢笼,以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去营造新的天地的一句至理名言[6]46。奥康纳笔下的人物也正是如此,在与他人的相处过程中,在这种暴力的震荡下,体味到被生活表面所隐盖的现实主义。
三 有限的选择和“反英雄”的诞生
加缪曾经这样解释个体的选择和努力:“从根本上来说,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对立的、离异的、不可调和的,所以,荒诞感从个体与世界产生关系时开始,到个体的死亡结束。个体的一生向往幸福,但不管怎样都无法得到,一切的努力付诸东流,于是“幸福”成了一个荒诞的概念;个体顽强地进行自由选择,却在种种磨难之后头破血流,自由原来是如此的荒诞,可遇而不可求;个体希望在生存中体验精神的存在,却往往发现自己扮演的是一个如此愚蠢的、可笑的、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恶心的角色。而在他谢世之前,这一角色无论多么让人难以忍受,他都必须坚持下去。”[6]49
在小说“人造黑人”中,黑德先生认为自己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人生,做年轻人理想的导师,他计划带着他的孙儿去见识城里的方方面面,这样他就会心甘情愿在家里度过余生了。他精心安排希望能通过这次短途旅程树立起自己在孙儿心中的权威智者的形象,却在途中每每被人奚落,鄙视,他作为一个乡下人的孤陋寡闻和狭隘也暴露无遗,他促狭地想给孙儿一个教训,没想到却陷入尴尬的境地,在孙儿最需要他的时候不敢承认自己就是祖父。在这次旅途中,他面临着多次的抉择,却在每次抉择后更迷茫,更难堪,把祖孙俩推到更危险和孤立疏离的境地。
尽管人扮演的角色是可笑的,加缪也通过创作了西西弗斯这样的“反英雄”来阐明了一种战斗的立场,[7]神祇们处罚西西弗斯,叫他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去,由于它本身的重量,巨石又从山顶上滚下来。他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项苦役,尽管知道没有完结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努力。巨石还在滚动。世界是荒诞的,人的选择是有限的,无论如何选择,人总会落入一种困境并发现幸福是无望的。但是,总能有人保持着一种战斗的,奋争的态度,总能有人执着于一种努力与注定的命运,设定的世界抗衡,这就是在存在主义困境中的“反英雄”。奥康纳小说“河”中的小孩贝富尔就是这样的反英雄,他独自一人从家中出发,长途跋涉到他曾受洗的河中,希望上帝能接纳他到基督之国,他一再把自己抛到河中,希望河流能接纳他,最终被河流带走。
四 对宗教意义的拷问
宗教是奥康纳小说中的永恒元素,小说中或出现神父角色,或试图刻画世人眼中的上帝。小说“河”中的牧师是个刻板的角色,他传教但是并不了解宗教的真实含义,因此他的说教显得苍白无力,面对人们对于宗教意义的诘问,他表现得不自信,也不能真正以宗教的精神去感召无知的人们。因此,人们心中的上帝就仅仅停留在“上帝是能治病的”,大家都希望牧师能帮忙治好身体上的病。牧师与平民都显得愚昧不堪。而小说“流离失所”中的神父,则被肖特利太太认为是,“当神父希望被人认出自己是神父的时候,就这么打扮”。身为神父,他虽有一副神父的外壳,挂着慈悲的面容,承担拯救苦难的使命,但是他无能也无力纾解刚从集中营逃出,希望能够开创新生活的波兰人一家的困境。神父怯懦而迟钝,没有办法令庄园主麦克英特尔太太放开怀抱,接纳这些外乡人,她的狭隘最终纵容她的帮工杀害了这个波兰难民。从这方面看,这是与神父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上帝的博爱之光在蒙昧的人们面前也被屏蔽了。这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普遍的宗教觉悟。宗教只是人们挂在嘴边的说辞,并没有实在的含义。在小说“乡下好人”中,作者对宗教现状的讽刺更为辛辣。兜售圣经的小伙子貌似真诚善良,实则污秽不堪。他把圣经挖空,把威士忌,淫秽的纸牌藏在里面。人们只执着于宗教的形式,实则有人以宗教的名义骗取他人的信任,披着宗教的外衣满足自己的私欲。
金莉认为,在奥康纳笔下的角色有两类,一类是心满意足的小资产者,物质利益是她们的生活目的和精神支撑,她们自以为在蝇营狗苟之余重复几句大众化的祷词就是模范的基督徒了,浑然不觉已堕落成怠慢上帝的逐利者,物质俘获了她们的灵魂,取代上帝成为她们顶礼膜拜的欲望对象。第二类人是迷失在虚无的理性神殿中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上帝已死,转而崇拜人类自身的理性力量。极度的傲慢和膨胀的自我意识遮蔽了现代理性主义者的视野,使得灵魂无所着落,迷失在空虚的情感荒原之中。[5]169
宗教意义的缺失更加突显出人们的存在困境。人孤独而无助,仰仗于上帝但得到的是空洞的答复,从而陷入更痛苦的心灵深渊,爆发出“这个烂透的世界就要把人吞没”的呼声。“哦上帝,爆发吧,把这个地球上的污垢洗去吧。”
正是通过厌恶感的传递,人与人之前的无望的痛苦的沟通,反英雄的塑造和对宗教意义的拷问,奥康纳的小说中体现出了存在主义的困境,这种困境奠定了奥康纳作品的基调和氛围,形成了作品的一大特色。
[1]Fitzgerald,Sally et.Letters of Flannery O’Connor:The Habit of Being[M].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79:104.
[2]奥康纳.好人难寻[M].於梅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3]Quin,John Joseph.Flannery O’Connor-A Tribute[J]. Esprit,1964,(8):23
[4]王晓姝.哥特之魂:哥特传统在美国小说中的嬗变[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5]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汪小玲.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7]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43.
责任编辑:李 珂
The Predicament of Existentialism in Flannery O'Connor's Short Stories
WU Duanming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Guangzhou,510000,China)
Flannery O’Connor,compared with Faulkner,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writers in south of America.She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in literature all over the world.Religion and the South are the two important elements in her works.From another perspective,her novels reveal the predicament of existentialism.The short stories collection“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is taken as an example for analysis:firstly,the novel conveys a sense of disgust.It could be felt in bo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econd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isworse than ever.People could feel only isolation and torture.Thirdly,although the society is full of varied choices,people are bewildered by the few options they could take.Still,some anti-heroesmake relentless efforts to pursue their goals.Fourthly,the novel questions themeaning of religion by describing some stereotyped priest.
Flannery O'Connor;existentialism;predicament
I106.4
A
1674-117X(2014)01-0140-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26
2013-04-05
吴端明(1980-),女,广东肇庆人,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