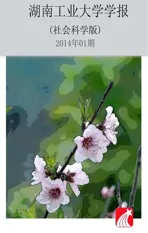情之所钟 正在我辈*
——读李少君诗歌
2014-03-31曹梦琰
曹梦琰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情之所钟 正在我辈*
——读李少君诗歌
曹梦琰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李少君诗歌创作一直在践行着他自己的理念:从山水、自然、人情中找到传统诗学中的“和谐”,将“深情”投射于自己的作品之中。“深情”这样一个亘古有之的、兼容美学与人文关怀的理念也就成了探讨李少君诗歌的重要切入点。在与现代人的“心碎”相遇后,“深情”必然会发生改变,但是在李少君的诗歌中不难找到我们源于记忆的“一往情深”,尽管来得有些无奈。
李少君;自然;深情;和谐
落在诗人和他的写作之上的会有各种称谓——自诩的或被冠以的。对于诗人李少君亦如此——“草根”“山水”“自然”,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种自圆其说的称谓。然而诗歌——人们透过它所关注的复杂与缭乱的色相,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人们扩散、浓缩,浅浅掠过、深深刺穿,复杂化或简单化——所有针对诗歌的写作方式或许只是源于纯朴的记忆和情绪。于是,“情”就成为了走进李少君诗歌的一个切入点,它亘古不变——或者说,终有不变之处。但更重要的理由是,诗人宣称自己是一个深情之人:“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动情”(《新隐士》)。
人们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记忆?记住一个在代代相传的族谱中同先人与后人一起被时间冲淡的名字;抑或一本书的作者、一首诗的吟唱者;又或者,仅仅是文字中寥寥几笔的形象,伴随着让人唏嘘的只言片语。实际上,和记忆相比,更多的时候加诸人们身上的是遗忘和被遗忘。时间蜿蜒到此刻,我们忘记了在幽深危险的森林中,自己怎样站立起来;忘记了曾经有一天,在哪束光芒的投射下,唇边含混的音节忽然浮出美妙的形象……时间中,我们死去重生周而复始,忽然某天,醒在“末日论盛行的年代”,听着窗外“复杂的机械现象”,一个愣神间——“十字路口/一辆汽车和另一辆汽车发生了碰撞/两辆趾高气扬横冲直撞的汽车瞬间粉身碎骨”(《事故》),高速、碰撞、碎片……它们令我们感到眩晕和不安。糟糕,这是一个事故——让你慢悠悠的农耕时代的故事彻底被颠覆,在你取到的第一束原始火苗还未完全熄灭前:“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一个巨型的大医院里/那些被时代列车碾过的残肢断体/独自在角落里小声祈祷上帝的抚慰”(《医院》)。速度给了我们最彻底的一次脑震荡,那些有关自己曾经是这样那样的记忆瞬间成了散落的碎片。你无法像曾经那样把自己隐藏在森林中——好像树木本身那般自然,好像它的绵延和你的成长在同步进行;你只能困惑地盯着那些巨型的异化物,为自己丢失的(却不知为何丢失和丢失了什么)感到失落和心碎:“这个死胖子,站在沙滩上/看到大风中沧海落日这么美丽的景色/心都碎了,碎成一瓣一瓣/浮在波浪上一起一伏”(《黄昏——一个胖子在海边》)。看呢,看看我们自己,这虚夸的胖、不健康的胖、恨不能死去的胖……
无奈感和滑稽感顺理成章地占据了李少君的笔端——他狠狠哆嗦了一下,我难道不是承诺过要写“异于现代怨恨派之外的另一种谱系/需要考古似的潜心学习,比如/青山一样的安稳,流水一样的缓慢/清风明月下自行散发的一丝丝芳香余韵”(《黄龙溪之秋》)?事实上,诗人李少君的大部分诗歌写作确实如此。可是时代——尤其是我们的时代,如同一个幽深的影子,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纵然人们可以纵情山水,可以一往情深于美景美女,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假山桃源,巨型的时代和它令人压抑的影子却无时不在提醒我们处境的虚幻与尴尬。实际上,我想说的不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不可以醉心于自然,不可以“把远行当修行”(《远游者说》)——纵然它再怎么被质疑。同样,我要从这个安稳而缓慢写作的诗人的诗歌中拎出这么几首,并非有意找茬,或非要证明在此和彼的对照中此是多么的可贵抑或多么的虚伪。——其实归根结底,写作关乎心性:一个诗人的真诚与否,是评判写作的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的合体,这是诗歌批评的难题,诗人彼时彼地写作的成立如何被追认?我想表达的,其实只是——在我开始探讨李少君的诗歌前,想引入的一个潜在因素,那就是现代人的心碎感。心碎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心碎是因为加之于我们所有的记忆——有关祖先和过去的都在这个令人眩晕的时代中被撞得散落天涯。而我们的心碎,首先是因为——曾情有所钟,曾一往情深,最终却不得不在密集的孤独中惶惶不可终日:“从背后看,他巨大的身躯/就象一颗孤独的星球一样颤抖不已”(《黄昏,一个胖子在海边》)。
深情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大概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痴情和至情至今仍然让我们感动: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1]130
衡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1]153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興,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任诞》)[1]155
多年后,我们遗忘了自己如玉山倾倒的风姿,只是看着这被有毒食品堆积起来的中年胖微微叹息。多年后,所谓情,在高调的电视节目和铺天盖地的垃圾文字中看起来华丽而不真实。所幸那些被写在文字中流传下来的曾经的我们看起来还是不俗的,还担当得起钟情、深情、为情而死。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以“美在深情”为题,阐释了古典文学中“情”的至关重要性:“屈与儒、道(庄)渗透融合,形成了以情为核心的魏晋文艺—美学的基本特征。”[2]于是,我们失落的、遗忘的似乎会闪烁在依然保持着前世记忆的残躯中,让我们眼前一亮……这是人性的永恒之物和诗歌的永恒之物。弗莱说:“不管可能作出什么样的妥协和社会安排,诗歌说的是神话的语言,而不是理性或事实的语言;进一步说,它表现的是社会里某种原始的东西,而不是持续改进和提高的东西。”[3]55也难怪诗人李少君有时沉迷且低语:“但就那么一小声,让我从此失魂落魄/成了海天之间的那个为情而流浪者”(《海之传说》;有时豪言壮语:“世事如有意/江山如有情/谁也不如我这样一往情深”;更多时候,在看清了这个世界、看透了生活本身时,“他会自我形容/不过是一个深情之人,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动情/包括美人、山水和萤火虫的微弱光亮”(《新隐士》)。他向所有显性与隐形的诘问——有关诗歌写作的诘问,发出了反诘问:“这个世界伤口还少吗?/还需要我们再往上面撒一把盐吗?/地球已千疮百孔,还需要我们踩个稀巴烂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然而它更是一种固执地对待诗歌本身的态度:我写,不戳痛世界地写,正如一往情深的恋人不会戳痛自己一身臭毛病的情人。当然,你可以说,所有应动情而生的美好瞬间是封闭在恋人的系统中,它们的有效性仅仅囿于其中。这也是事实,因为我们很难说,恋人一心一意的深情一定会打动别人。
可能李少君的写作缺少一个自己之外的出口。当我们品味其诗歌,往往会被一些细节打动:“不过,我的心可以安放在青山绿水之间/我的身体,还得安置在一间有女人的房子里”(《四行诗》);“我和她的争吵/也一下子被风吹散了”(《西湖边》);“只有伊心仪的镇中学林老师走过时/这妖娆少妇才会咦呀呀迎上去/身子一摇三扭,正经地风情万种”(《安良旅馆》)。在李少君的诗歌中,弗罗斯特那般“我和这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更多的是绵绵情意。他写山山水水,描摹人情事态,都有一份惬意——欲望、芥蒂和骚动缺少危险性。或许这样一种安全感——诗人寄情、朝圣的美人、山水,世间的活物无害地封闭了他的写作。说无害,是因为,当我们永远不会那样艰难而深刻地刺穿世界时,可能我们就是最幸福的,可以幸福地动情、深情。问题是,上帝,抚慰我们残躯的上帝!此刻生活着的可是已经心碎的人们。我们安全感的依托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
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
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
(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
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李少君:《抒怀》)
也许,在这首清新的小诗中,可以读到诗人最没有争辩性却无可辩驳的回应。翻开他的诗集,有旅途的风景,想象中的风景——如他所愿,他绘制它们,如绘制明信片。当旅途中的人寄出自己所在地的明信片时,他会去下个地方。我们收到的风景永远包含着一种时间差,一种错过的不真实,明信片的诗意在于时间而不在它本身。诗歌中的风景未必能靠近我们、穿透我们来化解生活中的暴虐和戾气。但是时间、错过,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往情深却令人瞬间动容与柔软:“而观测室里也记录了鹦哥岭近期的两件大事/一是十万只蝴蝶凭借梦想飞过了大海/另外一件是二十七个青年挟着激情冲上了山顶/下山时几支火把在漆黑的山野间熊熊燃烧”(《鹦哥岭》)。云、蝴蝶、娇滴滴的小女,它们都关乎一种弱的理想,源于情之所钟。“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里王戎的悲恸恳切之词令人唏嘘地道出了情与作为芸芸众生之我们的羁绊。诗人亦无意看穿,只是自得其乐或曰无可奈何地守护着这些源于情的弱的理想,即使明知“一切终将远去,包括美,包括爱”。偶尔,它们也会迸射出熊熊燃烧的激情。但不同于立传写史那样的公众写作,诗人为自己划定了私密的写真之地。弗莱认为:“内向性融入到大量的当代艺术之中,例如抽象的单调,排斥外部世界……一种内向情境的唯一优点就是隐私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日益增长的内向性却伴随着隐私性的持续减少”[3]104-105。时代的孤独病怪异地伴随着隐私危机,人们封闭自己的狭小空间恰恰被置于庞大而严密的电子、通信网络的监控之下,一切都被无耻地透明和不透明。我们的时代没有秘密——真正的秘密属于自然的那些不可言说的怡情和忧伤,这一切对于“慷慨激昂/俨然上帝一样严正发言”(《欧洲的冬天》)的人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诗人的秘密地带就是自然,以及一切带着自然风韵的人和物。他自己说:“对于我来说:自然是庙堂,大地是道场,山水是导师,而诗歌就是宗教。”[4]他写,安静、气定神闲地写下这一切,只为事物本身,没有观众:
静穆,晨光似弦
猫儿在墙上,迎着清风
悠闲地弹奏阳光的五线谱
然后,一曲完毕,挥一挥手
踩着猫步走了
良久
世界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李少君:《何为艺术,而且风度》)
诗人认为,不同于西方的“对抗”“个体”观念,中国传统诗学是对“超越”“和谐”的追求。当这种诗学观念化入诗人的性情与阅历中时,他的深情也均匀地分布于诗歌中的自然、大地和山水之中。借助于山水与花草的灵气,诗人希冀自己朝向灵魂自由的方向:“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最终做一个内心的国王/一个灵魂的自治者”(《自白》)。但是,要让诗歌本身说话,而不是借助它的外表来表达思想。德加曾因写诗的苦恼而求助于诗人马拉美,他说:“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完成不了这小小的诗篇,因为我满脑子都是想法。”马拉美回答他:“德加,我们作诗不是靠想法,而是凭靠语言。”[5]让诗歌本身说话,我们会发现诗人所建构的“和谐”是那样容易破碎。穿梭于复杂的机械现象和假山中的幽景——“低头饮茶,独自幽处/在月光下弹琴抑或在风中吟诗”(《新隐士》),诗人自己也会有迷离感:“后来遇到了她/我是悠闲的,让她产生了焦虑/感到了自己生活的非正常/她的焦灼干扰着我/让我也无法悠闲下去/成了一个在长江三角洲东奔西串的推销员”(《上海短期生活》)。这种破碎——或曰干扰是让人无从回避的。就像宇文所安透过沈复与他的妻子精心制作却终不免被外物所破坏的假山所看到的:“沈复的一生都是想方设法要脱离这个世界而钻进某个纯真美妙的小空间中。……但是,他的世界始终是一种玩物,一种难免破碎厄运的玩物”[6]。
太美好的东西都容易破碎,静谧而和睦的诗行让人们觉得不安而不去信任它们。反而是那些一开始就存在的无奈和心碎,令我们鼓起勇气承受打了折扣的愉悦、焦虑和深情。也许归根结底,是我们距离那个最开始的自己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再回去。衡子野一往情深,王长史登茅山恸哭,我们为之动容,只因为他们是被遗忘的我们。当然,诗人有权以他的方式在诗歌中动情、深情——对他人、世界和自己。而如果有回应,即使发生在很久之后,也属难得。我们是否能等到世界的掌声呢?
锡德尼在《为诗辩护》的结尾处,颇有点任性又不失可爱地诅咒那些说诗歌坏话的人:“当你活着的时候,你生活在恋爱中,然而由于缺乏写情诗的技能,总得不到青睐;而当你死的时候,由于缺乏一篇墓志铭,关于你的记忆便从大地上消失”。[7]我们姑且如此叫嚣一声——为诗歌这最有野心的脆弱。以情为切入点,可能会令我们难堪。难堪的并非情本身,而是心碎的现代人如何去把握这样一个太美而又太过脆弱的东西。可能李少君的诗歌写作也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但终归诗歌甘愿守护着脆弱的美和理想,也就为这种写作的可行性进行了辩护——即使它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诗人、诗歌和世界,出错的可能是其中之一——也可能是它们之间微妙的错位,这对诗人而言是无可奈何的。纵然这样那样,诗人也只能如此去写……
[1]刘义庆.世说新语[M].刘孝,标注.王根林,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40.
[3]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M].王逢振,秦明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李少君.草根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
[5]保尔·瓦莱里.瓦莱里散文选[M].唐祖论,钱春绮,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149-150.
[6]宇文所安.追忆[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18.
[7]锡德尼.为诗辩护[M].钱学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74.
责任编辑:黄声波
Profound Emotion in Poetry——Reading Li Shaojun's Poems
CAO Meng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China)
In his poem writing,Li Shaojun always acts his own idea relat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writing that human could get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themselves.Li pours his emotion into everything in his poems because of his temperament.Profound Emotion,an ancient idea combining aesthetics and humanistic care,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oint to study Li's poems.After encountering with the"heart-broken"modern people,profound emotion will change inevitably.However,we could still find it in Li's poetry,though it seems to be somewhat helpless.
Li Shaojun;nature;profound emotion;harmony
I207.2
A
1674-117X(2014)01-0028-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07
2013-08-28
曹梦琰(1986-),女,陕西榆林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