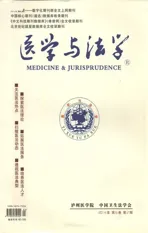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
2014-03-11凌霄
凌霄
◆医与法自由谈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
凌霄
诱惑侦查在打击特定犯罪时具有独特优势,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采用。但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但书条款却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给予了否定性评价。本文拟从两大法系主要代表性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规制着手,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引入诱惑侦查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制度设计进行探讨。
诱惑侦查;犯意诱发型;机会提供型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该条款确认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采用秘密的侦查手段,但其但书条款中对于引诱他人犯罪的秘密侦查手段——“诱惑侦查”——予却给了否定性评价。对此,笔者认为,尽管诱惑侦查作为一种本质上具有欺骗性的侦讯手段,不可避免地存在国家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公权力而带来的便利、诱使没有犯罪意图的公民从事犯罪活动的道德风险,但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应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新型犯罪却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应对此采取“一刀切”式的完全否定,而应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关国家的经验,建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对其进行规制。
一、诱惑侦查及其发展历程
“诱惑侦查”,又叫做“警察圈套”“侦查陷阱”,泛指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受侦查机关指挥的人员故意设定某种能够诱发犯罪的情形以诱使他人犯罪,或者为实施犯罪提供某种便利性的机会以鼓动他人犯罪,与此同时侦查机关以此为根据提起刑事指控,是现代国家为了追惩“隐蔽性无被害人犯罪案件”而采用的特殊侦查方式。[1]通过这种侦查手段,侦查机关能够将犯罪实施者的完整犯罪过程进行全程掌控,破案效率高,取证容易并且难以翻供,尤其是在侦破诸如走私、偷渡、毒品、伪造货币等新型犯罪中往往能够达到人赃俱获的效果。在当前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成为各国警方的普遍手段并且其应用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诱惑侦查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摸钟辨盗”的故事可以算做一种成功的“非典型性诱惑侦查”。作为一项应对政治犯的特殊政策,法国路易十四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用诱惑侦查手段,来镇压异己。现代侦查机关所实施的诱惑侦查,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二战期间为应对间谍破坏活动,将诱惑手段应用于侦查实践当中;二战后,为查禁卖淫、赌博、贩毒等犯罪活动,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上世纪70年代起,其更进一步扩大至侦破有组织犯罪和窃取产业情报当中。例如,纽约市警察局在1971年成立的“街头犯罪侦缉队”就常采用“诱饵”或“圈套”等战术来打击抢劫、扒窃、人身袭击等“街头犯罪”活动,其通过提供实施犯罪的机会或某种便利条件的方式实施诱惑侦查。[2]通过1932年索勒斯违反禁酒法案、1958年谢尔曼提供毒品案、1976年汉普顿贩卖毒品案等判例,美国司法界确立了诱惑侦查的一系列标准。[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此类侦查手段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屡见不鲜;意大利为打击黑手党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更是广泛地采用了诱惑侦查这一手段。
二、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分析
刑事侦查活动作为与公民一系列人身权利密切相关的公权力活动,涉及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界限,历来受到广大司法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出于对国家公权力这一“必要的恶”恣意妄为进而危害民众的担忧,司法机关对于刑事侦查手段的“创新”总是充满了疑惑。而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其内在的欺骗性特质,尤其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利用公民人性的弱点这一特征,备受法学界人士质疑。如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危害国家威信,违背执法机关的道德责任,影响国民的道德观念,容易沦落为“对特定公民抵御犯罪诱惑能力的检验”,与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的保守性质发生尖锐的冲突。因此,诱惑侦查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遭受着来自法学界的质疑。
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新型化的犯罪日渐增多,对司法机关的侦查手段提出了挑战。许多严重的犯罪,如贩卖毒品、伪造货币以及一些有组织的犯罪,对社会的整体利益造成极大的危害,但是这些犯罪又往往是所谓“无被害人的犯罪”或是“被害人同意的犯罪”,与犯罪行为相牵连的人对犯罪行为通常是放任乃至配合的;如果按照传统方式进行侦查,往往难以获得犯罪线索,侦破起来也将极为困难。而且,由于这些犯罪所能带来的高额经济收益,使得犯罪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出现了组织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若任其发展而不采取相应的对策,必将对社会的整体福利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只有采用诱惑侦查措施,这些案件的侦破难度才能大大降低,因此为了有效打击犯罪,保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受侵害,对于特殊的新型犯罪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存在其必要性。
此外,对于所扮演的角色早已从“守夜人国家”转变为“福利国家”的现代国家而言,如果对这些日渐增多且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新型化犯罪持放任的态度,将有失职之虞。同时,就取证而言,与传统的侦查手段相比,诱惑侦查更加简便高效,因为在传统的侦查手段中,对于犯罪实施主体和实施过程的查证必须从碎片化的线索着手、借助逻辑推理逐步完成,导致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是一个完全逆向的过程;[4]而与之相反,侦查人员如采用诱惑侦查手段,由于掌控了犯罪实施者的完整犯罪过程,对犯罪的侦查过程往往与犯罪事实的发展过程同步,极易在犯罪实施者的犯罪过程中对其进行抓捕,在降低对于实施犯罪行为证明难度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查证犯罪的准确性,这对于震慑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大有裨益,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完全否定诱惑侦查手段的合法性,在新型犯罪手段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显得过于僵化和保守。
总之,诱惑侦查作为与公民权利息息相关的一种特殊刑事侦查活动,其最终目的必须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其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合法利益的考量应该并重,任何片面强调打击犯罪或者片面强调保护公民权利的观念,都将为这一侦查手段的有效实施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必须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这有赖于精妙的制度设计,而两大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对于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从不同层面对这一制度的设计指明了方向。
三、两大法系对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由于诉讼传统的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诱惑侦查曾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受当事人主义的深刻影响,比较容易认可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对其适用也曾经较少进行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受到程序法定观念和职权主义传统的影响,曾经倾向于认为只有法定的侦查手段才能为侦查机关所使用,完全否定侦查机关对于诱惑侦查的使用。
随着时间的发展,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界人士逐渐意识到诱惑侦查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从而在一定程度对诱惑侦查进行了限制;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传统的侦查手段面对“隐蔽性无被害人犯罪案件”的严重不适应,也开始逐渐意识到诱惑侦查所可能带来的积极方面,逐渐通过立法的方式授权侦查机关对一些特殊类型的犯罪进行诱惑侦查。从总体看,两大法系国家对诱惑侦查呈现出“有限度地承认其合法性”的趋势,即用法律束缚侦查机关在使用诱惑侦查方面的随意性,强调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尽量避免其可能带来的消极负面后果。下面简要介绍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对于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一)美国
美国为了避免普通公民被诱使而卷入犯罪活动当中,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通过设置内部监督机构规制诱惑侦查,FBI于1978年成立秘密侦查委员会;美国司法部于1980年出台了《关于联邦调查局秘密侦查的准则》,其中包含了关于诱惑侦查的许可标准、申请及批准程序等内容,以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对诱惑侦查予以事前规制;美国法院还通过具体的判例,确立了一系列限制诱惑侦查手段的重要原则。
(二)英国
英国主要通过法院判例等形式,围绕是否采纳由诱惑侦查所采集的证据,从诱惑的后果、陷阱的性质、侦查人员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侦查人员是否滥用自己的角色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规定,以防止警方滥用这一手段。
(三)法国
法国在1992年对其刑事诉讼法典进行修订时,增加了“毒品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一编,突破了“禁止侦查人员参与犯罪”的传统,允许侦查人员以侦查毒品犯罪为目的,参与毒品交易,进而实施诱惑侦查。
(四)日本
日本于二战后受美国法的影响,较早承认了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通过包括《麻药管理法》《鸦片法》和《枪炮刀剑类所持等管理法》等在内的系列法律法规,授权侦查机关在特定情况下采用诱惑手段进行侦查。与此同时,规定区别对待“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情形,认定前者由于存在使本无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的因素,侵犯公民人格自律权而将其界定为非法;而后者由于被诱惑者已经具有了犯罪意图,因此对其采取诱惑措施的行为合法。[5]
相较于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总体而言对于诱惑侦查的认可程度不高,对其法律规制极为严格,在适用范围、诱惑犯罪所能采用的手段和实施前的审查程序上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例如,适用范围上,有的国家仅能使用于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案件,所使用的手段不能有主观的挑逗因素,实施前需经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等。这与大陆法系国家所固有的职权主义诉讼传统是分不开的。
四、对我国建立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型犯罪不断出现,法律应当允许侦查机关根据特殊的犯罪类型采取一定的诱惑性侦查手段,以最大可能地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对可能“诱使他人犯罪”的秘密侦查手段给予完全否定性的法律评价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时,鉴于诱惑侦查的特殊性,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严格规制,如诱惑侦查适用范围模糊、适用对象随意、适用过程缺乏监督机制等,极有可能给公民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权威造成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经媒体报道的此类案件并不少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甘肃马进孝制造系列假毒品案。①鉴此,为防范诱惑侦查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参照国外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我国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应注重以下方面:
(一)规制基本原则
1.对象特定原则。
即禁止针对不特定的缺乏犯罪嫌疑的对象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否则极易造成司法机关滥用职权、公民人人自危的局面。
2.必要性原则。
即诱惑侦查只应针对具有相当隐蔽性、无被害人且有严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诸如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之类,并且只有在传统侦查手段难以获得证据时方可使用。
3.方法限制原则。
即诱惑侦查所采用的方法必须顾及社会的道德底线。
此外,防止虚假原则和用途正当性原则也是制度建设必不可少的考虑。[6]
(二)具体规制措施
依据上述原则建构的诱惑侦查法律规制手段,需对“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诱惑侦查方式进行区分。侦查机关应当从根本上摒弃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否认其合法性。因为就犯意诱发型而言,其本质在于诱发原本无犯罪意图的人进行犯罪,这实质上等同于教唆他人实施犯罪,完全不符合诱惑侦查打击犯罪的本意。对采取这种手段获取的所谓证据要进行排除,并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法律责任。而对于机会提供型的诱惑侦查,由于被诱惑对象已经存在犯罪意图,因此可从以下方面加以严格规制。
1.就实施主体而言,诱惑侦查只能由享有侦查出书面纠正意见,侦查机关应在法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运用诱惑侦查侦破的案件,检察院审查时尤其应当慎重,必要时可以让侦查机关就诱惑侦查的运用情况作出详细的说明;一旦发现滥用诱惑侦查的情形,应当立即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理。
此外,法院作为刑事诉讼的最终裁判机关,在规制诱惑侦查方面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法院应当就审判前的追诉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判。在实践中,法院应当通盘考虑上述因素,就诱惑侦查是否恰当、给被告人最终实施犯罪造成何种影响作出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定罪量刑。对于非法的诱惑侦查所获得的证据,法院应当本着保护人权的原则进行排除,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最终救济功能和对侦查机关的制约监督。
五、结语
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力动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一旦被人滥用,那么任何保证都要甘拜下风。”诱惑侦查作为体现公权力强制性侦查手段的一种,能以较高的效率更为彻底地防范某些特殊类型的犯罪,因此赋予其合法性是有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但若国家公权力恣意妄为,则必将使其走上诱发犯罪、侵犯人权的反面。“程序的法治化首先是侦查的法治化。”[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诱惑侦查这一特殊的侦查手段,我们在将其引入的同时,也要最大可能地利用法律手段降低其负面影响,从而实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效果的最佳统一。权的侦查主体来实施。
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主体主要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侦查部门、军队保卫机关等。此外,海关对走私犯罪也享有相应的侦查管辖权,也应被纳入其中。诱惑侦查实施的主体应限定为由法律授权的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既不允许侦查机关及其人员委托或者授意普通公民实施诱惑侦查行为,也不允许普通公民从事诱惑侦查,从源头上避免诱惑侦查行为的滥用。
2.就适用范围而言,需对适用诱惑侦查的犯罪进行明确规定。
只有那些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但使用传统的从线索推理的侦查手段侦破难度又极大的犯罪,才允许使用诱惑侦查手段。
3.在诱惑侦查的方式上,应当严格遵遁比例原则。
即刑事案件的性质越严重,针对其进行诱惑侦查所采取手段的诱惑性就可以越高,将诱惑性程度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保持正向相关关系。同时,采取诱惑的方式不得超越社会伦理道德底线,否则用这种方式收集的证据应当被视为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加以排除。
4.在诱惑侦查适用的程序方面,应当采用公安机关内部控制与检察机关监督相结合的方式。
首先,侦查人员实施诱惑侦查前必须取得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除特殊情形(如情况紧急)外,侦查人员非经许可不得擅自决定使用诱惑侦查,否则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其次,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从主体、适用范围、程序等方面进行监督,在发现诱惑侦查所采取的诱惑手段有超出合理界限或者有违社会道德准则、极易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时,应当直接向侦查机关提
注释
①在马进孝制造系列假毒品案中,当地公安机关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利用社会闲散人员马进孝作为所谓特勤人员参与办案,而马进孝为了骗取奖金,竟然将白粉和感冒药片捣碎后混合在一起陷害无辜的民众,导致两人被错误判处死刑,一人死缓。案发后,马进孝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而当地公安机关的相关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刑事处罚和行政处分。同时,此案也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减少公安机关随意使用诱惑侦查手段的探讨。
[1]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56,261,264-271.
[2]吴丹红.诱惑侦查:既然实际采用,就该立法规制[N].检察日报,2006-3-20(3).
[3]姜翠玉.对诱惑性侦查手段的法学思考[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14(4):76-80.
[4]游伟、谢锡美.论犯罪特情侦查及其制度设计[J].政治与法律,2001(5):19-23.
[5]谢光永.国外侦查陷阱探微[N].检察日报,2000-12-13 (3).
[6]龙宗智.试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J].法学研究,2002(4):96-104.
[7]何家弘,南英.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0
(责任编辑:罗刚)
On the Regulations of Entrapment Detection——Comments on Article 151 of the Newly Amended"Criminal Procedural Law"
Ling Xiao
Entrapment Detection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fighting against some specific crimes,and has been adopted in some aspects of detecting practice in our country.While in Article 151 of the newly amended Criminal Procedural Law which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1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the legitimacy of entrapment detection has been given the negative evaluation.This article,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ions of entrapment detection of som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states of the two legal systems, intends to discuss the necessity to adopt such system and the methods of system design.
entrapment detection;criminal inducing type;opportunity-provided type
凌霄,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事法学、中国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