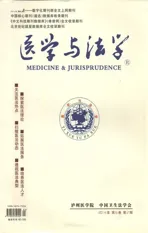美国马萨诸塞州精神病患者非自愿治疗制度初探*
2014-03-11陈绍辉
陈绍辉
◆海外医与法
美国马萨诸塞州精神病患者非自愿治疗制度初探*
陈绍辉
本文通过介绍美国马萨诸塞州精神病患者非自愿治疗制度及其发展启用标准和程序,评析该制度的不足及可供借鉴之处。
精神病患者;非自愿治疗;《精神卫生法》
在美国,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被称为“民事拘禁”(civil commitment)或“非自愿拘禁”(involuntarily commitment),是指将未实施犯罪行为的精神病患者监禁于精神卫生机构。[1]作为“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2]民事拘禁受到严格的法律规制;但美国并没有统一的民事拘禁法,其有关民事拘禁的法律均由各州自行制定,而各州有关精神病患者非自愿治疗的立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异。就此而言,如要了解美国的非自愿治疗法律制度,除了需要关注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作出的重要判决之外,还需把握具有代表性的州的相关法律及判例。本文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精神卫生法》为例,对该州的民事拘禁制度予以介绍,以期从中管窥美国的非自愿治疗法律制度。
一、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事拘禁制度的发展
美国民事拘禁制度起源于殖民时代,其目的纯粹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其具体措施是将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拘禁于特定设施之中,通常是监狱或济贫院。因此,在殖民地后期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初,监狱和济贫院内充斥着精神病患者。[3]尽管当时就有法律规定可拘禁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精神病患者,但此时还没有以治疗为目的的精神病医院等设施存在,对精神病患者的拘禁尚不能称为“强制治疗”。美国最早的精神病医院建立于18世纪末,而马萨诸塞州在19世纪30年代建立了美国最早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并开始引发将精神病患者从监狱转移至精神病医院之发展趋势。[4]当时的非自愿拘禁程序十分简单和非正式,通常只需要一名或两名医生同意即可,“法律程序被视为毫无必要且不利于治疗。”[5]
19世纪,精神病院模式在马萨诸塞州和美国其他州迅速发展。到19世纪中期,这些机构规模越来越大,住院人数急剧增加,但精神病患者获得“治疗”的希望几乎不存在。由于多数精神卫生机构条件简陋,人满为患,住院精神病患者的境况极为恶劣,精神病医院几乎成为无限期收容精神病患者的“人体货仓”。因此,一些精神病患者的亲属开始控诉精神病医院的条件和患者在医院内所受到的非人道待遇;也有患者公开指控被家人和医生共谋投入精神病医院,其中最著名的当属E.P.W.Packard。Packard因与丈夫之间的宗教信仰分歧而被其丈夫送入精神病医院拘禁达3年之久。在出院之后,Packard开始奔走呼吁、著书立说,倡导对民事拘禁法的改革,从而掀起20世纪中后期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民事拘禁制度改革运动;[6]其中,最为普遍的改革是规定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入院需经陪审团的审理。与此同时,自愿住院原则开始在立法和实践中获得认可,其最具代表性的是1881年马萨诸塞州所颁布的美国第一部允许个人自愿入院的法律。在1909年的一项法律中,马萨诸塞州对精神病患者非自愿拘禁和自愿入院规定了不同的条件,其中规定非自愿拘禁要有法院的审查,而自愿入院完全由个人决定。对于紧急拘禁,法律不要求遵循长期拘禁所要求的司法审查程序。
之前,马萨诸塞州的非自愿拘禁法基本维持不变;直到1970年,该州为顺应当时强化对精神病患者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对《精神卫生法》进行了大刀阔斧地修改,这些内容即构成了现行精神卫生法典的基本内容;即便是2000年和2004年的修改,也仅仅是对其部分内容进行微调,有关非自愿拘禁的实体标准和正当程序基本保持不变。现行《精神卫生法》构成马萨诸塞州“一般法”(General Law)的第一百二十三章(G.L.c.123),[7]该法共有三十六条,以精神病患者的治疗为规范重点。马萨诸塞州《精神卫生法》将精神病患者的入院治疗分为自愿入院和非自愿入院。自愿入院的申请人可以是患者(年满16周岁及以上)本人,也可以是患者的父母或未成年患者的监护人,或者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等。患者本人的申请只有在其具有作出申请的行为能力和接受治疗的意愿时才可以获得许可;如果是监护人的申请,监护人必须要有法院特别的授权,且这一授权必须是被认为入院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非自愿治疗只适用于符合法定标准的精神病患者,包括刑事审判中因精神疾病无受审能力和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被告,但对刑事被告和囚犯的拘禁则受特别程序的规范。[8]本文仅介绍刑事被告以外的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制度。
二、非自愿治疗的条件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各州有关实施民事拘禁的条件的法律规定差异较大。只有15个司法管辖区以患有精神疾病和对本人、他人具有危险或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非自愿拘禁的条件;14个司法管辖区以患有精神疾病和具有危险性或需要治疗与看护为非自愿拘禁的前提;7个州以保护本人或他人的“福利”之需要采取拘禁措施;其他15个州的强制住院以精神疾病导致本人需要照护与治疗或“适合住院”为前提。[9]在1975年的奥康纳诉唐纳森(O'Connor v.Donaldson)案中,[10]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精神疾病加危险性”的民事拘禁要件,即非自愿拘禁仅适合于患有精神疾病和对本人或他人具有危险性的患者。在奥康纳案之后,各州的民事拘禁标准逐渐趋于统一,“精神疾病加危险性”标准成为民事拘禁的普遍标准。马萨诸塞州也不例外,其非自愿治疗的条件主要包括:一是患有精神病;二是若不住院,患者具有将因精神疾病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三是没有比住院更小的限制性替代措施(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下文将具体介绍前述三个条件。
(一)患有精神疾病
根据马萨诸塞州精神卫生部(The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简称“DMH”)的界定,“精神疾病”是指因思维、情感、感知、适用能力或记忆的严重障碍从而严重损害患者的判断、行为、认识能力或满足一般生活需求的能力,但不包括酒精依赖。因此,精神疾病必须是严重精神障碍,必须要有证据证明“严重障碍从而严重损害”。实践中,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普遍使用《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诊断精神疾病。在民事拘禁的听证程序中,申请人的专家证人、精神医生一般都是以该手册作为证明被申请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标准。这些诊断标准确实有助于法院认定被申请人的状况是否符合法定精神疾病的概念,但是即便被申请人的状况符合该手册的诊断分类标准,也并不必然表明其属于法定的精神疾病,后者要求“严重障碍从而严重损害”患者的功能。因此,一些法院认为DSM-IV诊断标准只是建议性质,临床诊断本身并不是认定“精神疾病”的充分条件。
(二)严重损害可能性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一条的规定,“严重损害可能性”(likelihood of serious harm)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有证据表明患者具有将造成本人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性或危胁,试图自杀或实施严重身体伤害;二是有证据表明患者具有将以杀人或其他暴力行为对他人造成实质性的人身危险,或使他人处于暴力和严重人身伤害的恐惧之中;三是有证据表明患者的判断能力受损以致在社区中无自我保护能力和满足自身基本需求,从而具有伤害自身的十分严重的风险。因此,损害的表现形式包括对本人危险、对他人的危险以及不能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等,而第三种情形所造成的损害风险必须达到伤害自身健康的“十分严重”(a very substantial risk)的危险程度,仅仅是“严重损害”还不够;同时,损害危险必须是对本人或他人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并不足以证明严重损害的存在。
对于严重损害危险的认定,首先,要证明损害危险必须是因精神疾病所致,即证明精神疾病和严重损害危险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损害危险必须是精神疾病所导致的后果。其次,在Lessard v. Schmidt案中,[11]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危险性的认定以“试图或威胁实施严重损害本人或他人的最近的明显行为”为前提。因此,很多州对危险性的认定都以被告的“最近行为”(recent act)或“明显行为”("overt act")作为前提条件。马萨诸塞州对危险性的证明无须“最近的明显行为”要件,但也有判例表明,需以“即刻危险”作为危险性成立的条件。[12]最后,法院必须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严重损害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民事拘禁的证明标准采取“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标准,而不是联邦最高法院在Addington V.Texas案中所确立的“清晰、明确和令人信服”(clear,unequivocal and convincing)标准。[13]这意味着马萨诸塞州的民事拘禁证明标准采取了刑事证明标准。
(三)最小限制性替代措施
对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应符合最小限制原则,即只有在没有比住院治疗更小的限制替代措施的情况下,方可适用非自愿拘禁。因此,在民事拘禁听证中,法院必须考虑“所有可行的住院替代措施”。[14]但“最小限制性替代措施”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无论立法机关、法院还是精神卫生部门都未曾对其作出准确界定。从实践看,其适用主要把握两点:首先,申请人应证明只有将患者拘禁在精神卫生机构中才是保证其获得治疗和安全的唯一方法;其次,如果存在更小限制措施,但由于这些限制措施目前并不具有可及性,也可考虑非自愿治疗。
三、非自愿治疗的程序
马萨诸塞州《精神卫生法》本质上是一部程序法,其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和正当法律程序,以最大程度保障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自由和权利,防止政府和精神卫生机构权力的滥用。该法案针对不同的拘禁对象,将民事拘禁类型化,并针对不同类型规定不同的程序,如Bridgewater州立医院(the Bridgewater state hospital)对男性精神病患者的拘禁(第十三条)、对无受审能力或刑事责任能力被告的拘禁(第十六条)、对酒精等物质依赖者的拘禁(第三十五条)等都有不同的程序规定。本文仅介绍上述特殊主体之外的一般精神病患者的拘禁程序。根据作出拘禁决定的主体和拘禁期限的不同,可将这类拘禁分为短期拘禁和长期拘禁。前者由精神卫生机构决定,拘禁期限只有3天;后者由法院通过听证程序决定,且听证程序普遍适用于上述特殊主体的拘禁决定,因而具有普遍性和适用的广泛性。
(一)短期拘禁
短期拘禁规定见于《精神卫生法》第十二条,一般是在紧急情况下对特定患者所采取的临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拘禁措施。该措施由精神卫生机构决定,无需经过法院的审查,但拘禁时间只有3天。如果期限届满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除非患者同意继续治疗,否则,精神卫生机构应向法院提出拘禁申请方可继续拘禁患者。
1.短期拘禁启动的主体。
(1)依“被指定的医生”(a designated physician)的申请入院。
“被指定的医生”是指被专门指定有权根据精神卫生部的相关法规将患者收治入院的医生。经“被指定的医生”检查而认定一个人因精神病具有造成严重损害可能性的,该医生可填写规定格式的表格,将该人收治入院或送至相关精神卫生机构。由于患者可能仅依据“被指定医生”的申请表格入院,因而医生必须作出实际检查。尽管法律要求医生在有“合理理由”认为精神病患者不予住院将具有造成严重损害可能性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将该患者收治入院,但“被指定医生”必须认定不予住院将造成严重损害的实际可能性。
(2)依非“被指定医生”、心理医生或精神科护士的申请入院。
经检查,“被指定医生”以外的医生、具有资质的心理医生或精神科护士有合理理由认为患者由于精神疾病不予住院将导致严重损害可能性的,可以签署规定表格,将患者予以扣留,并将之送至精神卫生机构。在到达医院后,应由“被指定医生”立即进行精神医学检查,只有在“被指定医生”认定不予住院将具有事实上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时,方可将其入院。
(3)依警察申请入院。
在紧急情况下,当医生、具备资质的心理医生或精神科护士不在场时,警察有合理理由认为某个人由于精神疾病不予住院将具有导致严重损害可能性的,可将其送至精神卫生机构并申请入院。在到达医院后,精神科医生应在2小时内立刻实施检查。只有在“被指定医生”认定患者由于精神疾病不予住院将具有事实上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时,方可将其收治入院。
(4)依地区法院或未成年法庭决定入院。
任何人都可向地区法院或未成年法庭申请拘禁那些被认为不予住院将具有造成严重损害可能性的人。如该人经听证程序而有充分证据表明非自愿拘禁具有“必要性或适当性”的,法院可授权警察逮捕该人。一旦被逮捕,该人将被送至法院或其他地方接受指定精神科医生或具有资质的心理医生的检查。如果经检查认定该人由于精神疾病不予住院将具有造成严重损害可能性的,法院可作出为期3天的拘禁决定。
2.患者有权获得律师帮助。
患者入院有权获得律师代理,精神卫生机构应通知公共律师服务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Public Counsel Services,简称“CPCS”)为其指定代理人。CPCS接到通知后,应第一时间为患者指定律师,律师应在被任命后1个工作日内会见患者,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
3.短期拘禁的救济:紧急听证。
对于短期拘禁,患者或其代理人有合理理由认为拘禁将导致入院程序的滥用或误用,可向地区法院申请紧急听证。除是应患者或代理人的申请外,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的当天或不迟于下一个工作日举行听证。
4.被短期拘禁者的出院程序。
任何患者可在3天届满后随时出院,除非患者自愿继续住院、精神卫生机构的主管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七条的规定向地区法院或未成年法庭提出拘禁申请时,才可以继续拘禁该患者。此外,在为期3天的住院中,对于无须继续接受治疗的患者,主管可决定安排其出院。
(二)长期拘禁
长期拘禁适用于符合非自愿住院条件的精神病患者。长期拘禁由于需要较长时间限制和剥夺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自由,因此必须经过法院的听证,在法院作出拘禁决定后,提出申请的精神卫生机构才可以非自愿拘禁患者。
1.长期拘禁的启动。
精神卫生机构的主管认为患者不住院将因精神疾病而具有造成严重损害可能性的,可向有管辖权的精神卫生机构所在地的地区法院或未成年法庭申请拘禁,并将患者拘禁于该机构。精神卫生机构因存在以下情形时,可申请拘禁听证:其一,附条件自愿入院患者表示在期满后将出院,但精神卫生机构的主管认为应对其予以拘禁的,可在该患者入院治疗的3天期满前向地区法院提出拘禁申请;其二,对于为期3天的短期拘禁,精神卫生机构认为患者符合非自愿住院条件应接受住院治疗的;其三,拘禁超过6个月,需申请延期拘禁的。
2.长期拘禁的听证程序。
(1)举行听证的时限。
法院收到拘禁申请后,应通知患者本人、其近亲属或监护人并告知举行听证的日期。除延期拘禁的听证、无受审能力被告和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告的拘禁应在收到申请后14天内举行听证外,其他任何人的拘禁听证应在收到申请后5天内举行,除非患者本人或其代理人申请延期。
(2)举行听证的地点。
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民事拘禁的听证可以在精神卫生机构内举行,也可以在法院举行。支持听证在精神卫生机构内举行的理由主要有二个:一是在医院听证能够“避免法庭的严肃性和正式性”,[15]使患者对“法院恐怖环境”产生的焦虑和不信任降至最低,同时,也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法院听证可能给患者带来耻辱感和污名;二是降低听证的成本,在医院举行听证“避免了组织转移方面的问题,方便精神医生和医院职工出席听证”,[16]避免了患者、医生及专家证人等出席听证的舟车劳顿。但反对者认为,医院听证除非保持司法仪式贯穿于听证的布置和实施,否则听证可能看上去与治疗场合相混淆;[17]在医院听证中,代理人、律师、法官、证人和医院的各类人员围坐在医院的会议室,法庭的尊严几乎荡然无存,在此情形下,患者可能无法感受到司法的尊严和被认真对待;此外,尽管医院听证可以降低患者和医院方面的成本,但也不能忽视法院将整个法庭搬到医院开庭所增加的司法成本。尽管如此,从实践看,多数听证都是在精神卫生机构内举行,这几乎成为不成文的规则。
(3)患者有权获得律师帮助。
在拘禁听证中,患者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除非已经有代理人,否则法院应在收到拘禁申请后及时通知CPCS为其指定律师。如果患者拒绝律师代理,法院应判定其是否具有放弃的行为能力。如果不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或者他“不能在听证中有效行使其权利”,则必须为其指定律师;如果患者拒绝被指定的律师,应为其指定其他律师。律师应第一时间与患者会见,并保证患者在与律师会见后得有2天以上的时间准备听证。
(4)听证的举行。
拘禁听证即可在申请的精神卫生机构内,也可在法院内举行。在听证中,患者及其代理人有权出席听证。只有在患者或其代理人要求或特殊情况下,听证方可缺席举行。鉴于民事拘禁将严重剥夺人身自由,被告被赋予充分的、对抗式听证的权利,包括陈述权、提交证据、申请证人出庭、对证人交叉询问的权利以及不公开听证权等。
(5)听证的结果。
法院必须在听证结束后10天内作出判决。一旦法院作出民事拘禁的命令,申请人将被授权拘禁患者6个月。在期满前,精神卫生机构可向法院申请延期拘禁,经听证可延长1年。
3.拘禁上诉。
对于法院的民事拘禁命令,患者可通过两个途径提起上诉:一是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九条a款之规定,对于拘禁听证、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听证、无受审能力听证中出现的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作为民事案件向地区法院上诉的部门(the appellate divis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s)提起上诉;二是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九条b款之规定,在拘禁期间,患者认为其已不符合拘禁条件的,可向上诉法院申请出院。上诉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应举行听证,经听证认定患者不再患有精神疾病的、不住院不会具有造成严重损害可能性的、最近没有反复实施自伤行为或攻击行为的、或者可在其他机构中接受治疗的,法院应命令释放该人。严格意义上讲,这种情形并不属于“上诉”,而是在拘禁过程中的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出院。
四、对马萨诸塞州非自愿治疗制度的评析
如同其他州的民事拘禁法,马萨诸塞州的《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给予严格的实体和程序保护。尽管民事拘禁具有多重目标,如治疗疾病、维护患者健康和保护公众安全等,[18]但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对政府侵犯个人自由这一诉求进行限制。在人身自由、患者健康和公共利益的价值冲突中,立法的价值取向明显倾向于患者本人的自由权利,这在马萨诸塞州的民事拘禁制度中体现最为明显。其一,非自愿治疗的标准趋于严格。对于民事拘禁的条件,不少州除了采取普遍认可的危险性标准之外,还将“严重残疾”“需要治疗”“不住院将导致状况恶化”或“不能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等作为非自愿治疗的条件。马萨诸塞州尽管在“严重损害可能性”要件中将“不能满足基本需求”作为该要件的表现形式之一,但要求达到“十分严重”的危险程度,从而缩小了该条件的适用空间。其二,民事拘禁实行司法化、对抗式的听证程序,并赋予患者在拘禁程序中的对抗式听证权利,包括代理权、辩护权、提交证据、申请证人出庭、质证和对证人交叉询问的权利等。法律正当程序完全适用于民事拘禁听证,并受正当程序的严密保护。其三,民事拘禁采取刑事程序的标准,给予患者诸多刑事被告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例如,法院按规定要为贫困患者和没有代理人的患者指定代理律师,对民事拘禁的认定的证明标准采取刑事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等。其四,限制精神卫生机构短期拘禁和举行听证的期限,减少不受司法审查的拘禁时间。在2000年之前,不受法院审查的短期拘禁的期限为10天;2000年对《精神卫生法》修改时将之减少为4天,而2004年则限定为3天。同样,法院举行听证的期限也一度受到限制,由之前收到拘禁申请开始,在拘禁14天内举行听证减少为4天,2004年又将之修改为5天。
严格的非自愿治疗标准固然限制了政府干预个人自由的范围,使非自愿治疗仅限于具有危险性的患者,而对于大量需要治疗却不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因不符合非自愿治疗的标准被排除在强制治疗范围之外,从而无法接受适当的治疗。因此,严格的非自愿治疗标准最大的弊端是不利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和健康,而对患者过度的权利保护,很可能导致其“死于权利之上”。[19]对很多缺乏自知力而需要治疗的患者而言,最迫切需要的或许是健康权而非人身自由;如果固守所谓的“自由权利至上”的理念,很可能牺牲患者的健康利益和有质量的生活。因此,很多学者对严格的危险性标准提出了批评,改变单一的危险标准的呼声日益强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Stone教授所提出的“感谢”理论("thank you"theory)。该理论认为,对于缺乏自主决定能力的患者而言,最需要是的获得治疗,且能够从治疗中受益;在接受有效治疗之后,患者将会感激非自愿拘禁。[20]根据这一理论,美国精神卫生协会在其所制定的《民事拘禁示范法》中改变了以往的危险性标准,允许对因严重精神疾病导致功能障碍而无法作出治疗决定的精神病患者采取非自愿治疗。尽管这一做法并没有完全为各州所接受,但也有一些州开始放宽民事拘禁的条件,如,扩大“严重残疾”(grave disability)外延,使之包含“状况严重恶化”“不能照顾自己”等情形。
虽然司法化、对抗式的民事拘禁程序使精神病患者的正当程序权利获得充分的保障,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非自愿治疗的滥用和对人身自由的过度限制,但司法化、对抗式听证的直接代价是对医患之间的信赖关系的侵蚀——一旦精神卫生机构向法院提出拘禁申请,医患之间相互信赖的治疗关系立即转变为诉讼上的对抗关系,两者不仅无法在非自愿治疗的目的上达成一致,相反还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敌对关系。在诉讼中,代理人的介入固然增强了患者的对抗能力,但代理人的目标显然不是使患者获得适当的治疗,而是如何使患者获得释放出院,不管这是否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因此,正当程序权利的过分强调也可能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和健康利益。事实上,在民事拘禁中医患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关系,至少就患者的治疗和健康而言,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在民事拘禁程序中,医生、法官、律师、患者及其家人应共同合作达成共识,使需要治疗的患者获得治疗,这也就是Carol Warren所提出的“共识”(common sense)模式;[21]因此,不少学者建议修改以刑事正当程序为范本的拘禁程序标准,摈弃对抗式听证,限制正当程序的要求和证据标准;[22]即便是在坚持正当程序权利基础上,也应强调对患者的治疗,并以此作为《精神卫生法》改革的方向。[23]
我国《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也采取了单一的危险性标准,但何谓“伤害自身的危险”和“伤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其界定却是模糊不清的,例如,“伤害自身”除了自杀或自伤(自残)之外,是否还包括不予住院将导致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严重失能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和满足基本需求、需要治疗等情形?如果对“伤害自身”作狭隘的理解,是否会导致急需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因不符合非自愿治疗的条件而被排除在强制治疗之外呢?同时,我国《精神卫生法》武断地将“对本人危险”的精神病患者的非自愿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了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而尽管在多数情况下,监护人会本着为患者的最大利益行事,但也不排除监护人出于各种考虑,拒绝同意应当接受非自愿治疗的患者住院,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病患者的健康利益又如何维护?
对我国《精神卫生法》的批评之一是非自愿治疗缺乏正当程序的保护,没有将“非自愿住院置于司法机制的监督之下”。[24]在《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过程中,也有学者和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非自愿治疗应由法院决定。[25]无论出于精神病患者权利之保障,还是正当程序理念之要求,上述主张都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当我们在构建美国式的司法化、对抗式的强制医疗程序时,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过度的程序规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而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1]Garner,Bryan A.Black's Law Dictionary[M].6th ed.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0:p245.
[2]Humphrey v.Cady,405 U.S.504,509(1972).
[3]Paul S.Appelbaum.A History of Civil Commitment and Related Reforms in the United States:Lessons for Today[J].Developments in Mental Health Law,2006(25):13.
[4][6]Valerie L.Collins.Camouflaged Legitimacy:Civil Commitment,Property Rights,and Legal Isolation[J].Howard Law Journal,2009,(52):413,415.
[7]Chapter123.[EB/OL].[2014-1-3].https://malegislature. 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VII/Chapter123.
[8]G.L.c.123第十五、十六、十七条和第十八条.
[9]Note.Developments in the Law:Civil Commi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J].Harvard Law Review.1974,(87):p1203-1204.
[10]422 U.S.563(1975).
[11]421 U.S.957(1975).
[12]Commonwealth v.Rosenberg,410 Mass.347,363 (1991).
[13]441 U.S.418.
[14]Commonwealth v.Nassar,308 Mass.908,918(1980).
[15]Wexler&Scoville.The Administraion of Psychiatric Justice: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izona[J].ARIZ.L.REV.1971, (13):71.
[5][16][17]Michael L.Perlin.Mental disability law:civil and criminal(volume 1)[M].VIRGINIA:LEXIS LAW PUBLISHING,1998:54-55,321.
[18]Paul S.Appelbaum.Civil Commitment from Systems Perspective[J].Law and Human Behavior,1992,(1):63
[19]Treffert DA.Dying with their rightson[J].Am J Psychiary,1973,(130):1041.
[20]Stone AA.Mental Health and Law:A System Transition [J].Rockville,NIMH,1983.
[21]Carol Warren.Court of last resort:Mental illness and the law[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82.
[22]Donald H.J.Hermann,Barriers to Providing Effective Treatment:A Critique of Tensions in Procedural,Substantive, and Dispositional Criteria in Involuntary Commitment[J].Vand. L.Rev.1986(39):83.
[23]Francis J.O’Connor,Esp.Mental Health Law and Civil Commitment:Litigation and the Need for Further Reform.[EB/ OL].[2014-1-3]http://www.therogerslawfirm.com/documents/Litigation%20and%20the%20Need%20for%20Further%20Reform. pdf.
[24]杨承忻.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精神卫生法——司法精神病学的专业分析和建议[J].中国医院院长,2012,8(6):74-77.
[25]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14.
(责任编辑:黎志敏)
On the Involuntary Treatment System for Psychopaths in Massachusetts,USA
Chen Shaohui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involuntary treatment system for psychopaths in Massachusetts,USA,and examines its development,standards and procedures.Moreover,this paper analysies the defects and benefits of involuntary treatment system.
psychopath;involuntary treatment;Mental Health Law
本文系四川医事卫生法治研究中心立项资助项目“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研究”(项目编号:YF13-ZO2)的阶段性成果。
陈绍辉,江西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