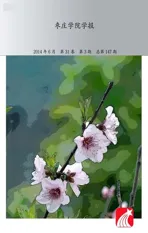文学寻根、青春赋形与主体建构
2014-02-05徐勇
徐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对于寻根写作,有必要把主要倡导者同被追认或归类的寻根作家区分开来。因为,如若按照研究者所指出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其(指的是寻根写作——引注)所包容的文学形态,即使在当时也并不统一……其中,既包括由‘寻根’的主要倡导者如韩少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以及与这些倡导者有着相类的文化诉求和历史经验的莫言、王安忆的作品;也包括寻根倡导者在发出‘宣言’时予以追认或嘉许的作家,如写江苏高邮故事的汪曾祺、写陕南商周文化的贾平凹、写草原文化的乌热尔图等的作品;同时还包括一些写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陆文夫写苏州文化的《美食家》、冯骥才写天津文化的《神鞭》和《三寸金莲》、表现‘京味文化’的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和《索七的后人》及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等。”①在这些被称之为寻根的小说中,理论诉求和创作实践之间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而在作家群构成上,这些作家中既有知青作家,也有五七作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家在创作所谓的寻根小说前后,他们创作上的“异”比“同”要大得多。他们的“聚合”只是短暂的,创作道路各不相同甚至相差悬殊,因此,与其把这些作家作品仅仅冠之以“寻根”写作了事,不如区别对待并做具体分析。
文学寻根作为一个潮流出现,其中无疑有这些倡导者的倡导之功在,但其之所以是潮流而不仅仅是一次命名,还在于这种命名背后的历史动因。对于我们来说,既要看到这些倡导者们的有意识的诉求,也要看到他们这一诉求背后的无意识甚至潜意识的成分来,尤其是后者,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寻根写作或许更为重要。
一、穷乡僻壤与文学寻根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不茂。”这句话几可以作为寻根文学的理论旗帜,在这一旗帜下,他也正式举起了“传统文化”的大旗。但问题是,“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好坏的,何况他提出“传统文化”时其意并不仅仅在传统,而是另有所指。“中国作家们写过住房问题和冤案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提出文化寻根,与他对当前现实主义写作——伤痕、反思和改革写作——的不满不无关系。很多年后,在谈到被视为与“寻根文学”有内在关联的“杭州会议”(1984年)时,韩少功回忆到“那次会议开得很热烈,大家谈得昏天黑地。主要的话题就是对伤痕文学的反省。伤痕文学的确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但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所以与会者希望在美学思想上实现新的解放。”②《文学的根》,据韩少功回忆说,就是那次会议发言的“延伸和展开”③。可见,这种不满,与他提出“传统文化”说之间无疑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而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十多年,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八五年的这篇文章时说道“我对传统并没有特别的热爱,如果历史真是在作直线进步的话,如果中国人过好日子必须以否定传统为前提的话,那么否定就否定吧,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守灵人一样为古人而活着。”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正是不满于伤痕、反思,特别是改革文学中那种现代性的伟大承诺他才倡导“传统文化”的。换言之,韩少功眼中的“传统”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有待阐释的客体,而实际上,“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构成,其中有各个层面。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之提倡“传统”与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否如甘阳所说的那样截然对立呢?)实际上,韩少功已经注意到了传统的复杂之处,他提出“规范文化”和“不规范文化”的区分正是看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僵硬之所在,在他看来,似乎只有那些边缘地带的“不规范文化”才真正具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属于不规范文化。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奇风异俗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统。它们有时可被纳入规范……反过来……有些规范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流入乡野,默默潜藏……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承托着我们规范文化的地壳。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上层文化绝处逢生,总是依靠对民间不规范文化进行吸收,来获得营养和能量,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文学的根》)可见,韩少功所说的“传统文化”的再生,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不规范文化”,正是因为它的“不规范”,它也就格外显得有活力。而这些“不规范文化”很多时候是被视为“正统”之外的,这与五四时期胡适和周作人等人从正统诗文之外去寻根五四新文学的源流其实有一脉相承之处。从这个角度看,韩少功提出“文学寻根”,与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之间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他是想从更高的意义上为当时的改革话语寻找传统的合法性。他虽然批判传统文学中僵硬而毫无生气的“规范文化”,但他提倡“不规范文化”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规范文化”,是使不规范变得规范,而令规范文化显得富有生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韩少功提出文学寻根,其实是想到边缘地带去寻找“不规范文化”。他提出的湖南的楚文化,贾平凹“商周系列”代表的秦汉文化,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所呈现的吴越文化,以及乌热尔图的小说表现的鄂温克草原文化,等等都带有这种特点。但我们还要注意一点,那就是韩少功之所以提出文学寻根,其实是和他的知青经验密不可分的,就像前面所引《文学的根》中开头所说“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而实际上,寻根倡导者的很多寻根作品都与他们的插队生活息息相关的。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阿城的“三王”系列了,这些小说,就是直接以知青生活取材的。而即使是韩少功的寻根小说像《归去来》、《女女女》、《诱惑》、《空城》等,也总是离不开他的知青岁月。更不要说郑义的《远村》和《老井》简直就是写他插队过的陕西山区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认为,寻根文学提倡的不规范文化,从大的方面讲,与20世纪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正是这场运动,使得那些日后从事文化文学工作的知青,一下子接触到广大的边缘地带,而正是这段经历,促成他们日后从边缘地带的不规范文化中提出寻根的主张。
这里还是可以从边缘地带的不规范文化这一表述入手。韩少功提出这一说法,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中心地带和中心地带的规范文化的存在。而实际上,边缘地带,既是知青一代人的历史处境和形态,也是他们返城后现实处境的表征。这一处境决定了他们很难进入到现实中心秩序中去,而即使是文学创作,就知青而言,他们对“文革”之“创”的一味的伤痕和反思式的写作,也并不能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毕竟,这种创伤中,就有知青——红卫兵一代的所造就的成分在。也就是说,“边缘地带”其实就是80年代中知青一代现实和历史处境的隐喻和象征。如果说边缘地带对应的是不规范文化,中心地带对应的就是规范文化了。而按照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的阐释:“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上层文化绝处逢生,总是依靠对民间不规范文化进行吸收,来获得营养和能量,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可以看出,寻根作家提出“不规范文化”的范畴,恰恰是他们想以此进入规范文化和中心地带的意图的流露,因为就像前面所引的,“不规范文化”最终还是为了使规范文化得以再生,而不是保持其自足自在状态。也就是说,“不规范文化”的提出虽然是以“规范文化”的“他者”而存在,但其最终还是想以“他者”的身份进入到规范文化中去。这其实也就是有研究者所说的“文学寻根”“看似反拨的顺应”⑤之义了:其是以“拒绝合唱”(李锐)的姿态,最后成了“合唱”之一部分。
当文学寻根小说出现时,有评论家纷纷表示担忧,如果寻根最终只是寻到深山老林,乃至永远长不大的畸形儿“丙崽”,那这样的寻根,其意义何在?⑥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意义,但其实是误解了寻根作家的初衷。而实际上,这也恰恰表现出寻根作家对传统的爱恨交织之情。他们深知传统并不一定可爱,其很大程度上是指“规范文化”,但如果不进入传统显然也不能真正进入到秩序中去,所以他们提出了“不规范文化”这一歧义丛生的范畴。这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策略和选择。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韩少功所谓的“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这一命题提出的内涵之所在了。在他这里,传统文化虽然包括两部分,但其实指向的是规范文化,而非不规范文化,因为据他看来,既然“不规范文化”处于边缘地带,富有活力,且“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自然就不存在所谓再生不再生的问题了,因此,他所谓的“再生”其实指的是“规范文化”,而这一文化的“再生”,某种程度上只能仰仗于“不规范文化”。
因此,对于寻根作家而言,其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作为边缘地带的“不规范文化”,如何才能进入“规范文化”并使之再生?郑万隆在《我的根》一文的开头这样写道:“我出生在那地方——黑龙江边上,大山的褶皱里,一个汉族淘金者和鄂伦春猎人杂居的山村。它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边境,国与国相交接的极限……正因为如此那里失却和中国文化中心的交流,而又不断发生战争;也正因如此,那里到处充满了荒蛮,充满了恐惧、角逐和机会。也可能就是这些令人神往和震颤的机会,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开拓者……因此,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温暖的,充满欲望和人情,也充满了生机和憧憬。”从郑万隆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一“不规范文化”形态,同规范文化相比,显然表明约束的不足,正是这种不足,也就使得这种“不规范文化”形态格外地自由而充满活力和野性。其虽“荒蛮”而令人“恐惧”,但无疑富有“力”的表现而洋溢着青春气息,永不会衰老。按照这一逻辑,不规范文化其实就是一种青春文化形态;而若联系寻根倡导者对“规范文化”的分析,便可看出,“规范文化”在他们眼里其实已形同迟暮,“地道的、正宗的中国文学,到了晚晴就算断流了。……如同两千年的帝制命该由清人送终一样,正宗的中国文学(确切说是汉民族的士大夫文学)到了那个时代,已是气数尽了。”“对于被我称为‘规范’的那部分传统文化,大体上我是不恭敬的。”⑦正是这一活力和暮气、青春形态和老年形态的区别,“不规范文化”相对于“规范文化”的意义被充分显示出来。而若如郑万隆所说,人类的行为模式在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话,人类显然是在文化中参与了对自身作为“人的本质”的塑造⑧。这样看来,表现“不规范文化”,其实就是表现了“人的本质”和对“人”的重新塑造。这一“人”的形象,显然是与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不同的,这一“人”的形象,既非社会主义新人,也非传统之子,而毋宁说表现出某种混杂性。如果说伤痕、反思和改革写作表现的是对“人”的形象在八十年代的重建的话,那么寻根写作则是对这一“人”的形象的再次重建,对于这一“人”的形象重建,既要注意到创作者的身份,我们还要看到其与知青写作的内在关联。
二、文化之“子”与青春赋形
李庆西曾在一篇分析韩少功小说的文章中谈到“我们建国以来的文学作品多强调人的外在的社会关系,比较忽略对人的本体的思考,缺少对人格的哲学思辨。韩少功的‘寻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寻找自我,寻找人的哲学。在舍弃了个体意识的前提下,发现了群体意识,就象《归去来》中的主人公那样,丢失了‘自我’以后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自我’。”⑨这段话其实可以用来概括知青一代寻根作家。因为实际的情况是,现实生活中,知青一代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回到城市,发现城市早已不再属于他们,陌生而又疏离,即使投入进去,也常常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表现在文学中,亦是如此。他们倾诉“伤痕”,并不能获得应有的同情和谅解,如卢新华的《伤痕》;他们投身改革和四化,虽万般努力,总遭遇怀疑和质询的眼光,柯云路的“京都三部曲”和郑万隆的《当代青年三部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他们的笔下,虽然表现的是主人公真实而具体的个人生活,但其实往往有意无意在代一代人说话和思考,其间关于个人身份焦虑的表征十分明显,因为显然,对他们而言,没有群体——一代人的位置,就不可能有自我的位置。而到了寻根写作,这种焦虑则不多见,其虽也有感伤和悲壮,甚至无奈和无助,但这种感伤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的,不是关于“自我”,而是关乎群体——民族的,因而也就没有了那种浮躁和凌厉,倒更显得气定神闲。这同知青写作截然不同。知青写作从个人经历入手,探求群体的命运,最后却发现,仅仅从现实中是很难找到集体乃至个人的位置;而寻根写作从更大的群体——民族的表现入手,在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最后也就有了集体——一代人的位置。
在这里,关键是对“人”的理解。首先,寻根作家笔下的“人”并不仅仅是个体之“人”,其首先是文化的象征,是文化塑造了“人”,因此,与其说寻根作家是在塑造“人”的形象,不如说他们是通过“人”的行止来表现或展现文化。这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截然不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其最为中心的任务之一是塑造人的形象,故而讲究情节,其情节也更多是围绕人物的塑造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但到了寻根写作,人则成了符号,文化成为他们表现的核心。李庆西在分析《爸爸爸》时,从“崭新走向”的角度预言道“跟以往的叙事作品不同,这部小说所揭示或者表现的不是某种个人命运。在情势发展中,个人的行动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不仅是情节淡化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叙事原则的改变。”⑩在这里,“情节淡化”显然是为文化的出场服务的,文化成了表现的中心。故而其次,对于寻根写作而言,对“人”的理解,往往就取决于对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说,小说对文化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实际上,寻根写作中,对文化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也决定了寻根小说中人的形象的复杂性。这也是我们对像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形象,《女女女》中的幺姑形象、王安忆的《小鲍庄》中文化子形象的难以分析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些人物形象,我们很难以一句话简单地概括,其既不能用好或坏的价值判断来衡量,也不能以立体或单调的性格特征来绳之,自然就不存在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这一问题的产生了。因此,李庆西在分析《爸爸爸》时才会把丙崽视为“人生的象征”。在寻根小说中,人物首先是作为象征和符号存在的,这是一方面,但反过来,这一象征内,对“人”的理解,并非没有现实的针对性,这也是我们今天分析寻根写作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寻根写作虽然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其核心诉求,但并不代表人物形象就没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对于寻根文学而言,透过人物形象可以更好地看到作家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如果说,寻根作家们在他们的寻根主张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比较鲜明而直接的话,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文化则表现出某种复义性来。这一复杂性在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中有最为形象的表征。这一方面可以看成是意图和效果的差异,其实又不尽然。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女女女》可谓是这样的典型。前者中的丙崽形象自作品发表以来不知引来多少侧目也一再让批评家绞尽脑汁而不知所措。这一形象的难解和晦涩,甚至在作品发表后二十多年作者还在为之辩护:“其实我把自然和历史都写得很美,也写了山民们在愚昧、贫困、暴力之下的团队精神和牺牲精神,甚至写得有点悲壮。批评家李庆西所这里有一种‘崇高’,但大多数读者看不到这一层。”[11]其实,作者大可不必这样辩护,这样一来反倒使作者陷入了“文明和愚昧的冲突”(季红真)这一当时的意识形态陷阱,因为当说“悲壮”或“美”与“不美”,以及“愚昧”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认同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观念。而实际上在小说中,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而分明。至少这种暧昧在丙崽这一形象上是如此。丙崽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很难说就是传统的象征,因为在他那里只会说那么简单的几个词,他很弱智,但同时他又极富生命力。诚然,丙崽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性,就连作者本人都不会反对,但这一象征并不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毋宁说有其他的含义。
韩少功在谈到这部小说时曾强调“《爸爸爸》有一个特点:时空特点没有。……模糊时空的目的,是引导读者面对一些超时代和超地域的普遍性难题。”[12]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小说背景设计中时空的模糊上,其实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丙崽形象的生理特征上:他永远也长不大,其既显年轻,但实际上已然很老,换言之,岁月和年龄在他身上是不起作用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再来看他的怪异和弱智之处可能就清晰得多了。在他嘴边永远就那么几句“爸爸”或“xx妈妈”。他不断地喊“爸爸”,而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无父之人(父亲的身份始终暧昧不明),可见,这一“爸爸”的喊声背后,其实显示出某种无父的内在焦虑。他不会说话,但并不表示他就不懂,很多时候他也会愤怒和哭泣,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因而只能出之以“爸爸”等名,这正表明他不能真正进入理性的正常人所代表的象征秩序,而这种不能进入恰好是因为他无父,没有父亲的引导。他是一个无名之人,既无父亲,也无自身,因而只能在想象世界中永远的徘徊。他不能形成关于自我主体的想象,哪怕就像在镜子中看见另一个自己那样短暂的时刻也没有,对他来说也就不会有时间的年幼和老态了,故而在他就只有想象的无意识世界的涌动。这是一个等待被命名被引导被规讯的混沌的状态,正因为生父的缺席,所以使得丙崽永远处于一种无名而又生命蓬勃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其实写的就是丙崽寻找父亲、混沌等待进入秩序的过程。直到最后,那场决定寨子生死存亡的“战争”和劫难,创造了机会,这场战争就像凤凰的涅槃,裁缝最后那句以父亲之名的询唤:“吾就是你爸,你跟我走”最终完成了丙崽的寻父之路,因而这时他的喝完毒药后奇迹般的活过来了是否意味着死后重生?他的留下或被遗弃,是否表明从边缘进入秩序的象征?因为此时,“外来者”已经完全进入鸡头寨。而这是否就是韩少功自己所谓的“规范文化”借助“不规范文化”得以完成的重生?
如果说,对于寻根写作而言,其最为关心的是“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的话,韩少功的丙崽的形象,恰好象征地提供了“现代再生”的原型,即涅槃式的重生,以及从边缘进入到秩序中去的传统。传统——不论是“规范文化”还是“不规范文化”——已如暮年,但传统的野性和价值还在,因而只有经历涅槃才能获得重生。
虽然,寻根作家笔下的世界大都是边远地区,这些地区也表现出模糊时空的倾向,但实际上现代文明已慢慢浸入,“最后一个”不可避免地将会来临。实际上,在寻根写作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始终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矛盾,虽然对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寻根作家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这是寻根写作中最为纠结和难解的问题,但如果从“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这一角度去看,其实问题相对要简单得多。换言之,虽然传统和现代之间表面上不可调和,但其实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或水火不容,而毋宁说有某种内在的统一,这种统一就表现在“再生”这一诉求,及其承担的连结传统和现代的功能上。而也正是这一缠绕,使得小说中人物构成表现出极其复杂之处。韩少功曾这样明确无误地表明:“从一九八五年以来……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与所谓传统一刀两断”,“事情只能是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传统’与‘现代’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互相渗透互相缠绕的关系……任何历史都是现在时的,任何‘传统’事实上都不可能恢复而只能再生”[13]。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韩少功笔下的丙崽和幺姑的形象之意义了。我们很难说这两个形象代表传统或现代,而只能说表现出某种混杂性。他们都经历了“死亡——重生”,一个是死而复生(丙崽),一个是老而返童(幺姑)。
这种复杂处可以从小说中青年老年形象的形塑上看出。这一最为典型的就是丙崽这一老小人形象,以及《女女女》中幺姑的晚年奇怪的返童现象。这与此前的伤痕写作、反思写作以及知青写作中明显不同。即使是像王滋润的《鲁班的子孙》那样表现传统和现代的复杂关系的改革写作,也与其不尽相同。在寻根写作中,青年和老年之间那种隐然或显然的对立,及其紧张关系,已然不存,而代之以两类形象之间的时间承继关系。其最为典型的就是被韩少功作为寻根作家例举的乌热尔图的草原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特别是在《七叉犄角的公鹿》这篇小说中,表面看来,青年(少年)“我”同继父之间关系紧张,继父经常打骂“我”,“我”对他更是充满仇恨,但这种仇恨其实都是源于对鄂温克男子汉的诉求上:继父虽凶悍,但有力而强壮,是一个好猎手,因而能获得人们的尊重;而“我”年龄尚幼,不被尊重也就再正常不过了。于是小说中就有了“我”对力量和坚韧品质的追求,“我”为了证明自己的鄂温克男子汉气概,就必须表现出强悍的一面,必须是一个好猎手,再无他途。而一旦最后“我”达到目的了,“我”和继父之间也就和解了:“我被背在他宽阔的脊背上。……一道透过乌云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把脸紧紧地贴在特吉(即继父——引注)的肩上。”
在这里,少年(或青年)同中年(或老年)之间的对立是力量和经验的对立。也就是说是经验区分了少年和老年,老年有经验,少年经验不足,因此少年要向老年学习。而一旦又有经验,又有力量和胆识,不论大小,都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这是传统社会的特点,在本雅明那里有极为精彩的分析。……李杭育的《葛川江上人家》中的大黑,《珊瑚沙的弄潮儿》中的老头,《船长》中的船长,等等都是这样的形象。但问题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这一依靠经验的区分,越来越显示出无效的一面,李杭育的《沙灶遗风》和《最后一个渔佬儿》就是这样的典型。老头耀鑫(《沙灶遗风》)的造屋手艺,终于敌不过造洋楼的现代建筑技术,以至于连他的儿子也公然背叛了。福奎虽然是好样的“渔佬儿”,但河里因污染已无多少鱼儿可捕,空有一身经验和不服老的气概也是白费。现代文明的入侵,无疑已造成经验的萎缩,这种萎缩一方面带有了波德莱尔式的对新的经验的表达,同时也带来对旧有经验的回忆和感伤。前面提到的两篇就是这样的小说,但这也只能是怀旧,就像《珊瑚沙的弄潮儿》中的康达,其虽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并再一次体验弄潮儿的冒险,但这时,康达显然早已不再是小时候的“赤卵将军”,他是作为现代文明之子登场的。
如果说,在伤痕写作及反思写作中,青年和老年之间是造反派和被打倒派之间的对立,改革写作中青年和老年之间表现的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对立,那么在寻根写作中,青年和老年之间的关系无疑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或现代之间的关系,而毋宁说表现出经验和体验的对立。这种复杂关系最为鲜明而集中的体现在“最后一个”的表现上。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就是这样的代表。《最后一个渔佬儿》、《船长》、《珊瑚沙的弄潮儿》和《沙灶遗风》都是这样的小说。但其实,事情往往是辨证的。“最后一个”,其实也可以变成“最先一个”,这在郑义的《老井》中表现出来。在小说中,“最后一个”无疑是作为传统的代表出现。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传统无疑表现出危机,这“最后一个”必然出现,但既然是“最后一个”其实也意味着顽强坚忍和毅力,如果并不拒绝现代文明,而是迎接并正视,反倒能成为新的契机,从这个角度看,《老井》中男主人公孙旺泉既是传统最优秀的子孙,也是现代最杰出的代表。显然,在小说中,如果主人公抱残守缺,死守传统的方法,拒绝现代科学——打井科学知识,老井村就永远也打不出出水的好井。小说正是把他当成那种既传统而又现代的代表来写的,他是英雄小龙再世,正是这一遗传基因,并结合他不懈地钻研现代科学技术,他才打出了老井村第一口科学井;他有责任感,这既是作为孙子、丈夫和父亲应负的责任,也是面对乡民应有的承担,这是历史赋予他的,他没有退缩。所以他才没有为了同巧英之间刻苦铭心的爱情,而抛弃妻子,远走他乡。郑义在谈到《老井》时,也这样说:“赵巧英、孙旺泉有点象征意味。……男主人公本是英雄小龙再世,自带几分神气儿。但积历史、道德、家庭、个性的包袱于一身,渐渐,竟由人变作一口井,一块嵌死于井壁的石。”[14]应该说,这种象征意味在寻根写作中普遍存在。而这种象征色彩又大多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并表现为一种传统和现代交汇下的排斥、颉颃乃至吸引和融合。从这点来看,寻根写作中的主人公其实大多都是某一文化符号,并不具有典型的性格特征。而既然是一种符号,其实也意味着某种意图,表明了作者针对现实的不同态度。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寻根写作都表现出这种超越时空的倾向。除了像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以及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之外,像阿城的《三王》以及《遍地风流》,以及韩少功的很大部分寻根小说如《诱惑》、《女女女》、《归去来》、《空城》、郑义的《远村》、《老井》等,则显然是有具体的时空所指的。其实,这两种时空取向,是可以对照着读的。也就是说,在那些超越时空的写作中,虽然虚构出一个模糊时空的自足的世界,但这世界其实是在作者叙述者之眼的关照下显示出来的,这一世界并不真正自足,而只是作为“远景”被无限地前移。相反,那些有具体时空所指的小说,它们虽然作为“近景”展现在作者笔下,甚至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参与其中,但其实也是把具体时空推向深处作为背景出现。典型地就是韩少功的《诱惑》、《空城》和郑义的《老井》。在《诱惑》和《空城》中虽然都写到指涉具体时空的知青形象,但其实是把知青作为“他者”式的存在以凸显乡土之奇和美的;而《老井》中老井这一具体的乡土意象,就像作者所坦言的那样,其实带有很强烈的象征色彩,正是这种象征色调反把具体时空之实给过滤掉了。换言之,在那些涉及到具体时空的寻根写作中,现代文明的进入,或侵入了传统秩序,或发现了传统秩序之美,但不论如何,现实社会及其现代之子往往是作为传统抽象秩序的“他者”出现,其根基还是在传统。从这里可以看出,具体时空不论是作为远景,还是作为背景出现,其实都是指向现代社会或现实社会,而这种具体时空的缺席或不明,也即表明小说远离具体现实或现代社会的意图。而也正是在这种模糊时空的倾向中,小说主人公也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象征意味。
这种超越或模糊时空的倾向,其实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回到人类童年的倾向。这是一种富有青春形态的人类童年,或青年时期。“童年,是个人的童稚时期的一段生活,也是一个民族、甚至人类的童年的、原始阶段的状态。在‘寻根’的一些作家看来,人类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失落了某种东西,造成了各种因素,如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本质和表象、经验和超验之间的普遍分裂,他们认为,在原初的阶段,这些本来是同一而不可分的。”[15]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入侵,及其表现出暮气和活力的并存。有研究者在读到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时已敏锐注意到这点:“一些表面上看来极不相称,甚至于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不仅在他作品中经常出现,而且也正是这种对立面相互排斥的共存刺激了作者的创作想象力。土地与神、原始的渔佬儿面对工业污染,传统的画屋师爹面对兴起的二层洋楼。弄潮的和观潮的,地道的船老大雇佣年青画家……事实上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我们这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集中反映,作者善于让过去与现在进行有趣的,有意义的对话,让读者从中强烈地感到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工业发展对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冲击,当今世故与古老人情的矛盾和冲突,贫穷如何使某些习俗得以存在,富裕又如何使某些习俗得以兴起”[16]。在寻根作家笔下,自然很少是秀美而柔媚的,相反大多表现为一种粗犷而充满力度的美。这是与童年形态相适应的,表现在小说中是原始自然的魅力,例如葛川江的“粗犷、豪放、硬朗且浑脱”以及“野性”(程德培)。这时,这些自然还往往不具备“风景”的现代含义,因为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人和自然是合为一体的。而一旦外来者或“他者”的出现,比如说画家、游客、流浪汉,或者现代秩序,随着他们的进入,“风景”随之产生,人和自然的距离随之产生,于是有了“观潮的”或旁观者出现,自然中人也被作为一种被凝视的对象出现。
三、“风景”的发现与主体建构:知青如何寻根?
其实,对于生活在自然之中的人们而言,是无所谓“风景”的,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之中,他们是自然的人,他们和自然融为一体。对于“风景”而言,必须要有距离。韩少功的《诱惑》的开头中有一段这样的描绘:
总是在雨后,这一钩银光就出现于苍翠远景。雨越大,它就越显眼地晶莹灿烂,然后一天天黯淡下去。
那时候,我们在马子溪洗尽一层汗盐,哆哆嗦嗦爬上岸,甩去耳朵里暖和的水珠,常常愿望着这道大瀑布,猜测大概不曾有人到那上面去过。
当夜色落下来,它自然熄灭了。而白日里远近相叠的峰岭,此时拼连融合成一个平面的黑暗,一个仰卧女子的巨大剪影。这女子一动不动,想必是累了,想必是睡了,想必是在梦想往事。她的头发太长太多,波浪形地向北舒摆开去,每夜都让星光来晒着,让山风来抚着——等待朝霞来再一次把她肢解。
那时候,我们的自由部落就建立在这里。大家常去山下的寨子里挑粮,听农民说些话。他们说马子溪是从这羞女峰的什么地方流出的,女子们喝了,会长得标致,而且将来多子多福。他们是瑶民,或者苗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他们黑洞洞的门槛里,地面坑坑洼洼,有嗡嗡的蚊蝇和朽木的酸味。
在农村,关于这种传说很多。传说的出现,正是在于所传之物的神秘,以及人们对之寄予的美好的想象。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关于羞女峰的传说其实反映的是山民们美好的愿望,至于羞女峰本身的自然之美,他们是并不在意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得意而忘“言”——事物本身。但对“我们”而言,羞女峰则无疑是一道“风景”的存在了。那“苍翠远景”和“晶莹灿烂”“常常”勾起“我们”的想象。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对乡民而言,这羞女峰并不成其为“风景”,而对于知青的“我们”却常常是一种“诱惑”呢?
显然,答案不在于羞女峰本身,而在于观看这羞女峰的人,也即乡民和“我们”。更进一步说,这羞女峰之成为一具有“诱惑”的“风景”之存在,关键在于“我们”的存在,而不在于乡民。对乡民而言,他们想到的是有用,即功利性——“多子多福”,对于“我们”来说,这羞女峰则成了驰骋想象的对象,“我们”在其中看到的并非有用而是“晶莹灿烂”是美。可见,“风景”的诞生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审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风景”作为美被发现。柄谷行人指出:“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为了风景的出现,必须改变所谓知觉的形态,为此,需要某种反转。”“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之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7]。这里的“风景”,虽然作为一种“认识装置”,其实同样适用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风景名胜”的发现。羞女峰之所以能成为“风景”,显然还在于某种距离的存在,这一距离并非可以用数字测量的物理距离,而是一种心理距离,也即精神上的对自然物的观照,是主体投入其中的感情的外化,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客体的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18]。在这过程中,是主体赋予了客体以“合目的性”也即“美”。换言之,对于生活在自然中的人而言,“风景”的被发现,显然是有“外来者”的出现才有可能的,而对于发现“风景”的人而言,“风景”的产生,其实也就是“主体”的生成了。可见,对于“风景”之发现的过程,其实也即“他者”变为“我者”或“主体”的过程了。从这个角度看,“寻根”的提出,也是一种“风景”之发现的过程。因为对于自然中生活的乡民而言,穷乡僻壤是不可能有“根”或“美”的,是“外来者”的出现,以及距离的凸显,才有“根”被提出。“寻根文学”的产生,也即审美的过程和结果,其结果生产的是叙述者——即知青——的主体性。
卢卡奇曾把世界区分为“生活的世界”(the worlds of life)和“本质的世界”(the worlds of essence):“本质的世界因形式的力量而高踞于存在之上(exisentence),这个世界的特性和内容都由那种形式力量的内在可能性所决定。生活的世界,如它们所是,形式只是接受并塑造它们,并把它们带到它们的先天(inborn)的意义上。”[19]在卢卡奇这里,虽然“生活的世界”和“本质的世界”分属不同的阶段,但其实可以从共时性的角度来分析:它们其实可以看成共时和历时性的结合。这种区分可以用来分析寻根写作中的“风景”和“自然”。“生活的世界”和“本质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恰好对应着“自然”和“风景”。对于“自然”而言,形式和它们的意义是融合为一体,不能两分的,也就是说,在自然中形式和意义之间没有距离,但对于“风景”来说,形式则是外在于存在的(这个存在(exisentence)一定意义上即“自然”),它们之间有某种距离,“风景”不是由存在,而是由那形式的力量所决定。这一力量显然来自于某一距离的存在,然后才有可能。卢卡奇把这种形式的力量称之为“赋形”(form-giving)。对于“自然”来说,它是自我赋形的,而对于“风景”来说,则是他者赋形的。从这个角度看,寻根写作,其实就是一种“他者”“赋形”的尝试和努力。
这一“他者赋形”的努力,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叙述者超越时代政治的倾向上。换言之,也即叙述者有意保持与时代政治的距离。在寻根小说中,虽然大都描写边缘地带的故事,也曾表现出模糊时空的取向,但时代政治始终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而存在的。最为典型的即乌热尔图的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这部作品集,一共20篇小说,开头数篇都表现出模糊时空的倾向,而到了第10篇《鹿,我的小白鹿啊》开始,小说中不时出现了“山下”的“学习班”或“群众专政指挥部”的字样。在这些小说中,“山上”和“山下”显然形成对比,“山下”混乱不堪,让人气闷和窒息,而“山上”则自古依然,让人心情舒畅,充满活力和朝气。后十一部小说中很明显,山下的世界已然侵入山上,往日的宁静和谐的山上世界,逐渐变得难以为继而焦躁不安。这时,如果从后面十一部小说返观前面的9部小说,我们发现,这些小说虽然都表现出对美好的山上世界的寄望,但这些世界其实已经是残存的孤岛式存在,其越是美好,越让人充满感伤和留恋。在这里,山上世界之“美”正在于其距离政治之“远”所致。
实际上,这种“他者赋形”,还表现为一种返回的意向。叙述者返回或返身故土,在故土中发现一直潜藏着的美来,而这美恰恰是叙述者在都市中所缺失或遗失了的。李杭育的《珊瑚沙的弄潮儿》和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是其代表。前者中,表现为小说主人公康达中年以后的返/恋乡。当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家,见到久别的生母时,小说这样写道“葛川江却一下子挑逗起他的情来,虽说二十年间它也象他的老娘一样变得有点陌生。……在这儿,在家乡的这条对他来说如同初恋时的女伴一样的江山,实实在在地寄托着他童年的无数个梦幻,象满汪汪的一江春水,经不得一阵风吹便要漾开来了。”在这里,都市和故土,中年和童年,衰竭和活力,理性和感性,等等构成隐然地对立,其间的价值判断十分显然。是作者回到故土,一下子记起童年时的荣耀和“抢潮头”的勇猛劲,而这些在多年的城市生活中无疑已经磨练得几无。这里有一段十分具有象征性。
从前百姓是不配在此观潮的。不过从前的百姓也没这分雅兴。他们更乐于弄潮。观潮须有闲,不愁温饱,而下滩弄潮,每日两回潮头上玩命,捡几条鱼,换几升米或几尺布,却是那些职业弄潮儿唯一的谋生之道。在他们眼里,如狼似虎的大潮呼啸扑来,在江堤上撞起冲天的水柱,这光景只有凶险,一点都不有趣。
……
现在的人性命宝贵,日子也过得富绰,所以葛川江两岸的弄潮儿越来越少,而观潮游客逐年增多。弄潮儿上岸观潮了,好比打猎的参观动物园。(第84页,李杭育:《最后一个鱼佬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观潮”其实就是把大潮当做“风景”来看,而弄潮则是身处其中,是在自然的狂暴中搏击。这段描述很像康德对“崇高”的分析。显然,对于弄潮儿,潮头是一点美感都没有的(“一点都不有趣”),因为他们面对潮头大浪,并不能保持有效的安全距离,而对于观潮者来说,他们距离潮头较远,因而既能感受到潮头的伟大又能不被潮头裹挟。观潮之所以是美(崇高是其一种)正在于这种距离,这一距离主要还是那些“游客”带来的,他们作为“外来者”,感受到这美。但美并不一定就是寻根作家理解中的文学之“根”,因为“观潮游客”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他们身处这一世界之外,他们并不能发现其中潜藏的“根”基所在。而对康达来说,则不同;康达既是作为“外来者”,他也是“弄潮儿”。他从小在此长大,因此,这是童年的世界,是他曾经拥有的世界,只不过长大以后走向城市,逐渐遗失了,因此,他返回故土,就带有重拾记忆和旧日之“根”的味道。这里一个很反讽的细节是,但当他重回潮头抢滩时,他蓦然发现,他原来已经成为了被观的对象了。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寻根,虽说是审美的过程,但只有对那些身处其中的“外来者”而言,才可能发现“根”之所在。这种返回的意向,还表现在题材的转移上。这在郑万隆那里表现十分明显。在写作“异乡异闻系列”之前,郑万隆写作了像《当代青年三部曲》(1980年、1981年、1983年)《同龄人》(1981年)等表现知识青年的题材小说,但到了1984年下半年起,作者陆续推出了像《反光》、《老马》、《老棒子酒馆》等一系列以“异乡异闻”:为总题的小说,这种转变之快在在让人惊异,但其实并非没有缘由。因为这些小说写的就是他的家乡黑龙江的故事:
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那里有母亲感叹的青春和石冢,父亲在那条踩白了的山路上写下了他冷峻的人生。我怀恋着那里的苍茫、荒凉与阴暗……但我并不是认真地写实。……我不是企图再现我曾经经验过的对象或事件,因为很多对我都没有也不可能经验过,而且现实主义并不等同再现。(《我的根》)
从作者这段夫子自道可以看出,题材上的重回,也并不是企图要去“再现”故乡的什么,或自己的童年经验,而实际上,在这些小说中,时空十分模糊,因此也几乎不见主人公形象中多少叙述者的影子。在这些小说中,所谓那种身处其中的“外来者”只是就叙述者或作者而言,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无关。这很像李陀曾说过的那样:“从我的民族来说,我也应该算作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作家。然而由于多年来远离故乡,远离达斡尔族的民族生活,我却未能为自己生身的民族,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事业做出一点点实际的事。这常常使我不安。我近来常常思念故乡,……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20]可见,寻根往往表现在创作主体上,而不是小说主人公身上。韩少功的《爸爸爸》也是这种类型。
这种寻根的主体,即表现为“熟悉的陌生人”。所谓既熟悉又陌生,是因为不熟悉就不知道其中之美,而若不陌生,又不能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发现这美。因而既要身处其中又要能出乎其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之所以“寻根”成为可能,还在于寻根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换言之,寻根虽属于,但并不仅仅止于审美。如果说审美在自然中发现的是“主观合目的性”,那么这一“主观合目的性”对于现实中审美的主体而言,并非自足而自适的,而毋宁说有其内在的焦虑。因为“寻根”的提出,即表明现实中主体性的缺失,因此所谓“寻根”,“寻”的就是文学的主体性之根。从这个意义上看,韩少功的《归去来》是一篇极有象征性的文本。对理解知青寻根十分具有症候性。
《归去来》中存在这样一个结构,即离开——归来——再度离开,这一略显简单明了的结构其实包含着两重互相矛盾的脉络:现实中的“黄冶先”无疑早已回到城市,历史中的“马眼镜”却永远地留在了下放过的农村。而之所以出现“黄冶先”和“马眼镜”这种同一个人两个名称之间的缠绕,一方面表明深陷现实和历史的纠缠中不能自拔的知青叙述,另一方面也表明知青一代身份认同的困境,即不论知青本人如何否定或遗忘曾经有过的知青岁月,知青记忆都会在不经意间流露,甚至以梦境的形式光顾并困扰着主人公,因而就常常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的现实身份,即“这世界上还有个叫黄冶先的人吗?而这个黄冶先就是我?”很难说这是一篇标准的寻根小说,但其无疑已标志着知青写作的困境和新的可能,即现实中的知青(“黄冶先”)早已离开农村,并且将永远离开,因为当“黄冶先”甚至开始相信自己就是“马眼镜”时,他还是选择了“潜逃”,但这并不妨碍这个叫着“黄冶先”的人精神上的返乡,他其实可以同时拥有两个不同的身份,现实中的身份和想象中或回忆中的身份,两者缺一不可,甚至这后一种身份对他们而言更为必要。
说《归去来》极富象征性,即在于这部小说一方面表明了现实中知青身份认同的焦虑,同时也表明了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求补偿的不可能。因为,在这部小说中,知青历史是以梦境或幻觉的形式出现的,而在现实中,就像“黄冶先”这一名称所表明地,他其实早已忘掉了知青岁月那一段历史,这样一来,即表明知青在现实处境中身份认同的“无根”状态:知青的现实身份没有历史感。换言之,这一现实身份认同是以否定过去那段知青岁月为前提的,这就是小说中的“黄冶先”不认识“马眼镜”的原因,因为“黄冶先”是现在之人,而马眼镜”是过去之人,而事实上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名称变了,因而他们的相遇或相交就只能在梦境或幻觉中以无意识的形式出现了。
四、结语
实际上,一个现实中的人,是不能没有历史的,对身份认同和主体的建构而言,尤其如此。阿甘本认为“现代人的根本矛盾恰恰在于他仍没有获得与历史观念相当的时间经验,因此被痛苦地分裂成两半,一半是作为难以捉摸的瞬间流动中的时间中的存在,另一半是作为人类起源的历史中的存在。……迷失在时间中的人无法拥有自己的历史本性。”[21]这种矛盾,对知青而言,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归去来》就是这样的一种象征性表达。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要么是批判和感伤,或者悔恨,要么就是从历史中剥离出抽象的浪漫主义,而实际上这一浪漫主义并不能很好的着陆,没有很好的附着。他们也很难在现实中获得应有的位置,就像梁晓声的《雪城》所显示出的,即使被命名或自我命名,总始终同社会之间处于某种游离状态,这一状态在八十年代一直存在,其在中期以前尤为明显。从这个意义上,“寻根”就成为他们寻找自身“历史本性”的一次文化/文学实践。这就有点像阿甘本所说的诺斯替教的时间观:“它拒绝过去,却又在典型的现在意义上珍重在过去被谴责为否定的东西”[22]他们越过历史,伸向历史的纵深处——传统那里。而这一文化传统实际上又并非没有附着,而是基于边缘地带,这就与知青的经验和他们的幼年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通过这一“寻根”,他们最终建构起现实中的他们和传统的联系,他们现实中的主体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声称自己是谁,而不需要怀疑“这世界上还有个叫黄冶先的人吗?而这个黄冶先就是我?”从这里可以看到,《归去来》其实已经预示着寻根文学的到来,因而可以看成是寻根文学的直接源头。
注释
①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第165—1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208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③参见《韩少功:历史中的识圆行方》,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第208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④《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韩少功:《在后台的后台》,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⑤王又平:《浪漫的叩问:兼论“寻根”小说》,《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第22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⑥即使是郭小冬这样有过“知青”出身的研究者,也这样认为:“这个口号提出之后,在实践上与解释上都发生了偏差”,“一些青年作家的所谓文化小说其实并无多少文化意蕴,而仅仅是一个似是文化的外壳,负载着作家本人贫乏得可以的文化知识。力求古些,怪些,原始些或者离奇些,粗蛮些,这是对寻根文学的误解。这些现象绝非是个别的。”(郭小冬:《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第327页,第328页,花城出版社,2005年).
⑦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⑧参见郑万隆:《我的根》,郑万隆:《生命的图腾·代后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⑨李庆西:《他在寻找什么?——关于韩少功的论文提纲》(1986年),《文学的当代性》,第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⑩《说<爸爸爸>》,《文学的当代性》,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