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一代人充满悖论的思考
2013-10-13山东张艳梅
/ 山东_张艳梅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韩少功之思想与艺术原创能力皆堪称一流。
自新时期寻根文学肇始,至《马桥词典》甚嚣尘上,韩少功制造了不少文学史热点。文坛其实从来不甘寂寞,总有一些热闹纷纷扰扰,娱乐大众,不过,真正称得上文学史热点,而非文坛闹剧者,其实并不多见。韩少功以其严肃的文学观,及独树一帜的文学写作,获得了应有的文学史地位,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尊重。当代作家自命学贯中西者大约不乏其人,确如钱锺书、梁实秋等现代作家之文化修养者寥寥无几。若论综合素质,韩少功毫无疑问算得上最为全面,其在小说、散文、评论、翻译诸领域,成就皆有目共睹。
韩少功于1985年首倡“寻根文学”,《文学的根》成为寻根文学旗帜。文中指出: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这一时期代表作是《爸爸爸》,表现出对文化的审慎思考,在文坛产生重大影响。小说中的丙崽形象亦随之深入人心。1990年代中期,《马桥词典》因其独特的形式引发众多话题,甚至带来一场诉讼。如今尘埃落去,清者自清。其实在韩少功那里,文学,一向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小说家,无论最不像小说的《马桥词典》,或是众人所言最像小说的长篇新作《日夜书》,皆包含着太多学理性因素。虽不能说先入为主,但也绝不会淹没于文本中滔滔话语之河,而试图为那些支离破碎的故事,找到一个完整链条,似乎也不是韩少功本意。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埋藏在话语泡沫下面的历史河床,以及河床上生长着的葳蕤的生命杂草,腐烂的政治淤泥。
历史 现实 反思
以前写文章曾提及,历史观于作家尤显重要。盖因我们面对的历史往往并不清晰,作家又多半历史观暧昧,一方面是怀着向前看既往不咎的心态回避问题,一方面是对历史缺少居高望远明察秋毫的能力。韩少功最新长篇《日夜书》是一部知青题材小说,涉及对知青运动、“文革”和“八九事件”的评述。近年来,“文革”叙事依旧是写作热点之一。2013年另一部重要作品李浩《镜子里的父亲》,同样是讲述那段历史,李浩作为“70后”作家,与“50后”作家韩少功显然不同。两部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各有千秋,思想立场上亦多有差异。虽则否定“文革”是叙事基准点,但是二人反思历史的视角,清理历史的路径,面对历史的态度并不一致(这个值得专文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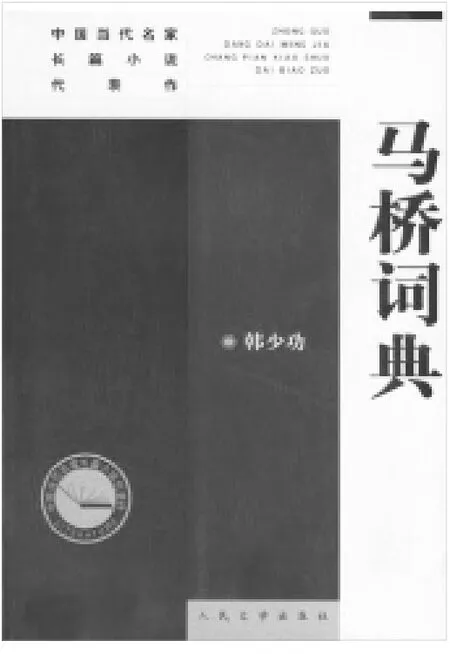
《马桥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日夜书》中的“日夜”,首先是时间概念;从生死角度看,也是哲学概念;当然,如果预设其为新旧时代表征,则亦不妨看作历史概念。日夜意味着时光流逝,意味着生死轮回,也意味着历史的两个侧面:有光的和黑暗的。那么,小说中写到的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哪一个才是作者种下的太阳树?哪一个才能开出太阳花?这世界没有天堂,连像样的乌托邦都没有,黑夜连着白夜,光,只有在梦中,在幻觉中,在臆想中,才会出现。那么,书写历史上的日日夜夜,生生死死,岂不是一如当年曹雪芹之浩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于是,经由日夜,言及乡愁。陶小布官场上去意彷徨的精神乡愁,姚大甲反艺术隐含的文化乡愁,甚至在马涛那里是客居异国的政治乡愁。这一切,在韩少功笔下,并不清晰,历史获得了某种解放,尽管人物都按照作者的安排向前走,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还是在细碎的生活和思辨中,读到了历史的多副面孔。一代年轻人在白马湖茶场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超负荷地劳动,没有什么理想主义的高歌。白马湖,包括北大荒、西双版纳,所有那些遥远的边地,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是故乡,还是他乡?

《爸爸爸》,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小说中有几处细节,令人过目难忘。关于饥饿。陶小布为了五十张饭票,吞噬从地下挖出的死人骸骨。一情一景惊心动魄。关于批斗。姚大甲旧报纸擦画笔,污了毛主席像,新来的杨场长要把他吊起来,小安子以杨场长用带有毛主席像的脸盆洗脚相挟,解救了姚大甲,杨场长却自此落下毛病,每每深夜惨叫。这一段拉长了视线,有点幸灾乐祸的语调,而深夜里狼嚎般的凄厉惨叫,是那个时代的恐怖回声吧。这一笔,同样有千钧之力。还有关于孤独。小说中写到陶小布的幻觉,移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一点也居然和李浩《镜子里的父亲》异曲同工)。在水家坡守秋的那些日子,爱与委屈相伴,个人孤独在庞大自然中,无限放大,而又壮怀激烈般向内在世界回溯。马楠的孤独似乎更具体,蛮不讲理的二姐,逼着她深夜一个人穿越大半个城市去换下铺车票。马楠母亲的孤独是无言的,落在马楠背上,无比沉重而又荒凉。还有关于回忆。回忆里包含着对往事的态度,没有沉湎,也没有控诉。大年初四的知青聚会,以无人付饭费尴尬谢幕。抱怨是相互温暖,谎言是自己镇痛。还有一段,是陶小布试图弄伤自己争取回城。那两根夹在门板之间的手指,直指历史的荒谬和时代的残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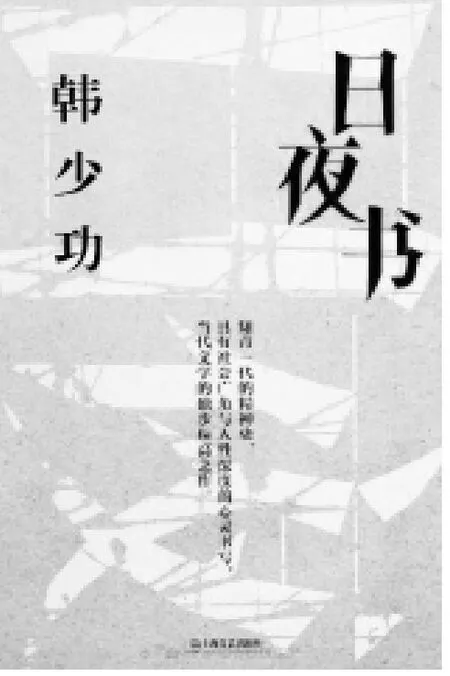
《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小说写到了“文革”武斗,写到了“八九事件”,甚至写到了马共的秘密电台,也写了这一切与当下现实的内在关联。历史,从来都没有过去,这不仅仅是克罗齐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涵盖的,我们今天面对的一切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如何去面对,有多少人清楚?《日夜书》一个维度是历史,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知青时代的白马湖,一个是后知青时代的都市和美国。知青返城的经过,非常惨烈,不是都能幸运地上大学和招工。回城之后,也不是都很幸运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功成名就。常有人说,如今是知青一代管理中国,其实,成功的知青背后,也许有无数当年一起青春热血过的失意人,流亡者、流浪汉,甚至流窜犯。后知青时代的身份差异,道路分化,命运处境,在这部小说中给出了全景图。并藉此为镜,反思现实。插叙陆副厅长那一段,是官场腐败。丹丹和笑月,因家庭破碎,无心读书,吸毒飙车,离家出走,也是教育失败。马家的兄妹关系,丹丹与郭又军的冲突,笑月对准陶小布的枪口,除却时代悲剧,亦是亲情伦理和个人生活的悲剧。
革命 消费 疾病
革命是历史深层的动力,消费是现实社会的标签。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活,到世俗化的民间生活,知青一代被历史与现实同时抛弃。作为被尘封的一段历史的主人公,知青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人可以借此向历史要挟什么,也不意味着知青群体本身对那段历史的完全否定。马涛曾经草拟党纲,试图改写历史,出国后所举新人文主义之旗,皆无助于重建社会秩序。负载着关于革命的记忆、书写历史的欲望,从“文化大革命”到文化消费主义,这一代人的精神失落,身份合法性的丧失,从被捕入狱,就已开始。对于马涛来说,政治,是其人生精神寄托的准宗教形式,而知青一代,其实是当代中国信仰破碎的开始。有意思的是,蔡海伦的女权主义,马楠的打砸抢的爱情犯,万哥的妄想狂和健忘症,马涛的冷血和多疑,在作者眼里,都属于准精神病。伊万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布罗茨基都是骗子;笑月说,陶小布和马涛都是骗子,自由道德科学艺术都不是人话。小说写到了革命和消费社会两个时代的断裂,以及内在的关联。那种精神上的幽灵,徘徊在两个时代之间,马涛忠于纯粹革命理念,姚大甲皈依消费社会;马涛心安理得地住进套房敷上高价面膜,姚大甲因裸成名得意忘形。作者对二人的否定和嘲讽,表明了对精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同时舍弃,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的双重批判立场,使得小说中的历史观不乏暧昧之处。
性爱 政治 死亡
知青时代那些夜晚,多少人独自在狂风暴雨中昏睡?后知青时代那些白天,多少人在高楼大厦之间失眠?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有时很远,有时很近。即使只是个人短暂的一生,仍有可能记录了沉重的历史。安然的母亲在结婚之夜,沉迷于性爱,窗外是枪炮轰响的武斗,一颗流弹打死了阳台上的儿子。这一细节包含着性爱、政治和死亡。陶小布与马楠结婚初夜,未完成性爱。韩少功在这里没有王小波以性爱对抗“文革”、解构政治的意图,却不期然接近了生命本体论思考。还有吴天保的满口脏话与姚大甲的裸体艺术。喜欢骂人的茶场场长吴天保,其语言暴力给姚大甲以艺术灵感。因为破坏计划生育丢了官。因为没有会可开醉酒而死。这个识字不多的人,喜欢在所有让他签字的申请或者账单上写下“同意报销”四个字。姚大甲的工作调动表,别人的入党申请书,县里关于病虫害防治的通知上,他都是写这四个字。甚至梁队长结婚的报告上,他依然写的是“同意报销”。吴天保的一生同样具备了潜在的性爱与政治维度。
那些走在命运和生活边缘的人
反体制的马涛:民间启蒙思想家,“文革”时代的红卫兵领袖,最终出国,从革命舞台退出。属于思想派。马涛曾是民办中学的高中生,有政治激情,有一定民众基础。是陶小布的启蒙者,陪伴他度过了最孤独的少年时代。“文革”期间曾提议建党,草拟过党纲。后来被捕。在狱中关了好多年。到底是谁告发了马涛,始终是个谜。出狱后,称自己是真正的“三反”分子。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分裂,满怀理想主义,却对亲人没有感情,似乎有过惊天动地的思想创造,却幼稚地与郭又军比跳水,受了重伤。阎小梅路边流血,他视而不见;家人为其求借无门,他抱怨不休;肖婷追随他飘零异国,他动辄怒骂;为了一件球星的衣服,迫使陶小布连夜驱车几百公里取回。这个冷血而幼稚的人,是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吗?韩少功在接受《时代周报》访谈时说起:“马涛的热情与顽强难能可贵,但他的自恋、偏执、空谈不实等确实构成了自己最大的障碍,也折射出某些社会病相和时代流习的深度制约。这在写作过程中一再使我感慨。他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问题人物之一,悲剧性的英雄之一。但问题显然不只这一个。姚大甲的嘻哈玩世,小安子的幻想症,郭又军的世俗沉沦……是不是也都值得反思?知识分子的身上经常流着小资血脉。小资擅长愿望与姿态,具有极大的文化能量,但拙于行动,拙于持久的、繁琐的、摸爬滚打和精雕细刻的务实性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小资被更多的焦虑所挤压,更多一些文化和精神的贫血症,因此更应该多一些自我反思。”这段话很有意思,如同马涛这个极端自我的新人文主义倡导者,由当年的红卫兵精神领袖,狂热的政治家,到出国后的受挫和转型,都很值得玩味。
体制内的陶小布: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最终主动退出政治舞台。如果说马涛属于广场上的演说者和布道者,陶小布则是庙堂上的实践者。陶小布当年本来不需要下乡,因为觉得孤单,渴望革命热潮,跟随郭又军去了白马湖。六年后,招工返城。上大学,副教授,科长,处长,终至厅长。曾是格瓦拉和甘地的崇拜者,也有过革命理想,不过没有马涛的彻底,在小说中,这是个颇有人文色彩和感情饱满的人物。得知郭又军自杀,车上恸哭的细节,也算是青春的哀悼了。陶小布是这部小说的主线,这个类似于鲁迅笔下魏连殳一样的孤独者,既是历史的叙述者,更是两代人命运的见证者。
技术派贺亦民:郭又军的弟弟,自学成才的典范。江湖上人称姐夫。一度在工厂和油城叱咤风云,被抓判刑,从经济大舞台黯然退场。贺亦民从小不学好,经常打架,被父亲打骂更是每天功课。有着孤独与耻辱的童年。没考上中学,离家出走,四处流浪,成了扒手头,后来到白马湖找郭又军,遇到陶小布,当了电工,推荐到技术大学学习。成了发明家。为哥哥打抱不平,打死城管外逃。这个神奇的科学家,把电工活搞成了艺术。
艺术派姚大甲:小说的叙事起点。大甲误为公用,作家顺便捎带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会画画的姚大甲,曾经是白马湖痛苦艰辛岁月的开心果。后来回城,进过剧团,办国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点投资煤矿,然后搞艺术展,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满脑子切割机和龙门吊,艺术,在他手里终于变成了一种技术。后来在国外受吴天保启发,办了个裸体画展,一夜暴得大名。算是把反艺术反智主义之路进行到底了。贺亦民和姚大甲,技术与艺术,互为镜像,仍旧是双重的时代反讽。
思想,人文,技术,艺术,无论选择何种人生,都没有出路。思想遭遇监狱和流放,人文遭遇腐败和清场,技术战胜不了城管,艺术因为无耻而成名。无论是反体制的渴望兼济天下者,还是试图进入体制的独善其身者,或者专注于技术的,有志于艺术的,都没有出路。韩少功对知青一代的命运解读,大抵上是悲观的。同时,小说中还写到了很多女性。有意味的是,这些女性同样大都是失败者。其中包括强势的小安子,阎小梅,二姐,蔡海伦;弱势的马楠,马母,肖婷;以及第二代的丹丹和笑月。这些女性基本属于阎小梅的那个空白边框,里面站着无数被时代和生活伤害的人。韩少功说:“作为一个写作人,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的性格、气质、情感、命运等等,如果一不小心遭遇到思想,我也会更注意思想的表情。比如一个刚愎自用的左派,不难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右派。所谓观念易改,本性难移。刚愎自用是比‘左’‘右’更让我困惑的东西,或者说是更让我揪心和入迷的人性指纹。我们现在还能记住李白、苏东坡是政治上的哪一派吗?还能记住托尔斯泰或马尔克斯在当年是‘左’还是‘右’?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大于政治,形象大于观念,好的文学作品对于一时一地的观念总是具有超越性。”“在这部小说里,我对同辈人有同情,有赞美,但也有反省和批评,包括写了一些可能让我们难堪的东西。”这些话算是辩解抑或自证吧。
韩少功的写作,无疑蕴含着中国文化更为深层的东西。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韩少功的授奖辞作为本文的结尾吧:韩少功的写作和返乡,既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件,也是文人理想的个体实践。他的乡居生活,不失生命的自得与素朴,而他的文字,却常常显露出警觉的表情。他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释放在广大的山野之间,并用一种简单的劳动美学,与重大的精神难题较量,为自我求证新的意义。他的文字,也因接通了活跃的感官而变得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