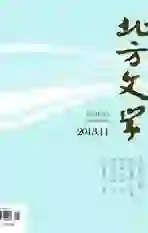南城根的根(外一篇)
2013-05-08王选
王选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身体上就会长出根须,慢慢,扎進了那片泥土。在南城根生活久了,亦是如此。
似乎没有人知道南城根的历史。一座城,豢养着一段残史,一方日月。总会有那么几个人记得。至于城外的风尘,是何等模样,就模糊了。是先有城墙,后有人,还是先安顿了人,再修的城墙,这么久远的事情,谁也理会不清,何况,理清了又能如何。多少年,南城根就这样在岁月的剥蚀中活着,像一株从尘埃深处长大的树。谁也不知道那枚种子,来自何方,又何时萌芽,如何成长的。只有风霜打磨过的枝干,长着一季又一季的春夏秋冬。
那些麦浪滔天的良田,早已不见了,那些瓦舍茅屋,还是不见了,甚至那些青瓦土房也跟着不见了。时间的手指,一层层剥掉了南城根打满补丁的衣衫,露出了现在水泥红砖堆砌的骨肉。一切都会过去,长在地皮上的事,都会被时间的手指掐掉,就连一阵漫不经心的风,都能让大地上的事情现出衰老的痕迹。那些在南城根出生的人,年轻时,反穿皮袄,蹲在城墙下,端一碗馓饭,把使不完的二劲在嘴皮上消磨了。他们没有改变什么,城墙还是高高在上,城墙垛子锯出了干硬藏蓝的天,只有墙根下,那坨被他们破皮袄蹭光的墙壁,平滑得粘不住一丝风。待他们老了,依旧反穿破袄,一溜子,瘫坐在城墙下,吸一锅自家种的旱烟,把松散的骨头摊开,让太阳烤烤,他们一辈子在城墙的阴影里活着,连骨缝里都有潮湿的霉味。就这样,一些人生下,一些人走南闯北,一些人在南城根卸下衰老,还有一些人死了。南城根从此在他们的记忆中,一同被埋入了北山的黄土里。
一切似乎就这么简单,一辈子也长不过城墙下的一根阳光。
于是这样想的时候,凡事都变得苍白了。然而南城根还活着,不紧不慢地活着,像一棵老榆树,把根扎进了这片泥土,那些逝去的人,犹如一枚枚叶子,终会落叶归根。那些枝头,春风一吹,又会吐出新叶,摇曳在黄土起伏的城墙下,如此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只要根不死,人就活着。
很多年以前,应该是遥远的连日光都泛黄的光阴里。藉河汤汤,蜿蜒东流,横川平铺着,田野肥沃。那些麦子、玉米、洋芋、胡麻、荞、荏,亲爱的粮食养活着这城外的人们,当天灾人祸袭来,这片养育着平凡子民的土地,没有遗弃他们,没有逼迫他们流亡、搬迁。他们也不想离开这里,虽然城墙坚硬地把他们拒在一边,但这里埋着祖先的骨殖,也飘荡着祖先的灵魂,这里还有肥沃的土地和善良的庄稼,这里也有鸡犬相闻邻里瓜葛,要走,是多么不容易的事。甚至他们轻轻的一动弹,就扯得脚底下的那些须根生疼。于是,那些年月,城墙下的人们依旧生儿育女,粮食、马匹、土地,便是他们沾着泥土的根。这条根,一直延续,像一脉血液,流淌着,流淌着,无论时光如何变幻,这血液里都有南城根的味道和温度。
后来,那些土地长出了高楼,那片河道也改造成了风景。牛羊弥散,庄稼远去,农耕时代的鞭子、镰刀收进了博物馆,唯有那些记忆,永远藏在自己的内心,到年老体衰时,就掏出来,慢慢咀嚼、静静回味。再后来,城墙拆了,岁月的风可以自由翻阅城里城外的身世了。没有城墙的日子,城下的人们,生活似乎亮堂了许多,城里的喧嚣和热闹也滚烫着,钻进了人们的耳朵,就连那些阳光,没有遮挡后,也把南城根多晒了半天。然而,日益筑起的高楼,再一次让这里披上了阴暗的衣衫。没有了生长粮食的土地,只有在老房子的基础上做文章了,盖起两层小楼,租出去,收一些租金。就这样,城外的人失去了对庄稼的依赖,用祖先留下的小小地盘,养活着妻子儿女。在这样的日子里,南城根的根,似乎浅了许多,一切都维系在八九间小房里,似乎任何动弹都会扯断。何况,日渐被水泥密封起来的土地上,一条根伸进去,回到那些泥土和水分的身体里,谈何容易。
可根浅了又能如何?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能靠祖先留下的微薄资产推天度日。南城根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像两手空空的小孩,唯有脚下的一片土地,和土地上盖起的小房子,他们就靠小房子的租金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打发这破旧的皱皱巴巴的日子。让他们进城上楼,是多么不现实,没有工作、没有技术,切断了房租就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所以,这片土地上,城堡一样的房子,成了他们的命根。
就这样在城市的一角窝着,没有多少欲望,更没有太多私心杂念。远去的时光没有人惦念,怀旧总让人伤心,连眼前这小光阴都过得并不如意,何必去遥想当年。就卷缩在现世的安稳里,一天天过吧,这里有熟悉的邻居,还有多年不曾走动、血缘稀疏的亲戚,这里的人都过着低调灰暗的日子,没有比较,更没有多少金钱和地位的悬殊,借着这份平衡,大家打个招呼、送把韭菜、打听一番东家的姑娘西家的儿子,相安无事地打发这流年似水。于是,所有人,在高楼林立的冰凉中,挤成一堆,互相取暖,像一群羊,羊毛贴着羊毛,心挨心。一天天过去了,就这样挤着挤着,一些暗藏的根须都伸进了彼此的骨肉里,谁跟谁,似乎无牵无挂,又似乎不可割裂。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就会扎下根。一群人,在一个地方繁衍生息,日子久了,就会长成一片森林。南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生了根,活在南城根的人,又在南城根扎下了根,如一棵老榆树和另一棵老榆树,根根盘错,生死相依。岁月的风沙吞噬着大地上的一切,包括一代代人,在南城根生下、长大、老掉、最后死了,然而岁月吞噬不了地下的事物,那些埋在黄土深处的根,永远活着,活成了大地的血脉。
一个人的南城根
海棠败了,丁香落了,蔷薇谢了,还有樱花、月季、玫瑰,一样样开到花事荼靡。就像有人,把她珍爱的精致瓷器,擦干净,摆了摆,又一件件收掉了。
接着,六月,芒种。石榴花,不紧不慢地开,像挑起的一团火焰。
南城根,看不到花,只有时间静静地流淌,如一架老钟表,指针上沾着灰,一步步迟钝地走着。向南,出南城根,藉河边,倒是栽满了名目繁多的花草,开了,败了,更替着,来来往往。住在南城根,看花,是没有意思的。不如找个午后,坐在27号院的二楼楼道上,看看风,看看辽远的日光,还有远处晾晒的衣裳。这样,多好。
泡一杯茶吧,就花茶,价钱便宜,味浓,放点枣和冰糖。搬个椅子,坐下。有本书也好,随便翻几页。迎面吹来淡蓝色的风,让人想起六月的乡下,开蓝色花朵的胡麻,闪烁着,卷起来波纹。风是温的,从四周的房顶挤过来。
抬起头,看天,天被切割成一口井,云是软的。阳光浓密,明亮的光线,从西边铺排过来,泼在对面的楼顶上,泛着微微的光芒。你不知道还有多久,光线会退干净,把黑夜交到你手里。天空还有鸽子,大约五六只,团在一起,飞着圈,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累不累,没有绑哨子,鸽子飞着是安静的,只有掠过头顶时,才会听到呼啸而过的声音。
南城根的天,像乡下,是蓝的,但又是狭窄拥挤的,没有让人要飞的错觉。
正对面,是一户人家的民房顶子。有铁丝绑成的晾衣绳,拴在焊于楼顶的钢管上。有长满碎花的米黄色被子,搭着,晾晒,沾满了阳光的味道。还有一条玫瑰红短裤,女式的,挂了两天了,没人取,风吹过,摆了摆,又摆了摆。是忘了?还是人不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租房的女子,这么粗心,想不来。
晾衣绳的钢管上,蹲了只麻雀,什么时候来的没看清楚,它歪头,用嘴梳了梳羽毛,又开始发呆,在想些什么呢?或许小小的麻雀也有小小的心事,小小的心事里,盛着一座小小的城,小小的城池里,会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或许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歇歇,就歇歇脚罢了。
喝杯茶吧,看着看着就眼睛酸了,眼泪粘在睫毛上,哭了吗?怎么会呢。
左边,就是南城根的老城墙遗址,约是五米高的地基,形成斜坡。有些地方,砖头从下到上砌了,防止裂开塌了。没有夯砖的地方,裸露着酥松的黄土,还有掺杂的石头。这些,曾证明,一墙之隔,就是城里乡下,像一道标签,紧紧地贴出了不同的生活,和不一样的流年。地基边,长着一溜稀稀拉拉的蒿草,可能是光照足,雨水充盈,单株都长得郁郁葱葱。
南城根上面,就是真正的楼房了,一排,两排,三排,七八层,虽然有点旧,漆都开始剥落了。但是像一个巨人,本来站得就高,俯视着拥挤、低矮、陈旧的南城根。这样一比,倒觉得南城根可怜兮兮,像个没娘的长不大的孩子。不知道住在楼上的人,爬在阳台,低下头,看南城根灰扑扑的民房和院子里熙熙攘攘的人,会作何感想?
有时候,楼房上会有说话的声音,从窗户里渗出来,落在南城根头顶上。也有时候,会有人从窗户扔下一个啤酒罐,“哐当”一声,砸在民房顶子上,或者房背后,水泥与罐子相撞的声音,异常清脆,南城根酝酿了半个下午的寂静,瞬间打碎了。院子里,闲卧的看门狗受到惊吓,就势一蹿,狂吠着,满院乱跑,像苍蝇把头掐了。房东钻出屋,仰着头,朝对面的楼上咒骂几句,你怎么不把你们家先人牌牌扔下来,你住的高就越不要脸了。狗看着主人骂,就交权了,又卧下,打起了盹。楼上没动静,也不知谁扔的,骂几句,唾口唾沫,歪着脖子又进屋了。
阳光慢慢收敛,巨大的阴影开始一寸寸摊开。风吹过,摇晃着挂在防盗栏上的干辣椒。
突然又听见细细的哭声,从右边的民房窗口里,细细地飘过来,在干燥的空气里,哭声很快就干了,化了。怎么回事?也没听见吵架声,莫名其妙,那哭声变成了哽咽,一抬头,一个长头發的女子,穿着碎花裙,捂着红红的脸,倚在窗台上。倚着倚着,就不见了。
茶凉了。太阳合拢了翅膀,黑夜渐渐包围了南城根。椅子搬进屋,风替你揭起了门帘。一个人,就这样把整个下午的光阴打发了。
剩下的凉茶水,就倒进花盆吧。
责任编辑 马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