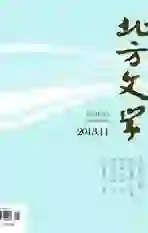从黑夜开始
2013-05-08黄金梅
黄金梅
午夜了,村庄进入了深度睡眠,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户人家全都悄无声息了,偶尔响起几声婴儿的啼哭和大人的抚慰声,很快又被沉沉的黑夜吞没,天上看不到月亮看不到星星,夜幕已经严严实实地覆盖了大地,于是,房屋没有了轮廓,树木没有了轮廓,河流没有了轮廓……一切都没有了轮廓。
这家建在庄稼地里的厂子灯火通明,在这漆黑一团的夜里显得很突兀,如海上孤岛一般。
门房的小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亮白的光线透过小门射了出去,诱惑着大脑还没有醒透的人们和蛾子蚊子们步履匆匆目不旁顾地从四面八方向它赶来。
一阵脚步声后,一切又静寂下来。这喧嚣过后的静寂,让醒了的空气很不适应,它开始和门房的小门一起翘首以待喧嚣的再一次到来。
终于,静寂被时不时响起的声音彻底打破。厂区的黑暗角落里时不时会冒出一个人来,“有人接班啦?”“嗯,你也交班啦。”“还洗澡吗?”“不了,累死了。”声音是压抑着的,较之于白天,小了许多,说话的时候,还不安地四处张望着,好像唯恐惊扰了他人的好梦一样。现在他们汇聚到了主干道上,四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向门口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这些基本都是女职工。男职工是不会这样的,他们大步行走,耻于成群结队,尤其耻于和女人们成群结队,似乎一和女人们成群结队就是堕落,当年多分的红蛋便白分了似的。这些男男女女下了班正往集体宿舍而去,宿舍就在附近,厂子里特为他们建的,很简陋,十几个人挤一间宿舍,上下铺、一张共用的桌子和两个方凳。
大门门柱的阴影里,他背朝门外,卧在支着蚊帐的简易床上,瞪着一双红眼,一动不动。宽大的门柱挡住了视线,他只能听到声音。对可能出现的熟悉声音,他有些惴惴不安,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人们三三两两地向他走来了,人没到身上的味道先飘过来了。那是一种厂子里特有的怪怪的味道,厂子里的很多人的手都是黄黄的,是在生产过程中被物料染上的色。谁也不呆,厂长他一个外地人,为什么会远离家乡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办厂?还不就是图省点治污费么。年轻时拿命换钱,年纪大了拿钱买命,这理谁都知道。但是,化工厂比其他厂高了不少工资,这是人们为什么睁眼吃老鼠药的原因。他手上没有黄色,本来也想去生产一线的,可是,他的年龄偏大了,从头学起有点难,便到了充装部门干些拿拿接接的活。
现在他们向大门走来,离他越来越近了,脚步鼓点似的敲打在他的心上,拖拖沓沓的,杂乱无章。说话的声音从模糊不清慢慢清晰得连咬字时齿舌间发出的气流声也听到了。吱地一声门开了。咣地一声门关了。脚步声停下,嘀地一声打卡了,每一个细微的声音全部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灌进他没遮没挡的耳道。他听出来了,这些工人他没一个熟悉,这让他提到嗓子眼儿的心又慢慢地落到了原处,他相信他和他的事这些工人一定不怎么了解。他出事有两年了。听说这两年,厂里招了一批新工人,老工人走了不少,他们可能都是新从外地招来的。不过,即使不是新工人,也不一定知道他的事,这里的工人一进厂就成了笼里的囚犯,各吃各的饭各做各的事,十二个小时没个休息。他们的作息时间晨昏颠倒毫无规律。所以他们认识的人了解的事很少,再说他只是这的临时工。厂子的所在地是他很熟悉的地方,以前他家的田地就在这。他和妻子两人以前过着所有农民过的日子,有田种有粮吃,闲时出去打打杂,赚点活钱补贴补贴家用,日子虽不富裕,倒也滋润。后来来了一个外地人,买通了相关部门收购了这儿的土地建了这家小型化工厂。他没地种了,只有服从安排进厂做了地皮工。妻子也找了个地方打打杂工。一晃八年了。从建厂到现在,每一个过程他都亲历了,一切全都了如指掌。
“这是什么人?”他们压低了声音在问保安。门房地下铺了两张席子,上面横七竖八躺着的三个男女中,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胞弟,另一个是他的弟妹。他们像丧家犬一样蜷缩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是为他而来,为了帮他讨个说法而来。两年前厂子里临时安排他去押车,出事后,刚开始虽然拿出钱来付了医药费,但是坚决不承认他的工伤,声称这是他私自接活而为,与厂子无关。现在倒是承认了,也承认赔偿损失,就是期限都过去两个月了,却连一分赔偿款还没见到。他照旧不吱声,妻子急得直哭,弟妹们一商议,决定在今天夜里一起出动明天早上堵厂子的大门。胞弟恨恨地发着狠,“上次太便宜他了,只是在门口坐了一会儿。这次我们去封他的门!看他们怎么进货发货!不怕他们不认账!”事实上,厂里出事也不是一例兩例了,几年里每年总有村民为了他们枯死了的庄稼成群结队地来封门讨说法。或多或少这个法子是管用的。
“嘘”地一声,一定是保安。他想象得出保安正把食指和中指按在嘴上作噤声状。便没了说话的声音,脚步声迟疑地再次响起,但轻了许多。
一丝丝花露水的香味向他飘来,脚步声突然消失了,他一下紧张起来,如芒在背。出事后,他的躯体麻木了,感觉却变得异常灵敏。这里一定有个女人,也是这个厂子里的,因为她身上也有那种特殊的怪味。她一定正停在我的床边打量着我吧?这灯光照不到的昏暗一角,一定勾起了她更大的好奇心,让她一时忘记了疲劳,在这里探头探脑。她如果看到了我,还会探头探脑吗?他这么想着,突然有了一个邪恶念头,咧开嘴狰狞地笑,想转过头来看看她的反应。她会怎么样?大叫?哭?还是拚命地狂奔,逃得远远的?想到这儿,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身子随之剧烈地抖动了起来。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逃也似的走掉。
自从上次来到这里,他就知道自己完了。
那天,太阳很好,亮堂堂的。他心里也亮堂了起来。他被妻子和胞弟合抱坐在椅子上。这是他出院后第一次走到了人前。开始他还知道低头躲闪着。要强的他不想让别人可怜他。但是,那天,他突然发现自己预料错了,没有人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他看到的是恐惧,深深的恐惧,面对魔鬼时才有慌乱无措的恐惧。这恐惧的眼神刺激了他。自从出事后他就没再看到自己的模样,只知道自己已经没手没腿成了一个废人,至于丑成什么样子,他却不知道。现在,他看到了,在人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原来自己已是青面獠牙凶神恶煞的魔鬼!那眼神足以杀死他!也果然杀死他了!那一刻,他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他清楚地知道,残废了的自己对这个家一无用处,只是累赘。他横下心,对妻子说,你还年轻,我死了你还可以找个健康的男人嫁了。妻子骂他,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早知你这么想死,当初就不该花那么多心思救你!现在你的命早就不是你的了。是我的!儿子的!债主的!你这么死对得起谁?妻子边骂边流泪。妻子说得对,我的这条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没有任何权力做自己的主了。他想着想着,绝望地号啕,你这个女人呀,怎么就想起来救我呢!把个好好的家折腾成这样!还不如让我死了呢!他用他残存的胳膊茬敲着床帮,浑然忘却了撕心裂肺的疼痛。妻子理直气壮,“我和儿子只要你活着!”妻子不怕他骂,更不怕他拿那短短的胳膊茬揍她,不但不怕,甚至她还走近了一步。他一下子心软了。妻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人到难时才识人。他便彻底断了死的念头。
他已好久不去想这件把自己置于求生不能求死不行的事了,只知吃了睡睡了吃,高兴了就在嘴里呵呵两声,傻子一样,过去的一切仿佛已被他完全遗忘了似的。现在,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少拖累妻子和儿子,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他只有听她的话,像孩子一样完全听她的话接受她的照顾。但是,一切不会因为他的故意遗忘而遗忘,现实总是把他的记忆从遗忘中抓回来。让那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午后主任笑呵呵来到他面前,说李铁今天没来,你去帮个忙押一下车。主任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否则,他一个打工的怎么敢擅自离岗去押车呢?再说押化学厂的气罐车又不是什么好差事。气罐里面装的都是对身体有害的液体。不然,主任怎么会跟他有点低三下四求他帮忙的样子呢?真是太倒霉了。气罐车居然在运输途中翻车了。事故现场真吓人呀,浓烈的化学酸液从倒扣的气罐里泄出来向他漫延,他像被钉在了地上,眼睁睁地看着,想逃脱却怎么也拔不动身子——头上、身上、手上、腿上,没有一处不巨痛,燃烧了一般。爬出去!爬出去!爬出去!求生的本能让他拼命挣扎,拼命地用头撞击着变形的车门,他终于爬出来了,脸上滴血了,衣服已被液体浸透,正在变硬变脆,一碰就会碎片一样剥落,他的头脑还算清醒,水、水、水地呻吟着……却没有水、也没有人,公路上什么都没有。他趴在地上哀号着,甩着手,甩着脚,甩着这钻心的痛。皮肤已在变色、紧绷了、起皱了、发黑了,巨大的疼痛进一步袭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今天,他已完全清醒着了,一动不动,大睁着惊恐的双眼,面部肌肉痛苦地牵扯着,扭曲着。
他猛然听见,布鞋摩擦地面的声音,是妻子从门房走过来了。他赶忙压制自己激动的身子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妻子俯下身看了看他,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他没应。妻子顿了顿,抬起头,又更近一点地俯下了身子,她一定感觉现在他没有睡着,她又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说,我知道你没睡着。
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不吱声。心里却有点恨意。这是第二次了。明天,明天自己又必须接受人们的注视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比他们看到我更可怕。人要脸树要皮,我这魔鬼的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我是人啊!还没死呢!真死了倒也好了!总胜似这么天天没皮没脸地活着。可是,恨谁呢?他任由内心翻腾着,不吱声。
妻子又轻轻地说话了,忍一忍,再忍一次,有了钱就好了,有了钱,我们就不用深更半夜睡这儿了。儿子说了,我们可以去大医院做个假肢,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再去整形医院好好整整容。一切都会好的。
说到儿子,他绷紧了的神经一下子疲软下来,待了片刻,他才从鼻子里唔了一声。妻子便很轻松似的,说睡吧,别想太多了。声音里带着安慰,很母性。这让他想起儿子小时候,动不动就惹事。虽然屡改屡犯,屡犯屡改,但每次惹事后低头认错的样子总是很真诚,让他和妻子心里软下来了,本想对孩子动拳脚,却已经狠不下心了。
出院后,妻子便开始了一次次地讨说法,总是希望而去,失望而归。昨天,妻子低着头恳求他,你再去一次吧,让他们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也好。虽然她答应过再也不让他受这份罪了。可是她实在是迫不得已。他无法逃避,说好吧,我去。好的,答应赔偿我们的日子已俩多月了,让他们多看看我,多想想他们自己,让这些当领导的畜牲快活得不那么安生。气愤之下他来了。现在,明天像高山一样堵在自己对面了,他的勇气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得没影了。他安慰自己,算了,这没什么,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和上班没什么两样。
“橐……橐……橐……”脚步声透着威严,是保安。现在这脚步停在了离他很近的地方。混杂着淡淡烟草味的鼻息声几乎就在他耳边,清晰可辨。“走走走,别看。”保安在挥舞着双手让围观的人们走开。空气一下子流通得快了起来,丝丝微风,拂着他的脸面。他们走开了,但是不远处立即传来了一阵窃窃私语声,有男有女,他们此刻并没有立即离去,正三五成群地谈着他。
“是吗?我们去看看!”惊异的声音传来,是很清脆很年轻的那种,有男有女。接着,脚步急促地走近,进了门房。“啧啧啧,真帅!”说话有男有女。这种赞叹,他一直是麻木不仁的,因为,从小到大,他的模样一直让村人啧啧称赞的。放大的照片里,是西装革履的他。“天啊,太可怕了!”说话声有男有女,发自肺腑的。又一张照片里,是现在的他,面目狰狞的他。这些惊叫声很沉闷,像从罐子里发出的,也许是捂着嘴说的吧?尖跟皮鞋橐橐橐急促地从门内冲出去,仿佛里面有个魔鬼似的,经过他时,脚步稍一迟疑,却更惶急,杂乱无章起来,像极被捅了窝的马蜂。
他早就知道这些人看他后是这个结局。他没有悲伤,他的悲伤早在出事后听到妻子的尖叫看到她一脸的惊恐就没了。很多时候,人们虽然知道真相可怕,但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那就知道吧,总比永远蒙在鼓里的好,但是,可悲的是,这些知道真相后的人们除了吓自己一跳之外一切依旧,他们根本就不会想到改变自己。
男男女女們依旧在窃窃私语。他倾过头来想听,却只听见嗡嗡的似苍蝇飞动的声音。
布鞋声又一次响起,是妻子的,很慢很慢的脚步。他听出来了。他的身子动了动,没吱声。她看到了,走近他,说,他爹,工人们都站在咱们一边呢,我上厕所时听到工人们说,你的遭遇太惨了,不赔偿就不是人了。这个月厂子里销售形势很好,供不应求呢。厂长整天乐得嘴都合不拢,一定会赔偿的。你放心吧。妻子掖了掖他的被角,停了片刻,嘴里嘟嘟囔囔着,自言自语似的,上次你一来厂长就答应了全额赔偿的,说明他还是有良心的。一定会说话算数的。要不然,他们还有脸在这位置上混吗?你放心吧。然后慢慢地走了开去,吱一声,门开了,咣地一声,门又关了。
一切又静了下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是恍惚时出现的幻觉。
明天一切都会好的。明天厂长一定会全额赔偿的。你放心吧。妻子不說谎的。明天会好的,妻子不会再为今后的柴米油盐苦巴皱脸了。儿子也会上大学的。一切都会好的。他安慰着自己。其他的呢?我?整容?装假肢?这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却又如见了猎人惊惶失措的兔子四处逃窜。不要想了不要想了,我已经完了,今天的一切全都是为了儿子,为了她。他在心里念叨着,念着念着,他什么都不知道了,睡梦中,妻子从厂长室回家了,他很紧张地看着她,妻子笑眯眯的,笑得这么舒展,满脸菊花开。我说得对吧,事情解决了,厂长把钱给我了,你看你看。妻子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拿出了一叠钱,又拿出一叠钱,又拿出一叠钱……好多好多的钱!摊在床上都摊不下了,就掉到了地上……他爹,我们有钱了,有了这些钱我们还债了,可以去大医院装个假肢,咱就又能活蹦乱跳下地干活了,再整整容,变成你原来英俊的样子,也许还能整得比原来还英俊。说着话妻子呵呵呵地笑成一团,直不起腰。他也嘿嘿地笑着,不停地搓手……
风在吹,草在摇,树在晃,架在铁门上“圣业化工公司”的几块铜字在晃荡,发出尖尖的哨声。铜字下方的简易床上有一个大葫芦,一只瘫软的大葫芦。现在,这大葫芦也在动了,一起一伏,一伏一起,也在响了,呼噜呼噜地自鸣,高一声,低一声,中途还会拐着弯,时不时还夹杂着“嘿嘿”的杂声。
妻子并没睡,正站在玻璃门前,看着床上的这个大葫芦。心沉到了最深处,他是大葫芦,大葫芦是他,也许他永远就只能是大葫芦了!为什么命运会这样作弄人呢?她就这样脸紧紧地贴在玻璃上,看了许久许久,直到眼神完全飘浮了,空洞得装不下任何东西。鼻头抽动着,喉咙也像梗着了似的,热热湿湿的液体流下来了,是泪。玻璃上了一层雾,她根本就分不清是她呼出的热气,还是她的眼泪花了门玻璃。他睡着了,他在做梦,梦里他在笑,出事后他这是第一次笑。她也笑了,苦苦的涩涩的,满嘴里楝树果子的苦味,脸上的五官都皱缩了起来。明天能见到领导的面吗?刚才工人们的话她全听到了。工人们在说,一直没现身的值班干部通知了厂长,厂长指示干部把他们轰走。干部说,找了保安了,保安说夜深人静的没法轰,这才罢了。工人们又说,明天一定解决不了这事!厂长这几天烦着呢,哪有心思理他这事啊!听说前些时候有工人写匿名信举报厂里的污染问题,省环保厅已派人检查,勒令他整改呢,说不解决污染问题厂子就等着倒闭了。这些时正是销售旺季,厂长才乐了几天,哪舍得停下来整顿啊,若再花几十万整改,厂长肉疼呢。不过,不怕他不整改……这事胞弟已知道了,她说给胞弟听了,胞弟闷着头瓮声瓮气地说了声,我才不管厂里什么整改不整改环保不环保呢,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只要我们的一份,又没讹他!我就不信这龟儿子们能躲一辈子。他明天不来,我们后天继续来,大后天继续来……做人太难了,人到这一地步活着太难了,他真想一头栽进河里得了,不过,他是她的男人,以前是她的支柱现在视她为支柱的男人,还有儿子……为了他们,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一步步走下去呵。
已是凌晨,天色很暗很暗,没一丝光明的迹象,一会儿工夫,天上突然簌簌地下起毛毛细雨来。浑然不觉外面下雨了的她慢慢地踮着脚尖回到席子旁躺了下来,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走到哪儿算哪儿,活着要紧。这么想着,她平静了下来。
雨一直下着,细密清冷,如针如芒,毛尖尖似的直向地上扎。下着下着,头顶的云朵开始由灰变白,房屋轮廓出来了,树木轮廓出来了,河流轮廓出来了……一切轮廓都出来了。天要亮了。
责任编辑 付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