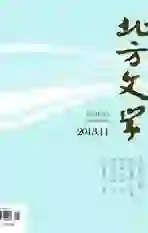残局
2013-05-08阿末
阿末
望着那盘残局,他成了发呆的老头儿了。
早先孩子同他下到这儿的时候,一场风暴怎样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海滩,那孩子飘忽中又怎样神秘地消失了,在他的脑海里成了往复不断的画面,像挥之不去的一个空白和幻觉,死死地卡在喉咙,咽不下去。
老头儿的小石屋掩卧在远离海滩的两块巨石夹缝之间。腌透了的蛋黄一样的夕阳,剪纸般的,大大地垂在屋顶后面。风圈逐渐消散了,他沿着那落霞佝偻着精瘦的身子缓缓地往回挪动着……天暗下来了,脚底的细沙越来越凉。望过去只有他嘴角那个木鱼石烟斗一明一灭地眨着,眨着,像慢慢移动的鬼火。
孩子把他从白马背上推翻那夜,他浑身冷汗地惊醒时,那孩子的小眼珠儿还深深地眨动在黑暗里。他抽出手来下意识地抠着耳朵,抠来抠去茫然若失,直到抠出大片大片的空无来。望着这些银屑般破碎的斑点,他哆嗦了一下,浑身鸡皮疙瘩。
在老头儿七十多年的棋史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竟在中盘将住了他——这沿海一带少有的象棋大师,是向来没遇过的稀罕事儿。在他们对峙的那些日子里,生活像绷满的硬弓一样在棋盘边摆着。老头儿的脊梁上大汗淋漓,面子挂在海滩所有围观者的鼻梁上。再这么没完没了地僵持下去,我这硕果仅存的一生就要废啦!那可真是个让人窒息的关口啊!心梗眼看就要发作的样子。恰在那天夜里,孩子不见了:风闻被卷进了大海。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那孩子爬过老头儿挂在门外梁柱上的大黄灯笼,登月而去。
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啊。
老头儿宁愿相信这后一种说法。我经历的沟沟壑壑已经够多的啦,守着这盘残局在小石屋就足够打发今后屈指可数的日子了。可干吗你的心上总是空落落的呢?那空豁儿忽小忽大……大起来的时候足以跑过一群群白马……老头儿顶着漫洒下来的月光歪在透凉的门槛上,另外的那颗虎牙无声地脱落了。不疼。也没有血。后来他竟枕着那条比他更老的门槛睡去了……直到那孩子把他从白马背上惊醒……他从半开的门缝儿望出去,远远的是一条铅灰色的海岸线。海啊,一辈子了,你每一天都是这副死气沉沉的老样子。孩子啊,你也还是那副瘦小黝黑的模样吗?在那个血红如花的瞬间,你的惊惧一如你的挣扎一样徒劳,而他竟像吹一根鸿毛似的把你吹落了。这可能吗?这不是真的。肯定不是。冥冥中一定有一些其他的启示在里面。
后来老头恍悟而自信地笑了:原来那盘残局你还没忘啊,孩子。这可真不错。那就来吧。
那天早上,他背上棋盘早早地伫立在苍凉幽暗的海滩上,等待着孩子,等待着那轮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太阳,就像在他的黄金年代里每逢重大的赛事之前做过的那样。可是那天没有太阳,也没有孩子,整个白天都挂着一幅灰凄凄的幕布。
黄昏把老头儿拽回小石屋时,他泄气得不行,低着脑袋斜倚在门框上。金黄色的,腌得透香的小金枪鱼就储在墙角的坛子里,可老头儿一点胃口也没有。他把那盘残局和今天的棋路在脑海里摆来摆去,可就是心不在焉,楔不入去。小鬼啊,没有人晓得你的来处。你在我们这儿露脸是存心让我栽跟斗哇。老头儿望着跟鞋底子一般硬的大脚板想:他是嫌我太老啦,所以不来,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
那一夜老头儿失眠了。他寂静地平躺在小石屋里,侧起耳朵,从海滩那边传来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越来越响的涨潮声哗哗地撞击着耳鼓。暗淡的海面上海濤的波纹映衬得夜色灰黑一片。老头儿胸中忽然涌起一股苍茫的感觉,他瞪起眯缝惯了的细眼,感到这股苍茫正在像决堤的大潮一样泛滥开来,淹没了被这夜色裹紧了的骚动与不安。
他一连到海滩去了三年。三年就这样早往晚归没有一天间断,竟渐变成积久难易的习惯了。他常常诧异自己那两条细瘦的长腿,在大脑整个麻木了的一些早晨,竟也能够把他拖到海滩上去。他悄悄地抚摩着这对老搭档,这一切都是无法阻止的啊。那孩子一定会回来。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唯一还信的,还等的,就是这个啦。
在正午太阳的映照下,大海绿成了一眼望不到底的深井。老头儿担忧起自己的眼睛来了。他开始错误地看到那个孩子晃着银铃般的小脑袋瓜儿一蹿一蹿地拱出海面向海滩而来。孩子为什么与海面是一种颜色呢?是海水浸泡出来的吗?其实,那只是海潮在一波又一波地涌动。就在那一天,他照着残局的样子把棋盘棋子留在海滩上了。孩子啊,这样你回来时就不会迷路了。你肯定忘不掉这盘残局和这个不认输的干巴老头子。你来吧,在我满口的牙掉光了之前来吧,我可不想像块老礁石似的空等一场啊。
一天早上,老头儿发现摆在海滩上的那盘残局不见了,仅仅拾到一枚绿卒。他把这卒对着太阳仔细地瞧来瞧去,突然兴奋地喊将起来:爷啊!那小鬼来过了!还把棋盘和棋子带走啦!咱们又能够接着那盘残局走下去了,唯一的区别是我在海滩上,你却在海洋里。让咱们卯足劲儿干好各自的活儿好啦!老头不易觉察地、难得俏皮地(目夾)了(目夾)眼,那双眼睛啊就很自然地陷入他满脸的褶皱中了。他体内所有的脉络也感电似的疏通了:救他于危难的那步绝妙好棋也是在这一瞬启示给他的。老头儿把这步盲棋放在想象中应占的位置,等着孩子走下去。
燃烧起来的海面是一副巨大的棋盘,老头儿端坐在海滩上,望着无法预知的结局,像一尊飞不动的企鹅雕像。即使再疲累,他也绝不斜倚着海滩或是干脆把自己放倒在那儿,那将是对这盘盲棋多么大的亵渎啊!我更愿意这么从容、硬朗地赢你。你得觉得这个老头子虽然老得不能再老,但是老得够味儿,仍在格斗,小鬼。他知道虔诚和专注对于生活是多么难得。但这种氛围对事态的发展没能产生太多影响。那孩子并未随着姗姗来迟的第五个秋天的到来而新奇地出现在海面上。老头儿前所未有地感到了脚下越来越短的道路的压力。他再也耐不住烦躁的欲望了,便试着替那孩子把棋走下去。他下得小心翼翼,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漫长的、萧条的秋天沿着老头儿额上的皱纹滑掉了,而双方却依旧在僵持不下的阶段徘徊。
起初,老头儿心里常常犯嘀咕:这每一步棋替下得能够令孩子心悦诚服吗?那小鬼的路数或许比我略胜一筹哩。可后来老头儿实在不愿在这上面耽搁太多的神思了。他放眼极目,对着海面上日渐稀疏的小小帆影叹道:无论如何,棋总得走下去啊,况且我总是施展出最佳妙的路数替他走,甚至替他走出了七十多年来最好的步子,变得比孩子更像个孩子,也并不感到有多大的委屈,反而隐隐中还透出一种莫名的兴奋和骄傲。
我想变成个孩子。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孩子,那样我就能从头来过,再拼上七十年。而且一切都将轻松而又漂亮地重新开始。你又能够亲切地抚摩那些抚摩不尽的圆圆滑滑的小棋子了。老头儿把手放在口袋里那枚小绿卒上,从指尖一下子暖过来的感觉真不错。实际上你已经在变着呢,只是你变得不是越来越像个孩子,而是越来越老,越来越是个老头儿了。你嘴里的牙没有几颗了,快掉光了;再毒的太阳也晒不痛你的脑门了,你的大脚板子越来越小,裂开了口子就再也不能合上。你离那个日子还会远吗?
“我不怕死!”老头儿喊起来,傍晚的海滩被这嘶吼荡得更显空旷。“我一点也不在乎!”只是肩膀上岁月的堆积太老太沉,你的腰杆儿不知不觉地就弯曲了,离大地更近了,有点挺不住了。可是所有的老头儿都是这样啊!你没法把肩上的担子卸掉。你可以躺在小石屋里装孙子睡大觉,可以大象似的慢慢地走进海里,沉在那儿一了百了,但肩上的担子你卸不掉;这样你才算是个够辣的老头儿啊,才能够牢牢地攥住你自己的拳头啊。可是,几乎所有的老头儿的结局都挺惨淡。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你守着这盘残局就是不肯撒手,就靠这个顶着你一天一天地喘着,活着。
直到除了杀子儿见血之外别无它途的时候,老头儿才逐渐恢复了诚实的美德。在此之前的那些年头里,他仅仅走出了不伤筋骨的二百零八步。他不愿走近结局,绞尽脑汁呆在原地不动。赢和输同样可怕。延续才能显示一种过程和呼吸,才能始终端坐在这里。可是眼下结局像个不安的、不断滚动的轮子似的逼近了。一个难以承受的念头恶魔一样地纠缠着他,他像船上的桅杆一样瘦,而那盘残局则是风帆,他生活中的风帆。
看来收帆的日子到了。继续回避将是对自己的背叛。孩子啊,我们与中国象棋陪着一个梦幻生活了很久之后在我们身体内外泛起了那么多泡沫碎裂之后的现在,应该有一个分晓了。
老头儿回到了他的小石屋。他从坛子里摸出一条条小金枪鱼塞进嘴里。他坐在门槛上仔细地嚼着这一条一条的小金枪鱼,慢慢地胃鼓胀成了小坛子一样的东西。这又腥又咸又香的一条一条吃了真长劲儿,真不错啊。我要把这些呱呱叫的小家伙们统统吃掉。尽管你的牙床挺不争气,但不妨慢慢地嚼下去。你是多么需要再来点力气啊。好在你的时辰到了,你一生好像都在为这个时辰做准备似的。风往南面刮过去了。你的精气神可来不得半点含糊啊。小金枪鱼呕得老头儿咽不动了。只要一张嘴,小金枪鱼就能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你咬碎牙关也要把它们咽回去。他望着手掌上最后的三条鱼,直起身子倚着涂上了落霞的糙木门框,茫然地嘟哝道:爷啊,剩下的就是这件事啦。
那时候,巨大的夕阳已经开始了最后的燃烧,整个白昼渐渐地沉浸到越来越深浊的海水中去了。
很久以前自他开始到海滩等待孩子那一天起,黄昏时分的海就令人泄气和恐惧。那一刻,他总会隐约感到一个熟悉得近乎荒诞的幻象已经随着潮汐退去,而他又正是这次潮汐中的最后一束浪沫。为了躲避这种浓重的、一层层叠压过来的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黄昏时老头儿曾一度在小石屋里闭上眼睛假寐。但这种睡眠只维持了很短一个时期,他不得不重又回到海滩上去。凡是命定了的你躲是躲不掉的。这多像今晚这轮挑得高高的月亮啊。老头儿暗暗吃惊:今晚的月亮多大啊。比孩子离开那天的还要大。月亮压根就没有这么大过啊。
这是个奇怪的兆头,孩子。其实那盘残局老早就摆在那儿了。传到我们这儿经历了多少辈子你知道吗?陪进去了多少老祖宗啊。腰弯了,背驮了,牙也掉光了,他们并没图赢,只求这么天长地久地守着不输就成了,直到把这盘残局万变不离其宗地交给了我。这最后一个。自从五十年前的那个长夜,难产把女人从我这小石屋夺走那时起,一切就已经被注定了。尽管后来你厚着脸皮又找了一个乳房肥大的女人,但你就是没法让她给你怀上个孩子。那种女人是不会在你身边待太久的,就像一只四海为家、飞来飞去的燕子。老头儿枕着湿漉漉的门槛不知躺了多久,直到有许多奇人旧事来入梦了,他才恍惚醒来,才觉出朝天大路上自己已走过了多远。他把烟斗里的烟灰统统磕了出去。同鬼怪阴魂一道转悠原来并非想象的那般可怖。你胆怯,没准它们比你更胆怯呢。老头想:大家这样摩肩接踵地相安无事,其实跟游来游去的小鱼儿差不多。
挂在梁柱上的晕黄色的大灯笼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灭了。老头儿却丝毫没有察觉。
从那个与你对视的黑洞儿里看到了什么啊?须发花白的头颅一个个地漂了过来,晃来晃去磷火越来越多……真是怪事。那些我没见过面的老祖宗们似乎就是这个样子。他爬起来从口袋里摸出那枚绿卒,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那个越来越小的黑洞儿走过去……就在那个黑洞从一片雾气中消散的时候,他把手心的卒子使劲儿扔了进去……然后蹒跚地走向不断下沉的海滩。流动的海平线已躲到暮色后面去了,尽管他像个盲人似的不屑于再看它一眼,但心里却在想,在天海相连之处,是死死地刻着那么一条分割线的。越过那条线就能登月了。即便再老,也能登月。那孩子就在月亮上。
他朝向海面端坐在海滩。月亮生凉的清辉洒满了他的脊梁和阴暗的礁石。沉甸甸的霜粒儿。彗星的尾巴。再大的海风也刮不掉它啊。老头儿先深深吸入一口长气,自语时,那气息就从已没有了牙齿的牙床间无声地透了出去:
“孩子,我俩开始吧!”
月亮挂在下弦的时辰,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替孩子走时,他感到对手是个老头儿;为自己走时,他感到对手是个孩子。而且,无论是圆睁双目还是闭眼沉思,他又能看到那个消失很久的黑洞了。
那是一只凝视了多少年的大眼睛啊。它望着你,远远地把力气注入你的脊椎。你不垮,它就会这么长久地望着。望着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守住这盘残局。可是我要赢啊。我要的是一个全新的能够主宰孩子们的开局啊……老头儿想,我很难这么无边无涯地守下去啦……爷啊,我没有儿子!他茫然地注视着那个忽大忽小的黑洞,来交换彼此的孤独。其实,没有儿子也满不错。老头儿想,这样我就能够九头老牛也拉不回地走下去了,要么赢尽,要么输光。多少年啦?你活的是不是有点太久了呢……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大脚板开始腐烂了。那股讨厌的气味儿缭绕着不断地从小石屋里溜掉,真丢人啊。老头儿挺了挺僵硬的身子,手又伸进了空空的口袋,他习惯于在那儿找到孩子那枚绿卒。这次马上后悔了。他讨厌那种茫然若失的感觉扰乱自己的思路。现在,他们已经走出了四百一十步,需要通盘关照一番虚实,以便敲定下一步的路数了。若到无回天之力时再做打算就已经太迟了。一经发觉不利的征兆,哪怕是微乎其微,也及时作出周密的调整和安排,这已经是老头儿几十年来的惯例了。每逢回顾起自己硕果累累的生涯,一片阴凉就会从他心头袭过,但这次浑身却突然一紧,记起儿时练棋前的那段宁静了。
不。你生来就是个下棋的。不下棋的你不如一条臭鱼!你爹爹、你爷爷他们就是因为下不完这盘棋才去找女人生孩子的。六岁上你爹爹就逼着你下棋了……这一下就是八十年。小石屋还是那般结实。坛子里若还有小金枪鱼的话,我宁愿再吃上十来条……等下完了这盘残局我还要枕着门槛子美美地睡上一大觉……可是,这盘残局几时才能够下完呢?!
他把嘴里的老烟斗狠狠地甩出去。在划出一条看不见的弧线之后,那烟斗落进水里。
海上起风了。寒气一丝丝地钻进了骨头缝儿。海滩上弥漫着浓重的盐碱味儿。向来少见的坏天气,今天算让我遇上啦。走吧,老家伙,接着走下去。你也是正在走回去。兜了多大的圈子,却在走回去。你正举手砰砰地叩你自己的门哩。内外都响起了风化的细音,积淀的岩层噼啪噼啪地脱落了,眼前迷过了一缕缕散发着海腥味儿的轻烟……这魂儿在外面游来荡去了这么多年,也该回来啦。我这副干巴巴的躯壳敞开了大门在等着你哩。听我的。咱们卯上最后的一股劲儿……然后就索性输给那个孩子好啦。咱们太老。老掉牙啦。牙都掉光了的人,黑翅膀就开始长出来啦……而且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月亮往后背似乎又沉去了一竿子……又沉去了……天就要放亮啦。
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那个黑洞从老头儿深陷的眼瞳里消失了。半空中竟幻出一大片静止不动的被认为是海市蜃楼的东西。那天早晨海上一条船也没有,一片片鸥鸟从太阳光里飞过来,不停地围着老头儿旋圈子,那一副副上下翻舞的翅膀红彤彤的。老头儿平躺在海灘上,如雷的鼾声使得那些海鸥们不敢在他身边落脚筑巢。他沉在梦中吗?不清楚。若有梦的话他所梦见的当如月亮所预言的:
孩子明天回来。
特约编辑 梁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