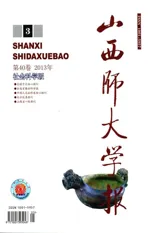论孙犁小说的生命意识
2013-04-11景莹
景 莹
(南通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孙犁是一个受到“五四”启蒙思想影响、尊重个体生命自由的作家,他的小说中始终贯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与时代相融合的时期,通过在文本中建构延展阔大的空间,以地名命名的作品,体现了鲜明的空间意识,以言说个体生命状态的自由舒展,营构了以“游走”为意象的表达方式。在政治标准第一的特殊时代,又通过书写死亡和死亡体验,表达对生命的珍视。特别是面对生命的被伤害和逝去,总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感伤,从而,不断招来批评,但他却不改初衷。综观孙犁的创作思想,“五四”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地域文化,特别是秉承京派和谐生命境界的生命追求共同影响了他的创作。
一、自由空间的驰骋
孙犁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同时又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早年在保定—北京—白洋淀的生活经历中,最合于他个性生活的就是白洋淀的教书经历。晚年,他回忆这段教书生活的情景时说:“学校设备很好,我住学校楼上,面临大街。有余钱托邮政代办所从上海购新书,深夜读之。暇时到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舒心目。”[1]6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发生,也许他会将这里作为一生事业的寄托之所。然而,战争改变了他优游的教读生活,也把个体自我的潜力在战争中全部挖掘、释放出来。
孙犁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2]241在山地故土的跋涉中,有敌人炮火的威胁,有忍饥挨饿的困苦,也有小知识分子的诗意抒发,战争把个体自我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也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诗意浪漫演绎得更加丰富多彩。山地的粗犷热情,水淀的月光苇影,都是诗意的寄托,因此,他把这段时间称为美好的极致,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书写的生命原乡。于是在战争间隙,笔走腾挪中将乡村山地做实。基于这样的感情,他的“山地回忆”与想象具有了鲜明的空间意识。也因此,他小说中的时间意识是笼统模糊的抗战期间,没有明确的时间标识,是非清晰的线性延续。这是因为生命在“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3]49的自由极致境界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
孙犁有不少小说、散文是以地名命名或与地名相关的,比如,《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蒿儿梁》、《在阜平》、《烈士陵园》、《老屋》等。乡村、山地、水淀、道路院落、低坡高山都是他书写的对象,好像他面前铺着一张老旧的地图,指引着迷路的读者,随他的视线,移动脚步就可以到达某个地方。这种地图式的建构包含了作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定位,即“我”与历史步调的关系和与战争的关系。一个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奔走于此地的老抗日工作者,正是在抗战的宣传报导中,熟悉了这里的地形地貌。行走在无边无际的平原旷野和崇山峻岭中,做着崇高的事业,心情是愉快的,同时在或清幽空茫或巍峨峻峭的大自然的千变万化中,领略自然的美和庄严,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同时,也有生命伟力的张扬。
荷花淀的月夜,水生嫂在银白的月光、水雾、芦苇席的包围中,闻着从水淀飘来的荷叶荷花香,整个的月夜水淀都成了她的亲密伙伴,陪伴着她,水生嫂这个灵秀的女人因月夜荷花的衬托而有了诗意的灵性。在诗意的空间中,人、大地、花草、树木相互依偎,自然因人的参与而变得更加富有生气,人与美丽的自然相融而变得更具有亲和力。人和大地天空相连接,而围列村落的低矮房屋,与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相连,再造出视线的无限延展性。人在大地的安慰和天空的佑护下既安全又舒展。
如果说人与自然相混融的混沌空濛是和谐的享受,那么峭拔伟峻的气势与人的对峙更显现出生命的光芒和无以争锋的伟岸。孙犁不少写冀北山区的篇什,就是将人类的生命智慧、生命强力与自然的奇伟峻拔联系在一起的。如在《吴召儿》中,他们来到居住在黑石山顶背后的吴召儿的姑姑家,那里仅姑姑一户人家,山顶上黑压压的,巨石覆盖,很难找到生命的迹象,姑姑家在巨石背后,只在太阳出来时,能见到一会儿阳光,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居然能看到姑姑一家精心培养出来的蔬菜,不禁惊叹:“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在《蒿儿梁》中,为了养伤,来到了这个位于山顶的偏僻小村庄。“站在这山顶上,会忘记了是站在山上,它是这样平敞和看不见边际,只是觉得天和地离得很近,人感受到压迫。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没有声音,卷起一团雪柱,……薄薄的雪上,也有粗大的野兽走过的脚印。深夜在这山顶上行走,黄昏和黎明,向着山下号叫,这只配是老虎、豹”。
在铁响板的扁豆和虎豹的蹄印中,注入了自然的蛮荒和生命的强劲,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上,姑姑一家居然能开辟出片片土地,种植粮食蔬菜,创造生命奇迹。在蒿儿梁,人能与虎豹比邻而居,人的生命意志于此以最雄奇的形式彰显出来。
有强烈生命意识的人,也时刻留意外界的变化,生命与外界环境融洽时,自我得到最大程度的舒展。一旦外界发生变化,就要注意调整自我的姿态,以免个体受到威胁。1950年代初,文学的个体表达空间越来越窄,孙犁小说的空间表达也由旷野高山走向乡村小路,以“游走”的意象体现出来。作为代表作之一的《铁木前传》,小说从第二节开始,以六儿为对象,将“游走”呈现出来。最初是他带着九儿到田野拾柴,稍长大点到街上游逛着卖花生,卖包子。在结识了小满儿后,为了和小满儿在一起,他爬树抓鸽子,上房顶捕鸽子,到野外的树林逮鸽子,最后,他赶着大车,带着满儿跑出了村子,走向了石门。六儿不停地走动,就是害怕被父亲使唤,害怕机械地生产队劳动,他是要在游走中摆脱束缚,试图在游逛中寻找与众不同的人生。
六儿喜欢走动,小满儿更像黑夜的精灵,游走在无边的旷野上,也像深夜外出的飞禽走兽一样,喜欢晚上一个人到旷野走动,“炎夏的夜晚,她像萤火虫一样四处飘荡着,难以抑制那时时腾起的幻想和冲动。在夜里,她的胆子变得特别大,常常有到沙岗上来觅食的狐狸,在她身边跑过,常常有小虫子扑到她的脸上,爬到她的身上,她还是很喜欢地坐在那里,叫凉风吹拂着,叫身子下面的热沙熨帖着。在冬天,狂暴的风,鼓舞着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飘落在她的脸上,就像是飘落在烧热烧红的铁片上”。
他们以夜游外出,伺机寻找白天无法释放的压抑,试着在不间断地走动中,抛弃烦恼,走出别一种人生,从而明确自我生命的存在和价值。
二、死亡和死亡体验
“不知死,焉知生”, 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家在关注生的自由快乐时,也时刻在瞩目着死亡,这是对生命珍爱的另一种表达。他的《爹娘留下的琴和箫》、《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和《芦花荡》是“一个故事的三种写法”[4]。《爹娘留下的琴和箫》发表于1942年,表达了个人之于战争的焦虑和恐惧,作品描述了一对琴瑟相和的恩爱夫妻和两个女儿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在抗战爆发后丈夫钱智修牺牲,家国同构的仇恨燃起了妻子复仇的激情,最后也殒命沙场。一对天真单纯的女孩大菱、二菱也死于日本人手下。撑船的老头儿在向“我”讲述大菱和二菱在芦苇荡里清洗后是那么漂亮,尤其是大菱不顾发烧,也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生命和美面对狰狞的战争而消失,个体面对战争的渺小在小说中都表现出极度的感伤情绪。《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和《芦花荡》则是俯就于政治的改写,去除了原来的感伤,弘扬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980年孙犁以《琴和箫》为题再次发表,恢复了1942年完成时的本来面目,再次表达他当初写作这篇小说时的初衷——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在另一篇小说《碑》中,叙写了几个战士在冰冷的滹沱河里因寡不敌众被河水卷走后,打鱼的老人每天在他们牺牲的河水附近不停打捞的故事,即使一件遗物都没有找到,老人还是每天继续他的打捞工作,他试图通过“打捞”证明生命曾经存在的迹象。《新安游记》中侄子处死当汉奸的大伯后,开枪自杀,这不是一个忠孝双全的道义话题,而是对生命尊重的最好诠释。
死亡体验是比死更痛苦的经验,它是对生命意志、毅力的最残酷的考验,也是对生命承受力的最痛苦的折磨。黄秋耘曾这样揣摩过孙犁文革间的感受:“我觉得, 他心里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看看近三四十年吧, 文坛里边那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家, 一个一个被批斗, 有的被迫害致死。像跟他熟识、要好的侯金镜, 是被迫害死的, 郭小川也是被害死的。没有文化大革命, 这些人都死不了!”[5]128其实,在文革之初,孙犁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被妻子及时制止了。后来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更是被死亡的情绪笼罩着,“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一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6]197
死亡是生命的最大威胁,也是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时,生不如死的恐惧和来自环境的无边的畏惧,会导致生命的变异。1946年他因《新安游记》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遭到批判,进城以后, 1951年10月6日, 《光明日报》针对其作品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 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7]的价值观,以整版篇幅有组织地展开对他的批判,对象就是前文提到有感伤情绪和涉及死亡的几篇小说,这是解放后对其创作方向的引导。可是《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还是偏离了大方向,由于过度的紧张忧虑和文坛内的各种政治批判的无形压力,终于使他大病,且一病十年,不得不搁笔。
三、自由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
“孙犁大半生身在革命文化中,可他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到的却不是主流革命文化的影响。孙犁人格心理与价值系统的形成,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鲁迅及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精神”。[8]除去这两方面的主要影响外,应该说孙犁还受到了地域文化中道教的“乐生”观念和京派文学的影响。
鲁迅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人首先要了解道教。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已经渗入到民间生活的点滴中。河北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东汉末年张角在巨鹿(今河北邢台境内)创立太平道,以此号召百姓推翻东汉统治,自此,原始道教开始在河北的城镇乡间流传。西晋葛洪曾在恒山(河北曲阳境内)炼丹,此后,这里成为道教圣地,并在北方普及,唐代吴道子曾在此绘制大量壁画,一直保存至今。《河北地方志》载,自宋代以来,整个河北大地是宋与契丹、辽国和金国长年征战的战场,而后这里长期被金国统治,老百姓多年处于异族奴役中,生活苦不堪言。原本道教在民间就有很坚实的基础,长年战争,朝不保夕的生存的艰难,使他们进一步接受了道教安贫乐道的观念。自元朝始,著名道士丘处机及其弟子一直活跃在河北一带,将道教乐生但不求大富大贵的小民思想广为传播。直至目前,河北的道观要远远多于佛教寺庙,而且有些因道教而起的地方文化活动,现在依然有广泛的跨区域影响。
道教乐生而亲自然的无为观念也影响着孙犁率真自然的个性形成。出生于农家,多年在乡村山地生活使他和大自然有着异乎寻常的亲近感,“无论雷电轰鸣,狂风怒吼,洪水爆发,山崩地裂,都是一种天籁”[9]56。他欣赏自然的普通美,于是每年春天,白菜花都是他案头的风景。他将自己的一生比作普通平凡的菜花,花虽普通,色彩也单调,但没有斑驳,纯净而自然。
对孙犁来说,与生俱来的地缘遗传是无法拒绝的存在,而后天的教育又使他将乐生的观念看得更重,并且把生和自由相连接,使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自由的生,快乐的生,在日常的生活中抒发个体的自由,表达对生命的尊重。
作为保定育德中学的学生,新文学对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除了鲁迅,他谈的最多的是《大公报》。他在《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一文中写道:“每天下午课毕,我到阅览室读报。所读报纸,主要为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主要看副刊。《大公报》副刊有《文艺》,《申报》有《自由谈》,前者多登创作,沈从文主编。后者多登杂文,黎烈文主编。当时以鲁迅作品为主。” “当时所读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读小说散文:《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作品,英法小说,泰戈尔作品。后来专读左翼作家及苏联作家的作品。”[10]214
四份报纸中,《大公报》和《申报》对孙犁的影响已通过沈从文和鲁迅的名字做了明确的交待。众所周知,鲁迅是孙犁最喜欢的、也是最敬仰的现代作家,这里又将沈从文和鲁迅并列,可见沈从文对他的影响也非同一般了。关于《益世报》和《世界日报》,两个副刊的主编和撰稿人都是自由主义者和通俗文学作家,马彦祥、梁实秋、老舍、李长之、张秀亚、张恨水、张秀鸾,等等。“《益世报》的自由主义文化取向吸引了大批持独立思想与中间立场的文学界人士,他们举起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旗帜: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新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等,聚合于《益世报》,共同构建了一个超然主义的文学阵地”。[11]10《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由张恨水做主编,他的小说《金粉世家》在上面连载达6年之久。上述各派的文艺观与京派多有相同之处:对个体和生命的尊重。
通过对青少年孙犁阅读过的期刊作品的分析,我们看到影响他的主要是五四启蒙思想的书籍期刊,占了他阅读量的3/4。其余1/4是苏联和左翼的革命文学的刊物。结合孙犁后来的个人行为和创作活动,首先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前者是其行为的指导思想,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这是后者对他的影响。然而,“孙犁参加革命时所身居的晋察冀部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统一战线文化不仅没有及时地为孙犁补上阶级论的政治课,相反还加强了他原有的人性观,这个起点左右了孙犁一生对于革命的理想主义态度”。[8]所以他一生都是革命队伍的“多余人”。
孙犁特别注重启蒙思想中个体生命自由的部分,是家庭出身、地域文化和后天习得等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后天的学习是最主要的。地处京津之间的小城保定,育德中学的文化氛围,无疑是以京津文化为主导方向的,也许流行于京津冀的一句民谣更具有说服力,“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狗腿子”不是汉奸之意,而是说保定人没有立场。身在育德中学,无论是京派的《大公报》、《益世报》还是《世界日报》应该都对孙犁的个性人格和价值观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孙犁对《大公报·文艺》的情有独钟是他说过多次的。在北京做小职员时曾给它投稿,并在1934年11月29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北平的地台戏》,而后又多次投稿。辞职离开北平赋闲在家的一段时间里,还定了一个月的《大公报·文艺》,为此和妻子闹了不愉快,向父亲要钱,父亲要他定一份便宜的地方小报,他坚决不肯,最后双方妥协,只定一个月的《大公报·文艺》,邮递员和乡亲们也把他视为异类。由此可见他对《大公报·文艺》已是心仪至极。京派对生命的关注,对底层社会淳朴民风的青睐,对生命和谐的追求,既贴近孙犁接受的启蒙思想,又符合道教的乐生观念,特别是京派小说静态中的自守与孙犁有些孤僻、有些柔弱的性格气质更相吻合。
如果我们把孙犁的作品与京派小说做一简单比较,就能看到孙犁对京派的师承。孙犁小说的抒情风格,现实主义特色中的浪漫情调,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对传统道德的尊崇,对乡土生活的怀念以及谆厚朴实人性的塑造,甚至小说中的残破意象,都与京派小说相同。而女性和老人形象的塑造,更是得京派真传了,对女性和老人形象的塑造是道教乐生向善与京派文学追求道德完善结合的最好的体现。不同的是,京派小说的人物形象是静态中的等待固守,孙犁小说中的人物是动态中的追求。
[1] 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A].孙犁全集:第8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A].孙犁全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 孙犁.黄鹂[A].孙犁全集:第5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 叶君.裂隙与症候——论四十年代不合时宜的孙犁[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5).
[5] 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6] 孙犁.女相士[A].孙犁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 林志浩,张炳炎.对孙犁创作的意见[N].光明日报,1951- 10- 06(10).
[8]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9] 孙犁.装修[A].孙犁全集:第9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0] 孙犁.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A].孙犁全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1] 杨爱芹.《益世报》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