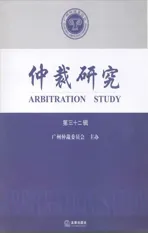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去身份化及其属地性(中)
2013-01-31张春良
张春良
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去身份化及其属地性(中)
张春良*
(续上期)
(三)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的制度表达与实践演绎
综观国际商事仲裁整体制度,其“去身份化”运动首先表现为仲裁协议的自治性,包括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独立性、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独立性;其次表现为管辖权自治,次之表现为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超国家性和仲裁实体法律适用的直接性,最后表现为仲裁裁决的去身份化。
1.仲裁协议的自治性(Autonomy of Arbitral Agreement )
仲裁协议的自治性已俨然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以及调整仲裁协议的根本性法律原则,①按照Philippe Fouchard等人的界定,仲裁协议的自治性本质上包括“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一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相对于主合同而言的仲裁协议自治性或者分离性;一是在完全不同的观念上使用的、相对于“一切国内法”(all nations law)而言的仲裁协议的自治性,这一意义尤其在法国法院而言更是如此,它通常关涉据以评价仲裁协议是否存在及其有效性的规则的选择问题。②而这两者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去身份化”运动。
仲裁协议的分离性涉及到是否需要赋予仲裁协议以独立的生命,是否需要让仲裁协议追随它所属合同的命运等问题,③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事实上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采取一体主义,将仲裁协议及其所归属的合同捆绑在一起,让主合同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格以吸收仲裁协议的身份;要么采取别体主义,将仲裁协议与其所归属的合同予以分割,赋予仲裁协议以独立的人格和身份。而第一种选择已然代表着曾经辉煌的过去,第二种选择则日益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④它符合并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仲裁条款的本质功用、仲裁制度的比较优势,乃至整个仲裁制度的发展方向。⑤在与主合同的兼并吸收相抗衡的情况下,仲裁协议完成了第一步“去身份化”运动,为自己创造了独立的身份,并且为第二步的“自治性”奠定了基础。
着眼于从与各国国内法的关系来界定仲裁协议的自治性,这是奇特的、但尤其是对法国法院而言却是一种主流观点。它意指仲裁协议在面对依据选法规则确定的用以调整它的各个国内法体系时保持一种超然的独立性,因此有人据此判断仲裁协议具有自我完足性(self-sufficient),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法律体制而有效,并且发展出一个新的概念(contrat sans loi)认为,仲裁协议是一个不需要准据法的合同。但这一概念与法国法院所理解的仲裁协议自治性截然不同,后者通常意味着对于仲裁协议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准据法选择方法,即所谓的实体与选法相结合的支持有效的规则,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典》第178条首先体现了这一精神。⑥支持有效或者有利于有效的规则是一种凯弗斯式的“结果导向”选择方法,它不拘泥于某一个或者几个特定国家法的限制,在这一意义上它表现出身份的超然性和独立性。
仲裁协议的自治性很快便被转译为仲裁实践。法国法院于1963年5月审理的Raymond Gosset vs.Carapelli案率先确立了仲裁协议独立于主合同的身份,其后美国于1967年通过法院审理Prima Paint vs. Flood & Conklin案、英国高等法院于1991年、上诉法院于1993年分别就Harbour Assurance Co.,Ltd. Vs.Kansa General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Co.,Ltd.案作出裁决,通过司法实践强化了仲裁协议的分离性原则。在仲裁协议的存在与效力认定超越各国国内法的司法实践方面,首要和典型地当数法国Cour de cassation在1972年审理的Hecht案件,该案表现出了支持仲裁协议自治性的精神,该案不仅表现出了与Gosset一案相同的审理逻辑,而且事实上远比仲裁协议分离性的逻辑结果走得更远,法院作出的裁决并没有对仲裁协议适用任何国内法,相反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的认定却是单纯从当事人的意志独立地推理出来的。⑦这一案件的积极意义是从司法角度肯定了仲裁协议超越于各世俗法律体系的框架约束,从而在“无身份”中取得了自己的独立规定性,即自治性。
仲裁协议的自治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运动的另一个表现,它首先脱离主合同的身份寄托而独立自为,并进一步使评判自身存在性与有效性的标准脱离国家法律的依赖,在与各国割断身份归附关系后仲裁协议获得了自身身份的独立,并保证仲裁制度与实践沿着这一自治方向前行。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自治性是“去身份化”运动的精神表现,仲裁协议的自治性则是这一运动最为关键的制度表达,它甚至决定着“仲裁活动的生死存亡,……而且也构成指导仲裁活动进行的宪章。”⑧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运动的后续表达与实践都建立在仲裁协议的去身份化运动之上。
2.自裁管辖权(Kompetenz-kompetenz)
仲裁庭自我裁断管辖权适格能力问题被称作自裁管辖权规则,有学者认为它含有“项羽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意思。该规则是仲裁协议自治性原则的逻辑推论,因此也是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运动的逻辑延伸。仲裁庭不顾世俗国家法院之意见独立地裁断自身管辖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国际商事仲裁独立于国家法律体系的超然身份,也使国际商事仲裁在各国的属地牵挂中脱离出来。具体而言,仲裁自裁管辖权规则中的“去身份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与国家法院的对话之中,并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⑨其一,它允许仲裁庭无需国家法院的支持即对自身管辖权限作出裁定;其二,它防止国家法院在已经作出决定前介入裁定仲裁院的管辖权问题;其三,这一规则要求国家法院在遭遇仲裁管辖权问题的早期阶段进行自律,限制自己去查明仲裁协议是否存在,也不得限制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
可见,仲裁庭自裁管辖权规则是相对于国家法院管辖权而言的,尽管它在这一问题上的裁定是不彻底的,国家法院享有共同管辖权(concurrent jurisdiction),而且国家法院的裁定具有优先性,但它与仲裁协议的自治性精神在逻辑上的循环得到了现实贯彻,与国家法院体制建立了一种离心张力并在这一对抗性和谐中显示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去身份化”趋势。
这一规则得到各仲裁立法和各主要国际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广泛接受,并在仲裁实践中得以贯彻。法国1983年《民事诉讼法典》第1458条确立了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但早在1971年的Societe Impex vs. Societe PAZ案中法国法院就以判例的形式接受了该规则;美国最高法院于1995年审理的First Options of Chicago vs. Manuel Kaplan et ux. And MK Investment,INC.案也表现了支持仲裁庭行使自裁管辖权的司法精神。
国际商会仲裁院更是经常性地行使自裁管辖权以决定因仲裁协议瑕疵问题而导致的效力问题之争。在国际商会1007/1959案件中,德国公司对它与法国公司之间缔结的合同及其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提出异议,其理由是该合同违反了法国外汇管制法。审理该案的独任仲裁员受理了案件并作出裁决,后该德国公司诉诸法院,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了质疑。受理案件的法国法院指出:“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管辖权不能仅仅以宣称履行合同义务违背法国外汇管制为由而被剥夺。”从而维持了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⑩国际商会仲裁院1968年受理的1526/1968号仲裁案例更具有典型性,它从反面阐明了国际商事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无须对国家法律体制予以理睬,也无须对国家司法机构“察言观色”。该案主要涉及一个非洲政府终止一项特许协议而导致的纠纷及其仲裁协议效力问题。作为仲裁协议当事人一方的非洲某政府对国际商会仲裁院管辖权权限提出质疑,并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受理该案件的独任仲裁员认为他仍然拥有管辖权,其理由是:“在国际仲裁事务中一个受到认可的规则就是:在国家程序法没有做出相反的规定时,仲裁员自己决定自己的权限……法国法律、国际商会总部的法律、瑞士法律、仲裁地的法律以及此案中非洲国家的法律都不能让此规则无效。在国际仲裁事务或在接受的程序中现在普遍认可的另一个规则就是:依据法国最高法院的说明,仲裁协议无论是被明确订立或是包含在契约内,除了特殊的情况外,具有完整的法律上的独立性,不会受到合同无效的影响。” 国际商会仲裁院当时的秘书长Derains 对此裁决评论说,他深感遗憾该独任仲裁员觉得有必要援引各种当地的程序法作为自己裁决的依据,而并没有强调规则赋予仲裁员决定自己管辖权限的这一特定权力。该权力本身就存在对合同的理解中;既然已得到当事人同意的规则已经赋予了仲裁员决定自己权限的权力,为何还需做更多的解释?⑪
显然,按照国际商会仲裁院秘书长的理解,仲裁院管辖权的取得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是仲裁协议独立性的必然要求,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应当从外在于仲裁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关的态度中求证,国家法律体系和司法机关的态度不应当影响仲裁庭判断的独立性,二者不是制约和被制约、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毋宁说是平行关系,这种平行关系解放了国际商事仲裁对相关国家法律体制的隶属,并在脱离这些属地关联的同时取得了自身独立规定性。
3.仲裁程序规则的超国家性(supranationality)
仲裁程序规则的去身份化集中表现为仲裁程序相对于世俗国家程序规范的超越性,或称“自我完足性” (self-sufficient),“自我完足性有的学者也称之为封闭性,封闭这个词与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意思有些联系,但我们这里所说仲裁程序的封闭性,是说仲裁程序独立开始、进行和结束,程序上不受外部、内部的干扰和影响的特性。”⑫仲裁程序规则广义地包括仲裁庭可能适用的程序法则,即国家制定法、司法判例、相关国际立法、仲裁机构制定之仲裁规则,以及临时仲裁情况下当事人自行拟订的程序规则。⑬在传统法律适用规则指导下,程序规则适用程序进行地国法,这突出了仲裁地这一连接点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重要意义,以至于仲裁程序法被习惯性地直接等同于仲裁地法。⑭因此,仲裁程序规则的法律适用“去身份化”运动首先是斩断仲裁地的属地包含,在法律适用上离弃仲裁地的排他性程序约束,改变传统的先验地适用仲裁地程序法的硬性做法,转向程序适用的可选择化,并进而致达超国家性的自由境界。
离弃仲裁地的程序排他性约束使某些学者表现出不必要的担忧,他们认为仲裁程序适用的非当地化会使国际商事仲裁陷入“法律荒漠”(legal desert),以至于他们更为激进地认为,《纽约公约》应当将不隶属于某一国内法的仲裁裁决清除出它的调整范畴以对抗(against)仲裁的非国内化;另一些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更喜欢用积极的仲裁规则的“超国家性”(supra-nationality)来替代消极的“法律荒漠”的称谓⑮对此类担忧显然属于学者的“多情之忧”,排除仲裁地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先天“前定”并不必然导致仲裁程序进行的失范,对于仲裁地法缺位后的“法律荒漠”会被当事人选择或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填补,而在仲裁地法向当事人自主意志或者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交接转换过程中,国际商事仲裁的“去身份化”趋势被凸现出来,而最为明显的身份无化则是国家为一方当事人的商事仲裁⑯
仲裁程序适用的“去身份化”趋势已经表现在相关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和仲裁实践中。以ICC仲裁为例,它在仲裁程序的适用上揉合了机构规则、当事人意志和仲裁庭意志,⑰没有给予仲裁地法任何直接适用的机会。国际商会仲裁院独任仲裁员在1970年对Dalmia Dairy Industry vs. 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一案中既没有考虑适用仲裁地国日内瓦法,也没有考虑适用当事人所属国法,而是在其所作出的中间裁决中指出:“国际商事仲裁应与当事人所属国法分离开来,且唯一地受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的调整,一旦当事人决定依据ICC规则进行国际仲裁以裁决争议,其后果是巴基斯坦法和印度法均不可能适用。”⑱
4.仲裁实体规则的“直接化”(voie directe)
按照学者对ICC仲裁规则第17条第1款的研读,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直接化”是指“仲裁庭完全可以直接采用其认为适当的法律,而不必去研究任何‘冲突规范’,不管这种冲突规范是国内法律还是其他。”⑲仲裁实体规则的直接化最大限度地剔除了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身份”因素,也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适当性。综观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局势,仲裁实体规则的直接化过程阶段性地表现为如下几个步骤:
(1)从单纯依靠仲裁地冲突规范转向综合考虑相关冲突规范。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单纯依靠仲裁地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已被认为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做法,它不当地将仲裁员类比于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国家法官,而“如果把仲裁员比做国家法官,受到法庭所属的国家和裁决权来源的国家的国际私法体制的绝对限制,这不是在强迫国际仲裁员睡‘Procrustean bed’吗?”⑳基于此,诸如ICC仲裁院等著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开始改变这一传统方法,他们倾向于“充分考虑和综合所有同争议有关不同国家的冲突规则。当这些相关的不同冲突规则都带来相同的结果时,仲裁员对这种方法尤其感到满意。”重叠适用相关冲突规范而非排他性地适用仲裁地冲突规范,这种被“国际商会最经常采用”的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方法为国际商事仲裁注入了“人性关怀的基调。”[21]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仲裁地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定位。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的“德伯沙治”法也能通过分化准据法所属国而导致国际商事仲裁属地联系的多元化和弹性化,从而以类似的方式弱化了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
(2)从综合考虑相关冲突规范转向运用冲突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在综合考虑方法下,尽管仲裁地国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约束得到解放,但在本质上它并没有彻底释放国际商事仲裁的属地依赖,它不过是以多国的属地身份来取代先前单一的仲裁地身份,属地联系的多元化只能弱化、但不能去除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归属,当国际商会仲裁员天才性地运用所谓“冲突法的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conflict of laws)来选择准据法时,国际商事仲裁真正“去身份化”的时代似乎已然来临。在ICC仲裁院1972年的2096号案件首次运用这一原则确定了争议问题的准据法,它以比较法为基础从各冲突法制中抽象引申出一些一般规则,并按照这些“统一冲突规范”来指引法律[22];该院随后于1977年第2585号案件再次运用这一方法,案件仲裁员通过裁决指出,根据“私法的国际观念”,该案合同关系重力中心地所属国的法律应当予以适用。[23]冲突规范的“一般化”进程悬搁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地域依赖,也抹去了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归属。
(3)从“一般冲突规范”范式转向“一般实体规范”范式。冲突规范的“实体化”不是国际私法领域中的辨证运动,而是特指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不再依靠冲突规范进行选择,而是直接确定某一或者某些实体规则作为案件准据法。这些被直接确定的实体规则之所以谓“一般”,乃是指其本身内容为各实体法体系所共享或者共有,于此处我们看到了世界共同体法的影子。国际商事仲裁抛开冲突规范直接援引一般性的实体规范裁决案件,这主要表现为通过当事人直接约定或者仲裁庭依据仲裁规则或直接确定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商人习惯法[24],以及适用一般法律原则两种情况。
在仲裁实践中,据统计,ICC仲裁院于1988-1998年期间作出的仲裁裁决有60多个适用了国际贸易惯例、商人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其中有9个案件当事人直接选择上述法律作为准据法,[25]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75年国际商会仲裁院裁决的案件2375/1975.,案件中的申请人是一个法国公司,被申请人是一个西班牙公司和一个巴哈马公司,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其为西班牙一个公共工程项目准备评价意见书的花费,仲裁庭拒绝采用合同标的所在地的西班牙法律来解释他们之间的一系列合同,仲裁庭认为西班牙的法律将不适用于调整当事人之间在操作前的谈判结果,或对工程做初步研究的准备责任。在这些情况下,仲裁庭认为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关系应该依据法律的一般原则和国际惯例以及习惯法而定。在国际商会仲裁先例中更显著的是,一些仲裁庭欣然地明确表示它们对案件的裁决没有参考任何国家的法律。作为这种最初的解放宣言之一的是国际商会案件1641/1969的裁决,在裁决中仲裁庭迫切地说明,当事人在它们之间的协议或通讯中都没有指出支配它们之间的关系或争议的国家法律。因此它们明确地给予了仲裁员自主权利来确定法律或者商务惯例以解释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认为使用贸易惯例在合同中是当事人之间一种明确的意愿或者是一种暗示。
在司法实践中,法国法院于1981年在Fougerolle vs. Banque du Proche Orient一案通过裁决认定,仲裁员应通过适用国际商业一般原则来正当地遵循自己的职责,因为它们也是法律的一部分;在1991年的Compania Valenciana de Cementos Portland S.A. vs. Primary Coal Inc.案件中,法国法院再一次裁决,仲裁员作出的终局裁决无须证明适用国内法的正当性,他可以适用被称作商人习惯法的原则和贸易惯例等规范体系。意大利法院于1982年在Topfer案中也表达了支持商人习惯法作为准据法的意见。[26]
由上可见,从一般性冲突规范向一般性实体规范转变过程中,由于一般冲突规范在指引法律时仍然需要把连接点属地化以确定特定的国家法律体系,这必然将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交付于该具体国家的法律裁断,而很多国家在立法中包括《纽约公约》也明确规定,仲裁所适用法律所属国对该仲裁裁决享有撤销权。换言之,按照一般冲突规范指引准据法情况,国际商事仲裁通常具有该准据法所属国国籍或者身份,而这一身份将为国际商事仲裁及其裁决设定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如果仲裁庭直接采取跨国规则、商人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等一般性实体规范裁决案件,则可以使国际商事仲裁避免落入准据法所属国的控制,规避准据法所属国的身份归附性,从而保障国际商事仲裁“去身份化”进程的彻底性。
(4)从“一般实体规范”范式转向“自由裁量”范式。如同一般冲突规范一样,仲裁庭采用一般实体规范能使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被完全抹平,因为一般实体规范在某一方面而言不是某一特定国家法,但是在另一方面而言也就是每一特定国家法,实体规范的“一般性”保证了它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均匀性”,它是从各国立法之中抽象出来的共通法,也是各国立法体系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就可以认为,依据一般实体规范进行的国际商事仲裁具有“全球通”的身份,它不具有某一个特定国家的身份,它身份的完全均匀化导致了就某一个国家而言的身份的“无化”,但是它却似乎具有每一个国家的身份,因此,在最抽象的意义上它没有完全达到整体“去身份化”。只有当仲裁庭在裁决案件的时候走向更为激进的“自由裁量”范式,国际商事仲裁的身份才能在法律适用环节被完全“裁量”掉,真正抵达彻底的“去身份化”。
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的自由裁量方法主要在两种情况下得以运用:一是授权友好仲裁;二是仲裁“无准据法之合同”。但二者并不必然排斥适用特定国家的法或者一般法律原则,只不过仲裁庭拥有更为灵活的选择自由和更为正当的选择权限,他们在裁决案件时甚至可以唯一地关注内心之“公平”、“善意”等抽象原则。ICC仲裁院3327/1981号案件阐述了友好仲裁的原理:“仲裁,就其本身而言,致力于与方便法院诉讼所追求之宗旨不同的目的。它以较少强调争议的法律性质而更多关注争议的技术性、心理性和商业性方面为特征。一项友好仲裁条款为仲裁员提供一项手段以限制争议的法律承担并优先考虑其他因素,它能因案情的变化而根据健全的商业政策确保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以避免僵性规则的适用。”[27]
“无准据法之合同”(contracts with no governing law)是鉴于下述情况而提出的概念,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赋予了当事人极大的选择自由,则“当事人能否走得更远以致于约定,他们之间的合同是自足的且无需受任何法律规则的调整?”[28]与之相关联的是“否定性选择合同”(contract with the negative choice ),[29]它是指当事人不需要任何法律规则对之适用的合同。不能将此类合同与适用一般性实体规范的合同相混淆,后者并不否认采取一定的规范作为合同准据法,而否定性选择合同与无准据法之合同则明示载明了当事人双方的“规则豁免”宣言;也不能将此类合同与因规避法律(Fraude à la loi)而导致选择无效的合同相等同,后者同样没有明确拒绝任何规则的适用。对此类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有人指出为了使当事人的意思有效,可以适用一般法律原则,但不必适用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内法。[30]笔者以为,当事人提交此类合同进行仲裁,同时又排斥任何法律规则适用的,可以合理推定他们是授权仲裁庭按照衡平原则进行善意仲裁,它是一种授权友好仲裁的间接表达式。不过与授权友好仲裁相比,否定性选择合同和无准据法之合同更加强调和突出法律适用的“去身份化”,它本质上包含授权友好仲裁以及追求仲裁自治“无身份化”效果两种意愿。
由上可见,仲裁的自由裁量范式下,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的“去身份化”才真正达到了极致状态,纯粹到了“无”身份。事实上,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抵达一般性实体规范阶段时就已经完成了“直接化”过程,于仲裁实践而言已然达到“去身份化”的法律效果,而自由裁量范式不过是实体问题法律适用直接化过程的高级发展阶段,在最抽象、最普遍的层面上升到了国际商事仲裁“无”身份状态。
5.仲裁裁决的“国际化”(tertium genus)
鉴于1958《纽约公约》是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制度“脊梁”,且该公约暗含仲裁裁决的内、外国之划分,因此赋予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以拟制的国籍实属必要。又鉴于各国立法模式多区分内外国裁决并实行非对等的国民待遇,在这一差别待遇的制度基础上,仲裁裁决身份问题的重要意义得以显现,它不仅象征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也暗示着在一国承认与执行时将面临何种待遇。当《纽约公约》确立起了仲裁裁决的非国内化趋势后,世界诸国多对非内国仲裁裁决采取较为优越的礼遇,这催化并助长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去本国化”的身份运动。某项仲裁裁决若能在各国都能取得非本国化的身份认证,这在理论上无疑使该仲裁裁决在全球均能通行无阻,获得最大限度的流通性,而这无疑是任何一个仲裁机构所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这为仲裁裁决的“去身份化”趋势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动力。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去身份化”的表现是裁决的“国际化”,tertium genus意指既非内国的,也非外国的仲裁,而是一种真正的国际性仲裁。按照M.R.Sammartano理解,[31]仲裁裁决的国际化主要通过主体标准、争议客体标准和程序标准进行判断:但凡争议主体国籍或者住所地位于不同国家者,他们之间产生的争议被提交之仲裁即属国际性仲裁;争议性质涉及国际商业者,其被提交之仲裁即属于国际性仲裁;仲裁程序法律适用发生上文提及之超国家性时,该仲裁即属国际性仲裁。
笔者以为,由于世界各国识别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身份主要依据裁决地国和程序地国两大标准,此外还包括仲裁员国籍国、仲裁实体法所属国、裁决书签字国,[32]以及仲裁机构所属国和当事人国籍国[33]等标准,因此,不同的标准下就会存在不同的“去身份化”的国际性仲裁裁决,而主要的表现形式是:
(1)裁决地国的“去身份化”。裁决地作为确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最主要的标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静态连接点,要去除裁决地国对仲裁裁决的身份制约,可通过裁决地的泛化、裁决地的中立化、裁决地的非法律化、裁决地的网络虚拟化等方式达到目的,并相应地表现为上文所述之多地/国仲裁、中立国仲裁、无主地仲裁、网上仲裁等。
(2)仲裁程序的“去身份化”。1958《纽约公约》也规定,仲裁程序所属国可依法撤销仲裁裁决。这表明仲裁程序对仲裁裁决的身份归属起着决定性作用。上文已经提及仲裁程序的“去身份化”运动,主要表现为仲裁程序法律适用的可选择性、意思自治性与超国家性,通过消弱乃至离弃仲裁地国对仲裁程序法律适用问题的影响,达到仲裁程序的“去身份化”,并最终斩断仲裁程序身份归属为仲裁裁决带来的身份定位。
(3)仲裁机构的“国际化”。以机构性质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这在我国尤其如此。我国仲裁相关立法就是按照仲裁机构的性质来区分仲裁裁决种类,即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这两类仲裁裁决均属于中国国籍的仲裁裁决。事实上,尽管学界和实务界倾向性地将裁决地国作为仲裁裁决的国籍国,但这是在仲裁裁决的撤销、承认和执行问题上采取的做法,在本质上将仲裁机构的性质决定仲裁裁决的国籍似更为合理,也更容易让人接受,凡是属于国际性的仲裁机构,其仲裁裁决为国际仲裁裁决,凡是属于国家性的仲裁机构,其仲裁裁决则为国内仲裁裁决。比如,当ICC仲裁院在上海作出仲裁裁决,或者CIETAC在伦敦作出仲裁裁决,按照一般的传统观点,前一个仲裁裁决属于中国裁决,后一个仲裁裁决属于英国裁决,但我们仍然习惯于将前者称为ICC裁决,后者则被冠名为CIETAC裁决,倘若我们采取仲裁机构性质决定仲裁裁决国籍,则ICC裁决属于国际性裁决;CIETAC裁决属于中国裁决。那么作为仲裁裁决“去身份”运动表现形式的则是国际性仲裁机构之仲裁。ICC仲裁院之仲裁裁决典型地属于国际性的仲裁裁决,它依附在拥有遍及世界近一百五十个国家的会员和六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委员会的国际商会下,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性民间。同样地,国际体育仲裁院(ICAS)作为一个国际性的仲裁机构,其仲裁裁决当属国际性仲裁裁决,摆脱了裁决身份的国家依赖,这典型地表现在Rague vs. Sullivan案件中。该案中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撤销了将位于悉尼的Lausanne作为仲裁地的裁决,其法律后果是否认悉尼法院具有撤销仲裁裁决的管辖权,尽管该仲裁完全在悉尼进行。针对这一案例,学者评价认为:“新南威尔士上诉法院开创了一个辉煌的先例,并有助于GAS建立一个符合体育全球化需要的国际性争议解决机制。”[34]
(4)仲裁裁决撤销令的非对世性。仲裁裁决撤销令的非对世性是指,仲裁裁决地国或者仲裁程序所属国,裁定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该裁决并不必然具有普及效力,其他国家可独立地判断并自主决定是否承认和执行该已经被撤销的仲裁裁决。有学者称作“仲裁裁决执行程序相对于撤销程序的自治性”。[35]一般而言,于一国作出的仲裁裁决并不当然在其他国家具有法律效力;类似地,一国撤销某项仲裁裁决在逻辑上也并不当然在其他国家具有法律效力,除非存在有约束力的国际立法作出这种要求。尽管1958《纽约公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种普及主义,即仲裁裁决一旦被裁决地国或者裁决所依据之法律所属国撤销或者中止,其他国家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但是以法国为典型的国家仍然持守仲裁裁决撤销令的属地主义效力,A.J.Van den Berg先生曾经戏言,即便仲裁裁决被撤销,当事人还是可以到法国去寻求救济机会[36]。巴黎上述法院于1993年4月12日在Sté Unichips Finanziaria vs.Gesnouin一案裁决中指出,执行仲裁裁决的法院可以适用内国程序标准来决定可仲裁性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只要这些标准比《纽约公约》更为宽容。[37]一国尽管能够通过否认仲裁裁决原产地国(state of origin)发出的仲裁裁决撤销令具有普世性的方式来确立自身在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方面的司法独立性,但如果走得太远则很可能陷入所谓的“Hilmarton噩梦”,[38]同时承认和执行两个相互冲突的仲裁裁决。
坚持仲裁裁决撤销令的非对世性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去身份化”运动的重要表现,它的内在逻辑是: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经作出就不受制于任何国家,不隶属于包括仲裁地在内的任何国内法律秩序,它在某国被撤销本身并不是导致内国不予承认和执行该裁决的依据,内国承认和执行与否唯一地取决于自己的独立判断。W.L.Craig先生从反面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非内国仲裁和无国籍裁决并没有得到各国广泛接受;裁决被撤销后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其他国家也不应执行被撤销的裁决。[39]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及Ghent University在站博士后。本文为比利时根特大学博士后研究课题《国际商事仲裁的案件管理》的阶段性研究成果(This paper is the partial achievement of Case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hich is post-doctoral research project in Ghent University)。
①Gary B.Born,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99,P.192.
②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196.
③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e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225.
④see U.K.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Proposed Clauses and Schedules for an Arbitration Bill,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10),1994,p.227.
⑤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5-97页。
⑥以上介绍详见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218,236.
⑦该案涉及包含在一个国际商事代理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效力认定问题,该国际商事代理协议明确地依据法国1958年出台的一个调整商事代理关系的法令而签订。被告辩称,依据当事人双方选择的法国法之规定,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因为法国法禁止商人与非商人之间缔结仲裁协议。巴黎上诉法院于1970年裁决中拒绝采纳被告的答辩意见,强调指出“无论当事人选定的法国法规定如何,双方当事人仍然有权在未经法国国内法授权许可的情况下缔结仲裁协议。”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p.215-216.
⑧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⑨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584.
⑩CitedP. Sanders,hommage a frÉdÉric eisemann 39 (ICC Publication No. 321, 1978). For confirmation by French courts that 1CC arbitral jurisdiction is not ousted by mere allegations that performance of some of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were contrary to French exchange controls,the decision of theJune 1956, Société Le Gant Nicolet v. SAFIC, 1957 rev. ARB. 14.
⑪W.Laurence Craig,William W.Park and Jan Paulsson,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rbitration,3rded.Ocean Publications,INC./Dobbs Ferry,NY.P.161-167.
⑫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⑬刘想树著:《中国涉外仲裁裁决制度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⑭高菲著:《仲裁法和惯例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⑮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485.
⑯有人就认为,ICSID仲裁程序的特征性元素为它相对于任何法律体系的自足性(self-sufficient)。See Bernardini,CIRDI,Il punto di vista dell’investitore(ICSID,The investor’s point of view),Rass.Arb.,1982,P.46.)和临时仲裁,其仲裁程序规则的适用几乎是当事人之间的完全“生造”或者参照适用。(如ICSID公约规定,仲裁程序规则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情况下则适用公约规定;《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uropean Energy Charter Treaty)第26条规定,如果投资者希望根据条约进行仲裁,他们可以在ICSID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规则以及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规则等三套仲裁规则之中进行选择。
⑰国际商会仲裁程序规则体系有严格的等级序列,国际商会仲裁规则优先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没有规定的,依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仲裁庭自决,仲裁庭可以(着重号为笔者所注)决定援用某国的程序法。See Michael E.Schneider,The Terms of Reference:The New 1998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Proceeding of the ICC Conference Presenting the Rules,in the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Specially Supplement,ICC Pub.S.A.,1997,P.42.
⑱该案案情是,申请人印度公司Dalmia Dairy Industries Ltd.与被申请人巴基斯坦的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就他们签署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发生争议,被申请人主张仲裁协议的效力应受巴基斯坦国法调整,其请求被仲裁员驳回。See Dairy Industries vs. 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ICC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980,vol.V,p.174.
⑲W.Laurence Craig,William W.Park and Jan Paulsson,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rbitration,3rded.Ocean Publications,INC./Dobbs Ferry,NY.P.320.
⑳Pierre Lalive,1976 rev. arb. PP.155-159.另Procrustea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怪人,他把不符合他睡床长度的旅客要么削去过长的腿,要么拉长他们的身躯也满足床之长度。
[21]汪祖兴著:《国际商会仲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7页。
[22]这是当代欧洲大陆比较国际私法学派的显著特征,他们特别强调采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各国冲突法制度的异同,并从中抽象出一些能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新的冲突规则,从而达到各国冲突法的统一。详见李双元等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3]上述两案例详见ICC Case 2096/1972和ICC Case 2585/1977,引自Y.Derains,Case Commertary,1978 JDI 998.转引自W.Laurence Craig,William W.Park and Jan Paulsson,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rbitration,3rded.Ocean Publications,INC./Dobbs Ferry,NY.PP.327-328.
[24]Lando指出,商人习惯法的运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无规则司法性过程,也不是一个严格规则司法性过程,更准确而言是一种半规则性、半选择创造性过程。See O.Lando,The Lex Mercatoria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Int.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ly(34),1985,p.747.
[25]Fabin Gelinas,Arbitrat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17(4),2000,p.122.
[26]上述三案例详见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P.443-444.
[27]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837.
[28]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799.
[29]L.Hjerner提出这一概念,详见其著作:Choice of Law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Arbitration in Sweden,Yearbook of 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Stockholm 1982.
[30] Philippe Fouchard,Emmanuel Gaillard and Berthold Goldman,Fouchard,Gaillard,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96.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p.801.
[31]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p.40-46.
[32]赵秀文著:《国际商事仲裁及其适用法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9页。
[33]谭兵等著:《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
[34]该案案情是:澳大利亚柔道协会提名Angela Raguz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参与奥林匹克52公斤以下女子柔道比赛。Rebecca Sullivan作为澳大利亚同一级别的女子柔道成员对这一提名向柔道协会内庭提出异议,失利后Sullivan转而依据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但不是依据CAS特别仲裁分庭仲裁规则上诉到CAS。案件由位于悉尼的、与CAS的Lausanne办公室相关的CAS大西洋登记处管理。三人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全部都是澳大利亚人,仲裁开庭也是在悉尼进行。仲裁庭裁决支持Sullivan,这使Raguz依据1984年《新南威尔士商事仲裁法》向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申请上诉令,要求将案件提交给上诉法院以撤销CAS作出的仲裁裁决,上诉法院于2000年9月1日作出了上述裁定,否认了自己具有撤销CAS裁决的管辖权。See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Issues of fast-track dispute resolution and sports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p.20-22.
[35]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p.926-930.
[36]see Eric A.Schwartz,A Comment on Chromally Hilmart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3),1997,p.125.
[37]Mauro Rubino-Sammartano,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2000,Aspen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 P.925.
[38]see Hamid G.Gharavi,A Nightmare Called Hilmarton,转引自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39]转引自赵秀文著:《国际商事仲裁及其法律适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责任编辑: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