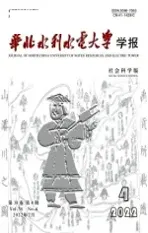司法过程中事实的动态理论界定
2012-09-11孙日华王晓东
孙日华,王晓东
(1.石家庄经济学院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2.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民一庭,北京100035)
司法过程中事实的动态理论界定
孙日华1,王晓东2
(1.石家庄经济学院法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2.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民一庭,北京100035)
在司法过程中,事实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事实”这一概念在现实中被广泛地运用,又增加了我们获得清晰认识的难度。学界从很多角度对事实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力量分散且“专业槽”问题严重。然而,对于司法最有价值的分类,应该是按照事实在司法过程中的动态运行,分为客观事实、案件事实和裁判事实。并且在不同的法律主体参与之下,形成不同的事实范式。
司法过程;事实;动态;范式
一、事实的概念
“事实”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着“事实”的概念,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说法:
第一,事实是客观的存在。即事实是先于人并不依靠人的一种客观存在,其与人没什么关系,其完全不受人的影响就可以完整地存在于世界之中。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情况,是不含有人的认识因素的自在之物,其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罗素就曾如是说:“我所说的‘事实’的意义就是某件存在的事物,不管有没有人认为他存在还是不存在……大多数事实的存在都不依靠我们的意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作‘严峻的’、‘不肯迁就的’或‘不可抗拒的理由’。”[1](P105)
第二,事实是对客观存在物的某种感觉、知觉、意识以及判断。罗素就认为:“当我们谈到一个‘事实’时,我不是指世界上的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指某种性质或者某些事物有某种关系。因此,我不把拿破仑叫做事实,而是把他有野心或者他娶了约瑟芬叫做事实。”[2](P39)也就是说事实是对“事实存在”的一种“事实判断”。
第三,事实是世界的总体。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其对事实和事物进行了区分,认为“原子事实就是各客体的结合,对于物来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原子事实的构成部分”[3](P25)。
总之,关于事实的更加细致的定义还有很多,上述三种比较有代表性。从中可以归纳出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事实”。
第一,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事实就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其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此时的事实就是一种社会的客观存在,是自在之物。因此,事实就是存在,包括社会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静止的事物与动态的行为、生活状态等。罗素说:“事实是不论我们对之持什么样的看法而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东西。”[4](P219)
第二,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事实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判断。此时,事实与主体的认识活动密切相关,是主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事实的认知。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就成为了主体实践和认识的结果,实际上是把事实等同于对事实的认知[5](P76)。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之中包含了判断性因素,也可以说是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也确实是这样的,“自然存在”如果没有进入人们的认识视野,那对人类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说“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6](P145)。
相比较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认识论意义上关注的事实是在实践中人们对客观存在的反应,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事实既具有客观性,同时也具有主观性。因此,事实必须是人们能够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所能观察到的,并且由主体做出判断并且陈述出来,一切事实都是经验事实。事实是客观与主观、经验与理性的统一,毕竟任何事实都离不开人们的主观判断[7](P175-176)。这样,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解释了进入人类视野的事实的真实状况。然而,进入法律领域的事实又该是哪种事实呢?
杨建军博士认为进入法律职业者视野的事实,排除了静态的自在之物这一静态事实,即它应当是一种动态的社会事实,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自然存在和人际实践都会进入法律调整的范围[8](P23)。因此,静态的本体意义上的事实是无法进入法律视野的,但是一旦事实进入了人的认识活动的领域,就有可能成为法律调整的事实。即使是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实,也不一定具有法律意义,比如正常的吃饭、睡觉、约会、聊天等,几乎不会受法律的影响和调整。因此,在法律上有意义的事实主要是那些受法律调整的事实,其无法涵盖社会的所有事实。
二、事实的分类
不管怎么样,学界对于事实的分类还是存在着动态的倾向,即在事实、证据和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中,进行事实类型的划分。也就是说在司法领域的事实都表现出事实外延不断地缩小,事实与司法裁判的距离越来越近,对事实的研究越发深入。
从现行的法律实践角度出发,主要存在着客观事实、法律事实的划分。在立法上,由于我国强调证明标准的绝对化,在法律上就做出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标准。我国司法中比较崇尚对客观事实的不断追求,而法律事实不同于客观事实,但是仍然具有客观性,同时还具有规范性的特点。按照学界普遍的分类标准,即是否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法律事实分为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这也基本上是国内大部分教科书上的分类方法。
舒国滢教授在其《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将事实分为客观事实、事实范式、和裁判事实。从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三个方面分析了客观事实,客观自在的事实、作为认识对象之自为的事实以及作为命题陈述内容的事实。事实范式指规范所规定的事实类型。裁判事实就是在个案裁判中确立的事实。其中,裁判事实与客观事实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但是客观事实规定了裁判事实的真实性维度。在裁判事实与事实范式的关系中,裁判事实是经由事实范式对案件事实涵摄之后确定的事实,事实范式规定了裁判事实的合法性维度[9](P280-294)。
葛洪义教授将事实分为法律规定的法律事实、能够被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客观事实。法律规定的法律事实指的是具体法律规范预先设定的作为适用规则所必须的事实条件;能够被证据证明的事实是法律人用于支持自己主张的事实,必须有合法的证据可以证明,但不是一般的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就是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们认识的对象[10](P144-147)。
陈林林博士区分了作为裁判依据的裁判事实、当事人陈述的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以及无法再现的(客观)事实。陈博士论述较多的是进入规范视野的事实,并将其分为两类:一是能够与规范建立一一对应的常规事实,即事实与规范可以直接等置;二是无法与规范建立一一对应的非常规案件。即分别为简易案件与疑难案件[11](P74-76)。
毛立华博士将事实分为生活事实、案件事实、裁判事实和法律事实。其认为生活事实、案件事实和裁判事实是逐步发展的结果,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并认为案件事实和裁判事实共同构成法律事实[12](P10-11)。
郑永流教授曾提出过事实分类与发生过程的图示,如图 1 所示[13]。

图1 事实分类与发生过程图
郑先生认为小前提的发生是由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由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的两个层面。其认为建构裁判的小前提,首先就是生活事实是否需要获得法律评价,即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然后再依靠证据去证明生活事实是否存在,即从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其认为从生活事实到法律事实是评价或者归属的问题,即生活事实是否符合法律构成。由法律事实到证明事实是求真的证明问题,即生活事实是否存在,被证明存在的事实就是证明事实,事实真实既可以通过物质证据也可以通过言辞证据得出。我以为郑教授图示中要表达的也是从生活事实向裁判事实转化的过程,但是他没有用这样的名称。这个图示和相关论述中,主要是以法官为主导进行事实的认定,当事人的参与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另外法律和证据的细微过程和作用没有获得足够的表达。应该根据动态的过程作一个更细致的图解。
以上这些关于事实的分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司法视野下进行动态的分析。还有很多学者依据这样的规则对事实进行类似的分类,区别就在于名称上和切入的角度稍有不同而已。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对事实的分类更应该是动态意义上的,以此反映不同阶段事实的形态,并能够充分地展示事实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因此,我对事实的分类也是设定在司法过程之中,通过在事实与法律之间不断地往返,形成事实不同的类型,这样的分类对最终的司法裁判将更加有针对性。
恩吉施将建构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分为三个步骤:具体的生活事件,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案件的想象;该案件事实确实发生的确认;将案件事实根据法律构成要件作出评断。恩吉施的思路也是一种动态思路,简化为:想象——确认——评断[14](P52-54)。笔者以为事实经历以下过程,事实的发生、进入人的视野、进入纠纷诉讼活动、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法律与事实是在不断互动中形成的。
笔者以为在司法裁判中所认定的事实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在法律程序中形成的,是法律与事实不断来回往返中形成的。因此,笔者将事实分为三种主要形态,分别为客观事实(也可以称为生活事实或者原初事实)、案件事实和裁判事实。客观事实就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发生的事件情况,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本体意义上的事实存在。案件事实就是在生活事实中抽离出来的,希望进入法律视野,尤其是司法视野的事实,或者可以叫做涉案事实。案件事实的形成主要是在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推动下,运用法律中的事实范式做出比较模糊的判断,认为某些事实可能需要进行法律调整,因此就将其诉至法院,就形成了案件事实①笔者在此将纠纷做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民事纠纷,也包括刑事诉讼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而且,此处所说的当事人是为了表达上的便利而使用的,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公诉案件中——当事人的概念就需要用公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来代替。。在此适用模糊的事实范式是因为当事人是无法决定最后涉案的事实情况和法律后果的,其只能根据相对模糊的法律观念和知识作出判断。案件事实进入法院后,在当事人广泛运用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主导法庭的审判,对案件事实进行精细化的调查和法庭辩论,依据法律规定的事实范式认定(建构)裁判事实(adjudicative fact),并最终作为司法三段论推理的小前提,并表现在法律文书之中。
三、事实与法律的关系
在司法过程中总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从广义上来讲,事实和法律既存在着分离,也有着无法分离的密切关系。
事实只有进入了法律的视野才可能与法律发生关系,否则其与法律是分离的。事实是事情的真实情况,更强调真实性;法律表现为行为的规范和评价,更强调价值判断。事实有时候可以通过感官就可以认知,但是法律通常需要运用理性的推理或者解释。事实经常是丰富多彩的,呈现多元的形态;法律却是相对单一和固定的。在通常的法律推理中也将二者做了区分,即大前提和小前提。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分类,但是将法律与事实“截然划分却不是到处都有的”[15](P83)。
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然而世界上存在着多种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模式,比如道德、宗教、礼仪等。自然事实如果没有进入人类活动的世界,就完全不会受人类社会调整方式的约束。社会事实也只有一少部分进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因为很多社会事实,包括很多纠纷都可以依靠其他社会规范进行约束和解决。就是在这些事实进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后才与法律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对法治形成了基本的共识,整个社会开始进入法律调整的时代,而且有运用法律格式化社会生活的趋势。因此,事实与法律发生关系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一切问题都可能成为法律问题。在中国,也同样经历着法治理想的洗礼,法律宣传、送法下乡,法律正在格式化这个社会,事实的调整方式正在逐渐单一化。事实与法律的关系也将在法治现代化的历程中越发密切。
从法律角度而言,法律的基本构成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行为模式就是对事实的一种抽象概括,将社会事实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法律中形成了类型化的事实模型,增强事实范式的广泛适用性。法律后果就是对类型事实进行评价,这部分也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从事实角度而言,在司法活动中事实时刻都要受到法律的影响。在法庭上法官需要根据法律对案件事实进行审判,结合证据最终决定具有法律意义的裁判事实。比如,真实存在的借贷关系,但由于超过了诉讼时效,虽然借贷关系是案件事实,但是依据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其也无法成为最终的裁判事实。“任何一个概念不但具有排除事实的能力,而且具有组织其他事实的能力。”[16]
法律规范中规定了事实的范式,但是这里的“事实”是应然的事实,凯尔森就从实证主义分析的立场指出,法律规范是一种“应当”的表述,既不意味着某一其他人表示意志要求他或者命令他这样,更不意味着他实际就是这样行为[17](P37-39)。这样抽象的、一般的规范中的事实范式与具体的、个别的行为和事件总是存在着距离。学界一般将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这些行为或者事件叫做法律事实。笔者在本文中并没有使用法律事实这一概念,而是使用案件事实这一概念,以此来区分法律规范中的事实范式和司法最终认定的裁判事实。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中的事实范式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同的对应关系决定了司法裁判的难易程度。如果案件事实能够与法律规定的事实范式建立对应关系,可以直接进行等置的案件,就属于简单的常规案件。如果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的事实范式无法建立对应关系,不能直接等置的案件就属于疑难案件。疑难案件中,法律规范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如规则的模糊、漏洞、不确定等。因此,可以发现法律规定中的事实范式也是永远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案件事实的,更不用说生活事实了。
司法活动过程中,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如影随行的,对法律和事实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也决定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在英美法系,主要由当事人对事实问题进行主张和举证,法官相对比较消极地听取双方的意见。事实的认定主要交给陪审团,法官主要负责法律问题的认定。但是,二者的认定也不是绝对的,陪审团也需要对事实进行法律考虑,比如有罪无罪的衡量标准就肯定是需要依照法律或者先例的。同样,法官也不是单纯地只从法律角度做出判断。大陆法系国家与之不同,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事实也主要由当事人提出,但是法官有为了查清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的权力。法官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都有最终的决定权。
总之,在司法视野里法律与事实的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更多的是两者交织在一起。进入司法领域的事实总是需要获得法律的约束和评价,事实的提出与证明要以实体法的规定作为价值追求,同时要严格服从程序法的规定,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正义的答复。
[1][英]罗素.人类的知识[M].范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英]罗素.我们关于外界世界的知识[M].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3][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英]罗素.逻辑与知识[M].范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孙伟平.事实与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7]雍琦.法律适用中的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杨建军.法律事实的解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9]舒国滢,王夏昊,梁迎修,等.法学方法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0]葛洪义.法律方法讲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1]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司法论证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2]毛立华.论证据与事实[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13]郑永流.法律判断大小前提的建构及其方法[J].法学研究,2006,(4).
[14][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J].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5]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6]苏力.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中[J].法律科学,2000,(3).
[17][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刘 明)
Abstract:In the judicial process,the fact is a complex concept.“Facts”in reality is widely used,and add difficulty for us to have clear understanding.Academic study the fact from the wide view,and have problems of scattered forces and“professional groove”.However,for the judicial process most valuable classification,it should accord to the facts in the dynamic judicial process;it is divided into the objective facts,the truth of the case and the referee facts.And under the different legal body participate the judicial process,concept forms different facts paradigm.
Key Words:the judicial process;facts;dynamic;paradigm
The Dynamic Theoretical Definition on Fact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SUN Ri-hua1,WANG Xiao-dong
(1.Law School,Shijiazhua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Shijiazhuang 050031,China;2.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Court,Beijing 100035,China)
D910.1
A
1008—4444(2012)04—0130—04
2012-04-2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期裁判客观性问题研究》(12YJC820092)阶段性成果
孙日华(1981—),男,满族,河北承德人,石家庄经济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