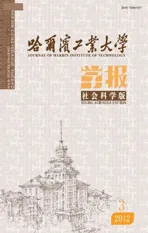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
2012-04-08高其才
高其才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与能动司法
高其才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建设和完善中国的司法体制必须以当代中国社会特质为基点。社会的司法变革、完善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能动司法为当代中国司法界的热门议题,对之需要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需要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质、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能动司法与民众的司法期待和司法需求基本相契合,根植于中国固有社会的司法传统,但是能否成为中国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内涵,尚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中国;社会特质;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能动司法
引 言
司法是运用法解决个案纠纷、将法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在近代的司法从行政等制度中分离出来之前,“司法”远非一种独立地解决纠纷的形态和制度。我们能够发现不同形式的“司法”:它可能是民间性的调解、仲裁活动,也可能是以国家暴力强制为后盾的官方行为[1]。近代司法的概念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以及分权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司法既是使书本上的法落实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中的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法进行宣示、使民众形成具体的法认知的过程。司法所担负的功能,除了将社会纠纷消解在法程序之中外,还负有适用法、发展法的社会职能,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法治的关键在于法律的实施和实现,司法使法有了真正的意义。
认识司法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司法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决定中国司法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制约中国司法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司法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基本价值,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因此,应当探寻司法中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特质,通过社会认识司法;同时,也要通过中国司法理解中国社会、认识中国社会。司法解决社会纠纷、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司法在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于2009年8月提出能动司法问题①2009年8月27—31日,就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更好地发挥司法职能作用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江苏南京、泰州、无锡、苏州、常州等地调研时提出了能动司法问题。王胜俊强调,能动司法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各级法院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涉及司法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积极作用,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他提出一要调整理念,增强能动司法的自觉性;二要调查研究,增强能动司法的前瞻性;三要健全机制,增强能动司法的有序性;四要有效服务,增强能动司法的针对性;五要提高能力,增强能动司法的规范性。参见贺小荣《王胜俊: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必然选择》,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9月1日。。此后,能动司法成为当代中国司法界的热门议题①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对能动司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作用空间和能动领域、程度和限度等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坚持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是时代对司法的新要求、人民对司法的新期待,是司法权的本质属性以及司法的运作规律所决定的;能动司法坚持把法院工作放在国家工作大局中去谋划,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要积极发挥诉讼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争取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要充分发挥司法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的政治作用;能动司法需要高度重视司法自律和自限。参见江必新《能动司法:依据、空间和限度》,载《光明日报》2010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认为,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司法权的行使才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活跃。司法能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司法权运用的被动性和中立性等司法应当恪守的规律。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能动不是盲动,司法能动不能恣意妄为,司法权不能无限膨胀。司法能动应该有其坚守的边界和分际。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行使法定的职能,制定相关的措施。参见沈德咏《司法能动不能盲动必须坚守法律边界》,载《法制日报》2009年7月28日。关于能动司法更全面的讨论,可参见罗东川、丁广宇《我国能动司法的理论与实践评述》,http://www.court.gov.cn/fxyj/spllyj/mssf/201002/t20100223_1624.html,2010 年4 月11 日最后访问。,本文拟就能动司法问题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法治实践等方面进行思考,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特质、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探讨。
一
就整体而言,中国固有的社会特质为乡土性。乡土社会是农业社会的一种形态,民众主要靠农业谋生,世代定居,安土重迁。世代传承形成了“熟悉”的社会,礼俗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家族承担着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功能,家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2]。
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有规划的变迁”的推进、乡土社会内生力量的推动和外生力量的催化,乡土社会也在变迁之中。随着国家“制度下乡”②“制度下乡”所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以及税费改革、土地制度和计划生育等新的外生制度,这揭示在“新乡土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中,运用“制度下乡”的生成、整合和激荡推动其向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参见洪建设、曾盛聪《制度下乡:建构“新乡土中国”路径依赖》,载《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策略的逐步实施,乡村社会的格局出现了“文盲乡村向文化乡村、差序格局乡村向辐射开放乡村、长老政治乡村向民主政治乡村”演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一个变迁的趋势,乡村社会秩序的现代转型远非易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的社会事实是农民依附于土地,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也使农民很少有改变身份的机会;这种体制同时还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瓦解了而是保留甚至强化了乡土社会的一些特性。一些研究者发现,在无论哪一种集体形式当中,家族制度的许多基本内容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父系的财产继承、从夫居、男性为主的家庭生活方式等等。
虽然乡土社会一直是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仍在变化之中,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它消逝。近年出现的意义重大的乡村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而是造就了一批“半工半农的村庄”。换言之,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乡土社会”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辨,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考察问题的背景[3]。从全国范围来看,完成了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只是少数城市地区,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转型初期的乡土社会,仍然体现了“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在这样的熟人圈子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除非不得已是不会撕破脸皮的,遇有纠纷矛盾往往相互谅解、忍让、调解,通常不会动不动就到法院打官司,先还得走民间程序自己内部解决,实在不行再说。因而现阶段的中国司法具有乡土司法特点。
当然,社会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导向和民主政治的一定发展使农民的角色发生一些变化,民众之间发生纠纷后,单纯依靠礼俗、民间习惯法进行自忍、私了的情况逐渐减少。集体、单位对社会的控制功能呈弱化趋势,个体的自主性开始逐步展现,家族、村落的意识进一步淡化,民间权威逐渐趋向多元;基层政府机构对乡村的管理功能在弱化,社会自治组织的社会调控功能也在重建之中。民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发生的纠纷、矛盾,自身解决不了的,大部分情况下还会诉之法院。
从这一角度认识,能动司法的提出是有社会基础的,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是一致的。中国司法是孕育和根植于当地中国固有社会这一特定土壤中的,由职业化而又具大众化特征的法官解决纠纷、处理争端;在与当地民众长期互动的过程中,法官日积月累形成了司法经验和解纷智慧;司法吸收传统乡土社会司法中的有利因子,并使其与形式上的现代制度兼容,以便符合民众的心理和需求;在解决纠纷时,法院注重与纠纷当事人、纠纷相关人和社会的交互讨论,通过多种形式的沟通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法官通过简便灵活的方式去亲近民众、方便民众,增强民众对于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4]。
能动司法强调立足国情,坚持走专业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道路;要求通过已经建立的民意沟通机制,广泛吸纳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为调整司法政策、弥补法律漏洞、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提供第一手资料;将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确定人民法院工作思路的重要依据。这与民众的司法期待和司法需求基本相契合,符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发展状况。
二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法律方面也形成了独树一帜、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华法系,而关于解决纠纷的司法、审判的观念和制度为其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①蔡枢衡先生认为:“从历史上看实际是先有裁判,然后才有裁判规定标准的刑法,最后才有为正确适用刑法服务的司法制度。”参见蔡枢衡《历史上定罪和处刑的分工》,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司法、审判的观念和制度也概莫能外。中国固有的社会基本特质为伦理社会,司法、审判方面相应地表现出伦理传统,②这种“伦理司法传统”也包括黄仁宇先生反复提及的“以个人道德之长来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的状态。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页。具有伦理指导、皇帝专权、实体优先、多元依据、“无讼”以求的特点[5],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司法。
中国固有社会司法、审判方面的伦理传统主要体现在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等方面。对此,中国古代思想家、法律家进行了广泛的阐述。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治”思想,把恢复和保卫周礼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对“礼崩乐坏”的局面深恶痛绝,要求各个诸侯“以礼让为国”,要求各阶层人士“克己复礼”,同时以仁充实礼的内容,将礼美化成为一种最完善的伦理原则和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为国以礼”、“礼其政之本”(《论语·先进》)等语,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盐铁论》在论述“《春秋》决狱”、引经断狱时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王充也进一步分析道:“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贳故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论衡·答佞篇》)实际上,司法、审判官吏特别是中央、省等司法、审判官吏不必为法律条文所约束和限制,而应发挥其自由裁量的权力。汉代的晁错认为,在执法、司法问题上不应囿于法律规定本身的限制,而是要求当政者按照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灵活地运用法律工具,从所谓“人情”出发,“情之所恶,不以强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他认为如果“合于人情”而后执法,“本于人事”而后“动众使民”,那么“天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百姓和亲,国事安宁,名位不失,施及后世”(《汉书·晁错传》)。而这些都在于“明人情终始之功也”,这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唐律》“一准乎礼”,将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在法律中,并成为重要的司法、审判原则和具体的法律规范。在司法机构设置、法吏的作用与责任、证人制度等方面,更是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明代王守仁也主张不要一味拘泥于死规定:对那些“据法在所难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之人,要根据具体情况,情、法两相衡量,判处适当的刑罚。这样做,就能既容于法理,又不至有失众论。至于对那些“闻变即逃,莫知讨贼之义”,有弃职之罪的官员,则根据“情罪轻重,通将各官究治如律,虽或量功未减,亦必名示惩创,庶有作新之机,足为将来之警”(《王阳明全集·收复九江南康参失事官员疏》)。这样既合于法,又合于情。只有情理并容的赏罚,才能称为适当的赏罚。当理与法二者不能兼顾时,要以理为重。“法虽若屈、而理补未枉”的处罚,也是可行的。可见,中国固有社会赋予司法、审判官吏以较大权力,具体处理复杂的案件,灵活解决社会冲突,通过司法、审判官吏的主观努力实现公正的司法目标。
由于“法之设文有限,民之犯罪无穷,为法立文,不能网罗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与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春秋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疏叔向之言》),因此在律无正文的情况下,中国古代社会又允许审判官依例定案或成案以附,类推定罪。汉有决事比、唐有条格、宋有编敕、明清有例,以例补律,使法律能不断适用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晋律规定:“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晋书·刑法志》)北魏也要求“律无正条,须准傍以定罪”(《魏书·礼志》)。中国古代社会刑事审判既不是严格的罪刑法定,也不是绝对的罪刑擅断,判决的作出要求依律,无律则依例,判例这种成案具有重要的参考甚至援引价值,强调重罪案件要依法裁判。民事纠纷的解决则律、例、礼、情等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③以南宋为例,除个别拟判外,现存南宋书判中引述法律依据的共159件,涉及法律197条(内容重复者不计),其中律(即《宋刑统》)文46条,敕27条,令20条,格1条,随敕申明10条,使州约束2条,乡例6条,形式不明的85条。在这类书判中,裁判结果与法意一致的89例,占56%;与法意不一致的54例,占34%。书判中未引述法律依据但可以考详的共61篇,其中裁判结果合乎法意的22例,占36%;不合法意的38例,占62%。以上这两大类书判共220件,裁判结果与所引或所考法律依据一致的111件,占总数的一半;与法意不一致的92件,占42%。可见法律的作用不可忽视。此外,法律依据未被引述且已不可考而以其他理由裁判的书判共有156篇。参见王志强《“名公书判清明集”法律思想初探》,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说:“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6]
中国古代社会以“和”为司法、审判的根本目标,纠纷解决中以和为贵、以礼为准,广泛运用调处方法结案息讼即为突出特点。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无讼”、“息讼”观念的影响,自秦汉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对民事案件和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广泛运用调处方法结案息讼。诉讼内调处和诉讼外调处是中国古代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现象,调处结案也是中国古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调处的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审判机构调处、乡保调处、亲族调处和乡邻调处等。宋代的真德秀在潭州发布的《潭州谕同官咨目》,即向属官强调听讼之际,要重视调处,“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真文忠公文集卷四〇》)值得注意的是,受自古以来圣哲追求“无讼”理想和体现爱民风范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有些司法、审判官吏即使断狱也不立案。如《隋书》记载牟州刺史辛公义“受领新讼,皆不立文案,遣当直佐僚一人,侧坐讯问。”(《隋书·辛公义传》)再犯立案,也是导民劝善的一种手段。更有三犯才定罪的。裴政任襄州总管,民有犯罪者,阴悉知之,或竟岁不发,至再三犯,用户因都会时,于众中召出,亲案其罪。由此而“令行禁止,小民苏息”;“不修囹圄,殆无争讼”。(《隋书·裴政传》)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审判以彻底消除冲突、彻底解决纠纷为最终目标。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审判的观念和制度在法与情、常与权、名与实等方面统一、协调的努力,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司法、审判的观念和制度的平衡、综合的特色。
人类从事每个时段的司法实践,都需要以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为基础,都需要借鉴有关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司法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司法形成和转变的历史,就在于其与现实有着复杂的关联,可以为现实提供资鉴。通过历史能够清晰观照当代中国司法的现实。
就能动司法的基本内涵而言,能动司法根植于中国固有社会的司法传统,对中国固有司法的伦理传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尊重。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为人民的司法;能动司法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理、情的有机融合,慎重平衡各方主体利益;能动司法要求通过审判、执行工作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人民法院工作的全过程;能动司法强调继续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对案件的处理能够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能动司法在司法的职能方面有一定延伸。能动司法在古今关联中继承了中国固有社会优秀的司法传统,汲取了一定的精神营养,总结出了某些规律性的认识。
三
从近现代中国的法治实践反思能动司法,可能另有一种启示。法治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在追求经济自由、追求政治民主、反抗封建专制过程中提出的思想和逐渐建立的制度。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就治理主体而言,法治是多数人之治;就治理对象而言,法治是管制公权之治;就治理工具而言,法治是良法之治;就治理手段而言,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治理形式而言,法治是客观之治;就治理目标而言,法治是保障自由之治。与神治、人治不同,法治是一种共治、自治[7]。
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进程,中国也在固有法制的基础上开始了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历程。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外发型法治建设的模式,是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一种自我选择,是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外力的影响下制度建立在先、观念变革在后。从清末的法制改革、辛亥革命的法制实践、北洋军阀时期的法律活动、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的法制、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中国建设法治的过程中,理念和制度方面基本参考、借鉴和移植西方法治。现代法治强调“人民主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通过法律严格限制公权以保障私权。孟德斯鸠精辟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为此,他提出了权力分立理论,认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①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其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一种他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参见[美]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他指出,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应该由议会、内阁(或总统)和法院掌握,建立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制衡的制度。权力制约是对权力至上的否定,不能把国家权力的良性运行建立在掌握权力者个人的能力和品德上,只有制度才能保证权力不被滥用。在萨拜因看来,“国家实行法律统治往往是对人性脆弱的一种让步”[9]。
按照法治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了国家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关于司法机关、司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126条又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在法治理念下国家司法权必须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必须与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互相制衡。由是观之,能动司法要求法院积极参与社会变革,要求法官广泛行使自由裁量权,这在现有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下可能存在较大风险。司法活动的惯常机制是“不告不理”,司法程序的启动离不开权利人或特定机构的提请或诉求,但司法者从来都不能主动发动一个诉讼,因为这与司法权的性质相悖。这样做,只能使司法机关混同于主动实施管理、调查或处罚等职务行为的行政机关。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惩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非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项法案,它就予以解释。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调查非法行为和纠察事实。”[10]司法需要谦抑和自控。
诚然,当代中国法院负有司法、释法的职能。由于法律文字和法律精神的反差,司法的解释职能“坚持回应了人的需求,而正是这种需求,司法的职能繁荣起来了并坚持下来了”[11]。因此,司法并非完全被动的、机械的,法院和法官有其能动性,“法官应该审判案件,而不是回避案件,并且要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权力,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保护个人的尊严。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适用手中的权力,尤其是运用将抽象概括的宪法保障加以具体化的权力去这么做”。一种更为激进的界定是“司法能动主义就是在宪法案件中由法院行使‘立法’权”,“在包含笼统模糊原则的宪法所留下的‘缝隙’间进行司法性立法”。①参见[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页。需要注意的是,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司法能动性是不同的概念,内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限于主旨对此不作展开分析。
法官应当高水平地运用法律,但不是简单地机械地运用法条,而是要对法律条文充分理解,即要从立法的原意、立法精神、法理关系来理解法律条文,正如庞德指出的:“19世纪的法学家曾试图从司法中排除人的因素,他们努力排除法律适用中所有的个体性因素。他们相信按严谨的逻辑机械地建立和实施的封闭的法规体系。在他们看来,在这一封闭的法规体系的起源和适用中承认人的创造性因素,在组构和确立这一封闭的法规体系的制度中承认人的创造因素,是极不恰当的。”[12]罗纳德·德沃金也曾指出:“可能在某些国家中,人们会认为,不管什么样的人做法官都无关紧要,法律是一套机械系统,就像计算机一样,任何一个受过适当专业训练的人都可以操作它得出同样结果。但在美国没有人会这么想。”[13]但是,必须承认司法的能动性是有前提的,必须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必须遵循法治的基本原则,不能与权力分立原则相背离。否则,可能影响法治社会的基本构架,引致合法性危机。能动司法可能招致的批评在于,法院在实施能动司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较为随意地突破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的现象,扩张司法的基本功能。能动司法也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中的不统一和可预测性的降低,损害司法和法院的权威性。能动司法也增加了社会舆论等干预司法独立、审判中立的可能性。
当然,如果承认并坚持法治及司法制度的多样性,那么能动司法可能给人类的法治发展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为法治的未来提供另外一种可能性。法治是社会在其现有的资源、知识、文化约束下,在各种社会关系的交互影响下可以实现的制度,而脱离具体地方性和社会条件的抽象的“法治”是不存在的。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厚实的历史土壤上培育新的种子,期望不应过于理想。必须以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进行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即从中国社会自身寻找和发掘法治的生长点,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推进法治的逐步实现。法治的形成不是主观塑造的结果,而是历史和文化演进的结果,它不仅同一个社会中人们所熟悉的社会规范方式有关,也同民族的思维习惯有关。能动司法也可能有助于补充现代西方法治思想、丰富人类司法理论,为探索中国特色法治提供司法方面的资源。
结 论
社会的司法变革、完善可能并不是一种强大的国家力量对固有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的“格式化”,而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当代中国司法不完全等同于正式制度层面所要求的状态,也有异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司法形态。中国的法官立足国情、尊重传统,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核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面对以现代化为趋向的强势话语和制度要求,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策略以及一种“或附和或创新或隐退或反抗”的态度,积极利用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手段,回应社会需求,务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以及“情、理、法”的统一。这是当代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司法进步和完善的起点。
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建设中国的司法体制,而是否以能动司法为其基本内涵,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1]高其才,等.司法公正观念源流[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204.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11.
[3]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C]//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19-421.
[4]高其才,等.乡土司法——社会变迁中的杨村人民法庭实证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61-362.
[5]罗昶.伦理司法——中国古代司法的观念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1.
[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311.
[7]高其才.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54.
[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9][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98.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0.
[11][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
[12][美]庞德.法律史解释[M].邓正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3.
[13][美]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M].刘丽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73.
[责任编辑:张莲英]
Local Society,Ethical Traditions,Practice on the Rule of Law and Active Justice
GAO Qi-cai
(School of Law,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Judicature is a core part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judicial system must be anchored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haracteristics.Change and perfection of social judicature is the consta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forces and selection process.The active justice is the hot topic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udicature,which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such as local society,ethical traditions and practice on the rule of law and so on and should be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an accurate grasp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haracteristics,and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udicature.Active justice and the public justice expect to fit the needs of judicature,which is rooted in the inherent social tradition of judicature,but whether it can become the core substance of the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system needs to be observed and reflected furtherly.
Chinese;social characteristics;local society;ethical traditions;practice on the rule of law;active justice
D920.4
A
1009-1971(2012)03-0020-06
2012-0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立法与习惯法研究”(11BFX002);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瑶族习惯法与法治现代化关系研究”(2011081094)
高其才(1964—),男,浙江慈溪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