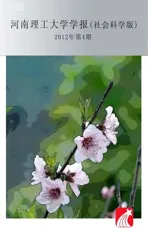哈贝马斯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以《认识与兴趣》为主要依据的考察
2012-04-07钱厚诚
钱厚诚
(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哈贝马斯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以《认识与兴趣》为主要依据的考察
钱厚诚
(浙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哈贝马斯明确地把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作为重大的基本问题提出来加以论证,在《认识与兴趣》中,他试图通过认识论研究为批判理论寻找到可靠的规范基础。为此,借助于从康德哲学那里提炼出来的“兴趣”概念,他提出了兴趣框架以及相应的知识类型,并且把它们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即“劳动”与“相互作用”结合起来。哈贝马斯给出了一幅关于社会生活的认识论图景,也为批判理论争取到了存在的空间和特殊的地位。但是,由于他囿于意识哲学的范式,不能真正解决“兴趣”概念以及“解放的认识兴趣”概念的论证问题,因此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这促使他把目光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批判理论;规范基础;兴趣
所谓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是指批判理论的基础论证问题,即批判理论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的最终根据问题。如果不能为批判理论寻找到可靠的根据,那么批判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无疑将会备受质疑。可见,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不过,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缺乏充分的关注,本文打算就哈贝马斯在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上的理论思考做一番考察,从这个角度来揭示他为什么从认识论最终转向了交往行动理论。
一
在众多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当中,哈贝马斯是明确地把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作为重大的基本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论证的第一人。这当然不是说在哈贝马斯之前,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研究没有根基;而是说,虽然他们的理论建构都有自己预设的基础和来源,但并没有明确地把规范基础问题拿出来作为重大问题详加探讨。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的主要任务是把哲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为此,他们从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柯尔施等前辈那里找到了理论工具,而诸如“总体性”、“理性”、“真理”、“异化”等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力量似乎是毋庸置疑、不言自明的。再后来,他们的工具理性批判和文化批判又越来越涂抹上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甚至陷入到非理性当中去,反倒出现了把批判理论消解掉的可能。
哈贝马斯清醒地看到了批判理论的缺陷与危机。他认为,以往的理论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克服:“首先,批判理论对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和分析哲学一直漫不经心,没有给予认真对待,也从未与之系统性地交锋过,如能交锋,便可借以显示自己的意义。其次,它隐身在抽象的工具理性批判中,对我们这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只做了贡献微乎其微的经验主义分析。最后,它没有替自己的基本准则和地位提供一条确凿的理由。阿多诺总是毫无保留地宣称他否认有向理性概念提供系统基础的可能性。”[1]17
显然,最后一点直接指明了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急需建构。同时,笔者认为,前面两点实际上也关系到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其一,第一代理论家从其理论本性上看,主要继承了黑格尔主义传统,并且结合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韦伯的合理化理论等要素,而黑格尔主义传统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氛围下不能不接受根本的改造,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也不能不在变化很大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前接受修正——凡此种种都要求批判理论必须吸收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批判理论奠定符合时代精神的可靠基础。其二,不可忽视对西方社会的经验研究,工具理性批判也需要寻找新的出口。在前期的批判理论那里,工具理性批判是基本的理论思路,但如果按照工具理性批判这个思路一直走下去,难免要回到韦伯所说的“铁笼”这个暗淡的结局里。而前期批判理论确实最终走进了这个死胡同。
就哈贝马斯本人来看,他对西方社会抱着具体分析的态度,在他看来,民主宪政是其成就之一,而第一代理论家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这个理论模式不能自拔,提出了“大拒绝”,这样就无法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做实事求是的经验分析,而不得不或者求助于宗教慰藉,或者遁入审美乌托邦。所以,不转换理性批判的路径是不行的,否则批判理论将难以为继。可是,如果失去了工具理性批判这个基本思路,那么批判理论将凭借什么来支撑自己呢?无疑,这就需要为批判理论提供新的基础。所以总的看来,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事关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和前途。
在哈贝马斯那里,对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建构有两次尝试,并且主要体现在《认识与兴趣》和《交往行动理论》这两本著作当中。鉴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本文只对《认识与兴趣》这部早期著作进行考察。只有理清了哈贝马斯的早期思想,我们才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其后来理论转变的全貌。
二
《认识与兴趣》是哈贝马斯唯一的一部认识论专著,他之所以要写作这本书,是打算通过思想史的考察来“形成社会批判理论的恰如其分的自我理解。这里涉及到给以批判为手段的社会学奠定基础和进行认识论的辩护的问题”[2]2。显然,他的认识论研究是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服务的,更明确地说,哈贝马斯着眼于在认识论研究当中为批判理论寻找到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依据。为此,他回到了康德哲学的传统。
近代西方哲学家们在宗教神学的统一力量已经崩溃之后,试图把人的理性确立为自身思考和行动的根据。他们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人具有理性,理性保障了人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首先认识人自身,认识人的理性能力及其结构。在康德那里则表现为“人是什么”这个总问题,它又体现为“我能认识什么”(科学)、“我应该做什么”(道德)和“我可以希望什么”(艺术)这三个分支问题。也就是说,人本身是科学、道德和艺术的根据。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要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文化价值形态,则应该从人自身进行说明,因为人是主体,人创造了这一切。而在批判理论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与文化价值形态也正是由于人自身的启蒙理性走到其反面的结果。只不过,哈贝马斯不像他的前辈那样最终用非理性对抗理性,而是试图让理性自我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把现代性事业更完善地进行下去。所以哈贝马斯回到了康德,他想通过反思人的理性来寻找到重新平衡工具理性的主体资源。一旦找到了这个主体资源,那么通过重新规划文化价值形态来整合分裂的社会状况就成为可能。
哈贝马斯认识论的核心概念——兴趣——正来源于康德[2]194-212。康德提出“理性兴趣”的概念,这种理性兴趣是“纯粹的”兴趣,而不是“经验的”兴趣。在康德那里,“理性兴趣”概念具有强烈的先验哲学特征。所以,哈贝马斯对之进行了改造,“把认识过程纳入生活联系,使人们注意到指导认识的兴趣的作用:生活联系即兴趣联系。但是,这种兴趣联系和社会生活赖以发展的水平一样,不能不依赖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知识的固有范畴加以解释。维持生活的兴趣,在人类学的层面上,同由认识和活动决定的有组织的生活紧密相关。因此,指导认识的兴趣决定于两种要素:它—方面证明,认识过程产生于生活联系,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在生活联系中告诉人们,社会重新建立的生活方式的特征首先是通过认识和活动的特殊联系表现出来的”[2]213-214。这段话的信息很丰富: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了兴趣概念与社会生活的互动联系;试图抹去兴趣概念的先验色彩;把认识论与社会生活联结起来;揭示兴趣作用于社会生活,并形成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知识类型;指出认识论可以以反思的方法把兴趣从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知识类型中揭示出来。抓住了这几点,就抓住了理解哈贝马斯理论的钥匙。
在哈贝马斯看来,自己的兴趣概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表明,它已经不同于康德那个先验的理性兴趣概念了,所以它“既不服从经验规定和先验规定之间的区别,或者实际规定和符号规定之间的区别,也不服从动机规定和认识规定之间的区别”[2]200。在这个基础上,哈贝马斯通过对皮尔士、狄尔泰、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理论考察,提出了系统的“兴趣”框架: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和解放的认识兴趣。技术的认识兴趣旨在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扩大人类在自然界的活动领域,并且利用和改造自然,它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实践的认识兴趣旨在理解“文本”的内涵、体悟历史文化的精神,它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交往需求;解放的认识兴趣着眼于批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宰制和扭曲现象,它表达了人类始终潜藏着的对现状不满、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一超越需求。
哈贝马斯接着指出,兴趣先于认识,是认识的基本导向;认识是实现兴趣的行动,受到兴趣的支配;在兴趣的引导下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就是各种知识类型,兴趣框架与知识类型具有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兴趣的引导下,分别形成了经验—分析的科学、历史—解释学的科学以及批判性的社会科学,这些知识类型分别解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符号互动与交往行动的实践需求以及以反思和批判为纽带的解放需求。其实,所谓经验—分析的科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所谓历史—解释学的科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而所谓批判性的社会科学,特指的是哈贝马斯所力图凸显和论证的批判理论,也包括“深层解释学”层面上的精神分析理论。
在阐述知识类型与兴趣框架之间联系的同时,哈贝马斯当然没有忘记把它们与自己的社会理论目标结合起来。他认为,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可以划分为“劳动”与“相互作用”这两大部分,劳动是指物质生产活动,而相互作用指的是人际交往活动。在他那里,技术的认识兴趣和经验—分析的科学体现于“劳动”的领域,而实践的认识兴趣和历史—解释学的科学、解放的认识兴趣和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则体现于“相互作用”的领域。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就给出了一幅社会生活的结构图。
如果进一步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幅图景的话,就能领会他的良苦用心了。在哈贝马斯那里,理性与兴趣是统一的,相互蕴含[2]284,[3]133。更确切地说,兴趣是比理性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需求,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内驱力。哈贝马斯一再强调,兴趣之类主体是“在文化条件下自我再生产的,即在形成过程中自己创造自己的类”[2]198,“认识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一个具体的潜在欲望(Antriebspotential)的生物遗传上……产生于同劳动和语言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需求中”[4]9。在这个意义上,兴趣框架乃是人类理性结构在社会文化需求维度上的内驱力。而这个理性结构,众所周知,当然运行于由“劳动”与“相互作用”这两大部分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且,在“劳动”那里是工具理性在起作用,在“相互作用”那里则是交往理性在起作用。总之,技术的认识兴趣以工具理性的形式与“劳动”相对应,实践的认识兴趣、解放的认识兴趣则以交往理性的形式与“相互作用”相对应。所以,联系上面所说的知识类型来看,哈贝马斯的认识论是一种由“兴趣框架—理性结构—知识类型—社会需求(劳动与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结构论式的认识论。
总之,哈贝马斯通过对兴趣的三元划分,瓦解了工具理性的垄断地位,凸显了交往理性的“实践”和“解放”功能;同时,通过昭示知识类型的多元化有着深层的主体根基,也就为批判理论争取到存在的空间和特殊的地位。从理论构思上看,哈贝马斯的手法无疑是巧妙的,似乎实现了为批判理论奠定规范的基础这个既定的目标。他认为,自己对兴趣框架的追索、对知识类型的界定,重新理清了理性的结构与功能,从而为人类社会重新创造自己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画出了一道起跑线。
三
虽然《认识与兴趣》这本书具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但它还是受到了“枪林弹雨般的批评和攻击”(吉登斯语)。情形如此激烈,以至于哈贝马斯不得不在几年内不断地从各个角度进行自我辩护并修正观点。譬如,他曾经借自己的另一部著作《理论与实践》(1971年)以及《认识与兴趣》再版之际(1973年),分别以“导言”和“后记”的形式作长篇回应。在大量的批评意见中,对兴趣概念的质疑无疑具有颠覆性,因为在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建构中,它占据着支点的地位和核心的作用。
哈贝马斯把指导认识的兴趣规定为“既不服从经验规定和先验规定之间的区别,或者实际规定和符号规定之间的区别,也不服从动机规定和认识规定之间的区别”[2]200,这样的规定难免让人感到困惑,批评者认为,他没有把兴趣概念的性质说清楚。[5]45为此,哈贝马斯解释道:“只要这些认识的兴趣能在反思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研究逻辑的道路上得到确认和分析,这些认识的兴趣就有权要求具有‘先验的’性质;然而,一旦这类认识从认识人类学的角度被理解为自然史的结果,它们就具有一种‘经验的’性质。我给‘经验的’这个词加上引号,是因为要求一种进化论从自然史上来解释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特征的种种特性。”[4]23
上述这段话至少透露出三层信息:①他在“先验的”和“经验的”上面打上引号,表明自己放弃了严格意义上的先验逻辑观念,也不赞同纯粹的自然主义生物学观点。②正如上文已经说明的那样,他的兴趣概念是以反思的方法从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知识类型当中追溯得出的。换言之,他事实上是通过从现实层面的反向推导来获得兴趣的,即“社会需求(劳动与相互作用)→知识类型→理性结构→兴趣框架”。这就显示出典型的先验哲学、意识哲学的痕迹:认识论的理论陈述是对在有效性上已经获得肯定的经验对象的重构与论证,以寻求其先天条件与根源[2]315-323,327。③他的某种“认识人类学”的视角使他着眼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文化这种既定的背景因素在人类身上的自然史性质的沉淀。兴趣就是这样一种沉淀,它与生俱来,顽强深厚,以至于具有一种既非先验也非经验但可以说是“准先验的性质”[4]9。
哈贝马斯之所以特别强调兴趣的准先验的性质,当然是要显明它是“不变的”和“抽象的”[4]9,否则它怎么能够具有普遍性从而担当起指导人类活动的重任呢?他的认识论又怎么能够具有广泛的结构性解释意义呢?然而,难就难在既要说明兴趣是人本身所固有的,赋予它以普遍性,又要把它与严格意义上的先验哲学或纯粹的自然主义生物学划清界线。在德国伦理学家Eve·Marie·恩格斯看来,哈贝马斯走上了调和折衷的道路。也就是说,他试图把先验哲学和哲学人本学汇合起来阐述兴趣概念。但是,这两种哲学思想在本性上有巨大差别:先验哲学一开始就指出可能认识的先天条件,而哲学人本学则力图确定人的本质。哈贝马斯的汇合工作没有取得成功,在兴趣概念上就出现了含混不清的现象[5]42-46。哈贝马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兴趣概念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先验哲学概念”,“这个概念在我的和艾培尔的某些著作中都有论述。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不能说我们对人们提出的正确问题已经作了充分的回答”[2]313,并且,“指导认识的兴趣是把人类的自然史同人类形成过程的逻辑相联系(这里我只能强调还不能证实这一论点)”[2]199。
既然哈贝马斯不能把兴趣概念这个阿基米德点确立好,那么他的整个认识论也就岌岌可危了。即使暂且把兴趣概念放到一边,来看看它框架中的“解放的认识兴趣”概念,情况也不容乐观。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构思中,解放的认识兴趣旨在实现反思本身[3]133,“自我反思能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自我反思是由解放的认识兴趣决定的”[3]129。也就是说,解放的认识兴趣着眼于批判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扭曲现象,它表达了人类始终潜藏着的对现实社会不满、追求更美好的理想生活境界这一超越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批判理论得以存在的主体根基和先天条件。但是,对解放的认识兴趣的存在论证却是一个难题。从“兴趣—经验对象”这种对应关系的层面上看,如果说技术的认识兴趣和实践的认识兴趣与社会现状、知识类型都具有对应关系,因而可以反向推导的方式来进行理论构思的话,那么解放的认识兴趣却不能从社会现状上进行反向推导,因为人类社会本身正陷入启蒙与现代性的负面后果之中,解放还只是梦想而已!所以,只能从知识类型上寻找对应关系以便进行反向推导。为此,哈贝马斯把目光投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哈贝马斯看到,以自我反思为中介的“分析具有直接的治疗效果,因为批判地克服意识障碍以及终止虚假的客观化,能够唤起病人重新占有失去的那一部分生活史,从而取消分裂过程”[2]233。也就是说,以自我反思为中介的精神分析能够使压抑的个体得到解放。在哈贝马斯看来,“心理分析的认识,是典型的自我反思”[2]229,“与这种自我反思的学习过程相适应的是扬弃压抑和虚假意识的解放的认识兴趣”[2]301。一言以蔽之,精神分析学说表明,解放的认识兴趣在知识类型上是存在的。由于找到了这种对应关系,他的反向推导也就得以进行,似乎解放的认识兴趣这种理论构想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要记住,解放的认识兴趣仅仅是理论构思、推导的产物。哈贝马斯也承认这一点,“当技术的认识兴趣与实践的认识兴趣深深地扎根于行为结构与经验之中时,即同社会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时,解放的认识兴趣则具有一种推论出来的性质。它保障理论知识同生活实践,即同在系统上受到扭曲的交往和在貌似合法的压制的条件下才形成的‘对象领域’的联系。因此,同这种客观领域相一致的经验与行为的类型也是推论出来的”[2]328。
不言而喻,这种理论推导意义上的解放潜能是十分脆弱和渺茫的,它又如何能够整合处于强势地位对技术的认识兴趣与实践的认识兴趣呢?换言之,在面对整体性的社会异化时,解放的目标如何得以实现?哈贝马斯心里实际上也是没底的。其实,解放的认识兴趣以及解放行动的推论性质,无疑已经把人类解放的目标划入了乌托邦的范畴。所以吉登斯曾经辛辣地指出,“哈贝马斯试图提出批判理论中的一个新观念,即批判理论的基础是由兴趣的认识构成的。但是那种‘解放的兴趣’看起来仅仅存在于将另外两种构成认识的兴趣勾连起来的短暂瞬间”[6]245。
若干年后的哈贝马斯宣布放弃通过认识论来为批判理论奠定基础的尝试:“我再也不会把认识论当作康庄大道去信任。社会批判理论不需要借用方法论术语来证明它的可信度;它需要一种实质性的基础,并把自己从意识哲学的概念框架所产生的‘瓶颈’中引导出来。”[1]145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建构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哈贝马斯之所以失败,吉登斯和他本人都看得很清楚,那是因为他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即在“传统的探寻认识的先验基础——‘第一哲学’——将被抛弃”[6]246的时代背景下依然陷入了“意识哲学的概念框架”这个瓶颈中了。简言之,他通过反思模式而获得了改头换面的、先验的兴趣概念,并且,知识类型、社会行为方式(“劳动”与“相互作用”)也通过主体的兴趣框架而得以解释和论证。于是,他的认识论似乎只需要通过“兴趣”这个阿基米德点就能把整个世界给支撑起来了。所以,从其认识论的本性特征上看,把他的认识论划归在“意识哲学”范畴下是可以成立的。虽然哈贝马斯确实提出了许多改良意见,但是,现代哲学经过不断的自我批判,早已超越了“意识—反思哲学”的阶段而进入了第三期,即语言分析学[7]13。也就是说,在当代的后形而上学氛围下,带有明显的先验论色彩的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尝试是不能得到有效承认的,因为“康德之后,不可能还有什么‘终极性’和‘整合性’的形而上学思想”[7]18。
所以哈贝马斯最终认为,关于意识、自我、主体等概念的思考,关于社会状况的改造路径以及关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的建构,都必须在语言、交往行为、主体间性等新的范畴中重新起步。这些方面在他后来的著作《交往行为理论》当中得到了展开,需要另文探讨。
[1]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李安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M].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4]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 Eve·Marie·恩格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观念述评[J].哲学译丛,1980(5):42-46.
[6] 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M].文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位雪燕]
HabermasandtheStandardBasisofCriticalTheoriesA Case Study ofCognitionandInterest
QIANHou-cheng
(InstituteofMarxism,ZhejiangSci-Tech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In Habermas’s opinion, the standard basis of critical theories is an important point that must be testified. He tries to prove it through Epistemology in his book Cognition and Interest. So he advances the conception of interest which originates from Kant’s work. Then Habermas puts forward the interest structure and the types of knowledge. Besides, he connects the interest structure and types of knowledge with social life, namely, labor and interaction. In his Epistemological picture, Habermas provide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space for critical theories. But he can not prove the conceptions of interest and emancipation interest because he follows in the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Habermas turns to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with more and more criticisms from the public.
Habermas;critical theories;the standard basis;interest
2012-07-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20033);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0918857-Y)。
钱厚诚(1976—),男,江苏盱眙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E-mail:qianhoucheng_88@163.com
B089.1
A
1673-9779(2012)04-04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