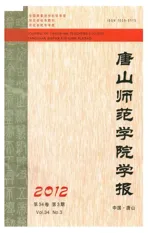重新评估《上清传》的思想价值
2012-02-15周承铭
周承铭
(长春社会主义学院 长春中华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41)
文学研究
重新评估《上清传》的思想价值
周承铭
(长春社会主义学院 长春中华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41)
《上清传》是政治小说,但并非党争政治小说,其用意不在攻击陆贽,而在批判皇帝。德宗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小说向人们揭示,封建官场各色人物的升降、荣辱和生死皆为皇帝所掌握,只要皇帝不信任、不满意、不高兴,厄运就会随时降临。小说在批判皇帝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过《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著名传奇小说,在小说史上理应给予应有的地位。其思想价值是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皇帝的道德和人格,敢于直白表达对皇帝的不敬和否定,充分体现了唐传奇作家的政治勇气;反映了封建帝王信重臣子有始无终,封建官员难有善终的现实,揭示了当时当官从政的巨大风险;反映出皇帝是官场斗争的总根源,揭示了祸自君出,乱自上作的历史规律。
《上清传》;主题;思想价值;政治小说;德宗;批判
中唐文人柳珵的《上清传》,《太平广记》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等均有收录,是唐代传奇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关于其思想价值,当代学者给予了不同的评价。第一,揭示了中唐时代的社会政治特征。“通过《上清传》,我们完全可以呼吸到那个时代的气息。这里首先是皇帝的昏庸,轻易听信谗言,武断而又反复无常;朝臣之间相互陷害诬告;地方官吏看风使舵,投靠权贵且落井下石。”[1]第二,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残酷。“此为党争政治小说。”[2]“概括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由争权夺利而引起的角逐,使用栽赃诬陷等阴谋诡计打击政敌。”[3]“真实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和佞臣专权。”[4]“反映出中唐上层内部不择手段争权夺利的重大问题。”[5]第三,是唐人以小说为攻击政敌之工具的重要例证。柳珵是柳冕之子;柳冕与李吉甫亲善;李吉甫是窦参集团成员,与陆贽敌对;故柳珵作《上清传》以攻击陆贽及其门生[6]。“小说作者正是通过虚构的情节,旨在为窦参翻案,攻击陆贽,把传奇当作了攻击政敌的工具和手段。”[7]第四,歌颂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的正直、忠诚和智慧,与当时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现实构成强烈对比。“在上清身上,寄托了柳珵对于美好人性——正直、勇敢、忠诚的向往。”[8]“这一封建社会下层女性的形象,是塑造得丰满而光辉的。”[9]深入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和若干细节,我以为当代学者们的这些评价还不足以充分而正确地说明小说应有的思想价值。
破解《上清传》研究中目前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是深入推进其思想价值评价的关键所在。
其一,李吉甫与陆贽究竟是仇敌还是挚友?认为小说是为攻击陆贽而作,是“党争工具”、“党争之物”或“党争政治小说”,主要依据就是李吉甫与窦申、李则之、吴通玄、吴通微等,都是窦参集团成员,都反对陆贽,且陆贽为相时曾出手打击过吉甫,贬吉甫为明州长史,由此结怨至深。柳冕与吉甫既是同僚又过从甚密,当为同党,冕子珵与吉甫子德裕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颠倒黑白以攻击其宿敌陆贽及其门生故吏,乃势所必然。由于此说最先出自卓有建树的一代文史大家卞孝萱先生,故为近30年来学术界最占据主流地位且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然细考史实,吉甫与陆贽之交可分为两段,二人或许有隙,但那是陆贽罢相之前;迨陆贽罢相,乃由相疑渐成莫逆。《旧唐书·陆贽传》载:“初,贽秉政,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量移忠州刺史。贽在忠州,与吉甫相遇,昆弟、门人咸为贽忧,而吉甫忻然厚礼,都不衔前事,以宰相礼事之,犹恐其未信不安,日与贽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贽初犹惭惧,后乃深交。时论以吉甫为长者。”[10,p4679]《旧唐书·李吉甫传》再载:“宰臣李泌、窦参推重其才,接遇颇厚。及陆贽为相,出为明州员外长史,久之遇赦,起为忠州刺史。时贽已谪在忠州,议者谓吉甫必逞憾于贽,重构其罪;及吉甫到部,与贽甚欢,未尝以宿嫌介意。”[10,p3992-3993]《新唐书·李吉甫传》则进而记载吉甫与陆贽置怨结欢还为自己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贽之贬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与结欢,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岁。”[11]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原本就是复杂的,而官场中人物置身于权力斗争的复杂环境和矛盾中,比之一般人无疑更为复杂,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都是善恶并存,魔佛同在,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此并非故作雷人之语,古人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则更有言“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12]封建正史之所以被世人称为“信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记载人物不抑美不掩过,善恶兼录,妍媸并举。既然我们承认《旧唐书》为一部信史,也主要引用其记述为论证依据,那么就不能(也没有道理)专拣合意者信之用之,不合意者即疑之弃之。李吉甫因打压牛僧孺、李宗闵,常为后世史家诟病,但史传记其与陆贽先为仇敌终为挚友当是不争之事实。既然吉甫当年即已与陆贽捐弃前嫌,并渐成“深交”,作为吉甫的后世子孙及其同党则没有理由做出违忤先人的不肖之举。窦参集团之关键人物与陆贽敌对的基石既不存在,那么所谓“攻击”说、“工具”说的大厦又岂能安然矗立!
其二,这篇作品究竟是史料还是小说?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上清传》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和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在《上清传》的归类上自北宋以来即存在分歧,有人将其归入历史,视为笔记类史料,有人将其归入文学,视为文言小说。相形之下,前一种认识不止历史久远,且影响深刻。司马光述其撰《资治通鉴》不采信《上清传》的理由:“信如此说,则参为人所劫,德宗岂得反云蓄养侠刺!况陆贽贤相,安肯为此!就使欲陷参,其术固多,岂肯为此儿戏!全不近人情,今不信。”[13]不是因为《上清传》是小说,不可作史料使用,而是认为所记内容与正史相左,不合采择史料的标准。卞孝萱认为《上清传》歪曲史实,诬蔑陆贽,美化窦参,目的是为李吉甫洗刷罪行;郝润华认为“《上清传》所述事实是靠得住的”,人物、事件皆非虚构,“是一篇为窦参平反的传奇”[14]。两种观点泾渭分明,截然对立,但前提却是一致的,即强调的都是作为史料才有的历史真实,而非作为小说应有的审美真实。其他绝大多数当代学者虽然明确强调《上清传》是传奇小说,对它的研究和评价可以不必陷入历史公案的是是非非,但同时也承认作为“一篇颠倒忠奸的小说”[15],在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很不妥当,既“记载失实”,又“观点错误”,“可取之处”十分有限。《上清传》所记故事在唐代即如作者所云:“此事绝无人知。”宋以后其真实性则更无从查考。司马光怀疑其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以史学家审慎的态度将其从史料中摒弃出来无疑是正确的。往事越千年,我们今天更难以搜寻将其作为史料来对待的依据和理由。但是,它不是可信的史料,未必不是可读的小说。换言之,在已无法充分证明其内容尽皆属实的今天,我们只能把它作为小说来看待。是小说,就要用研究小说的方法来研究,也要用评价小说的标准来评价。《上清传》可能是目前我们可以见到的所谓“颠倒忠奸”之最早的一篇小说,但绝对不是唯一一篇,在后来的小说史上“颠倒忠奸”现象可谓屡见不鲜,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三国演义》,然而学界几乎一直公认把史传中的“红脸”曹操变成小说里的“白脸”曹操是这部经典名著的一大特色和价值所在。历史真实可以作为评判文学描写是否真实可信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永远不该是唯一的标准。不遵循历史真实算不上是《上清传》这篇小说的缺陷或缺点,也不该以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来评判这篇小说的优劣。
其三,小说的主要人物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小说虽然只有寥寥几百字,却有窦参、上清、刺客、德宗等多个人物先后登场。当代学者们认为,尽管窦参、德宗的形象塑造也很生动成功,但最为丰满最富有内涵的还是上清这一女婢形象,“作为婢女的上清,有正义感、有勇气、有智谋,是小说极力所歌颂的。”[16]上清无疑是一个主要人物,但从小说的实际内容看,作者所着力塑造的人物应该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另一个就是德宗皇帝。一是就结构篇章的需要而言,德宗是除上清之外,另一个贯串故事始终的人物;二是就人物形象的生动性而言,德宗非但不比上清逊色,相反个性特征和魅力更为突出,尤其是“厉声曰”、“怒曰”等极具鲜明特色的神态以及完全个性化的语言,使其在唐代小说的皇帝群像中独树一帜;三是就人物矛盾的焦点而言,德宗是一切人物命运的主宰,小说中上演的所有悲剧、喜剧无不是他的决定和导演。如果我们把他定位在为主要人物设置的陪衬性人物,那么小说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就将无从揭示和理解。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其四,上清究竟是普通侍婢还是介于主奴之间的小妾?《太平广记》以“上清”为题,将这篇小说收入第275卷“童仆奴婢”类,实际是把上清作为一个义奴来看待。当代学者们因袭旧说,亦把上清视为普通奴婢,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歌颂了上清这一当时社会最底层人物,揭示出了高贵者丑恶,卑贱者善良这一由阶级决定的人格特质和属性,“与这官场上的一片黑暗相对照,作者赞颂了奴婢上清之正直忠义,使此文在实际效果上成了对蔑视妇女和‘小人’的封建传统观点的有力反击。”[17]这样认识和评价固然十分深刻,但遗憾的是并非符合小说内容的实际。上清自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某妻早亡,故妾得陪扫洒。”这“得陪扫洒”即表明上清不同于《红线传》等其他传奇小说中那些侍奉老爷的一般女婢,乃是窦参的小妾,地位在主子之下,奴婢之上,而且由于窦妻早亡,窦家主母的位置长期空缺,更使其在窦府虽然没有主母的名分,却享有主母才有的权力,是窦府事实上的女主人。也正因为上清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和身份,窦参才会在危难时刻以身后事相嘱托;同时,也恰恰是因为与窦参有如此特殊而深厚的关系,她才会尽心竭力为窦参洗雪不白之冤。窦参选择上清托付后事,不止是看重她的聪明伶俐,更主要的是缘于特殊关系而产生的那种别人无法替代的信任;而上清为窦参翻案也不仅仅是出于对旧主的一片忠义,而更主要的是缘于女主人对家庭的应尽责任。既然上清的身份不是一般的所谓地位低下的女奴,那么源于女奴这一前提的所有价值揭示和判断,必定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一人物在小说中串联故事,结构篇章的意义远大于其揭示思想的意义。
其五,小说究竟意在攻击陆贽还是意在批判德宗?换言之,小说着重揭露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残酷斗争,还是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政治的最高主宰之多疑、阴险和恶毒的本性?如果把历史上的陆贽定位为“贤相”或“君子”,则小说把他丑化为不择手段、阴谋陷害他人的宵小之徒,确乎是属于一种攻击。但是小说“攻击”陆贽不是目的,只是为了牵出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在小说的人物布局中陆贽不过是铺垫,其批判矛头的真正和最终指向是作为整个封建官场和社会之最高主宰的德宗皇帝。一则窦参的获罪,根本原因不在陆贽是否争权用计,以及他本人是否“蓄养侠刺”,即使没有这些,德宗整治窦参也是迟早的事。因为窦参早已受到德宗的猜疑,陆贽制造的“蓄养侠刺”的事件,不过是被德宗利用以乘势发作的由头而已。这一点,窦参本人有清醒的认识。“今有人在庭树上,吾祸将至。且此事将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于道路。”“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君叫臣死,在劫难逃,一切辩白都将无济于事。二则德宗首先和重点追究的罪责不是“蓄养侠刺”,而是“交通节将”,这与陆贽的设计陷害没有任何瓜葛。执金吾奏报的是“蓄养侠刺”一事,而德宗却突然提出“交通节将”,关心的不是朝臣间的争斗,而是窦参“位崇台鼎,更欲何求”(认定窦参蓄意谋反),后来着意强调的也是“交通节将,信而有征”,至于“蓄养侠刺事”仅仅是居于“又问”的位置。“交通节将”先后皆出自德宗之口,而非陆贽等人之口,说明德宗对窦参早有疑忌,如何处置也久已心中有数,窦参的最终获罪和被处死乃势所必然。三则陆贽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比陆贽还恶的是德宗。贞元八年,德宗利用陆贽等人构陷的由头除掉了他早想除掉的窦参;四年后,亦即贞元十二年,德宗再次利用陆贽等人构陷的由头贬黜了也是他早想贬黜的陆贽。陆贽一心陷害窦参,结果自己最终也落得个“受谴不回”的下场,同一件事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州县“希陆贽意旨”在恩赐官银“上刻作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以证实窦参的罪状;陆贽既从未提出过窦参“交通节将”这一致命问题,言州县“希陆贽意旨”,那么陆贽又是希谁的意旨呢?当然只能是希德宗意旨,换言之,真正想坐实窦参罪状的是德宗而非陆贽。而陆贽遽然遭贬的真正原因也不是因为他构陷窦参的阴谋一朝大白天下,而是因为其时陆贽已经“恩衰”,总根子还在德宗。表面上看,先是陆贽加害窦参,然后又是裴延龄加害陆贽,揭露的似乎是封建官场无止无休的倾轧和斗争,但深而究之,则可以发现这种倾轧和斗争的总根源和总导演其实是德宗,陷害窦参以及陆贽的元凶也是德宗。陆贽的凭空诬陷充其量是让同僚丢官,而德宗的欲加之罪则一定是让臣子丢命,相比之下,谁更凶险、恶毒,可谓昭然若揭。在当代《上清传》研究中,也曾有一些学者比较敏感地注意到了小说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但仅仅归结为暴露了皇帝的“昏庸”,或“轻易听信谗言”以及“武断而又反复无常”等能力缺陷和性格弱点,照小说对人物的实际刻画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上清传》的核心人物不是窦参,不是陆贽,甚至也不是上清,而是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德宗皇帝,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主要集中在这一人物形象上。封建官场各色人物的升降、荣辱和生死皆为皇帝所掌握,只要皇帝不信任、不满意、不高兴,厄运就会随时降临。这就是自身也在封建官场中的小说家向人们所揭示的思想主题,用小说中的语言来表述,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这一主题反映出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员们在家天下之政治体制下所具有的恐惧、悲哀和无助无奈的心态。
《上清传》作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并不比众所熟知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著名传奇小说逊色,在批判皇帝的深度和力度上可以说远远超过了这些小说。在小说史上理应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其思想价值尤不容忽视。
第一,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皇帝的道德和人格,敢于直白表达对皇帝的不敬和否定,充分体现了唐传奇作家的政治勇气。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既讲究臣守“臣道”,同时也讲究帝遵“帝德”,强调君要像君,臣要像臣,“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也即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礼记》把“君仁”、“臣忠”作为君臣之大义提出,孟子则明确“仁”、“义”、“正”是帝王应守的道德底线,“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君正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唐代文士官员对“帝德”和“臣道”问题也很重视,沈佺期有诗句云“大业永开泰,臣道日光辉”(《和户部岑尚书参迹枢揆》);张九龄有诗句云“人伦用忠孝,帝德已光辉”(《和苏侍郎小园夕霁寄诸弟》)。《上清传》是一篇难得的着重审视和评判帝王道德和人格的小说。窦参身为宰相,位崇台鼎,是皇帝股肱大臣,所谓“交通节将”既未做深入核实,而且即便属实,也只是存在谋反的可能,并不等于谋反的事实,但德宗却以此为由对窦参先是贬官、流放,最后是“诏自尽”,仅仅是出于猜疑和担心,就要结果一个朝廷重臣的性命,如此狠毒,是谓不仁。窦参原本就是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贬被杀,却还要籍没其家资和人口,甚至一定要搞到让窦参“一簪不着身”的地步,如此刻薄,是谓不义。动辄“震雷霆之怒”,说话则既带脏口,又是婆娘腔:“这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衫着。又常唤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枉杀却他。及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于泥团。”逾越君臣之分而以世俗的行第称谓称呼身为朝臣的陆贽;杀掉窦参原本是自己的过错却要将罪责推卸给他人;骂出当时最粗俗最歹毒的脏话,且数数落落,翻尽旧账,有如撒泼的村妇,又如碎嘴的阿婆,帝王的修持和威仪如此不堪,是谓不正。封建主流思想道德文化强调的帝德,在德宗这一人物身上几乎一条不占。作者以此老辣的春秋笔法对本朝的先皇陛下进行全盘否定性的描写(在普遍崇尚春秋笔法的当时应当是多数文人都读得懂的),不加掩饰地表现了对皇帝和皇权的大不敬,这在封建社会实际上已经是犯下了不能饶恕的欺君大罪,即使是文禁相对松弛的唐代,作者要这样写这样做也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
比之于产生在贞元元和之际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小说批判皇帝主要集中在昏聩、荒淫等方面,介于中晚唐之间(大约为宝历、大和年间)的这篇《上清传》则进一步拓展到猜忌、阴毒、刻薄、虚伪等道德和人格的更深层次,更注重的是揭示帝王的本性和本质,而且出发点也不再是为统治者总结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而是着力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和鞭挞,隐约之中流露出一种失望以至绝望的消极情绪。把两个阶段的小说加以对比,从中不难发现与唐政权走势相一致的一部分文士官员之思想、心态的微妙变化。
第二,反映了封建帝王信重臣子有始无终,封建官员难有善终的现实,揭示了当时当官从政的巨大风险。窦参、陆贽皆起于微末,如窦参是“刀笔小才”,陆贽是“绿衫”下僚,没有德宗的一力奖拔或超拔,是坐不到宰相位置的,而德宗奖拔或超拔他们的前提必然是很“称意”。但在他们走上高位的短短几年时间——如陆贽只有四年,德宗就失去对他们的信任、亲近和倚重,取而代之的是猜忌、疏离和防范,以莫须有的罪名枉杀窦参,以无足轻重的缺点贬黜陆贽。先前无比宠信窦参、陆贽的是此一德宗,后来一心整治甚至整死窦参、陆贽的亦是此一德宗。面对这样欠缺仁德,气量狭小,反复无常的君主,哪个臣子还会有安全感和好结局?还能有多少人会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上”?古代伦理道德规范极为重视君臣关系,始终都把“君臣有义”作为人伦的重要构成,称为“五伦”之一,强调良好的君臣关系,特别是帝王对臣子的信任和礼敬,是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要求对“义”这一政治道德,君臣都要坚守,但首先是君主必须坚守。在这一点上,孟子说得十分透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臣子如何对待君主,最终取决于君主是如何臣子的,君仁、臣忠不止是并列关系,更是主从和因果关系。在唐王朝建政初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就注意到了构建和维系良好君臣关系的极端重要,贞观十四年魏征在奏疏中就唐王朝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君臣关系所作的精辟论述,被唐太宗所“深嘉纳之”。“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18]考两《唐书》,这些治政理念,不仅唐太宗为之终生践行,其后任君主如高宗、玄宗等也大体能够在一个时期坚守,“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局面同时出现,并非成于偶然。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君臣关系急转直下,特别是在德宗皇帝经历了泾原兵变和李怀光之叛后,更加日趋恶化,先前的治政理念被动摇,以至于被抛弃,从而出现了频繁撤换宰相和十官九贬的局面,当官从政成了高风险的职业,主要活动于贞元时期的诗人戎昱当时即有诗句云:“谁人不谴谪,君去独堪伤。”(《送新州郑使君》)《上清传》就是要以其比较生动细腻的笔触,向人们再现德宗皇帝如何视臣子如“犬马土芥”的史实,从而隐曲地表达对当朝皇帝的不满。不能形成君臣同心,上下一气的局面是封建政治的最大失败,由小说对德宗以疑惧而杀宰相,以小过而贬大臣之一系列阴险而愚蠢举动的描述,我们今天也就不难理解遭受安史之乱打击的大唐王朝何以不能实现中兴,以至每况愈下,最终灭亡。
第三,反映出皇帝是官场斗争的总根源,揭示了祸自君出,乱自上作的历史规律。“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小说中德宗所播之恶首先就是引发和推动了封建官员之间构陷成风,明争暗斗不断。领会了德宗意在杀人,陆贽及州县吏才会捏造致命罪证;确认了“陆贽恩衰”,裴延龄才会“恣行媒孽”。有心存险恶的君主,必有乐于和善于整人的大小臣子风云际会。君疑则臣斗,官争则民散,产生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责任无不在最高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上之好之,民风尤甚”(《东城老父传》),自古而然。比之于这篇小说,像后来的《水浒传》批判封建政治和封建官场,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1] 李剑国.唐宋传奇品读辞典(上)[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7:428.
[2]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375.
[3] 吴志达.唐人传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2.
[4] 周振甫.中外小说大辞典[Z].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52.
[5] 钱仲联,傅璇宗,王运熙,等.中国文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384.
[6] 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194-200.
[7] 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97.
[8] 关永礼,等.中国古典小说鉴赏辞典[Z].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342.
[9] 谈凤梁.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518.
[10]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38.
[12]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566.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69.
[14] 郝润华.唐传奇《上清传》史实考释[J].甘肃理论学刊, 1990(1):72.
[15] 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M].长沙:岳麓书社,2005:134.
[16] 胡大雷.唐宋小说选[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173.
[17] 李宗为.唐人传奇[M].北京:中华书局,2003:112-113.
[18]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3-85.
(责任编辑、校对:王文才)
The Reevaluation of Moral Value in Qing Preach
ZHOU Cheng-ming
(Changchun Socialism College, Changchun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Changchun 130061, China)
“Qing Preach” is a political novel, but not one about party struggle. What it criticizes is not Luzhi, but instead Dezong, the emperor who is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this novel. This novel reveals that everyone’s fate, promotion or demotion, living or dead, is totally in emperor’s hand in a feudal dynasty. The depth and strength of critique on emperor is fiercer than those in other stories, including “Everlasting Regret” and “East Father”. Thus the novel should figure importantly in the history of novel. It is of high moral value in that it criticizes the morality and ethics of a feudal emperor, shows bluntly its disrespect to and negation of an emperor, displays the political courage of Tang novelists, reveals feudal officials’ tragic fate and huge risk in their political career; demonstrates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is the root of all political struggle, and reiterates the historical pattern that the emperor is the source of all disorder and tragedy.
Qing Preach; theme; moral value; political novel; Dezong; critique
2011-12-30
周承铭(1961-),男,吉林德惠人,硕士,副教授,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中华文化。
I207.41
A
1009-9115(2012)03-0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