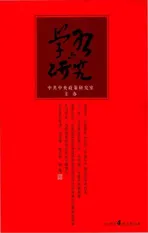前诸子时期的“道”——关于古义之“道”及春秋“天道”思想的考述
2012-01-27梁一群
梁一群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浙江 宁波 315012)
追溯前诸子时期的“道”,意在钩沉“道”概念的来源“出身”。作为先秦诸子核心话题之一的“道”概念,学界一般认为是来自“人行之道”;至于“道”思想的发展,则多认为是从《老子》之“道”出发,衍变为诸子各家之“道”。但是,《老子》之“道”是自我完成而圆满的:包罗万象,纤毫无遗,既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又是其生生不竭的动因——这是一种已经包赅天地万物、且又决定其运行规律的自我完善之“道”。这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意义的“道”,在其面世之前,应该有过一个漫长的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先秦诸子学说的兴起,并非从一个无所不包的“道”开始,然后分化为各家之“道”,相反,高度抽象之“道”应该来自具体之“道”。当然,早先的具体之“道”,并非“人行之道”,而是一种具有沟通“上”(神)“下”(人)内涵的“道”。本文所谓“前溯”,首先是有求于此“道”字古义。
古义之“道”是如何演变为诸子之“道”,例如《老子》那种全能之道的?其中应该另有一番转折,而“天道”思想,于此影响极大。
《老子》之“道”,来自“天道”;然而不曰“天道”,而谓之“道”——此有其赅括“人道”与“天道”二界的全能之“道”意味在。但这种“道”思想话语系统,若欲取代西周以来的“天命”话语系统而居于思想范畴链的顶端,需要有几个条件:其一,“天命”说的话语解释能力逐步萎缩;其二,“天道”说的兴起及发展。惟有能够打通“天-人”二界的“道”,方能成为赅括万事万物的全能之“道”,而在“人行之道”基础上提升的“道”概念,不能达此高度,然而“天道”之“道”,则隐然具此功能——是为“道”字古义流变之一态,也是“道”概念发展的一种途径。探索前诸子时期的“道”,于此亦不能不详加研求。
一、“道”字古义的前溯:沟通“上”“下”之“道”
“道”字首见于金文,通常认为是指人行的道路。其例为:周《易》中,“履”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小畜”初九爻辞:“复自道,何其咎,吉”,“復”卦辞:“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前一爻辞是说:“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走,对于处于幽禁中的人是吉利的”。后二爻辞,则有“在同一条道路上来回是吉利的”之意。通常认为,由此而生发的“人所应经由之道路”、“导致某一方向之道路”诸义,亦可引申出“人们必须遵循的途径”之意,由此发展出准则、规范和规律性等义。但此见解,须再经考析,以求辨证。
⒈张涅先生认为,“‘道’的原始义是原始人在集合地娱神敬神的巫术活动的符号记录。”他指出:金文中“道(衜)”字构型的大致可分为四类组合方式:(1)由“行”“首”构成,如《貉子卣》;(2)由“行”“首”和“止”构成,如《散氏盘》等;(3)由“行”“首”和“手”构成,如《曾伯簠》及《散氏盘》等;(4)由“行”“手”和“止”构成,如《矦马盟书》等。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假如‘道’解释为‘行走的路’,那么指示行走的‘止’就应该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但是第一、三类没有‘止’,在第二、四类中‘首’、‘手’的位置也远比‘止’醒目。显然,‘道’没有特别强调‘止’指示的行走意义。”而与此相映照的,是“除一例(矦马盟书)外,‘首’都占有特别醒目的位置,其无疑是指示着精神活动的意义。”至于四类组合方式中必不可少的“行”,他认为其本义应该“是能通达四方的集合地”,因为“‘行’在那时不会只具有交通意义,通达四方的地方一定有特定的社会活动需要,应该近似现代意义上的广场。‘行’即人集合起来进行巫术活动的场所。”此外,“道”字形出现的“手”和“止”(或一并出现),是“指示形体动作,可以推知为舞蹈动作。矦马盟书的字形,即‘蹈’的古形,‘道’、‘蹈’同源。”事实上,张氏所列典籍证据,如《尔雅·释宫》的“路、场、猷、行、道也”,《说文》的“场,祭神道也”,以及《释名·释形体》的“蹈,道也”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种见解。
⒉“道”字此种古义,至春秋之际,人已多昧。但《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8世纪末),随国大夫季梁“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的说法,却是对此传统的回顾和体认。季梁所谓“道”,正是沟通连接“上”(神)“下”(民)之“道”。“道”字此义,亦可以《国语·周语上》内史过(公元前7世纪中)“道而得神,是谓逢福”提法佐证之。内史过之说,是与“淫而得神,是谓贪祸”并提的,其所谓“道”,内容是“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以此为前提,“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于是“神明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按此,“道”属于沟通“人”“神”二界的“途径”。
⒊“道(衜)”字初义,最初并非是“行走”或“人行之道”之意。这一点,长期研究中国文字及殷周文化的日本学者白川静曾指出过。白川静对“道(衜)”、“途”,以及与之相关的“术(術)”等字的释义如下:
在古代,道路与外界相接是最危险的地方,比如停在他乡有危险,在道路上设关卡,从古代文字的构造上也能了解。道,是携带异族之首,因此是引导敞开的意思。途,将咒针立于地上,是表示防止邪灵从其途侵入进行祷告礼仪的字。术,在道路中是意味用具有咒灵的兽进行祷告礼仪的方术的字等。
白川静此见,以他对金文的释义为基础。对此,白川静在《金文的世界》中,有过相关的介绍。例如金文中有关于军事活动的“先省”、“省道”等词,他认为“就是把敌人加诸道路之上的诅祝等障害予以祓除的行为,因此那不是单纯的侦察行动。”因为“道路在非常时期,常被施加许多诅祝……古时出外旅行,固须行祖道之祭;而在道途之上,亦恐有不识之神作祟,故作战时沿途先行祓祟之仪式,以确保进攻道路之安全就叫‘先’。”准此,上古人对“道路”的认识,并非泛指外出“行走”,而是含有军事性活动(若更早,则是外出觅食、狩猎)的祭祷之义。这种“道”,被赋予祓祟和诅祝性含义,以求消除凶险而便于出行,体现于具体的字符,则是对“衜”造字中的“行”和“首”两种元素的强调。按此,《易》之“道”(见上),亦属此类祭祷占卦活动所关注的道路安全问题,其中应含有神祝活动及其祭祷之义。
⒋这一解释,显然不同于历来的见解。《释名·释道》中对“道”和“路”曾有过一个互联性的解释:“道,一达曰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此种说法,认为“道”字源于“人行之道”,具体可落实为“践蹈”。因此,有意见认为,《散氏盘》及《矦马盟书》的“道”,其中指示“首”的字形,应为“舀”,其实“皆从‘舀’得声,与‘道’字异构,就字形而言,‘舀’疑为‘首’之形讹。致讹的原因,可能与形体相近、声音亦相近有关”。按此说法,“首”在“道”字构型中并不重要,它应是“舀”之形讹:而“舀”与“行”的组合,则为形讹之“道”(衟);与“足”组
合,则为“蹈”——二者都是指示着“人行”义的。如此,方可与上引《释名·释道》的释义相应。
⒌学界另一种意见认为,“道”的源词,应该是“首”,“道”字是因为“道无歧路,直通直达,型同颈首”而得名。此说从“首”本义为“头”而引申为“始”入手,又从“始”引申而为“根本”。该说从“道”字源出于“首”而展开,认为:“另一方面,因为首颈相接,是人体直达的顶端,所以又有‘直’义。《礼记·郊特牲》:‘首也者,直也。’又引申直述其事。如‘自首’。”
⒍上述前一说否定“道”字型构中有“首”,而代之以“舀”(“践蹈”义)。然而,如果此一表示“践蹈”义的“舀”,与同样表达“行走”义的“止”在金文“道”字中并存,则为同义重复——造字型构,似无此必要。而后一说认为,“道”字构型的最基本元素,不在“行走”而在于“首”,其理由是“道”的“直通直达,型同颈首”。但既如此,金文“道”字何以将此“首”与表示“四通八达”的“行”,而不是与某种表示“直通直达”的符号作一组合?“行”,金文作“ ”,而甲骨文作“ ”,似非“四通八达”而经画交界之义,当是周边辐辏而“四方来集”之所,亦为“四通八达的处所”。上古交通初辟,凡有“四通八达”之处,当为重要
场所,某个中心所在,此“ ”与后人所谓的“道路”关系,当是在有关出巡(或出征)、田猎(或镇抚四方)的活动之前,须在此举行某种告祭、祈神祓祟等仪式,而并非指示那种未经过诅祝仪式予以祓除的、因而很少有安全感的荒路四野。或者可以这样说,唯有经过诅祝仪式而被施加了本族(我方)神灵影响的“道路”才是安全的,其标志是能够保证我方行动的有利进行。
准此,早期“道”字来源,当与上古祭祷神祇仪式有关,“道”字本身,含有祭祷神祇,以沟通“上”(神)“下”(民)之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自古以来,祭祀与战争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关系重大。“道”蕴涵有沟通和 连接“上”(神灵)“下”(军国之事)之意,这对后 来“道”概念的发展,当有极大的影响。虽然上 古“道”字所含的祭祀神祇的意蕴,未必直接与 “天象”挂钩,但其所含的沟通“上”(神)“下” (人)内涵,应是其成为打通“上”(天)“下”(人) 的全能之“道”词义源的重要因素。
二、“天道”思想的衍变及其与“道”的关系
殆至春秋时期,古“道”字义衍变,大致分别 向着“下”(人)、“上”(天)两个方面作展开:前者 为“人行之道”及其字义的拓展——即“人道”(被 当时人称为“道”);后者为“天道”。《老子》全能 之“道”形成,即此两种思想取径的融合,不过不 是出于“人道”的提升,而是“天道”的“扩容”—— “人”取法于“天”以规划“人事”(社会活动)准 则,而并非以“人事”(人道)来形塑“天象”(天 道)。
对《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国语》等典 籍的分析表明:周代以来,“道”字的用法,逐渐 多倾向于“人事”方面,而上引季梁、内史过等 人所说的古义之“道”,几乎成为例外,这大概与 当时人文理性思潮的兴起有关。三代以下,社会 文明繁盛,道途之行的祝诅祭祷,已多衍变为一 种仪礼,如典籍(《左传》《周官》《礼记》等)记载 的“祖道”神祭祀,而“道”则衍变为“人行之道”, 是为(能够“沟通上下”)“道”字古义发展的向 “下”(世俗)一路。但与此同时,古“道”字义的 向“上”发展,有与“天”相接之势,是为“天道”思 想。但此“天道”思想的发展,并未直接指向全 能之“道”。
按典籍,上古时曾有过一个“民神杂糅”阶 段,集体性活动的敬神娱神曾经泛滥到“家为巫 史”的地步,然而在著名的“绝地天通”之后,感 通神明的事务已由特定的世袭家族掌管,“世叙 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此后即建立“民神不 杂”的社会文明系统。按今人理解,这意味着古 人开始从“人神”同源(其中有所谓“血缘纽带” 观念,认为人、特别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们是“神” 的后裔)的意识,逐步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过渡。特别是西周以降,以“敬德”精神为标志的理性化自觉意识出现,“自贻哲命”观念日益具有重要作用,“道”字古义日渐淡化,亦属势所必然。然而在此过程中,对“天”的信仰如果尚未有所取代,人们仍须通过原始思想资源的再运用来加以表述——此为早期的“天道”思想,是遗有传统的“天命”观痕迹的。对此,按其历时性的发展进程,予以详述。
(一)“天道”观念的初始形态及其流行:“天命”与“天道”
最初的“天道”思想,从“天命”观的转述而来。所谓“转述”,是因为其中已含有一定的“规律性”内容。
1.《左传》中“天道”一辞,首见于庄公四年(前690)邓曼所谓“盈而荡,天之道也”,语出当时多巫觋之风的南方楚国,似为后世“天道”概念之滥觞。
此“天道”含有两种含义:一是“天命”的别称;二是含有“规律性”的意味。这种认识,某种意义上应该来自对天象运行的观察,及其规律之了解。但该时自然之“天”思想尚未成熟,不容有完全脱离“天”意的“天道”思想出现。例如,此前9年(即公元前699年),同是这位邓曼,曾有过“天之不假易”之语(《左传》桓公十三年),其所谓“天”,当然是有意志的人格之“天”。此外,当时另有“天常”一辞,与“天道”相似,人们也以伦理性的内涵来释义。例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前609),鲁国大史克曰:“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檮杌。”
2.较具“规律性”意味的“天道”观,与此同时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的三晋地区。其时,晋国史苏所谓“天道”(前672),已有后来“天道好还”的意味(《国语·晋语一》);其后狐偃对“天事必象”(前644)释义,亦有“循环规律”之意(《国语·晋语四》)。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天道”观念已经颠覆了西周以来“天命-敬德”(“天命靡常”与“唯德是视”对应)话语框架。直至60多年之后,当鄢陵之战(前575)结束时,晋国大夫范文子引用“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古箴,其实仍然是将“天道”理解为“天命”之表现。
其时以“天命”观思想而释义“天道”概念,甚为普遍。周定王(前606~586)朝的大夫单子之所谓“天道赏善而罚淫”,此一“天道”,实为“天命”。而《左传》宣公十五年(前595),晋国伯宗所谓“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其谓“天道”,实为“天德”,亦属“天命-敬德”叙事模式。
3.但是,礼乐文明制度的衰败,继续增强人们对“天命”的怀疑和不满;而“天命”既难全信,人们转而探求“天道”,亦属正常合理。从《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单襄公与鲁成公对话(前575)看,可知上层社会的讨论中,将“天道”知识系统,归诸“瞽、史”传统,但不以“天道”为然,而将治乱之迹,归诸执政者的“德”行。古代瞽、史阶层掌天文知识,对天象运行之探索,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天道”观念之兴起,当与之有关。但是,出于上古“瞽史”传统的“天道”观,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和不确定因素。当时计算天象与人事之间的相关结果,相当复杂,并非仅仅是对客观规律之“道”的把握和理解。例如公元前655年,晋国假道灭虢,围虢国上阳,晋献公问卜偃克城之期,卜偃答以“童谣”及“天象”两种因素的结合,而不仅根据“天象”。(《国语·晋语二》)
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天象”之“道”的理解,是极端不同的。《左传》昭公十一年(前531),苌弘答周景王问诸侯国凶吉之预测,根据“岁”(木星)运行所在方位而作的先后两种判断:当“岁在豕韦”时,“蔡凶”,“楚将有之,然壅也”;而后“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但子产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此事的真正意义在于:“天”以此而昭示了“德”的重要性,而无德者即使暂时得益,终不过是遭受“天”惩罚的前奏而已。对此,子产有云:“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恶周必复,王恶周矣。”子产在此,表达了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认识:“盈”及“复”的往复运行都是“天”的意志使然。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天”的意志,表现为“盈”与“复”来回往复的规律性运行。在子产那里,规律性的表现并未被纳入“天之道”的视阈,而仍在作为人格神的“天(命)”的意志范围内;而在苌弘,“天象”运行是规律性的表现。
⒌“天道”观念中规律性内容的充实,某种意义上应归于“数”因素的渗入。见于公元前七世纪前期的单襄公语“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国语·周语下》),应反映了当时人对“天”、“地”运行中“数”因素作用的理解。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铸无射钟,问律于伶州鸠,伶州鸠有“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的说法,认为十二时辰反映了“天道”,而乐理知识中具有规律性意味的数(“十二”),恰可与此“天道”相应(《国语·周语下》)。在此,数(“十二”)可以表征“天道”自我运行的轨迹。按此具有一定规律性意味的“天道”与“人事”作对应,并对后者有指导作用。但此所谓“数”,应为“术数”,当与上古巫史(祈禳)文化有关,因而其所谓“规律性”,也并非仅仅是客观的研究对象。
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层多以“天命”释义“天道”,而其对应之法,应该是上古祈禳之术的“人文”型转换(礼、德)。例如,《左传》文公十五年(前612)季文子所谓“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前516)记载:“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星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在此,“天道”是既可以“禳祓”而影响之,也可以“礼”或“敬德”来加以改变的对象。晏子极力反对“禳祓”,主张“敬德”来影响之:“若德回乱,民将流之,祝史之为,无能补也。”由此而言,《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前551),晏子所谓“君人执信,臣人执共(恭),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此一“天道”,亦为“天命”,因而可以“敬德”感应之。
(二)“天道”观念的发展:“天道”与“道”
当“天道”概念逐渐为人们所习用之时,“道”与“天道”,各有所指,有时甚至相反,因而不可互替。
1.《国语·晋语三》记载秦穆公君臣讨论是否救济晋国之事(前647),秦穆公以为:“天殃流行,国家代有。补乏荐饥,道也,不可以废道于天下。”公孙枝则说:“君有施于晋君,晋君无施于其众。今旱而听于君,其天道也。君若勿予,而天予之。……”在此,“道”与“天道”两种概念,非但不同步,甚至相反。其中秦穆公所谓“道”,是“道义”,属于“人之道”;而公孙枝所谓“天道”,虽有“规律性”的意义,然其所谓“天”,仍是操有予夺之权柄者。在此,按照“道”行事,与按照“天道”行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
2.同样的事例,又见《左传》襄公九年(前564)晋悼公与士弱的对话。当时,晋悼公问以“天道”,而士弱认为,“人事”的确定性,并非在于“天道”,而是取决于“道”(即“人之道”范围内的)“有道”、“无道”之“道”。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在此,“道”与“天道”相对而异,既不与“天道”想通,更非囊括“人—天”之“道“,仍是游离于“天道”的“人之道”。与此相似,襄公十八年(前555)晋国君臣论事,董叔以“天道多在西北”为据,认定晋军必胜,而更具权威性的叔向认为:“在其君之德也。”不认可“天道”说。叔向所谓“德”,即是所谓“有道”“无道”的“道”。自此而言,当时所谓“天道”,似是出于瞽史传统的缘故,因而未能在诸如晏婴、叔向、子产,以及孔子等人文型知识者那里得到热烈的反响。
3.在那时人看来,人事方面的“道”(或君主之“德”),与“天”所眷顾(“天命”、“天之道”)者,有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轨迹而运行。《左传》昭公元年(前541),晋国执政赵孟与秦国的出走公子(后子)有如下对话:
赵孟曰:“秦君如何?”对曰:“无道。”赵孟曰“亡乎?”对曰:“何为?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力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赵孟曰:“天乎?”对曰:“有焉。”赵孟曰;“其几何?”对曰:“鍼闻之,国无道而年谷熟,鲜不五稔。”
在此,“天命”与“数”相联系,而秦君是否有“道”,这对于“天命”眷顾所决定的“数”(国运、世运),并无多大的影响。而在此100多年前,著名的王孙满曾申言:君主之“德”(有道)能够影响和决定其国运(世运)之“数”。此间,如果按后子的说法,“命”与“数”的关系是确定的,“天”有相对独立的运行轨迹。这暗示着:“天命”及“惟德是依”的观念(“天命—敬德”叙事模型)动摇之后,对客观规律性的“天道”之研究,早已进入上层社会的话语场阈。
(三)“天道”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祓禳”与“顺因”之“道”
对于“天道”的探求,在渗入五行及阴阳等思想内容以后,逐渐更多获得了可被研究和掌握、并以之改变人自身命运的特征。此一转变,表现为从“祈禳”之术的奉行,到“规律性”内容的掌握。是为“天道”思想的成熟期,直接影响《老子》之“道”的形成。
1.《左传》昭公八年(前534)记载陈国有灾,郑国的裨竈与大夫子产讨论此事。裨竈依照陈国属水、楚国属火的特点,探究它们相互关系在五行依次运行中的变化,得出陈国五年后的“复封”、及其在五十二年后“遂亡”于楚国的结论,明确指出这是“天之道也”。“天道”观念加入了五行因素,对其规律性方面的研究更趋于精密化,这是其摆脱人格化的“天命”“天意”而归属于客观规律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同样对此事的分析,并非所有的人都持这种观点。
是年,晋平公同样以陈国灾事问史赵。史赵认为,陈不至于因此而灭国的原因是:其一,“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其二,“盛德必百世祀,虞(陈先祖舜)之世未数也。”前一理由,与裨竈所谓“天之道”相同;而后一理由,是说最终决定陈氏享国世数的,是“盛德”,是“人事”方面的因素。这是兼合秦国后子的“数”不在“德”说,以及历史上著名的王孙满“在德”说的一种混合型思想。
2.当然,“数”与“德”两种观念因素的遇合,又可表现为祈禳而“交感”互通的行为模式。《左传》昭公十八年(前524),子产提出著名的“天道远,人道迩”说,这是为了否决裨竈用“瓘(珪)斝(玉爵)玉瓒”禳火(灾)的。然而两个月后,子产即又举行了补偿性的祓禳。与精通“天道”的裨竈相同,子产也认为有必要用祓禳来“振除火灾”。只是,裨竈所依仗的“天道”,含有甚浓的传统巫术感应思想内容;而在子产看来,基于“天道”的祓禳,不如基于“人道”的祓禳更为重要。子产的祓禳,其名义是“礼也”,并非对应于“天道”,而是尊顺“天命—敬德”的话语传统。裨竈的“天道”观,与子产的“人道”观一样,都有“交通互感”的思维模式成分:“天道”给予“人事”的影响,是可用“人事”(祓禳)来改变的。此一“天道”观念中,明显有“道术”的影响。
3.此一认识,另见于《国语·周语下》所载周大夫单子论苌弘在成周筑城墙之事(前510)。其中所谓“天道导可而省否”,明显具有人格神意志的痕迹;至于“将天以道补者也”说,韦昭注曰:“以道补者,欲以天道补人事也。”则此所谓“道”,虽可比附于“天”而被认为是“天象”运行之“道”,但其含义,与裨竈的理解有一致之处,即是以祓禳活动而避凶趋吉之“道(术)”。单子认为,苌弘“将天以道补”的做法必招致“三殃”:“违天,一也;反道,二也;诳人,三也。”三种因素中,居于天人之间的,是作为“道术”来理解之“道”。“道”字在此,应该是沟通人天两途之“术”。联想到季梁及内史过释义之“道”(见本文第一部分),可以隐约看到“天道”观念的思想取法来源。
4.表现为祓禳活动的“天道”思想,与基于天象运行规律而掌握的“顺”(或“因”)之“天道”思想,是两种取径不同的“天道”思想资源,前者似来自五行运行及其数术的掌握,后者似来自阴阳往返循环规律的掌握。前者所谓“道”,可与“术”互换运用;而后者之“道”,则已超越了“术”的层面,其例为公元前五世纪初(来自楚国的)越国大夫范蠡言论。
在范蠡,被表述为人格神的“上帝”有双重的体现:既仍具有意志及其执行能力:“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国语·越语下》)另一方面,其意志又和能力,又须在规律性的意义上得以认识。这一点并不新鲜。但其所谓“上帝不考,时反是予”,所谓“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国语·越语下》),值得重视。在此,“反”是一个重要概念,它表现在“上帝”、“天”昭示于人的“天道”中:“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同上)不仅此也,在此规律性的“天道”观图景中,人必须遵照(顺因)规律以取得最大的成功:“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用则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强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彊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国语·越语下》)
察此“天道”观所述用途及其思想内容,似是来自对战争规律的把握。但若联系前述裨竈以祓禳影响“天道”的观点来看,又与上古所递传的“人天”感通知识系统不无关系。虽然古代兵家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亦有祈禳厌胜之术内容,但范蠡“天道”观的关键,在于对“反”(循环往复规律之谓)的把握。所谓“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无非“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关键在于“无过天极,究数而止”。此即表现为对于规律性的“反”的把握运用:“必顺天道,周旋无究”。范蠡所言“天道”,已然引进“阴阳”概念,同于《老子》所阐之“道”,然而仍称之为“天道”,而不是似《老子》的那种更具概括性的“道”。然而,此所谓“天道”,其实仍只是“天之道”:它是“天”所生发者,其主格为“天”,而不是“道”。这一提法,显然有异于《老子》中“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提法。所谓“天之道”,是杂糅了前者(天)的意志、能力,以及后者(道)的规律性运行的结果。因此,被赋有“人格神”及“自然”双重意味的“天”,其运行的规律(“道”)不管如何,都只能是从“天”而生。“天道”既然仍为“天之道”,则其所谓“道”,就不可能是“象帝之先”(《老子》四章)。
范蠡的“天道”,是权谋之士对于包括史官阶层的天文历象研究的概括和理性升华。这种“天道”观,范蠡的同僚文种似亦未能掌握,但同样来自楚国的伍子胥却颇为熟稔。公元前484年,吴王将伐齐,伍子胥进谏言,有“天命有反”之说(《国语·吴语》),韦昭注曰:“反,谓盛者更衰,祸者有福。”此种“天命”亦具规律性表现的思想,当属人们在“天命”“天道”杂糅混用期的认识。另外,《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伍子胥被赐死时所谓“盈必毁,天之道也”,亦可证当时人认识中,“天命”与“天之道”二者所含,一定程度上仍可相互融通。
(四)前诸子时期的“天道”思想,及其与“道”的关系之小结
春秋时期的“天道”,某种意义上说,是西周“天命”观的衍变。所谓衍变,是因为其中出现了“规律性”的意味;而此一“规律性”的意味,难以沿用“天命”作表述,故曰“天”之“道”(“天道”)。“道”与“命”不同,在于其较为客观、且含有(对“人”而言、并非是对“天”而言的)“预期性”、“掌控性”诸义,而所有这些涵义,在上古祭祈之“道”词语的具体运用中,早已蕴含。由此而言,“天道”之“道”,并非来自“人行之道”的直接提升,从根本上说,它是上古祭祈之“道”的新衍生。然而,此一意欲打通“天-人”二界的新概念,未称为“道”,而仅谓之“天道”,大致是局限于“天象”而言。这是因为,“天”之“象”及其运行轨迹,虽有指示引导“人事”活动的意义,但其内涵之说明、勾划,当时尚未与“人道”(道)完全合一,也即尚未熔铸成为囊括“天-人”二界而有机统一的“道”思想体系,故此“天道”与“道”,当时并未融为一炉。从“天命”演变而来的“天道”思想发展,表现为“命”的痕迹逐步弱化,以及“道”的意味愈益突出。
春秋时期的“道”(“人行之道”),源于上古的祭祈之“道”,是其“祛魅”之后的转义;而其未尽转义者,则为“祈禳”之术,即当时“天道”话语拥有者如裨竈等人所实行的。因此,上古祭祈之“道”,一转而为“人行之道”,一转而为“天道”之道;从后者,可衍生“规律性”、“预期性”诸义,又转存有“祈禳”、“可控性”诸义,即是不同于“天命”概念的“天道”。就此而言,春秋时期的“天道”,是西周“天命”观念大致穷尽其合理的解释效能之际,社会上层、知识精英转而运用上古祭祈之“道”这一词语,来表述当时发见的新义之表征,而其中容有“祈禳”与“规律性”、“预期性”及“可控性”诸义的混合,是其重要特征。此一“天道”,正是后世打通、并囊括“人-天”二界,因而成为最高概念的“道”思想系统的前驱。
综上,前诸子时期的“天道”观,始终与传统的“天命”观(“天命-敬德”话语系统)有若隐若现的关联,而与“人道”之“道”,始终未能一致。“术数”的应用,是“天道”思想不断发展的内在支持;正如“礼”、“德”等概念的发展,是“天命”观的内在支持——这表现为各自不同的“祈禳”方式。此外,由后者所支持的“天道”观,如晏婴等所为者,其内在理念,实仍为“天命”思想,此可上接子产,下启孔子“君子之道”(人道)。而孔子之“道”的思想贡献之一,是对传统“礼”、“德”等概念的内化(以“仁”为内在支持)、普泛化。
在尚未上升为赅括“人-天”二界的“道”(“人道”)中,不可能抽象出具有高度赅括性的全能之“道”——如《老子》之“道”。同样,在专注于祈禳之“术”的“天道”中,即使因为有“术数”的渗入而表现出某种规律性,且具有打通“人-天”的功能,也不能成为摆脱“天”意志控制的自然之“道”;而由兵家权谋之士揭示的阴阳刚柔往还盈缩“天道”,亦仍为“天”之“道”——但凡此均非《老子》之“道”。《老子》之“道”,当产生于“自然”之“天”的思想形成后,而此“自然”之“天”的本质性内容,应该是“内化”于“人”的,同时成为“人”内在之质。凡此“道”思想的前提,其时均未形成。
三、前诸子时期之“道”的回顾与展望
对于“道”字用法的历史性分析表明:含有祭祷和祝诅祓除之义的“道”,衍变为“人行之道”,是在文明昌化之后;然其沟通“上”(神)“下”(人)的功能并未被忽略,而是转用于表述能够影响“人事”的“天象”运行,是为具有祈禳功能的“天道”之术,此为古义之“道”衍变的一种形态。而“人行之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道”(人道),是古义之“道”发展的另一形态。
含有祭祷祈禳意义的“天道”源自上古举行军国之事——例如出征、镇抚等等——祭祷仪式之“道”。当文明开化之后,“道”字用于祓除路途不测和险阻的祭祷意义日益淡化,而以其指示“人行之道”的功能取而代之。然而,由此衍变而生的“正确的途径”、“道义”、“法则”、“方法”诸义,只是人间世的法则(人道),而不是“自然”之“道”。正如上引诸文所显示的,“道”(人道)的表现,有时与“天道”不相一致,因而它亦未能统括“人-天”二界而成为最高概念之“道”。
同样,前诸子时期的“天道”,亦仅只是“天”之“道”,尚未抽象上升为《老子》书中“天”所效法之“道”(“天法道”)。在此,具有意志和决断力的人格之“天”,可以祈禳之术影响之,这是上古祭祷祝诅之“道”的向“上”(天)发展的取径。当然,按照子产的“道”(“人道”)思想,“天”也能用某种方式——例如“礼”、“德”——来影响之。其时,“天道”仍是人格之“天”与某种规律性表现的集合概念,而“道”(人道)则是人格之“天”与宗教伦理性的准则(礼)的集合概念。
按此,古“道”字义在前诸子时期的发展,已分衍为“天道”与“道”(人道)——此可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想取径,如裨竈之与子产。后者思想作为一种资源与诸子学说兴起时的对接,表现为孔子之“道”(人道),反映了知识界重建西周“天命-敬德”话语系统(文明礼乐制度)的努力,而其内在支持者,是与“礼”为表里的“仁”(是故孔门弟子认为,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作为儒学对立面的墨子“天志”说,应是较“天道”说更为古老,远溯于上古传统的思想资源。对于前诸子时期的“道”(人道)思想文化遗产,孔子之“道”,是为顺接;墨子“天志”,则为反拨。以儒家之“道”(人道)为基点,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出发,可臻于荀子所谓“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但荀子之所谓“道”,亦非打通“人-天”的全能之“道”。
由“道”(人道)而向上与“天”相融合、以打通“人-天”的思想系统构筑之努力,来自儒门的《易传》,以及思孟学派。这在《中庸》、《孟子》,是为“诚”(《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下》:“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而在《易传》,此则为“善”之“性”,(《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对此“善”之“性”的理解,是某种规律性内容的掌握。(《系辞下传》:“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生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所谓掌握,其实是对此“性”之“理”的一种认识,(《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由此生出人世社会各项准则。(《说卦传》:“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但此能够与“天”“感而遂通”(《系辞传上》)之“人”,其“性”质——即能够勾连“人-天”的自然之性的推明,尚需有一种学理上的基础,而这种讨论的发萌及其过程,见于《庄子》书——尤其展现于其外篇。
《庄子》书对“人-天”相通的自然之性的讨论,影响了被后世称为“道家学派”的全能之“道”形成。前诸子时期的“道”,如何可能衍变为赅括“人-天”二界的全能之“道”?这取决于传统的人格神意义的“天道”,如何可能衍变为自然之“天道”。对此,《老子》书中并无解释——《老子》之“道”一旦问世,似乎是立时就自我完整的,浑无涯际,不可得其端倪。但是,《庄子》书对于“天”的讨论,可为此揭秘提供线索。例如,从《逍遥游》“天地之正”、“六气之辩”出发,以至于《齐物论》“天钧”、“天府”、“天倪”等概念,此为战国时期讨论自然之“天”的思想取径。以此《庄子》内篇的讨论为前提,拓开《庄子》外篇对于自然真常之“性”(如《骈拇》、《在宥》所谓“性”,《马蹄》篇所谓“真性”“常性”),以及对于“物”之精微基质(精、气)的研求(如《秋水》、《知北游》诸篇),彻底摆脱了有意志的人格之“天”(天志、天命、天道)而导致先秦时期“道法自然”观念,为“道”思想系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