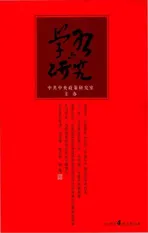廖纪思想的学术定位
2012-01-27葛荣晋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廖纪(1455~1532)字廷陈(时陈),号龙湾,生于直隶(今河北省)东光县,原籍广东琼州府万州陵水县(今属海南省万宁市)。明弘治三年(1490)进士。历任考功司郎中、太常寺少卿、四夷馆卿、工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吏部尚书、《献皇帝实录》监修官、《宪庙实录》总裁、少保兼太子太保等职。主要著作有:《大学管窥》、《中庸管窥》》、《性学原》、《心学原》及若干《奏疏》等。他是明中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一、廖纪思想的社会背景
廖纪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主要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从明正德年间起,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空前激化,明王朝开始由盛世转向衰世,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当时社会政治危机的主要表现是:(一)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赋税、徭役的极度繁重,全国各地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多次农民战争。其中最大的是正德五年(1510年)在京畿地区爆发的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公开提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口号,充分地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推翻朱明王朝和建立农民政权的强烈愿望。(二)国内少数民族暴动。由于明朝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在云、贵、川、两广等省相继发生了少数民族暴动,如广西的瑶族、侗族起义;川西的藏族起义;广东的黎族起义;云南、贵州的苗族起义等等。(三)来自塞北蒙古贵族的不断侵扰,不但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也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官僚和宦官(如刘瑾专权等)、朝廷与地方王(如朱宸濠叛乱等)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总之,自明中叶以后,明王朝处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困境之中。
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面前,地主阶级中的社会改革派经过深刻的反思,认为它是“道学不明”、“士风不正”所致。自元代封建统治者把程朱理学抬上统治地位、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之后,明代仍之。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程朱理学,日趋僵化,愈益暴露出空疏误国和虚伪迂腐的弊端。所谓“虚伪”,是指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口谈仁义,行若狗彘,是一群十足的伪君子。正如明末李贽所说:这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三教归儒说》)“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所谓“迂腐”,是指他们只知空谈性理之学,死背程朱之书,醉心于功名利禄,对于经世致用的“实学”却一窍不通。在现实问题面前,一个个束手无策,是—批无用的迂腐之徒。正如与廖纪同时代的王廷相(1474~1544)所说:“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则暗然而不知。”(《雅述》下篇)
廖纪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亦深刻地揭露了程朱理学所带来的“士习大坏”的社会弊端。他指出:“国家所赖以制治保邦、修政之事,惟在多士。士风淳,则人皆务实;士风漓,则人皆务名。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当其时士习淳朴,绝无伪巧,勉修职业,不务虚名。故事治民安,国家赖之。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嘉靖四年九月上“正士风,重守令,惜人才疏”》)这就是说,许多士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往往出于“功利”目的,把程朱理学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在学风上则表现为“大率牵合附会,必求不背传注而后为得”。在士人登第之后,或“尽弃其前”,即把登第的敲门砖扔掉;或“刻意枝叶之文”,即专注留心于传注之末节,而不从事于有益于民生、世道的学问。究其原因是程朱理学衰颓、士人溺于科举功利所致。
因此,当时地主阶级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正士风”,批判程朱理学和佛老的“空寂寡实之学”,大力提倡“经世之学”。于是,随着社会危机的产生和程朱理学的衰颓,从程朱理学中分化出了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以适应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二、廖纪思想的学术流派
明中叶的实学思潮,在哲学上,主要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从朱学中分化出了一个以罗钦顺(1465~1547)、王廷相(1474~1544)、杨慎(1488~1559)等人为代表的实气实学派别。他们反对程朱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之说,提倡“元气之上无物”的宇宙观;反对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只有“气质之性”;反对“知先行后”说,力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宣传“理欲统一”的思想。二是随着程朱理学空疏本质的暴露,从程朱理学中又分化出了王阳明(1472~1528)等人为代表的实心实学派别。不管是实气实学派别还是实心实学派别,在当时,都是极具创新意识和生命力的哲学流派。
在明中叶进步的哲学流派中,廖纪的学术思想主要是属于哪一哲学流派?根据初步研究,我认为他不属于以罗钦顺(1465~1547)、杨慎(1488~1559)等人为代表的实气实学派别。历史上,廖纪在《嘉靖五年正月请复杨慎等原职表》中,向嘉靖皇帝请求复其原职,在政治上同情杨慎。正德十六年,廖纪由吏部左侍郎升任南京吏部尚书。他在吏部的同仁、时任吏部右侍郎的罗钦顺接了他的职位,出任吏部左侍郎。对于廖纪赴南京任职,罗钦顺以《送太宰廖公之任南京》一诗相赠,诗云:“春风飞盖出长安,兰臭弥襟执别难。河近故园分马颊,山临东省见龙蟠。经纶业共年华远,举措功归士习端。便儗从公从未得,永怀遥寄碧琅玕。”嘉靖元年,明世宗诏王阳明入朝任南京兵部尚书,而王阳明“不赴,请归省。”(《明史·王守仁》)廖纪转任南京兵部尚书,即是接任王阳明“不赴”的职务。而他原先的南京吏部尚书职位则由罗钦顺接替。对于廖纪转任兵部尚书,罗钦顺撰写《赠大司马廖公参赞南京守备机务序》一篇,以表示他对廖纪寄予厚望。由此可见,廖纪虽然在政治上同杨慎、罗钦顺等同仁虽然友好,甚表同情,但是在哲学理念上却不是同一哲学派。他在理气之辩上未见他发表什么观点,在人性论上,他既反对程朱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也不赞成杨慎、罗钦顺的“气质之性”的性一元论,主张“天命之性”的性一元论。
在我看来,在明中叶哲学派别上,廖纪基本上属于王阳明的实心实学流派。他在《嘉靖四年十二月议席书之言疏》中,曾两次会推王守仁,以补提督边务员缺。在《嘉靖五年正月请复杨慎等原职表》中,对于在“大礼议案”中被罢官的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季本等人甚表同情,上疏请求嘉靖皇帝复其原职。他不仅在政治上对王阳明及其弟子表示同情与支持,而且在哲学理念特别是心性学说上,同王阳明甚为相近。他是明中叶实心实学流派中的重要成员。
三、廖纪思想的学术倾向
我们通过王阳明与廖纪思想的比较,证明王阳明与廖纪在学术倾向上虽有某些差异,但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学术倾向上,皆属于实心实学型态。
(一)在经典文本上,他们都是高举《礼记》中的《大学古本》批评程朱的《大学今本》(亦称《大学改本》)、高举《中庸古本》批评程朱的《中庸今本》(亦称改本》)。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以金都御史巡抚南赣州、汀州、漳州,他编撰《大学古本》、《中庸古本》,包括《大学古本序》等,正德十六年“始揭致良知之教”,开始与程朱学派商榷。廖纪继王阳明的《大学古本》、《大学古本序》等,八年之后,于嘉靖五年完成了《大学管窥》一书。廖纪的《大学管窥》,根据他与王阳明及其弟子的亲密同仁关系,有可能受到王阳明及其弟子的思想影响。
将王阳明的《大学古本序》与廖纪的《大学小序》相比较,廖纪虽不如王阳明激烈,但都将批评矛头指向程朱学派的《大学今本》,批评他们违背孔子、曾子本义。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大学古本序》中,痛斥朱学之支离,“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因为他“惧学之日远于至善”,故“去分章而复旧本”。又将其《大学古本傍释》说成是“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的著作。廖纪在《大学小序》中,只是说朱子的分经补传“于古本小异”,亦是“非敢求异”。但是,他因程朱的《大学今本》学者宗之五百余年“不复知有古本,深为此惧。”所以,他对程朱的《大学今本》也提出了批评,指出:
《大学》一书,乃孔子所遗,曾子所受,而门人所记也。汉儒收入《礼记》第四十二篇,程子表而出之。愚尝详味古本,纲目分明,次第不紊,初无经、传之别,亦无阙文错简之误。每于熟思之余,偶有一得之见,并所闻切当之论,书于逐节之下,以备遗忘。积数十年,不觉成集,以求正于有道之君子。今本《大学》乃更二程子并朱子改定,分经补传,于古本小异。朱子《章句》注释详矣,学者宗之已五百余年,不复知有古本,深为此惧。故释古本全文以示后学,非敢求异,盖欲其观古本、今本之不同而知所用力也。
可见,廖纪所深惧者是学者“不复知有古本”。他所以诠释《大学古本》全文,只是欲使学者“观古本、今本之不同,而知所用力也”。王阳明与廖纪虽在态度、口气上有所不同,但都是针对朱熹的《大学章句》而发,都是要“复旧本”,这是两家所相同的。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编撰《中庸古本》、与朱熹学派商榷。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廖纪撰写《中庸管窥》。他在《中庸序》中,认为《中庸》“与《大学》实相表里”,是“贯六经之道,纲目功效,秩然有序而不紊,诚千圣传授之心法,百王致治之大经”。数十年虽“研精其微意”,“必质诸经书之言并先儒之论有合焉。”积十余年而成书,“以求正于有道者。”不管是王阳明的《中庸古本》还是廖纪的《中庸管窥》,都是针对朱熹的《中庸章句集注》而发的。经典文本的争论,实际上是不同学派的理论观点的分歧和论辩。
(二)在性学上,廖纪与王阳明都主张性一元论,极力批评程朱学派的性二元论。程朱学派从他们的理本论出发,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理”,“气质之性”是“气”,从本体论高度回答了人性善恶的来源。
王阳明立足于他的“心也,性也,天也,一也”(《传习录》中)的心本论,认为“性一”而非“性二”,只有“天命之性”,根本不承认“天命之性”外还有什么“气质之性”的存在。他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传习录》上)既然“性即理也”,所以,在内涵上,“性无不善。”(《传习录》中)既然性是“至善”,由性衍生出来的“四端”之气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气也是善的,人性本不必分为二,从而修正了程朱学派的性二元论。
廖纪认为程朱之言违背“经书圣贤之论”,五百余年,“世皆陷溺其说,迷而不反(返),深可惧也”。为了世人不为“异说所惑”,“恐夫流弊之不止”,他“不得已本诸圣之论作《性原》,以开后世之惑。”在他的《性学原》一文中,根据他的性“本善而无恶,纯乎理而不杂于气质”的性一元论,也尖锐地批评了程朱学派的性二元论。他说:
夫何孔孟既没,性学不明?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杨子曰:“人之性善恶混”,皆昧乎性之本善而兼以恶言之也。张子曰:“天地之帅,吾其性。”又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是不知性出乎天而纯乎理,兼以地与气质言之也。其诸异乎圣贤之论矣,荀与杨也。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无足怪者。张子,世之大儒也,后学之所宗也,张子言之于前,学者述之于后。达而仕者曰:“我知性有天地之性也,有善恶之性也,有气质之性也。”穷而学者曰:“我知性有天地之性也,有善恶之性也,有气质之性也。”穷达一词,牢不可破,是皆舍圣贤之论,而宗儒先之说,信其言,而不求之心者之过也。其不思也甚矣,其不知也亦甚矣。
廖纪心目中的“人性”,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从人性之来源上,人性源于天命。《中庸管窥》云:“天命即《诗》‘维天之命’,天以是命降于人,而人禀于有生之初,所谓性也。”“性乃天命之谓,舍天命而言性者,非性矣”;二是从人性之内涵上,人性即是天德,即是“至善”。《大学管窥》云:“至善者,性无不善,即天命之本然,如仁敬孝慈之类是已。”“天德,即上文仁义礼知之德,至诚能全天命之本然,故曰天德。”;三是针对人的私欲之蔽,主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功夫复其人的本性。《大学管窥》云:“明德者,人秉天之明命,具于心而明无不照也。人莫不有是明德,但蔽于私欲而昏之者众,故当格致诚正以明之,而复其初也。”《中庸管窥》亦云:“人莫不有是道,而为私欲所坏,苟能修治,去其私欲之蔽,以复其初,是乃由于学习,所谓教也。”“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由上可见,人性“均善而无恶”,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才质有异,存在“昏明强弱”之差别。这是由“所赋形气不同”、后天“私欲”所造成的。所以,应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功夫来恢复人性的本然之善。廖纪在《性学原》中强调说:“圣贤论性,其大原皆出于天而不出于地也。”又说:“圣贤论性,皆本善而无恶,纯乎理而不杂于气质也,彰彰明矣。”《大学问》又云:“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廖纪和王阳明一样,都是只肯定“天命之性”的观点,而否认宋儒以来所谓“气质之性”的说法。这是王阳明、廖纪在人性论上不同于程朱学派的地方。
(三)在心学上,程颐发挥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引申出心有体用之论。指出:“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所谓性之“体”,是指寂然不动之性(天理即仁义礼智);所谓性之“用”,是指感而遂通天下之情欲。朱熹继二程之后,提出“心主性情”之说,不管是从天理上发出的仁义礼智之心,还是从耳目之欲上发出的情欲,都是“本于一心”的。
廖纪与王阳明都从“体用合一”的“实心”论高度继承与补充了程朱学派的“心论。”
王阳明从“性一元伦”出发,指出:“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在王阳明看来,不管是“仁义礼智”、“聪明睿知”,还是“喜怒哀乐”、“私欲客气”,都是人的统一心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都是“实心”或“良知”不可或缺的内涵。
王阳明所谓“实心”或“良知”,包括“体”与“用”两个方面。
从“体”上讲,“实心”即是“良知”、“天理”。他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答徐成之》);“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王阳明全集》卷三)从其“虚者以实而虚,无者以有而无”而言,心亦是“实心”。不管是“良知”、“天理”,还是“实心”,都是从本体论高度,描述“心之本体”的。所以,从本体上说:“实心”是“纯乎天理之心”,“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传习录》上),亦即“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
从“用”上讲,王阳明认为,实心“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传习录》下)“吾良知的流行不息”,既包括人的知与情的精神活动,也包括“声色货利”之物欲等。王阳明指出:“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传习录》下)又指出:“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夫喜怒哀乐,情也。既曰不可,谓未发矣。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指其本体而言,性也。……喜怒哀乐之与思与知覚,皆心之所发。心统性猜。性,心体也;情,心用也。”(《王阳明全集》卷四《答汪石潭内翰》)王阳明指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传习录》下)他肯定人的感官之欲,声、色、货、利,都是实心、天理或良知的流行发用。
廖纪在心学上,提出了“心性一理”的命题。他论证说:“盖性即道心也,情即人心也,心性一理也,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窃尝庄诵而精思之,夫天下之心一而已矣,而有道心、人心之异者,何哉?盖人禀天命之性,浑然在中,寂然不动,乃天道之本然,故谓之道心也。感物而动,喜怒哀乐之情,发皆中节,乃接乎人事,故谓之人心也。当其寂然在内,无声臭之可求,无形迹之可窥,微妙而难知也。要当研精以察之,而务知之极其明。及其感物而动,如火之始然,如泉之始达,危大而难制也,要当专一以守之,而务制之中其节。道心能明,则不偏不倚,而中之体立矣。人心能制,则无过不及,而中之用行矣。”(《性学原》)这同王阳明的心、性、理合一的观点是相近的。
廖纪根据他的“心性一理”的观点,虽然肯定宋儒“探索性命之源,发明心学之要,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厥功亦伟矣。”但是,他“揆之经书之论则又有可疑焉。”他针对程明道的“心有主则实”、程伊川的“心有主则虚”的观点,批评说:“盖心本至虚也,若‘有主则实’而非虚矣。然以有主则实之言推之,心譬则室也,人譬则主也,居中御外,人皆主之,何虚之有?人本一心也,若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则人有二心矣。”他又针对张载、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批评道:“以心统性情之言求之,道心性也,人心情也,由中形外,心皆统之,何二之有?”(《性学原》)
廖纪把“心”分成“道心”与“人心”。“道心”属“性”,“人心”属“情”。“道心”(性)是心之体,“人心”(情)是心之用。当然,这种区别只是相对而言,而非绝对的。所以,廖纪强调指出“心性一理”。这种观点,既不同于张载、朱熹的“心统性情”的说法,也不同于程明道的“心有主则实”、程伊川的“心有主则虚”的观点。充分显示了廖纪在学术上从不迷信权威和善于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
廖纪在心学上的最大理论贡献,是以“心性一理”的命题诠释“中庸”(或“中和”)之道。他根据《中庸》“与《大学》相表里”的认识,指出:“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中庸管窥》)可见,“中庸”与“中和”只是表达角度不同,其实质是相通的。可以说,中庸以“中”为体,以“和”为用。廖纪进一步论证说:“性为天下之大本,然性具于心,无形而难知;情见于外,有迹而易见,故先言喜怒哀乐之情在外而易见者,以验难言之性也。犹孟子言性善则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也之意。”又指出:“夫道原于性,性具于心,无形而难知;情见于外,有迹而易见。情者何?喜怒哀乐是也。当其未发而在内,寂然不动,不偏不倚,所谓中也。及其已发而形外,感而遂通,不乖不戾,所谓和也。谓之中者,即天命之性,乃天下之人共具之大本也。谓之和者,即率性之道,乃天下之人共由之达道也。君子既全性、道于己,使中有不致,则天下之大本不立矣。和有不致,则天下之达道不行矣。”(《中庸管窥》)由上可见,廖纪是以“性”解“中”,以“情”释“和”。“性”与“中”,“情”与“和”,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心性论是中和论的理论基础,“中庸”或“中和”又是涵养心性、实现天下太平的康庄大道。所以,廖纪要求“以我之中以中天下之不中,致使天下之人皆归于中,所谓立天下之大本者是已;以我之和以和天下之不和,致使天下之人皆归于和,所谓经纶天下之大经是已。”(《中庸管窥》)这充分地证明了《大学》和《中庸》“相表里”的观点。
(四)在经世实学上,王阳明针时程朱理学末流的空谈之风,提出了“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的“明德亲民”论。廖纪和王阳明一样,也大力提倡“爱君之诚,忧国之心”的“明德亲民”论。他在《大学管窥》中指出:“盖道之大本,在于修身,而其用不外乎治人。明德则治人之本立,新民则治己之用行,此圣贤之学,体用之全,不可偏废者。”
方鹏在《矫亭存稿》中指出:廖纪自幼“蚤有大志,年数岁,淡庵命读医卜书,跪曰:此末技耳,非丈夫事也。淡庵异之,听习举子业。稍长游邑庠,成化庚子京闱乡荐,登弘治庚戌进士。……(正德年间)擢太仆少卿。岁巡边阅马,出都门百里外,即停骖遣使取马册进呈而已。公遍历广览,无远弗至,山川之形胜,将士之勇怯,关隘之险易,边储之虚实,靡不究心焉。(正德年间)无何改太常,进正卿,俱提调四夷馆。教诸生于常业外,读儒书,识义理,多所造就。(正德九年)升工部侍郎,总易州山厂。履任浃旬,弊去八九。……(正德十六年)升南京吏部尚书,……见亷陛不严,纪纲渐废,力振举之。”(大司马龙湾廖公传》)所以,罗钦顺在《整庵存稿》卷七中指出:廖纪“官京师三十余载,间将使指,曾不逾千里外,而四方吏治之得失,民情之疾苦,风俗之媺恶,鲜不究知,盖其留心于世务然也。”(《赠大司马廖公参赞南京守备机务序》)罗钦顺对廖纪留心世务、勇于改革的经世之学表示充分的肯定与赞许。
这里,我们将重点选择廖纪的《宥言官以彰圣德,用将才以固根本疏》和嘉靖四年九月上“正士风,重守令,惜人才疏”,说明他的“爱君之诚,忧国之心”的“明德亲民”论。
明嘉靖元年,廖纪由南京吏部尚书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他以强烈的“爱君之诚,忧国之心”的忧患意识,在《宥言官以彰圣德,用将才以固根本疏》中,不仅通过认真调查,指出南京守备中存在着军士逃亡、城墉无恃、操练不力三个主要弊端,而且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办法。他指出:
盖南京祖宗根本重地,四方都会,承平日久,武备废弛。……(臣)曾逐一点视军政,该行整理者,不胜惊愕玩愒之势,已至七八。虽尝竭愚摅虑,补救一二,偶因言官论劾,旋以衰疾乞休,遂归。衷情耿耿,恒以负任为愧。臣虽身居田里,而一饭未尝不以南京为忧。
盖南京有操江营,有内小营,有外大营。先年军士大约十万余名,迄今逃亡事故,仅可六万余名。中间又多瘁弱不堪,其精壮可用者,但可万余。未经战阵,不识坐作攻刺之法。一有惊急,难便驱使。此兵之可忧者,一也。
南京城墉周围七八十里,东、西、南三面,犹有重门,人烟辏辐。独北边一面,人烟稀少,多蔬圃荒芜之地。守御之备,了无所恃。此城之可忧者,二也。
平时操练并守门军士,所戴者木盔,所执者木刀、竹枪。追原其故,皆谓军器悉贮内府,该班军官俱不敢领,以军士每每逃亡,并此器械不可追究,恐累倍偿。夫以平昔无事之时,虚应故事,习为轻便。卒然有事之日,戴此木盔,执此木刀、竹枪,岂能御变!此军器之可忧者,三也。
三者不独臣忧之,凡任南京有职者,皆以为忧也。三者既为可忧,而所恃者在将领耳。南京坐府、坐营,自公、侯、伯、都督、指挥以下,中间晓畅军士事,固虽有人。俱未曾经战阵,有警之时,欲其折冲御侮,难保必胜。而将帅亦为可忧也。臣近荷召用至京,退朝之余,每与已故尚书李钺私相论及南京可忧,宜预择练习戎务、堪任将领者二三员,奏请用之,坐营督率,振起疲弱,恢扬军政。平时之声威,可以慑人心;有事之谋勇,可以成事功。斯为根本重地之至计,不可不急图也。
方鹏在《大司马龙湾廖公传》)中补充说:“(廖纪)改南京兵部兼守备参赞。内官等监私役军匠,及借拨人匠各若干名。又军匠逃故者,责令千百户代偿月钱。人匠逃故者,坐令二县坊厢顶补。又神帛堂人匠原额四百余名,今加至及千余户,皆富室营允以祈避役。凡此数弊,其来已久,牢不可动,公悉查革。偶以目疾,月余不视事,挟旧怨者以为言。公尝累疏乞骸,至是求去益力,遂得致仕。闻者为天下惜之。”
廖纪升任吏部尚书后,仍对南京兵部兼守备参赞衷情耿耿,他说:“臣待罪銓曾,用人者,臣之职;用将者,兵部之任。今以吏部而言用将之事,出位之罪,自知难逭,但犬马惓惓一念,爱君之诚,忧国之心,顾自有所不避也。干冒天威,仰祈俯纳。臣不胜战惧待罪之至。”(《宥言官以彰圣德,用将才以固根本疏》)
嘉靖四年九月,吏部尚书廖纪上“正士风,重守令,惜人才疏”,在吏治改革上,向嘉靖皇帝疏陈三事:
(一)正士风。认为“修政之事,惟在多士。”但是,自“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因此,建议“今宜遵照旧例,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堪任事者,方准致仕。果病不能行动者,方准养病在外。方面官员年六十以上准致仕,不准养病。有不奏弃官,及奏不侯命而去者,许本部并科道抚按官紏举治罪,罢职不叙。其言官以言事被责,听本部量年资渐次擢用。养病者病痊赴部,仍照原官选除。”
(二)重守令。廖纪认为“皇上励精图治,勤政恤民,于兹五年而未臻实效者,殆于守令待之未重,任之未久也。祖宗朝守令率九年任满以为常,间有保留且复再任,比三年朝觐,政迹卓异者,或赐之燕赍章服。故当时令守皆惟修职,天下赖之。迩来官不久任,迁转太频。人无固志,政多苟且。小民怨恣,上干和气。灾变不息,水旱频仍。”因此,廖纪建议“今宜遵照旧制:守令必以九年为满。其政迹可嘉者,知府升布政使、按察使等官,知州升副使、知府等官,知县升知府、郎中等官。朝觐毕日,都察院及科道官查访,贤能尤异者,疏名上闻,宴赍如例。或于清燕之暇,俯赐召对,询问民,闻疾,特加优礼。将人皆响风,而良吏布满于郡邑矣。”
(三)惜人材(通才)。廖纪认为“为政以人材为先。然有材而不爱惜,与无材等。正德末,巡幸不休,财力弹竭,天下岌岌乎危矣。幸赖大小臣工,或调护于内,或镇定于外。宗社保于无虞,皆内外得人之効效也。然当其时,人皆知擒获逆濠诸臣之功,而不知保厘京师诸臣之功。皇上入继大统,任贤图治,时有以保厘诸臣为言者,陛下以为心腹股肱,必能竭忠宣力,治平可指日而致也。无何,大臣皆自陈归休,老成持重者接踵而退,好名喜事者连茹而进。以出位敢言为贤,以凌分犯礼为高。自取罪愆,远致谪斥。数年以来,人材渐不足用。”因此,他建议“皇上思养材之难、用材之急,于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厘之功,有年力未衰、才识可用者,量加推用。一应降职之官员,僩悯其流离之久,察其悔悟之深,查照年资,渐次升擢,以开自新之路。其远方谪戍及为民者,量移近地,或量许还乡闲住,以示无终弃之人。如此,庶人材日感而政事靡不修举矣”。这里,所谓“昔年致仕大臣”,既包括杨廷和、蒋冕、毛纪、乔宇等阁部大臣,也包括嘉靖三年在“大礼议”中被廷杖谪戍的一批官员。充分体现了廖纪所谓“事关国体,职在用人”的正义凛然的大公无私精神。
嘉靖皇帝虽然肯定廖纪“所奏深切治体。”同意“自今有假托养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方面官年六十以上,方准致仕。外官不准养病,京官真病不能行动者,方准。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紏举,各罢职不叙。言官被谪者,量年资渐次擢用。病痊赴部,仍照旧选除,不许改别衙门。守令俱以九年为满,有政迹卓异者不拘。进士、举人、监生,依拟升秩,仍旧管事。风宪有缺,于三年以上,知县行取选用方面官,照旧例佥事,递升副使、按察使、参议。不必骤迁数易,以致奔走废事,爱惜人材。所司因事升参政、布政,即于本省及附近省分推升,不必骤迁数易,以致奔走废事。”但是,“爱惜人材所司因事奏请,朝廷自有斟酌。”最终嘉靖皇帝只采纳了前两个建议。
吏部尚书廖纪嘉靖四年九月上“正士风,重守令,惜人才疏”后,嘉靖四年十二月向嘉靖皇帝上“议席书之言疏”、嘉靖五年正月又上“请复大臣杨旦、杨慎等原职表”、嘉靖五年六月再上“霍韬内外官升迁资格议”、嘉靖五年十月又上“荐马永、救魏有本疏”等,坚持“惜人材”的意见,充分地体现了廖纪的“臣子事君,当务诚实”的品德和坚持原则、“爱惜人材”的美德。
由上可知,廖纪是一位品德高尚、正直清廉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针砭时弊、勇于改革的思想家。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