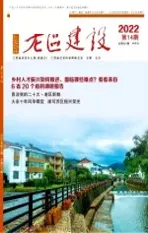浅论中国文论“文道之辨”的意义循环
2011-08-15汪素琴
●汪素琴
“文道”关系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由“文”与“道”的关系可以自然地引发出文学理论中一系列核心问题,如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与制度文化的关系,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及文学的本质等问题。也正因如此,“文道之辨”成了历代新文学运动不容忽视的一大重要论争点。归根结底,论争的核心落实到了“文”与“道”的具体内涵上。由于不同时期“文”与“道”各自的内涵都不尽相同,所以尽管人们对二者关系的论述有破有立,有承传有消解,然而总逃不出这样一个意义怪圈,即:“文”和“道”一直有扯不断的联系。探究我国文论史上“文”与“道”的关系,不仅能更全面地把握中国文学的核心思想,也有助于了解文学的本质问题,对当代文学的走向也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笔者认为,中国文论史上的“文道”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道同一阶段”,该阶段主要指先秦时期,此时“文”的含义是混沌的,并无本体学意义,而只是“道”的一种呈现方式。“文道分离阶段”,这一阶段有一漫长的过程,两汉至唐宋都属此阶段。在该阶段“文”的含义由混沌走向明晰又走向混沌,其存在的独立性也随之消失,“文”成了“道”的工具。“文道融合阶段”,明清乃至近代都属此阶段。人们对“文”的内在本质有了明确地认识,因此在扩大“文道”内涵或消解“文道观”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走向了“文道融合”。
一、文道同一阶段
先秦时期,“文学”一词兼有文章博学之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这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文学子游、子夏。”[1]此处的“文”即是博学的意思,其侧重点在学术上。这一时期“道”的含义更为宽广。仅在《论语》里,“道”就有多种含义:如“道听而途说”(《阳货》)里的“道”指的是本意道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道”即指道德伦理的最高原则;“道千乘之国”(《学而》),“道”可解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此外,孟子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里的“道”则是指途径、方法。老子更是将“道”提升到了哲学范畴,在《老子帛书》乙本中说:“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这里的“道”乃是万物的本体,虽不知其名,却可生一,继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韩非子·解老篇》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即“道”是自然界乃至人类文化的总根源、总法则,具有本体或本源的意义。
从上述对“文”与“道”含义的解释上我们不难发现,先秦时期二者都具有最广泛的意义,与我们现在通行概念有本质区别。“道”更多的是在哲学范畴和伦理学范畴上使用,而“文”在很大程度上则是“道”的一种呈现方式。此时还不存在文体学意义上的“文”,“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郭绍虞先生在论孔门文学观的影响时指出:“孔门论文,因重在道的关系,于是处处不离应用的观念,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倾向。《论语·宪问篇》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即是后世道学家重道轻文的主张。所以《述而篇》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数语,诸家解释均阐发孔门重道轻文之意。这种说法,决不能算是后人之附会。观于孔子论诗重在‘无邪’,论修辞重在‘达’,重在‘立诚’,则知其主旨所在,固是篇中在质;而所谓质,又须含有道德之意味者。”[2]笔者认为这一见解十分深刻。先秦时期首先将“文道”放在一起进行界说的当属荀子:“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管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荀子·劝学》)“辫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荀子·正名》)此处说的虽是圣人之道与文的关系,但不可否认他是最早阐述“文道之辨”的论说家。
二、文道分离阶段
汉代开始“文”与“学”,“文章”与“文学”的概念开始有了区分,“文”的概念慢慢地走向了明晰。此时的“文学”专指学术,而“文”、“文章”则专指词章,与近人所称“文学”之意义相近。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其它学术开始有了分别,其含义与近人所指基本相同,同时又有了“文”、“笔”之分,“文”重情、美感,“笔”重知、应用。这时“文”渐渐有其文体学上的意义,“文”与“道”的关系也慢慢地产生了分离,“文”渐渐成了言“道”的一种工具或载体。“原道”、“宏道”、“宗道”、“明道”、“贯道”、“载道”等一系列名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王充在《对作篇》中说:“故夫圣贤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此处讲“为文”要内容不空,因时因事而作,虽未言及“文”与“道”的关系,但却点出了“文”应有功利性特征。三国时的桓范在阐述“文道”关系时,针对当时人们为追求“立言不朽”而互相抄袭,只重华丽辞藻而忽略文章思想这一风气,提出了“文以宏道”说:“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宏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世可行,后世可修。”[3](P7)虽然此时的文已经有了独立的意义,然而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完全要“文”与“道”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在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和挚虞“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文章流别集》)等论断中也可见一斑。当“文”的含义越来越明晰时,“文”的存在也渐渐走向了另一极端:“文”成了“道”的工具。
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原道”专章,认为无论是“玄圣创典”还是“素王述训”,都是“原道心以敷章”,圣人与“道”之间是通过“文”来沟通的,所以有“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4]如果说刘勰《原道》是根于人文立论,较重于自然,不局于儒家之旨,那么唐人之论人文,则渐渐狭其范围,成为儒家的论旨。“原道”说渐渐成为“贯道”说,而至宋代“载道”说的提出,文的独立性完全被泯灭。
隋唐五代以降,兴起了古文运动,提出了“文以明道”说、“文以贯道”说。此时“文”由自然之“文”向古文家的“文”再向道学家的“文”演变,“文”的含义又从明晰走回了混沌。“文”成了不同论说家自己的“文”。隋末王通在《事君篇》中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郭绍虞先生认为:“其重道轻艺之意显然可见。所以文以载道之旨,实以王通首发其端。”[2](P116)王通可谓开后世道学家之先声。唐代韩愈更是将“学文”、“作文”的原因归结为“得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送陈秀才彤序》)然而,韩愈与后来宋代道学家所提倡的“文以载道”说、“文以害道”说还是有区别。“韩愈是因文而及道,道学家是求道而乎文。一个是体会有得,一个则得鱼忘筌。”[2](P155)宋代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文以载道”说的道学家。其在《通书·文辞》中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如果说周敦颐还没有完全否定“文”甚至说对文辞的修饰作用还给予肯定的话,那么到了二程,文学观已经偏到了极致。此时“文”与“道”完全的分离了。“文”成了承载“道”的工具而毫无其自身的价值。
三、文道融合阶段
从明代开始,“道”又渐渐的从圣人之道上回到了自然之道,而“文”也回到了广义的“文”上,“文道”关系走向了融合。但这与最初的“文道同一”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先秦由于“文”、“道”概念都处在混沌状态,人们对二者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往往将二者合而为一进行论说。到了明代,“文”的概念经历了从混沌到明晰又到混沌的过程,人们对“文”的内在本质有了明确地认识,此时提倡“文-道”融合是文论家对“文”的本质进行反思的结果。明初宋濂在《曾助教文集序》中说:“传有之,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无文人者,动作威仪人皆成文;无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汉以下则大异于斯,求文于竹帛之间,而文之功用隐矣。”认为历代“文”的含义经历了一个由广到狭的过程,并提倡“文”应是指原初意义上的“经天纬地之文”[5](P1043)(《文原》),而非显于竹帛之上的文人之文、文章之文。与宋濂相比,苏伯衡论“文”更有包容性,他“天之文”和“人之文”一并包括在内:“天下之至文,孰有加于水乎?”“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于自然,独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云霞烟霏、河汉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泽、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鸟兽,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郊庙朝廷、礼乐刑政、冠婚丧祭、畋狩饮射、朝聘会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王生子文字序》,《苏平仲文集》卷五)可见此时“文”的含义是十分宽广。
到了清代,文论家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的文学观,要求“文”要做到“文质彬彬”。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明确地提出了文道融合的说法:“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文以载道,犹为二之。”[6](P401)他主张学统不离道,道统不离学,即以文兼道,以道兼文。章学诚在《文理》篇云:“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而已。”这即是说为文应有所见,应有自得之处。可见实斋重著述之文而轻文人之文,想兼取道学家和古文家之所长,以使古文家之“文”与道学家之“文”融合在一起。
如果说明清时期是在扩大了“文”与“道”的内涵上来提倡文道融合的话,那么五四时期则是在消解“文道”观的进程中不自觉的走上了文道的融合。虽然各种反对“文以载道”的说法层出不穷,然而,“新文学在对文以载道的批判同时,也把自己带进了‘文道’关系的话语逻辑。”[7]新文学运动“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8](P140)因此从“文道”关系发展的本质来说,五四时期与其说是对“文道”观的消解,更不如说是对“文道”关系的另一种回归,只是此时的“文”和“道”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这样,“文道”关系便发生了意义循环。当然,循环并不意味着回到原点,而是回到了一个更高的逻辑起点上。在文道之辨中,人们对于“文”的本质进行不断的探索,虽然“文”的概念从混沌走向明晰又一度走向了混沌,但我们不能忽视整个过程所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启发。当代文学娱乐化问题盛嚣尘上,厘清文道关系,对于正确评估和认识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判史 [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3]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刘勰著,范文澜注本.文心雕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宋濂.宋濂全集·芝园后集(卷五)[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10册)[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7]王本朝.“文以载道”观的批判与新文学观念的确立[J]. 文学评论,2010,(1).
[8]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