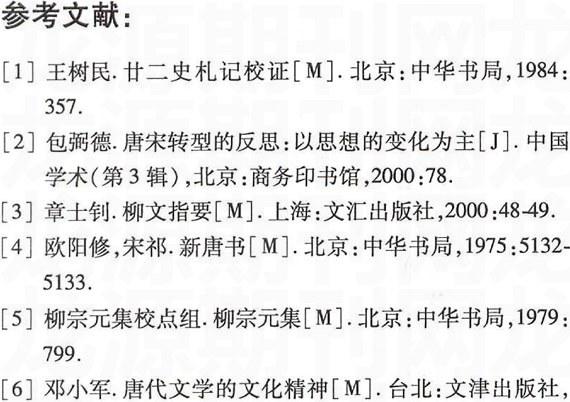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2011-07-01田恩铭
田恩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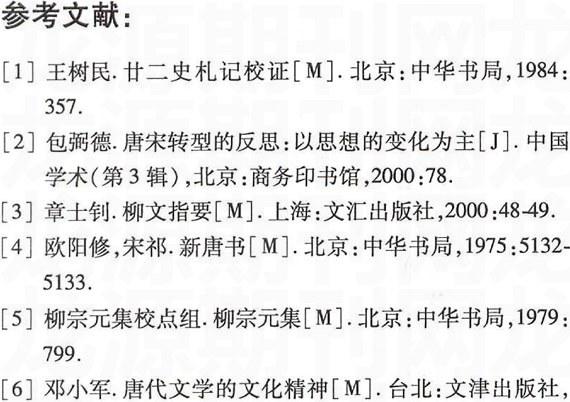

摘要:唐宋思想的转型,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新唐书》一改《旧唐书》的格局,通过全面采摭柳文入传展现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柳文被广泛采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议论”和“史才”的价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传分别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传记则更使韩、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寻求资源的阶段。通过采摭柳文入传,既建立了本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无形中有意地让柳宗元与韩愈走到一起。
关键词:《新唐书》;唐宋变革;柳文;思想转型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2-0099-06
唐宋思想的转型离不开对思想家所著文本的解读,透过文本的意义指向往往能够找到转型的端倪。史书采摭文学家所创作的具体文本入传并不一定从文学的层面上考量,往往是因为叙事的需要或者保存文献的目的。韩愈、柳宗元无疑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两《唐书》采摭他们的作品入传呈现了较大的差异,而从旧到新的过程却往往能够与唐宋思想的转型联系起来。
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云:“欧、宋二公,皆尚韩柳古文,故景文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愈文,《段秀实传》则用柳宗元书《逸事状》,《吴元济传》则用韩愈《平淮西碑》,《张籍传》又载愈《答籍》一书,《孔戣传》又载愈《请勿听致仕书》一疏,而于宗元传载其《遗萧俛》一书,《许孟容》一书,《贞符》一篇,《自儆赋》一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实际上,《新唐书》采摭的韩、柳文还不止赵翼所述的篇目。不过,采摭韩、柳文入史确实让《新唐书》与《旧唐书》相比,在思想意义指向、叙事效果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的主要方面并不一定是基于文本意义,而可能存在多重考量因素。本文拟就《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相关性展开分析。
一
美国学者包弼德著有《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一文,他认为唐宋思想转型的—个特征在于“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换句话说,从思想构建的方式上,是由叙事的纪实性阐发转向了明理的主体性阐发。这显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而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章士钊认为,“子京平视韩柳,传中所采各文,殆无轩轾轻重之意,而却有分别护惜之心。如韩文不采《三上宰相》,及《上京兆尹李实》各书,似旨在为退之留存士大夫面目。”自中唐至北宋,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被接受状况与两《唐书》的书写态度呈趋同走势。基于本时代文化构成中柳宗元的被忽略状况,也基于对柳宗元政治选择的错误路线以及对柳宗元仕途失意的认定态度,《旧唐书》无论在本传还是其他传记文本中都并没有采摭柳文入传,本传之中也把柳宗元写成了失意的文学家形象,故而许多学者认为《旧唐书》对柳宗元的文学成就评价较高,而韩愈则相对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宋初之际,中唐古文成为文人寻求文化重建的资源库,韩、柳自然成为被选择的目标。韩愈的地位直线上升,柳宗元也逐渐浮出水面。韩、柳虽然并提,却没有被放在同一高度,柳宗元只是韩愈这面大旗下的一个羽翼,故而宋祁本人也将柳宗元列于韩愈之下。如果撇开这一点,而专就对柳宗元个体形象的书写上说,则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新唐书》在不涉及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采摭了宋祁认为可以采摭的文章。这样两《唐书》对柳文的采摭态度上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此差异形成的书写效果自然不同,进而对其人其文的认识也会不同。在本传和其他人的传记当中,《新唐书》共采摭柳文9篇,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传采摭柳文4篇,其他传记中采摭柳文5篇,多为议论性文章,以弘扬忠义道德为主要内容。就采文之广而言,自是不如对韩文之采摭。然而,就柳宗元自身形象的被接受而言却实现了质的飞跃,即柳文从被忽略到被集中采摭,这显然传达出了由唐至宋的变革信号。关于《新唐书》采摭柳文给传记本身带来的变化与采摭韩文有些相似,也主要侧重在柳宗元的史才、议论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
《旧唐书》本传中并没有采摭柳文,传文很短,只是记载了柳宗元艰难的一生。而《新唐书》本传采摭柳文4篇,都是元和四年(809)以前的作品,由时间之定位来看,就是着重于柳宗元被贬谪之后的忏悔心态,借以弘扬中央集权之中心思想。对柳宗元的政治选择,两《唐书》史臣们都持否定态度,而在对柳宗元形象刻画上却呈现了不同的特质和风貌。尤其是《新唐书》采摭柳文进入本传,成为文本内容质变的一大表征。章士钊在批评了《新书》采摭韩文的情况后说:“至《子厚传》录载《致萧、许》二书,《贞符》一篇,及《自儆赋》,可云斟酌尽善。两书子厚自道隐曲,如见其人,可招致千载同情者之诵叹;《贞符》一篇,明辟封禅,可表子厚政治主旨;《自做赋》者,即《惩咎赋》也,此赋步武《骚经》,声情激越,令人百读不厌。或谓此讼冤,非惩咎,说亦有理”。章氏扬柳抑韩之意自不能免,而针对宋祁在传记文本中采摭柳文的分析则有可取之处。本传中采摭的柳文从内容来说,都是抒发柳宗元身世之感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却各有侧重点,将柳宗元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身份纳入其中。透过这些作品,宋祁是要刻画一位被本时代认同的自己心目中较为全面的柳宗元的形象。
宋祁在本传中采摭柳文的目的是为了重构柳宗元的形象,这四篇文章则各有侧重点,而采摭两封书信入传显然是展示了一位失意的政治家形象。我们首先将这两封史书所采摭之内容与原文对勘一下,就会发现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两封信都省略了抬头和信尾的谦辞。除此之外,删改之处亦多。先看《与萧翰林侥书》,据施子瑜《柳宗元年谱》,此文作于元和四年(809年),此时的柳宗元在永州司马任上。《新唐书》采摭此信,与柳集中的文本多有不同,从内容差异上看应是出于宋祁对原文的删改。其中删改最多的在第一段和第三段。第一段变化犹多,故录之:
仆(不幸)向者进当臲卼不安之势,平居闭
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兴游者,岌岌而操
(造]其间。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
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则)
孰能了仆于冥冥间哉?(然)仆当时年三十三,
(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
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疾,可得乎?(凡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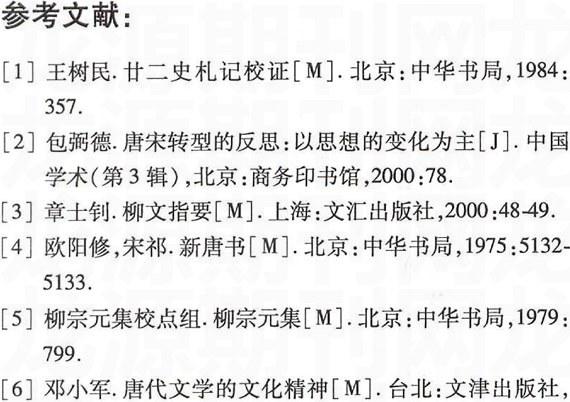
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
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宽[弘]大,贬黜甚薄,
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
怪人[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
心,日为新奇,务相悦[喜]可,自以速援引之
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
(伏自思念,过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
少(得)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
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
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为
罪。(兄知之,勿为他人言也。)第二段只是有几处删改字,而第三段则在“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后删去下面一段文字:
独喜思谦之徒,遭时言道。道之行,物得其
利。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身被之,
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
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诚如此。直接接上:“然居治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一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句意。这样的处理显然遮蔽了柳宗元私域范围内的个人思想观念,而是呈现了作为一个忏悔者和对自我认识进行反思的痴者形象。《寄许京兆孟容书》一文中被删去的文字主要是对自己当时处境的描述,这样自己的被孤立状态就展现主来了。这两封信所删改的内容存在着共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将富于私人色彩的词汇进行删改;二是被删去的文字均是关于永贞革新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涉及对自身立场和命运的解读。从书信的被删改情况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宋祁确实是在回护柳宗元的政客形象,以突出其文学家的主体身份。
被采摭入传的这两封信的文本内容也具有明确的意义指向。《与萧翰林俛书》一文主要将柳宗元贬谪之际的生活状态,困顿中的解脱意识,升平时代的脱罪渴求一一表达出来。在柳宗元自己看来,《寄许京兆孟容书》所抒发的是“中心之悃幅郁结”。这两封信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柳宗元“谤语”中被边缘化的被迫选择。正如《与萧翰林俛书》所云:“圣朝宽大,贬黜甚薄,不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人”这是他对自身选择的认识,因“附会”而得罪,因得罪而生谤语。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又针对:“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这句话展开倾诉。第二,柳宗元对个人身世之感的省思。仕宦之途的不得志,人生立功之理想的失落,对他的打击相当沉重。于是,他走向司马迁、曹植之选择,即“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欲秉笔覙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当前之生存状态必然影响人生理念之实践,柳宗元试图在发愤著书中消解痛苦,但焦虑之体验难于自拔。宋祁所采摭柳宗元的这两封书信确有自己的阐释目的,一个方面,借助《与萧翰林俛书》还是表述了传主之认罪态度,另一个方面展示了柳宗元作为文学家的高远志向。宋祁因为推崇柳宗元之文笔,所以善于从柳传之中采摭他的文章。而从他对柳文之删改中就可以明确一点,即透过被贬者之心态也表达了传主公共空间内所蕴含的公众态度之一面。
《新唐书》本传采摭了柳宗元的《贞符》一文,文字上的变动不大。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柳宗元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展示了柳宗元身份中的思想家形象。宋祁采摭此文在于表现柳宗元在历经苦难后的忏悔中思考社会发展的思想路向。从民本与君权合法性出发的理性追溯实际上并没有否定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至于对自身的悲剧结局,柳宗元只能采取“惩咎”的态度。宋祁在《宋景文公笔记》中有一段话,云:“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文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那么,“自出新意”体现在哪里呢?邓小军认为:“《贞符》的政治哲学,旨在解释君权的合法性的来源这一问题。其中包括三层意义。第一,君权决定于人民的意志。第二,大公之道的政治是天下为公。第三,否定了天命论。”关于《贞符》系年问题,施子愉《年谱》系于贞元二十一年。根据《序》则知这是两个时段完成的作品。柳宗元在被贬之后上《贞符》一文本身就具有自身的政治目的,主要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作为政治革新的失败者,他承认自己及所属群体失败的同时却在彰显自己所坚持的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宋祁在柳传采摭文章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将柳宗元所形成的焦虑性体验通过不同文体、不同表达方式呈现出来,注意避免个人化的语言论调,这本身就证明了他所持有的书写态度,即自身在政治理念的追求之路上虽然是一个失败者,但是他是一个善于反省并忠于皇权的士大夫;他的社会理念和道德文章是不能被否定的。围绕贬谪这个政治生涯的低落时段来集中采摭柳文,存在着宋祁对柳文的评价态度。文本叙述中存在着一种价值取向,即柳宗元的政治博弈形成了苦难人生,而苦难人生造就了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贞符》入传确有另一层意味,即柳宗元之所以落得个悲凉结局实在是遇人不淑;另一个方面也展示了虽为逐臣,却依然对君权合理性予以肯定的忠直形象。这也符合宋初士人对柳宗元的评价所持有的态度,如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从传记文本的叙述语境来看,宋祁显然有意凸显了柳宗元本于儒家观念的政治思想的纯正性,他对柳宗元传记的改造并没有过多的修补,而是在《旧唐书》基础上结合韩文展开的。柳宗元献《贞符》一文本身是为了表白自己,既为自己参与革新的动机作出解释,也由此希望获得机会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宋祁采摭这篇文章也正是为柳宗元辩白,在宋祁看来,柳宗元最大的失误是遇人不淑,这导致了他的政治前途的悲剧结局,而他所坚持的政治理念和对道统的张扬则有其可取之处。宋祁肯定了柳宗元的杰出才华,而为他的仕途失意而扼腕叹息,一个思想者形象就这样浮现出来了。
采摭《惩咎赋》入传显然展示了柳宗元作为文学家的形象。宋代晁补之认为:“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堙厄感郁,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惩咎者,悔志也。其言日:‘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后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读而悲之。”这段话的前一句就是化用《新唐书》传记之文。在晁补之看来,柳宗元此文是悔过之作,是对因咎而获惩的哀怨之辞。而严羽则推崇柳宗元的这类作品,评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这是出于艺术表现能力上的考虑而作出的论断。宋祁没有欧阳修、范仲淹等人身上那种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对政统的归依感,只是以作为儒者的个人生命体验来观照文学家的经典取向。这样,自然就对士人的心态变化相当关注,这正是《新唐书》传记在写法上超越《旧唐书》的地方,也是文学家身份的史官的一种自觉意识。由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被流贬到边远角落,政治理想的破灭和文化取向的偏失都
使柳宗元陷入失去已有情境的陌生化境地。这种离群的孤独感让他找到了精神皈依的栖息地,这就是楚骚的艺术空间。他的情感在这里得到释放,形成一次次不断内省的精神之旅。
从宋祁对柳宗元本传采摭文章入传来看,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所采摭的作品都是柳宗元贬谪永州之际完成的。正如陈幼石所说:“总而言之,柳宗元在永州时期的各种作品很能代表一个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在历史变乱的时期及环境下所能达到的思想及感情上的广度、深度和高度”。陈先生随后对柳宗元柳州时期的创作心态亦有深入分析亦可以参考。二是宋祁将自己的态度在引文前后表达出来。他在采摭的四篇文章中所写的阐释文字也很值得注意,在采摭两封书信之前他说:“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雅善萧傀,诒书言情曰……”,之后他说:“然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这就肯定了柳宗元的才能;采摭《贞符》之前说:“宗元久汩振,其为文,思益深。尝著书一篇,号《贞符》,曰:……”这里突出了柳文“思深”的一面;采摭《悔咎赋》之前说:“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念往吝,作赋自做曰:……”这些用语都有深意可求。《新唐书》采摭柳文显然对其骚怨之作有所倾向。在关于柳宗元《惩咎赋》的文学评价中,我们已经明确了宋祁对柳宗元接受屈骚传统的关注,在对柳文的采摭上依然如此。三是宋祁对柳文的删改关乎柳宗元贬谪心态的真实反映。宋祁将柳宗元的个人表达语境进行调整,导致了后来洪迈《容斋随笔》中所说:“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这一结论。宋祁采摭柳文的时间范围只是到永州时期的创作为止,而没有涉及其他时期的作品。将君权的合理性,自身的选择失误与渴望得到机会证明自己等方面的文章组合在一起,传记的写法显然具有意义的指向性。这样看来,《新唐书》本传对这四篇文章的采摭试图反映出柳宗元外放中的整个心路历程。从最初的贬谪心态到思想行为的理性思考,再到政治理想幻灭后的情感哀思,这是柳宗元作为政治人的悲剧一生,却是他作为文学家光辉的一生。另一方面,宋祁如此采摭柳文实际上具有文本构成的叙述倾向,那就是为柳宗元“正名”,而其依据则是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的观点,宋祁采摭柳文是韩愈的一种回应。被采摭的文章形成了贬谪中的柳宗元的情感释放网络,通过与别人倾诉、对自身理念的内省、对政治选择之悲剧结局的艺术诉求达到释放自己情感的创作目的。由此可见,宋祁对柳文的采摭是具有目的性的有意识行为,他展示了一位因政治选择而付出代价的文学家在遭遇艰难之际的焦虑性体验,而这一焦虑性体验将以文人士大夫身份而侧身于官僚士大夫群体中的身份转变的阵痛过程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从一定程度上说,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表达的认识态度成为柳宗元传记文本的指导思想。
从本传以外的采摭柳文入传来看,采文篇目数量不多却分布广泛,且所采之文均涉及对相关人物的人格评价。如采摭《段太尉逸事状》《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意在突出段秀实、阳城的士大夫精神;采摭《驳复仇议》《寿州丰安县小门铭》意在弘扬“孝友”伦理层面之品格。采摭《封建论》彰显柳宗元对“国是”的识见。《新唐书》除本传以外所采摭的文字都没有离开忠孝节义,而这些内容正是构建新资源的基本理念。余英时在《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说:“事实的真相是,如果我们拓广我们的视野,并尝试去辨明从唐末到宋初中国人的精神发展的普遍趋势,我们就会发现,这最后重要的突破远超出通常被当作新儒家兴起的思想运动的范围,纵然对于新儒家从11世纪以来处在重要的中心位置是毫无争议的”。唐宋思想的转型应该是全方位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只是被人为地分割开来,思想转型首先是作为一个基本点铺展开来,并没有自觉地专门领域定位。而史学思想从唐末到宋初的转型也突出地体现在对唐史的重新建构过程中,这个时间段也体现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分界。而柳宗元的思想观念正是在北宋初期被作为思想资源不断阐发的,从石介、穆修这样的明道古文家到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政治家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论定柳文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而从宋祁对韩文的采摭来看,与柳文用意相同,只是更为广泛而深入。但是,这并不是因崇韩而尊柳,而是将韩、柳的文本作为本时代的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指向。
实际上,《新唐书》柳宗元传记的写作实际上也是在《旧唐书》本传的基础上采摭韩文写成的,采摭的韩文则主要是《柳子厚墓志铭》。尤其是对柳宗元人生去取之选择上,韩愈的观点则成为立论的依据。通过比对可以看出,《旧唐书》也是受到韩愈文章的影响,只是在传记文本构成上多用叙述性话语入传。而《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的评价性话语引入文中,实乃精心剪裁而成。事实上,到了北宋,韩、柳才成为古文运动的同步者,在这之前,只有刘柳而无“韩、柳”之说。最早将韩、柳并称的是柳开。他既要肩愈,又要绍元,在弘扬道统的背景下有着确立文统的理论诉求,也就将韩、柳统为一个阵营中了。在《旧唐书》的叙述视野中,韩愈并没有出现在柳宗元的传记中,柳宗元只是作为文学家和失意政客的形象被书写出来。《新唐书》却并不一样,宋祁对刘、柳的评价不可同日而语,柳宗元成为一个有思想的表达者,他的政治思想、文化理念、文学才华通过自己的文本被展示出来,形成了一个真诚而执著的忏悔者形象。经过这样的处理,柳宗元就与韩愈走到一起,虽然难于脱离党争之政治群体,却在思想上与韩愈成为同路人,文学上则被划入古文阵营,成为盟友。由此可见,柳文被广泛采摭入传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思想的价值上,处于唐宋思想转型之际的北宋,柳宗元的资源性意义被广泛认同。与韩愈不同的是:韩愈作为道统的弘扬者,无论事业还是文学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崇;而柳宗元则要复杂得多。无论北宋的士大夫怎样推崇柳宗元,一旦面对他在政治场上的“问题”则会坚持原则,最多如范仲淹一样认为柳宗元是一个被诱入歧途的牺牲品。面对士大夫之处事理念、传记书写对象之行事动机等诸方面问题,宋祁通过采摭柳文来申述己意,在本传中采摭柳文重构一个易于被本时代接受的新形象,在列传中采入柳文这就充分肯定了柳文的思想意义,当此唐宋转型之际柳宗元的形象则因之改变。从本传的采摭文章和评价取向来看,宋祁还是对柳宗元的文学才能体现出推崇之意。至于在其他传记中采摭柳文则在主观层面上并不是出自文学层面上的考虑,而在弘道意图上。而在客观效果上,确实将韩、柳拉入一个阵营,这既符合宋祁本人“自名一家”的文学观念,也反映了本时代的文化思潮。
正如葛兆光所说:“在唐宋时代,文学努力和政治努力如此紧密地契合在一起,对它的研究,本身对于中国研究中的现代学科体制和习惯就是一个挑战”。在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中发现唐宋思想转型的端倪是一次有效的尝试过程,也是一次学术探险。而采摭柳文入传确实具备了一个研究的平台,透过这一现象,唐宋思想转型中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并在扬弃的过程中被合理延展下来,最终形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一个直接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