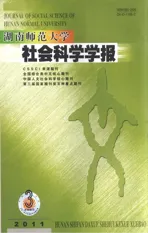论古诗词的“张力美学”文本特征及其翻译策略
2011-04-13颜方明
颜方明,秦 倩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论古诗词的“张力美学”文本特征及其翻译策略
颜方明,秦 倩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张力”论源自新批评对诗歌美学特征的分析。该论自提出之后迅速发展为现代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自身的文本实体特征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张力美学”作为中国古诗词重要审美特征,主要包括主题张力,意象组合张力,意义空白张力,互文张力等张力结构。该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古诗词中应该采取“张力优先”和“语境顺应”策略,在译文中再现或重构原文的“张力美学”结构。
张力美学;古汉诗词;结构特征;翻译策略
“张力美学”源于英美新批评学派,最先由美国学者艾伦·退特1937年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张力”(tension)概念是“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1](P117)。诗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的有机整体,它是公认好诗的共同特点”[1](P109)。此后,“张力”论逐渐成为现代文论的重要理论之一。维姆萨特甚至认为“张力美学”论是“现代批评的顶点”[2](P69)。时至今日,“张力美学”研究已经从诗歌拓展到所有文学文本,乃至摄影、美术、音乐等领域。但是自艾伦·退特始,有关“张力”的研究主要注重其内涵特征,外延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罗吉·福勒将“张力”定义为:“互补物、相反物和对立物之间的冲突或摩擦”[3](P280)。其定义也没有对“冲突、摩擦”所依附的文本实体特征进一步探讨。总体上,现代文论基本上把“张力”当作文学文本的一种基本审美属性,而忽略了其实体构成。因此,文本结构微观层次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因而以“张力”为核心概念形成的“张力美学”理论也没能得到系统化发展。
在退特提出“张力”概念之前,瑞恰兹的新批评语义理论就对“复义”现象予以了关注,燕卜荪的“复义七型”更是对复义进行了分类,对微观层次的几种“张力”结构有过关注。在“张力”概念被提出之后,由于它集中于向理论的宏观方向发展,微观文本结构视角反而被搁置。我国古代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也谈到: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意为工[4](P387)。但是关于如何“隐”在其后国内则鲜有学者论及。近代林语堂在谈及语言之美时指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5](P329)。其文字审美多层次观与瑞恰兹提出的四种意义类型(文义、感情、语气和目的)大体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剑在瑞恰兹的基础上尝试从语义层、形象层、情感层、意蕴层等四个层次构建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他认为“这四个层次的张力构成了诗的立体结构,使诗的内蕴得以扩展和丰富”[6]。该文在微观层次上对“张力”论进行了研究,属于为数不多的批判性接受成果之一。但笔者认为该视角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挖掘。鉴于此,本文拟探讨中国古诗词的“张力美学”的文本结构特征及其翻译策略。
一、古诗词“张力美学”结构
王剑认为诗歌的“张力美学”结构建立在诗歌语言的语义层、形象层、情感层、意蕴层各个层次之间。我们认为上述四层次张力结构属于内容层次的“张力结构”,其形式层次仍处缺失状态。班澜认为诗歌张力主要由语境和句法构成。他提出诗歌高度压缩的语境使诗歌张力的构成大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即抒情角度、语象组合方式与情感态度,而删略、嵌合和倒装等句法形式则使诗句会产生较强的语言张力。他的论述涉及了诗歌张力结构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但我们认为其研究尚不全面。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结合形式与内容对诗词的“张力结构”进行较全面的研究,探讨“诗歌语言张力的建构规律”[7]。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形成中国古典诗词的“张力结构”主要有主题张力,意象组合张力,意义空白张力,互文张力等张力结构。
1.主题张力
“主题”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见《现代汉语词典》)。一般说来,在主题确定的情况下,“文艺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确定形式和结构,都必须服从表达主题的需要”(见《辞海》“主题”)。但是,主题本身“常常就是隐藏在行为之后丰富而多样的思想”[8](P11),它既可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信息”[8](P12),也可能是“隐性的观点”[8]。现有的诗词中,很大一部分就存在主题的不确定性现象。甚至在不同的读者眼里有些诗词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主题解读。这种情况既有读者主体因素,也有作者创造过程的主体因素。如有关李商隐的《锦瑟》主题“自宋元以来就争论不休,有诗集总序说、爱情说、悼亡说、自伤身世说、政治寓意说、咏物说等等十几种”[9]。而且李商隐的很大一部分诗歌都难以概括主题,其含蓄隽永的诗风在古诗词中别具一格。现在学界普遍认同其隐秀之风是受当时“牛李党争”的政治环境所迫,只能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都深度融入了诗歌中,以隐晦的手法抒发心迹。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诗人的诗词也存在多重主题现象。正如接受理论所说:“阅读总是一种动态过程”[10](P67),这种主题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动态地受解读主体的主观因素所支配,如:不同的读者对孟浩然的《春晓》主题就持不同观点,有的读者从“春眠不觉晓”中读出了“喜春”,有的读者从“花落知多少”中读出了“伤春”。这些不同的主题解读构成诗词部分“张力”。
2.意象组合张力
中国新诗理论的先驱者闻一多曾指出:“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妙花祥,装得进无限的内容。”[11]诗歌意象的弹性组合就是构成“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杜甫的《春望》中“感时花溅泪”一句中的“花溅泪”,该部分的三个个体意象就构成了一组弹性意象组合。不同的读者对于“花溅泪”的解读出现了多个版本。其解读有“花瓣象泪花一样溅落地上”,“泪花溅落在花瓣上”,“花让人伤心落泪”,以及“花像人一样伤心落泪”。也就是说,除去“花溅泪”,还有“溅泪花”,“泪溅于花”和“花使泪溅”几种意象组合。同样,“感时”也可以理解为“伤感时候”和“对时局的感伤”两组意象组合。这些不同意象组合都有其合理性,我们很难选择其中一种而排除另一种。从审美的视角看,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上述几种意象组合构成了多层次的审美感受,形成了审美的“张力”空间。这种美学效果恰恰是诗歌创作的追求之一。究其原因,在于诗歌语言的高度凝练简约性,尤其是作为意合语言的汉语在表达形式上的灵活性赋予了诗歌语言更高的弹性度。从本质上看,意象组合构成的“审美张力”源自于诗歌语言的“结构性”空白,即关联词语的省略。这一点是英语所不具备的长处。同时,也是翻译中传译该类张力的难点所在。
3.意义空白张力
“作为诗人们乐于使用的艺术空白的手法,同样也可以产生诗的‘张力’效应,这是因为艺术空白中的省略部分或虚写部分是作者有意的空缺,字面义与蕴含义也构成意义上的层次,从而构成诗的张力”[12]。中国水墨画“留白”手法的艺术本质与文学作品的“意义空白”一样,都是利用余留的“艺术空间”让读者发挥想象,在主客体互动中领略“张力”之美。我们在本文中所指的“意义空白”并非传统“意境”论强调的整体意义上的“境外之境”,而是指诗词作品中具体微观的“意义空白”结构。如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中的诗句: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诗中“北还”和“白发”的主体究竟是谁呢?在这个语境中读者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作者本人,也可以理解为与作者一同南去的故人。正是由于诗中的这种“意义空白”结构使得它具有了一种复合的“意义空间”和“张力之美”。这种所指的意义空白在中国古诗词中比比皆是,甚至局部微观的空白张力还会产生相应的宏观主题张力,如宋词人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中的诗句: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在对该词句的理解上,有的将“眼波”和“眉峰”理解为王观送别的“眼泪”和“皱眉”,有的将它们理解为鲍浩然身处浙东的情人的“眼泪”和“娥眉”。在该词中因为所指的空白而相应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前一种解读的主题是“悲情伤别”,而后一种主题则变成了“轻松戏别”。
4.互文张力
“互文性”指某一特定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关系。该术语最早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1969年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此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建立互文关系常用的具体的手段主要有:引用前文本;用典,即在文本中使用出自宗教故事,历史、神话、传说及名作中的原型;以及仿拟,即通过模仿人们所熟悉的谚语、俗语、成语、名篇名句等形成新的表达方式的一种修辞手段。这些互文手段是古诗词中常见的创作技巧。诗词中互文手段的应用方式各不相同,有的用得不落痕迹,有的则相对一目了然。前者如李白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诗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其中的“散发”行为源自《后汉书·袁闳传》:“常(锢)事将作,闳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扁舟”源自《史记·货殖列传》:越亡吴后,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散发”与“扁舟”因这两个典故而常常为后人用来比喻避世隐遁。一般读者很难在这类诗句中找到相关的互文性。相对而言,有些互文手段则易于发现。如孟郊的《古别离》: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临邛”在本诗中的应用就属于显性的互文手段。如果不了解“临邛”的相关典故,读者很难理解其含义。相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相识于临邛,此后私奔。故“临邛”有“弃家私奔”之意。该处的互文手段可以被看作标记性用法,其“陌生化”表达方式使得读者必须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这两类或显或隐的互文手段都能增添诗词的文化厚重感和审美层次性,形成了互文的审美张力。
二、古诗词“张力美学”翻译策略
诚如纽马克所言:“当诗歌被高度传神地翻译成另一语言时,翻译活动最能体现其艺术性。”[13](P38)其中“高度传神的翻译”也包括了对诗词“张力”之美的传译。无论我国传统的“神似”论、“化境”论,还是西方的“对等”论都蕴含着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再现原文审美效果该命题。但是,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符号负载的认知范畴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虽然人类的认知具有某些共性,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个性反映在认知范畴中呈现为不同的认知范畴体系”[14],相应地就决定了在翻译该跨语言、文化的活动中完美地再现诗词的“张力”之美是很难的,但“张力”作为诗词重要审美构成又是译者必须考虑的因素。甚至译作对原作“张力”的继承应该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张力优先”和“语境顺应”应当作为传译诗词张力美学的两大基本策略。
1.“张力优先”策略
传统翻译理论和现代翻译理论大部分研究者都将讨论的中心放在对“忠实”原则及如何实现该原则的策略之上。他们认为“译者必须努力使原文形象和原文读者感受到的愉悦呈现给译文读者”[15](P101)。诗词的各种形式的“张力”之美是构成诗词美学形象的重要一维,读者在“张力”中欣赏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局部感受,张力构建的立体形象提供的“象外之象、境外之境”更是诗词意境的媒介,“张力”结构则成为意境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要将如何在译文中重构原文的“张力”之美作为优先策略。仍以宋词人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中的“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词句为例。
许渊冲译文:A stretch of rippling water is a beaming eye;The arched brows around are mountains high.
龚景浩译文:The water is the light of her eyes,The hills are the knitting of her brows.
这两个译本都将“眼波横”和“眉峰聚”的行为发起人理解为鲍浩然身处浙东的心上人,但在情感形态上的感受却又各不相同。由许译文中的“beaming”可知译者完全将原词理解为“轻松话别”主题,因为英语中的“beaming”指“愉快的微笑”(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而龚译文中的“knitting”则既可理解为“美人蹙眉”之外在形态,又隐含有“伤感情态”,较之许译文的调侃式“轻松话别”的单一情态又增添了“张力”之美。但两个译本都失去了原词中的主题张力,因为“beaming”的使用排除了“伤别”主题,而龚译文中人称代词“her”又将送别的男主人公排除在外。我们试将上述词句改译为:A stretch of rippling water is the teardrop of eyes;The mountains are clouded brows in cry. 该译文重构了原词的主题张力,其中的“teardrop of eyes”和“clouded brows in cry”可解读为作者的“伤别”和鲍浩然心上人的“遥盼”双重情态。我们认为只要可能,译者就应该尽量再现或重构原诗词的“张力”之美。
2.“语境顺应”策略
当然,由于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语言的言语交际行为,这就决定了在很多情况下译者必须进行适当地变通,以适应目的语语言文化的规范和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也就是说,诗词的翻译还应该遵循“语境顺应”策略。语境顺应是“人们从一系列的语言选项中进行灵活的变通,以满足交际的需要”[16](P61)。翻译作为一种特殊语用行为,同样具有顺应性特点。这在现有译论中的意译和归化的讨论中都有涉及。尤其是归化更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次涉及了“语境顺应”的理据。“语境顺应”较之归化能更进一步从中观、微观层次系统探讨如何归化,因此本文倾向于使用“语境顺应”该术语。“张力美学”的“语境顺应”策略包括了语言顺应和文化顺应两个方面。先以杜甫的《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诗句译文为例,对语言顺应进行探讨。四种译文如下:
Fletcher译文:In grief for the times,a tear the flower stains.
Bynner译文:Petals have been shed like tears…after the war-fires of three months.
许渊冲译文:Grieved over the years,flowers make us shed tears;
杨宪益译文:Even flowers shed tears,it seems,for this sad times.
上述四种译文包括了前述的“花”、“溅”、“泪”四种意象组合,但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基本上失去了原诗中所具有的“张力”特征。这四种译文都反映了该诗“伤怀”的主题,因此仅从对错或恰当与否的角度来判断很难说孰优孰劣。综合比较,杨宪益的译文可以理解为“花流泪”和“花瓣凋落”,保留了上述四种两种意象组合中的两种,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原诗的“张力”审美特征。我们认为该译文更能表现中国古诗词高度意合特征赋予的“张力美学”,与原诗更能“神似”。但在具体翻译中,由于英语这类形合语言更讲究形式衔接,因而很难再现原诗词的“张力美学”。这就需要译者在把握原诗词主题特征的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语言顺应。当然,顺应的结果就是部分或全部“张力”特征的损失。我们认为语言顺应策略中也应该优选具有“张力”特征的译文文本。我们再以杜甫《月夜》中的诗句“清辉玉臂寒”为例探讨一下“张力美学”的文化顺应。“玉”在汉语文化中具有“纯洁”的联想意义和“晶莹剔透,洁白无暇”的意象意义。这种文化的联想意义和意象意义增添了诗词的“张力”审美特征,“玉臂”的“主人”和诗歌本身被赋予了特殊的诗意形象。这种“张力”属于前面所说的源自深层文化积淀的“互文张力”。试比较下面两个译文:
吴钧陶译文:Your fair,smooth arms are chilled in the silver hues.
许渊冲译文:Your jade-white arms would feel the cold of clear moon-beams.
在吴钧陶的译文中,原文所具有的“互文张力”被彻底移除。许渊冲的译文则尝试保留这种“张力”审美特征,将“玉臂”译为“jade-white”。但这种处理招致了不少批判,因为“jade”在英语文化中用于女子有贬义互文联想。为此,马红军提出将“玉臂”译为“milky arms”。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处理方式。因为“milky”能再现原诗的意象意义,且该语境中的月夜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能与英语文化中的神话原型“Milky Way”能建立隐性互文关系。这种“文化顺应”策略能很好的重构诗词的“互文张力”,再现原诗的诗意形象。
三、结 语
新批评文论家克林斯·布鲁克斯认为“诗歌所包容的张力的力量大小是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3](P280)。我们不能不承认“张力美学”是评判诗歌的重要标准。正是这种丰富的“张力”特征使中国古诗词“产生足以让西方意象派诗人倾倒的神妙的魔力”[11]。因此,我们在翻译古诗词时必须对其中蕴含的“张力美学”予以足够的重视,原诗词的“张力”结构应当作为“客体设置的阐释阈限”[17]之一,约束译者主体的再创造活动。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应该尽量采用“张力优先”的策略在译文中再现或重构原文的“张力”特征。“语境顺应”策略则是译者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1]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A].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袁德成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刘 勰.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6]王 剑.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J].当代文坛,2004,(1):91-92。
[7]班 澜.诗歌语言的张力建构[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1):63-70。
[8]Guerin,W.L.et al.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9]徐 艳.略析《锦瑟》的语言张力[J].名作欣赏,2002,(3):86-88.
[10]Eagleton T.Literary Theory:AnIntroduc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s,2004.
[11]俞兆平.诗歌语言的组合张力[J].当代文坛,1986,(5):27-31.
[12]黎德锐.诗歌“空白”艺术与“张力”效应[J].玉林师专学报,1996,(4):56-58.
[13]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4]颜方明,秦 倩,范畴原型观照下的影视片名翻译[J].电影文学,2009,(4):131-132.
[15]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16]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Edward Arnold(Publishers) Limited.2000.
[17]颜方明,非模糊性语词在翻译中的多元阐释机制[J].暨南学报,2009,(5):98-101.
(责任编校:文 一)
A Study of the Tension Aesthe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and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YAN Fang-ming,QING Qia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2,China)
Stemming from the aesthetic analysis of poems by the new criticism,tension theory became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aesthetic theory quickly after its birth.But in its developing process,the textual characteristics were largely ignored.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holds the view that the tension,being a key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ms,mainly includes the tensional structures of theme,images combination,meaning blank,and intertextuality.Tension aesthetics determines that the translator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rategies of“tension priority”and“contextual adaptation”to represent or reconstruct the tension aesthetic structure in the TT.
tension aesthetics;classical Chinese poems;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translation strategies
H059
A
1000-2529(2011)03-0133-04
2011-01-2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古典诗词英译研究新视角——主题与主题倾向下的社会文化语境关联性融合”(08K-0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08JJD74006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翻译创造的认知机制研究”
颜方明(1974-),男,湖南隆回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翻译学博士;秦 倩(1978-),女,湖南益阳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