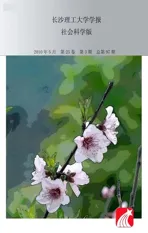美学范式视域内的当代中国城市景观设计解析
2010-04-03黄柏青
黄柏青
(长沙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在当今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景观设计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全国各地正在掀起景观设计和建设的大跃进。从规模宏大的城市广场到小家碧玉的社区花园,从从光彩夺目的户外广告到大放异彩的城市核心地标建筑,从城市的标志性雕塑到大街小巷的微观街景,从繁华热闹的商业步行街人文景观到优雅宁静的的公园绿色景观。各种各样的“景观”遍布于我们身体之外,无时不刻地充实着我们的视野之中。“景观”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对象。这些景观提升着我们的情操、滋润着我们的感官,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虽然,中国当代设计的城市景观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但是剔除表面的纷繁芜杂,却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着两种根本的美学范式,即如画美学范式和生态美学范式。正是这两种美学范式影响着我国当代的景观设计,从而使得我国城市景观设计呈现出这种类型。本文拟就此加以探讨,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同仁的进一步分析。
一
如画美学范式中的城市景观设计强调景观的视觉化审美倾向,要求景观的视觉化审美效果突出如下两种特色:一是景观最后呈现于审美之中都是以可视的“平面化”风格出现,即各种三维的立体形象也要强调通过艺术手法的处理后,以二维的、平面的状态呈现在公众面前,以吸引观众的眼球。我们经常观赏到的“景观”,往往是被景观设计师刻意地将其塑造成有利于观赏的风格化式样,通过采用诸如平衡、比例、对称、秩序、生动、统一等一系列形式设计审美原理细心地构成“美的”植物风景,就如同早期的风景画家那样,景观设计师必须以线条、形式、颜色的变化以及肌理等形式来描绘和处理画卷的方式来描绘和处理景观的变化;二是强调景观的直观性,强调景观视觉的逼真、光艳、甚至夸张的姿态,剥夺了人们的想象和感受空间,审美接收者无需参与,无需进行深入思索,只需睁大眼睛去看,支起耳朵去听就可以,却不在意于景观本身原来的饱滿度、纵深感、丰富感。
比如,在景观时代作为景观的城市雕塑设计中,雕塑的表皮即雕塑的外形、色彩、肌理等吸引人们眼球的元素成为雕塑设计师首先要考虑的因素。雕塑设计师们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雕塑的表皮,这就是材料的肌理成为表现主力的原因之一。雕塑设计师们在充分表现普通肌理效果的同时,对于其特殊的、不为人们熟悉层面的研究和发掘,亦是不遗余力。又例如,作为景观的城市建筑的外墙都被设计为各种各样的瓷砖或者玻璃墙面加以装饰,从而突出其光艳亮丽的外表。即使是一般的混凝土材料,也要注意色彩的设计和运用,从而突出其视觉冲击力。有的建筑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在对混凝土等材料的设计使用时,更是别出心裁地在混凝土中加入各种彩色添加剂,使其具有普通混凝土不可比拟的外观效果。
这种景观设计审美观念直接导致了我国当代景观设计表现形式上两种倾向:一是古典化倾向。即不管在何处,何时进行景观设计与建设,都强调要运用中国古代景观的形式来体现。在各地的景观设计与建设中,中国古代景观中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也被看作是最好的表现形式,被当作民族文化传承的普遍形式而加以复制。比如,在古都北京,曾经有一段时间,城市建设中甚至出现了现代建筑上加盖一个大屋顶的帽子普遍景观。这种景观设计审美的根本误区在于简单的将大屋顶、将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当作中国民族文化永恒不变的身份认同。所以,在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风景名胜区,因为不考虑自然遗产本身的特色,而在景区内大建外观形式具有中国古建筑文化特色的楼台馆所而受到了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的批评。
二是西方化倾向。即将西方国家的城市广场、巴洛克建筑、古希腊柱、威尼斯空中花园等成为当代建筑、当代景观建设的首选形式。乃至于在北京出现了象征着现代化进程的“大蛋”建筑形式——国家大剧院,出现了“敞开大门”的建筑形式——CCTV大楼景观。在这一浪潮中,全国各地的“景观大道”、“世纪大道”层出不穷;奇花异卉,整齐划一的景观树木也被普遍的加以复制,塑料椰树和热带棕榈树成为很多北方街头的首选。彩色的棕榈树整齐的有规律性地“装饰”于大道两边,营造了及其炫丽的视觉效果。在各地的园林景观中,西方式的大面积的草坪、形态整齐的树木配置在一起成为常见的设计模式。这种城市景观设计观念盲目认同现代西方的帝国景观,误认为只要是西方现代的形式,便有现代的意义,误认为奇花异卉奇景就可以产生美,高雅的巴洛克景观可以标榜自己出众的身份,简单地将奇花异卉、古希腊柱、城市广场等当作西方文化,当作西方现代化的身份确认,尤其是当作西方现代精神的确认。
总之,当前这种“如画”美学语境中的城市景观设计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却透露出本质上相当的统一性,即都存在机械性、片面性。这种景观设计美学范式集中于景观优美一面,强调其视觉、静态、单调、固定的形式因素,重视景观的图画性和引人注目的特征,持一种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观念,注重景观的表面价值,认为景观是有界限的、框架性的特殊场所,重视整洁而纯洁的景观,这种景观设计理念往往将审美主体的人排除在景观之外,追寻对于优美风景的直接愉悦,重视“视觉质量”(visual quality),不考虑景观的生态整体性(ecological integrity),忽略了“生态价值”,忽略了景观设计的根本目的是构建人性化的、家园式的、供人分享的环境这一理念。这种景观设计和建设在我国当代被推崇备至,存在盲目化的倾向,具有很大的局限,乃至于“我们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土地;我们得到了装点着奇花异卉、亭台楼阁的虚假的‘造景’,却失去了我们本当以之为归属的、籍之以定位的一片天地,因而使我们的栖居失去了诗意”。[1]
二
生态美学范式中的城市景观设计强调:要改变单维度的视觉审美景观设计观念,开启一个全知觉审美的多维度身心体验的景观设计理念。一方面要求我们改变、超越以往“如画”美学范式视域内将景观设计集中于优美景观的视觉、静态、单调、固定的形式因素,超越“如画”美学重视景观的图画性特征,持一种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观念,注重景观的表面价值,认为景观是有界限的、框架性的特殊场所,重视整洁而纯洁的景观等传统景观设计观念。而采取与此相对的生态美学范式下的城市景观设计方案——即一种综合的、动态的、活动的、变化的、细微的、无风景的审美模式,它注重景观的象征意义,认为审美对象是无界限的,甚至包括那些凌乱、肮脏部分。在生态美学范式中的城市景观设计审美,审美愉悦来自于了解景观的诸多部分是如何与整体相连的,例如,稀有或珍贵的动植物是如何在未触及的生态系统中维持的。而这些动植物被西方学者称为“审美指示物种”(aesthetic indicator species)。
这种生态美学范式视域内的城市景观设计,其中的“人——景观”处于互动之中。它不是消极的、以对象为取向的、被动地接受现成物,遵循“刺激——反应”的审美模式;而是活跃的、参与的、体验性的,包含着人与景观之间的对话,它要求我们积极地参与、融入到景观中而不是消极被动地观看景观。景观不再仅仅单纯是一幅绘画或其它艺术对象,而是随着时令和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活的景观。这使审美体验观念超越了康德和其他理论家的“无利害性”概念而走向伯林特的“融合”(engagement)观念。通过这些互动关系,我们与自己、与景观进行着“对话”,而对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2]
另一方面,生态美学范式中的景观设计要求我们将日常审美惯性所遮蔽的丰富之美重新发掘、展示出来;必须对我们的敏感性进行培养,必须获得“对于自然对象的一种提纯了的纯净趣味”,从而捕捉大地上超越“如画”风景的审美潜力。它通过知识的培育等方法来改变我们的审美判断力,提升我们的审美感受力,将帮助我们穿过事物表面,使感官体验超越一般优美风景而欣赏平凡、甚至丑陋的事物。如,美国的利奥波德即以如何欣赏沼泽之美为例:沼泽之美在于它对于周边生物共同体的功能。尽管无法直接感知这种功能,但一旦通过生态学知识认识到这种功能,我们就会改变对于沼泽的看法而对之进行审美欣赏。这表明:在生态美学范式中的景观审美体验,概念性行为(conceptual act)改变并完成了感官体验,使感官体验成为强化的审美体验。对于利奥波德来说,乡野的审美诉求与其外在的缤纷色彩和千姿百态关系很小,与其风景品质、如画品质毫无关系,而只与其生态过程的完整性相关。这表明:与西方传统“如画”美学相比,大地美学的审美范围大大扩大了,从景色优美的自然环境扩大到所有自然环境。随着环保运动的展开,西方改变了传统的风景审美模式,将自然审美扩大到湿地、沼泽这些与西方传统景观美学迥异的对象上:从北极冻原到热带雨林,从沙漠到沼泽、湿地。[3]
这是因为生态学研究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是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其它物种一样,人类也完全地被包容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之中。人类是一种自然存在,与自然中的其它部分处于连续性之中。人类并非站立于自然之外而静观、使用和探索自然。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认为生态学意味着一种无所不包的环境背景(environmental context),一种流动的介质(medium),一种四维的全球性流动体。它具有不同的密度和形式,人类与其它万物一起共存于它之中。在它之中,无论是有机的、无机的、社会的、文化的,每个因素都相互依赖,并且与其它因素密切相关。这种相互依赖、密切相关性使各个参与者互利互惠,确保着一种持续的平衡。这种平衡促进着所有有机体的共同福利。[2]在这样的基础和前提下,生态美学注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对话、沟通、交流,强调审美的终极意义在于人类自身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美学主张注重感知的能力,关注感官的意义,通过感知来连续性地体验着环境,并体验着环境的连续性,并思索我们从事活动的意义。在生态美学范式中的景观审美,强调一种生态系统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审美考虑不仅引起重视,而且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人、对象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运动等所组成的相互关系中,生态体验成为中心特征。[2](P25)因此,审美意指一个具有明确知觉特征、结为一体的区域:不仅关注到形状、颜色、肌理、音响、韵律等形式美因素;与活动着的身体相关的体积宏大的块体;还要关注到与人身心和谐发展密切相关的光线,阴影和黑暗、温度、气味、运动等等。所有这一切融汇在一起。在这里,更为主要的是审美欣赏是交互的。审美欣赏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的,它同样是主动的。审美欣赏需要欣赏者的亲身体验和积极参与。欣赏者要辨识环境的性质,为环境赋予秩序和结构,从而为环境体验增加意义,同时也在审美欣赏中为体验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内容。通过审美活动我们与环境紧密地融合为一体。[4](p14)
对于生态美学范式中的城市景观设计来说,其意义正在于引导我们从事景观设计的时候更多的考虑我们如何去控制、去改善什么样的负面知觉条件。许多状况是非常明显的,诸如大气污染与水污染,噪音污染,有害而令人生厌的气味,还有酷热和严寒,强风和过度的光照,如此等等;在巨大、单调、拥挤的购物广场和停车场,以及混凝土建筑丛中、闹市中心的通道上,经常遇到类似的通病。将城市景观中特有的为害情形罗列出来,我们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交通噪音和汽车尾气,建筑工地的噪音和烟尘,公共场所邻近以及私人场所的唱片“音乐”,忽然从身边窜出的车辆,等等。其实还远远不只这些。[2](P25)生态美学范式中的的景观设计就是要减缓这些对人类生活有着很大负面的环境。
同时,在这种美学范式的城市景观设计中也可以加强我们对环境体验的因素。比如,在商业或工业区那样的“混凝土建成的野兽世界”里,可以布置些绿色,设计些相对安静的空间,使人能够得到安全感而放松;从喷泉中传出的轻松乐曲,流水潺潺的水道景观,海滨的浪涛,都能够使人放松;躺卧在长椅上安逸、野餐和游泳胜地的悠闲,都能使环境体验更加丰富;在商业街区上设计步行街道和人行道,修建防晒防雨的拱廊;在酷热或交通特别拥挤的区域修建封顶的或封闭的人行道、人造天桥,等等,都是改善环境体验的途径。在最低限度上我们可以说,减少噪音和污染,有助于缓解感觉压力而使环境体验变得轻松。[4](P25)
所有这些环境知觉方面的考虑并不仅仅是为了舒适和愉悦,而且是为了健康和安全。如果我们将城市景观理解为生态系统,并认定城市景观不应该压抑居住者,而是应该有利于居住者审美地融合于城市景观中、从而提高其生命质量,这些考虑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种充满和善的审美生态学,也就是一种有利于审美融合的审美生态学。它能够指导我们修建更富人性的城市环境,使之能够丰富人类生活而成为宜居之地,从而完善人性。
总之,一种富有正面审美价值的生态系统将考虑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和娱乐休闲区如何各具特色并互相影响,将考虑在形成知觉体验中什么因素更加重要。在一个人性化的、功能正常的审美生态系统中,城市景观并非外在环境,而是一个包容一切的环境:它与它的居住者结为一体。这一环境的居住者积极参与并维护着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要使城市景观更加人性化,严肃认真地考虑审美融合将是重要的一步。
三
“景观”(landscape)一词最早见于《圣经》,被用来描述耶路撒冷所罗门王子的神殿,以及具有神秘色彩的皇宫和庙宇;在德语中这个词是“landschaft”,在法语中是“paysage”,都含有风景、景色的意义,它可以代表一幅风景画,也可以表达某一城区的地形或者从某一角度所能看到的地面景色,它的初始意义是指一种瞬间产生的庄严、典雅的场景,有戏剧化的含意,这种场景或许只是特定时间与特定角度的产物,因而传统的景观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均极重视画面效果,即客观物像的完美与和谐,通常情况下,三维的风景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成了二维画面,因为从特定的角度去透视一个既定的环境,尽管有科学的光学原理会使观者主观产生三维的感觉,但客观事物的成像过程乃至结果终究拥有极强的二维特征,那么既然景观具有画面特征,传统的造景过程就极讲求画面的美学法则,比如构图方面无论对称的、不对称的都一定要有均衡感,景物轮廓线的起伏要有节奏和层次,色彩的构成要丰富而不失统一,植物、建筑与自然土壤及水体之间的色彩要相互呼应,产生和谐的美,从我们所知的初始的景观概念出发,可以看出景观的构成要素不仅仅包括自然风景,还包括建筑、广场、雕塑等人造景观,但在传统人的视野里,该类人工景观因素所占的比重较小,同时古典的建筑或是雕塑造型中均包含着很强的人性内容,如人的尺度、比例以及人的形象特征的变形,人工硬质景观在材质使用方面也均以天然的材料组成,因而传统的景观中各组成要素是充满自然气质的,是和谐的,硬质和软质景观之间无论形态变化或色彩构成、质感对比方面均没有过强的冲突,因而也不会产生挣脱画面的张力,这时依据平面造景的法则去描绘景观之方式非常适宜,那时人虽穿梭于景观之中,但其路径却是线状的,方向很单一,这样就为其最终获取画面的完整性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如画”美学语境中的城市景观设计强调借助由艺术确立的标准来估价景观:景观被当作绘画来欣赏,景观只有得到精确展示才有价值。景观只有按照绘画范畴才能得以恰当地欣赏。这种景观设计其实质是受到传统景观设计审美理想的影响。这种景观设计片面强调视觉审美,强调视觉审美的霸权,而偏离对景观的全面理解,本质上是对自然、对生态一种粗暴的践踏,,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片面化的理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显现。这种景观设计观念与审美观念,最终也会伤害人类本身,强化视觉,弱化其他感觉,使得人们失去了作为此时此地人的自我,也失去了自然、大地、景观的本真。俞孔坚教授将这种“盲目”的景观设计理念上升到生命的意义和民族身份的危机。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现代景观的设计必须重新回到生态、自然,归还人与土地的本真,找回栖居的诗意。
生态美学范式语境中的景观设计则认为,景观首要地并非被体验为“景色”,而是被体验为“环境”;身处环境“之内”的审美主体将景观欣赏为动态的、变化的和不断展开的。这种审美立场重视事物的多重感性特征,综合运用生态学知识、想像、激情,将景观理解为讲述着自身故事的新型景观。[4]当然,这种审美模式依然是人类中心的,也就是说,它依然是人类做出的审美判断。但是人已经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其中的每个因素都相互依赖,密切相关,其本质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这样的基础和前提下,生态美学语境中的景观设计注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对话、沟通、交流,强调审美的终极意义在于人类自身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一种真正的景观审美将祛除人类主体的中心位置,将促成一种更加深入的、也可能是更加丰富而敏感的景观——环境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俞孔坚.寻常景观的诗意[J].中国园林,2004(12):25-26.
[2][美]阿诺德·伯林特.审美生态学与城市环境[J].学术月刊,2008(3):13.
[3]程相占.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J].文学评论,2009(1):69-70.
[4][英]埃米莉·布雷迪.走向真正的环境审美:化解景观审美经验中的边界和对立[J].江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