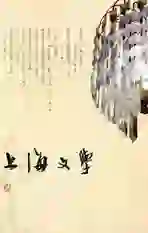幽深的潮湿
2009-01-12朱以撒
在本文中,我又一次感受到清、真、直切而执著的气息。这是与商潮、名利、金钱、争锋、尔虞我诈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里的洁净气息。满眼的植物、动物都是契机和暗语,在向人类提出生命的指向问题,特别是我们的灵魂将向何处皈依?朱以撒熟读古文打下的文字功底,亦营造出一种完全没有烟火气的风致,让我们也随着他在那个山中小寺的台阶上坐下来,观满山绿色,听鸟语花香,静静地体味人生的真谛……
韩小蕙
站在开阔处,看南岳水汽如纱巾一般地飘飞过来,头顶乱云翻卷随风飞度。山底下还是酷热难熬,山上已暑气尽消,清凉满身了。人在绿阴下,心态、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那么慌慌张张,匆匆忙忙,斯文又重回附身。主人说,待会儿到房间把窗打开,让山风进来,睡个好觉。果然,推开木质窗户,隔着纱帘,一丛丛茅草的前锋已经擦着过来,沙沙作响。夜间,躺在床上,我听到了好久没有听到的声音,山风呼号,林涛应和,由远而近,由近走远,便很兴奋,起身伏于窗上,看外面黑黝黝的世界。山野之气太厚重了,以至于人气微渺,甚至不如正在穿行的夜鸟。山中的品类都安睡了么?当然不是,那些乐于在深夜中持续鸣唱的小昆虫——恕我只能分辨出其中的一种是蛐蛐,正在不知疲倦地下着气力。黑暗使眼睛失去审视或者欣赏的力量,只得托付耳朵了。倾听只是一个大概,方位不定,这些声响过于紧密,荡过来漾过去,听觉也一时把握不住了。不过,完全可以说这些声响都是本能的、兴致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在这个称为福严寺居士楼上住下,着实没有什么值得生出忧愁,这些暗夜中的声响,带着喜悦平和的心情倾听,是一支支多么美妙的曲子。
如果没有人动一座山,不在山中架设缆车开凿路径,任由一座山生长,它是往野性蓬勃方向去的,它是大地突兀而起的一块坚硬的骨节。
来到农家饭庄,主人问,如何烹煮可口?我都一如既往地认为:照旧。我是不会指手画脚地点拨少放辣子或者多加佐料。每到一处,地方风情总是从炊爨中体现出来的,它们必然与我的故乡口味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表面上只是口舌上的差异,背后却是很深的渊源,其中就含纳了一代一代对于水土的理解,是以符合生存来取舍的、运用的,同时也符合身心的快乐。对待生存的理解,就是最小的口舌之需,也是与生长的水土融为一起的。在筷子落下之际,夹起来的就不仅仅是一筷子菜肴了。农家饭庄的摆设都如出一辙,简单、朴素,无论是杯盏还是板凳,都是遵循这一原则。这反而使人乐于相信开饭庄的年轻人的坦诚,装饰是毫无必要的。在绿树包裹中,食欲出奇地好,而蔬果、鱼肉陈粲盈几,足以经得起视觉、味觉的挑剔,不由连下三碗。对于农民,我还是乐于相信的,如果连他们都不能相信,那我真觉得情感倾向很危险了。我是从粗浅处来判断的,容貌衣着,眉目神情。这大抵与我曾经有过的农耕生活不无关联,使我在农民面前毫无戒备之心,对他们的言语、举止都怀有好感。尤其是大山之腹,对于朴实的破坏有一种天然的抵挡力量,空气如此清新,也有理由对于人性的真善提出同样的要求。
蝉声无歇,这些短暂的生命在南岳的密林中生生死死,总是在朽烂的湿气土层里顶出新的歌者。飞来飞去,飞不出如此高耸的山岳,见到外边的世界。此地甚好,真的毋须有对于外面的好奇。山中的夏日尤其短暂,立秋已过,这也使有限的生命对于鸣唱更抓紧。潜伏于更为深暗的林木高处,人的肉眼难以望见其中之一,只是万千的蝉声,会使闲下来的心情,琐屑一些。蝉只是微小之物,形貌难以悦人,蝉声又单调沙哑,只是以蝉为题材的诗文依然不少。生物的生命旅程无论短长,从自然规律括之,过程都是一致的。蝉还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飞物,以至有被记录的可能,更多的不知名的细微物,在茂密丛林的阴翳潮湿处,也同样进行着自己的行程。落叶堆积陈腐,踩上去松软柔韧。时而日照,时而雨淋,潮湿助长了萌生的速度。相比于干燥,潮湿易于朽烂,也益于诞生、繁殖。更多的生物是置身于潮气之中的,蹲下身来,拨开一层落地成绺的叶片,只要视力正常,都会看到被惊起的细微虫豸,急冲冲地朝着更湿的深处躲藏,潮湿和暗处是它们绝好的栖身之所。
寺门前有一片洁净的石坪,可以在这里看远。暮色下来的时候,远处有星点的光亮闪烁,那是一家又一家向晚的灯火。巨大的柳杉、罗汉松随着风势抻展,在有规则的摇曳中,淡淡的植物香气徐徐散了开来。已经不是开花的季节了,这一定是从体内沁出的暗香,它的素淡、隐约,也许是最适宜一个中年人此时闲散的心气的。和百花竞放的浓艳相比,它们是似有若无的。不同的植物,内部贮存着不同的汁水,饱满和壮硕,被坚韧的树皮紧紧包裹,难以泄露。南岳风势强劲,使枝叶的摇摆、碰撞程度达到极限,香气便从拉抻的缝隙中沁了出来,融入流动的空气里,为外来人灵敏的嗅觉触摸。这些气味的倾向是生涩的,或者辛苦的,却都一样的淡薄,容不得多想、分析,它已经悄然走远。不同种类的植物,都在共同地承接着雨露,在一个山坳间适得天性,笔直、蜷曲,秀逸、丑陋,越往后越鲜明了。一个幽深潮润的山岳,应该成为丛林的乐园,任不同层次的绿意泰然伸长。与丛林下飞奔窜动的禽兽不一样的是,树是独立不动的,二十年前来旅游,它根植于此,二十年后依然如此,便使重游者有了如见故旧的温暖。独立不行,也就使每一棵树都充满深深的宿命。有的种子被风吹着,落实于沃壤之中,不仅长势生动,品相亦佳。这一点从树冠的形态上完全可以看出,是很有一番雍容华贵的韵致的。那些于崖壁上搏命的枝条,则显示着艰难与挣扎,全然是一寸一寸在挤压中延伸的,这很像生计艰辛家庭中的少年,经常吃不饱,又得不到好的教育,加上外界歧视的目光,渐渐就变成一个野孩子,容颜古怪不端,神情冷漠幽怨,让人生畏。没有办法,只能怪命数不济。这与人生太接近了,艰辛如影子跟着,难以剥离。
“独秀”是我在南岳中最常见的字眼。比起其他山岳,南岳土地肥沃,雨水丰沛,我甚至能嗅到土层中丰富的气息,是那种利于植物种子落下便生出绿叶的一个场域。余下的,就看树木自身的攫取能力了。
与松柏樟枫相比,银杏自然是稀罕之物。我经常看到的不是扎堆的银杏,而是捉对而立的,雌雄二株,或近或远,以能够相互交流为理想距离。这也是很让人难以理解的距离,保证着生殖的可能。黄昏中的银杏树只有一株了,在寺门边上,树皮老厚,开裂如畦,顶上依旧当风有声。以前离此不远必定还有一株异性银杏,却因不测而为尘泥,使生者茕然独立,无法尽其扬花授粉或籽实累累的义务。这也使它的历程从此简单起来,略去许多细节。那些扬花春日,结实夏日,有着丰硕秋日的植物,可以视为一种十分圆满的历程。在我眼里的树大都没有变化,一个看到变化的人,一定是他的内心发生巨变了。
树是静默之物,再多种类的树群的聚集,只能使一座山更为幽深,只有风雨骤至,它们才发出雷霆般的轰鸣。一座寺院安置于丛林深处再也适合不过,它们都希望静谧,在静谧中持守等待。
有两个年轻僧人出来了,在银杏旁的台阶上坐下,不言语。这个傍晚更加清淡。
湿淋淋的祝融峰顶,香客如堵,烈焰冲天。有步行登临的,也有坐轿而至的,都怀有共同的祈求佑福之心。民间信仰常常在这个时候让我震撼,等同于不可阻挡的潮水。人被推搡着进入,火神庙内满盛着呛人的烟火气味,意味着这已不是一个寻常的所在。祝融已被崇仰者敬奉的香烛熏染得失去了本色,多少年安坐不动,领受一代代的跪拜和供品——他的一切承诺、引导、暗示都是在岿然不动中进行的。同时,也倚仗香客的意念,怀祈求之心而来,抱如愿的喜悦而归。这么多人互不相识,不辞劳苦地朝着一个方向,也就很值得思忖。并没有人策划、鼓动,也无大道理可言,都属于自然而然的精神需求。其中有被父母怀抱着的孩童,也有步履蹒跚的老妇人,身上被雨气打湿了,发梢垂落着晶莹的雨珠。对于不谙世事的孩童而言,父母不吭一声,这里的氛围、气味、姿态、动作,可以用最传神的字来形容,就是“熏陶”。熏陶毋须出声。一种精神走向渐渐被确定,也就相继有一些动作追随,运用自然。在我们进入任何寺院庙宇,都可以遇上如此相同的眼神和姿态——人矮了半截,眼里充满渴望。地上那么湿漉,甚至有些泥泞,似乎无人察觉。一个妇人用杯珓祈求祝融引领。杯珓似乎是竹根所制,她诉说已毕,将一对杯珓相合,轻轻抛起,落在地上,声响顷刻被淹没。我一看,杯珓的两个平面都是向上的,从民俗角度看,她所祈求之事,祝融并没有明确表态,拿不定主意。她又连续抛了几次,均如此。这使她有些失望了,却不愿休止。后来有两次,杯珓倒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完全可以解释为,祝融对她的祈求已经赞同。妇人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她不忙着起身,依然跪着,表达如愿之后的谢意。
这么密集的场面,里边的香客不乏有学问者,难道可以如教科书所说,以愚昧指嗤之?在祝融金身的背后,是我们看不到的、摸不着的,又难以言说、实指,像南岳的雾气缥缈虚幻。我们的敬畏,也就自然升起。
登高永远是我们生活中的需求之一,很少有人登临峰巅还颐指气使的。对登山者而言,不应给自己创造省却脚力的机会,缆车一类的机械都对登临的原心态进行着破坏。在这点上,我倾向这些山野老太,她们的虔诚以拄杖步履来实现。愿祝融护佑她们平淡而朴素的晚年。
又一场雨下来了,整座山饱含着润泽,连同山上无数的生命,又一次被清洗或者发生。
装模作样地吃了几餐素食。尽管内心乐意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至少接近出家生活的皮毛吧。口腹还是有一种本能的不满足——其实,我们的素食已经比僧众丰富得多,是有所加工的。终年茹素,这个行为也就很少一部分人才能做到,是趋于简易、单调,从物质上来节制精神上的贪婪。出于礼貌,我表示很满意,如果时间长了,能够经得起肠胃的煎熬,成为一个自觉的茹素者也不是没有可能。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古训始,美食的进展长风万里,使每一个城市的酒楼业兴旺繁荣,不管是精神交流还是物质交易,首选之地总是酒楼。饮食不是趋于简单了,而是愈加复杂,花样如戏法翻新,使人目眩神摇。素食是趋简的,用尽可能少的调料,使植物本身特有的滋味不被掩盖,在素食中更多地品尝到了不同植物的差异,口感进入微妙。看着刚从寺院菜地拔出,菜叶上还闪动着晨露的光亮,纹路清晰,叶片舒展,汁水饱满。一种生命被另一种生命品尝、吸收,说起来是自然规律,却也不难看出,生长是需要许多其他生命扶持的,其中就包含这些翠绿的菜肴,它使我们在接受时神清气爽。
我埋头吃菜,不吭不响。算起来,茹素花费的时间是很少的——你没有什么理由在饭桌上拖延下去,饭菜的量是如此巧妙地达到正好,或者即将正好。
简单,也算得上生活最基础的方式了。尽量地削减瓜葛枝蔓的纠缠、攀援,很简单地茹素、穿着、安息、行路。娱乐是不在简单之内的,它使人萌生竞胜心事,生出不少淫技,并不适宜山居生活,只有反复地习静、说法、翻经、奉佛,大概是最合乎简单的法则。我对简单的生活有一种突出的向往,这当然要追溯到四十年前的知青时代,悬在人际网络关系的空中,除了家人的联系,就是应对简单的农事,面对四季轮回的风景,想法是极其单纯的。一个人如果可以温饱,寄身烟霞,清修清赏也不失为闲淡的过程。只是后来由于农耕生活的结束而中断,在光怪陆离的都市里,复杂渐次上身,它们的宗旨正是悖简单而行。我的性情并不乐意于此,也本能地欠缺足够梳理复杂的能力,就像与人打交道,缺乏应有的热情与耐性,在复杂面前暴露出了无能。这也使我在快刀斩乱麻的时候,斩出一堆的麻烦。有人总会对我说:“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么,是什么让简单变成复杂呢?我一直相信,这种性情与湿淋淋的水田耕耘有关,可以在那些日子里找到痕迹。那种生也简单死也简单,日子过得粗糙、朴实,是与山野环境分不开的。都市正是要改变这种情调,改变已经过上城市生活的我的心理和生理。寺藏深山,自然比都市中的寺院更具有简单的条件——山岭阻隔,道途险要,人于寺中,身心都被收束,慢慢就培养起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向度,从心理上不屑于繁华喧沸,从生理上抵制声色犬马。
一拨拨的雨,充分地浸润着古寺和古寺中人。每一拨的雨量不同,速度不同,倾斜度也不同,却如一地洁净晶莹。功课做完的几位僧人站在檐下,抬头看雨水遥遥垂下。高大的树冠缀满了雨珠,一阵风过,珠玉迸溅,坠入松软的土层。简单有简单的功用,徐徐平息了对于俗常时日的怀想,欲望销蚀以至归于乌有。山中潮湿,没有什么可以逃过它的潜浸。年长的僧人,有的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没有世俗的渴望,无喜无嗔,安之若素中,目光澄澈有如年幼的婴孩。那些初入佛门的年轻者,毕竟还会思念山下的红尘红粉,而今要在山中的润泽中,渐去火气躁气,湮灭那些花哨的虚妄。在都市中,十年之后再见一个人,已是越发蹈厉张扬,忙碌更甚,索求更甚。可是十年后再见一个山中僧人,已经看到眉宇间神情被平和包裹,问一句他答一句,既不积极也不懈怠,像黄昏中的色调,合了过来,这就是一种修为的力量吧。需要分辨清楚的是,他们与所谓的隐士不同,那么些隐士习惯在山林与市井之间闪转腾挪,窥测方向,既要标榜清高,又无法摆脱对于官场生活的酷爱,隐居只是策略也。
久于寺中听雨,伴着梵乐,身心俱轻,不由得内心感受与常人相比,岔口已是越来越大。
再简单也需要细细品味,或者说——简单也要有人懂。
我看见那位在晨曦中敲钟和暮色中击鼓的僧人了,应和着自己手上的动作,他唱起一首外人根本听不懂的歌。每一天,钟的清亮和鼓的深沉之声从他的动作里散发出来,穿过寺院的高墙,进入茫茫的丛林里。每一天他都在做这么一件事,一直要到老迈不能胜任方可停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引用者多半是带着贬义的,很少想到这正是一种职责,不可不撞,亦毋须多撞,但要长久不辍,这才是难度所在。在一个夜里,我从方丈室出来,看到那位每日怀抱虔诚之心写经的僧人。已经有两年了,每日以手指头应对针尖,取血为墨。现在看来,十指应是千孔万孔,心里却越发喜悦。方丈说了,他是没有与人、与外界交往的欲求的,一个人的心事何必要向外人倾诉呢?唯有日日闭门不出,事佛抄经,书法没有功底,笔迹不佳,却一本一本地摞了起来。此时他正在一个昏暗的房间来回踱步,房门出乎意料地打开着。我不敢进去,也看不清他的脸色,想来,他应该是没有什么脸色的。出家就是这样,当许多人奔向光怪陆离的都市时,另一些人却背道而驰,向那灯火阑珊处。弘一曾说,当和尚就要像个和尚的样子。这不仅是指容貌衣着,更主要的是指向内心的世界。在静寂中,许多外在的关系中断了、剔除了,简之又简。传说弘一出家后他的日本太太不远万里,来寺院求他回去,最后仍然绝望而归,说明出家人是用不着那么多情调来抒发的,在向往彼岸的行程中,静静地被引导就是不要四顾。
我在方丈室还见到一位年青人,满头乌发,殷勤地为我们搬凳子。见我疑虑,方丈说他是来出家的,但须考察一年半载方可决定。
我赞同物质生活的朴素简单,只是超出了我的限度——寄居数日颇为快意,长居却难。临走时,那位接受考察的青年也来道别,但愿下次再来,他已经是有道行的僧人了。
值得一说的是:我们在寺院里栽了一株罗汉松。每个人象征性地铲了几锹土,拍了几张照片。大家知道,这株落在南岳湿润土壤里的罗汉松,要比在场的每一个人,更为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