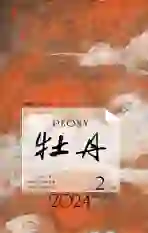万物有灵,和谐共生
2024-03-26张向辉
张向辉
20世纪50年代,奥地利学者路德维系·冯·贝塔朗菲提出:“生物学的世界观正在取代物理学的世界观”[1]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物理学的世界观是一把双刃剑,既让人充分享受科学发展带来的便利,也带来了诸如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等影响人类生存的诸多社会问题,而生物学的世界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自然生态观与生物学的世界观不谋而合。
一、天人合一,万物有灵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家‘穷天人之际的基本思路,既是一种宇宙观,伦理观,同时还是一种生态观。作为一种生态观,其基本要义就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体,共存共荣。‘天人合一观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高扬宇宙生命一体化,自然万物无不是生命的结晶。”[2]
祖克慰的动物散文包含着朴素的自然生态观。其书稿《动物映象》《观鸟笔记》《画中读鸟》《乡村鸟谱》是关于动物的系列散文。《动物映象》中曾经生活在自己家乡的豹子、野猪、老虎等动物的逐渐消失,引发作者的怀想和忧虑,使他重新审视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观鸟笔记》《画中读鸟》《乡村鸟谱》中,司空见惯的麻雀、云雀、燕子、灰喜鹊等鸟类,在作者笔下,不仅是寻常百姓的亲朋好友,也成为画家情感的寄托的主要载体。
在祖克慰笔下,一切生物都有靈性。夫妻之情、舐犊之爱、同伴之助诠释着大爱无疆的本质。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鸽子,时常一起觅食,一起嬉戏,彼此忠诚,坚贞不二。燕子“入则成双,出则成对”,被喻为“两个劳动模范,一对恩爱夫妻”,同时又是高质量陪伴的父母的典型,一对燕子,每年孕育两窝子女,三四月份开始,六七月结束,将近五个月的时间,燕子将大部分的时间奉献给自己的子女。黄鹂是“情侣鸟”,它们形影不离,终身相伴。成年的黄鹂鸟,如果一只被捕获,另一只就绝食,为情而亡。这是对“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旷世爱情的呼应。面对猎枪显得格外宁静、安详、无畏的一只待产野兔催生出的母爱,瞬间让猎手产生恻隐之心,放下猎枪(《与一只野兔对视》)。一只偷嘴狐狸,为了挽救自己的妻子儿女,表达忏悔的诚意,硬生生在石头上把自己的嘴磨出血;它用自残的方式撞向石头,只是为了给妻儿争取逃命的时间(《灵狐》)。两只白头翁面对号称“雀中猛禽”的伯劳,毫无畏惧,用生命相互保护;一只绣眼鸟面对被撞死的同伴,不停凄厉鸣叫,久久不肯离开,这是同伴之间的有情有义。红嘴蓝鹊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也不会攻击人类,只攻击伤害它的人或者动物。狼本能地保护幼崽,“我”依据对狼性格的了解,各自划定边界,以退为进,平安逃脱,这是自然界的质朴的道,也是人类的生存之道(《与一匹狼对峙》)
“人与自然是在同一个浑然和谐的整体系统之中的,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美就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那种化出化入、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3]乡村丰收使者的黑卷尾(又名“吃杯茶”),虽然聒噪,但也很有趣,它们有时会撵着孩子飞,和孩子一起嬉戏、捉迷藏,充盈着童真的快乐。在草丛里对峙的两条蛇,踏着舞蹈的节奏,忘我地舞着,仿佛馄饨万物之初萌。幼年时的“我”精心照顾一只红狐,伤好后的红狐,像猫一样温顺,在“我”的身上蹭来蹭去,与“我”嬉戏玩耍;离别时的红狐依依不舍,眼里涌满泪水,发出一声声哀鸣。(《寻找一只红色的狐狸》)。燕子依恋旧巢,农人倾心迎送。灰喜鹊偷吃东西,人们也不打扰,至多吆喝一声。母亲在雪天为麻雀撒下的一把碎米或者谷粒,是乡村人的善良,更是对“万物皆有灵,草木亦有心”的生命的敬畏。
二、心存敬畏,珍视生命
“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有着它自己运动演替的方向。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森林、土地,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生之物,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4]任何物种的存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生态的平衡,靠的就是一个个种群的存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松树、槐树、柿树、栗毛都没了;黄鼠狼、刺猬、狐狸也没有了影子,百灵、黄鹂、山麻雀、斑鸠、鹌鹑也不多见。”森林的过度砍伐,使山坡荒芜,环境破坏,大气污染,从而导致动物的大量迁徙。大苇莺栖息的苇园被填土开田,种上了庄稼,大苇莺失去了家园,他们离开家园时凄厉的鸣叫,是故土难离的不舍,是失去魂魄的哀怨,是对乡关何处的恐惧。曾经郁郁葱葱的青山,被一块块梯田代替,没有了树,狼就没有了藏身之地,变成了一个虚无而抽象的名词。鸟类的思考者蓝矶鸫,孤独地离开,这份孤独来自人类惘惘威胁的警惕。村里的最后一只野猪被围杀时发出的一声吼啸,是深陷绝境时的无助,更是向人类发出的最后的、最强烈的抗议;山林里的最后一只豹子,因饥肠辘辘,面对猎枪,没有躲避,急切地吞下到手的猎物。被射杀的豹子掉下一瞬间流露出的绝望的眼神,骨瘦如柴的体态,让人动容唏嘘。最后一只老虎离开家乡,半是因为感恩,感恩乡亲的不杀之恩,恐怕也是因为它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得不选择离开。可爱的蓝矶鸫已经不见踪影,它的离开可能只是为了寻觅更适合居住的环境,为了逃避死亡的威胁,何处是家园?
记忆中的乡村与眼前的乡村,存在很大的差别。原先的花红柳绿,一片死寂,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原先适宜鸟儿们居住的草房、瓦房变成了钢筋水泥堆砌的楼房、平房,那个由人、树、鸟和炊烟组成的村庄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中,诗意不再。“村庄里,少了些人声,少了些禽畜声,少了些鸟声。村庄,陌生而又孤独。除了家人,你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的乡村我的家”。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注重亲情、乡亲变得注重物质,过去乡亲帮忙,只讲感情,从不谈钱,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金钱和利益。其实,“真实的生活价值来自人们之间的关系,包括死去的亲朋邻里。生活价值不仅来自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也来自在生老病死的日常事务中与环境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细密联系,所有这些构成了人获得情感满足与和谐安全感的重要根源”。[5]然而,物质的极大丰富没有带来精神的富足,人们在一轮一轮以现代化名义进行发展中,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三、画如人生,人生如画
祖克慰动物散文《画中读鸟》部分,将名不见经传的鸟禽与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宋徽宗赵佶、唐寅、沈周等联系起来,可谓人生如画,画如人生。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拥有较高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他成立翰林書画院,画花鸟画自成“院体”,《写生珍禽图》是其中的典范。《写生珍禽图》之《乐意相关》和《原上和鸣》很值得关注。这两帧画都画了百灵鸟,画中的百灵鸟穿越几百年的岁月风尘,如今看来依然鲜活如初。这些散发着生活气息和艺术品位的生灵,能否为解读赵佶的情感世界密码提供一种可能?《乐意相关》画的是一只雌性凤头百灵鸟正准备喂食两只幼鸟,雌鸟漫溢着母爱的眼神,两只幼鸟接食时迫不及待的神态,令舐犊之情跃然纸上,让人动容。《原上和鸣》画中所画两只百灵鸟,在空旷辽远的原野中,一前一后走着,雄鸟在前,雌鸟在后,雄鸟的顾盼回顾,雌鸟的恬淡自然,流露出浓浓的爱意和深情。身为大宋皇帝的赵佶沉湎于歌舞酒色,拥有后宫嫔妃一万余人,恐怕很难对后宫的佳丽们生出纯真的感情;据说宋高宗赵构有“仇父恋母”情结,其诱因源自父皇赵佶在他母亲韦皇后生日那天,突然出现而后又决然离开,这成立时年六岁的赵构永远挥之不去的痛;真爱和亲情的缺失,可能是“自古君王多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的真实写照,而赵佶画作《乐意相关》《原上和鸣》中所显示的母子之爱,夫妻之情,或许就是赵佶以独特的艺术世界传递自己对普通天伦之乐的神往和钦慕。
八大山人,名朱耷,字雪个,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他本是皇家世孙,明亡后流落民间,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和怀念。他早期作品《松鹤图》,画面里一棵古松树,一块怪石,一只松鹤。尤其是白眼看天松鹤,显得特立独行,俨然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安静祥和,像一名桀骜不驯的斗士。同样关于松鹤的另一幅画作《松鹤图》,是其晚年的作品,画里的松鹤是长寿鹤,没有了白眼看天的眼神和势不两立的站姿,反而充满着自然和谐、宁静淡然。同样是其晚年作品《双鹰图》,画的是两只相互凝视的鹰,一只鹰站立在巨石上,俯视下方;另一只鹰栖息在枯树苍干上,仰视上方。与冷血、凶残、孤傲的苍鹰形象不同,画面中的两只苍鹰像极了喁喁私语的情侣,是有温度的。从白眼的松鹤到长寿的仙鹤再到温情的双鹰,八大山人由斗士变成了隐士,标志着进入垂暮之年的他,在历经佛门和道门之后,逐渐看破红尘,逐渐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与社会和解。
清代著名画家胡湄,善画花鸟虫鱼,其画作《鹦鹉戏蝶图》中,繁盛的花枝与散落在地上的落叶,蹁跹飞舞的蝴蝶和被铁链禁锢的鹦鹉,充满着强烈的对比。由蹁跹的蝴蝶和禁锢的鹦鹉突然想到了微尘众生。想起了《牡丹亭》里杜丽娘的感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那是青春易逝的无奈。想到了《红楼梦》里林黛玉潇湘馆廊下架子上养的那只鹦鹉,那是一只会说话,会模仿林黛玉“长吁短叹”,会念出黛玉《葬花吟》诗句鹦鹉,“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的忧思,鹦鹉是懂的。也是在《红楼梦》里,贾蔷为了讨龄官欢心,借了一两八钱银子买了名为玉顶儿,会衔旗串戏的小鸟,反遭龄官的一顿斥责:“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干这个浪事!你分明弄了来打趣形容我们……”贾蔷听后,赌神起势说自己没想到这上头,随即将雀儿放了生。
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鸟儿被关进笼子里,供人把玩。有学舌的鹦鹉,鸣声婉转悠扬的百灵、云雀,羽毛艳丽炫目的黄鹂,还有八哥、绣眼、靛颏、画眉、金丝雀……突然想起了欧阳修的“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想必关进笼子里的鸟,无论笼子如何富丽堂皇,其叫声都比不上悠游林中时的自在啼唱。因为,禁锢的生命是不完美的,只有自由的生命才是美丽的。
也是在这部分《画中读鸟》,祖克慰在关于画作缘起方面,唐寅的《枯槎鸲鹆图》和沈周的《鸠声唤雨图》有着非常相似的描述:“唐寅是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走进了山野,也可能就是这天,唐寅住在山里的朋友家。当他在细雨中漫步时,听到几声鸟鸣。在空旷的山野里,鸟鸣声是那么的动听。唐寅抬起头,看到干枯的树枝上,有一只八哥正在鸣叫,此情此景,多么的动人啊!具有独特观察力和敏锐力的画家,在一瞬间捕捉到这一场景。于是,就有了这幅《枯槎鸲鹆图》。”“也许,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寒冬,沈周外出访友,走在原野,突然听到几声咕咕的鸟鸣,沈周抬起头,看到一颗枯树的枝头上,蹲着一只肥胖的斑鸠,仰头鸣叫。面对阴暗的天空,鸣叫的斑鸠,是多么美妙的鸠声唤雨图啊!于是,沈周突发灵感,画下了这幅《鸠声唤雨图》。”是穿越还是巧合?值得思考。
注释:
[1][3] [4]鲁枢元:《生态批判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68,235页。
[2] 张华著,高旭东主编.《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 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2-213页。
[5]舒可文《城里,关于城市梦想的叙述·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