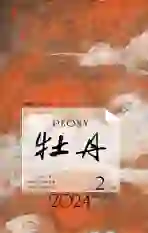我长大了
2024-03-26陈麒汇
陈麒汇
长大真无聊。旁边那穿着双破人字拖的乡巴佬瞟了下我,又扭过头紧盯着电脑屏幕。好久没人跟我眼神对视敢超过三秒了。以这样的方式开篇叙述,不免有些震撼。这样想,嘴上叼着的烟被我噗哧一笑,烟灰像雪一样地绽放;挠挠半个月没洗的头,头皮屑也随之散落,像雪一样。散落在我18岁大寿刚过,那刚长齐毛隆起的某些部位周围。
寿宴在烧烤摊落幕,一帮猪朋狗友相伴。
网吧通宵,游戏打麻时,我喜欢看点片子。看得心乱如虫时,我就尝试着写点小说。“煮剑喝酒”的《道上靓仔》是我所膜拜的。多想我就是他。多希望他就是我。
可是,怎么开始写呢?我写的不是我,但我一写起来,就会写成是我。所以……好吧,那你就当作是我。
就是我。
万般如常的一天,屋顶的太阳能,阳台上的镀铬懒懒地哈出热气。电视机微笑着讲一场发生在北海道盛夏的肥皂剧。窗外花香馥郁,一只蝴蝶选择栖息在这。屋内的乃喜成绩总是不上不下。
小升初入学考,刻板的试卷都被写哭了。却落了榜。
事已至此了,向来严厉的母亲也不再絮叨,一贯严厉的批评转成了温和的鼓励。
母亲对他说没事嘛,下星期报考“大同”再好好考。
客厅地图上标注着陆地跟海的比例是3:7,肥皂剧里的男人对女人说只有我和你。无量个元素在缤纷的世界中与之对立。每颗细雨里,说不定就饱含着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世界。乃喜想。
偶数和奇数,质数跟合数。考试时,乃喜和笔,轻松地就想起了它们的性质。
笔也知道,这是归功于——乃喜父亲六年来的辅导。乃喜上课总是不太听讲,往往是,前几分钟听得认真,感觉自己都会了,便安稳地沉入白日梦中——蓝天碧影,一望无际,拥有和《罪恶都市》里汤米一样的豪宅,早上9点才上课,下午4点便放学。梦境的世界,虚幻的秘密,藏在笔悄悄勾勒的本子里,乃喜的眼眸里。
鸡兔同笼,亏盈问题。无需多想,惯性答题。就算碰到变相题,乃喜和笔,平时练得太多了,稍作思考,也难不倒他们。
窗外一棵树上的琥珀,又对年轻的蝉讲起了琐碎且无聊的事——你话太多,命不长,断了的笔讲给我的,我且都讲给你听——多多过往而不复的周日午后,它们陪着乃喜在书房做习题,他父亲接过本子后看得直跺脚。每年都有蝉诉说不到夏天的尽头就在透明盒子里枯萎,每年都有笔未写尽最后一滴墨汁就被折断。
AABB,ABAC,根据意思,写出相应的成语。那不就——仔仔细细,干干净净,惟妙惟肖,自言自语。乃喜和笔写得行云流水不带犹豫。
以前,纵使母亲卧病在床,也不忘让乃喜默写成语。狡猾奸顽的足球和这个爱做白日梦的乃喜没能掩饰作弊的痕迹。脏兮兮的足球,身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慌慌张张”“匆匆忙忙”……母亲从床上一跃而起……诚实刻苦的孩子在窗外玩得尽兴,乃喜的白日梦换来了忧愁的千字手抄。
琥珀和蝉诉说的夏天在窗外继续。
肥皂剧里的男人骗了女人。
乃喜又想明明答得如此顺畅,题也毫无难度,怎么就落了榜?老师总是说考试时,做得快的,至少也要反复检查三遍,慢点的至少一遍;自己向来不检查,想这定是原因其一,但实在找不出其二。
只有笔知道。
漫漫白日梦,总是和乃喜上课时欺负那张老实的桌子,总是给它布满沧桑的脸哒哒地刻上不规则的星星。与那个,总是,揭发他们罪行的同桌就要分离。很多谋划好报复她的计划还未曾实施呢!想着想着,乃喜目光的焦距,和笔尖一起定格在了作文那。白日梦又在窗外,冉冉升起。
最后10分钟交卷提示铃“叮铃叮铃”,钢笔早在白日梦的辉煌中干涸,抢救过来时,半命题作文“同桌的XX”下是乃喜急忙胡写一通像是排列组合成的乱句。
那么,过去就过去了,考砸也没什么。
窗外斑斓缄默的蝴蝶,沉睡在了几天以前。
绯红的光从这延伸至柏油路的尽头,尽头是落日,有两颗流星从里那划过。乃喜父亲蹬了一脚摩托车启动杆,乃喜坐在他身后。燕子成群成群地飞过,乃喜想到语文课上老师讲的——燕子低飞要下雨。它们的軌迹有点像飞镖,旋入高空。父亲带他驶过的路上依旧万里无云。
明日即是大同中学入学考,乃喜想和父亲出门兜兜风。
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因为乃喜觉得明天开始——我便是大人了!
大人是不需要父亲带着的,大人再也不需要父母辅导功课了。单车昨天就看好了,银色的车身在玻璃对面召唤着这个即将成为大人的我。
我知道,也明白。
去大同中学的那段路上,会经过香蕉巷。
香蕉巷里有许多缅甸人经营的翡翠店,福建人开的游戏厅;很多家广西人开的卡拉OK,以及,香烟弥漫的刨冰店。发黄的老墙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自古人生谁无死,攀到顶峰是英雄”,“张晓源,我永远爱你”,“悲哉千世仇,快哉杀无赦,谁能奈我何”……
我经常,会看到,许多染着黄头发的少年在路边打桌球。那些少年,总是,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成群地围在一起。总是,警察赶到的时候,已经有人受伤,或是,死亡。大人是不能怕的。我摸摸兜里揣着的刀,提醒自己。
刀是前天买的。
前天和父亲去逛超市,我直勾勾地望着玻璃柜子里那把包罗万象的瑞士军刀。指南针、铰剪、开瓶器、木锯、小改锥、拔木塞钻、牙签、镊子。我想,即使有天,我像鲁滨逊那样置身孤岛,有了它,也便活得下去。
我一定要要!爸不得不买。
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世界地图,小时候母亲指着说世界是由七大洲,四大洋组成。又告诉我西班牙的冒险家,加勒比的海盗,他们之间流传着世界上有七大洋有三片海域,只有智勇双全的人才可踏足。我让母亲指出它们的位置,她摇摇头说不知走,进厨房。我猜,也许鲁滨逊所在的孤岛,就沉睡在那三片海域的某个地方。
不要在河边玩耍。青草的芬芳下掩盖的是柔软易滑的淤泥。不要去游戏厅,那些一味沉溺于此的孩子长大了往往没有出息。过马路一定要左右看啊,红灯是停,绿灯是行,不要去那些偏僻的地方啊。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的话啊。儿子啊,你是我们心头上长的肉,掉了一块,你猜会怎样呢?不要因往事而懊悔,明天又是新的开始。乃喜啊,千万要注意啊。乃喜喔,你要争气点哟。乃喜,不要为往事而去悲伤,至少今天不要。
——母親总是这样对我说。
然而这样的母亲,也不会再有了。
子时叶露,透彻清凉,犹若斑斓,顺光顺地。睡梦中爸唤起我。唤起我来到客厅。客厅黯然,只有走廊上的灯幽幽地洒在沙发的那端,那端与黯然相偕的母亲侧脸。
母亲拉我贴近怀里。我闻着她身上恍似柚子的味,熟悉的味。感受着我肩膀和脖子上她温热的眼泪,陌生的眼泪。感受着,感受着。如丝绢般包裹的安稳,如抖落心头上的霜雪。脑子里不断闪过四岁时某个醒来的午后,很多个不可复返的晨昏。此时一切真实的感觉又或者是白日梦在我还未完全从睡梦中清醒的意识间纵横交错。我感到无比的舒服无比的幸福无比的简单。简单如窗前梨花点点,白如母亲身上的衬衫。
父亲对我说,以后你要要要,更加地懂事点。懂事意味着长大。感觉身体的某处突然弹了一下,全身都听得到嗡嗡的回响。
哭了,大概十秒。
我说知道了,我去睡觉了。
第二天,母亲离开了。我感觉那只是一场梦而已。我和父亲去了超市,买了刀。
又过了一天,母亲还是离开了。醒来时,我感觉那应该还是一场梦。我和父亲去看了单车。我烧了童年陪伴我的玩具。
再过一天,母亲的确离开了。我不想醒来。我在梦中度过了阳炎拷问的白昼。傍晚时,我想到明天便是大同中学的入学考。我想和父亲去兜兜风。
我说的是乃喜。
日落,湖光,狗尾巴草。
父亲骑摩托车带着乃喜行驶在一条郊外的小路上,四周回荡着虫鸣。也许有两只,一只在清醒中,一只在迷失里。
某个路口急刹了车,惯性将乃喜紧紧地吸在父亲厚厚的背上。父亲的前面有人大吼你他娘的找死吗?前面的父亲大吼你才是找死!父亲的背震动得跟摩托车一样,强劲有力。
黄河250发动机再次轰鸣,盖过了嘈杂声,风又吹起来咯。风吹着,感觉有点凉,但是很舒服。只有虫鸣和路边不停闪过的狗尾巴草呼呼地响,它们的声音穿透进这轰鸣包围的空间里。不知为何下起了细细的雨。乃喜感到脸上被滴到了几滴。滴到的几滴却不是雨,咸咸的,是父亲的眼泪。大人原来是会哭的。现实中没见过大人哭。乃喜想到——我也是大人了,明天我就是大人了。
于是我也哭了。
我哭得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哭和在学校打架打输了的哭不一样。打输了的哭是哭给老师看,哭给爹妈看的,是没种的哭。现在哭是因为我长大了,明天我就是大人了。大人哭是不给别人看的,就像此时背对着我的父亲。我看见前面山坡上的那个太阳就要没了。我看见后视镜里的母亲一只手紧紧捂着鼻子,常年的鼻窦炎让她被风吹得眼泪四溅,她拍了拍我的后背,叫我喊爸骑慢点。
但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我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叫他骑慢点,再骑慢点。摩托车开始减速,减速到停了下来。熄了火。此时太阳已经完全落下,但天色还微微明朗;我们平安抵达一个小镇上,路边一盏灯一闪一闪吱吱地响。父亲对我笑了笑说都到这里了啊,以前还在这,带着几个兵按了个携带两颗手榴弹的逃犯呢!你妈,她她,是知道的,那时候你还没生。
小镇背靠着一座青幽幽的大山,深渊巨口一般,像是饿了很久会吃人。当听到父亲甩下句买包烟在这等我时,我隐约感到不快和一丝不知所措。直到那吱吱的灯完全亮起,天空只剩星星那刻,四周的虫鸣和远处的犬叫声压迫而来,不知所措的感觉愈发突显。
夜长梦便多。做梦是人抵御黑暗带来的不安的幻觉。过去,现在,总是,用安徒生的视角将这世上的一切都误解。如果白日梦的幻觉蔓延开来之际,能被清醒的意志顷刻间瓦解,此刻会在这地方胡思乱想吗?灯吱吱,再吱吱。不远处两个看不清的人形,好像在商量着什么,好像盯上我了。暗影中,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
我长大了。明天而已。
摸摸包里揣着的瑞士军刀,却是一支笔。笔对我说我是支笔,不是刀。我说我知道!必要时,你也可以是一把刀。
灯吱吱,又吱吱,两个人形似乎又被它提醒,它提醒着他们这里停着辆黄河250,还有一个单薄的身影。于是他们来了。灯光形成的暗影之外,他们开始往里走,每走一步,乃喜的心就更加的紧缩了一点。笔此时才知道,它也可以是一把刀。
于是刀子说:这样的时候,就来不及自我介绍了!只要他们靠近,就朝着他们脖子那插进去,不要多一句废话,看准点。看准点!手要稳,清楚了吗?手要稳,清楚了吗?
清楚了吗?
上了个厕所,等久了吧?我知道,爸大喊的这话,不是给站在一旁傻愣着的我听的,是喊给那两人听的。其中一个,正坐在黄河250上用一大串钥匙一把把地试了几次锁呢。我爸对那人喊你你你,你干嘛?那人说这这,像我的车!
你你他娘的放屁!
爸吼完,冲上去。站着那人挨了记掏裆砍脖,捂着肚子倒地蜷缩一团。看爸正犹豫要从哪补几下时,坐着那人跳下摩托,手里亮出把银晃晃的刀。爸慌了,看了眼我,马上转头紧紧盯着那人。
快往里面跑,儿子!喊喊喊,喊人去!爸大喊。
我看见那人冲上前在爸肩膀还是脖子上砍了一刀。我哭了,我撕心裂肺地哭了,我一无是处地哭了。我边跑边哭,眼前尽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跑了几十米,却感觉过了很久,久得像个春夏秋冬。爸粗粗的喘息声还在后面清清楚楚地听得见。
我转过头,看见裤子上都是血的爸,没有躲开那人冷静蓄意发起的又一击。爸背上又中了一刀。我紧得快要咬碎的牙齿缝里发出吱吱的声音,脑子一片空白。
后来的事,我只大概地记得。
我麻木地摸出包里的笔,打开笔套冲了回去。爸看见我跑了回来,他不再闪躲,慌张地对着那男人张开双手扑了过去。我爸狠狠抱住那人死死不放,那人用力挣脱出拿刀那只手,像猫抓一样快地反复扎着爸的后背。我紧张又发疯的左右环顾,围着他们不停地绕。终于看准了,终于看准了,笔对着那人的屁股还是腰子那扎了进去。
后来好像是感觉眼睛一晃,不知道被撞到还是踢到,我们三人都栽倒在地上。脑袋碰到地面时,我恍惚看到路边躺着一辆轮子还在滚动的单车,恍惚看到旁边冲过来一个大人,看到他咬着牙死死地按着拿刀那人的脖子和手。
我还记得,当时的我好像还恍惚地想到,明天就是大同中学入学考,还有我长大了。
按了屏幕,揉揉眼。
乡巴佬好像又瞟了下我。
疲惫不堪,无心打趣。天色微明,香烟抽尽。
冷清的早晨,明媚的一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再过七个月,就是高考了,谁也不知道谁的将来会是如何。
两个骑着踏板车的小青年,一把扯走一个扮似上班族女人的挎包,从我身旁疾驰驶过。女人不知所措却还摆出一脸镇定的样子,象征性地追了几步。路边空空的易拉罐被风吹着哐哐地滚,一只流浪猫看到路过的我,装模作样的害怕跑了。夜市的油烟味还未散尽,那些“黄天在上,厚土为证,山河为盟,四海为约”的辛辣话语,似又在耳边回荡。
东边升起的火球,裤包里的手指虎,手上把玩的zippo,还有,手机里下好的《道上靓仔》第三部。这一切,我开始感到厌倦。
现在的我就很疲惫。我就想回家,好好睡一觉。18岁的第一天,往后会有什么波澜壮阔的事情发生吗?至少,我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了。然而,乃喜,不要为往事而去懊悔,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不要为往事而去悲伤,至少今天不要。
好吧,原来如此。
我转身,往回跑。
你别以为我是要去追那两个抢包的杂种!我只是饿了,想想想,想去吃点东西。
责任编辑 李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