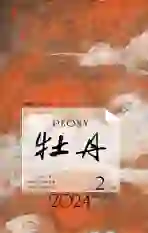江湖艺人
2024-03-26虞燕
虞燕
一
人们被敲锣声引来,闲闲散散地占领了晒谷场一角,自动围成个圈儿。圈子中央,腰扎红绸的男人边作揖边扯着嗓子说话,听的人半懂不懂,回应者寥寥,他干脆又拎起了锣,敲得“嘡嘡嘡”,示意越围越拢的人群朝后靠。场地够不够大,似乎得两个女孩连续翻跟斗来丈量,随着密集的锣鼓声,瘦小的身影弹跳、腾空、翻转,如鱼儿在海里游跃,跟斗从这头翻到那头,从左边翻到右边,横的竖的斜的通通来一遍,赢得阵阵喝彩声。场子就这么热了。
天气倒不热,入秋有些时日了。天阴着,像一张不大开心的脸高高挂着,我自然是开心的,哪个小人不爱瞧热闹呢?母亲抱着我挤到了最前面,跟旁边的婶子攀谈起来,说这些搞杂耍的外地人真会选时间,三点左右,午休的醒了,做晚饭还早,怪不得可以哄那么多人过来。我扭了扭身子,以示抗议,可不喜欢在认真观看时受干扰了。
场上的人拥有十八般武艺,且能说会道。节目一个接一个,打着赤膊的男子舞动长矛,扭腰斜挑,飞身劈刺,舞得空气“剌剌”作响,矛上的红缨如蹿动的火苗,红影缭乱。突地,又一人跳上去,两人对打,闪展腾挪,时缓时急,人群中不断有人叫好。他们很会见缝插针,适时插段话,诸如“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之类,声音高亢,盘旋于晒谷场的上空。
翻跟斗热场的两个女孩再次出场,一大一小,大的已是婷婷少女,小的看上去最多比我长两三岁,她俩的身体里似装了弹簧,上肢后仰,头朝下,手掌撑地,整个身体呈拱桥状,而后,或迅速弹起,或囫囵翻身,凌空一跃时,衣袂飞扬,我脑海里突然浮现电视里女侠的模样。那个剧是在邻居家看的,叫《偏向虎山行》,心想,她们以后肯定要去演女侠的。
有人搬上了狭长的木头长凳,长凳下摆了两个杯子,各插一支塑料花。两个女孩儿站于长凳两端,瞅准位置,齐齐下腰,脑袋靠近杯子,脸一偏,塑料花便叼在了嘴里,待直起身,站稳了,伸展双臂,从凳子跳下,红色的花依然绽放于唇上,两张小脸泛起轻松的笑意。
长凳上又加了长凳,像一条凳子背着另一条凳子,上面凳子的腿险险立在其下凳子狭窄的面上,没有丁点儿富余的位置,凳子腿稍一挪动,可能就会翻下来。大女孩从地上拾起插了花的杯子,摆放在第一条凳子的中段,她往后退了两步,盯了数秒,又上前把杯子往边上移动了下,这才试着爬上凳子,方才舞长矛的男子扶了她一把,转眼,她已把两条凳子踩于脚下。这回,小女孩没上去,在不远处看着。
我稍稍仰头,着粉色衬衫宽松裤子的大女孩在上面踢腿、倒立,神情淡定,动作平稳,她张开双臂时,还以为是落地前的预备动作,不曾想,她微微曲腿,身体开始缓缓向后仰,弯到一定程度,两手撑在了凳子上。她的腰软如海绵,身体带着脖颈和头继续向下,四周发出的赞叹声是轻的弱的,像几粒细沙丢进河里,几乎见不到涟漪荡起,大家生怕惊扰到她。
意外发生时我有点儿懵,随着人们“啊呀”一声惊叫,恍惚看见有两三只乌鸦惊惶飞过。大女孩掉了下来,砸在晒谷场的水泥地上,上面那条长凳子亦随之倒下,歪在一旁。小女孩箭一般窜过去,比他们中的两个男人都快,小脸紧绷着,蹲下拽住大女孩的衣袖。大女孩垂着头,捂着痛处,颤抖着试图站立,腰扎红绸的男人搀起她,轻声说着什么,表情严肃,甚至像在责备,女孩用手背擦了下眼泪,点点头,歪斜着身子走了几步。倒地的椅子被重新搬了上去,女孩顾不得掸掉裤子上的灰,再次攀爬。人群骚动起来,几个声音石子般掷向场上,“还上去啊,吃得消吗”“让她休息下”“看着就挺疼,换个节目呗”……腰扎红绸的男人做出个手势,意思是大家保持安静,那些声音才不大情愿地隐下去。
女孩好像并未受周围影响,在凳子上从容重复着之前的踢腿、倒立等,当她又做下腰叼花的高难动作,四周变得格外静寂,我紧张得攥紧了拳头。女孩肚皮顶起,把自个儿弯成了个半圆,再如拉皮筋似的拉长肩颈,往下探,从我这个方向看去,像倒挂在那儿。她终于咬住了置于第一条凳子上的花,我轻舒了口气,但还没彻底放下心,待其将“半圆”还原成“直条”,安全落地,大家的掌声方大胆放肆地响起。
随后,有人猛敲一阵锣,嚷着“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同时,数人上场,各自出拳扫腿,跃跳打转,下腰叼花的大女孩把锣翻过来,圆盘似的,捧着走向观众,硬币掉落于铜锣的“叮当”声不断,她不时鞠躬致谢。终于轮到我们这边了,两枚硬币已被我的手心捂热,我极其慎重地将它们放进“圆盘”,她垂着眼,紧抿嘴唇,眼周有些发红,一边脸略肿,隐约有乌青,可能觉察到了我的注视,她抬起眼,又快速垂下。女孩穿过场子把铜锣上交时,我发现她走路不大自然,一条腿的膝盖总是曲着。母亲在旁说,唉,这么摔下来哪能不受伤的。
散场了,我死活不肯离开,母亲没辙,陪着我看他们收摊,两个女孩跑前跑后,搬道具,绑凳子,把零碎物件装进大箱子,相當利落。大概已习惯了被围观,她俩做这些时目不斜视,好似这个世界除了他们这群人,其他人都不存在一样。
接下来的几天,我老缠着母亲问:表演杂耍的人从哪来?晚上住哪里?那些人中有女孩的爸爸妈妈吗?女孩不用上学吗?他们会给受伤的女孩医治吗?……多半,母亲也不知道答案。有时候,我跟弟弟不听话,母亲就说应该把我们送去杂耍团受受苦。
多年以来,我总会莫名想到那个女孩,一想及女孩,关于她的那些画面就会自动串起来,拉洋片似的在脑子里过一遍——她从高处跌落,她用手背擦去眼泪,她曲起膝盖走路,她发红的眼周脸上的乌青……
其实,那些年,有不少类似的杂技团到过我们岛上,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二
渐近的梆子声打破了午后的沉寂,“梆——梆——梆”,期间混杂着拖了长音的吆喝声,这个吆喝声听起来陌生,不像卖豆腐,也不像卖香油,透着某种不可捉摸的气息。母亲有些坐不住了,扶着门框往外张望,说好了似的,隔壁家的婶子婆婆们也复制了此举,吆喝者多敏锐,想来有戏,便大摇大摆地从大路拐进了小道,直至进入我家的院门。
那个中年男人头顶蒲凉帽,裹着一团热气,被母亲迎进了屋,他手里提的东西,罩了黑布,乍一看,宛如提了个黑灯笼,婶子婆婆们则像收到了无声的召唤,麻溜跟了过来。母亲收拾起吃饭的大方桌,麻利又细致,桌角有处疑似水迹,她用干抹布擦了两遍,最后,推动了下桌子,让其更靠近窗户,以便亮光充分抵达。我觉得略怪,一年到头,只有谢年祭祀前,母亲才会对那张桌子如此尽心照拂。
母亲后来提起过多遍,说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她那些天就想着给我算算八字,结果,人和鸟就送上门来了。
男人是江湖算命的,以鸟抽签算命。他脱了帽子,端坐于桌前,面朝大门,“黑灯笼”往桌上一放,揭了黑布,露出精致的鸟笼,笼中的小鸟应是见过大场面的,一点都不惊慌,眼睛滴溜溜转,而后,自顾自低头冥想,一副懒得理你的模样。我和弟弟乐坏了,什么算不算命的,鸟儿才最好玩啊,弟弟更是奔走相告,马上,我家桌子边围了好几层。
大伙儿七嘴八舌发问,男人并不急着回答,他把一长溜儿卡片似的东西排开,摆弄一番,他的手指略短粗,指甲秃得像被啃咬过,然毫不影响其灵活地拈取、穿插,在众人的围观中,颇显气定神闲。
围观者中,小人和大人的目的完全不同,小人们纯粹为鸟而来,看看它逗逗它足矣,大人们的心态就复杂了,比如母亲,她是铁了心要给我算一卦的,但又不愿先站出来,有的则主意未定,在观望中伺机而动,还有的光看个热闹,这样的场合,常常能光明正大探得别人的隐私,或所谓的命运。
男人说话慢条斯理,口音跟我们不大一样,但基本能听懂,他开口之前,微仰头,眯一下眼睛,仿佛在接收什么神秘的指令。众人大致清楚了,鸟主人按签上所写的钱数收费,一角到一元不等,什么命格付什么钱。这价格让大家觉得,算命的实在到几近仁慈,一下便平添了几分信任,参与的积极性也高了,跃跃欲试的心思毕露。
胖胖的珍姨最先按捺不住,摇着蒲扇挤上前,报了生辰八字。男人把桌上的“卡片”当作了扑克,洗一遍后,依次排开,然后,打开了鸟笼,他轻轻唤了声什么,小鸟在笼子口忸怩,直到喂了它一粒谷子般大的食物(看着像面粉搓的),方扑棱着翅膀飞出来。我们几个小人担心死了,也没在小鸟腿上绑个绳,要是飞走了怎么办?当然,多虑了,人家很乖的,出来就落在了卡片上,跳来蹦去,果真叼出了张“卡片”,男人轻抚了下它小脑袋,再喂食一次,作为奖励,鸟儿脚步悠闲,一忽儿回到了笼子。
才发现“卡片”其实是信封状,男人郑重地从信封里抽出张纸,众人伸长了脖子,恨不能把眼睛贴到签上去,珍姨更是丢蒲扇在一边,凑过去时胖肚子还顶了把桌子,惊得笼中小鸟张开翅膀扑腾了两下。签上有图,画了一个人坐在大树下,大伙齐刷刷看向鸟的主人,等着他讲解纸签。纸签被男人粗短的手指捏起,他微微仰头,眯了眯眼睛,说背靠大树,就是有人庇佑,一生平顺不愁,图后还写了钱,一元,属最贵的命格。珍姨顿时容光焕发,极其爽快开心地付好了一块钱。
“开门红”多多少少令人激动,好些观望者争相变成实践者,鸟儿有得忙了。鸟儿不一定每次出笼就抽签,偶尔在边上徘徊不前,偶尔出笼进笼数次仍不干活,男人不急不恼,轻言细语,手指摸头,外加食物诱惑,总有办法让鸟儿继续完成自个的本职工作。每回,男人都会把签洗一遍,再排好,抽出的签均有图,图后也都写了钱数,有的六角七角,有的三角四角,婶婶给堂弟也抽了一签,画的好像是一人走在宽阔大路上,命格八角,有前程远大的意思。婶婶满意地摸出了八毛钱。
我们当然希望男人讲解得越详细越好,他却偏偏简练到吝啬,能一两句讲清的,绝不说第三句,往往从他做完仰头到眯眼的动作,解签也就结束了,且脸上如被人涂了胶水,表情几乎无变化,颇有一种天机不可泄露过多的意味。
母亲终于指了指坐于桌边的我,男人点点了头,他或许也一直在等,想着坚定把他迎进门的主人家还真沉得住气。母亲报八字时,面色凝重,好似她女儿一生的遭际真的即将揭晓一样。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粗短手指划过那叠纸签,开笼门,放鸟。这回鸟儿倒干脆,第一时间跳了出来,它把一排纸签当作了小桥,在上面走走停停,看看风景,低下脑袋时,以为要啄一张出来,却别过了头,继续前行,最终,在大约“桥”的三分之二处啄了一张,邀功似的跳到了主人面前。
男人打开了签,我觉得好玩,还有点儿激动,看向母亲,她早已站了起来,眉头微皱,紧张地盯着纸签。签上的图不大好辨认,黑乎乎一团,上面有只石臼样的东西,男人慢悠悠解说,一只石臼陷入了淤泥,比较麻烦,愁云袭上母亲的脸,未等发问,男人安慰似的加了一句,大意为,未必是定局,出来了就好了。
母亲为那一卦叹气无数次,那么重一个石臼陷进烂泥里,弄出来谈何容易?我的签上只写了一角钱,全场最少,对应上我的病,她认为这鸟算命算得挺准,一个患有后天之疾的孩子,未来很难不困顿。
尽管此后,好些人说起灵鸟算命纯属骗人的把戏,说鸟都是训练过的,指定的签上偷撒了鸟食,或抹了鸟熟悉的气味,而鳥的主人最擅察言观色,看人下菜,我的知识和眼界也告诉我,这不可信,然,那一卦终因母亲的反复提及和她的叹气,强势入驻于我的记忆系统,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我已然确定自己的人生并不糟糕,那只深陷淤泥的石臼却还会时不时闪现。
三
那时的夜晚,只要出现个灯火通明的地儿,那必是惹眼的,充满诱惑的,人们潮水般涌过去,将那一处围起来,暖黄色的亮光从人与人的缝隙间漏出来,远远望去,恍若一个大灯笼被遮挡了部分,呈现出一种影影绰绰的氛围。自外婆家回来的路上,我们就遇见了这么个“大灯笼”,那里的嘈杂声忽高忽低,一波又一波地飘过来,我和弟弟用手指往那个方向一点,态度坚决,父亲母亲明白,这回绕不过了,不然两个小人到家铁定哭闹不已,整晚都不用睡了。
父亲和母亲一人抱起一个,母亲还用胳膊将小小的我往上顶了顶,我的视线才得以穿越人群,落在打把式班子搭起的场子上。他们位置选得妙,刚好在大路凹进去的部分,那里相当宽阔,观众多了也不至于影响交通。电线不知怎么架起来的,大瓦的灯悬起,旁边的树上也挂了灯,照得场上的人不大真实,像在梦里,在电影里,在一切够不着的地方。
旁边有人嚷嚷:“这些人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语气颇兴奋。话音未落,一年轻人鲤鱼打挺出场,手一扬,有人抛给他一个金属圈,并解说一番,意为这可是祖传的缩骨功,大伙儿要睁大眼睛好好看。钢圈已套进了年轻人的右腿,往上拎,至大腿处时,他猛地蹲下,弯下身,脑袋竟意欲钻进钢圈跟大腿争空间。顷刻,原本还算平静的周遭鼓噪起来,人们的声音里带着质疑、惊讶和不可思议,毕竟,那钢圈看上去比银项圈大不了多少,年轻人置若罔闻,他正专心致志地对付那个圈。
秋夜寒凉,我们都穿了较厚的外套,而他光着上身,额头好似还冒了细汗,在灯光下晶莹着。随着众人的惊呼声,他的脑袋进入了钢圈里,与右腿紧紧相依,整个人看着甚是别扭,身体的几个部分像被强行焊在一起,圈子勒着脖子,让人觉得会随时窒息。他张着嘴巴,脸涨得通红,裸露的肌肤也发红,我差点要喊出“救命”了,他应该很难受吧?这要是摘不出来了怎么办?他抬不了头,不过可以伸出手,向观众招了招。那只手收回后便艰难地塞进了圈里,然后,塞另一只手。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禁锢在一个圈里,看似卡在那里,只有前臂能小幅度摆动,然其肩部和后背一块块凸起的肌肉,手臂手背暴起的青筋,被抽了鞭子般越来越红的皮肤,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他正调动全身之力攻克钢圈。大家唯有呆呆看着,大气都不敢出,场上场下一起静默,这样的场面实在难得一见。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钢圈一厘米一厘米地挪过肌肤,已挪进一个肩膀,又一个肩膀,他曲着腿蹦跳一下,两下,左右肩膀扭来扭去,身上如抹了润滑油,圈儿顺服地慢慢下滑,至腋下时,他站起,身体前倾,与地面呈平行状,而后,双手抓住钢圈,推向臀部,稍微一使劲,钢圈痛快地掉落,就那么从左腿出来了。他举起钢圈,沿着场边跑了一圈,现场掌声如雷。
虽为亲眼所见,个别人还是心中存疑,会不会钢圈装有机关,趁人不注意半途偷偷放大了?仿佛料到有这种心思,年轻人站于场子中央,头随目光转了大半圈,最后,停留在我弟弟身上,他微微一笑,径直上前。弟弟被父亲抱着,正看得高兴,没想到场上的主角已在跟前,惊得“啊”出了声。年轻人比父亲高出大半个头,他用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跟父亲交流,借了弟弟的灯芯绒外套,众人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一个健壮的成年男子要穿下六七岁小孩的衣服,这谈何容易!
年轻人对各种声音报以镇定的笑容,他两手拈起外套的领子,抖了一下,抬起右臂,伸进窄小的衣袖,卡在了肘部,他似乎甩动了下手臂,很快,便能往上拉了,两个肩膀则像两只颠簸于浪尖的小船,晃动数下,衣服奇迹般穿在了他身上,只不过长袖成了半袖,外套变为超短的袄子。穿上弟弟灯芯绒外套的年轻人耍宝似的走过来走过去,还不时旋个身,灯光映照下,他闪闪发亮。全场沸腾了,这下,所有人都被折服,还有小伙子追着喊,要拜他为师。
外套还了回来,父亲不由得里外翻看,旁边的人纷纷凑过来,极认真地细查了一番,没撑破,没脱线,完好无损,遂感叹刚才的一幕简直像做了个梦。
彼时,会缩骨功的年轻人已穿上了薄衫,向观众一抱拳,瞬间转换了身份,开始报接下来的节目,他声音激昂,手势夸张,节目未上,气氛先渲染了起来。一壮汉上来就往地上一躺,另兩人抬了一块石板压在他身上,又招呼观众下去验证石板的真假,还真有几人兴冲冲而去,忙不迭反馈:“是真的,真的石板。”接下来,年轻人抡起大锤,果断砸在石板上,可能好些人还沉浸于他的缩骨功中,突然这么一砸,有点出乎意料。石板无恙,石板下的壮汉怎么样了?我的心悬了起来。不等人多想,又一锤下去,石板应声碎裂,壮汉抖落身上的碎块,一跃而起,在场子上来回蹦跶,表示自己一点事儿没有。
正当大伙情绪高涨,一个沉甸甸的大麻袋出现得猝不及防,会缩骨功的年轻人用上了喇叭,音量大且闹哄哄的,他从麻袋里掏出两包玩意儿,用姜黄色马粪纸裹着,说是草药,泡酒喝,可治疗跌打损伤,平时用,则强筋健骨。年轻人继续卖力吆喝,随后,胸口碎石的壮汉和班子里的另几人也一起助阵,大致意思是,他们自己亲身试验,绝对有效,年轻人更是拿出个透明的壶,内泡草药样的东西,给每人倒上半碗,场上诸位均大口喝下,以证明刚才所言不虚。
年轻人张口就来顺口溜:“有钱买药治伤强身,是你的福气;没钱买药赚个眼福,为我传名气。”一时之间,场下的观众化作了蜜蜂,“嗡嗡嗡”声不绝。“他们是真功夫,药应该不假”,多数人持这个看法,包括父亲。父亲以前也在江湖卖艺的那里买过药,薄薄的黄纸折成一小包,打开,一撮细沙般的棕红色颗粒,像红糖,泡水一喝,就是红糖。
但父亲深信这回定然不同,他们一身真功夫骗不了人,尤其缩骨功,而且,再怎么着,草药总是有益的,有病治病,没病强身。
父亲捧回了好几包,泡了酒,出海回来,总会倒上一杯。每次,看父亲喝那个药酒,我就想起神奇的缩骨功,我甚至隐隐期盼,父亲喝着喝着,也有了一身好功夫。
责任编辑 李知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