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父!夸父!
2023-04-13王鹏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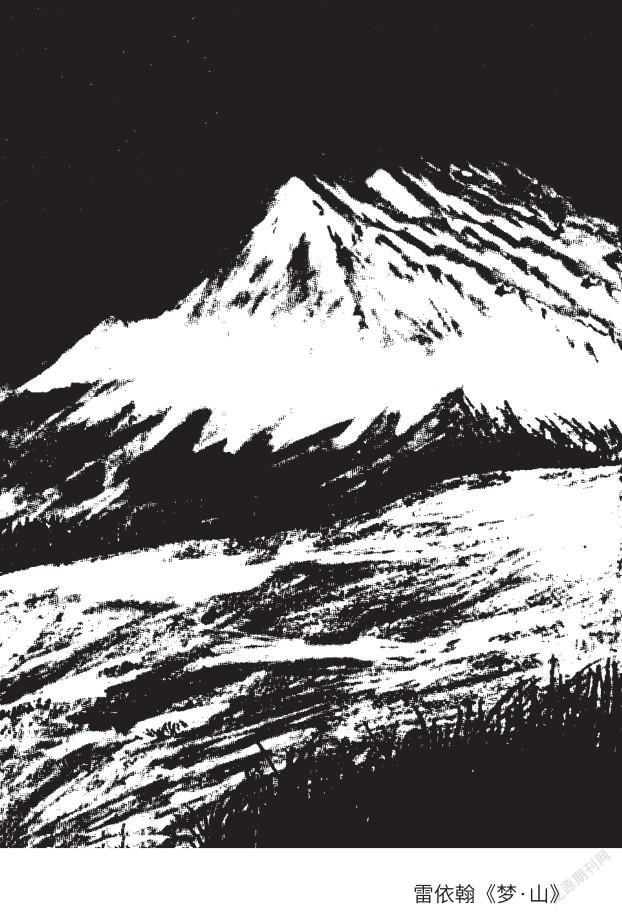
一
“我说,如果他醒不来,你准备去哪儿?”一条黄蛇边咬啮着旁边断臂上的腐肉边问它近旁的另一条黄蛇。两条黄蛇长得十分相像,长短粗细甚至两对眼睛几乎没什么差别。
“那还能怎么着,无非是回到深山老林,靠吃剩下的活呗!”另一条正蜷着身子休息,日头刚刚升起,远处林中传来清亮的鸟啼。
“但愿不是龙鸟那家伙。”撕咬着腐肉的黄蛇边说边缩起来,“我们在这儿已经整整七七四十九天了,每次看见那家伙飞过就得装死,否则……”
“否则就会没命。”另一条接道,“不过,我真的怀疑它是否能看得到我们。”
“罢了,罢了!”它又吞下一块肉,才慢条斯理地继续说,“这场大战实在可怕,你看这四周尸横遍野,我们能活下来实在是万幸。”
“也是拜这家伙所赐。他体躯庞大,当我们俩的庇护所,简直像大海之于两条游鱼!”
“不过同样拜他所赐,成群的尸骨已经要同土壤融为一体了,周围的腐肉也已所剩无几。若再无法挣脱开,我們真就和这些骨头葬在一块儿了。”说着,它扭过头望了望身后,一只巨大的手臂死死压住它们的尾部。
“恐怕是醒不来了。我们也即将和他一样,长眠不醒。”
一声闷哼打断了它们百无聊赖的对话,地面开始颤动,山上的石块骨碌碌滚下来,同无数尸体和骨头混在一起。一个高大的影子缓缓升起,把地上的尸体蒙上一层荫翳。
“他醒了,他醒了!”黄蛇们瑟瑟发抖。
巨人大喝一声,支撑着站起身,长吸一口气,又重重吐出来。一阵狂风刮过,在枝头栖息着的龙鸟嘶叫着飞入青天。
“睡了好久啊。”他兀自叹着,古铜色皮肤嵌着一块块黑色血污,上面的寸寸伤痕也似枝丫交错。四野满是附着凝固黑血的横尸与白骨,断肢残臂堆积成山,沿着山麓一直延伸,他一眼没望见尽头。
“夸父,你们失败了!”刚缓过劲儿的黄蛇们齐声说道,“你看这遍野的横尸碎骨,整整三天的大雨也没能洗净血污……”
夸父垂下头睁圆双目,两条黄蛇立刻合紧嘴巴,麻利地蹿上夸父的身躯,分别缠绕在他的左右臂上。
“大战已经结束七七四十九天了。夸父,你的躯干没之前那般巨大了!”左臂的黄蛇打趣道,但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现在的夸父仅有五六丈高,相比之前的确要相形见绌得多。
“没错,之前我们勉勉强强才能绕上一圈,现在足足绕了三圈!”右边的黄蛇附和着。
夸父兀自握紧拳,单膝跪地抓起一根硕大的骨头,猛地朝对面悬崖顶部掷去,崖顶凸出的石块轰然破碎,激起阵阵飞尘和腐尸的气味。
黄蛇见状立马闭口不言。太阳不断升高,夸父不动声色地立着,只是微闭着眼,不多时,他展开双手,两摊黑乌的血从掌心渗出,顺着深重的掌纹缓缓流动。他霍地大喝一声,将两手举过头顶。
“我要回成都载天!”
“夸父,恐怕你无法回成都载天了。”其中一条黄蛇冷笑道,“你朝西南望望,看能不能望见山顶!”
“别打趣了。”另一条蛇也劝道,“以现在他这般体躯,恐怕九九八十一年也无法抵达那里。即使到了山脚,他也无法登上去。可惜了,成都载天山,那曾是夸父族的净土圣地!”
沙土平息下来,阳光利箭般刺在大地上。夸父踏上堆积成山的残骸,仰起头凝望着云端金灿的光轮。
“我一步可跨河泽,五步可穷江海,十步可攀高山,百步可登青云之巅。吾乃夸父!”夸父把双臂置于腰间,“成都载天,我回定了!”
二
正午,热浪蒸腾,毒辣的太阳使万物陷入缄默。山巅的植株都缩成一团躲在荫翳处,兽们就慵懒地卧在阴凉下。成都载天山地势高耸入云,直逼天边,在这等热浪翻滚之时更是有如火焰炼狱,顶峰的云块竟慢慢化成了缕缕云絮。
成都载天山巅上,立着一个巨人。他身高约七丈,体躯如石块般坚硬,似一座密不透风的高墙,脸孔颇为俊美,年纪也很轻。耳朵上缠绕着两条黄蛇,不时朝天吐着信子。他仰头正视着头上方的太阳,大颗的汗水顺着头发和脸颊滴落,还未落到地上便被蒸发得无影无迹。地面像是生着火,灼烤得他脚底发出嘶嘶的声音,像雏鸟的啼鸣。但他似乎没觉察到灼烫,只是死死盯住头顶,两眼始终未闭合一下。持续片刻后,他开始慢慢挪动左脚,双目迸出金光。待到左脚落稳,他霍地跃起,巨硕的双臂直指苍穹制高点。
巨人名为夸子。黄帝蚩尤大战结束次日,成都载天山山脚下一棵巨树忽然化作人形,即为夸子。夸子有着夸父族那般庞大的躯体和无比的力量,耳上缠绕两条黄蛇。他每日跟随太阳的轨迹奔跑,休憩于禺谷,日出前来到旸谷。正午时,便登上成都载天山巅,竭尽力量跳跃,以求抓住太阳。
“这次我离太阳还有多远?”夸子落回原地,一面摇头一面问耳上的黄蛇。
“大概更近了些。不过要是再高一点的话,我恐怕就会被烤死。”左耳的黄蛇回答道。
“一点儿不错。而且你也会受不了那种温度,你会和我们一样化成飞灰。”另一条黄蛇附和道,“为何你总要和太阳过不去呢?”
夸子轻吐口气,就势倒在树荫下,惹得山体一阵摇晃。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为了寻找世界的终极。而终极的入口就藏匿于太阳的背面。”
“可终极究竟为何物?可否能让我得道成神?可否让山海皆为我平?可否让天地皆由我命?”
“这我不清楚。”夸子摇头道,“我只知晓,终极能让我穷尽这世间的一切。天地山海,万物生灵,皆由终极支配。若我能进入终极,我便能通晓世界的一切奥秘。”
黄蛇们来了精神,嘶嘶吐起信子。
“甚好,甚好!黄帝与蚩尤大战刚结束七天,虽蚩尤大军溃败,但黄帝也损失惨重。若你得到终极,定会使天下都臣服于你。到时,你便能称王天下了。”
“我心不在此。”夸子坐起身,目光投向天边,“通晓世间的一切于我而言足矣。”
蛇们发出一阵嗤嗤的冷笑,夸子双手扶膝,轻闭着眼,似在仔细谛听着什么。
“和那家伙简直太像了。是吧?”左边的黄蛇问它的同伴,还没等对方回应,它便继续说道,“不愧是夸父的儿子。可惜,夸父族曾经拥有称霸天地的机会,可夸父那家伙完全不听劝告!真是可惜,太可惜了……现在他已经成为大战的牺牲品了,甚是可怜!你知道吗——那家伙的躯体比你还要巨大,他元气盈满时,和你脚下的成都载天一齐高!你在他眼里不过是只小蝼蚁罢了……”

“我并不屬于什么夸父族。”夸子打断它,“更不知晓你们所提及的夸父。不过,若他真似你们所言这般强大,我倒想同他一会,说不准能助我一力。”
夸子右耳的黄蛇爬到地面,绕着他爬了几圈,随后盘成一团,挺直颈部眯着眼打量起夸子。
“夸子。”它说,“你自称为夸子,体躯庞大,力大无比,能轻而易举登上成都载天,居然称自己不是夸父一族!笑话!你为子,他为父,如何不是他的后代!”
夸子只意味深长地笑一声,并不回答。他将黄蛇从地上拾起,它也不再作声,温顺地沿着他的手臂归回原位。
“上路了。”夸子用力伸展四肢,“日落前赶到禺谷,这次一定不能再让它逃走!”
三
夸父面向黄水席地而坐,低头注视着两手上的血污。
“夸父,你现在真的没法变得像之前那般巨大了吗?”其中一条黄蛇问他。
夸父缄口未语。澜动不止的水面扭曲了他的映像。手心的血污黑得耀眼,他轻声叹口气,将双臂伸入黄水中,两条黄蛇赶紧爬上夸父肩头。
湍急的水冲掠过他巨大的手掌,河底的泥沙翻涌起来。浑浊的水流中,夸父看见几日前大战的场景——厮斗的态势,灼人的火光,血与死亡。倒下时的无力,云幕的罅隙里倾泻而出的光亮……
夸父皱了皱眉,徒然把手臂从水中拔出,古铜的皮肤经水浸后,颜色更加深重。他展开手掌,掌上的血污丝毫未褪去,似天生长在那里一样。
“这血怎么洗不净?”黄蛇伏在他肩头,惊讶得直吐信子。
夸父合上手掌,再次将手臂置入水中。黄水迅猛如豹,沙石汹涌成潮,有似万般利刃飞掠过他的巨手。他在水中将手伸展开,透过浑黄的水流,殷红时隐时现,一如流云满天的晴昼上空赤红的日头。
约过了半个时辰,夸父才将手从水中捞起,可血污仍未被冲洗下去,似两块烙印一样深深打在上面。他闷哼一声,面露愠色,黄蛇们也不敢言语,不安地缩紧身子。
接着,夸父将手臂上残留的碎石细沙抹掉,慢慢站起身来。不时有水漫上岸,舔舐着他宽大的脚趾。他仔细地观察着黄水,从脚下望到对岸。忽地,他伸展开四肢,庞大的躯干似山丘那般坚实。水中几近破碎的倒影凝视着自己,而他则像在凝望深不可测的旋涡……似有什么力量牵引着他,那坚若磐石的身躯蓦地向前倾去,整个身子都浸在了潺潺奔腾的黄水之中,但并未完全把他淹没。几近滔天的水幕拔地而起,无数片青叶簌簌落下。他霍然坐起身,拿手用力抹了一把脸。
“喂,好歹也告诉我们一下!”其中一条黄蛇吼着,“差点一口水呛没了气儿!”
夸父盘起腿,又倒下去,脸孔对着上方的青空,谛听着水汩汩流过耳边。太阳在贴近天边的位置悬着,依旧火红,依旧刺眼。
“想不到,黄水有一天也能载得下我夸父。”他喟叹一句。
天幕渐渐变成蓝黑色,黄水也平歇下来,默默地淌着。夸父卧在水中一动不动,头顶洒落的淡淡月光覆在他的皮肤上,泛出微微亮的光泽。水流洗净了全身的血污,他伸了伸手臂,有种久违的惬意拥裹住了他。
“只是,为何两手上的血迹仍是未能褪去……”
一股阴风霍地袭来,夸父察觉到了不祥,便猛然腾起身子。疾风吹落了大片的叶,黄水也被激起水花。
“好像是那家伙。”黄蛇说道。
一阵尖厉刺耳的笑声顺着风而至。风愈发急骤,渐凝聚成一团,显出人的状型。
“风伯,”夸父搔了搔耳后,“没想到你竟还活着。”
“没错,你应该在大战中死了。”黄蛇附和着。
风伯又笑了一阵,笑得比刚才更为尖锐,像是一根根针直刺进心头。黄蛇们似乎听出这笑声里的不和谐,眯起眼朝他吐信子。
“不,这只是我的一点精魄。”风伯回答,“我只是过来看看老朋友。”
“有什么事大可以直截了当一些。”夸父说,声音低哑。
风伯又笑起来。他在夸父身边绕了一周,才慢条斯理地开口:“你果然还是老样子啊。不过,千万别误会了。我只是带着残躯来向你道谢。”他嘴角微微扬着,“其实,你们夸父族完全可以同这场大战脱开干系。不过啊,这是在大战结束后才明晓的事。或者说,在败北后才浮出水面。可一切都太晚了。你败了,我们也败了。我体内的精魄只能终日随风而荡,而你,再无从前那番威武。”
“你究竟想说什么?”夸父闭上了眼。
“我只是想向你表示感谢。若没有夸父族的协助,我们……”风伯话锋一转,“不过,我挺想知道,夸父族同我兄弟蚩尤和那黄帝都无恩无怨,为何你要支援我们?”
夸父沉沉地叹口气,忽地抬起头,目光落在风伯脸上。
“我想阻止那场战争。”
风伯诧异万分,旋即仰天大笑。
“夸父,你该明白,这场战争是无论如何——不管早晚,也不管双方是谁,总归势必要发生的。没有谁能阻止得了。”风伯边摇头边说,“更何况,你们夸父族大可等待我们双方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真是可怜,竟为此葬送了全族,自己也落得如此田地。”
夸父从黄水中抽出手臂,猛地向前出拳。空气中生出风来,把风伯的样貌吹散。
“何必动怒呢?我所言只是事实罢了。你大概已经失去了神力,再无法与天并肩。”风伯悄悄在夸父背后显形,“你打算去何地?隐于海或是藏于林?”
夸父肩头的两条黄蛇发出嘶嘶的叫声,似利箭般窜了出去,风伯的身体似烟雾般四处散去,在另一处聚合,如此几回。风伯似乎十分享受这种乐趣。
“我要回成都载天。”
“回成都载天?”风伯轻笑一声,轻掸一下袖口,黄蛇们被风刮回夸父肩头。“你现在不过是失去了神力的凡子,怎么可能登得上成都载天!”
见夸父不言语,风伯继续说:“自夸父族离开成都载天,许多势力都试图占领那儿。无数神兽也企图将那块宝地变成自己的栖息地。”风伯顿了顿,“对了,我可听闻有一样貌似你的家伙,名曰夸子,没日没夜地追赶太阳,日中登上成都载天,日落前跑到禺谷,日出前再赶到旸谷。”
“疯子。”夸父轻描淡写地说。
“的确。不过——”风伯紧盯着夸父的眼睛,“该不是他盗走了你的神力吧?”
每日往返于旸谷和禺谷,在阳光最炽烈之时登上成都载天山巅,确非凡人所为。
“那又如何?”
“我只是提醒一下你,夸父。”风伯说,“不过,你为何要回成都载天?”
“杀了那家伙。”
“你是指——我刚才说的那‘疯子?有趣,有趣。”风伯拍了拍手,在空气中划个圈后又回到原地,“还有一事。在你沉睡的这些日子,又有一人与黄帝大动干戈。很可惜,他同样失败了。”
“此人是谁?”夸父抬了抬眼。
“去常羊山吧。”风伯的身体渐渐化作风,激得水浪四起,“若你需要我助,我可以让风载你前去。”
“不必了。”夸父迈出黄水,兀自瞟了眼掌心。血污仍在。
四
夜下的野林幽静得如同深冬上了冻的河。这是个晴夜,月色如水,薄云似纱。夸子坐在林中一片空地上,边啃野果边盘算在什么位置能够最快追上太阳。
“只要处于旸谷的制高点,我就能在太阳一露头的时候朝它扑过去!”夸子似在自言自语,“但我已登上那制高点,为何还是扑了个空?”
“夸子,若你真想捉住太阳,不妨换个方式。”其中一条黄蛇说。
“什么意思?你想到什么方法吗?”
“虽然你每日往返于旸谷和禺谷,还在正午登上顶峰,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那你的意思是,我离太阳还远得很?”
“不错。”它回答道,“所以,必须借助其他力量。比如说,寒冷之时,一团火便可使生命回暖;大旱之时,一场大雨便可润泽万物。”
“可我又能借助何等力量?”夸子叹道。
“我听闻沿黄水向东一直走,可看到一座野山。野山脚下有一片无名林,有一族栖息于此。首领名曰大羿,此人善射,威勇无比。若他肯助你将太阳射下,岂不美哉?”
夸子没再做声,咀嚼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了。见他举棋不定,黄蛇赶紧煽动道:“就算你真的擒得住太阳,也会被它给烤焦!到时候,便功亏一篑了。若大羿能将其射下,待其热量散发殆尽,你再去把它捉住也不迟。”
“太阳不过是一颗小小的火球罢了。”夸子伸出手,“它还没我一片指甲那般大!”
“太阳虽小,却足以使这世间皲裂破碎,使万物生灵饱受苦热,使大湖江海蒸发直至消亡。”黄蛇龇出牙,哑着嗓子说,“纵使你是夸父之子——不,纵使你是夸父,也未必是那太阳的对手。”
夸子仰头朝东方望去,那里现在是茫茫黑夜,上面点缀着几颗星。
“既如此,我们现在便去找到大羿,以求他协助!”
翌日,日出后两个时辰,夸子行至一片密林中,这里的树木生得分外繁茂,几近遮蔽了天日。林中极静,甚至听不到风吹草叶的声响。
“这里为何如此……”黄蛇轻声说道,但还未说完,一旁的树干上便插上一支箭。夸子警觉地转过身,身后瞬间飞来无数支利箭。夸子见状霍地跳起,两手抓住顶头的枝干,占据了高位,他也看清了对方的位置。袭击之人就藏在树旁的灌木之中。
“且慢。我是来见大羿的!”夸子朝袭击者所在位置喊道。
对方没有应,却又连射出几箭,夸子轻轻闪过。这箭生着风,虽未触到他的皮肤,但划破了空气,还是在他身上留下几道痕迹。
“先报上名来!”
“吾名夸子!”
“为何要见首领?”
“有一事相求!”
“何事?”
“我想请他助我射下太阳!”
没人再发问,取而代之的是大笑。笑声响彻整片树林。夸子看到灌木中站起来许多士兵模样的人,他们的弓箭握在手里或背在身上,手笑得发抖不止。
“喂,就算首领能够射下太阳,”其中一个士兵说,“可为何要助你这等疯人一臂之力?”
夸子并不理会他,转过身默默前行,嘴角微微扬起一道弧度。
“不能让这家伙闯进领地!喂,若你再向前踏出一步,马上让你万箭穿心!”
夸子停下脚,侧过头瞥了眼无数支架在弓上的利箭,眼里绽出一点笑,霍地朝前奔去,千万支箭紧随其后。夸子机敏灵活,但躯体实在过于庞大,左小腿被射中。夸子失去平衡,重重摔倒在地,而无数锋锐的箭尖已然抵在他的脊背上。
“都退下!”林子深处传来一声大吼。
士兵们果然收起弓箭,低下头单膝跪地。夸子抬起头,林深处有一黑影缓缓朝他走来。
“大羿在此。阁下找我何事?”
“大羿。”夸子麻利地拔去腿上的箭,掷到一边,“今日我来是……”
“先不必多說。”大羿打断他,“属下多有得罪,还望见谅。”
夸子这才看清大羿的样貌:皮肤黝黑,赤着上半身,身材精干,目光深邃,看不出里面的一丝波澜,颇有首领风采。
“请。”大羿做了个手势。
只走了半刻钟,便进入了大羿的营帐。两人席地对坐,都缄口未语。
“阁下,伤势不要紧吧?”大羿先打破了沉默,“先敷一点万灵药?”
“没什么大碍。”夸子摇头,“我还是开门见山。今日前来拜访,是有一事相求。”
“那我也开门见山。其实,我已经听见了你的请求。”大羿顿了顿,“但我想知道,为何阁下想射下太阳?”
“太阳的背后便是终极的入口。”夸子的眼里闪着光。
“哦?”大羿显出几分疑惑,“所谓‘终极为何物?”
“进入终极,便可知晓这世界的一切,生死之规律,万物之运转,所有皆在眼底。还望得到大羿首领的协助。”
大羿点了点头,却擦拭起一旁的金弓,夸子似乎很有兴趣地默默看着。待到他将金弓擦完,才给出答复。
“恕难助你。”大羿半低着头说。
“既如此,”夸子轻轻笑着,“叨扰大羿首领了。”说罢便起身告辞。
“请留步。”大羿追上去,“我未助你,是因我并没有你那般胆识。我的箭,还离太阳远得很。不过若是你的话,定然能抵达终极,得到至理。”
夸子两手抱拳:“多谢大羿首领!”言罢,他露出一抹笑容,转身大踏步向林中走去。
“首领,为何你要让那样的疯人进来?”夸子走后,大羿身边的侍卫问道。
“他不是疯人,是有信念之人。”大羿沉默良久,才回答说,“我有心助他,但实在无力。他所要做之事,只有他一人能完成。这就是为何我要拒绝他。”
侍卫又问:“首领,所谓‘终极,确有此物?”
大羿摇头道:“这我未有耳闻。”
“那恐怕还是这人在妄想。”侍卫笑道。
“未必。”大羿向着夸子离开的方向看去,“有些事物,当存在于内心的那刻,便已经真真切切地存在了。”
五
“夸父,當真要去常羊山?”
夸父不语,只默默披着月光行进。黄蛇们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也懒得同默不作声的夸父再说什么,便蜷在他的胳膊上睡去了。
路比想象中要难走,大概体力还未完全恢复。夸父不由喟叹,自己也曾踏山丘如平地,而今却连走在平地也如此吃力,真乃笑话!躯体也不似之前那般有力量,尽管看起来还是比常人要庞大许多倍,可已然失去了神力……
夸父十分清楚,一旦失去了神力,自己便同凡人无异。拖着一具凡躯,如何登得上成都载天?成都载天乃灵山,一石一尘,一草木一生灵,都带有灵气。凡人是无法登上那山的。
“即使如此,我也要走回去,再将它征服。”
他向成都载天的方向望去,满月似圆玉,树冠呈黑色,几近掩蔽住了大片天空。不见那山的一点儿轮廓。
行至正午,常羊山显了影儿。阳光毒辣刺眼,夸父暂且在荫翳处歇脚。他两眼深凹下去,鬓上竟也染了几丝白色。
“风伯说的那家伙是谁?”一歇下来,黄蛇们马上来了说话的劲头,“太阳实在毒热,赶在这个时候赶路简直要命。”
“没错。”它的同伴马上附和道,“而且我们离成都载天似乎越来越远了。”
夸父对这一唱一和不理睬,只闭眼歇息着。但它们却说个没完,似蚊蝇一般扰人,内容大多是关于前往成都载天有多么艰险之类的话。
“要我说,找一处没人的深山老林,过无名无姓的日子就惬意得很。”其中一条黄蛇故意慢条斯理地说。听闻此言,夸父猛地睁开眼,一把揪住那黄蛇的头,狠狠朝地上摔去。还未等另一条黄蛇叫出声来,它也被抓在手中。
“再乱叫,小心我把你们俩的脖子拧到一块儿!”
黄蛇们不再出声,温顺地绕在夸父的胳膊上。休息片刻后,夸父便准备登山。常羊山险峻无比,但夸父气力过人,纵使身为凡躯也未被拦住。待爬到半山腰的一片空地时,忽地一阵风从头顶袭来。夸父眯起眼,见一道黑影从上空落下。
夸父连连后退,黑影扑了个空,山体被冲击得晃了几晃。夸父稳住脚,透过滚滚烟尘,他似乎看到一个无头怪物缓缓朝他走来。
“风伯那家伙不会是让我们引火烧身吧?”黄蛇小声说,“这分明是个怪物!”
夸父警觉地攥紧拳头,摆出作战姿态。那怪物渐渐走近,模样也渐渐清晰了,果然是个无头怪物,手里操着一柄巨斧和一块盾牌。
“夸父首领,你竟还活着!”他先开了口,“我还以为是黄帝派来的刺客,这才鲁莽出手。刚才多有得罪!”
夸父见他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便略放松了一点警惕,可只凭身体,他记不起站在自己面前的究竟是何人。
“请问阁下姓甚名谁?”
“吾名刑天,曾是炎帝的手下。”他回答道,“在黄帝和蚩尤大战结束后,我独自杀到了黄帝的领地,同黄帝大战数回合,打到日月无光,天地昏暗!”
夸父觉出他在颤抖,尽管刑天无头,但仍能想象得到他在说这话时凛然的姿态。
“但我败了。”刑天继续说道,“黄帝砍下了我的头,并将这常羊山劈开,把我的头颅葬在里面。但我不甘就这样倒下,即使砍掉我头,也无法斩尽我意!”
这番话让夸父喉头发紧,似有什么梗在那儿,竟一时喘不过气。
“你……为何知晓我的姓名?”良久,夸父才开口。
“夸父族的首领——何人不知,何人不晓?”
“我已然成了这副模样,神力也失尽。族人也都死在了大战中。”夸父边说边摇头,“我已惧怕被人记得。”
“之前听闻夸父身高十丈,是因为大战的原因,你才……”
“从昏睡中醒来我就成了这副样子。”
“话说回来,大战结束后我听闻蚩尤一方都被斩绝,也包括夸父族。可为何——”
夸父轻叹口气:“大战结束四十九天后,我才醒来。”
“或许正是因为丧失了神力,才得以醒来。”刑天把巨斧刺入脚边的岩块中,“我在与黄帝厮斗后,同样失去了神力。这也是为何我这副模样还能活着。既然我还未倒下,终有一天,我会再杀回黄帝面前。这常羊山,姑且就当作修炼场,盾坚刃锋之时,便是天地震颤之日!”
温度越来越高,刑天说完这番话后,已是大汗淋漓。
“那——现在有何打算?”刑天问道。
“回成都载天。”夸父的语气平静得如同冰封了的湖面。
刑天似乎欲言又止,半晌没说出话。夸父也没再言语,只微低下头,便转身告辞。
下山后,夸父忽闻背后传来几声雷鸣般的巨响。转头一望,见刑天还立在半山间,以巨斧敲击着盾牌。这声音久久萦旋于天,不绝如缕。
六
“喂,夸子,在想什么呢?”黄蛇打断沉思中的夸子。
此时夜将至深,夸子仰着脸靠在树上,不知注视着何物。
“我在想,我离太阳还有多远的距离。”他回答道,“我的心里燃着一团火,它愈发炽烈。每当我望向太阳,那火焰便同其混在一起,灼烤着我的心。”
“看你的意思,即使大羿那家伙不肯助你,你还要自己继续去追?”
“那是自然。”夸子说着站起身,“走吧,天亮前还得赶去旸谷。”
黄蛇们又嘟囔了几句,大概是抱怨的话,夸子没听清楚,也没多理会。还没走出百米远,背后霍然袭来一阵寒风,直刺骨髓。夸子缩紧身子转头望去,见一只生着蓝羽、状似白鹤的巨鸟嘶鸣着朝他扑来,来者绝非带有善意。
“是怨鸟!”黄蛇喊道,“快跑!”
黄蛇还未说完,夸子已经大步往前跑去,怨鸟扑了空。这似乎把它惹恼了。它发出更为刺耳的啼鸣,眼睛闪起血红的光亮。
“这怨鸟为何物?”夸子边跑边问耳上的两条黄蛇。
“怨鸟为一种灵兽,据说是怨灵相聚所化。白昼时羽毛为赤色,能喷出火焰;黑夜时羽毛变成幽蓝,可冰冻万物。”
“可它为何要追击我?”
“这……这就不清楚了,”黄蛇扭过头,“跑快点,再快点,要追上来了!”
怨鸟见追不上猎物,便发起袭击。它飞到高处,用力扇动了几下翅膀,幽蓝的羽化成一道道锋利的冰刃,顺着疾风飞落。夸子体躯巨大,难免被冰刃划出几道伤口,好在并无大碍。这鸟见夸子不停脚,便更猛烈地扇动双翅,让更多的冰刃落下来。两条黄蛇把头蜷在身子里,不停催促夸子快点儿摆脱这家伙。
夸子脚下生风,不觉竟跑出了树林。没有树木的阻挡,跑得要自由很多,正当他准备大跨步甩掉巨鸟时,却忽地重重摔倒在地,腿上有血汩汩地淌出。黄蛇定睛一看,一道冰刃不偏不倚地刺进了夸子小腿上的旧伤。怨鸟见夸子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仰起脖子长鸣一声,翅膀上的羽毛汇聚在了一起,变成一只巨大的冰锥。
“夸子,快,快起身,跑!跑啊!”黄蛇的声音越来越尖锐。
夸子吃力地挪动着受伤的腿,另一条腿跪在地上,拖着身体一点一点往前移动。怨鸟发出怪叫,似在欢呼。寒气直逼夸子的体内,他甚至觉出身体在结冰。怨鸟的巨翅猛地一振,冰锥便刺向夸子的头。
一道影子从夸子头顶飞过,随即一声巨响贯进他的耳朵,震得他耳里发颤。冰锥飞向了一旁,破碎成大大小小的冰块,里面还掺着碎石。
夸子循着黑影掠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巨大的人影朝自己走来。他耳上的两条黄蛇马上竖起上身,嘶嘶地吐着信子,似在挑衅。
借着月光,那人的脸孔渐清晰起来。怨鸟大叫一声,似被激怒,可一见到这巨人的面庞后立马扭过脖子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夸子直直地盯着眼前的巨人,不知为何,他心里蓦地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不安。
“他就是夸父。”黄蛇在夸子耳边轻声说。
“他竟还活着。”另一条黄蛇讶异地说。
夸子在看到影儿时便有此人是夸父的预感,但当他看清他的面容,在黄蛇口中确认后,他还是心中一颤。夸父似没看见他,不紧不慢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月光之下,夸子能看到他发上的缕缕银色。四条黄蛇面面相觑,相互吐着蛇信,发出可怖的怪叫,像在和对方示威。
“夸父!”夸子突然喊道。
夸父停下脚步,却没有轉过头。但他只停留很短的时间,很快便踏进林中,没了影迹。在夸父即将消失在视线的那刻,夸子瞥见他左手手掌上落下几滴血。
七
“夸父,你为何要救那家伙?你不是要杀了他吗?”
夸父靠在树干旁,正屏气凝神地望着左手手掌上的血污,确然比之前少了一块。现在手掌上血污的纹理一如缺了一个口的琥珀。
“夸父,你为何不杀他?”黄蛇紧追不舍,“他可是那个盗走你神力的疯子!”
“笑话。”夸父对黄蛇的话嗤之以鼻,“连怨鸟都不及的家伙,怎么可能在体内蕴有我的神力!”
黄蛇缩起身子不再吭声。夸父仍目不转睛地望着掌心,眼前竟浮现起夸子的模样。
难道血污消失和他有关?夸父在心里猜道。如此想着,不由苦笑一声。同他有关又如何?即便他体内真的有我的神力又如何?
夸父取下一缕头发,黑白混杂,一半是尘,一半是雪。
方才举起的巨石,在从前不过似一颗小小的尘埃那般,但那一掷,几近耗尽他全部气力。他深觉自己的身体在一点点消逝,在一点点失去力量。
果然我这具凡躯现在只是没用的皮囊吗?罢了,血污还未褪尽,吾命尚不可休!
成都载天……
歇息了一夜后,夸父来到水边,豪饮一通后继续上路。天宇上浮动着块状的云,火焰一般的太阳十分耀眼。夸父行进的速度明显要慢下来了,他折了一根长木作拐杖。天气炎热,走上一段路便大汗淋漓,于是他尽量靠近水源,待到疲累时便能及时止渴。
他足足行走了一天一夜,直到破晓他才坐在水边短暂歇息一下。成都载天的影儿依旧没能出现在视野里,木杖也换了几根。晨光熹微,将夸父这一双凹下去的眼映得更为深邃。水面的倒像几乎让夸父认不出自己。他把灰白的头发散开,而后一头扎进水中。喝饱后,他把双臂置入水中,手掌对着自己。自那晚后,血污再没掉落。
透过清水看去,凝在手心的血污变得更为剔透。夸父把两只手并在一起对照,可当两只手触到一起时,两手上的污迹竟渐融在一起,由两股合为一团。在水流中打了几转后,黑污缓缓如烟雾扩散,水面平静下来,似冰面一样静止不动。
水浊,但更能清楚映照出自己。他的手臂潜在水下,竟一点觉不出暗涌。可当他想要抽出手臂时,却又似插进泥沼。他的脸变得扭曲,继而水面现出了昔日夸父族人的模样,却又被血污抹去。战争,血,火,黑暗。
他又看到树,巨大的繁茂的树,遮天蔽日。树间有小径,顺着小径走下去,有一抹黑影从前面一闪而过。直到走到尽头——那里有光——整片浊水恢复澄澈,映在水面的并非夸父的面庞,而是成都载天山。
夸父的身体霍地抖了一下,这才发觉手臂仍无法拔出,任凭他如何用力,只是越陷越深。他绷紧身子,准备做最后的抵抗,但身后像是有人推了一把,随即一头栽进水里,眼前渐渐变黑……
再次醒来时,夸父看到了雪。
很厚的雪,几近覆过他的小腿。四野一片白茫,大片树木无言地伫立着。雪仍在落。
这是何地?他努力回想,终于记起了水边的场景。他瞟了眼掌心,血污未褪。黄蛇们也苏醒过来,冰冷的空气让它们瞬间清醒。
“莫非这是梦境?”夸父望着纷飞的雪自言自语道。
“这天寒地冻的……哪里是梦?”黄蛇发出嘶嘶的声音,看来着实被冻得不轻。
一阵似雷的轰鸣响起,夸父立马握紧拳头。这声响片刻后便平息,继而一个声音响起:“穿过这里,你便能回到成都载天。”
夸父心头一颤,他仔细回想了一番,却没能辨认出这声音是何人。
“可否请教一下,阁下是何人?”
没有回应。夸父望了望皑皑的四野,拂了拂肩上的雪,迈出了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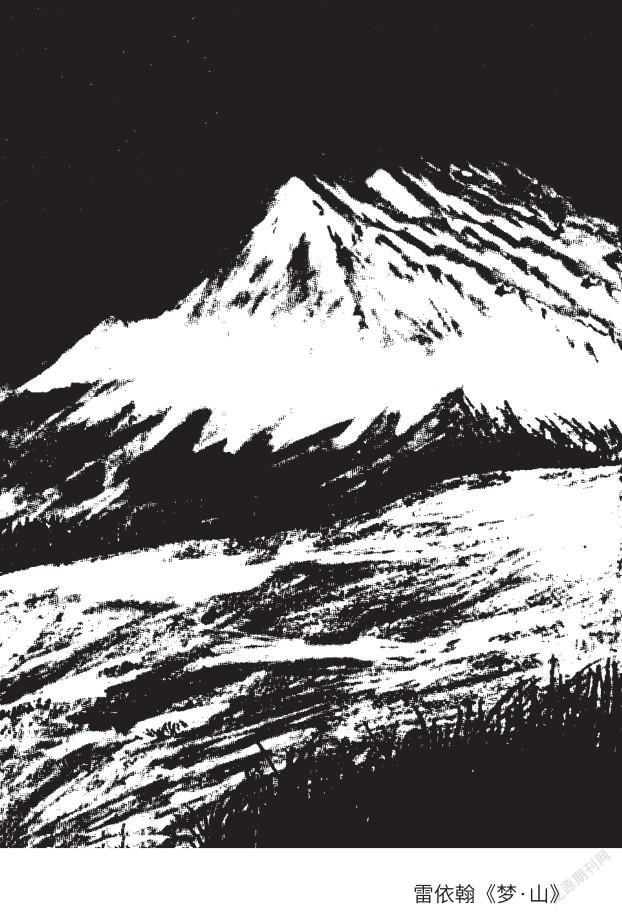
雪愈下愈大。夸父用手臂挡住额头,一步一步向前踏着,虽然这积雪并未让他举步维艰,但也绝称不上如履平地。夸父担心雪会越来越厚,便伸手去折近旁的一根树枝,可它就似空气一样,眼看着已经握住了,却是抓了个空。夸父又尝试去摸另一根树枝,依旧如此。他望了望天,又摊开手,雪片融于掌心。
我憎恶这雪,我不希望遗忘,哪怕所有的一切都由我来背负。是幻是实,是假是真,都有个尽头。夸父在心里喃喃道。
他再次迈步。雪渐渐小了,树冠和地面的雪正迅速消融,上方的积雪化成雨,脚下的水汇成河。太阳从云幕中现出,树木顺着水流方向倾倒,化作成群的游鱼。夸父蹚水而行,大鱼从他身边掠过。他指缝里有几滴黑血落下来,很快被冲散。
随着树木一排排倒下,水面渐渐扩大,夸父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水涨水落,泛起一上一下的澜动。水色渐变至深蓝,所有游鱼聚在一起,幻化为一条生着翅膀的巨鱼,飞鸟一般跃出水面,激起滔天大浪。
“是海。”夸父说。
又几滴污血坠下。他摊开手掌,两块血污已经破碎得不成形状,比起之前状如玉石,现在更似两条扭舞的长蛇。
海水不似方才的水路好走,夸父一面凝视着手掌一面行进,速度降下来很多,他也明显觉出自己的腿愈发沉重,气力也几近耗光,双眼满是血丝。他停下来舀一捧海水,朝面前广垠无边的海大呼:“夸父在此,山海皆不可挡我,天地皆不可灭我!”
飞在空中的巨鱼骤然落回海里,海水汹涌奔腾,巨浪腾翻滚滚,一浪高过一浪。腾起的海水呈阶梯状,竟化为一座高山,脚下是混着碎石的黄土。夸父弓着腿一步一步往上爬。热浪灼人,山顶直逼天穹。
“这山比起成都载天,可要逊色百倍。”夸父两手扶着阶梯,躯体上的肌肉在金光下一如山丘起伏那般凸起弧度,汗液浸满他的发,淌进眼里,再流入口中。
蓦地,他两手抓了空,险些失去平衡。夸父努力稳住脚,挺直身子,踏上最后一级阶梯。他伸直双臂,做出擁抱状。亮眼的光让他有些目眩。干渴。他觉出强剧的干渴。两道黑魆魆的痕迹沿着小臂流下,很快被热浪蒸发。
夸父瞥了眼掌心,还剩下一点血污,一如素色布匹上的一点污渍。
狂风骤起,扬起了他的发。云层迅速聚合,金光也随即消失。周遭为沙石所模糊,只上空有一道口子,里面闪着白光。
夸父半蹲下去,两手扶地,做出跳跃姿态,眼望头顶的出口轻笑一声。大风又起,刮乱了他满头白似霜雪的发。他猛然大喝一声,跃向那道白光。
八
被怨鸟袭击后,夸子仍每日往返于日出日落之地,也会准时登上成都载天。他的体躯愈加矫健,也能觉出自己在一点点接近太阳,甚至能将双臂穿过云层。即便如此,他的心里始终有种隔阂感,像是蒙了一层雾。他觉得自己无法真正接近太阳,即使近在咫尺。
同夸父相遇的那晚,夸子一夜未眠。黄蛇们也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它们都想不到,夸父居然在大战中活了下来,更没想到夸父竟成了这副模样。
他还听见许多人说,夸父已经死了。
“被巨兽吞了,渣也没留下一点。”
“是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尸体被猛兽瓜分了。”
还有说夸父躲进某处深山,在荒林野店过活,长隐于世。各种各样的说法,夸子每次听见都会摇摇头走开。他并不存有那种偏激的信念——夸父一定死去或活着。他也在穿梭途中确认过夸父的踪迹,可始终未能找到一点影儿。
“或许他真的……倒在了某处。”黄蛇也如此猜道。
关于夸父的传言越来越少,他在奔跑途中几乎再听不到了。夸子似乎并未真正在意过这些话,他只是每日不停赶路,尽力离太阳更近一些。日头仍十分毒辣,像是在向他示威。
一天夜里,风伯来见夸子。
“他死了。”
“怎么死的?”
“掉进河里,大概淹死了。”
“为何不见尸体?”
“这就不知了。”风伯耸耸肩,“也许被河里的鱼瓜分了。”
“为何前来把此事告诉我?”夸子问他。
“觉得你可能想知道。”风伯来到夸子身旁,“不过,那家伙没杀你,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夸子皱起眉,说:“此话是什么意思?”
风伯嗤笑起来,化成一阵风。风吹落了大片的叶子。
这日——许是很多天之后,正午的太阳格外毒辣。和每天一样,夸子从成都载天上爬下后,照例要去近旁的小林中歇息一阵。刚刚消耗了大量体力,又流了许多汗,让他觉得疲惫不堪。
夸子往树林走的时候,忽见一高大人影徐徐从林里走出来,同他相向而行。那人走出荫翳,容貌渐显。夸子睁大双目,直直地盯住他。但他像是并未看到夸子一样,只兀自往前迈步。阳光覆着他全身,给他瘦削的身体镀上了一层金。白发似雪,眼窝凹下但目光熠熠。
两人很快相遇。四目相望,却无一言,也并未停脚,很快便擦肩走过。四条黄蛇都盘起身体,转过头回望对方。但二人各自向前,没有一人回头。夸子直视前方,心脏跳得厉害。
蓦地,夸子听见一声巨响,像是什么倾倒在地。他停下脚,但没有回头,只几秒的时间,便再次迈出脚。那瞬,他觉出有强旺的生命正源源不断地注入他的身体。
夸父五體伏地,手指上滴下几滴黑血,继而身体似被蚕食般消逝,融于土壤之中,不见一点痕迹。不多时,有树木从土下拔地而起。一棵为木,百木成林,万木便似川河生生不息,如天壁延绵不绝。成都载天山脚下,竟被这郁苍的林海围拥住。
夸子身后的偌大影子一如藤蔓般野蛮生长,很快没过了他脚下的影儿。他的躯体也在一点点变大,直至他的影儿挣脱了树影的束缚,他才停止生长。又两条黄蛇不知何时爬上了他的手臂,蛇头朝着行进的方向吐着信子。
在这当儿他忽地转过身,望了望成都载天,继而微低下头向山的方向走去,一路走到山脚,肩头与树冠上的叶摩擦发出簌簌的声响。他大步跨上山,霎时耳里灌满风的疾响。
“我一步可跨河泽,五步可穷江海,十步可攀高山,百步可登青云之巅!”
他登上山顶,头上的金轮变得巨大无比。空气中跳动着火焰,周遭的一切都被灼烤得扭曲。而后他蹲下身,抬头凝望着太阳,嘴角微微扬起,摆出跳跃的姿态。少顷,他纵身而起,大张着双臂。
“吾乃——”
作者简介
王鹏宇,西南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生在读,写小说和诗。
责任编辑 张范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