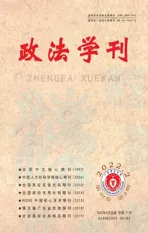身份犯本质理论的二元论重构
2023-01-08陈梅
陈 梅
(梧州学院 法学院,广西 梧州 543002)
身份犯的本质,又有学者称之为身份犯的规范本质或身份犯的处罚依据,虽然在措辞上略有不同,但其指向的问题是同一个:为何刑法立法对特定身份者的罪与罚进行了特别规定?换句话说,为何只有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某种行为才构成犯罪,以及为何实施同样的行为有身份者的处罚更轻或更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揭示了身份犯存在的理由与目的,同时也是解决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了身份犯的犯罪构成,以及身份犯共同犯罪情形下应当如何处理的前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基础性的理论意义。
一、身份犯本质的理论脉络梳理及评析
对于身份犯的本质问题,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多种理论学说,综合梳理来看可将其概括为法益论、义务论、综合论与新综合论,各种学说均有各自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且理论纷争仍在继续。
(一)特别法益侵害论
特别法益侵害论是指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探寻身份犯的本质,即刑法之所以会特别设立身份犯,是因为其在法益侵害上的特殊性。具体可以包括“法益侵害说”、“法益侵害区别说”以及“三重法益侵害说”的不同观点。
持“法益侵害说”的学者认为,身份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其本质问题与犯罪的本质密切相关,一旦在犯罪的本质问题上选择了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则在身份犯的本质上也持相同的立场,即认为“同样,在身份犯之场合,法益侵害说亦应当得到提倡”。[1]但早期持“法益侵害说”的学者所讨论的对象实质上都仅仅只是真正身份犯,最常见的分析对象是贪污罪、受贿罪等公务人员犯罪的情形,主张在身份犯中,只有有身份者才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不具备身份的行为人没有侵犯法益的可能,例如德国学者奥本海姆的“特别保护对象理论”等。[2]149
有学者认识到此种分析方式只看到了身份犯的一部分(真正身份犯),为此发展出了在身份犯本质内部进行细分的学说,笔者将其概括为“法益侵害区别说”。这种区分在主张将身份犯划分为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的学者那里,表现为认为无论是真正身份犯还是不真正身份犯,其本质都在于法益侵害,但区别之处在于真正身份犯的本质体现为身份决定了法益侵害能否发生,而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体现为身份影响了法益侵害的程度,继而造成行为人因身份的不同而处罚不同。[3]主张将身份犯划分为违法身份犯与责任身份犯的学者则认为,违法身份犯与责任身份犯的本质都在于法益侵害,行为人都是因为侵害了法益而受到处罚,但不同之处是违法身份犯中的身份决定了犯罪是否成立,即决定了法益侵害的结果能否发生,责任身份犯中的身份则只与法律规范对人的期待有关,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西田典之等以及我国学者陈洪兵、周啸天等持此种观点。[4]415-456
“三重法益侵害说”则主张“身份犯的实质在于特定的犯罪主体违背了自己特定的义务,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特定的法益,同时也侵害了法律所普遍保护的普通法益。”[5]该说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混合身份犯共犯的定性问题,为不具有身份者的处罚提供理论依据。
虽然该说同时强调了主体对义务的违反以及对法益的侵害,似乎最为全面,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身份犯的特殊性,实际上仍是以法益侵害说为核心,只不过在此基础上拓展出义务违反的辅助前提,并将身份犯罪中被侵害的法益区分为特别法益和普通法益,通过这种区分主张无身份者可以侵犯身份犯中的普通法益,从而可成立共犯。论者在提及主体对义务的违反时,指出所有犯罪都以行为人负有一定的义务为前提,且认为身份犯主体的义务与普通犯罪主体的义务有时无法区分,界限极其狭窄(如强奸罪),这是对身份犯主体所负有的特殊义务的一种误读。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身份犯都有着对应的特殊义务,论者所例举的强奸罪主体就没有这样的特殊义务,但据此将义务违反边缘化为对身份犯本质认定的辅助要素,忽视了部分身份犯是以义务违反为核心内容的。
此外,在身份犯罪所侵害的特殊法益中分离出普通法益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要论证非身份者作为身份犯共犯的可处罚性,只需基于共犯的可罚性即可,而共犯的可罚性从来都不来自于其亲自侵害了法益。同时,要将所有的身份犯都分离出一个普通法益实际上也是困难的,如渎职罪,就难以从中分离出一般性的法益。
(二)特殊义务违反论
特殊义务违反论是指从规范违反的角度解释身份犯本质的理论类型,即身份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违反了与其身份相对应的特殊义务。而特殊义务本质上就是一种特定的行为规范,为此身份犯本质中的特殊义务违反论与犯罪本质理论中的规范违反说密切关联。但持此论的学者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内部仍存有一些争议,根据学者们对身份犯本质与犯罪本质的规范违反说之间联系程度的不同观点,可以将学者们的主张分为“例外义务违反说”和“彻底义务违反说”。
“例外义务违反说”意味着在整个犯罪本质问题的大致立场上,仍主张法益侵害是犯罪的实质,但在身份犯领域内例外性地认可规范违反、义务违反是身份犯的实质,即身份犯的处罚依据不在于有身份者侵害了特定的法益,而是在于有身份者违反了其特定的义务(行为规范)。在日本,川端博等学者持此种见解,“的确,作为一般理论,将犯罪作为义务违反来把握并强调‘义务思想’并不妥当,犯罪应首先把握为法益侵害。但是,即便肯定真正身份犯的‘义务犯’性,这是有关身份犯的‘特殊的’犯罪问题,绝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将犯罪理解为‘义务犯’。因此,将身份犯作为例外的义务犯的理解与其说是直接强调‘义务思想’,毋宁说是合乎其真正身份犯特质的解释。”[6]112我国陈兴良教授[7]342、林维教授[8]的观点也十分接近“例外义务违反说”,虽然在论述时,皆只提及了真正身份犯的实质,而未详细论述不真正身份犯的实质,但其意在于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与普通犯罪并无差异,身份只是刑罚加重、减轻的责任要素,而不再是身份犯本质这一层面上的问题。
但也有学者认为不仅真正身份犯的本质在于义务违反,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也在于义务违反。如日本学者野村稔教授提出单纯遗弃罪与保护责任者遗弃罪一样,违法要素都是对被遗弃者的生命、身体的抽象的危险,但后者的违法要素中加上了保护责任者违反了应负担的保护义务,因此刑罚较重。[9]94
“彻底义务违反说”则指的是不仅主张身份犯的本质是义务违反,在整个犯罪本质的问题上也主张规范违反说。在德国,雅各布斯教授主张的义务犯理论将特别义务违反作为了义务犯的可罚性基础,同时,从雅各布斯对刑法的理解来看,整个刑法的归责基础都在于规范的违反,可见雅各布斯教授将义务违反(规范违反)贯彻到了整个犯罪本质的领域,义务犯的特殊之处仅在于其义务的特殊性。[10]23-30我国学者除何庆仁教授明确支持义务犯理论之外,周光权教授在不法问题上提倡行为无价值二元论,在身份犯的问题上也偏向义务犯的理论[11],但由于行为无价值二元论中同时糅合了法益侵害的违法性判断要素,周光权教授的主张与雅各布斯教授的主张差异仍是较为明显的,尤其是近期周光权教授的观点中对行为规范违反的体系地位和分量进一步进行了调整,规范违反成为了只是表征法益侵害的形式[12],为此周光权教授仅采用了义务犯理论中对正犯的判断标准,而没有进一步明确身份犯的可罚性基础也在于义务违反。
义务犯这一理论是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最先在其正犯体系理论中提出来的,但罗克辛教授提出的义务犯理论主要并不是在探讨身份犯的本质(处罚依据),而强调的是义务犯的正犯准则与一般犯罪的差异。即义务违反在罗克辛教授这里仅仅只是确定正犯性的准则,而不是刑法设定义务犯的理由。在犯罪本质的问题上,罗克辛教授仍是一以贯之的支持法益侵害说。但出于该理论在表述与内容上的特殊性,笔者仍将其归在义务论中提及,从本质上看,罗克辛教授的理论在身份犯本质的问题上应属于法益论,而非义务论。
(三)综合论
前述法益论和义务论在身份犯本质的领域内,贯彻的都是同一种理论立场,即使主张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有具体形态上的差异,也只是在该理论立场内部的细致化和精细化。而综合论则指的是在身份犯本质的范畴中同时并存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即在真正身份犯的本质上主张法益侵害说,而在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上主张义务违反说。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犯罪,首先可以解释为把法益的侵害作为各个核心而构成。可是……被侵害的法益尽管是同一的,在不真正身份犯中,身份者的行为比非身份者的行为处罚要重……离开身份者的义务违反这一点,是认为就难以彻底理解;所以犯罪的本质,一方面基本上是对各类法益的侵害,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义务的违反可以作为本源。”[13]
除此以外,对于将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理解为对“较强期待”的违反的见解,有学者认为这与义务违反是内在一致的。如阎二鹏教授认为,日本学者山中敬一所述的“在不真正身份犯中,对身份者比一般人较强的期待着避免犯罪。如业务者中的‘业务者’的身份,对身份者是特别强烈的期待着不侵害占有他人职务的”[2]150-151,是将身份犯的本质解释为了法益侵害说与期待说的综合,其中期待说就是义务违反说,因为“只能是因为有身份者基于特殊身份所负担的特定义务才存在‘较强的期待’”[3]90。但这样的理解应当说是一种误读,身份犯的本质是违法性层面的问题,而较强的期待,或者说期待可能性程度是责任层面的问题,与身份犯的本质并不在一个层面。为此,将不真正身份犯与期待可能性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回答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昌教授指出:“用对身份者的较强的期待,解释为不真正身份犯的根据,似乎还值得研究”[2]151,值得研究之处并不在于将不真正身份犯与较强的期待相关联,而是在于较强的期待原本就不是犯罪本质层面的问题。
对于综合论,有学者认为此种理论将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差异过度渲染,将两种毫无关系的有关犯罪本质的理论机械地统合到了身份犯的本质这个问题下,研究的价值成疑。[12]对此,笔者认为此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并不认为身份犯本质内部不能容纳多种理论,因为身份犯原本就只是根据外部特征而组合在一起的特殊犯罪形态,其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完全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使是理论路径不同的解释方法,统合到身份犯本质问题项下,也只为更为精确和清晰地展现身份犯的内部构造,只要能够找到可以合并的“同类项”,就并不会产生疑问。除了理论体系上的质疑,还成为问题的是,综合论的研究前提为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的区分,这种区分方式只是根据立法形式进行的分类,而身份犯的本质问题是在实质层面进行的探讨,这就难免会出现对身份犯本质的细分,与身份犯种类的划分无法一一对应的问题,如不真正身份犯中就存有以法益侵害更重(更轻)为本质的类型。需要说明的是,持综合论的学者主张不真正身份犯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侵害的法益是同一的,是因为违反了义务、违法性加重,为此才处罚得更重。但在我国刑法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从形式上看属于不真正身份犯,但很难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与无身份者非法拘禁侵害的法益是同一的,前者至少还侵犯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权的公正性这一重法益。为此,这种交叉与重叠使得综合论内部体系化不够严密和合理。
(四)新综合论
除了大陆法系学者从法益侵害或义务违反的角度探究身份犯本质的路径,我国还有部分学者绕开了此种纠缠,从其他视角对身份犯的本质进行了研究,可将其概括为新综合论。其中包括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展开的“身份四要件论”,以及从犯罪论不同层面展开的“三重身份本质论”“身份四要件论”指的是从身份本身去寻找身份犯的本质,即从身份犯的四个要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分别论述身份的作用。明确提出此种立场的是杜国强博士,但最初将身份放在构成要件当中考察的是康均心教授。康均心教授认为,身份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程度产生影响,是因为身份影响着构成要件中的每一个要件,换句话说,在将犯罪的本质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进行理解时,身份犯的本质便在于身份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特殊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是通过身份对构成要件中的每一个要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具体来说,“在犯罪客体方面,身份决定了行为侵犯的客体性质及侵害程度;从犯罪客观方面来看,身份决定了犯罪行为的性质;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身份是犯罪主体的构成要素之一;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身份决定着罪过的有无及其程度。”[14]杜国强博士也采用了这种思路,其具体的论述内容基本与康均心教授无异。[15]“身份四要件论”虽然角度新颖,但从根本上说讨论的是刑法规定了身份犯以后,如何进行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而讨论身份犯的本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刑法为什么要规定身份犯,处罚身份犯的根据是什么?这一问题是在刑法规定身份犯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身份四要件论”未能上升到这一层次。
“三重本质论”则是从行为的实质违法性、罪责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分析身份犯本质的理论,其基本主张为:“身份犯的实质就在于不同的身份基于与犯罪构成要素的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或影响了行为的法益侵害性、罪责性和人身危险性,从而决定或影响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16]此种理论看似综合性最强,集合了国外的法益侵害说、义务违反说,以及我国学者提出的身份四要件论等等学说,并将犯罪论各个阶层的问题都融入到了身份犯的本质当中来,同时又还有我国学者所主张的“犯罪本质二元论”的影子。[17]189-190然而正是这种超强的“综合性”,使得其缺陷更为明显。
该理论将罪责性和人身危险性要素也看做身份犯的本质,理由是“在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往往坚持以法益侵害为原则、例外地采取伦理规范违反说的二元论,因此也存在把仅仅违反伦理规范而很难说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影响规范违反性的要素是罪责要素”[16],因此罪责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是身份犯本质的要素。在这一论述中,将讨论违法性的规范违反理论,通过“规范违反性”与罪责要素联系在一起,显然犯了偷换概念与逻辑不清的错误。此外,在客观主义刑法的框架下,行为人个体的个性——人身危险性,也难以在犯罪本质问题中被涵盖。对身份犯本质问题的探讨说到底是为了讨论为什么设立身份犯、身份犯的处罚根据的核心,而不是在现有立法框架下讨论身份如何影响定罪量刑的问题,将罪责要素以及人身危险性等要素同时拉入其中,只会使得相关理论更加混乱。
二、身份犯本质学说的根本对立点与立场选择
(一)身份犯本质学说的根本对立点:“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对立
通过前文对身份犯本质现有理论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身份犯本质问题中,“法益论”与“义务论”的对立是根本对立点,前者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探寻身份犯本质,后者从义务违反的角度探寻身份犯的本质,各种综合论的观点不过是这两种立场的组合。将这一对立点推至犯罪本质问题的层面,即为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的对立。
身份犯的本质与犯罪的本质是“一脉相承”的命题,脱离了犯罪本质的框架讨论身份犯的本质(例如新综合说中“三重本质论”),对厘清问题的实质并无益处,因为身份犯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解释现有的身份犯现象,更重要的是对身份犯与普通犯罪差异的根本点进行明晰,为身份犯诸多基本问题提供切入点,从而为立法、司法活动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基础。关于犯罪的本质,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界主要存在着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义务违反说、规范违反说以及折中说的争论[2]84,在我国则主要有传统的社会危害性说,以及新近形成的刑事违法性说、犯罪本质二元论说等等[18],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前述理论在我国也有支持者,共同参与到了我国学界有关犯罪本质问题的探讨争鸣中。从总体上看,法益侵害说、规范违反说以及社会危害性说的阐述在学界占据的分量最重,其中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对立十分明显,探讨也十分深入,而社会危害性说的定位尚不十分明晰,虽然其强调主观与客观统一进行考察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如何统一进行考察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在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上的提炼,而这种提炼可以借由法益侵害理论或规范违反理论完成。[19]为此,基本可以认为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是犯罪本质问题上的基本对立点,而身份犯本质问题基本上也在这一维度内展开,即使发展出了形形色色新的学说,实际上争论的根本点还是可以还原到法益侵害或规范违反的基本立场上去。
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在基本主张上,法益侵害说主张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或者危险,也只有事实上侵害了法益的行为才是需要动用刑罚来处罚的。而规范违反说主张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对规范的违反,根据规范违反说内部观点的不同,行为所违反的规范可以分别指代德国学者主张的法规范违反(宾丁)、国家一般规范(贝林格)、文化规范(迈耶)、行为规范(盖拉斯)等,以及日本学者所主张的社会伦理规范。
其次,在基本立场背后,存在着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对刑法目的和任务的不同理解,在法益侵害说的角度来看,刑法所要保护的是人的利益,而在规范违反说的角度来看,刑法保护的是规范的秩序和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法益侵害说的学者往往认为自己的学说更有利于保障人权,且指摘规范违反说有“通过裁判将国家的道义标准,强加给国民个人的危险。”[20]95
最后,在不法理论层面,法益侵害说往往导向结果无价值论,规范违反说则导向行为无价值论,但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主张犯罪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但在不法的认定标准上,也可能主张只要行为产生了法益侵害的危险且不具备社会相当性时就产生了不法性,而这是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
具体到身份犯本质的问题上来看,法益侵害说从有身份者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具有的特殊性上对身份犯的本质进行规定,即身份犯设定的出发点在于对身份犯所侵犯的“法益”的特殊保护。而规范违反说将身份与特定的行为规范(义务)相连接,从身份者行为的特殊性上(义务违反性)上解释身份犯的本质,根据这种思路,身份犯设立的出发点在于对身份者特定行为规范的维护。
(二)身份犯本质学说的基本立场选择:犯罪本质的二元论
在明确了身份犯本质相关理论的基本对立点之后,面临着选择何种立场的问题。立场的不同,在身份犯各领域内所构建起来的理论形态也是不同的。对此,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身份犯本质的基本立场是否必须与整体的对犯罪本质问题的基本立场一致?即可否在犯罪本质的基本立场上选择一说,在身份犯本质的问题上选择另一说,正如前文所述的“例外义务违反说”的主张一样。
笔者认为,犯罪的本质与身份犯的本质都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本质性的问题就必须有相当的概括性,即身份犯的本质应当能够反映出所有身份犯的核心,而犯罪作为包括了身份犯的上位概念,对其本质的概括应当能够反映出身份犯的本质,为此,身份犯的本质与犯罪的本质应当是一致的。“任何概念,只要不能科学地概括法律规定的所有犯罪,就不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因此,对每一个犯罪的实质概念来说,只要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它不具有‘最小公分母’的性质。”[21]73这就表明,在选择身份犯本质立场的同时,对犯罪的本质也需同步进行选择,并且这二者应当是同一的。
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学界的讨论十分热烈,但实际上,犯罪的本质并不应当在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中做单一的选择,融合二者的二元论是更为合理的选择。虽然前文所述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是犯罪本质问题上最主要的对立立场,但仔细分析来看,二者并非南辕北辙,完全没有融合的空间。
首先,犯罪的本质问题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例如重视法益价值的理论在刑法的目的和任务上表述为法益保护论,而在犯罪的本质问题上表述为法益侵害论(即侵害法益的行为是犯罪)。虽然二者息息相关,且在多数情况下立场互相对应,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这主要是因为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可以是多元的,这就使得犯罪的本质也并非一定是单一立场的。在现代国家,没有谁会否认法益保护的重要性,刑法具有保护法益的目的和任务这一命题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但何为法益,法益如何得到保护,这离不开对规范的作用和价值的维护,进而维护规范的效力同样可以成为刑法的目的之一。为此,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对立或许只是理论立场上的一种表现,但二者在终极目的(保护人在社会中的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上分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德国刑法学家耶塞克就将犯罪的本质视为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统一体。[22]63
其次,虽然犯罪的本质可以是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的综合,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组合的关系,而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组合。周光权教授近期以来主张规范违反的判断从属于法益侵害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规范违反判断的独立价值。[23]但从规则功利主义与行为功利主义的哲学角度来考量,规范维护与法益保护不仅能够互相融合,且比行为功利主义(主张一元化的法益保护)更具合理性。[24]在规则功利主义角度来看,虽然也计算法益的保护,但这种计算与行为功利主义并不相同,前者进行的是行为长期累积性效果的衡量,后者进行的是当时、具体的效果衡量。这就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益侵害与规范违反是同一的,犯罪行为即侵害了法益,又违反了规范。但当二者不同一时,就需要选择是采取当时、具体的思考模式,还是长期累积性效果的思考模式。笔者认为后一种立场是更为合理的,即规范本身所代表的整体性的功利计算法更具有说服力。
最后,需要明确的问题是,犯罪本质的二元论中的规范违反必须与一元的义务论划清界限。义务论崇尚的是规范的绝对有效性,不考虑法益侵害的结果无价值,甚至不考虑具体的境遇。而犯罪本质二元论中的规范违反判断内含了规范的效果判断,并不坚守规范的绝对性,还需同时考虑法益侵害的结果无价值。
三、身份犯本质学说二元论的提出与阐述
(一)身份犯本质学说二元论的提出
从犯罪本质的二元论立场出发,对身份犯本质问题的解析,首先需要厘清与前述“综合论”之间的区别。
前述综合论是在身份犯本质的领域内将法益侵害与义务违反分别作为真正身份犯的本质与不真正身份犯的本质,这种综合正如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机械的组合。而从犯罪本质二元论出发对身份犯问题进行的考察,必须同时考虑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的两个侧面。但由于身份犯内部本身的类别差异,不同的身份犯类型所考虑的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其次需要明确的前提是,身份犯的本质与犯罪的本质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一组概念。探讨犯罪的本质是为了明确区分出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之间的实质差异,即违反了规范且侵犯了法益的行为就是具有违法性的,而没有达到这个实质性标准的就不应当是刑事违法行为。
身份犯的本质探讨一方面是区分出身份犯罪与无罪行为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在犯罪的本质项下已经基本解决了,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身份犯与普通主体犯罪之间的区别,以及身份犯内部不同类别中本质属性的差异,这就需要在身份犯本质的特定性内进行进一步分析。
身份犯与普通犯罪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体现在了所侵害法益的特殊性上,还是体现在有身份者行为规则(义务)的特殊性上?这是引发前述身份犯本质理论中的特定法益侵害说与特定义务违反说不同观点的核心所在,笔者认为,应当从犯罪本质二元论的角度出发,看到身份犯的本质同时体现为侵害法益的特殊性与身份者(行为规则)义务的特殊性,但在不同类型的身份犯中,法益侵害与义务违反的组合形态有所不同。
身份犯的类型,学界一般采用的是真正身份犯与不真正身份犯的形式化分类,这种形式化的分类始终难以把握住身份犯内部的实质差异。笔者认为,从身份犯的二元化本质的角度,应当将身份犯从实质上划分为法益依附型身份犯与义务依附型身份犯,并以此分别探究其本质。
(二)身份犯本质学说二元论的阐述
法益依附型身份犯,指的是刑法中对此类身份犯的设定,更多地考虑的是对法益的保护,行为与法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身份和被保护的法益之间不具备同一性,在犯罪行为实施时身份与法益之间的关联才被表现出来,且立法规定只有身份者的行为可以导向法益的侵害。[10]290换句话说,法益依附型身份犯与普通犯罪的特殊之处在于,该种法益从物本逻辑的角度来看,只有行为人的行为可以侵犯,不具备身份者,一般不可能支配法益侵害过程,身份要么展现出来的是行为人对特殊法益侵害的支配性方向的能力,要么体现的是立法者通过对典型犯罪人的确立,从而限缩或提示处罚的范围。
此类身份犯的违法性判定更多是事实意义上的,而非价值意义上的判断。比较典型的如需具备男性身份的强奸罪,需具备被依法关押的罪犯身份的破坏监管秩序罪、脱逃罪,需具备投保人、被保险人身份的保险诈骗罪等等。但同时这类身份犯的主体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同样违反了其行为规则,但其行为规则与普通犯罪的行为规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实质意义上仍以法益侵害为违法性判断的依据。
义务依附型身份犯则是指刑法中对此类身份犯的设定,虽然也与法益保护相关联,但更多地是体现了对规范(义务)违反的惩治。正如周光权教授所述:“刑法中一些条文的设计与法益侵害有关,但是,其可能更多地考虑了惩治规范违反行为的要求。”[12]
在这类身份犯中,身份者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与法益侵害是一体的,身份者并不是必须直接地、亲自地实施行为才能表征对法益的侵害,即身份本身表征的是身份者的特别义务,而不在物本逻辑上法益侵害的能力和可能性,比较典型的如贪污罪、受贿罪等职务犯罪。一般认为,贪污罪的法益是国家公共财产权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除了国家公共财产权以外,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以及职务行为的公正性都有相当的抽象性,其是否受到损害必然是一个规范上的评价,而不是一个实在性的事实评价,在这种规范性的评价中,必须有身份对相对应的行为规范的违反才能充足对此类法益的侵犯的判断。
虽然在事实上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能有能力侵犯国家公共财产权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如行贿罪中,行贿者也可以侵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这一法益,但行贿罪并不是身份犯),这就表明这类身份犯从事实上侵害法益的特殊性无法表现出其本质,必须考虑身份者的义务违反性,且后者是规范性评价的重点。实际上,表述为廉洁性、公正性的法益,已经可以看做就是规范(义务)的同类表述。张明楷教授认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25],这就已经将该法益的义务性展现了出来,即“不可买卖职务行为”的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义务依附型身份犯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抛开了法益保护,走向一元的规范论,法益保护始终起着对象性的限制功能,只是此时的法益与规范更具同一性,脱离了侵害法益危险的判断,义务违反只可能发生在头脑中,根据现代刑法的基本立场,这种主观性的规范违反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