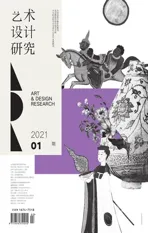“书法式线条”
——罗杰·弗莱对中国书法艺术资源的提取与运用
2021-12-02刘庆
刘 庆
中国书法艺术对英国现代形式主义美学家与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于他抓住了中国书法最基本的美学与形式特征,从中提取艺术理论资源,创见性地提出了“书法式线条”(Calligraphic Line)这一理论术语,并将其运用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艺术的分析与解读中。
一、“书法式线条”的提出
中国书法对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当时的西方很难接触到中国书法作品,直到1907年斯坦因从中国敦煌盗运回大量的经卷文书与绘画,后入藏大英博物馆东方绘画写本部,才得以有机会看到。那么罗杰·弗莱是如何接触到中国书法的呢?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说,弗莱对书法的兴趣,是在与“纯洁英语社”的成员罗伯特·布里奇斯之间的通信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布里奇斯曾写信给弗莱请他帮助收集名人手迹样本。①但这或许更多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笔迹学研究,弗莱对中国书法的关注其实更多是出于自己艺术批评与研究的需要。1906年弗莱第一次见到塞尚的画,便转向现代艺术,也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兴趣。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兴起以来,在绘画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线条这一表现方式。然而,不管是后印象派的梵高、塞尚,还是野兽派的马蒂斯等现代艺术家都没有被大众接受与理解,甚至遭到攻击,但弗莱选择为现代艺术辩护,并在美学与艺术批评理论层面为现代艺术寻求支撑。试想一下,欧洲的绘画艺术,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伦勃朗以后,画面都是剔除得干干净净的,光滑平整到从中找不到任何笔触与线条,因此在欧洲古典传统艺术批评中,严重缺失关于线条的理论与美学。而印象派之后的艺术受到东方艺术的启发,画作中涌现大量的线条和笔触,这自然引导弗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因为中国艺术在线条表现上是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可以称得上是线条的艺术。这成为弗莱关注中国艺术最重要的一大契机,或者说内在需求。
除了大英博物馆的敦煌经卷文书,弗莱主要是通过阅读关于中国艺术研究的书籍著作了解到中国书法,比如翟理斯(Giles)的《中国绘画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的《远东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费诺洛萨(Fenollosa)的《中日艺术时代》(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等。另外,《伯灵顿杂志》(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也是弗莱接触与了解中国艺术重要的窗口与平台,该杂志在此期间刊发了大量关于中国艺术的文章,并设有中国艺术研究专栏。还有就是与诸多汉学家的交往,像狄更斯(Dickinson)、宾雍、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等,都是他获取中国书法知识的渠道与途径,尤其是通过其好友宾雍,比较深入地接触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理论与美学,特别是关于“线条”的艺术理论,“在他的朋友、汉学家劳伦斯·宾雍的指点下,弗莱迅速发现了中国绘画与书法的魅力,对于绘画质地、笔触、书写和线条在艺术表达中的作用,很快就有了超人的见识。”②在《远东绘画》这本书中,宾雍这样写道:“唐代艺术中有一种把书法与绘画有意识地结合起来的努力。我们应该了解,这是一种画家寻求通过运笔而获得表现力的尝试。运笔既需要有可以传达生命神韵的线条,借以表现真实的生命形态,又要有蕴含在张弛有致、一挥而就的书法家笔下的那种韵律的美,书法家的字写得美,是因为掌握了那种令任何画家都羡慕的运笔的功力。”③翻看弗莱的著述,我们会发现弗莱充分吸收了宾雍的这些观点,因为他同样使用了“线条”(Line)、“书法”(Calligraphy)、“韵律”(Rhythm)、“书写”(Handwriting)、“笔触”(Stroke)等术语,这些修辞与宾雍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宾雍的观点被弗莱所消化与继承。但是在弗莱那里表现得更为灵活,因为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中国艺术的了解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这些理论观点运用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阐释与解读中,从而发展与建构了自己的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批评理论,正如包华石在谈到宾雍对弗莱的影响时所说,(后来)弗莱继续发展了以线条和手势的笔触来传达感情的理论④。
其实,在看待中国艺术上,弗莱与宾雍的分野,很大程度上在于是“以中释中”还是“以中释西”。弗莱受中国书画影响提出“书法式线条”这一观点,就是他“以中释西”的一大尝试。而且中国书画同源的观念也给了弗莱很大的信心,他在《中国艺术的几个方面》(Some Aspects of Chinese Art)中指出:“(中国)绘画艺术一直被视为是书法艺术的一部分。”⑤在《最后的讲演》(Last Lectures)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从相对较早时期开始,那些精美的书法范本就被人们所钦佩和尊崇,它们几乎与最伟大的绘画杰作一样多——事实上,这两种艺术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⑥这为他运用中国书法资源去阐释欧洲现代绘画提供了可能性与合法性的支撑,尤其是中国书法线条的抽象性,与西方现代艺术在形式上的追求与表现相契合,使他确信线条是现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一大表现手段,因此,中国书法的线性或线条特征极大地满足了弗莱建构线条理论的需要。1918年他在《伯灵顿杂志》上发表了《线条之为现代艺术中的表现手段》(Line As a Means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Art)一文,也就在这篇文章中,弗莱正式提出了“书法式线条”这一理论术语。为了更好地表述与理解,弗莱用了马蒂斯所画的一幅玻璃瓶插花的素描来加以说明,他认为马蒂斯画这样一幅素描的处理方式在于把一个相当复杂的景象的某些侧面,却仅以区区数根线条就记录下来。这些线条看上去仿佛是在极其迅捷、极端自由的情形中草草画下的。这样一种画法画下的线条被他称之为书法式的线条。⑦在弗莱看来,马蒂斯⑧的整幅画作没有显示出一点儿拖沓、迟疑,是在一种绝对的确信中画下的,因此有“一种令人惊叹的线条韵律感,这种韵律感是极富连续性、极富弹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适应对规范的异乎寻常的变异而不失其连续性。”⑨
二、“书法式线条”的美学特质
1、书法线条的线性韵律
弗莱认为中国书画艺术在本质上是线条的艺术,尤其是中国书法艺术纯粹是以毛笔为工具,以水墨为媒材书写而成的线条艺术,这是中国书法艺术最突出最显著的一大特征。弗莱说,中国人将自己的文字书写发展成一门独特的艺术,这让欧洲人很难理解,以至于一时找不到任何可以解释它的外部原因,只能假定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不过,他已经对此有了一定的探究,那就是他认为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线条是变化的、流动的,非常富有线性韵律,充满了生气与活力,同时它还细腻感性,体现了一个艺术家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与领悟。中国艺术家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要素,往往寥寥几笔,就用线条勾画出事物的神态与轮廓,因此,这样的线条又极具生命力与表现力。弗莱在《中国艺术的几个方面》中是这样概括中国艺术的:首先,他认为最突出的一点是,线性韵律(Linear Rhythm)在中国艺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部分。轮廓往往是构成形式最重要的部分。线性韵律的主导优势体现在所有的中国装饰艺术中,甚至在雕塑中都能感受到。其次,中国艺术中的线性韵律特别具有连贯性和流动感。它从来不会像印度艺术的韵律那么松散,也不会像欧洲所熟悉的某些韵律那样严苛粗糙,以至于断断续续,显示出停顿感和断裂感。⑩由此,可以看出弗莱对中国艺术中的线条所表现出的韵律甚为推崇。尽管他并没有像中国或日本的学者那样深入地研究书法,但是凭借着其高超的艺术直觉与感受力,却精准地抓住了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线性韵律这一关键美学要点。
其实,“线性韵律”(“韵律”也翻译为“节奏”)这一术语是弗莱从谢赫的六法之首“气韵生动”提取与化用而来的,特别是经由其好友劳伦斯·宾雍对“气韵生动”的译介,弗莱汲取了中国这一著名艺术理论。其实,“线性韵律”构成了“书法式线条”理论的肌理,因为弗莱借此意在发展与建构自己以“线条”为特色的形式主义美学以及艺术批评理论。首先,弗莱发现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线条”以最简单、最简易的方式,或者说以最经济的手段方式,去表现与描绘最复杂的事物。虽然看起来简易,但是却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特征与要素,这是艺术家经过深思熟虑或静观默想后进行抽象提取的结果,这完全契合他对形式的思考。因为在他看来,形式是抓住事物最本质的要素提取出来的,而不是面面俱到,其他不必要的要素都可以删去,“形式是通过不断地删除一切次要因素来获得的,直到纯粹的实质得到揭示为止。”⑪这一观点完全符合中国书画美学理论中的“简单原则”。其次,具有“线性韵律”的线条是灵活多变的,就像中国书法一样,书写线条的不同与变化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字体和风格,而且可以在创作中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这构成了“书法式线条”的另一大重要品质。“线条的品质拥有一种可识别的韵律,却又不机械,这就是线条的感性。这里,最显而易见的东西无疑是线条可以有无数变化,可以在其过程中的任何一点上调整自己以适应对象的形式。”⑫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艺术家表达不同心情与感受的需要。再就是,富有节奏韵律的线条,更容易引起观看者的快感。中国书画中的线条往往一笔写画而成,下笔后不许修改,一旦修改就是一种破坏,因此,这需要创作者极高的艺术感受力,对客观事物与主观内心有较好的把握,才能创作出自由流畅的线条。总之,它是艺术家内心愉悦的记录和写照,给人视觉上的愉悦与美感。
在这里,弗莱提出“书法式线条”是为了与“结构式线条”相区别,其实是对中西艺术做了一个比较与区分。“结构式线条”建立在三维透视法之上,代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美学法则,而“书法式线条”是以中国的“线性韵律”作为美学准则。“我试图表明至少有两种审美愉悦,可以从线条赋形中推导出来——从线条本身有韵律的序列中,即我称之为书法性的因素中得到的愉悦,以及造型形式,亦即我称之为结构性因素作用于人类心智而得到的愉悦。人们可以说,书法式线条之为线条,停留在纸面上,而结构性线条则进入了三维空间。”⑬弗莱将“书法式线条”纳入到西方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中,并将其视为是新的美学准则,显然是对西方传统的一种逾越。
2、感受力的自由表达
弗莱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判定一种线条是书法式的线条,其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展示了一个艺术家强大的感受力。就像中国书法一样,尽管看起来是由线条组合而成,但其线性韵律却是灵活多样的,以满足与适应不同人的心理表达需要。“纯粹线条中存在着表现的可能性,其韵律也许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类型,以表现心境与情境的无限多样性。我们称任何这样的线条为书法,只要它所企求的品质是以一种绝对的确信来获得的。”⑭即使书写同一种字体,或者模仿同一幅作品,每个人的作品也存在着或显著或细微的差别,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力不同。书法线条在形式上似乎达到了一种多样性与自由性的统一,以至于中国艺术家在以一定的程式书写时又可以获得自由嬉戏。弗莱认为艺术家如果懂得遵循自由的感受力,那么他将从传统的观念习惯中解放出来,“这种感受力在探测那些能促进其最强有力的整体感、最融贯的体块感的形式特征时,总是非常敏锐。”⑮除了整体感与体块感,即便是最细微的笔触,弗莱也不放过,他认为笔触也传达出一个艺术家的意识与无意识,同样耐人寻味,富含感受力。
弗莱认为中国人如此重视感受力,或许可以从其对待书法的虔诚态度中找到一些解释,在《最后的讲演》中,弗莱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艺术家不仅极其关心允许他自由发挥的感受力,而且公众也非常愿意阅读并欣赏其含义。在中国人对书法艺术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家在表达内心深处和潜意识的情感时的那种喜悦。字体本身,在其早期形式中或多或少经常呈几何线性状,就是根据这种感觉发展而成一种程式。它一下满足了中国人对清晰标记形式关系的渴望,以及通过自由韵律运动来表达自己感觉的需要。”⑯因此,在弗莱看来,中国书法结合了希腊和罗马字体建筑般的坚固性以及阿拉伯字体的自由,就是因为感受力受到较少控制或抑制。当然,也不是毫无节制地宣泄,而是在一种他称之为有机控制的作用下,将凝神结想都倾注于笔端,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与客体达到融合,或者说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消融了,人与笔合为一体,书写的线条记录了一个人的个性与情感。
弗莱的这一认识与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其好友劳伦斯·宾雍,因为后者在1908年的《远东绘画》中直接写道:“据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称,它(绘画)与书法艺术同时存在,纵观中国历史,这两门艺术是紧密相连的。一幅好的书法在价值上与一幅好的绘画等值。而在一幅作品中,对艺术家来说,最珍贵的是,书法作品应该和他的手迹一样具有个性。艺术家借笔触将情绪与思想直接传达于他所画的纸张或丝绸上。”⑰包华石在其文章《笔触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Brushstroke)中认为宾雍所提到的一位“本土历史学家”很可能是11世纪晚期的艺术批评家郭若虚,“(郭若虚)他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艺术家的笔触,就像他的签名一样,是他个性的直接记录。”⑱并引用了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的话,“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郭若虚这里所说的“心”就是感受力,也是创作之本源,如果所书写之字迹与心吻合,就达到了心形相印,即字迹线条与感受力相印。因此,线条在中国书画艺术中,是心之印迹,书法作品字里行间中充溢着作者的感受,线条是个人意识的一种延伸。
3、身体姿势的视觉记录
书法式线条的另一大美学特质是,它是艺术家身体韵律姿势的视觉记录,就像舞蹈者跳跃的舞姿,在生命的律动中呈现出一种流动的、连贯的、自然的线条美。“书法式线条是对一种姿势的记录,事实上是对那种姿势如此纯粹、如此完整的记录,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一种愉悦来追踪它,就像我们追踪着一位舞者的运动一样。它倾向于比任何其他赋形的品质更多地表现观念的不稳定性与主观性的一面。”⑲其实,弗莱早在1909年的《论美感》中已经提出这一观点,直接指出“所画出的线条是一种姿势的记录,通过直接传达给艺术家的感情使姿势得到修正。”⑳在弗莱看来,如果是一件优秀的作品,线条的每一抑扬顿挫如同我们的目光沿着线条的运动使我们产生秩序和变化感。也许,这样一幅画几乎完全没有我们习惯于对一幅画所要求的几何形平衡,但它仍具有,而且是高层次的统一性。中国书法作为纯粹的线条艺术,尽管不具备几何形的平衡与对称,却以线条运动的方式在表现抑扬顿挫与变化感上,相较于其它艺术而言,显得更加灵活多样。中国书法所达到的,是一种被蒋彝(Chiang Yee)称之为“不对称的平衡”㉑。因此在激发人的感情因素方面,弗莱首推用于勾画形式的线条的节奏。
其后该理论观点不断得到强化,在《中国艺术》(Chinese Art)这篇专门谈中国艺术的文章中,弗莱写道,“自远古时期到现在,中国绘画艺术从不失线性韵律,线性韵律始终是最主要的表达方法与方式。而且这只是极为自然的,所使用的媒介往往是水彩,并且绘画艺术一直被视为是书法艺术的一部分。一幅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韵律姿势的视觉记录。它是用手表演的一种舞姿。”㉒中国艺术家在创作书法时,用手运笔时的确像用毛笔在表演一段舞蹈,如行云流水,跟着艺术家的意识在流动,最后一气呵成。因此,一幅杰出的书法或绘画作品,通常集创作者的身体姿态与势能于手笔,身体、意识与思想在运笔之间融为一体,挥洒的线条像跳跃的舞姿一样富有节奏感,生机与活力跃然纸上。弗莱在致罗伯特·布里奇斯的一封鲜为人知的信中写道,复制书法与创作不一样,“(创作时)节奏会以某种方式发生变化……它像说话的节奏一样,似乎跟随着人的思想在流动”(1925年9月18日)。帕特丽卡·劳伦斯说弗莱所认为的书法线条或者中国视角的运笔,不仅仅是身体的运作,而且是源自于艺术家的意识和身体深处的“富有气韵”的“线条”,这与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机械性的书写显然不同。创作时整个身体是融入在笔势当中的,这令人不禁想起杰克逊·波洛克在落笔时会围着画舞来舞去的情形。笔的“舞动”很有表现力,因为笔画和线条能够反映人的内心。㉓
三、“书法式线条”的误读与正解
不过,有人对弗莱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与解读,提出“书法式线条”是对中国书法的一种误读,因为弗莱只注重书法的形式,而完全脱离了汉字、章法、结构、文化等要素,从本体论与整体功能论意义上讲,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一种切割与剥离。在许多人看来,这与传统的书法理论是相背离的,至少是偏离的。因为在传统理论中,书法离不开汉字,它的艺术形式也被汉字所控制,汉字就像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质料因,书法的形式因被质料因所控制,形式一直被视为是汉字的依附。因此,历来对书法的研究都是围绕以汉字为原点而展开的,形式研究是次要的。弗莱对书法形式的提取与重视,显然与传统书法理论的捍卫者格格不入,所以被视为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弗莱也的确对中国书法艺术存在着误读,比如他对“书法”的定义,然而这样的误读却是一种有意义的误读。美国文论家布鲁姆曾提出,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伟大诗歌都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作不断误读的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释读,它不在于对某一具体作品的释读实际发生与否,它实际上是一种接受影响与打破影响,继承与创新的悖谬状态。若按布鲁姆“影响即误读”这一观点来说,弗莱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误读也是一种“特殊性误读”与“合理性误读”,以及“创造性误读”。弗莱对中国书法艺术资源的提取、借用和化用,更多地是结合自己的需要,尤其是结合欧洲现代绘画艺术特点,撷取中国美学资源,以适应与满足本土艺术批评的需要,非常具有针对性。再就是弗莱长期专注于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批评,不可能完全照搬或照抄中国书法艺术理论,那样只是一种机械地复制而已,完全没有任何创造性与建构性可言,而弗莱的努力其实更属于是一种现代艺术批评与美学理论的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还原与回到原初的时代背景之中,来考量弗莱理论的现代建构意义,而不能囿于传统的视域来做评判。
其实,弗莱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解读已经触及到了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的分野问题。正如王南溟在《理解现代书法》中这样写道:“与传统书法理论相区别,现代书法理论关心的就是书法的形式结构,并让人们知道,这种形式是如何被建构的;即形式中的形式组合,而不是汉字书写。艺术的关键在于形式,也就是说,它关心艺术的艺术性,这种使一部作品成其为艺术作品的艺术,而不是笼统的书法,因为只有形式论才能使书法成为艺术,而不至于使它沦为文字学或文章学的依附。”㉔或许,弗莱对中国书法的理解以及对其形式的关注可以视为是现代书法理论的一部分,或者以他作为“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批评之父”这一名分来说,至少可以从中看到现代书法理论的开端。况且批评与创作相比较而言,往往是滞后的。事实上,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在吸收与借鉴东方线条上的实践探索已经先行一步,这为如何看待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撕开了一道裂口。王南溟说,回顾一下西方抽象画如何地吸收中国书法以及在理论上如何论证西方艺术书法化的意义,对我们了解西方艺术和中国书法的关系是不无裨益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反对无文字的书法,这种反对从根本上导致了西方的抽象画和书法的区别,并导致了任何研究中国书法与西方抽象画的联系都是伪装的,当西方艺术家或理论家在引用、借鉴中国书法的时候,其实已经对中国的书法进行了形式主义的割裂,中国书法的形—音—义统一体被割裂为一种‘形’的单方面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都能得到反映。”㉕所以,弗莱是在理论上对中国书法影响做出的回应,其“误读”与现代艺术运动的发展相适应,也是同步的。
另外,还涉及到一个跨文化的问题,即弗莱是从自身文化艺术传统去理解与解读中国书法艺术,所以对于中国艺术的吸收与借鉴不可能原汁原味,况且中西文化艺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非是同构的,不同文化艺术之间发生交互作用后,那么由跨文化引起的“误读”也就不可避免了。与此同时,这样的“误读”也有其合理与创造的一面,那就是不同文化的交互也意味着文化的重组与重构,这带来了文化艺术的创造。因此,“书法式线条”的提出是跨文化误读的结果,是中西艺术交互与重组后创造的产物。所以,很有必要从这一视角出发,对弗莱的努力与尝试重新做出认识与评判,而不能简简单单地认为是一种“误读”,并且止步于“误读”,我们需要在“误读”中发现创造与建构的意义,重估弗莱所提出的“书法式线条”这一理论观点的价值。王南溟在谈到如何看待西方抽象画派借鉴与吸收中国书法时指出,西方绘画书法化只有从跨文化超越的视角来理解才能深入到它真正的意义,虽然针对的是绘画创作,但是对于分析弗莱的理论同样适用。“我们确实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家吸收中国书法来进行创作实验的事实,而又远没有理解到他们的绘画书法化的深层文化指向——西方现代艺术家对中国书法的赞美和吸收恰恰代表着一种对无意识文化超越的决心,而且,正是因为西方人有这种否定自己文化引进外来文化的勇气,他们的艺术才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形式革命性,这种形式革命性,从印象派、浮世绘线描引用到绘画开始,屡屡出现并产生了一个个以线的实验为代表的艺术家。”㉖如此看来,弗莱对中国书法艺术美学资源的提取是在理论层面发动的形式主义革命,不管是往前推,还是向后看,弗莱回到影响的源头直接探寻美学与艺术批评理论都是正确与合理的,与现代绘画艺术运动的发展相关联。
弗莱的理论观点在其后蒋彝的《中国书法——美学与技艺方面的介绍》(Chinese Calligraphy:An Introduction to Its Aesthetic and Technique)中得到了认同。《中国书法》写于1935年,也就是弗莱死后的第二年,在书中蒋彝对书法中的“线条”这一形式特征同样甚为推崇,专门用一章来谈“中国书法的抽象美”。他说书法是中国人民族精神最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人珍视书法纯粹是因为它的线条及组合的线条那美妙的性质的缘故。“与绘画和雕塑相比,书法中的节奏、线条和结构都得到了更完美的体现,即便其中的形态和动势也至少与它们不分上下。”㉗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共同的因素是线条,就是“我们称之为‘线条的韵律’,因为这个词语更能精确地表达出所期望的线条美。”㉘另外,他认为中国的书法美、图画美和舞蹈美属于同一性质,将书法与舞蹈进行比较是颇有益处的,因为赏玩书法珍品或练习书法时所体会到的乐趣,与观看优美的舞蹈时所感受到的快意是完全相同的。
宗白华在对中西画法进行比较与溯源时指出,中国画具有线条美、节奏美和姿态美,与弗莱所推崇的书法美学观点也直接相呼应,“中国的瓦木建筑易于毁灭,圆雕艺术不及希腊发达,古代封建礼乐生活之形式美也早已破灭。民族的天才乃借笔墨的飞舞,写胸中的逸气(逸气即是自由的超脱的心灵节奏)。所以中国画法不重具象物象的刻画,而倾向抽象的笔墨表达人格心情与心境。中国画是一种建筑的形线美、音乐的节奏美、舞姿的姿态美。”㉙宗白华在此虽然说的是中国画,但也适用于中国书法,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形线之美,注重飞动姿态之节奏和韵律的表现,有情感与人格的表现。他说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飞舞,“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唐代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因悟草书;吴道子观裴将军舞剑而画法益进。书画都通于舞。它的空间感觉也同于舞蹈与音乐所引起的力线律动的空间感觉。”㉚这些观点都与弗莱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们都取源于中国书画艺术理论与美学。因此,不管是从蒋彝那里,还是从宗白华这里,弗莱从中国书法艺术中提取资源而建构的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批评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四、提出“书法式线条”的意义
弗莱如此重视线条的作用与意义,这在西方艺术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这完全离不开中国书法艺术给予他的启示。首先,他从中国书法艺术中提取美学资源,从而进一步发展、丰富与完善了他的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批评理论。第一,弗莱从中国书法中抓取“线条”这一艺术特征,并借用“书法”这一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书法式线条”这一术语与理论。第二,弗莱从中国艺术理论中借用与化用了一大批术语,比如书法、线条、笔触、节奏、韵律等,与“书法式线条”理论相配套,构成一个以“线条”为主体的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批评修辞,这些术语构成了现代视觉修辞的一部分。第三,弗莱重视书法与线条,提出“书法式线条”是为了服务于“以线赋形”这一理论,这成为弗莱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一大特色与支撑。他在《线条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中这样总结道:“就我所知,这些就是现代艺术在线条赋形方面所做的努力的结果。首先,这是一种更加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的综合的形式结构——一种更加有力的统一性,恰恰是因为艺术家不再听命于大自然的任何特殊事实,而是必须在每一个情形下重新确定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偶然的东西。其次,这样一种建构性的赋形是从韵律的角度加以表现的,而其韵律则要比过去的数个世纪里获得的种种节奏更为自由、更为微妙、更有弹性,也更具适应能力。”㉛这也是弗莱为何如此看重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因之所在,也就是说,“书法式线条”构成了他“以线赋形”理论的重要一环。
其次,弗莱从中国书法艺术中提取理论资源,为新兴的现代主义艺术辩护。正如我们所知,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以及其后的现代艺术,绘画艺术中越来越重视线条,并不断地以线条作为表现的手法与形式,线条在画作中的作用得到凸显。而在欧洲古典传统绘画艺术批评理论中,极其缺乏线条理论。罗杰·弗莱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书画艺术,发现中国书画艺术以“线条”为主要特征,并拥有非常丰富的“线条”美学理论,故从中国艺术中提取美学资源,对现代主义艺术进行阐释,以消除当时普通民众的漠视、偏见与诘难,为现代艺术家辩护。像印象派的惠斯勒,后印象派的梵高、塞尚,尤其是野兽派的代表马蒂斯,立体主义的毕加索,还有一直追随他的邓肯·格兰特,都得到他的肯定,认为这些现代画家的作品中存在“书法式线条”,并给予高度评价,“我认为,没有谁会否定邓肯·格兰特的素描那伟大的书法之美,及其节奏的自由、弹性与轻松。”㉜而将“线条”为代表的现代形式主义美学与艺术批评理论运用于对塞尚的分析与解读,使弗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为止,《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一书仍然是研究塞尚的著作当中不可逾越的力作。甚至更为年轻的艺术家,比如沃尔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等都受到弗莱的鼓舞。“现在,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年轻的艺术家,例如妮娜·汉姆内(Nina Hamnet)与爱德华·沃尔夫(Edward Wolfe)的素描的复制品,我们还能更清楚地看到同一种趋势。书法是新的类型,比旧有的更微妙、更细腻,也更自然,但最先震惊我们的还是其书法。”㉝
最后,弗莱提出“书法式线条”这一术语与理论,为现代主义艺术运动指明了方向。其实,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弗莱通过其理论研究,想进一步指明西方现代艺术将继续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这一发展动向。事实上,像马蒂斯、毕加索、保罗·克利等一大批现代艺术家的确对中国书法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受到过影响。故弗莱大胆地提出,中国艺术将成为欧洲现代艺术的一种标准,如在谈及马蒂斯时,他这样写道:“我在这个书法问题上逗留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在我的下一篇文章里,我将要指出,马蒂斯崭新而又微妙的韵律,与学院派艺术那种武断的节奏形成了如此奇妙的悖反,以至于正在成为现代艺术家的一种书法标准。”㉞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艺术所表现的美学观念是现代艺术发展中的一种观念,并对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现代艺术的发展,通过确立一种更自由、更富有弹性的书法观念,以及一种更加符合逻辑的造型整体的本质观念,给了素描以新的推动。”㉟像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邓肯·格兰特、温妮莎·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等都是罗杰·弗莱线条美学理论的信奉者与践行者。伍尔夫更是将弗莱的线条理论与美学直接移接到其小说创作当中,比如《到灯塔去》就借用了线条的流动,延伸到叙事的流动,再到意识的流动,以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差异,并成功地塑造了“丽莉·布瑞斯珂具有一双中国眼睛”这一女画家的形象。劳伦斯说,不知不觉中,英国作家在中国美学原则的影响下,在写作上获得了发展:意识得到了拓展,主客体之间的差异开始消融,热衷于线条、气韵、多视觉的表现手法。㊱此外,还影响到现代抽象表现主义,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代表人物康定斯基,他也认为线条是最简洁但信息量最丰富的形式,在其著述《点、线、面》中,他说“线条的张力在于它在最简洁的形式中表现出运动的无限可能性。”㊲甚至战后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运动,例如杰克逊·波洛克、马克·托比等艺术家都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
无疑,弗莱的这一理论观点对抽象表现主义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书法对西方艺术产生的影响日益引起大家的重视。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在《现代绘画简史》中指出,抽象表现主义与东方的书法艺术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绘画运动的崛起多少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抽象表现主义作为一个艺术运动,不过是这种书法的表现主义的扩展与苦心经营而已。”㊳西班牙著名画家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apies)也曾说,尽管他连一个中国汉字都不认识,但是“我们,特别是围绕各种抽象表现派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们,多亏中国的书法家们,才懂得了借用运笔方式而产生的这种情感语言。”㊴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到弗莱,然而,弗莱在理论上的探索与所做的铺垫却功不可没。
注释:
①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583页。
② 沈语冰:《2010上海新水墨艺术大展·水墨时代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③ Laurence 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ictorial Art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London:Arnold,1908,p.68.翻译转引自包华石的《中国体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43页。
④ 包华石:《中国体西方用:罗杰·弗莱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第144页。
⑤ Roger Fry:Transformations: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London:Chatto & Windus,1926,p.73。
⑥ Roger Fry:Last Lectur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p.101.
⑦ (英)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⑧ 事实上,马蒂斯的确受到东方艺术的影响,并曾承认自己的灵感来自东方,还在自己卧室里挂着一幅中国书法匾额。
⑨ 同注⑦,第308页。
⑩ Roger Fry:Transformations:Critical and Speculative Essays on Art,London:Chatto & Windus,1926,p.72-73。
⑪ 同注⑦,第218页。
⑫ 同注⑦,第217页。
⑬ 同注⑦,第220页。
⑭ 同注⑦,第217页。
⑮ 同注⑦,第222页。
⑯ Roger Fry:Last Lectur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p.101.
⑰ Laurence 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ictorial Art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and Japan,London:Arnold,1908,p.51.
⑱ Martin J.Power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Brushstroke.The Art Bulletin,Vol.95,no.2,p.320.
⑲ 同注⑦,第220页。
⑳ (英)罗杰·弗莱著,易英译:《视觉与设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㉑ (美)蒋彝著,白谦慎等译:《中国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
㉒ Roger Fry:Chinese Art:An Introductory Review of Painting,Ceramics,Textiles,Bronzes,Sculpture,Jade,etc.London:Published for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by B.T.Batsford,ltd,1925,p.2.
㉓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573-574页。
㉔ 王南溟著:《理解现代书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㉕ 同注㉔,第62-63页。
㉖ 同注㉔,第89-90页。
㉗ 同注㉑,1986年,第99页。
㉘ 同注㉑,第188页。
㉙ 林同华编:《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0页。
㉚ 林同华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3页。
㉛ 同注⑦,第219页。
㉜ 同注⑦,第221页。
㉝ 同注⑦,第221页。
㉞ 同注⑦,第218页。
㉟ 同注⑦,第220-221页。
㊱ (美)帕特丽卡·劳伦斯著,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591页。
㊲ (俄)康定斯基著,罗世平译:《点、线、面——抽象艺术的基础》,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㊳ (英)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43页。
㊴ 《世界美术》编辑部:《塔皮埃斯答〈世界美术〉问》,《世界美术》,1988年第2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