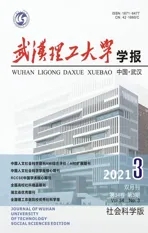社会无意识理论视域下消费异化的成因与规避*
2021-03-06袁罗牙
袁罗牙
(江西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南昌 330098)
身跨弗洛伊德与法兰克福两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希·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分析论引入社会领域,又自视为马克思学说补入了心理因素,创建了“社会心理分析”思想,弗洛姆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披露了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以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为视域,从社会的过滤与消费者的心理认同,探究消费异化的成因与规避是很有价值的。
一、 社会无意识之内涵
弗洛姆认为,在精神分析论中,没有比对无意识的发现更为重要的,但不满意弗洛伊德将无意识限于个体与生物学,指出“理解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1]弗洛姆又自认为,与弗洛伊德相反,马克思立足于异化时代,钟爱于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忽视了行为人的内在心理,指出“正像不了解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就不能理解相应的心理现象一样,没有关于心理机制的基本知识,也就不能理解社会现象。”[2]180依据需要,弗洛姆将弗洛伊德思想和马克思学说做了融合,创建了“社会心理分析”思想,在无意识理论上表现为从个体、生物性向社会、文化性转变。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内容是受到压抑的个体原始欲望和本能冲动,在弗洛姆看来,无意识内容是受到压抑的对社会事物的真实反映,是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3]93
对于社会无意识的形成,弗洛姆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其一是社会过滤器的过滤。在弗洛姆看来,什么是意识,什么是无意识,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以及该社会所产生的感觉和思维方式。任何特定的不合理的社会必然不允许社会成员的某些感觉和思维成为意识,要求将它们置于无意识层,为达此目的,社会需要过滤器对这些感觉和思维进行过滤,“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当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时,这个‘社会过滤器’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这时,那些不需要必然留在潜意识的东西便可能成为意识上的东西。”[4]凡是社会允许的感觉和经验都能够顺利通过过滤器上升至社会意识层,那些处在社会无意识层的感觉和经验则难以通过过滤器,即使侥幸通过也是历经改装、文饰过的。社会无意识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原来属于社会意识的内容由于新社会的压制可能成为无意识,而先前的社会无意识内容由于新社会的解压可能成为社会意识。
社会无意识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个体对孤独和受排斥的恐惧与焦虑,不允许意识到自己的感觉和思维与社会思维、文化模式相冲突,对于这些感觉和思维,或者顺应社会的压制,或者利用内化的方式自行化解,弗洛姆在此考虑的是社会无意识形成的心理机制。基于人的相关性需要,个体必须与他人发生关联,畏惧孤独与受排斥,“正是对孤立与排斥的这种恐惧,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对阉割的恐惧’,使人们压抑了对那些被禁忌的事情的认识。”[3]132而“只要我顺从国家权力、教会权力或公意,我就会感到安全和有保障”[5]。社会、大众对于个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个体对社会、大众所宣称的事情熟视无睹,全当真理接受,尽管他的感觉和思维告知整件事情是并非如此。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探究了社会的发展规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决定性地位,但没有说明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认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之间存在多层中介结构,社会无意识正是中介结构之一,其功用表现为,社会借助有效的过滤器对人们的感觉和思维进行过滤,将人们的部分感觉和思维转换成无意识,使人们形成适合社会要求的性格,进而维持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
二、 消费异化之成因
(一) 社会过滤器的过滤
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品种与结构的复杂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普及,消费对于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资本拥有者在趋利动机的支配下,关心的焦点从怎么扩大生产转向如何刺激消费。为了获取利润,资本拥有者不但制造物品,而且制造消费欲求,要求大众把消费当成唯一生活方式,把购买和使用物品变成一种宗教仪式。
资本拥有者刺激消费,即“制造欲求”给消费者,秘诀绝不是改变消费者的肉体结构,而是改变消费者的心理结构——对消费品、消费行为的意识,致使“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6]在制造消费欲望过程中,资本拥有者须要对大众灌输、宣传虚假消费意识,这就需要与早期资本主义不同的过滤器,大众传媒和银行信贷是过滤消费理性,鼓噪虚假意识的有效机制。借生产、复制、迎合消费主义文化,大众传媒和银行信贷尽情地过滤“不必要的”、“无用的”思考和疑问,成为判定消费什么、怎么消费是有身份、有品位的标准,消费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文化的洗脑,成了无知的婴儿,愿望是消费“更多”、“更好”、“更奇”、“更有意义”的物品。
广告是消费主义文化传播的首要媒介。在当下繁茂的物欲时代,对外在的商品,消费者只知道操纵或消费,对于商品的来源和性质一无所知,不得不依赖于广告。而在消费主义文化实践中,广告对商品信息的告知功能退化,时刻用花言巧语、消费时尚、意义暗示等诱导消费者接受并不需求的物品,人们“正在消费一种由广告公司炮制出来的假象”,“消费基本上是对人造幻觉的满足,是一种与我们具体的、真实的自我相分离的幻想”[7]。广告把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赋予商品,将商品的物理属性与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巧妙地整合在一起,“许多广告几乎不提供任何信息,而是用形象化的描述来代替。”[8]“资本主义‘挖空’了产品的真实意义,与此同时,广告把自己的意义灌注进去,填满了那些空壳。”[9]借助与推销的商品有关或无关的形象操纵大众的欲望和趣味,广告使人浑然不觉地沦为社会控制的奴隶,“我消费,我自由”无非证明了控制方式的有效性。
银行信贷迎合了消费者新欲望的产生,因为“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己的欲求。”[10]信贷大众化绝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超前消费。超前消费实际是一种“异化”文化,因为信贷消费文化制造了一种假相:由物质约束造成的社会差异得以夷平,消费者瞬间获得了身份大解放,而问题在于,信贷毕竟是一种向未来借取的时间和空间,在无度消费物欲中追求的自由加剧着对人的未来时间、空间的挤占,消费者成了物品消费和符号消费的奴隶。人是渴望幸福的,资本拥有者把消费主义幸福观灌输到商品当中,使得消费者天真地以为,购买了某种商品,不仅是占有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拥有了幸福,该幸福观实际是建立在金钱和物对人的奴役基础之上,而奴役总是意味着异化,意味着人的本质向外抛出。
(二) 消费认同心理
从心理层面看,相关性需要是人的迫切需要,人害怕孤独,注定了人需要追求认同。“认同”有两层含义,即同一性和独特性,相似性与差异性是“认同”的两个面。“定义自我意味着找到我与他人的差异中哪些是重要的有意义的。”[11]在传统社会,人们通过臣服于他人、团体或者统治他人实现认同,在现代社会,个体往往借助消费认同来摆脱因孤独与受排斥引起的焦虑,“人的认同和消费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体现为认同支配了消费,消费体现了认同。”[12]消费认同指人们借助消费,即怎样消费和消费什么来表达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从而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和归类,是消费异化的重要成因之一,主要表现为消费的符号化和“意义”化。
在传统社会,法律、社会习俗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所使用的物品,物品的符号、意义有着特定的服务对象,特定的符号所具有的特定意义专属于特定的人。在现代社会,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被打破,不同阶级之间的区隔淡化,物品的使用不再受到法律、社会习俗的限制,消费越来越成为人的身份、社会地位的确认方式。“生产方式往往是碾平差异,把空间和时间压缩,但这却为消费方式的差异制造了相遇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消费在不断制造新的差异和不同的认同。”[13]如此,物品的使用价值逐步退却,符号价值跃升至第一位,以至鲍德里亚作出结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14]无视消费者的消费认同心理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再创造是有失偏颇的。
人内心的消费认同产生的消费需求决定消费行为,而消费行为借助内化方式容易把赋予物品的符号意义转化成对消费主体自身的意义。当商品本身已经超越使用价值,更多地被赋予满足消费者内心需求的意义时,消费对于消费者的价值便成了一种心理体验,消费认同就绝不是主体自主、理性的认同,而是成了努力且需要更加努力加以捍卫的目标,正如萨特所说,“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都像中产阶级那样生活”。一旦消费者将商品的符号价值内化为不同个体的共同属性,消费又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选择,消费认同就演变成了人们无意追随的社会规范。消费者借助消费告知社会“我是谁”,借助对特定物和服务的占有来改变、提升、炫耀自我主体的特质,“当我们消费物品时,我们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我们自己。”[15]这种在“我是我,因为我拥有X”理念中寻找自我灵魂、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愿望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我认同过程,是借助对象化客体的实践过程。“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16]简言之,主体在有意识地实现自我理想的实践过程中,经由“物”来确证自身本质是必要的,物是人确证主体本质力量的基础,个体通过对象化出去的“物”彰显与他者的差异,“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7]而以消费建构的认同完全赖于“占有”的物及其符号,消费认同对于“我是谁”、“我将是谁”的回答本质上是人受到物与符号的奴役表现。
三、 消费异化之规避
健全的人希求成为自己所理想的而不是社会所要求的人,在消费上遵照自己真实、自主的需求而不是外在刺激制造的欲求,然而,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无时不在资本的算计中。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模式不仅大批量生产物品,而且利用文化、信贷资本对经济资本的屈从,生产为资本利润服务的消费文化:将大众的人生意义单一化为对物的占有,宣传生活的幸福与对物的占有正相关,“我们很满意于无用的占有。……所有这些都说明:不是使用而是占有才带来愉快。”[18]为消费品制造各种象征符号,将符号蕴含的意义内置消费者心理,使消费者确信消费了物品,便拥有了符号所承诺的意义。
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个体消费的内容和方式看似遵照自我的需求和兴趣,然而,透过个体间千差万别的消费选择将会看到,个体的消费意向总是“意向”于社会指向的消费理想,个体的消费取向总是“取向”于社会的消费导向,个体的消费认同总是“认同”于社会的消费规范。如果个体偏离社会需求与规范进行消费,就会被斥责为失去公共形象或者给贴上不能接受的标签,如“不正常”、“神经症”等,即被“污名化”。为了摆脱消费异化,消费者必需对消费主义文化进行知识性解蔽,勇于去触礁社会无意识内容,将深层的内在经验作为一种“反抗意识”呼唤出来,使之成为意识的常态经验。
承继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精神,弗洛姆的社会无意识理论揭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虚假性与奴役性。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多数人易于执着于不现实的、社会过滤后的范畴,受着所谓“常识、专家意见、广告”因素的制约,在强大的文化意识形态面前怡然屈膝。弗洛姆揭示,这种“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规性、公众舆论”[2]222的权威是匿名性的,但较公开权威的危害更大。反思工业资本主义的富足物质与大众文化的锁链,弗洛姆诉求于“不从”进行抗议,抗议人所信仰的技术理性、大众舆论与陈词滥调,呼吁让人压倒一切,要求人们顺从内心的理性与信念,在消费上做到自主理性,注重消费的质而不是量,注重可持续消费而不是不顾自然生态而一味追求物欲的满足。
在弗洛姆看来,健全的社会应该视人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应服务于人,他给出了实现健全社会、自由人格的“爱”之方案。弗洛姆说的“爱”是创发性的,乃是“保全个体的个性,整体性的结合。……爱使人克服孤独感和分离感,然而又让他仍为自己,依然伫立于其整体性中。”[19]基于人道主义,弗洛姆注重意识革命、心理革命,故而被斥为诵经布道的传道士,他的思想被指控背弃了马克思学说的本真。批判的武器当然替代不了武器的批判,然而,撇开理论的人道主义基础,社会无意识理论要求还原人的本真状态,在消费上追求人的生存与发展,无不展示出弗洛姆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的关怀,理论的深刻性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