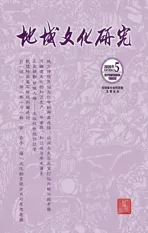国内“苏武研究”述论
2020-11-30
“苏武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传统课题,目前在海内外学界、文化界已成为一个显著的学术热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1980年至2019年间,中国大陆地区(知网显示)直接涉及苏武研究的各类文章达200篇(部),间接涉及苏武的文章超过500篇,此外还有历史学(文化史、思想史)领域数量可观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可谓蔚为壮观。但若以严格的学术标准看,除了史料征集、整理这一块外,真正创新性成果并不多,因而“苏武研究”本身就是个值得反思的课题。
由于苏武(前140年—前60年)生平的传奇性和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历来从事苏武研究的,既有专业人文历史学者,也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民间学者和文人,这其中不少是来自苏武家族后裔成员。这样,所谓“苏武研究”也就不再是一个纯粹历史学的课题,而扩展为了广义、繁复的“苏武书写”。
一、“苏武研究”回顾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不论是史学领域纯学术性的“苏武研究”还是呈百花齐放态势的“苏武书写”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在苏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以苏振武教授主编的《苏武研究文丛》①苏振武教授主编的《苏武研究文丛》第一部《历史苏武:史书有关苏武文献研究》已于2020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丛》的第二部至第四部也将于年内出版。等为代表,史籍、史迹方面的史料征集已近于穷尽。
一是史料征集、整理和苏武研究史总结方面的推进,也包括对“苏武牧羊”史实的考辨、考古研究等,所获成果相当可观。史料搜集以陕西苏振武教授亲撰和主编的系列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如上述《苏武研究文丛》之一的《历史苏武:史书有关苏武文献研究》等。
二是在史迹考古方面,任继周等著《苏武牧羊北海故地考》①任继周、张自如、陈钟:《苏武牧羊北海故地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期。一改传统认识,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提出苏武牧羊地实为古白亭海地区(今甘肃省民勤县北部石羊河尾闾),而非贝加尔湖地区;而刘振刚博士在《苏武与白亭海关系的疑案》②刘振刚:《苏武与白亭海关系的疑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中又提出新解,他认为武牧羊地既不是贝加尔湖周边也不是白亭海一带,而是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的荒原。上述二文观点值得重视,实际上已使苏武牧羊地成为一桩历史悬案,考辨、确认苏武牧羊地究竟位于何处,这便将一个新的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三是基于汉民族正统理念、国家大义观、忠君爱国立场,将苏武作为民族英雄和儒家思想道德典范的研究与书写。这方面可谓历久弥新,其基本规律是:每遇国家民族危难时刻,苏武研究和书写(近代以来也包括文学艺术创作)便会出现——复现一个高潮。就当代而言,还是以苏振武教授的研究为代表,他的著作《苏武精神与儒家伦理》③苏振武:《苏武精神与儒家伦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及《试论苏武精神的儒学底蕴》④苏振武:《试论苏武精神的哲学底蕴》,《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等论文,将苏武精神纳入儒家思想史和总体道德观,并在论证“苏武精神已经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上,进一步弘扬其恒久的思想道德价值,阐发其当代价值,实现了对气节、民族、忠君、英烈一类传统历史叙述和学术话语的超越。
本文之所以用了“书写”一词,是因为与上述学术论著相关,还产生了大量类似于“颂辞”“赞辞”式的文章,其总的价值取向就是表彰苏武“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节操坚贞”,或基于此种精神品格,赞颂苏武的“人格魅力”⑤参阅安杨华《〈苏武传〉的哲学解读》,《语文教学通讯》2015年第31期。杨文缺少学术上或“哲学”的创新性,但作为“颂辞”式文章颇具代表性。,形式上介于政论、散文、学术文章之间,水平参差不齐,良莠并存,多为民间写作,且多为重复写作(其中一部分实属粗制滥造,其学术性、文学性皆可疑)。但这些文章大多刊载于面向青少年读者的教育类报刊上,对普及历史知识、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还是发挥了实际作用的。
四是异文化交往和政治外交视角的研究,如朱健《从斯托雷平想到苏武》⑥朱健:《从斯托雷平想到苏武》,《读书》1993年第12期。,王庆宪《西汉与匈奴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⑦王庆宪:《西汉与匈奴频繁密切的使节往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丁瑜《从〈平家物语〉苏武故事看日本中世纪的武士道精神》⑧丁瑜:《从〈平家物语〉苏武故事看日本中世纪的武士道精神》,《湖南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论文,这类论著将近代以前基本囿于历史范畴的苏武研究推向了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因而愈加宏阔高远。
五是苏武氏家族史研究的多视角展开,如前述苏振武教授的有关著述及《苏武研究文丛》的第三部《谱牒苏武:家世脉衍与名人评传》等。
六是针对国内学界已有苏武研究的批判式思考和研究,即“研究之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刚开展起来,大多为有关论著间接涉及,因而不成规模,真正有力度有深度的文章不多,待拓展的学术空间十分可观。比如,王渭清的《从历史苏武到文化苏武——苏武精神辨析》,就帮助我们厘清了苏武研究史的主要脉络和当下研究踽踽不前的症结所在。王文认为,纵观《汉书·苏武传》以来近两千年的苏武书写史,作为知识形态的“苏武”经历了由“历史苏武”向“文化苏武”的转换;“历史苏武”研究旨在“求真”,“文化苏武”则指向“求善”,二者皆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王渭清:《从历史苏武到文化苏武——苏武精神辨析》,《传承》2013年第12期。。而笔者以为,在王文所谓“文化苏武”(以及苏振武教授等知名学者论说中的“文化苏武”)还隐含着一个政治权力化——意识形态化的“苏武”。
最后,还要看到苏武题材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成绩。自苏武生平事迹被记入《汉书》之后,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们以苏武为题的文学咏颂和艺术创作就从未间断。近现代的创作高峰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傅抱石先生的国画《苏武牧羊》②傅抱石先生的国画《苏武牧羊》创作于抗日战争关键时刻的1943年,画作中的时代氛围十分明显。、顾毓琇先生的话剧《苏武》③顾毓琇先生的话剧《苏武》1943年11月18日于重庆首次公演,后收入《顾毓琇全集》第二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便是其佼佼者。最近40年来,虽说国家民族的总体处境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出于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需求,还是产生了大量苏武题材的绘画、音乐以及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作品,如果算上民间创作,那数量可以说是难以计数。近年来就有长篇小说《苏武父子传奇》(李树林著)④李树林:《苏武父子传奇》,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苏武牧羊》(林仑著)⑤林仑:《苏武牧羊》,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年。,天津人艺的集体创作话剧《茂陵封侯》,陕西省歌舞剧院推出的大型原创歌剧《大汉苏武》,河南豫剧《苏武牧羊》,京剧《大漠苏武》等等,同时民间创作的苏武题材的音乐、书画类作品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文学艺术创作的盛况绝不亚于学术研究。
以上虽然只是近几十年苏武研究与书写的概况,却可看做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学界、文化界总体苏武研究与书写的一次总结。我们首先看到了成绩,但又不能不严肃地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则,苏武研究必止步于当下难有新进展。
苏武研究无疑属于历史学研究范围,因此它应服膺于一般历史学研究的规则和要求。那么历史学的根本原则和终极目标是什么?柯林武德曾言:
“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大家都认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是,他应该认识自己;在这里,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其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认识你自己还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他已经做过什么。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⑥(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8页。
可以确信的是,这里的“人”“他”“你”等概念,意味着历史上的个人、群体、阶级阶层、民族、种族、人类。而“认识自己”“人是什么”“人能做什么”等,则表明历史研究终将而且必须提升到哲学高度,必须用理念、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等最高价值标准衡量自己。
这便是何兆武先生曾论述过的历史研究不仅需要科学、思辨理性,还需要“科学之外以至于之上的某些东西:价值、目的、理想、信念。他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畴之内,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①何兆武:《历史的两重性》,《何兆武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在另一处,何兆武先生进一步谈到,史家治史,除了科学实证、解释与理解外,“还需要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或精神贯彻始终。人文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本身就是历史和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是历史精神的核心。”②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历史研究是人的自我认识;史家不仅要具备科学精神、理性意识,还要拥有人类正义的价值取向、信念、理想,并要持守和追求最高的人文主义目标。无疑,当代苏武研究要接受这一标准的检验,今后的苏武研究也必得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行才能有突破。这让笔者自然想到已故张中行先生发表于《读书》杂志1993年第8期上的文章《读〈汉书·苏武传〉》。张先生正是遵循上述原则,“由人文主义的角度看”《汉书·苏武传》,对“历史苏武”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再次否定传统中国通行了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制的“忠君思想”,并由此对某些“颂辞”式苏武研究给予批判③参阅张中行《读〈汉书·苏武传〉》,《读书》1993年第8期。。该文恰恰映鉴出当代苏武研究的主要问题:观念保守,视域狭窄,理论方法陈旧,缺少创新和超越,史学研究和文艺创作自我重复现象较为严重。
二、未来“苏武研究”展望
第一,立足于全球化视野,深入思考“历史苏武”、“文化苏武”在文明互融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启示,揭示作为历史存在的苏武的当代意义。
第二,历史(史料、遗迹)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拓展,如对苏武牧羊地的确证等,这项工作恐怕需要中、蒙、俄学界的合作才能完成吧。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工程的顺利推进和中俄经贸文化交往的密集密切,涉及苏武的贝加尔湖周边考古工程亟待启动,若能顺利推进,或将苏武研究推升到一个新水平(这方面空白点很多,而且新学术研究的连带效应是不可估量的,如推动旅游业和旅游文化建设等)。
第三,立足于当代学术前沿,基于比较历史学、比较政治学、比较文明论视角的研究,如与苏武相关的东北亚民族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学研究等。
第四,自汉以来,苏武书写史、研究史、形象史的批判式总结与研究(立足于当代史学精神,基于人文理想的反思和批评)。
第五,苏武家族史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展开,但处于零散状态,在深度广度上远远不够。中国历史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某些文化精髓往往通过几个从未断绝的文化大家族代代传承,苏武家族传承的是什么?这方面有待深探,也可以做家族史的横向对比研究。
第六,作为“人”的苏武形象建构和人文内涵拓殖,这是一项必须通过跨学科比较研究才能完成的任务。
第七,努力开拓以苏武为对象的文艺创作的新境界。作为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苏武,历来就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资源。艺术领域绘画音乐一以贯之,文学上古代以诗词为主歌咏塑造苏武,现当代加入了小说、戏剧,还有大量的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但这些作品中精品极少,绝大部分属于重复写作,而苏武形象的深广历史内涵,比如其蕴含的人文思想和深重悲剧性,从来没有被挖掘表达过。这一方面是受时代环境所限,但主要是与写作者的视野、能力、境界直接相关。
审美创造能推进人类的理性认识,提升人的思维境界,这已为很多艺术家的实践所证实,也为许多历史学家的审美性写作所证实,如柏拉图对历史人物苏格拉底的塑造,普鲁塔克对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的书写等,对后世的启示超过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成功的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必是塑造了鲜活、真实的历史形象,必赋予历史人物、事件以新的精神内涵,比如莎士比亚戏剧(历史剧和部分悲剧),高尔基对列宁、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历史人物形象的再创造,郭沫若对屈原和曹操形象的重塑等,已大大促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甚至拉动了历史研究本身的进步。当然,这首先要求那位创作者要具备与时俱进乃至超于时代的科学精神、求真意志和人文主义理想信念。
有鉴于此,我们期待着睿智的艺术家们能重拾“历史苏武”这份珍贵资产,发挥审美认识审美创造之威力,超越“文化苏武”,创造出活生生的既贴切历史本真又着附理想光芒的“人文苏武”像。
哲学家罗素(1872—1970)同时也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主张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研究,除了要在事实、史料、文献资料上做到翔实穷尽,还要有志于发现那些有限历史内事件间的内在联系(所谓规律或相对真理),总结人类实践的真知和智慧,努力将人类引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此即何兆武先生所说的历史研究的理想、信念、信仰)。而作为艺术的历史(研究和书写),则一定要讲究趣味性,史学家要在本人个性气质基础上形成独特的风格,可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倾注个人感情(直书爱与憎),运用激情创造历史文本;同时也要讲究文字表达上的“文学技巧”,甚至需要发挥一下“丰富的想象力”,唯有那“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历史学,才能将人类全体引向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一个比过去任何存在过的世界都更加美好的世界”。①罗素:《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载(英)汤因比、罗素等著,张文杰编译《历史的话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9-176页。
笔者认为,“苏武研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课题,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今后苏武研究和书写要注意挣脱权力话语、儒家道统和意识形态的拘束,相关创作也要力求避免堕入自我玩赏和重复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