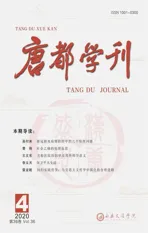朝鲜林椿散文与中国文化之关联考论
2020-10-09王成
王 成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林椿(生卒年不详),生活时间大致在高丽毅宗(1147—1170年在位)、明宗(1171—1197年在位)。他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林仲平、父亲林光庇都曾在朝廷为官。到了林椿之时,因武臣政变,家道衰落。据《高丽史》卷15《列传》载:“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鸣世,屡举不第。郑仲夫之乱,阖门遭祸,椿脱身仅免,卒穷夭而死。仁老集遗稿为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于世。”(1)参见郑麟趾等《高丽史》,首尔大学校奎章阁馆藏本。林椿的创作得到后人一致的赞誉,朝鲜肃宗时期崔锡鼎(1674—1720)《林西河集重刊序》言:“林西河耆之先生,生负绝艺,大鸣于世,文苑之评,谓得苏长公风格”[1],李仁老《西河先生集序》曰:“先生文得古文,诗有骚雅之风骨,自海而东,以布衣雄世者一人而已。”[2]209林椿的散文创作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一、引经据典,以中国文化典故来议论、说理
按高丽科举制度,像林椿这样的功勋之后可以不经过科考而进入仕途,但以才华自恃的林椿并没有选择这种方式,他并不想借助父亲林光庇的权势而走上仕途,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心境:“仆自幼不好他技,博奕投壶、音律射御,一无所晓。唯读书学文,欲以此自立。”[2]244别无他好、只嗜好读书为文的林椿,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扬名显身,“而耻籍门户余荫,以干仕宦,故先君柄用时,岂求取禄利、以为己荣哉?”但现实是残酷的,林椿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并未因富有才华而科考中榜。
希望被赏识、得到有识之人相助是林椿一直的渴求,他曾多次引用这类事典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赵胜之门,虽未作请行之毛遂。孔融之表,遽已为被荐之祢衡。毫发身轻,丘山恩重”[2]263,此处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毛遂自荐于平原君赵胜,出使楚国,促成楚、赵合纵,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一是孔融向曹操推荐好友祢衡。自荐需要有能赏识的人、有知己才有意义,林椿在《谢金少卿启》中写道:
伏念某,一曲之士,三尺之童,弧矢射天地四方,早怀壮志,锦绣为心肝五藏。未负奇才,久对扬黄卷之圣贤,犹未得青云之岐路。伤足泣泪,自贻献宝之疑。斫鼻成风,谁识运斤之巧。我辰安在,自进诚难。以此痛心,不遑宁处。虽将寸管,愿瞻乐广之云天。犹冒覆盆,未睹仲尼之日月。[2]263
“斫鼻成风,谁识运斤之巧”典出《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墓地,他对身边跟从的人讲述发生在郢人、匠石、宋元君之间的故事,庄子以石匠的故事表达了知音难求以及对好友怀念的心情,慨叹惠子死后,他再没有可以谈话的知己了,“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3]。林椿引此典要表达的是,没有真正识得自己才华的人,如同庄子痛惜好友惠子之死一般。
林椿又引用了乐广的典故,乐广为西晋名士,出身寒门,早年即有重名,受卫瓘、王戎、裴楷等人欣赏,得以步入仕途。卫瓘曾称赞他“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4]林椿希望能得到赏识,如同见到乐广一样,拨开乌云见到太阳。但自己犹如顶着覆盆,无法沐浴到圣人孔子的光芒。“覆盆”,语出晋葛洪《抱朴子·辨问》“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5],谓阳光照不到覆盆之下,后因以喻社会黑暗或无处申诉的沉冤。
林椿多次向人言及自己的穷困以及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仆自遭难,跋前踬后,隐匿窜伏,投于人而求济者数矣,皆以犬彘遇之而不顾。故居京师凡五载,饥寒益甚,至亲戚无有纳门者,乃挈家而东焉”[2]248。他在《与赵亦乐书》中还把自己与古代贤人的穷厄相比较,“嗟乎!自古贤人才士例多穷厄矣,而无有如仆者。子美之流落,韩愈之幼孤,挚虞之饥困,冯唐之无时,罗隐之不第,长卿之多病。古人特犯其一,而亦已为不幸人。仆今皆犯之,岂不悲哉!”[2]246杜甫、韩愈、挚虞、冯唐、罗隐、司马相如等都有不幸的经历。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韩愈3岁时,父亲去世,由兄长抚养长大。后兄长病亡,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挚虞曾流离到鄠、杜地区,粮食断绝,以橡子充饥,最终清贫饿死;汉武帝求贤时,冯唐已年过古稀,后世文人常用冯唐之典来比喻老来难以得志;罗隐应进士试,断断续续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史称“十上不第”;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患有消渴病。林椿认为自己相比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吴郎中启》是林椿写给吴启的一封信,全文一千五百余字,几乎全篇用典,引用中国历史、文化典故达近百处,显示出林椿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谙,同时这些典故的运用也使他的表达、诉求显得真诚,合情合理。现录几段文字于下,以见其实。如开篇曰:


这段文字所引都是士子受礼遇或士子因受举荐而最终发迹的典故,这也是林椿一直希望能遇到或者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因为自己就如同那些历史人物一样,勤学苦读,“早乐父兄之训,切勤翰墨之功,童而习之纷如,谩自勤于昼夜”。但由于没有遇到真正的伯乐,自己又“宁误身于儒冠,耻藉荣于门荫”(7)参见《上吴郎中启》。,所以蹉跎至今,受到世人的不解、唾弃。但是“燕雀焉知鸿鹄志四海九州,骐骥不与驽骀争一日千里”(8)参见《上吴郎中启》。,“燕雀”句典出《史记·陈涉世家》,“骐骥”句典出《荀子·劝学》。林椿对于他人的不解是不屑的,自己甘心“慨然抱璞,翘以待求”(9)参见《上吴郎中启》。。在他看来,这些人就如同燕雀、驽马,是不知道鸿鹄之志、骐骥能一日千里的。
林椿写家庭遭遇的变故以及自己的心情时也运用典故来作衬托:“曩者因其积衅之所萌,忽尔私门之发祸,遭家不造,叫天无辜,以有涯之生,罹不测之患。抛戈泣血,方衔桓氏之冤。陟屺兴悲,继有魏人之苦。何中散之途穷,信贾生之命薄。闭门却扫,绝交游而远谗。丐食假衣,携细弱而避地。一涯流落,几度寒暄。迺遑遑而无归,常郁郁而居此。久类虞卿之羁旅,谁怜令伯之零丁。”家门惨遭横祸,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作者用了一连串的历史典故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桓彝被杀,其子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10)参见《晋书·桓温传》。。作者引用这个典故,表达了对造成家祸之人的愤慨。《诗经·魏风·陟岵》有诗句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后以“陟屺”为思念母亲之典,林椿引此典故传达出对母亲的思念。嵇康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向往出世的生活,一生穷顿。贾谊曾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是失意士子的代称。不幸遭遇使林椿“闭门却扫,绝交游而远谗。丐食假衣,携细弱而避地”(11)参见《上吴郎中启》。,常常遑遑无归、郁郁寡欢,就像羁旅的虞信、丧母的李密。不幸的处境、遭遇,使林椿产生了回归田园的心愿,他说:“乐潘岳田园之居,输阮籍黍稷之税。凿而饮,耕而食,但虚老于太平。用则行,舍则藏,无苟容于斯世。于焉养志,不复有求。”[2]265“凿而饮,耕而食”语出汉代王充《论衡·感虚》“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6];“用则行,舍则藏”语出《论语·述而》,这几句话连用潘岳、阮籍、《击壤歌》《论语·述而》等典故抒发心志。
林椿几乎篇篇引用中国文化典故,如他恭贺李奎报高中状元时说:“武帝读相如之赋,喜于同时;明皇闻李白之才,召而亲见。朝纔缀行于桂岭,夕必待诏于玉堂,选士以来,唯公而已。”[2]271《汉书·司马相如列传》载:汉武帝读《子虚赋》,大加赞赏,感慨自己不能与作者同时。后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唐玄宗读了李白的诗赋后非常欣赏,召李白进宫,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李白面前,并亲手调羹。后多用作皇帝赏识臣下之典。林椿引用此二典,不仅表达出对当今贤明君主的赞扬,善于取才,也对李奎报能“首登优第”,并“位伫登于廊庙,使闻风而大振,为儒者之极荣”充满艳羡,反观自身的遭际,心情可想而知。再如《上安西大判陈郎中光修启》中的典故引用,“闻循吏善政之风,其惟良二千石也,使游民不耕而食,故取禾三百囷兮,不有仁人”[2]272,语句化用《诗经·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伐檀》诗歌原意是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讽刺,林椿在此反用此典,突出陈光修的循吏善政,能使民丰足安乐。
受韩愈《毛颖传》及《下邳侯革华传》的影响,高丽文坛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假传”。所谓“假传”,是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为动植物、日常用品等立传的文学形式。林椿作有《麴醇传》《孔方传》两篇假传,二文在介绍传主籍贯、世系、生平经历等背景时大多采用典故。
《麴醇传》云:“麴醇,字子厚。其先陇西人也。九十代祖牟,佐后稷粒蒸民有功焉,《诗》所谓‘贻我来牟’是也。牟始隐不仕曰:‘吾必耕而后食矣。’乃居畎亩。”[2]259“牟”又作“麥牟”,即大麦。醇酒是用麦子等酿造出来的,所以说麦为醇之祖先。《诗经·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酎”“醇”都是味道醇厚的酒,分别作为主人公及其父系的名字。
至魏初,醇父酎,知名于世,与尚书郞徐邈偏汲引于朝,每说酎不离口。时有白上者:“邈与酎私交,渐长乱阶矣。”上怒,召邈诘之,邈顿首谢曰:“臣之从酎,以其有圣人之德,时复中之耳。”上乃责之。及晋受禅,知将乱,无仕进意,与刘伶、阮籍之徒为竹林游,以终其身焉。[2]259
语段中提及的几个人物都以爱酒闻名于世,如徐邈,“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7]刘伶、阮籍与嵇康、山涛、向秀等人结社饮酒作诗文,号称“竹林七贤”。刘伶作有《酒德颂》,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
《孔方传》也运用了大量典故,如在描述钱币的使用历史时,作者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列举历史上重视钱币的人物,如吴王刘濞、汉武帝、和峤、刘晏、王安石等;另一方面举出历史上轻视甚至主张取消钱币的人物,如汉元帝、贡禹、鲁褒、王夷甫、司马光等。
时吴王濞骄僭专擅,方与之为利焉。虎帝时海内虚耗,府库空竭。上忧之,拜方为富民侯,与其徒充盐铁丞仅同在朝,仅每呼为家兄不名。方性贪污而少廉隅,既总管财用,好权子母轻重之法,以为便国者不必古,在陶铸之术尔。遂与民争锱铢之利,低昂物价,贱谷而重货,使民弃本逐末,妨于农要,时谏官多上疏论之,上不听。方又巧事权贵,出入其门,招权鬻爵,升黜在其掌,公卿多挠节事之,积实聚敛,券契如山,不可胜数。其接人遇物,无问贤不肖,虽市井人,苟富于财者,皆与之交通。所谓市井交者也,时或从闾里恶少,以弹棋格五为事,然颇好然诺,故时人为之语曰:“得孔方一言,重若黄金百斤。”[2]260
孔方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富民侯”,总管财务,权倾一时,有“得孔方一言,重若黄金百斤”之语。汉元帝时期,孔方“蠹国害民”,使得“公私俱困”“贿赂狼藉”,终被朝廷驱逐。
二、林椿“文气”观、“诗乐”观与中国文学思想
林椿作为高丽文坛大家,对文坛发展有着深刻的体悟、认识,如他对高丽文坛模拟苏诗现象的认识。林椿生活的时期,正是宋诗风盛行之时,学苏轼、仿苏轼是文坛主流,是一种时尚,并且,不学好苏轼诗文也很难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李奎报《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曾言:“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时所尚而已。然今古以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者也。岂以属辞富赡,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匮故欤。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8]515李奎报指出了当时社会对苏轼诗文的推崇程度,苏轼的文集成为高丽文人创作的典范。徐居正《东人诗话》云:“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二东坡出矣。’高元间,宋使求诗,学士权适赠诗曰:‘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千古芳名不可焚。’宋使叹服。其尚东坡可知也已。”[9]185这里所说的“高丽文士”包括朝廷文人,也包括备考学子以及一般诗坛文家。可见在高丽科考中苏轼诗文已成为必读之书目。
林椿曾写信给李奎报,阐释了自己对于苏轼诗文的认识,《与眉叟论东坡文书》中说:
仆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伏膺呻吟?然徒玩其文而已。就令有挦摇窜窃、自得其风骨者,不亦远乎?然则学者但当随其量以就所安而已,不必牵强横写,失其天质,亦一要也。唯仆与吾子虽未尝读其文,往往句法已略相似矣。岂非得于其中者暗与之合耶?[2]242
林椿指出了苏轼诗文盛行于世的客观事实,同时也指出存在的弊端,即只是学习其形式,“徒玩其文”,模仿其形而不得其神,所以他提倡“自得”,通过“自得”而得诗文之“风骨”,不失诗文之“天质”。所谓“自得”即不“牵强模写”、不“挦摇窜窃”。林椿认为自己和李奎报的诗文是“自得”之作,未尝读苏轼诗文,却做到了句法相似,“岂非得于其中者,暗与之合耶”。林椿所谓的“未尝读其文”当指没有刻意模仿苏轼诗文,而不是不读苏轼诗文。
作为高丽文坛大家,林椿对文坛的认识,不仅仅体现在关于苏轼诗文、地位等认知上,还体现在他关于“文气”观、“诗乐”的诗学理论命题的阐释。
(一)林椿“文气”观对中国文学思想的接受
自曹丕将“气”引入文学批评中,“文”与“气”的关系就成了历代诗家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韩愈、苏辙等人在继承曹丕“文气”观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见,如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分文章风格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指出这几种文风都是因作家不同的才、气、学、习而形成,作家的气是根本性的。韩愈《答李翊书》也论及文气与作家道德修养的关系,韩愈认为作家的思想道德如果得到提高,培养出旺盛的正气或浩然之气,文章也就可以写好了。苏辙认为“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为文应该追求疏宕平淡的文风、抒发不平之气。
韩国古代文论也频繁讨论“文”与“气”的关系,如高丽李奎报《论诗中微旨略言》曰:“夫诗以意为主,设意尤难,缀辞次之。意亦以气为主,由气之优劣,乃有深浅耳。然气本乎天,不可学得。故气之劣者,以雕文为工,未尝以意为先也。”[8]524李奎报突出了“气”在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但也走上了形而上的道路,他认为“气”本于天,人是不可学得的。晚于李奎报的崔滋《补闲集》(卷中)说:“诗文以气为主,气发于性,意凭于气,言出于情,情即意也。”[9]111崔滋认为“气”是文学创作的动力。李奎报、崔滋关于“文气”关系的论述,过于理论化,没有具体的指向性,这必然会增加理解的难度,也不利于学习者学习。
林椿也探讨了文学创作与“气”的关系,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他在《上李学士书》《上按部学士启》中曰:
文之难尚矣,而不可学而能也。盖其至刚之气,充乎中而溢乎貌,发乎言而不自知者尔。苟能养其气,虽未尝执笔以学之,文益自奇矣。养其气者,非周览名山大川,求天下之奇闻壮观,则亦无以自广胸中之志矣。是以,苏子由以为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于人见欧阳公、韩大尉,然后为尽天下之大观焉。[2]243
文以气为主,动于中而形于言,非抽黄对白以相夸,必含英咀华而后妙。历观前辈,能有几人?子厚雄深,虽韩愈尚难为敌。少陵高峭,使李白莫窥其藩。圣俞身穷而诗始工,潘阆发白而吟益苦。贾岛之病在于瘦,孟郊之语出于贫。至如以李贺孤峰绝岸之奇,施于廊庙则骇矣。虽张公轻缣素练之美,犹得江山之助焉。才难不其然乎?贤者足以与此。[2]268
林椿指出,文学创作是复杂而难以言说的事情,一个作家想要创作出一部作品,就必须培养出“至刚之气”,做到“充乎中而溢乎貌,发乎言而不自知”。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家内心深处刚健之气的结果。如果作家能养其气,即使没有模仿他人,文章也自然能有自己的风格,“文益自奇”。那么,如何养成这种可以使文章“自奇”的“气”呢?林椿认为需要遍览名山大川,观览天下的奇闻壮观,这样做的话,就可以“广胸中之志”了。
“苏子由以为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以下几句化用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10]《上枢密韩太尉书》开篇提出养气与作文的关系,认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进而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苏辙结合自身经历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他非常重视人生阅历,他认为多接触自然界与现实社会,了解其规律和内蕴,提高认识,获得创作的灵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林椿引此典是为了下文做铺垫,他希望能拜见“以雄文直道,独立两朝,为文章之司命”的李知命学士,“仆常愿抠衣函丈,执弟子礼,与其门人贤士大夫,然后将以退理其文”。
“文以气为主”出自曹丕《典论·论文》、“动于中而形于言”出自《毛诗序》、“抽黄对白”出自柳宗元《乞巧文》、“含英咀华”出自韩愈《进学解》。文章开篇连续引用四个典故讨论文气关系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林椿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观并有所发挥、拓展,他连续引用《毛诗序》、柳宗元、韩愈的话语,认为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又形成文字进而成为文学创作。文学创作、鉴赏以及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下应以“气”为主,不能只求语句对仗的工稳,而是要品味、体会诗文中所包含的精华。文学作品之“气”与作者之“气”也是相一致的。气有清浊之分,作者的才性、气质也有不同。先天禀赋的区别、后天的不同经历,是决定文之高下的根本原因。由此林椿指出,柳宗元的雄深,韩愈难与之相匹;杜甫的高峭,李白望尘莫及。这是禀赋不同导致文风各异。梅尧臣之诗穷而后工,潘阆年老而愈苦吟,这是后天经历不同而使文风有异。郊寒岛瘦,也是个人气质所致;李贺的奇绝不能施于廊庙,张说的诗得江山之助而体现轻缣素练之美。
文章以气为主,如果没有“气”会变成怎样?林椿云:“仆废锢沦陷,为世所笑。屏居僻邑,坐增孤陋,学不益加,道不益进,遂为庸人矣。凡作文,以气为主,而累经忧患,神志荒败,眊眊焉真一老农也。其时时读书,唯欲不忘吾圣人之道耳,假令万一复得应科举登朝廷。吾已老矣,无能为也。”[2]245林椿“凡作文,以气为主”中的“气”,指作家精神气质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文”与作家的精神之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深深影响到作品的优劣。他以切身经历、亲身感受作为事例来阐说这一观点。1170年的武臣政变改变了林椿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命运,他屡试不第,过着窘迫的生活,靠朋友的救济勉强度日。在这种境况下,他的锐气日渐消磨,精神状态也大不如从前,写作文章的状态也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即是他所说的“屏居僻邑,坐增孤陋,学不益加,道不益进”(12)参见《与皇甫若水书》。。由此可见,精神气质、生活状态与文章有着密切的联系。林椿累经忧患,神志困怠,在这种状态下,自然无法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尽管他没有放弃读书,但目的却是不忘圣人之道,并不是真心于文学创作。
(二)林椿“诗乐”观与中国古代诗学
古代诗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诗篇都是可以合乐而歌的,诗歌与音乐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也是历代文学批评家积极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正因为诗与歌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后来就合称为诗歌。
高丽文学以汉文学为主流,文人们学习创作汉诗汉文,但对中国古乐的认知却存在一定的困难,林椿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皇甫若水书》云:
仆观近古已来本朝制作之体,与皇宋相为甲乙,而未闻有以善为乐章名于世者。以为六律之不可辨,而疾舒长短、清浊曲折之未能谐也。嗟乎!此亦当世秉笔为文者之一惑也。苟曰能晓音乐之节奏,然后乃得为此,则其必待师旷之瞽然后为耶?盖虞夏之歌、殷周之颂,皆被管弦、流金石,以动天地、感鬼神者也。至后世作歌、词、调、引,以合之律吕者皆是也。若李白之乐府、白居易之讽喻之类,非复有辨清浊、审疾徐、度长短曲折之异也,皆可以歌之,则何独疑于此乎?[2]242
林椿认为高丽文学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与宋朝文学比美也不为过,但尚未听说有以音乐闻名于世的人存在。如果无法辨识“六音”,那么就不可能知道音律的疾舒短长、清浊曲折,也就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乐章。对于音乐的不熟识,正是高丽文人的一大困惑,也一定程度上滞后了高丽文学的发展,影响了更多优秀作品的产生。但是大多数高丽文人盲目无知,都以为能知晓音乐的节奏就可以了,不需要懂得乐理。照这样的话,只有成为师旷般的乐师才能作出乐章。高丽文人还是停留在“虞夏之歌、殷周之颂,皆被管弦、流金石,以动天地、感鬼神者也。至后世作歌、词、调、引,以合之律吕者皆是也”的认知世界中,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乐府诗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白、白居易的乐府诗“非复有辨清浊、审疾徐、度长短曲折之异也,皆可以歌之”,他们的乐府诗已经不再以是否入乐为标准了,而是一种写时事的新诗体。所以林椿鼓励黄甫沆大胆去尝试,“今又于乐章,推余刃而为之”。
林椿进一步指出:“正声谐韶頀,劲气沮金石,铿鋐陶冶,动人耳目,非若郑卫之青角激楚以鼓动妇女之心也。论者或谓淫辞艳语,非壮士雅人所为。”所谓“正声”即儒家所认可的“纯正之音”,也指符合音律标准的乐声。儒家思想认为,文艺应该“发乎情,止乎礼”,必须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审美标准,为教化服务。“韶頀”,指庙堂、宫廷之乐,或泛指雅正的古乐。如果用儒家认可的纯正之声来协调庙堂或宫廷之乐,那么就可以获得“动人耳目”的效果,其“劲气”可以“沮金石”,“铿鋐”之声可以陶冶人心。但是,也无法做到“若郑卫之青角激楚以鼓动妇女之心”。也就是说,庙堂或宫廷的音乐之美,也不如郑卫的民间之乐可以悦男女之情。同时,林椿猜想会有人认为这是“淫辞艳语,非壮士雅人所为”,林椿打了形象的比喻,“然食物之有稻也粱也,美则美矣,固为常珍。至于遐方怪产,然后乃得极天下之奇味,岂异于是哉”。稻子和高粱都是美好的食物,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人们的日常饮食生活只有这两样食物是不够的,也需要杂粮特产、奇珍山货等补充、搭配,人们的口味、营养才能丰富、均衡。林椿认为庙堂之乐与郑卫等民间之乐的关系,与此是一样的道理。
诗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学家们必须学习音乐知识,懂得乐理,从而创作出更高水平的诗歌作品。林椿强调了音乐于诗歌的重要意义,无疑会对高丽文坛产生一定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上可见,林椿的散文与中国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他不仅大量引用中国文化典故来议论、说理,还对高丽文坛的现状、高丽文学的发展等有着深入的理解,他关于“文气”观、“诗乐”观等诗学理论的阐发,在继承中国诗学观点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突破,为我们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域外的审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