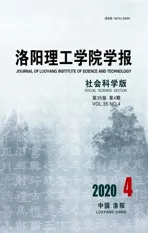释君子
——兼论孔子学说中“君子”的道德含义
2020-09-01李玉洁
李 玉 洁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中国古代“君”与“子”是两个概念。拥有土地、臣僚、奴仆者,为“君”。“君”,因有土地、臣僚及奴仆,所以尊贵,即位高权重的人可称为君。“子”初为滋生之意,指的是春天万物滋生萌芽的现象,引申为人之生子。春秋时期以前,时人把年轻的男子或女子都称为“子”。《诗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春秋时期人们很少称女子为“子”,基本上把男子称为“子”。战国以后,男子通称为“子”。自孔子始,赋予“君子”以道德的概念。孔子认为,有道德的男子是值得尊重的,是“君子”。笔者试对“君子”概念的演变进行研究,以正于学术界同仁。
一、中国古代的“君”之含义
什么是“君子”?孔子之前,我国基本上是把地位高、掌握一定权力的人称为“君子”,把下层劳动人民称为“小人”。孔子之后,“君子”逐渐被赋予道德的内涵。

《诗经·小雅·大东》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郑玄《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视之,共之无怨。”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左传·襄公九年》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中所讲的“君子”“小人”仍着眼于时人所处的地位。
《礼记·祭法》有“共工氏无禄而王,谓之霸”:“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共工氏无禄而王,谓之霸。”《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山西通志·氏族一》亦云:“吕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这个记载说明,共工氏占有弘农之间的地域。所以,《管子·揆度》云:“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帝。”唐代房玄龄注:“共工氏继女娲有天下。” 共工氏本为伏羲、神农之间的一个古帝王,称“伯”“霸”或者是称“王”。中国古代的“伯”“霸”“大”“王”都有相似的意思。
根据我国“君”的含义,共工氏也许没有称王,但最少也是有地之“君”。是否辖有土地,是衡量能否为尊、能否为“君”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我国上古时期“君”的含义是“有地者为君”,换言之,无地者不为“君”。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地就无法让别人为你服役、为仆,也就是说没有臣。无奴仆和臣怎么为“君”呢?说到底,“君”之称号当与其拥有的政治经济实力有关。有地者就有经济实力,有经济实力就有政治实力,就可以为君、为霸、为伯、为王。
《尚书·大禹谟》云:“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孔安国传:“废仁贤,任奸佞。”这里的“君子”,似乎有道德的含义,其实细品其意,君子、小人的区分,还是一种对地位的理解。孔安国所作的《传》,当是汉代人的理解。
《礼记·杂记下》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古籍,反映的多是春秋之前、或是西周时期的现象和史实。《仪礼》当成书于春秋时期。《仪礼·丧服》曰:“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服传》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贵臣,其余皆众臣也。君谓有地者也。众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绳屦者,绳,菲也。”郑玄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阍寺之属。君,嗣君也;斯此也。近臣从君丧服,无所降也。绳菲,今时不借也。”
《仪礼·丧服》“君”条下郑玄注:“《曲礼》云:‘臣无君,犹无天’;则君者,臣之天,故亦同之于父。为至尊。”《服传》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仪礼·丧服》注释曰:“卿大夫承天子诸侯,则天子诸侯之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案《周礼·载师》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县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卿大夫有地者,若鲁国季孙氏有费邑,叔孙氏有郈邑,孟孙氏有郕邑;晋国三家亦皆有韩、赵、魏之邑,是诸侯之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以其有地则有臣故也。”
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君”之嫡妻,称为女君。很明显,女君是由“君”引申而来的称呼。《仪礼·丧服》“女君”条下曰:“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郑玄注:“女君,君嫡妻也。”又曰:“女君与君一体。”因为,女君是“君”之嫡妻,与“君”一体,所以,女君对于君之妾来说,如同儿媳之于舅姑(我国古代女子称公婆为舅姑)一样。可见,女君的地位是很高的,与妾的关系就是君臣的关系。
二、先秦时期“子”的含义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就可以理解古代最初对年轻的女子、男子皆称为“子”的意思了。“子”,其实就是小孩子、小姑娘、小伙子的意思。
在《诗经·周南·桃夭》《诗经·召南·鹊巢》中,把女子称为“子”。《诗经·邶风·凯风》《诗经·郑风·遵大路》中的“子”指的是男子。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古代我国曾把男子、女子皆称为“子”,就如春秋时期,贵族把国君的女儿、儿子皆称为公子一样。
《诗经·周南·桃夭》曰: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朱熹注:“桃木,名华,红实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华之盛也;木少则华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妇人谓嫁曰归。《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宜者,和顺之意。室,谓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
《诗经·召南·鹊巢》曰: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朱熹注:“鹊、鸠,皆鸟名。鹊善为巢,其巢最为完固;鸠性拙不能为巢,或有居鹊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两,一车也,一车两轮,故谓之两。御,迎也。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皆百两也。”
《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曰: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朱熹注:“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际也。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言女曰鸡鸣,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则不止于鸡鸣矣。妇人又语,其夫曰若是则子可以起而视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烂然,则当翱翔而往弋取凫雁而归矣。其相与警戒之言如此,则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女曰鸡鸣》中的“子”指的是丈夫起来“视夜”,看星光灿烂;“知子之来之”,指的是来的宾客;皆指男子。
《诗经·邶风·凯风》曰: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朱熹注:“南风,谓之凯风,长养万物者也。棘小木丛生多刺,难长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劳,病苦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诗以凯风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时,盖曰母生众子,幼而育之,其劬劳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责之端也。”浚,卫邑也。
《诗经·郑风·遵大路》曰: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
朱熹注:“挈其袪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宋玉赋有‘遵大路兮,揽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说之辞也。”
春秋以降,文字成为人们表达所思、所想的重要工具,所表达的内容也更加复杂繁多。随之,更多的文字被创造出来,古人开始用确切的文字表示男人、女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把未婚女子称为“女”,已婚女子称为“妇”,老年女子称为“媪”“妪”等;而把男子仍称为“子”。如《论语·八佾》云:“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里的“子”指的当然是孔子。太庙,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开国之君的庙也称太庙。
《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话,皆为“子曰”。《论语·学而》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又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魏人何晏注引马融曰:“子者,男子通称也,谓孔子也。”梁人皇侃《义疏》:“‘曰’者,发语之端也。许氏《说文》云‘开口吐舌谓之为曰’,此以下是孔子开口谈说之语,故称‘子曰’为首也。然此一书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时俗之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预录,故称‘子曰’,通冠一书也。”
《吕氏春秋·慎小》曰:“卫献公戒孙林父、宁殖食,鸿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鸿,二子待君,日晏,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二子不说。”这里所说是“二子”,指的孙林父、宁殖,这两个男子。
战国初年,徐无鬼想通过女商拜见魏武侯。《庄子·徐无鬼》记载,女商对徐无鬼说:“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徐无鬼说:“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径,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侧乎。”“子不闻”中的“子”指的是您,指代男子。春秋战国之后,“子”,基本上指的是男子。
三、孔子学说中“君子”的道德含义
孔子之后,人们逐渐把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称为“子”,或者把老师尊称为“子”,如孔子、孟子、先秦诸子等。“君子”开始逐渐地被赋予道德的属性和含义。《论语·学而》梁皇侃《义疏》认为:“子是有徳之称,古者称师为子也。”
《论语》是孔子与其学生谈话的记录,仅《论语》一书提到“君子”就有150多处。
孔子认为,“君子”的所作所为应处处符合仁、义的规范,不应做不仁不义之事。《论语·里仁》云:“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宪问》云:“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孔子认为,作为一个统治者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人人都想要得到富贵,但是“君子”必须在不违背仁的情况下,取之有道,决不能脱离了仁而得到富贵;君子必须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才能够“不忧”“不惑”“不惧”,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雍也》云:“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尧曰》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孔子认为,真正具有“君子”之风、廉洁正直的人,才可以跟他共事,不会背叛他。如果有人以义为品德的基础,行事按照礼仪,说话谦逊,诚实守信,也就是博学、守礼,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认为凡贪婪之人皆非“君子”。
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该结党营私;不应该贪婪、骄傲。《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子路》云: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认为,“君子”应容忍别人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即“和而不同”;相反,小人才强迫别人与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相同。别人虽然表面上勉强与你相同,但实际上内心是和你不同、而且是有嫌隙的,也就是“同而不和”。
孔子认为,“君子”绝不陷害别人;如果你讨厌一个人可以让他走,但不要陷害他。《论语·雍也》云:“子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论语·颜渊》云:“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述而》云: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反对只说不做的人,认为那些骄傲的人是不值得一提的;看一个人不仅要观其言,更要观其行;不能光凭一个人的言论、或会说奉承话而作为推荐此人的标准。《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论语·里仁》云:“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为政》云:“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子路》云: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孔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君子”的概念,即国家统治者清正廉明,那你就可以为官理政;如果国家被无道之人操纵,那么你就赶快离开,以免受辱。在这方面,孔子有很多的论述。
《论语·公冶长》曰:“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魏何晏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宫绦,鲁人也,字子容。不废,言见用。”宋人邢昺《疏》引《正义》曰:“此章孔子评论弟子南容之贤行也。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国有道,则常得见用在官,不被废弃;若遇邦国无道,则必危行言逊以脱免于刑罚。戮,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如此,故以其兄之女与之为妻也。”
《论语·泰伯》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宪问》云:“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何晏注:“孔曰:谷,禄也;邦有道,当食禄。君无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耻辱。”如果国家有道,你还很贫穷,得不到俸禄,说明你不愿付出辛劳或者没有能力,是耻辱的。如果国家无道,你能得到俸禄,很富贵,说明你与坏人同流合污,也是耻辱的。
《论语》中被孔子称为“君子”的人,主要有子产和遽伯玉。
《论语·公冶长》云:“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说,子产具有“君子之道四”,自己行事对人非常谦恭,侍奉国君怀敬上之心,对百姓施以恩惠和仁义。从这四方面看,子产确实有“君子”之风。

孔子认为,蘧伯玉也是一个“君子”。《论语·卫灵公》记载:“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宋代邢昺《疏》引《正义》云:“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君子之徳也。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者,此其君子之行也。国若有道则肆其聪明,而在仕也;国若无道,则韬光晦迹不与时政。故亦常柔顺,不忤逆于人,是以谓之君子也。”
《论语·泰伯》云:“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曹魏何晏注:“言行当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乱邦不居。今欲去乱,谓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将乱之兆。”
孔子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即不要到危乱之邦;在坏人当道时,不与坏人同流合污。天下有道则出来做事,“无道则隐”,这样使自己不受辱。《论语·宪问》云:“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魏何晏注:“包曰:危,厉也;邦有道,可以厉言行也。孙,顺也;厉行不随俗,顺言以远害。”
孔子认为,国家有道之时,可以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即“有道则见”;国家无道之时,要装聋作哑,即“无道则隐”;但是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容易,装傻很难做到。《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宁武子。”魏何晏注:“马曰:卫大夫宁俞,武,谥也。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佯愚似实,故曰不可及也。”
国家统治者有道,任何直言直行,都不会受到侮辱和伤害;国家统治者无道之时,言语一定要谨慎,不要冒犯坏人,但是行为上不要与坏的行为同流合污,就是守住底线。“守死善道”这是孔子关于“君子”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