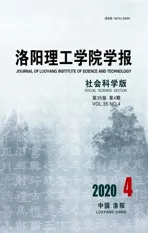“上官体”流行成因探源
2020-03-02韩达
韩 达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昌平 102249)
一、可资仿效:上官体流行成因的新视野
上官仪作为贞观朝至唐高宗前期的大诗人,其绮错婉媚的诗风在龙朔年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效仿,并被命名为“上官体”。“上官体”上承六朝以来的诗学经验,总结吸纳了唐初庾信体、颂体诗文的优长,以秀朗清丽的诗句统率全篇,避免了许敬宗肤廓空泛的弊病,从而达到了自然流畅的艺术效果。对“上官体”的诗史贡献,学界已有深入研究①。值得注意的是,唐人对“上官体”的接受其实是一个先扬后抑的过程,对其评价也表现出两极化的倾向;而此后学界对于“上官体”的优劣也各有所见,褒贬不一。但从总体上讲,这些研究皆试图从重估“上官体”诗学史价值的角度为其风靡一时的原因找到合理的解释。
唐初诗坛面对“上官体”时,一方面争相仿效,在朝野迅速形成了一股热潮,恰如《旧唐书·上官仪传》所载“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1]2743。上官仪不但有诗学理论《笔札华梁》传世,成为时人学习诗歌创作的范式,元兢、崔融等人的诗学著作也祖述其法,奉为圭臬。另一方面,由于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从浮靡纤微、毫无骨气的角度彻底否定其诗学价值,在他们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中打击嘲讽“上官体”,使得“上官体”逐渐失去了影响。受到王勃、杨炯、卢藏用等人观念的影响,部分现代学者也认为“上官体”不过是继承南朝风气的绮丽靡曼之体。如谢无量批评它“益为绮错”[2]19,罗宗强认为它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是“齐梁绮靡文风的继续”[3]55,吴小林指摘它“讲究辞藻对仗,内容空洞贫乏”[4]687。这些批评揭示了“上官体”所存在的弊病,但却无法解释其为何受到唐初诗坛的欢迎。唐人仅以上官仪在贞观末期至龙朔年间的显贵地位来阐释其诗风流行的原因,也未免失之于疏略草率。故而,以赵昌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力图从诗歌技巧的继承与发展角度重新发现“上官体”的诗学价值。赵昌平认为“上官体”的历史意义在于迈出了取法六朝而终于自成高唱的艰难的第一步[5]44-62,肯定其在唐代诗风新变中的作用,着重探讨了其声律和对偶的艺术成就。杜晓勤则从便于学习诗歌创作的角度肯定了“上官体”的贡献[6]49。在此基础上,学界已基本肯定了“上官体”的价值,并从“上官体”风格特征的角度阐释其体制特点。诸如赵昌平、杜晓勤、聂永华、黄琪等学者皆从分析“绮错婉媚”[7]的含义入手,通过对“上官体”所具有的诗句单字音义相对、句法节奏跳跃及浓密有致的结构等特点的把握,揭示其在唐代诗歌史中的地位,并对近年来学界拔高“上官体”地位的倾向进行了反思[8]。
以上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上官体”的体制特征和诗史价值提供了新的视野,而发掘“上官体”的诗歌史价值并不能完全解释“上官体”流行的原因。因为诗歌史价值的评估是从诗歌内部的发展脉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忽略了接受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时,现有研究多以唐人评价“上官体”“绮错婉媚”为切入点,认为是这种风格吸引了当时的学诗者。但从六朝至初唐的诗歌风貌来看,这种风格特征并非上官仪所独有,几乎所有浸润六朝诗风的诗人或多或少都会带有这种特点,区别在于程度不同而已。在解释为何只有“上官体”能独占此评价的理由时,研究者多试图从单个字音的角度入手。如王梦欧认为上官仪“着眼于构成各种偶句的每一个字的音和义的对称的效果,并即根据那不同的效果来区分各种偶句的形式”[9]243,此说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②。有的学者则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入手,提出其仿效小谢(谢朓)“直致”“直寻”的艺术特色,从而使“上官体”的优势在于“绮错成文而能缘情婉密而得天真媚美之致”[5]57。如果说“上官体”受到时人赏识乃是由于字音相对,叠换词性导致的对偶变化,那么这种风格和写法在虞世南、李百药等人的诗歌中也有体现。比如上官仪提出的“隔句对”在李百药的诗歌中就已有发明。如果以写景见意,即目会心为审美标准,那么虞世南、杨师道等人的诗作亦不遑多让。这说明,仅以“上官体”的风格特征进行解释,并无法排除其余唐初诸家的“干扰”,也就难以真正揭示其流行的原因。因此,探究“上官体”流行的缘由仍需从时人为何认为其可资仿效的角度入手,即从接受者的视角展开讨论,其中既涉及“上官体”便于仿效的体制特点,又应对初唐宫廷诗坛的创作机制加以分析。
二、唇吻流利之美:“上官体”与口号诗
考察“上官体”何以风靡一时,首先需要还原的是初唐时人接受这一诗体的具体情境。以上官仪诗中最著名的《入朝洛堤步月》为例。《隋唐嘉话》云: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上官仪此诗一出,首先在晨起上朝的同僚中引起剧烈反响。这说明当时的朝臣都能读懂其诗所蕴含的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与其按照今天的标准理解为“读懂”,不如回到历史的现场,他们其实是“听懂”的。这从时人“音韵清亮”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朝臣们欣赏此诗的原因之一在于诗歌音节的婉转流美。上官仪创作此诗并非宿构,身边也没有纸笔涂抹修改,乃是即目写景、随意吟唱而得,现有题目很有可能是后来增加的,此诗本身更像是一首六朝以来常见的“口号”诗。
“口号”即随口吟咏而成,不起草稿,类似于“口占”。最早是为处理政务的应急之举,口述章草。如陈后主时期的中书舍人施文庆,“仍属叔陵作乱,隋师临境,军国事务,多起仓卒,文庆聪敏强记,明闲吏职,心算口占,应时条理,由是大被亲幸”[10]1938。这种情形直到唐代依然存在,王勃之兄王剧也曾有类似的救急之文,“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等五王初出阁,同日授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相相顾失色。剧立召书吏五人,各令执笔,口占分写,一时俱毕,词理典赡,人皆叹服”[1]5005。
在现存的文人诗中,以这种不加深思、随口吟唱的形式进入诗歌领域的,最早见于刘宋鲍照的《还都口号诗》,此后为历代诗人沿用。如刘禹锡为其诗文作序时就说“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1]4212。“口号”诗产生的地点往往是上朝、巡城、陪侍出行的途中,它正式作为诗歌体式而获得文人的关注并发展起来,则是在梁代宫廷内。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王筠皆有唱和之作传世。“口号”诗本是随意性较强的创作形式,早期并没有特殊的体式要求,但经过南朝宫廷的加工改造后也逐渐形成了一套需要遵守的音律声辞标准。据统计,现存南北朝至唐代的“口号”诗共有87首。通过分析这些“口号”诗的声病特征可以发现,“口号”诗的音律虽比较自由,但也有一定的要求。受到鲍照首创此体的影响,“口号”诗的第一联需犯“上尾”病,即首联尾字声调必须相同。而“上尾”病是齐梁时期诗人严格避忌的声病之一,但“口号”诗的体制则可以无视此要求。即使在“永明声病说”已非常流行的梁代,诗人依然遵循诗体的要求,如萧纲《仰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首联即犯上尾。当然,并非所有的“口号”诗都遵循此规律,如庾肩吾和王筠的唱和之作就没有践履此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梁陈诗人发现了以首句入韵规避“上尾”的方法,但萧纲此诗中并未使用。一方面说明“口号”诗首联的声律要求确实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南朝诗人对于如何认识“口号”诗的声律规律还未能达成统一的标准。
这一情况到唐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唐人依照五言、七言的区别将“口号”诗区分为两类。七言口号诗基本上全部遵守首联犯上尾病的旧规,而五言口号诗则不需要。但经分析后可以发现,五言口号诗不遵守标准的情况出现在盛唐时期,初唐诗作依旧奉行这一标准。而废除旧规则的正是唐玄宗、张九龄等人。如唐玄宗《潼关口号》五言四句,首句用止韵,全诗押庚韵。张九龄的奉和之作十分相似,首句押纸韵(与止韵通押),全诗押侯韵,亦步亦趋之感甚强。他们有可能是受到了李峤“口号”诗创作的影响。李峤是初唐宫廷诗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对“口号”诗的声律特征进行了改造。而在李峤、唐玄宗等人确立新规之前,五言“口号”诗有犯上尾的,如阎朝隐在陪侍皇帝赴登封途中所作的《侍从途中口号应制》即犯上尾。此次随侍途中的同行者还有宋之问,他也有《扈从登封途中作》一首,其声律特点与阎朝隐诗相同。
那么,上官仪对“口号”诗的改造又在何处呢?从《入朝洛堤步月》的用韵和声病来看,与前人之作相比,此诗以首句入韵的方式规避了上尾病,从而解决了由于诗句尾字同音所导致的声调趋同、殊无变化的弊病。同时,句末连韵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柏梁体或古诗的音乐效果,更符合宫廷内部的审美。上官仪之所以要改造“口号”诗,是因其本人是初唐时期对前代声律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的第一人。同时他将此经验推广到其他各类诗歌的创作中,形成了“上官体”的特色之一。如《安德山池宴集》《酬薛舍人万年宫寓直怀友》《和太尉戏赠高阳公》等。上官仪对沈约以来的声病学说加以发展,对“八病”的要求作了具体说明。而“八病”中最为隋唐人诟病的就是上尾,因此又称其为“土崩”。隋唐人认为不但诗不能犯,赋、颂也不可犯,即韵文要力避上尾。而只有符合古体色彩的诗歌或乐府歌行体才可以首句入韵的形式犯病,如《饮马长城窟行》中“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隋唐诗格就认为“唯连韵者,非病也”[11]937。“口号”诗本就是随口吟唱的诗篇,或许唐人正是根据这个特点,将其视为古诗歌行体之流,故而允许其使用首句入韵的方式来避忌上尾,况且七言“口号”诗的语体色彩本就与七言歌行体非常相近。如孙逖的《途中口号》:“邺城东北望陵台,珠翠繁华去不回。无复新妆艳红粉,空余故垄满青苔。”[12]1198又如王维的《寒食汜上作》(亦作《途中口号》):“广武城边逢暮春,汶阳归客泪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12]1307其体制风格近乎歌行,读来朗朗上口,而盛唐诗坛将这种风格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李白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和杜甫的《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等。
“口号”诗本身所具有的美感在于唇吻流利,因为它原本就是口语经过加工而来的,故而在节奏上更近于人的自然习惯。这种节奏感有助于解决因宫廷诗文严格的对仗所带来的审美疲劳。如《入朝洛堤步月》最为人称道的后两句,“鹊飞”“蝉噪”都是常见的主谓结构,“山月曙”“野风秋”实际上也是主谓结构,只不过“曙”“秋”被用作了动词,此句其实就是两个主谓短语的叠加。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主谓短语是我们日常使用得最多的语法结构。主谓短语本身又可以包含主语加形容词、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等组合方式,这种句法在上官仪的其他诗歌体式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如“木落园林旷,庭虚风露寒”,即“木落”(主谓)+“园林旷”(主状);“银消风烛尽,珠灭夜轮虚”即“银消”(主谓)+“风烛尽”(主补)。这种语法结构也为唐人所接受。如李峤《奉教追赴九成宫途中口号》中“雨余林气静,日下山光夕”就是主谓结构的叠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主谓结构为主的诗句在上官仪之前就已出现,他的句法是继承前人而来。如褚亮的“野净余烟尽,山明远色同。沙平寒水落,叶脆晚枝空”、杨师道的“鸟散茅檐静,云披涧户斜”、许敬宗的“鹊度林光起,凫没水文圆”等。只不过前人并不注重推广此类句法,也不重视其在诗歌整体中的结构搭配,往往是在“名+动+名(状)”占多数的句法中穿插若干这样的句子。上官仪则不同,他的诗歌往往首句散起,推进如流水般畅快。如“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近似精致化的口语,然后再使用主谓结构叠加的对仗句式“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或者前句有单个主谓结构的铺垫,然后始用叠加。如“密树风烟积,回塘荷芰新”中“风烟积”和“荷芰新”就是两个单独的主谓结构,然后次联“雨霁虹桥晚,花落凤台春”再变为两个主谓短语的叠加。
上官仪特别擅长使用主谓结构,他的诗歌中常常能够见到主谓结构充当主语或谓语的情况。如“云飞送断雁,月上净疏林”,“云飞”“月上”都是主谓短语用作主语,然后再与“送断雁”等动宾短语构成一个完整的主谓结构;而“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中“流莺满”和“芳草积”都充当了谓语,对“晓树”“春堤”进行评价或描写。这说明上官仪对诗歌声律婉转的体会在于使用贴近自然口语形式的主谓结构,与许敬宗颂体诗文常见的固定化的双音节词属对相比,这种形式具有搭配自由、对仗便宜的优点,可以避免成词熟典对偶所造成的呆板。而主谓结构叠加的形式恰好需要大量的单音节字或单双音节组合来完成,这就使得上官仪必须关注单字不同词性之间的组合方式,从而为其对属理论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受到同僚推崇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风度的体现,他们将口吐金玉之声的上官仪视作“神仙”临凡,而这种潇洒风流的气韵正是初盛唐人所推崇的。王维、张说皆有模仿上官仪此诗的诗句,但胡震亨认为他们的诗达不到上官仪原作所体现出的“风致”[13]91,其原因并非张、王二人诗才不足,导致其模拟徒具表象,而是他们的气度与上官仪相去甚远。而这种“风致”之所以难以习得,是因其不仅来自诗歌体制的内部,更与外部诗坛整体的文学风习与诗人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有关。
三、初唐宫廷文学教育与“上官体”的流行
初唐宗室贵戚子弟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作为其文学能力养成的主要途径,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对言语谈论的训练。上官仪吟诵其诗而众人皆喜,这与宫廷文学训练所营造的风气不无关系。朝臣贵胄日常接受的文学训练中就包含了声韵清通、音节浏亮的要求。唐初贵族认为这种文学训练可以体现他们的教养与学识。实际上则是因为唐代帝室贵戚大部分出自鲜卑贵族,他们迫切地需要学习汉语知识。然而,南北分裂历经3个世纪,音韵上已有较大的不同,而南朝士族因被视作中原文化的正统,其语音声调也受到北地士族的追捧,故而,唐代帝室在为子弟简选教授时,特别看重南朝士族在言谈声韵上的优势。唐太宗在选择太子辅臣或诸王僚属的时候,一般按照关陇、山东、江南三地区分,关陇贵族以门资、姻亲入选,一般担任亲卫官,主要负责太子、诸王的卫率。山东士族由于经术出众,又有门阀士族优雅教养,被视为经学和道德上的导师。南朝士族则由于文学闲雅、音韵晓畅、辩言得当而负责太子、诸王的文学教育。如张览因身为“南朝士族,音韵清通,讽咏谈端,声高兰坂”[14]74而入选为蒋王府参军。唐人的言谈主要模仿南朝士族的谈论,以经史大义、玄虚至理为主要内容,其方式则如王僧虔《诫子书》所述,需掌握诸家经典及其注解。谈论的优劣不但代表了其学行的高低,更能获得人主的赏识,唐太宗就曾称赞王珪“识鉴清通,尤善谈论”[1]2529。清谈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文史的方式,如崔赜与元善、王劭、姚察、诸葛颖、刘焯、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15]1758。王勃、骆宾王等人求学时,都喜爱与同学进行讨论。唐代两监诸生日常课业之余主要的活动就是探讨辩论。因此,唐人非常看重言谈在个人学养中所占的地位。
在唐人眼中,言谈与文学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如崔融《哭蒋詹事俨》中称赞蒋俨的文学才能与言谈相埒,所谓“逸翰金相发,清谈玉柄挥”[12]767。杜甫《送高司直寻封阆州》中云:“清谈慰老夫,开卷得佳句”[12]2368。可见唐人将清谈视为一种文学能力,它能使人直接感受到受教育者的学殖深厚。如袁公瑜“年十有五,乃志于学,谈近古事,若指诸掌”[14]975。15岁正是唐人学习属文的年龄,而袁公瑜专好谈论掌故,曾经在唐太宗面前谈论“音仪娴雅,声动左右”[14]975,使唐太宗即席叹服。由此可见,唐人在学习文学的过程中不仅偏重落于笔端、形诸文字的书面表达形式,也非常重视音节浏亮、内容丰富的清谈训练。
唐人根据“三礼”和《诗经》的记载,视清谈为雅宴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与赋诗作文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唐人如此描述天宝以前的宫廷宴集:“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1]485初盛唐时期,宫廷宴集之风甚为流行,宴集中雅谈纷纭也是对南朝宫廷宴饮歌舞之风的效仿。尤袤《全唐诗话》云:“太宗尝谓唐俭:‘酒杯流行,发言可喜。’是时,天下初定,君臣俱欲无为,酒杯善谑,理亦有之。”[16]65更重要的是,善清谈被隋唐人视为风度的外化,他们往往将“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15]1726联系起来。清谈议论乃是“风流余事”,它与音乐、书画、文学一道被视作个人风度仪表、风流余韵的外在体现。齐梁以来人们对文学的评价标准中,“风流”是其中非常重要且优异的表达。沈约评价太康群英“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17]695,姚思廉称赞江总“风流以为准的”[18]346。唐人继承了前人的标准,将有文采者视为风流之士。如李迥秀“雅有文才,饮酒斗余,广接宾朋,当时称为风流之士”[1]2391,陆象先才学不及陈子昂等人,但“风流强辩过之”[1]2877。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上官体”受到时人推崇与仿效的缘由。上官仪身为南朝衣冠子弟,既擅长音韵知识和言谈辩论,同时其诗歌体现了一种风流的韵致,这种风流韵致正是唐人接受南朝文化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上官仪用事之时,正是承贞观余烈、天下太平的好年景,唐高宗羽翼未丰,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掀起清理旧臣的政治斗争。因此,朝臣的生活环境与审美心态还延续着唐太宗朝的旧风,他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还是南朝以来流行的方法,审美趣味也偏向于南朝士大夫式的绮媚轻柔,所以其诗歌也追求一种舒卷自如的韵律和流转轻扬的美感。同时,“上官体”长于主谓结构的诗法使得诗歌语言偏向于口语式的简便,与其时强调言谈之美的文学训练紧密结合,使人们写诗从摘抄文章佳句、典故史实变为即目状景、语写天真的自然流利,使凝重典雅变为清灵空秀。从理论反哺文学的角度看,越简单易行的理论就越容易受到接受者的欢迎和使用。上官体精于属对,操作简便,同时诗语更加自由,贴近口语的天然状态,自然受到了时人的欢迎。
“上官体”的衰落也与唐代宫廷文学教育的转变有关。武则天诛杀上官仪代表着其政治集团正式登上舞台,她掌权后为抵抗和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大力提拔山东寒庶士族进入宫廷。山东地区寒庶士族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更强调“经世致用”“不平则鸣”的文学精神,与南朝士族截然不同,所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人极力批判“上官体”的弊病,使其影响力迅速衰竭。而此时的宫廷诗人出于依附武则天的目的,创作了大量的歌功颂德之文,诗赋文章继续在华丽夸饰的道路上竞相追逐,重新回到了许敬宗颂体诗文揄扬鸿业的老路上。更甚者,武则天为了压制宗室贵戚子弟曾一度关闭太学,官学出现时有停废的情况。韦嗣立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便上书痛陈“国家自永淳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1]2866的情况。武则天时国子祭酒也多授予诸王和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1]4942。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上官体”的流行有着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原因。内在原因主要在于其属对理论的简便易行,以及偏向口语化的诗法结构,导致当时宫廷文学流行的多是正名对、异类对、同类对、双声对、叠韵对、隔句对、双拟对、连绵对、回文对等主攻词汇变化的对偶句式,耽于辞藻的垒砌和琢磨,而无暇关注句法的讲究,更不谈意境的构思。外部原因则在于初唐宫廷对于齐梁士族风度的歆慕,以及南朝诗风的流行。然而前者会随着诗歌技法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对诗歌意境的逐步提倡而变换形态,后者则会随着政治斗争导致的迁谪升降或反思齐梁,追求复古的风气而失去魅力。武则天主政后官学衰微长达20年之久,学官不得其人,学徒严重流散,重视清谈之风消歇,宫廷文学教育几乎难以为继。因此,绮错婉媚的“上官体”也只能在唐初宫廷流行一时,特别是唐太宗后期至唐高宗前期这一特殊时段。而由“上官体”所总结和发明的对偶理论、玄远风度则可因超越其体式本身而传诸后人的优秀经验而被继承下来。
注 释:
① 自刘开扬20世纪50年代始,周维德、黄永年、吴宗国、韩理洲、杨恩成、傅璇琮、葛晓音、钱志熙等已从齐梁文风的嬗递、初唐四杰与上官仪之关系、唐初宫廷政治斗争史实、科举制度、初唐宫廷文风的变迁等多个角度对上官仪的生平和上官体的诗学意义进行了探讨.商伟、贾晋华等人则引入了以宇文所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界对初唐诗的论述,对上官体在宫廷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总结.日本学者兴膳宏、大陆学者邝建兴、杜晓勤、吴小平、卢盛江等则针对声律理论的发展对上官体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
② 赵昌平《上官体及其历史承担》(《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62页)认为此说法“相当精辟”.赵昌平认为上官仪扩大了六朝以来偶对理论的内涵,从着眼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拓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黄琪《“上官体”的诗歌史价值重估》(《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第65-72页)提出上官仪诗歌形式作法上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重视单字音义相对,纤密的结构和跳跃的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