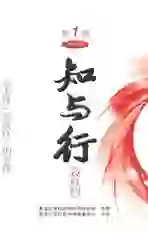生命伦理学脆弱性原则之意蕴
2019-06-11潘麒羽
潘麒羽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良好生活的追求开始延伸至更广泛的空间。其中,与人类健康幸福生存密切相关的生命医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生命医学领域的蓬勃发展切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伦理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不仅体现在临床治疗中的医患关系上,也同样体现在医学研究领域中研究者与受试者的关系之中。生命医学领域的伦理冲突呼吁相应的伦理原则来发挥规范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下广义应用伦理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不同的现实问题,相应催生了不同的生命伦理学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内涵与规范效力也仍处于讨论之中。我们对欧洲生命伦理学原则中的“脆弱性”的内涵及其规范效力展开研究。作为一项生命伦理原则,脆弱性原则在医学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对脆弱性含义的界定却仍处于讨论之中,其中有以伤害为基础的脆弱性、以同意为基础的脆弱性、以不当为基础的脆弱性等定义方式。以上三种定义方式都揭示了脆弱性原则的重要内容,但缺乏对脆弱性内涵的深刻理解。而以能力为基础定义脆弱性的方法既全面揭示出脆弱性的描述性特点,同时也为研究伦理中的道德义务及其冲突提供了更有效的论证和解决方案。作为一项生命伦理学原则,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使人们承认并尊重自身的脆弱性状态,进而在生命伦理领域发挥着沟通联结各项伦理原则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脆弱性;伦理原则;规范效力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1-0130-05
醫学对疾病和疫情的防治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们热切盼望医学的快速发展,以便更有效地治愈那些阻碍人类幸福生活的各类疑难杂症。医学以及防治手段的进步与医学研究密不可分,可以说未来的医学就是现在的医学研究。与临床治疗一样,生命医学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生命医学领域的蓬勃发展切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同样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伦理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不仅体现在临床治疗中的医患关系上,也同样体现在医学研究领域中研究者与受试者的关系之中。大多数生命医学研究都需要将人类作为受试者,这也意味着研究过程中任何误差或隐患都可能会对受试者的身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在医学研究中,这种特殊的“研究者—受试者”关系以及其可能产生的恶果都呼吁建立相应的伦理原则与法律规范。从1947年至今,各类国际组织先后出台并反复修订了多项国际生命伦理准则,其中与涉及人体的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有《纽伦堡法典》《赫尔基辛宣言》《关于人体受试者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三部准则。医学研究中受试者相对于研究者来说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准则的出台与修订彰显了一个重要理念:保护医学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受试者。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识别脆弱者以及确定脆弱者的需要,伦理学研究中提出了脆弱性的概念。脆弱性也已经成为欧洲生命伦理与生命法规中基础性的伦理原则之一。
脆弱性概念在研究伦理中逐渐发挥出规范性的作用。脆弱性概念本身貌似是清晰直观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处于一种脆弱状态),但对其内涵的理解仍然存在争议。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可能会用“脆弱的”来形容不同性质的对象,如某段关系是脆弱的、某个人是脆弱的。在这些语法中,脆弱性的内涵包括了不稳定、糟糕或劣质、身心易受伤害等意味,这也表明脆弱性概念可能存在过于模糊和宽泛的倾向。作为研究伦理中的伦理原则,脆弱性需要具有规范性的维度,而不仅仅是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描述性事实。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总结目前有关脆弱性概念讨论的基础上,试图论证: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概念的定义既满足了脆弱性概念的描述性含义与规范性维度,又综合了既有的生命伦理原则的基本精神;既阐明了脆弱性的内涵,又揭示了脆弱性中蕴含的道德义务。
一、关于脆弱性概念的讨论
脆弱性是研究伦理中经常被提及的概念。研究伦理中用“脆弱群体”概念来指代那些需要被特殊保护的对象,如妇女就通常会被视作需要保护的脆弱群体——这样划分脆弱群体的方式被称作“标签进路”。通过对比《贝尔蒙报告》《美国联邦法规》等不同文件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文件对脆弱群体的界定和划分标准不尽相同,甚至还存在一定的概念交叉。“这种简单、齐一的识别脆弱者的方法极利于伦理委员会来操作执行,但忽略了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1]同时,“标签进路”没有帮助我们理解脆弱性概念的实质内涵,也无法提供判断(而不仅仅是指定)脆弱群体的普遍标准。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索定义脆弱性概念的方式,其中有从对脆弱性概念的词源考察出发而确立的“以伤害为基础”的脆弱性、有借助知情同意视角而确立的“以同意为基础”的脆弱性、还有着眼于实际应用层面而确立的“以不当为基础”的脆弱性。这些定义方式互为补充,丰富了人们对脆弱性概念的理解。
(一)以伤害为基础的脆弱性
英文“vulnerability”与拉丁语动词“vulnerare”、拉丁语名词“vulnus”密切相关,它最简洁的含义是“容易受到伤害、影响或攻击”。基于词源的含义,“伤害”便是理解脆弱性概念的重要中介之一。为了更好地阐释研究伦理中的脆弱性概念,Kottow将脆弱性与易感性(susceptibility)做出了区分,脆弱性的程度是可以通过给予社会成员公平正义的保障而降低的,而易感性是一种注定的缺乏状态,这种因易感性而可能遭受更大程度伤害的群体,更符合研究伦理中脆弱性概念的定位[2]。更进一步地说,脆弱性是人类必须承认的基本生存状态,而易感性是需要诊断和治疗的一种特殊和偶然的情况;脆弱性意味着个体必须依靠额外的道德支持来获得尊重和保护,而受到损伤的个体则需要修复和治疗。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Kottow提出了以伤害为基础定义脆弱性的路径,这有利于将脆弱性这一指向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宽泛概念界定在研究伦理领域中,脆弱性意味着更容易遭受潜在的伤害。
以伤害为基础的脆弱性概念无疑揭示了受试者在研究伦理中的特殊处境:医学研究带有实验性质,受试者很可能因实验不当而遭受伤害;同时为了确保实验数据的完整和全面,需要招募不同健康状况的受试者,因此其中健康状况较差的人们更容易遭受额外的伤害。以伤害为基础的脆弱性概念表达了研究伦理中保护受试者的基本精神,但作为一项伦理原则,这种定义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虽然通过易感性概念的提出,使宽泛的作为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脆弱性得到符合研究伦理要求的界定,但这种定义方式本质上还是单纯从一种描述性的事实(人类脆弱的生存状态)出发,进而得出脆弱性概念难以发挥其作为一项伦理原则的规范效力。另外,这样的定义中缺乏关于对伤害来源、伤害性质的界定,也就难以判定何种受试者在研究过程中更易遭受潜在的伤害,从而也无法对受试者群体容易遭受伤害的程度进行排序,进而就难以在应用中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
(二)以同意为基础的脆弱性
除了从伤害的角度定义脆弱性的路径外,另有学者借助“知情同意”——这个生命伦理中的重要原则来定义脆弱性。知情同意是指受试者在了解所要参与研究内容的基础上,自主选择是否要参与研究。知情同意的主张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病人和研究参与者的利益和权利,使他们不受欺骗、侵害和剥夺——这符合保护受试者利益的原则。在1993年出台的《关于人体受试者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涉及脆弱人群的内容中,就提供了以同意为基础定义脆弱性的范例:“在传统上被认为脆弱的人是同意所需的能力受限或自由受限的人群”[3],因此研究中脆弱性通常適用于无法给出同意或更有可能被剥削知情同意的个体。脆弱性与知情同意紧密联系在一起,受试者的脆弱性表现为可能做出错误的同意而损害了自身的利益。在这种定义方式下,脆弱性原则保障受试者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自主做出决定的能力。
以同意为基础定义脆弱性概念的路径将脆弱性与生命伦理中的知情同意原则联结在一起,揭示了脆弱性在研究伦理中的另一个维度。但这种路径方式同样存在缺陷。保障受试者的知情同意并不足以保护受试者在医学研究中不受损害,脆弱性成为影响知情同意发挥效力的因素,这在实际上就将知情同意中“有限的同意能力”与“外在环境导致的知情权的限制”等问题转嫁到脆弱性原则之中,不仅遮蔽了脆弱性概念本身具有的“容易遭受伤害”的含义,也无法为脆弱性作为一项伦理原则而提供规范效力。
(三)以不当为基础的脆弱性
上文的两种定义方式都是从造成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受试者自身的原因)出发,提出理解研究伦理中脆弱性的含义。二者都揭示了脆弱性中极为重要的方面,但也都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规范效力不足等问题,从而不利于脆弱性原则在研究过程中的应用。Hurst在反思上述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以“不当”(wrong)为基础来定义脆弱性概念,不当表达了两重含义:一是不正当的伤害;二是当我们提出正当要求而被拒绝时所遭受的不当。以不当为基础的脆弱性含义是“遭受额外或更严重不当的可能性”[4]。对于受试者而言,“遭受不当”中其实也包含遭受身心损害以及因错误决定而遭受的权益损失。同时,“以不当为基础”从造成脆弱性外在原因的角度定义脆弱性概念,这一方面有利于判定研究活动中的脆弱群体(是否遭受不当);另一方面也为研究活动中如何归责的问题提供准绳(造成不当的研究者承担责任)。相比于前两种定义方式,以不当为基础的脆弱性伦理原则能够更有效地应用到研究活动之中。诚然,从外在原因的角度定义脆弱性概念,增强了脆弱性原则的规范效力,但同时也遮蔽了脆弱性内在于主体自身的含义。同时,不当本身也面临着与伤害和同意相似的问题:程度界定,即如何理解不当的含义以及如何划分不当的程度以区分不同的脆弱群体。另外,根据以不当为基础的脆弱性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出脆弱性原则所表现出的伦理规范要求是避免不当发生的可能,即遵守研究过程中正当的义务,但这一路径仍然没有充分论证出研究者为何具有不损害受试者健康或权益的规范性义务。
以上三种定义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对脆弱性概念做出了界定。每种定义方式都揭示了脆弱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其中前两种定义方式已经揭示了脆弱性概念的基本内涵,但仍然倾向于描述性界定,而缺乏规范性的效力。以不当作为外在原因的定义方式的确有助于应用到研究过程中进行伦理归责,但缺少对脆弱性内涵的深刻理解。因此,定义研究伦理中脆弱性概念的关键就在于:既要揭示其描述性的内涵,又要阐发其规范性的效力。
二、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
在探寻脆弱性概念的内涵及其规范效力的过程中,不能止步于对脆弱性的描述性定义。描述性定义实质上是通过总结脆弱性的表现形式而得出的,无法阐明引起脆弱性的根本原因,从而很难在实际应用中给出普遍有效的原则指导。我们需要深入探寻脆弱性的来源以及脆弱性原则的规范效力。对此,Rogers等人做出为脆弱性概念进行分类尝试,进而指出这些类型的脆弱性共同带来了无能为力、失去控制或失去能动性的感觉,这种考察便将能力的缺失与脆弱性的形成联系在一起。
(一)脆弱性的三种分类
面对关于脆弱性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的现状,Rogers等人认为脆弱性概念的恰当定义需要能够面对两个挑战:一是如何协调脆弱性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普遍主张与脆弱性因特定情况下来源和种类而产生的要求;二是如何协调保护弱势群体的义务和尊重自主的义务[5]。首先,为了克服第一个挑战,Rogers等人从特殊脆弱性来源和种类出发划分了三种脆弱性:内在的(inherent)脆弱性、情境性的(situational)脆弱性和诱发性的(pathogenic)脆弱性。内在的脆弱性是人类与生俱来表现出的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它是由我们需求所决定的;这种脆弱性的表现形式(性别、健康状况等)是偶然而充满变化的,它也会取决于人的恢复能力和应对能力,以及他们可获得的社会支持。情境性的脆弱性是由外界所引起或加剧的,其中可以包括他人或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状况的影响。诱发性的脆弱性则是指因人为干预而加剧了原有的脆弱性或形成新的脆弱性,理解这种诱发性的脆弱性的关键就在于它对能动性的损害与对无力感的增加。
(二)脆弱性与能力缺乏
Rogers等人所划分的三种类型脆弱性的来源和种类虽有所差异,但它们都与能力(capacity)概念密不可分,每种类型的脆弱性最终都指向了能力的缺乏(无力感与能动性的丧失)。能力衡量的是人们用以实现价值性功能的实质自由(指人们所拥有的机会和选择),与此相对的能力缺失就意味着人们缺乏实现价值性功能的机会和选择余地,这便与脆弱性所描述的人类境况不谋而合:对于脆弱群体来说,会因为个人或社会等因素而导致实现生存状态或开展活动的机会受到限制[6]。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研究伦理中受试者易受伤害、容易做出错误决定等境况,表达了脆弱性概念的描述性特征,而这些特征也都可以被划归为某种能力的缺乏:易受伤害是保存健康能力的缺乏、做出错误决定是自主能力的缺乏。
与上节所提到的定义方法相比,这种从能力缺乏的角度来理解脆弱性概念的方法更具优越性。能力概念包含了研究伦理中伤害和同意所要表达的含义,脆弱性可以被概括为某种类型的能力的缺乏;能力的缺乏既从受试者内在的维度出发来表达了主体能力的缺乏,同时也包含因情景或人为因素导致脆弱的外在维度,进而囊括了脆弱性概念的描述性内涵。
(三)脆弱性原则的规范效力
除了具备脆弱性概念的内涵外,对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其规范效力,以便在应用于研究活动时可以发挥其作为生命伦理原则的引导作用。广义上能力的缺乏意味着主体无法自由地实现其价值性的活动,因此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政府或其他机构应确保社会成员的能力达到基本水平从而实现其兴盛发展。具体到医学研究活动,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就要求研究者在研究活动中保障受试者的利益,而这种要求的规范效力既有其普遍性,同时又有属于研究活动的特殊性。就普遍性意义而言,研究活动中受试者也是属于社会成员,也同样享有实现自身价值性活动的权利,作为在研究活动中占据相对主导地位的研究者,应负有不损害保障受试者自身能力的义务;而医学研究又具有其特殊性,受试者的参与推动了医学研究的进程,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先行履行了帮助实现对方兴盛发展的义务,因此研究者更应积极面对这一过程中受试者可能展现的能力缺乏(无论这种缺乏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在以能力为基础定义脆弱性的视角下,脆弱性原则也处理了上文提到的第二个挑战:协调保护弱势群体的义务和尊重自主的义务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避免以保障受试者利益为由而实施的“家长主义”作风。能力进路的特点在于它关注个体选择或自由的重要性,它重视选择所基于的多样性事实和多元性价值的承诺。在医学研究中,不同的受试者个体可能会重视不同类型的能力,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要求研究者在保障受试者利益的前提下,尊重不同受试者个体做出的选择。
本节通过探寻脆弱性的来源以及脆弱性原则的规范效力,得出能力概念作为理解研究伦理中脆弱性原则的关键。以能力为基础定义脆弱性的方法既全面揭示出脆弱性的描述性特点,同时也为研究伦理中的道德义务及其冲突提供了更有效的论证和解决方案。
三、生命伦理中的脆弱性原则
至此,本文叙述了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的内涵,以及它应用于研究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规范作用。但是在思想史上,脆弱性却是时常被忽视的。伦理规范往往奠基于人类的理性、德性等象征着人类独特性和优越性的能力之上,传统伦理学所追求的目的主要是积极意义上的美满和完善,即使探讨脆弱性也只是将其视为需要克服或扬弃的对象。而在生命医学领域,脆弱性概念却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甚至成为欧洲生命伦理与法规的重要伦理原则之一。这一方面源于生命医学领域的特殊性质,无论是患者还是受试者,在医学治疗或研究活动中都处于一种弱势而需要帮助的地位,更容易展现出自身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也与当代伦理学研究视角的转向密切相关。不同于奠基于神圣律令、普遍法则与抽象人性观的传统伦理学,当代伦理学(特别是美德伦理学)更多将视角转向行为者的心理动机和需求,也就离不开对行为者本性和生存状态的把握。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則不仅表达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具有一定的规范效力,同时在研究伦理中也起到了联结和沟通其他生命伦理原则的纽带作用,使各个伦理原则协调一致地应用于医学研究活动之中。
(一)脆弱性表达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
人类的脆弱性意味着能力的缺乏,而与之相对的完善性则体现为人类理性和德性的充盈,但是很难将这种抽象的完善性视为人类现实的生存状态。康德将人类看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类既享有理性的实践能力,同时也无法完全摆脱主观的感性偏好,这就是说人类的意志和行为并非完全合乎理性[7]。对这一观点更为生动的描述则是将人类看作“依赖性的理性动物”[8],麦金太尔认为人类无法摆脱自身因动物性的成分而产生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最直接体现为人类极易遭到疾病、灾难的伤害,在普遍的生命过程中人类总是要经历童年和老年时期的脆弱无能,还会有部分人陷入生理或心理上的残疾中。脆弱性不仅表现为生存能力的不足,也指向人类在具体实践事务上理性能力和实践智慧的缺失,现实中的个人难以在每一件具体的实践事务上都做出恰当的选择。就此而言,脆弱性表达了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
人类普遍脆弱的生存状态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这种事实本身却也蕴含着规范性的要求。人类的脆弱性需要积极保护以免受伤害等负面力量的影响。自古以来人类自觉结成氏族、部落、国家等共同体形式,人类在本能上即懂得唯有共同体成员彼此间的分工与合作,才能实现个人的幸福与群体的公益。脆弱性使我们在整个生命活动中都可能会处于依赖他人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并承认这种脆弱性和依赖关系,在相互依赖与合作中克服脆弱性给个人或群体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脆弱性是联结生命伦理原则的纽带
目前在生命医学领域发挥重要伦理原则,主要有针对反思纳粹人体试验而提出的“知情同意”原则,盛行于美国在临床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公正”四原则[9],以“自主、尊严、完整、脆弱性”为内容的欧洲生命伦理四原则[10]。生命伦理原则是针对生命医学领域出现的现实矛盾冲突而制定的,其内容和要求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都旨在保障临床或研究中患者和受试者的利益。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各项生命伦理原则都无法绕开患者和受试者脆弱的普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表现为可能出现各项能力的欠缺,如同意的能力、自主选择的能力、保证身心完整的能力等。就此而言,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综合了各项生命伦理原则的内容和要求,成为联结生命伦理原则的纽带。
脆弱性原则的纽带作用还体现在,它为各项生命伦理原则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提供了协调对话的基础。生命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为不同原则之间的优先性问题上。优先性问题在理论中就存在,但在应用层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如果A认为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应当优先于不伤害的要求,而B对此有相反的优先性排序,那么在这样一个情景中,尽管二者都出于保障患者利益的考虑,但在如何取舍尊重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的问题上就难以取得共识。对此,脆弱性原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共识基础。人类普遍脆弱的生存状态要求承认脆弱性和保护免遭伤害等负面力量的影响,因此面对临床治疗或研究活动中的伦理冲突时,承认并尊重患者和受试者的脆弱性、保护他们免遭脆弱性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便是在以脆弱性原则为共识基础下处理各项生命伦理原则之间冲突的基本要求。
四、总结
脆弱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识别研究活动中的脆弱者以及确定脆弱者的需要。通过分析对比几种主流的对脆弱性概念的界定,我们发现:同其他概念界定方式相比,以能力为基础定义脆弱性概念的方法,既全面揭示出脆弱性的描述性特点,同时也具有规范效力,为研究伦理中的道德义务及其冲突提供了更有效的论证和解决方案。脆弱性原则的重要性源于患者或受试者在医学治疗和研究活动中所处的相对弱势地位,这种相对弱势地位令“知情同意”“自主选择”等规范要求在实践中时常陷入困境。因此,脆弱性原则在缓解既有伦理原则间的冲突、保障患者与受试者的权益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脆弱性概念在思想史上历来处于一种易被忽视的地位,但它在近来的生命伦理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脆弱性概念表达了人类普遍脆弱和相互依赖的生存状态,而它对这个生存事实的揭示同时也具有号召人们互助关爱的规范效力。作为一项生命伦理学原则,以能力为基础的脆弱性原则使人们承认并尊重自身的脆弱性状态,进而在生命伦理领域发挥着沟通联结各项伦理原则的基础性作用。当然,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脆弱性原则也许还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生命伦理学所面临的现实诉求,它仍要随着经济社会和医疗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加以修正和补充,而这也体现了伦理学所担负的“追求良好生活”的永恒使命。
[参考文献]
[1]陈慧珍.论生物医学研究伦理中的脆弱性概念[J].道德与文明,2015,(6):93-100.
[2]Michael H. Kottow. The Vulnerable and the Susceptible[J]. Bioethics,2003:460-471.
[3]杨丽然.国际生命伦理重要准则演变研究 基于NC及DOH和CIMS的多种文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35.
[4]Samia A.Hurst. Vulnerability in research and health care; describ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J]. Bioethics,2008,22(4):191-202.
[5]Wendy Rogers, Catriona Mackenzie and Susan Dodds. Why bioethics needs a concept of vulnerabi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2012,5(2):11-38.
[6]Henk ten Have. Vulnerability: Challenging Bioethics[M]. New York:Routledge,2016:163.
[7][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注释本)[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美]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M].刘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9][美]汤姆·比彻姆,詹姆士·邱卓思.生命医学伦理原则(第5版)[M].李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0]Jacob Dahl Rendtorff. Basic ethical principles in European bioethics and biolaw: autonomy, dignity, integrity and vulnerability--towards a foundation of bioethics and biolaw[J].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2002,5(3):235-244.
〔责任编辑:崔家善〕